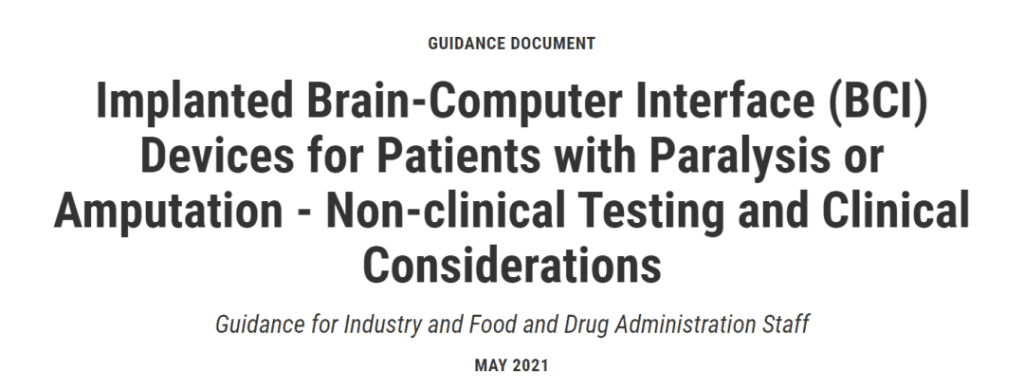在新脑论坛第一期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骁健,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二级教授吕宝粮,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裴为华,蓝驰创投投资副总裁别西,就“脑机接口,商业化难题何解?”展开精彩讨论。下文为本次论坛圆桌部分的整理文稿。
别西:最近这5-10年的脑机接口,不管是在商业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老师们认为脑机接口领域进展的驱动是什么?它是技术驱动,还是应用驱动?
李骁健:我认为应该是两方面同时存在。
如果从需求上来说,这是两者互相促进的效果。这就相当于拉车,有人在前面拉,有人在后面推,这是共同发力的结果。当然,从医疗器械等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强烈的市场需求在牵引,实际上也没有人想做脑机接口方面的投资。就好比我开始提到的DARPA的资助,这肯定不完全是为了追求科幻,满足技术方面的酷炫,它本身归属于美国国防部,是有明确需求的。
实际上,互联网技术早期,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有DARPA很多资助。后来技术逐渐成熟并且扩大化应用,才扩展到民用方面。这都是同一个逻辑。
其实对于脑机接口来说,也正是因为早期至少存在一些医疗需求,才能有现在的发展。最直接也最明显的,就是针对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病人。除此之外,还包括老龄化社会中不断增长的瘫痪病人。整体来说,需求应该是第一位。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有这个需求,就立马有产品了。就像刚才我提到早期的Blackrock那种脑机接口装置,那是有线的很庞大的一套设备。因为它需要在头上引出线路,这虽然是可用的,但对于需要普遍使用的场景来说,太傻太笨重,还有感染风险。这种从头皮上钻出来的金属罩,就算是平日研究者来使用,也不好用,更别说普及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微型化,甚至是无线化。
近些年,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微型化,甚至可以完全植入,再把头皮缝合,通过无线传输,这样就不会有明显的感染风险。
再比如刚才裴老师提到的各种植入电极,如果采的信号质量比较差,且不能长时间使用,也是比较大的麻烦。可能费了半天劲做植入手术,结果没用几天就废了,这肯定也不行。
最近,一方面是微纳加工技术及设备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材料方面的进步,已经可以做柔性的植入传感器,它能延长传感器的使用时间。也就是说,这些硬件技术,甚至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算力的提升,都对脑信息的快速分析和解码有很大的推动。这都是由重要的技术支持而形成的解决方案。所以说,这些软硬件技术确实提供了推动力。
对脑机接口这辆车来说,需求有方向的牵引,而后的软硬件技术则产生了推动。牵引和推动共同促进脑机接口技术,向着实际的应用落地。这是我的想法。
别西:在讲座中李老师和裴老师都对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做了比较多的分享,而吕老师更多关注的是非侵入式。在商业应用方面,非侵入式走得要更快一些。所以想请吕老师也谈一谈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年脑机接口的进展是由什么驱动的?技术驱动、应用驱动、还是两者都有,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吕宝粮:我认为刚才李老师说得很对,应用和技术两方面都有。
随着我们国家的老龄化,老年人的脑血管疾病、精神疾病等问题也变得严峻起来。而传统的技术却遇到了瓶颈。比如在脑深部电刺激(DBS)这一领域,我们国家做得非常好。譬如昨天我刚好在瑞金医院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内部会议,在神经调控方面他们做得相当出色。不像二十几年前,核磁共振设备基本都是国外的。在DBS这方面,我们国家就有两家不错的公司——景昱和品驰。
只不过在美国,如果你得了帕金森病,医疗保险是可以覆盖做DBS的费用。但相对来说,我们国家帕金森病患者大概有几百万,数量也很多,可因为公费医疗没有完全涵盖DBS的费用,有的患者很可能负担不起,这些人就没办法享受到先进的治疗技术。所以我认为需求和技术是动态变化的。
还有一点,方向也非常重要。举电动车的例子,我们国家看的方向比较准,而有些国家可能就没有看准这个方向,因此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可能你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个层面,但是否选择投入资源,在几年之内,就会形成比较大的差距。
我个人认为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它的器件和设备还是有点贵,用起来也存在信号质量不好等问题。但要是等到问题全部解决了再研究和开发,可能也不行。像现在这样几个渠道同时做,随着硬件、算法以及范式的改进,一些应用的落地可能会更快。
我不知道企业里是怎样的,但高校还是受一些政策的影响比较大。相当多的人是在做一些容易发文章的东西,也不太讲求效益,创新性可能也不是特别高。
总结一句话就是:硬件、软件、算法和范式相关的创新,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做应用的阶段。我20年前从日本到交大的时候,当时要买64导Neuroscan设备需要120多万,是非常大的一笔开支。但现在,我们国内高校要想买这样的设备已经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了,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可以参与的阶段了。

SR1101可充电植入式脑深部电刺激套件
景昱医疗
别西:谢谢吕老师的分享。我们作为投资公司,可能更关注商业化落地的方向和应用,并且我自己是神经生物学背景,所以跟国内做这块的公司和老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接触,也有同感。可能大家以发文章为主要驱动,就会忽视许多真正重要的问题。不知道是导向的问题,还是说大家的兴趣偏好,甚至可能是能力问题,导致有很多低水平的重复,这么说有点太严重,但确实有很多真正重要且难度更大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沿着刚才吕老师提到的国内外的比较,这个问题我想提给裴老师,因为刚才您的工作也比较了很多国内外的公司以及高校正在做的一些工作,您觉得我们现在脑机接口这一领域,从底层技术来看,跟国外有哪些差距?同时我们有没有一些差异化的优势?
裴为华:我报告里提到的电极有无创和有创两块,整体上来说咱们两块跟国外,尤其是跟美国比,可能都有一些差距。无创这方面,尽管国内也有无创采集放大器做得非常好的,但无创采集的硬件涉及多个关键配件,例如脑电帽。但你别看它只是个纺织产品,但在应用中,它其实需要很多技术的积累,比如说一个帽子戴上去以后,怎么样才能让每个电极都很好地跟头皮接触,这就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做好。所以在无创这方面,我认为我们的电极,放大器甚至有些帽子目前都做得很好,但整合成面向实际脑机接口应用的产品还需要积淀,再有就是放大器的核心芯片,还是国外提供的,这是硬件本身的底层技术。
所以,在硬件上,国内跟国外相比有一些差距,但更主要的差距是在应用方面,差距还要稍微更大一点。
再一个是基于无创脑电的算法或解码方法方面,我觉得以吕老师、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做无创脑机接口的团队,我们的有些技术还是走得挺靠前的。
而有创方面,我们本身起步比较晚,所以在植入电极这块,确实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他们的种类更丰富,器件的技术也更先进,其相关技术不止我报道里提到硅基的、PI基的等有限的几种,其探索的范围更广更深。虽然很多工作都是华人在那边去做的,但是美国的积累确实比较长,植入式电极,尤其是在用于人的方面,美国的发展确实要好一点。
有创电极的放大设备,特别是其核心放大芯片,它的近况可能比无创电极还要再滞后一点。因为它不像无创那样有很大的需求,所以国内的一些公司很早就开始开发无创电极接口的放大电路,但是有创这一块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实验室里。直到十几年前,才有一些国内的机构以国外的一款芯片为核心,搭建我们国内的有创采集系统和设备。
经过十来年的发展,目前国内的这些脑电采集设备也做得很不错了,但在面向用户的软件应用方面仍然较弱。比如说信号采集过来以后怎么怎么进行信号的分类以及信号处理,以满足采集人员分析信号的需求。这方面我们经验还是不足,和用户互动的时间也比较少。所以有创跟无创比起来发展得又慢又晚。而有创能够做的事情又更多,我们滞后的更多一点。比如说,美国已经做了几十例的病人了,具体的数据可能李老师更清楚,但是国内可能只有个位数。这是我大概的一个看法。
别西:因为脑机是一个特别复合的工程,有软件有硬件,还涉及到神经生物学,以及芯片电极算法,您觉得这些方面中,我们最有可能在哪方面产生突破?
裴为华:就像您说的,我也觉得脑机接口每一方面的进步,都离不开其他几个方面的支撑,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就我自己来说,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个方面的进步都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约。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电极、芯片、算法、系统、做动物实验的人才、以及使用平台和方式等等。
像是研究神经生理的人会给我们提一些需求,需要记录5个通道的信号,我们拿只有1个通道电极分别放5个地方,以前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现在国外出了Neuropixels,一下就能同时记录几百个通道。分别记录的效果且不说,通道数少的效率相比人家低了若干倍。再者信号记到以后,你还需要有能力来传输和处理。这又涉及到通讯速率、带宽、无线传输等技术,所以这里面涉及到许多技术,相互之间会有许多制约和限制,都需要一一去解决。
如果要说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有突破,我真看不出来。原先我们是想就买国外的设备,我们好好做后头的应用。但是国外把你前头一卡,你后头那些就是镜中月水,无源之水。没有了前头的这些采集,你后头信号处理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在某一方面的强可能不是真正的强,而且也强不起来。如果没有国外的设备芯片或者是其他团队的支撑,许多事情没法做起来。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没有芯片,做多通道的时候只好靠在工艺上去把线条做得更细,增加密度;或者通过堆叠增加数量,做出来的器件很大。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所以仍然需要各个不同专业的团队来配合,才能把整个技术链条做大做强。
别西:我们自己在观察医工结合领域的时候,感觉中国存在一些优势。可能时间积累的关系,在底层技术上有点落后;但在临床资源这一块,其实我们是有优势的。对于这方面,吕老师跟瑞金医院展开过很多合作,可能有更深层次的体会,您能展开我们有可能利用临床资源的哪些方面,比如抑郁症,能有一些弯道超车或者是做出突破性进展的机会吗?
吕宝粮:举个例子,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用DBS做难治性抑郁症,应该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最近,美国UCSF的Edward Chang团队在Nature Medicine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文章。实际上可以说,现在可以用侵入式脑机接口来做难治性抑郁症的治疗了。
我认为至少在情感障碍疾病这方面的脑机接口应用,我们必须自己做。比如说现在的DSM-5量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都是美国人弄的,但是里面的问卷内容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所以必须中国人自己做。
第二,我认为,我们外科医生的手术水平肯定是很厉害的,一天的手术量要比国外多很多,但是我们的瓶颈就是欠缺一点底层的东西,假以时日是可以追赶上的。同样是电动车的例子,你原来不会做电池,你搞几年,等出现那种有想法的人和公司,比如说宁德时代。当你把电池做好了,其他的那些控制算法就可以比较快地实现。所以还是要瞄准一个应用把它做实了,而不只是发些文章。这个领域是特别交叉的,但现在我们的学生的认知可能有些片面。有的同学觉得做脑机接口研究,可能会影响找工作。我觉得我们大学老师也有责任,因为你没有教育和引导好,学生就很难看准方向。所以说教育也非常重要。
确实像刚才裴老师所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说觉得很有希望我们才去做,而是现在这个形势已经逼着你无路可选了,只有华山一条路可走。所以,你必须做。不管是芯片也好,其他的也好,你都必须做。而且我觉得这是经过努力我们应该可以做好的领域。
李骁健:刚才吕老师说的很关键的一点是,其实无论是穿戴式或者植入式的脑机接口,国内这些年的学科建设是比较滞后的。包括裴老师前面提过,因为这是个学科大交叉,可以看到我们几个人都是做这个领域的,隶属于不同的单位,甚至在不同的院系里。这其实跟美国差的比较远,这样的话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从个人来说,我们的实验室对于自己所在的单位,甚至院系、院所都属于小众领域。包括吕老师讲了招生问题,因为我们跟别人做得不大一样,培养的学生会被认为不合群。刚才别总开始也提到,国内发展脑机接口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能力问题,一方面大家比较分散,没有形成重要的合力,另一方面人才培养也比较不足。当然国内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在临床资源上。
在美国前面20来年,一共做了大概有30来例植入式的,就只有这么几个积极临床志愿者。我开始介绍时,也提到通用解码器,它需要有足够的数据库。就需要有足够的临床数据,才能建立一个比较通用的数据库。
前面我也提到去年美国FDA出了植入式脑机接口的IDE指南,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有规范监管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东西。在临床上,美国目前是处于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的。而中国在这方面能够跟上的话,实际上能获取的临床资源会更丰富,起码在获得数据方面肯定是要比美国强得多。
话说回来,真正能将脑机接口做起来的,应该也只有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具有科技体量的国家。特别植入式脑机接口,其实欧洲根本就不怎么做,甚至连猴子的脑机接口,欧洲也是严格限制的。因此,欧洲其实已经被排除在竞争的队伍之外了。只有美国跟中国有体量、资源和认知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的优势就是持续的资助,它的积淀是非常深的。中国这方面在技术上虽然起步晚,但也有不少的团队在做,包括这些年有挺多的海归回来。所以也是能够把技术培养起来,只要多投入还是有机会的。
当然从整体上来说,客观上的社会资源还是主要集中在临床上,这方面中国确实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换句话说,我们能够通过数据的优势,更快地提升脑机接口技术的性能,以及在社会面,至少在医疗方面,将脑机接口的临床应用普及,这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别西:刚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底层技术的中外进展做一个比较,包括现状和未来发展。接下来回归主题,聚焦于商业化应用。我们都对吕老师跟米哈游的合作很感兴趣,譬如对脑机接口在游戏方面的应用前景。吕老师能展开给大家介绍一下您们和米哈游的合作情况吗,在未来有可能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吕宝粮:我简单地给大家分享一下。米哈游最近几年发展的很快,特别是原神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喜欢这款游戏,这也促使他们的队伍在迅速扩大。
我刚才在讲座里说过,零唯一思是去年12月和米哈游联合成立的,脑机接口这一块也是他们整个战略布局的一部分。今年我参与了尧德中老师任首席科学家的无创脑机接口国家脑计划项目,我所在的课题是由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易正辉主任担任课题负责人,研究主题是面向抑郁人群的无创脑机接口应用及验证,米哈游也参与了这个课题。未来把情感脑机接口与游戏结合起来,肯定很有意思。比如说开发头戴式设备,哪怕我们获取的脑电信号只能识别出这个人打游戏是不是很开心,就可以在上面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评估打游戏是否会上瘾,如果有可能上瘾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游戏交互的策略。整体来说是把用户的情绪状态和游戏本身实时地联系起来,而不是现在这种人和游戏分离的交互方式。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元宇宙等热门话题,情感脑机接口技术肯定是可以用上的。比如说未来具有6G的设备,使用那么大的宽带,肯定不只是为了传声音,它可以实现更加细腻的真人表情。现在我们就很幸福,微信电话就可以直接视频了,可能再过多少年,我们开会,裴老师、李老师和别总就像真实地面对面一样。这里边的情感智能非常重要,所以这些未来的底层技术都是要放在一起探讨的。目前我们的侧重点只是在抑郁症的客观评估与数字疗法方面。
别西:评估数字疗法,大家可能关心如何去做标志物,而我其实好奇如果说要去替代量表,或者说对量表所采集的信息作为补充,那在临床设计上,我们是需要跟量表做对比,还是说它只是辅助型的疗法,只需要做单独的临床就可以了。
吕宝粮:我可能刚才没介绍清楚。首先肯定是一步一步来的,现在医生的诊断是金标准。我们构建这个系统先是作为医生的辅助工具,但评估系统背后的很多算法是具有学习功能,因此评估系统的性能可以不断提高。当然,如果能发现生物标记物,这肯定不得了。但生物标记物可能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多模态的,也可能是一个和人相关的随时间变化的指标,因为你的大脑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现在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只是因为过去这些信息我们获取不到,也没法获得重要的特征。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觉得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需要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我确信一定会找到一个金标准,将来不需要依靠医生的经验和量表来判断。寻找生物标记物也将是一步一步发展的,无论怎样,至少它是可以逐步来实现的。所以可能一开始是辅助,但未来一定会形成一个诊断的金标准。
别西:我自己是觉得可能是要结合生物标记物,如果在临床上能找到一些数字标记物,那也是划时代的发现。
吕宝粮:因为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也在不断发展,这肯定是一个趋势,而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找到。
别西:脑机接口作为交叉领域,老师们会希望具有哪些背景的人才或学生加入呢?比如老师们是希望找一个学BME(生物医学工程)的,还是EE(电子工程)的,还是学神经的,或者说学CS(计算机)的,老师们觉得哪块缺,如果给大家做建议的话,可以选哪些?
裴为华:我们这边是需要EE和生物医学工程,甚至我觉得做材料和化学,特别是电化学的都可以。尤其是对神经工程和传感技术比较感兴趣的都欢迎。因为身体里电极的反应,说实话是一个电化学的过程。
吕宝粮:这个问题还是受到了学科的限制。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太火了,所以要进交大计算机系读硕士或博士,学生的排名要非常靠前。结果是我们这边进来的全是计算机专业的,我倒是希望有生物医学工程、自动控制、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不同专业的学生进实验室,但是我招不进来。
所以,这也是国内和美国的差距,我们给学生不必要的框框太多了,实际上根本不需要。
李骁健:前面两位老师说得都很好,因为学科大交叉,所以也应该尽早地进行学科交叉融合培养,这很关键。
从我的角度,尤其我做的虽然是植入,但是我是做全栈技术研发的。所以说刚才别总提的这几个专业我们都很需要,都很欢迎,甚至机械自动化这块也是非常需要,因为涉及到执行器部分,最后都在应用端,所以需要这些东西。
别西:我给大家一点不成熟的小建议,还是选自己最喜欢的,因为你喜欢你才能做得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对于脑机接口,我们做一个近5年的预期,老师们觉得脑机接口会如何发展?
李骁健:因为我在做植入式脑机接口的全栈技术和应用研发,这里面我们提到了应用场景三步走,主要根据技术成熟度来开展。因为毕竟它是医疗器械,要进入临床审批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三年方案,主要是为了更多地获取脑信号数据,对现有的医疗脑信号监测设备进行升级。另外便是把更多的数据用于通用解码器的建立。诊断方面可以用传统的电极,包括新研发的高通量的各种硬质的和柔性的电极都是可以的。
实际上5年的目标是变革性的,主要是做功能替代体。针对瘫痪的、失语的或失明患者,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全植入脑机接口帮助他们进行功能重建。因为这一阶段主要是依据神经科学研究基础来说的,感觉运动的脑功能图谱这块的理论建设是比较完善的。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在疗法上,我们是比较明确地知道要如何进行,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把解码器效果提升,就可以普遍地使用了。
我们在做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临床化,最先落地的场景就是在这些瘫痪、失语、失明患者,还有行动不便的病人上,给他提供功能替代或是功能康复的服务。这是我认为在后面5年能够完成的一个目标。再往后将针对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进行治疗,但因为这方面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还不是特别完善。所以,5年,还是做刚才我提到的感觉运动相关的功能替代和康复这方面的医疗服务。
吕宝粮:我们零唯一思,在5年内要完成情绪“X”光机的开发并获得三类医疗器械许可证。在这个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将会开发面向一般人群的抑郁症筛查系统。比如说9月份入学了,高中和大学都需要快速的抑郁症筛查和预警。还有家庭情绪指示器,类似家里的血压计一样,用于抑郁症患者服药效果的评估。目前没有客观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可以使用,基本是看完病之后,过两个月才能约上医生,才能得到相应的评判。所以希望能早日把家庭情绪指示器推向市场。
另外,今年启动的国家脑计划的研究期间也刚好是5年时间,我们承担的研究任务是情感交互的抑郁干预BCI系统及应用验证。正像前面介绍的那样,在完成医院级和家庭级的抑郁症客观评估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将会开发相应的数字疗法。这个数字疗法不仅仅是游戏,游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其它的一些情感脑机交互技术。我相信这些技术将会对情感障碍疾病的诊疗发挥重要的作用。
裴为华:我还是从有创和无创两个角度来说。我们这里谈的更多的是双向的,其实现在单向的挺多的,比如说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一些临床上的试用了,国内其实也有好多单位在跟踪这一块。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民用方面。在消费类市场里可能有一些保健类的产品。目前有很多已经在淘宝上出现了,但它的效果怎么样?不能肯定。比较严谨的一点,就是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特别是聚焦在经颅电刺激这些产品。据我所知,目前有一些公司是在做的,我相信5年左右可能会像吕老师那样,他们会申请进入临床或者是临床前期的研究,这是无创的。
有创的可能是针对一些需求更明确的疾病,像给予深脑部位或脊柱的这种刺激,针对残疾人或者针对疼痛等专用的疾病,因为这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例如DBS。所以在未来5年里可能在植入式刺激方面会有更多的公司加入,来应对更多的疾病的干预。
具体存在什么病是最适合脑机接口的,现在还不太明确,尤其是在干预这一块,比起记录型脑机接口来说,它的需求更明确。在5年里,这些公司以及市场应用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别西:希望三位老师的预测都能成真。总体来说咱们还是比较乐观,听上去可以做的事还是挺多的,在神经生物学整个领域临床未解决的需求,也是非常巨大的,这是所有从事者的一个共识。
主持人 :别西 | 嘉宾:李骁健、吕宝粮、裴为华
整理:海星、光影 | 校对: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