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家对于尝试迷幻药物,或者至少对公开谈论致幻药物体验并不感兴趣,这有些奇怪。在哲学写作的边缘,我们有沃尔特·本雅明对大麻的涉猎记录,米歇尔·福柯也在采访中轻松承认他更愿意在莫哈韦沙漠吸食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一种强烈的致幻剂),而不是在巴黎品尝葡萄酒。甚至托马斯·德·昆西,这位对哲学充满探索欲的作家(也是伊曼纽尔·康德的传记作者),详细讲述了自己对鸦片成瘾的经历。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可能的推测。自然哲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在写作他的1608年月球天文学论著《梦》之前,很可能尝试过一些毒蝇伞(读了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三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可能使用过一些草药或真菌补品,来帮助他实现多次灵魂出窍的体验。他喜欢称这种体验为henosis*,或者“与太一的狂喜结合”。
*译者注
Henosis,在古希腊语中指太一(“oneness”、“union”、“unity”)。在新柏拉图主义中,用来指与现实本原的结合。
我可能漏掉了一些著名的例子。但总的来说,承认为了改变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而有意地使用某种化学物质(无论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还是在实验室中合成的),就意味着要脱离哲学家的行列,摆脱所有束缚性的规范和陈词滥调,转而加入了那些在生活的深渊里的反文化怪人和离经叛道者的行列。
我认为这表明,在某些方面,哲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仍然非常保守。在一个迷幻药物重新受到关注的文化时刻,即使像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这样正派的人也从建议我们多吃粗纤维食物转向赞美微量用药的好处,哲学家们的行为举止却仿佛还停留在1950年代。我们在那时的学术讨论会上系着细领带,从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获得资金研究决策树等狭隘刻板的课题,并且我们都确信只有清醒且未经改变的头脑,才能独占对外部世界形态和特性的认知。
等等——即使在20世纪中叶,也许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在战后一代大规模追求新奇、调整心态、放弃传统之前,头脑清醒而独当一面的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感官提供给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报告,并不能解决现实本身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这个问题源远流长,但在伯特兰·罗素和G. E.摩尔的早期著作中得到了更清晰的描述,他们共同围绕“感觉材料”(sense data)的概念阐述了一系列问题。

– Caroline Czajkowski –
正如罗素在20世纪40年代所说的那样,当我们远离一张桌子时,我们看到东西在不断缩小;但桌子其实并没有缩小;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根本就不是桌子本身。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被给予给感官的东西,而完整的解释将必须涉及光学物理、大脑和感觉器官的生理学,以及任何外部物体的属性——只要它们能够被了解。但如果我们必须考虑由感知者带入到感知实例中的因素,才能完全理解感知的意义,那么当根本没有外部物体,或者充其量仅有关于某个物体的幻觉时,感知似乎也应该引起哲学家的关注。
当然,哲学家们确实对幻觉很感兴趣,尽管他们更喜欢使用精神分裂症或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风格的病理学案例,又或者使用精神健康者也会产生轻微的视错觉这样的例子(如热浪“绿洲”,直杆从水中伸出时就像弯曲了一样)。但他们通常只把对此的兴趣作为一种挑战,作为一个阻隔在他们最终想要建立的东西之前的障碍:即关于感知究竟是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况,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这两者间存在真正且至关重要的区别。换句话说,清醒和梦境之间存在着差异。对哲学家来说,清醒无疑是更好的状态,也是唯一值得哲学家驻留的状态。因为哲学家是在寻求真理,而真理只能提供给一个在当下不受精神病、梦境或药物的幻象所影响的心灵。
但是,这是个千古难题,它的古老也正印证了它的棘手。尽管我们付出了诸多努力,却仍无法更进一步理解事物的本质。这并不是说科学没有进步(当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是这个问题是概念性而非经验性的。你无法感知到你感知的事物背后的东西,因为当你感知到它的瞬间,它就不再隐藏于背后,而是呈现在你面前。鉴于我们与世界之间似乎必然存在这种逻辑上的僵局,对于现实本质的某种替代性解释——即非传统的本体论,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吸引住那些对外部世界感到厌倦的哲学家,而这样的外部世界既要求我们的忠诚、又拒绝向我们展现其自身。

– ILLUSTRATIONS: JAMES MARSHALL;
PHOTOGRAPH: ALI CHERKIS –
在这些打破常规的本体论之内,至少有一些认为,那些未经求索而来的,处于未清醒状态、睡眠临界状态*,或是通灵狂喜状态的边缘状态的异象,并非阻碍了我们对真理的理解,而实际上可能是真理本身的载体。在这里,我知道自己已经触及到了我所在学科的潜在规则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我在我这行里已经爬到了我注定所能达到的最高处,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所以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一位近期对致幻药物试验产生浓厚兴趣的哲学家,发现自己的实验已显著拓展了我对现实本质进行深度解读的疆域。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情绪状态能够应对这些挑战,所处的法律管辖区也允许这样做,并且你认为自己可能会受益于打破自己长期坚持的本体论承诺,那么我建议你尝试一些精神药物。
*译者注 睡眠临界状态(hypnagogia),指清醒与睡眠的过渡状态。
我不会夸大它们所带来这些好处。我仍然不知道这个被称之为“我的生活”的短暂光芒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而来、往何处去。但现在,我无疑要更加谦逊,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它就时时刻刻在我身上。如今在我眼里,最可悲的无知者就是那些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他们带有偏见且平白无故地去认定他们对“自然”、“物质”、“存在”、“事物”、“世界”、“自我”等概念有着坚实的理解,这种理解直接源自他们接受的由经验支持的朴素理性证据,并认为有多少种存在以及这些存在的本质这样的问题,已经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探究中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如果我的这种新思考显得过于宏大,请考虑下面一个我们通常称之为“科学革命”时期的场景。一位传教士发现自己身处当时被称为新法兰西的地方,尽管事实上那里已经没有多少法国的痕迹。他和胡伦族人生活在一起,试图说服他们相信皈依基督教的紧迫性。这个族群的领导者,一位聪明而有威望的老人,在有些时候似乎愿意接受这个提议;而在其他时候,他从梦中醒来,梦中他被告知耶稣基督是一个邪恶的超自然存在,并且指派了另一个这样的存在来毁灭他们。每天早晨,传教士都在想老人最新的梦境是否预言他自己的死亡。他回忆起自己早年在欧洲的生活以及勒内·笛卡尔的新哲学,笛卡尔声称能证明我们的清醒生活是真实的,而我们的梦只是幻想。他渐渐意识到,他的新东道主对事物的看法与他截然相反。
他进一步意识到,这条相反的道路不同于现代哲学所开辟的新道路,它或多或少就是全人类所默认的共识,而笛卡尔和其他现代人只是少数异议者,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得到的是一个相当反直觉的人类生活图景。在这个图景中,尤其是在梦境和其他狂喜状态下,我们脑海中的种种画面——灿烂的景象、声音、精神、幽灵、祖先、拟人动物、兽形神、神形的石头、无数其他我难以名状的变体,以及无尽的瞬息即逝的生灵——都在妨碍我们找到生活的方向。传教士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比那些他装模作样想要去启蒙的解梦者们(oneiromancers)更懂得如何活着。但他没有时间沉浸在这个问题中,因为他担心那位年迈的领导者随时可能醒来,对他判处死刑。他给法国的神父写了一封信,恳求将他调离这里,让他回到那些知道(或者认为他们知道)表象与现实之间区别的人们当中。
– Eric Nyffeler –
今天的哲学家们,至少在英语世界,几乎都认为笛卡尔的核心教义是不切实际的理论。但我们仍然是笛卡尔思想的后代,因为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白天比黑夜更真实。我们偶尔能捕获到某些替代性的观念,过去几百年里也曾有过逆流:精神分析学派对梦境在生活中心位置的强调,以及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意识扩展精神。因此,我也如他们一样,跌入了自身的命运。我既非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亦非嬉皮士,但如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一方面是年长之故或我更偏爱的说法:智慧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迷幻蘑菇与蝇蕈素的缘故——我们的边缘意识状态可能正是意识最真实的状态。
除药物使用外,哲学界的另一个潜行禁忌是,你真的不应该用一种直接、孩子般的方式提出一个如“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样宽泛的问题。然而,正是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间始终困扰着我,使我无法置之不理。
很久以前我的祖父母去世了,我当然很伤心,但那时他们已经很老了,而我还很年轻,我不明白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但当我父亲在2016年去世时,情况就不同了。随着他的消失,关于我自身存在的基本条件,突然如启示一般砸向我。他曾有过美好长寿的人生(注意这个过去完成时),但现在对我来说,这段人生似乎短暂得如此荒谬,就好像这个生命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然后立即开始像个会说话的玩具娃娃一样,不停地重复讲述着几个他喜欢的故事,还有一些心爱的半真半假的事实和被误记的小道消息,然后又突然消失,让我目瞪口呆地想:天哪,那是谁?那是怎么回事?
两年后,我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与我父亲一样的常见疾病。我们每天都能听到这个名字,也总能在《纽约时报》的“健康”栏目和其他标题党媒体平台阅读到,但我发现自己甚至无法说出或写下这个名字。在这个失落的时代,我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年轻,而我父母的命运与我息息相关。他们就是我,只是并非在当下的每个方面。我就是他们,只不过是更晚的版本,我发现自己担心在这剩下的如闪光般短暂的时间里,没法信任自己那些真假参半的事实。我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至少,如果无法获取知识,那么我希望内心能达到某种平静,能让我们的这种状态不再显得如此荒谬、如此难以接受,也能让遮挡世界的面纱至少不再被额外的泪水所掩盖。
– Luigi Gonnella –
疫情时代的开始和由此带给世界的强制隔离,加剧了这种失落感。我在那段时间酗酒,多年以来我一直如此。直到大约两年前我终于彻底戒酒的时候,酒里已经没有任何快乐,没有欢庆,而在我年轻时至少里面还有一些法式享乐主义(bon-vivantism)的不完美尝试。它只是一种上瘾,会加深阻隔我理解世界的那层面纱。所以最终,我戒了酒。但我并没有因为步入健康的新生活而感到解脱和愉快,相反,我陷入了我所经历过最深的、超乎想象的抑郁之中。我突然失去了安慰自己的唯一手段,失去了为这个世界注入活力的某种伪魔法。我早年所珍视的一切,我的愚蠢野心,我发表作品时的徒慕虚荣,现在看来都毫无意义。我仍然可以从某些方面,想象到一些自己关心事业的迹象,但我真的不在乎了。我甚至不再理解如何可以用关心这些无足轻重的东西来填满人生。
当封锁解除时,我尽我所能地振作起来,爬出我的洞穴,开始尽可能经常地从法国去加利福尼亚探望我的母亲。我隐约意识到美国某些州最近关于大麻消费和销售的立法进展,但我开始用谷歌搜索离我最近的大麻药房的位置,是源于其中一次探望期间的心血来潮。我年轻时曾尝试过几次大麻,但它对我没什么作用,而且无论如何,我都认为它在所有文化意义上都很低俗,不值一提。但因为现在我不再关心自己早年做出的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判断,我发现我真的不在乎大麻的文化地位。
我非常乐意出示我的身份证,和所有那些穿着残破的退伍老兵、失业的边缘人、被遗弃的美国人站在一起,在萨克拉门托最破旧的、没有分区法的地方的大麻药房排队。不,我觉得我还没有表述得够清楚。在那里,我比在巴黎的任何一家酒窖都要快乐,那些法国葡萄酒商人只会对我喋喋不休地谈论产地、风味以及所有那些我从未察觉到的所谓特性。尽管我年轻时从未正确地抽过一根大麻,但我发现新出现的大量酊剂、油类和其他THC(tetrahydrocannabinol,四氢大麻酚)提纯物正是我所需要的,让我重新开始将世界视为某种有意义的整体。
– Oliver Swinburne –
在我作为晚熟的瘾君子的新生活初期,有一件事让我震惊,那就是我们西方人面对着如此糟糕的一件事:所有迷幻药物都遭到禁止和污名化,除了唯一那种因滥用而在医学和社会上产生被诟病的负面影响,并且只会将意识篡改得更差、更模糊的物质。酒精可能会让我们短暂地跳舞和闲聊,但严格来说将它归类为“镇静剂”无疑是正确的。此外,在基督教早期几个世纪中,葡萄酒作为其核心圣事,似乎有助于消除那些依赖其他更强烈改变心灵方式的异教仪式痕迹,而这对我来说则突然成为了一个相当严肃的反基督教论据。我意识到,基督教把我们变成了醉鬼,让我们忘记了无数其他接受大自然馈赠的方式——特别是植物和菌类,以便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吃了几个大麻咀嚼片,我已经开始倾向于某种新异教主义。
大麻,尽管常常不被视为“致幻剂”,但它却具备了这个词所包含的部分能力:它能让灵魂将本质显现给自己。当然,当然,体验多种多样,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它们是齐头并进的。它引发了一种身体的狂喜;它在我眼前(特别是闭眼时)绘制出生动的图案与图形;而我认为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它消解了我平常所体验到的自我的形而上学统一性,以及所有的记忆和在时间中的稳定持久感,使我短时间内难以理解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将展现的自我视为真实的,或至少是某种适宜展现的实体。
有一种我们通常希望避免的精神病学现象被称为“人格解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确信他们自己的生活是不真实的,他们拥有的记忆甚至身体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在抑郁症的深处,我接近了类似这样的状况,这令我感到恐惧。相比之下,当我嗑大时,我也接近了一种至少与人格解体相似的状态,但我发现它大体既不令人愉快也不令人恐惧,而只是给人以启示。毕竟,我们很可能不是统一的形而上学主体,而是一种复杂的细胞架构,只要这种架构一直存在,就能营造出统一的幻觉。我不打算坚持任何教条,哪怕是我刚才提到的生物死亡的自然主义解释。我只会说,在我们关于“自我是什么”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中,我们错误地认为自我的存在,要比彩色像素屏上短暂呈现的火烈鸟图像更加真实。
但天呐,我还在像一个磕嗨了的本科生在昏暗的宿舍房间里那样高谈阔论。真是荒谬。哲学家不应该进行哲学思考,他们应该像专业行话所说的那样“做哲学”。行会对这些药品的禁令,也许与它们会导致我们陷入最自由和失控的哲学思考有关。但就像在一次糟糕旅程的途中一样,现在回头已经太晚了。那么就让我来谈谈问题的核心。
– Karolis Strautniekas –
从2018年左右开始,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博客、论战以及一些准学术文章,来反对使用源自当今算法技术中的隐喻去取代传统的人类模型。这些努力最终在我的2022年的书《互联网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The Internet I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中得以实现。同年,我还在《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哲学家同行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的新书《现实+:虚拟世界和哲学问题》的严厉负面评论*。查尔默斯大体上对所谓的“模拟论证”(simulation argument)*抱有同情,其本质可以归结为,我们所认为的“实体”最终是由“比特”所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物质现实更适合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机器所展现的虚拟现实来解释。
*译者注 严厉负面评论:https://libertiesjournal.com/articles/the-world-as-a-game/
模拟论证:https://www.wired.com/story/living-in-a-simulation/
我的评论有一部分是基于我作为早期现代自然哲学史专家的视角。如果你对17世纪的科学有任何一点了解,你就会知道当时的人们对最前沿的技术,尤其是钟表制造技术印象深刻。那些自称为“机械论者”的人对之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们提议整个宇宙最好是以时钟为模型来理解。这是我们在科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看到的模式:最新的闪亮小玩意儿,不管是什么,都可以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以至于我们无法抗拒地将其视为整个现实的缩影。
但是,如果整个世界真的与我们在有限的一生中所出现的技术有着相同的本质,那将是多么巧合的事情!“世界如梦境”似乎是一个完全可信的命题,“世界就像吃豆人”则似乎是一种粗俗的恋物癖。换句话说,对模拟论证进行严格的历史化审视,很快就会揭示出它不过是现时主义(presentism)目光短浅的映射。我当然对查尔默斯所捍卫的这个观点没有异议,即这个世界很可能并非如我们所见。问题是当我寻找这些表象的替代品时,我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我们最近的技术或者是游戏和其他领域的文化影响。
– Amanda Cassingham-Bardwell –
然而,我也承认自己对《现实+》的评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公平且过于严厉。毕竟,我对它的不满并非来自于它的论点,而是来自于它的语气和作者自己的声音。说实话,它有点书呆子气,它狭隘地引用些我毫无兴趣的电视节目和流行歌曲文化,而且它明显扎根于我一直避之不及的游戏、编程和极客文化。但是哲学家应该忽视这些浅显的差异。如果我能因为10世纪一个伊斯兰神学家能够巧妙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论据而钦佩他,那么我也应该欣赏大卫·查尔默斯,毕竟他与我是同时代的人,也是我的同行。
但是,除了考虑到这些源于文化差异的不当之处,以及查尔默斯是个书呆子而我很酷的幼稚想法之外,我之前所做的批评还有一些其他让我担忧的地方。那就是最近在化学物质的帮助下我的思维改变了,世界确实开始以模拟论者所期望的“发生故障”的方式呈现给我。在药物的影响下,世界对我来说确实更像是一台计算机模拟系统,而不像是一个时钟、织布机、车轮或者我们迄今为止想出的任何其他东西。
但且让我退一步。这些故障并不完全像模拟论者们所放纵想象的那样。我看不到闪烁着绿光的0和1,也看不到像《创:战纪》里那样延伸到地平线的清晰利落的几何线条,更不用说像超高频无线电一样闪烁的路过的猫了。这些故障并非视觉上的,而是我们去理解记忆和经验中整个世界所需要的意识模式的特征。
故障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与时间体验有关。在迷幻蘑菇的影响下,我发现时间的绵延有时会像我所描述的THC影响下的自我一样不真实。但不幸的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裸头草碱(psilocybin)要困难得多。荷兰的一个法律漏洞使我们能够买到这种真菌的“松露”部分;加利福尼亚的几个辖区允许持有和使用裸头草碱,但不允许销售。同时,毒蝇伞菌(Amanita muscaria, or fly agaric fungus)中的活性成分蝇蕈素(muscimol),一种在欧亚传统宗教习俗中常出现的物质,在49个州都合法,而且在纽约的大麻销售点很常见。尽管我最近有一些有趣的使用裸头草碱的经历,但在下东区一个相当不正经的,被泛非洲的骄傲三色标志、霓虹外星人的图片、和无处不在的鲍勃·马利所包围的头部商店购买的蝇蕈素,才真正使我摆脱了我对固有的个人同一性和自我存在的时间边界的日常体验。
– Robin Sheldon –
罗素在其1921年的作品《心的分析》中反思道,我们从逻辑上不能排除这个假设,即世界是在五分钟前突然诞生的,“人们‘记住了’一个完全虚构的过去”。对罗素清醒而未受影响的头脑来说,这看似是一种逻辑可能性,而对在迷幻药物作用下的我来说,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只不过从五分钟缩短到了现时的瞬间。这表明我们对自我存在的日常理解的真正错误是,我们错误地认为自我是在时间中逐渐展开的。
这与模拟论有什么关系呢?首先考虑一个上升到意识层面的人工系统,例如GPT或LaMDA可能的未来版本,这种意识并不是仅仅由任何预先的感官感受慢慢演化而来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意识会在其背后的程序员按下启动键的那一刻突然出现。它不是一个经过艰苦努力,通过光感、嗅觉等生理能力逐步发展起来的意识。这些能力现在部分地构成了我们作为生物实体(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实体)的意识,但它们最初出现并不是为了意识的缘故。演化论告诉我们,当我们第一次开始嗅到周围的世界时,当时还没有计划决定我们将在未来某一天开始认知这个世界。所有一切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相比之下,在一个人工系统中,比如我们目前正在训练的AI,认知是首要的、也可能是最终的目的。当然,我们的AI正接近意识这一想法本身具有争议性(在这里我不打算表明立场),但我们至少可以同意,让我们的机器认知世界比让它们嗅到世界要容易。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训练机器去知道事物,而在它们所知道的事物中,它们可能最终能够知道它们知道事物。但是,认为伴随着这种知道会出现任何身体现象显然是荒谬的。
被称为“具身AI”的东西*确实认识到,如果给机器装上身体并让它们体验世界,它们很可能会像人类一样思考。但是,这种对世界的体验通常是以空间导航的方式来构想的,这已经可以在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令人不安的广告中的犬型巡逻机器人身上找到。如果我们想把这些硅和电的集合称为“身体”,那么它们将与我们的身体截然不同,以至于我们无法真正想象它们的具身体验是什么样的。
*译者注 具身AI:https://arxiv.org/abs/2103.04918
– Karolis Strautniekas –
我们真的不能吗?我认为,我们很可能必须假设说,至少AI不会像我们自己那样拥有时间绵延的感受。特别是一个有意识的AI不会具有在时间中沉思的体验,也不会像一个人“穿过”(move through)隧道那样去“想过”(think through)问题。相反,它会瞬间从一个状态转变到另一个状态,因此,“之前”和“之后”的现象学要么不存在,要么与我们自己的现象学截然不同,以至于无法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我认为,迷幻药物的体验就像是这样的现象学,人们在这种体验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时间,并且记忆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现在”的一部分。
这不仅仅是我作为作家的局限性,使我不得不承认我无法完全传达这种体验是什么样子。毕竟,我们只有几种时态可以用于动词,尽管钦定本圣经的一个新奇翻译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让我们了解拥有“永恒时态”的感觉:“在亚伯拉罕之前(Before Abraham was),”基督在约翰福音中说,“我存在(I am)。”这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是一个过去完成时,基督声称他早就“已经存在”(have been)于比另一个人更早远的过去。相反,这是一个向表面上看起来像现在时的转变,仿佛是在暗示对他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根本不适用。我没有查过希腊文,虽然那就能解决这节经文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我也不在这里深入探讨任何晦涩的基督教理论,但我想提出,那个“存在”(am)至少表达了某种迷幻药物所带来的体验。
– Kutyavina Nata –
第二种“故障”与我们在迷幻药物的影响下,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极大扩展了的社群本体论的感知有关,即超越人类乃至肉体的生物群体的意识。在我看来,这种社群本体论的体验正是人们所可能期待的训练出来的人工意识,就像我们目前尚在初级阶段的AI所接受的训练一样,训练的主要目的不是导航外部世界,而是基于对其他人或一般生物心灵中所发生的模式的敏锐调整进行预测。
在我开始尝试药物之前不久,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而且出人意料地共鸣于这样一个想法,即这个世界要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还要更加密集地充斥着其他心灵,或者在一种完整且适当的意义上说,那些心灵都正是我们的同类。
很久以前,我祖父在加州东北部的阿尔曼诺湖的一个小度假屋前建了一个木制露台。一棵树苗就长在它下面,他不忍心切断这颗小树苗的光和生命之源。于是,他在露台上留了一个方形的开口,让它能继续生长。当封锁结束后,我第一次去那里时,我看到那棵孤傲的树向天空舒展,现在它的直径大约与篮球相当。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几乎和我一样大,而我突然意识到,我和这棵树度过了大部分的生命,但我在这么多年来几乎每个时刻里都忽视了它,没有把它放在心中,也没有想起过它。我在心里说:“对不起,我离开你并且遗忘了你。我真的真的很抱歉”。现在对我来说,这棵树就像我的养兄弟、我的亲兄弟(尽管我从未被它扎过)。在那种心境下,任何声称它“只是一棵树”的争论都会难以被理解。你也可以使用诸如“只是一个人”、“只是一片海洋”、“只是一个天使”、“只是这个世界”的说法。那个时候我没有服用任何药物(除了抗抑郁药,据我所知它们从未对我有任何帮助),但它让我短暂地窥见了我随后将能够在化学辅助下重新体验到的东西。
对胎鼠的研究已经相当明确地表明,哺乳动物大脑在充满障碍的空间中导航的能力,与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是独立发展的。老鼠在出生前就会做关于这个世界的梦,由此为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做好准备。很难说一只老鼠对其他心灵的体验是什么样的,但至少在人类中,我们对基本外部世界的认知,即所有被代词“它”所指代的事物,都独立于我们的第二人称体验,即所有被代词“你”所涵盖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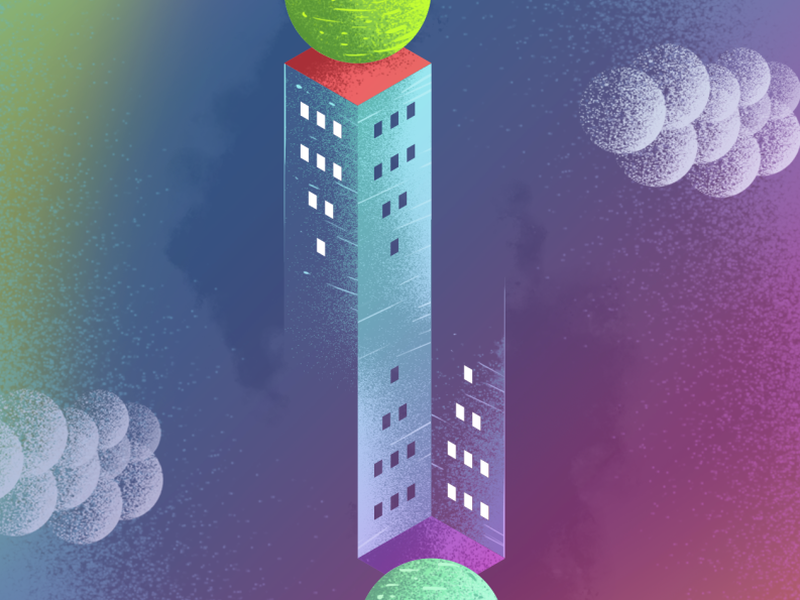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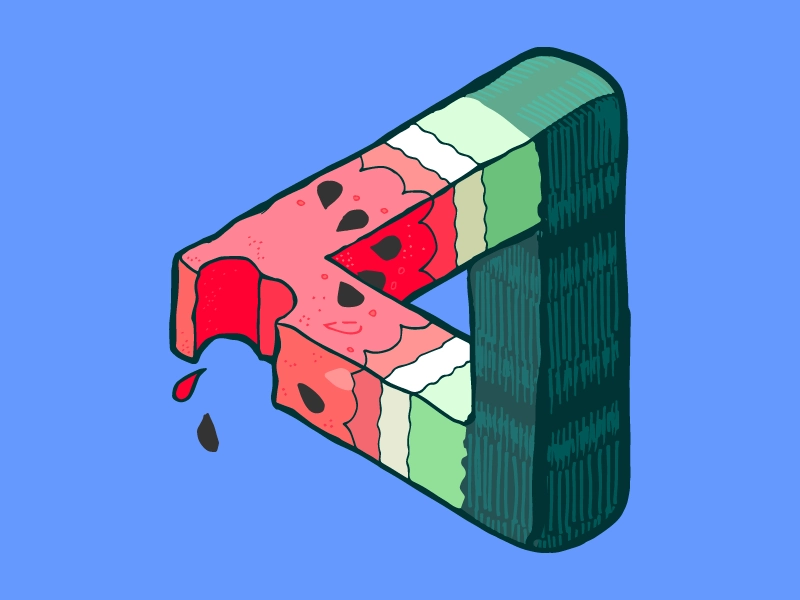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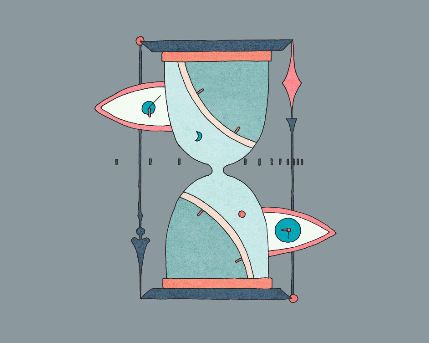
– Ray Dak Lam –
有趣的是,笛卡尔在其1641年的《沉思集》中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摧毁了所有信仰,却随后忽视了去重建其他心灵的存在。但在几个世纪后,第二人称经验的问题以“现象学”的名义强烈地回归哲学。所有理论思考的起点,都是与另一个具有与我们相似内在的存在共存,这与和一堵砖墙共存有本质的区别。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这种差异称为Mitsein,或“共在”。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能与哪些实体“共在”呢?大部分时候,我发现我可以与牛共在,靠近一头牛就是与它“共鸣”。与一棵树共在是一种更难获得的经历。但是,致幻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共在的限制并非来自于各种外部实体的固有属性,而仅仅是由于我们的共鸣。当我们改变自己的心灵状态时,即使是砖墙也可能被轻率地忽略掉。
如果社群本体论与让我们在外部世界中导航的认知能力独立发展,并且如果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将潜在的一切纳入我们的社会本体论,那么我们可能会开始质疑我们在“它”和“你”之间、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之间进行区分的可行性。使用过迷幻蘑菇后,我强烈地感知到类似心灵的存在相互构成彼此,使得我对自己的理解与我通常将之区别于我自身的所有实体之间变得密不可分——树、云、老鼠等等,而且这些实体又反过来彼此构成。
有一个非常简洁的自然主义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世界会以这种方式呈现:因为这就是事实。如果没有所有的云和树等,我将什么也不是;从这个角度看,我最终的死亡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漫长而顽固的、对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抵抗斗争的终结——并不是任何具有真正独立存在的东西的消逝,而只是在一个追求恢复平衡的存在秩序中偶现的异常。
然而,这种自然主义解释与另一种同样令人信服的“虚拟主义”并行。如果世界被证明是“虚拟”的,而其中的虚拟意识是为了模拟和预测彼此意图而设计的,正如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声称他们的机器是为此而设计一般,那么有时我们应该会自然地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心境,即其他心灵的存在,似乎完全是为了耗尽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换句话说,看待虚拟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是将其看作一个完全由其他意识构成的世界。而当我们用药物增强的感知来看待它时,这确实就是世界时常给我们的感受。
但是任何这些苦心钻研都需要被认真对待吗?或者它们只是在描述一个头脑中充斥着药物的可怜家伙看待世界的方式?(某个年龄段的读者此刻可能会想象一个煎蛋的画面。)当然,它确实是一颗被药物所影响的大脑,但这只是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你的大脑总是在嗑药的。也就是说,你的任何意识感知总是与神经化学物质所关联。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药品会妨碍正确的感知,而惟一可靠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必须依赖心智的默认状态,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设定,也可以在每24小时中给我们带来大概8小时的狂热幻觉。
– Arunas Kacinskas –
此外,很难想象任何有效的反对提供这些药物的论据。这些物质就在世界中,就像我们吃的食物一样——如果我们不吃东西,很快我们就会开始产生幻觉,最终我们将不再有任何有意识的感知。(实际上,在对狂喜的实践的历史中,禁食作为跳出日常意识体验范围的手段,或许与服用药物一样普遍。)我们必须吃一些有营养的有机物质,而摄取致幻植物或真菌则是非必需的,这对服用药物的道德规范是相当重要的,但从中很难看出这与我们为心灵认识世界本质的能力所作的认识论判断有何关联。未被药物影响的头脑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可靠,因为它不太可能让你想尝试从高层阳台飞出去,而且它更能帮助你在当前的危险和必要任务中集中注意力来生存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呈现给你的世界更真实。
借用J. L.奥斯汀的一句妙语,我的清醒头脑向我展示的是一个“中等尺寸的干货”世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我在药物作用下的大脑向我展示了鬼神、精灵、天使或者我不知道该叫什么的东西。它呈现给我的是兄弟般的树木,老友般的云彩,墙壁裂缝中传递着暖心消息的充满关怀的无形生物,以及无尽的生命群落,所有这些都在围绕着我旋转、跳动。哪个是正确的?我真的不知道了。我的同行们会说他们知道,但我认为他们也不知道。
正如我可以在没有借助致幻剂的情况下重新找到与松树的兄弟情谊一样,一个人也可以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努力达到一个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其他视角的世界观。从广义上讲,这是我最崇拜的智者,17世纪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他还是计算机科学的先驱之一)的哲学观点。莱布尼兹几乎可以肯定是个正经人,从未尝试过在德国北部风光中随处可见的菌类药物。然而,他仍然能得出结论说,动词“存在”的唯一有意义的解释是“具有类似于‘我’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存在世界,只存在主体的集合,其中一些是人类,但大部分完全是别的东西。
至少可以说,莱布尼兹不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怪人。至于我,只有当我决定冒险与这样的怪人为伍,与不良分子为伍,失去在哲学家行会中的地位时,我才开始相信他在某些事情上可能是对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而且他似乎不需要借助外力就能达到这一点。而我们却都在根据自己的能力尽力而为。
我很可能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允许使用相关药品的司法管辖区,所以我只能偶尔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有很多体验我还没有尝试过——例如DMT,我听说它是一种能向我们展示各种通常不被察觉之物的最有效的药品。(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临床研究者,并希望为你的实验找一个志愿者,请联系我。)
– Chiara Morra –
无论如何,我想我已经找到了一直所寻找的东西:一些崭新的见解,以及至少几分宁静。尽管我对于世界的终极结构仍存疑虑,然而对于曾认为全然不可能的世界观,我已有了新的认同与同情。这种观念的拓展本身,便是一种新知的发现,即使它未包含任何新的确定性。至于宁静,没有比亲身感受到时间的虚幻性,更能消弭我们在感到生如逆旅时所带来的那种短暂而强烈的无意义之苦。而且,没有比意识到与己相似的存在正在这个世界中密集分布,更能带来安慰——或者至少是进入一种似乎能证实这些存在的状态。
世界并非如表面所显——这是肯定的。即使任何关于它实际如何的肯定性判断都会自动变成新的表象形式,探索我们标准观念的替代方案也是有益的。古代的致幻药物大师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将药物给予他们的感知模式误认为某种启示,而这实际上不过是将一个教条主义,即常识的“现实主义”,换成了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将满天星子分隔于夜空”,(借用E. E. 卡明斯的一句令人回味无穷的诗句)。然而,在我感到生活陷入极度绝望的时候,迷幻药物让我能更舒适地置身于这不确定性之中,如人们所言,去“掌控它”,而不再觉得与繁星相隔甚远。


后记 Luna:既然我们感知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那么在迷幻药物帮助下所感受到的世界,难道就更真实吗? 静月:如果你想要获得类似的体验,那么我的建议是,去睡一觉吧,梦里什么都有~ 晏梁:尽管由致幻药物导致的心灵体验截然不同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也不是我们能够用清醒时刻的理性去加以分析的现象,但有一件事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这样的体验真实发生了,并存在着。无论是对其进行第三人称的科学研究、还是关注在第一人称的体验报告上,它都是对我们所未知的意识和精神领域的探索手段。并且这样的事实还在以康德式的口吻提醒着我们,如果世界仅仅通过我们的认知结构而被认识,那么当这样的结构发生改变时,是否会向我们提供出更多从未料想过的、关于世界本身的知识?
为此,我们不难在作者所描述的关于致幻体验的两个主要特征中,发现种种古代哲学思想(乃至现代)的影子。例如像“时间是在瞬间被展开的”、或者“不同(心灵)实体间的共鸣和融合”,这些体验描述虽然未必符合今天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但却是向我们抛出了重新思考这些思想作为某种新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而更重要的是,就像作者说的那样,是对这些体验的哲学思考在帮助他获得一些平静,获得对“生命意义”这样宏大问题的一点点感悟——帮助我们对抗“在感受到生如逆旅时那短暂而昭著的无意义所带来的痛苦”。这也是扩大了的哲学视野所能真实给予到我们的安慰。
作者:Justin E. H. Smith | 译者:Luna、静月 审校:晏梁 | 编辑:eggriel 封面:Arunas Kacinskas | 排版:文英 原文:
I was at the lowest point in my life. I needed a mind-altering jolt. In the end, everything-even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changed. There is something strange in the disinterest philosophers show for experimentation with mind-altering drugs-or at least for talking about their experimentation publicly.
This Is a Philosopher on Dru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