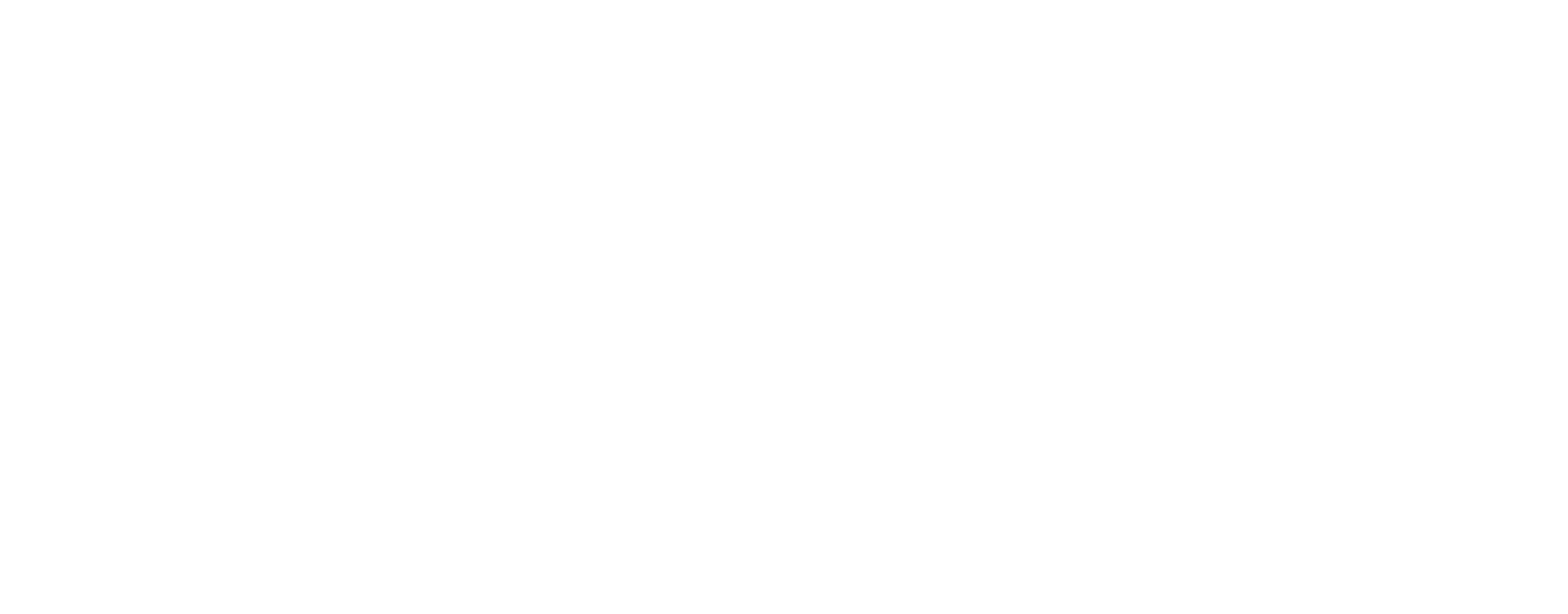想象你是一个旅行者,来到一片陌生的大陆。一个当地土著向你走过来,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对着你嘟嘟囔囔。他看起来很热心,并且指着远处的某个地方。然而,无论你多么努力,你仍然无法弄懂他在说什么。
这差不多就是幼儿第一次遇到语言时的情形了。事实上,她所面对的情形可能更艰难。一方面,她所处的环境充满了深奥难懂的术语,另一方面,与假想中的旅行者不同,她甚至无法意识到这些人是在尝试进行交流。然而,这个星球上每个认知正常的小孩,在四岁左右时,都会变为一个语言天才。这一切的发生,要早于他们正式上学,早于他们学会骑自行车,早于他们学会系自己的鞋带,也早于他们学会基本的加减法。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奇迹。而解释这个奇迹,可以说是50多年来语言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
The evidence is in: there is no language instinct – Vyvyan Evans | Aeon Essays
Imagine you’re a traveller in a strange land. A local approaches you and starts jabbering away in an unfamiliar language. He seems earnest, and is pointing off somewhere. But you can’t decipher the words,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That’s pretty much the position of a young child when she first encounters language.
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了一种观点,看上去是个不错的解释。他认为儿童事实上并不是在“学”他们的母语,或者说,至少不是在语法构建的层面“学”(整个过程实在是太快太轻松了)。他推断,儿童们一定是生来就有基本的语法知识——一种被写入DNA中的“普遍语法”。由于这种内嵌的因素,学会不同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不算什么难事,例如英语和法语。这样语言学习的过程就解释得通了,因为婴儿有一种语言的本能:一个在全世界所有语言中都能运行的语言工具包。
这样一个工具包一下子就消除了人在学习母语时的痛苦,并且也解释了儿童为什么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毫不费力地学会母语。这很机智。乔姆斯基的观点主宰了语言学界40年。然而,结果表明,它不过是一个谬见。过去几年来,出现了一连串的证据,证明乔姆斯基显然是错了。
–
–
不过,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吧。每个人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人类展现出一种明显的生物本能,它为语言做好了前提准备。我们的大脑在某些方面已经做好了“语言准备”:它有着合适类型的工作记忆,可以处理句子层面的语法;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前额皮质,赋予了我们联想学习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首先使用符号。其次,我们的身体也做好了“语言准备”:相对于古人类,我们的喉位置较低,让我们得以控制喉部的气流。并且,我们咽喉中的舌骨的位置也允许我们对嘴巴和舌头进行精细的肌肉控制,让我们能够发出各种不同的语音,在某些语言中甚至高达144种。没人可以否认,上述这些都是先天的,并且对于语言来说都很重要。
引起争议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关于语言本身的知识——语言软件——是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乔姆斯基的观点认为:正如我们生有不同的人类器官那样——心脏、大脑、肾脏、肝脏——我们的头脑中也生有语言,乔姆斯基将其比作一个“语言器官”。这个器官在婴儿期的早期出现。它包含了一个蓝本,描述了所有语言的语法规则所可能出现的形式。因此,学习任意一种自然生成的人类语言只不过是一场儿童游戏。出生于东京的小孩毫不费力地学会了日语,而出生于伦敦的小孩则毫不费力地学会了英语。尽管在表面上这些语言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在深层次上,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运行在一个通用的语法操作系统上。加拿大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将这种能力称之为我们的“语言本能”。
关于语言本能的存在有两个基本论据。第一个是“差老师问题”。乔姆斯基在1965年指出,儿童们学会他们的母语看起来并没有经过很多显性的教导。当他们说“爸爸,看那些羊们”,或者“妈妈,生气我”时,他们的父母并没有更正他们错误的语法,而是惊讶于他们是那么可爱。此外,这些表面上看很基本的错误掩盖了儿童在语法上的惊人成绩。不知何故,儿童们明白,有这样一类词语——名词——是有单复数的,但这种区别并不能用在其他词性的词语上。
这类知识并没有被显性地传授;大多数父母自己也没有显性的语法训练。并且,很难看出儿童们是如何能够仅仅通过听就能够掌握这些规则的:领会一门语言如何运作似乎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明白有些词是名词,它们可数,并且与其他词性的词是有区别的,例如动词。儿童们自然而然就理解了这些基本特性,无需代价。而这正是语言本能观点获得支持的地方。
儿童们并没有接受关于母语的正式指导,那么他们是怎样获得语法知识的呢?
乔姆斯基的第二个论据集中在儿童的能力上。考虑“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当儿童们获得语言能力的时候,用了哪些通用学习能力?当乔姆斯基系统化的阐述他的观点时,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关于学习的理论——例如美国心理学家B.F.斯金纳(B F Skinner)提出的行为主义学方法——看起来严重地不胜任研究语言所面临的挑战。

行为主义将所有的学习过程看做是一系列刺激-响应的强化过程,非常类似于巴普洛夫训练狗在听到铃声之后分泌唾液。但是,正如乔姆斯基在1959年对斯金纳的说法所作的一篇令人震惊的评述中指出的那样,儿童们并没有获得关于他们母语的正式指导,这一事实意味着行为主义无法解释他们如何获得语法能力。乔姆斯基总结道,儿童的语言学习过程一定是预先准备好的。如果他们并没有被明确的教导语法如何运作,并且他们天生的学习能力并不足以应付仅仅通过观察来学习语言的任务,那么根据排除法,他们的语法智慧只可能与生俱来。
从此,这些论据或多或少都让乔姆斯基的事业得以持续。他们看起来相当妥当,不是吗?然而,事实上,他们给基本观点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包袱。在过去的二十多年,语言本能学说一直在这幅重担下蹒跚行进。
–
–
让我们从一个相当基本的点开始。不管我们对于语言有着什么样的先天基础,把它称之为一种本能有什么意义吗?深思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本能是一种趋向某些特定行为的内在倾向。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必须无须训练即可产生。一只新手蜘蛛并不需要看一位导师才能“学会”结网:当蜘蛛准备好之后自然而然就会结网,无须指导。
然而语言不同。流行文化可能赞美人猿泰山和狼孩”毛格利这样的角色,身为人类,却成长于野兽之中,在成年之后最终还是掌握人类语言。但现在,我们有几个论据充分的关于所谓“野孩子”的例子,野孩子是指那些不管是意外还是人为因素而未能接触人类语言的儿童。这里有一个美国小女孩吉妮的悲惨故事。她从小就被她的父亲关在房间里,一直到1970年才被解救出来,那一年她13岁。从这些不幸的人们身上,我们所获得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没有暴露在正常的人类环境中,一个儿童根本无法学会人类语言。蜘蛛并不需要暴露在网中才能学会结网,但人类婴儿必须听到大量的语言之后才能学会说话。无论你怎么简化,语言也无法是蜘蛛结网那样的一种本能。
不过,这是随口一提。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关于全世界大约7000种语言的基本知识都是天生的,那么在某种层面上,这些语言应该是一样的。每一种语言之间必须存在一系列纯粹语法的共性。然而目前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共性。相反,我们发现的是语言的多样性。
口语在使用的语音上差异化非常之大,有的语言只有11个语音,而某些科伊桑语(一种使用倒吸气音作为辅音的非洲语言)却多达144种。语言在单词顺序上也很不相同,主语、谓语、宾语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在语言中都有。英语使用的模式相对还算通用:主谓宾,例如“狗咬人”。但其他语言就非常不一样了。在Jiwarli语(一种澳洲土著语言)中,“This woman kissed that bald window cleaner(这个女人亲吻了那个秃顶的窗户清洁工)”这句话就变成了这样一种顺序:That this bald kissed woman window cleaner.(那个这个秃顶的亲吻女人窗户清洁工)
有个拟声词叫“ribuy-tibuy”,来自北印度的蒙达语,用来形容一个胖子在走路时屁股的样子、动作和声音。
很多语言用词序来标明谁正在对谁做什么。而有些语言则根本不这样。它们通过将较小的单词组件拼接成更大的单词来形成“句子”。语言学家将这些较小的单词组件称之为词素。你可以常常使用词素来合成单词,比如英语单词“un-help-ful-ly”(无用地)。在加拿大东部所用的因纽特语中,单词 tawakiqutiqarpiit大致相当于:你有烟叶卖吗?当每个单词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的时候,词序就没那么重要了。
语言的基本成分,至少在我们说英语的人看来,口语的各个部分是由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组成的。然而很多语言并没有副词,而有些语言则没有形容词,例如老挝语(使用于老挝以及泰国的部分地区)。甚至还有说法称,海峡撒利希语(加拿大BC省及周边使用的一种土著语言)连名词和动词都没有。此外,有些语言所特有的语言范畴,在我们这些盎格鲁中心主义的观点看来实在是怪异。我最喜欢的就是拟声词,一种某些语言用来使叙事更丰富的语言范畴。拟声词是一种完整的词类,它将某个单一动作中出现的多种感官体验结合在一起。举个例子,有个拟声词叫“ribuy-tibuy”,来自北印度的蒙达语,用来形容一个胖子在走路时屁股的样子、动作和声音。
当然,语言并不一定需要说出来:世界上大概有130种被承认的符号语言,它们并没有语音,但运行的相当良好。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语言的意义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递:交谈、手势、打印字或者电脑屏幕等等。它的表达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媒介。多么奇怪啊!如果在所有人类语言中有一个通用元素,那么它必须隐藏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之下。
多年以来,随着这些不利于语言本能说的发现呈现在人们面前,语言本能说的游说者也逐步的精简关于大脑中存在通用组件的假设。在2002年的版本中,乔姆斯基和他哈佛的同事们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人类语言能力所独有的其实是一种通用的计算能力,我们称之为“递归”。
递归让我们能够将单词和语法单元重新排列,组成无限复杂的句子。举个例子,我可以通过递归地嵌入关系从句(以who 或which 开头的短语)来组成一个无穷无尽的句子: The shop(商店), which is on Petticoat lane(位于Petticoat街), which is near the Gherkin(靠近Gherkin大楼), which……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人类并不是唯一有能力理解递归的,欧椋鸟同样也可以。人类语法的这种“独特”的特性其实并不那么独特。而且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递归”到底是不是真正普遍存在于人类语言中。许多研究者提出,事实上递归在人类语法系统演化中出现得很晚,它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2005年,美国语言及人类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声称皮拉罕语——一种亚马孙雨林的土著语言——根本就没有用到递归。如果语法真的“内嵌”在我们大脑之中,那也太奇怪了。
–
–
关于语言共性就先说这些。也许语言本能说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它所作出的关于我们如何学习说话的预测。它试图对这样一个观察结果做出解释,即语言学习看起来相当快速自然。然而,问题在于,它让这个过程过于快速和自然了,远远超过了语言学习的实际过程。
当一个具有天生的普遍语法规则的儿童学习她的母语时,如果她认出了其中一条规则,那么这会引导她将这条规则运用到所有类似的情境下。以“猫”这个名词为例,当儿童听到父母提到猫时使用了定冠词“the”,这就提醒儿童定冠词可以用于所有名词。普遍语法预测到会有名词并可能需要一种方法来修饰名词,所以儿童期待着遇到这一类词性并寻觅着英语中用来修饰名词的方法,即冠词系统。仅仅有少数几次听到“the”后面紧跟名词就应该足够了,学习英语的儿童应该可以立即掌握这种规则并熟练的运用于所有名词。简而言之,我们期望看到儿童在语言学习上有跨越式的进步,每一次一条新的规则被激活,儿童在语法复杂性上就会进步一大截。
习得语言的速度或许快得惊人,然而那建立在痛苦的、不断试错的基础之上。
这是个惊人的预言。但很不幸,在发展语言心理学的发现面前,它站不住脚。正相反,儿童似乎以一种非常零散的方式习得语法。举个例子,以英语中冠词系统的用法为例,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将某个定冠词(比如说“the”)用在他们曾听到过这么用的那些名词上。只是后来,儿童逐渐扩展他们听到的内容,他们才逐步将冠词用在更多的名词上。
这个发现看起来适用于我们所有的语法范畴。如果存在一个天生的语法蓝图,那么语法“规则”的使用就会是毫无差别的阶跃式的进步,然而事实并非我们期望的那样。我们构建语言的过程似乎是通过在我们所遇到的语言行为中总结规律而来的,并非是应用内置的语法规则。随着时间的过去,儿童缓慢的认识到怎样使用他们所遇到的各种语言范畴。因此,尽管语言的习得可以惊人的迅速,但它并不是自发的过程:它建立在痛苦的、不断的试错的基础之上。
–
–
语言本能是什么样子?如果语言真的从一个语法基因中生成,这个基因在发育过程中设定了我们大脑中的某个特殊的器官,那么我们自然会认为,语言应该在我们的头脑中组成了某个特定的模块。大脑中应该存在某个特殊的区域专属于语言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推测,大脑的语言处理器应该是封装起来的,不受其他大脑功能的影响。
碰巧,最近这二十来年,认知神经学的研究已经渐渐揭示了语言在大脑的哪个区域被处理。四个字:每个区域。曾经,一个被命名为“布罗卡氏区”的区域被认为是大脑的语言中心。但现在我们认识到布罗卡氏区并不仅仅用于处理语言,它还参与到大量无关语言的行为之中。除此之外,大脑几乎所有地方也都参与了语言知识与处理。人类大脑在处理诸如视觉之类的不同信息时表现出了专门化,但在处理语言时,并没有显现出专门化。
但是,或许语言的独特性并不是来自大脑的某个区域,而是大脑的某种方式。假设存在某种类型的神经过程是为语言特设的,而不管这一过程发生在大脑的什么地方呢?相比于“物理”模块,这便是“功能化”模块的观点。证明这个观点的一种途径就是,找到那些语言能力正常但智力低下的例子,或者反之。这将提供一个被科学家称作“双重分离”的实例,即语言能力与非语言能力相互独立。
如果普遍语法是“内嵌”在人类的大脑中,那么它应该需要通过基因进行传递。
史蒂芬·平克在他的著作《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对大量的语言病症做了调查,以便找出一个例子来支持上文所说的“独立性”。例如,某些儿童患有特定语言障碍症(SLI),他们的智力整体上正常,但在语言方面却遇到很大的困难,比如无法完成一些特定的口语表达、无法正确运用某些语法规则之类。这看起来是个确凿的证据,或者说,它本来可以是。然而,很不幸,SLI 实际上是一种听觉处理系统的缺陷。这是一种运动缺陷所导致的结果,而并非语言方面。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每一个平克所宣称的证明语言“独立性”案例都被证明是错的:口语问题最终都被证明是由于语言能力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
上述论据显示,大脑中并不存在任何专用于语言的器官。另一证据链进一步指出: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东西。如果普遍语法“内嵌”在我们大脑的“微电路”中,那么它需要通过基因传递。但是最近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显示,人类的DNA 根本不具备这样做所需的编码能力。我们的基因组的信息容量高度受限。大量的基因编码被用来构件神经系统,并且优先于其他任何部分。要将假定的普遍语法的某些详细而具体的内容写入人类婴儿的大脑,将会耗尽庞大的信息资源,庞大到我们的DNA 根本无法提供。所以,语言本能说的基本前提——能够通过基因遗传——看上去并不成立。
–
–
关于普遍语法的假说,还有最后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是它关于人类进化过程的奇怪解释。如果语言是在基因层面“内嵌”的,那么不用说,它应该在我们演化谱系的某个点上显现出来。巧合的是,在乔姆斯基发展他的理论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其他与我们同属的物种中并不存在语言,例如尼安德特人。这也就缩小了语言可能出现的窗口期。同时,与之相关的其他复杂文化(复杂工具制造、首饰、洞穴壁画等)也是直到大约5万年前才出现,这似乎也进一步佐证了语言的出现很迟。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最早于10万年前出现,而且一定由基因突变引起。
仔细想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观点。首先,乔姆斯基声称语言由一次重大突变一蹴而就,这与目前广泛接受的现代达尔文合成论(不承认如此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跨越式进化)相悖。适应性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并且,乔姆斯基理论的一个怪异推论是:语言根本不可能为了沟通目的而逐步形成。毕竟,即使语法基因在某个不大可能存在的幸运儿身上突然出现,那么两个人同时出现相同突变的几率,实在是低到难以置信。所以,根据语言本能说的理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语言的人类想必没有同类可以交谈。
看来是某些地方出了错。事实上,我们现在相信,乔姆斯基关于进化的一些假设都是错的。最新的尼安德特人声道重建结果显示,尼安德特人很可能实际上有一些语言能力,而且还挺现代化。同时我们也逐渐清楚,尼安德特人也根本不是传说中不会说话的野兽,他们也有复杂精细的物质文化,包括制作洞穴雕刻与精制石器的能力,与5万年前人类文化爆发的方方面面并没有什么不同。很难想象,如果他们没有语言的话,他们要如何做到这些需要复杂学习与合作的事情。另外,最近的基因分析显示历史上人类与尼安德特人曾经发生大规模的杂交,所以大多数现代人类身上其实都有一些特殊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现在看来,早期智人与尼安德特人是可以混居并杂交的,而不是现代人类一登场就立刻消灭了倒霉的猿人。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们之间也存在交流。
这固然很好,但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到今天只有人类掌握语言这种最复杂的动物行为?一定有什么东西将我们同我们现存的近亲分割开。反语言本能说阵营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找出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一种合适的解释来自于我们所谓的“合作智力”,以及200万年前启动它的一些事件。
我们的世系——“人属”,可以追溯到250万年前。在那之前,我们最近的祖先直立行走的猿类,被称为南方古猿,他们的智商大概和黑猩猩差不多。但是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的生态位发生了变化。这些早期的“前人类”从吃水果为主(就像今天大多数类人猿一样)变成吃肉的了。新的饮食结构需要新的社会安排以及一种新的合作策略(单独捕获大型猎物非常困难)。这也导致新的合作思想更为普遍,社会分工从此出现,确保猎手们对猎物有平等的配额,并保证无法参与狩猎的妇女和儿童也能分到食物。
根据美国比较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观点,在大约30万年前,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出现时,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合作智力。这很容易从考古记录中看出来,这些考古记录证明了人类祖先拥有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相互交流。他们很可能会使用符号(预示着语言),并且能够进行递归思考(有些人说这是愈加复杂的符号语法慢慢出现带来的结果)。他们所面对的新的生态环境不可逆地改变着人类的行为。工具的使用、合作狩猎以及一些新的社会安排,比如说由于男性外出狩猎所导致的一夫一妻制的交配特权,这些都成为必需。
我们不必假设一种特殊的语言本能,我们只需着眼于那些造就我们的变化。
这些新的社会压力促成我们大脑的变化。最后,我们看到了语言能力的出现。语言终究是一种合作行为的典范:它需要习俗(群落中公认的规范)支持,而它也可以用来协调新生态位所要求的其他一切复杂行为。
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不必假设一种特殊的语言本能,我们只需着眼于那些造就我们的变化,那些为语言铺平了道路的变化。这让我们可以根据许多交叠的趋势画出语言形成的渐进过程。比如,它可能发端于复杂的手势系统,直到后来发展到以声音为表现形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语言之路上最深刻的促进因素一直就是我们合作的本能在不断发展。我不是说我们人类总是在合作。但是我们确实始终将其他人视为有思想的生物,他们和我们一样有思想、有感觉,并我们试着去影响他们。
我们可以在人类婴儿试图习得母语的过程中,看到这种合作的天性发挥作用。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比乔姆斯基所预见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很小的时候——可能9个月大的时候——就能够运用复杂的意图识别能力,来开始理解身边成年人交流的意图。从根本上讲,这是我们合作思想的产物。语言一旦形成,它使我们有能力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塑造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或者更糟。这么说并不是贬低语言。语言释放了人类发明和改造的惊人力量。但它并非毫无缘故的突然出现,也并非同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毫不相关。最后,21世纪了,是时候抛弃“普遍语法”的神话了,让我们开始实事求是地审视我们人类独特的这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