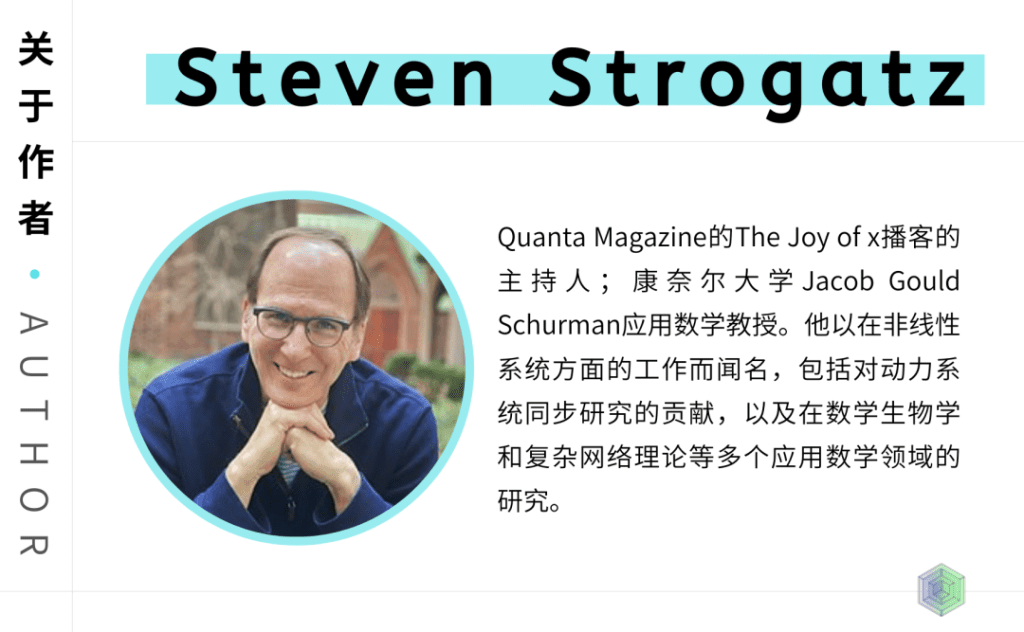梦境是主观的,但我们可以在人们做梦的时候窥探他们的心灵。史蒂文·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与研究睡眠的安东尼奥·扎德拉(Antonio Zadra)在这一期播客中讨论了新的实验方法如何改变了我们对梦境的理解。
梦境是非常个人化的、主观的和短暂的,我们似乎不能用科学客观的方法直接对其进行研究。但近几十年中,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已经发展出先进的、可以在人们做梦时深入其心灵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更多地了解到为何我们需要这种神奇的夜间活动,以及我们的大脑如何造梦。在这次对谈中,史蒂文·斯托加茨与蒙特利尔大学睡眠研究员安东尼奥·扎德拉[1]讨论了新的实验方法如何改变了我们对梦的理解。
斯托加茨:我是史蒂文·斯托加茨,欢迎来到Quanta Magazine的播客节目The Joy of Why,带领你探索当今数学和科学中最大的未解之谜。
在这一集中,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梦。梦究竟是什么?它们为何存在?为什么它们总是稀奇古怪?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梦到了一些奇幻的东西,梦中发生了一些有着叙事弧并从未真实发生过的疯狂故事,你和一些并不一定认识的人一起,置身于从未去过的地方。这只是大脑在试图理解随机的神经放电吗?还是说做梦的背后有演化方面的原因?
梦境就其本质而言很难被研究。尽管科学和技术一直在进步,我们仍然无法记录别人的梦境。另外,众所周知,我们醒来之后也很容易忘记梦的内容,除非我们非常小心地将它们记录下来。但即便有如此多困难,梦境研究人员仍在艰难行进,试图发现我们如何做梦以及为何做梦。
今天参与讨论的是安东尼奥·扎德拉博士[8],他是蒙特利尔大学的教授,也是睡眠医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其研究聚焦于噩梦、重复梦境和清醒梦。他还是最近出版的《当大脑做梦》(When Brains Dream)[9]的作者之一,这本书探索梦境的科学与奥秘。托尼,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扎德拉:感谢邀请。
斯托加茨:我很期待与你讨论梦境相关的东西。让我们从你和你的同事现在如何看待梦的科学开始吧。为什么梦如此难以研究?
扎德拉:研究梦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不能直接对其进行研究。我们研究的是关于梦的报告,这些报告可能是人们讲述梦到了什么,或者是他们就此写下了什么。因此,关于梦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事后研究。即便是在实验室里研究梦,能看到被试在做梦时他的大脑或身体里正在发生什么,例如在快速眼动睡眠中,但他们当下的梦是关于什么,我们往往也只能在唤醒他并让他讲述梦中的经历之后才知道。所以,梦是一种私人的、主观的体验。
但这些困难并不仅仅存在于梦的研究中,许多其他领域也会遇到这些挑战。例如对疼痛的研究,没有一个让你直接看到疼痛的机器。我们只能从人们描述疼痛的形容词中推断他们经历的是灼痛,跳痛,还是刺痛,以及疼痛的具体位置。人们会说,“我的下背部在疼,我的腿在疼。”这些也都是私人的、主观的体验。这些挑战存在于人类拥有的许多主观状态中。
斯托加茨:真是一个有趣的类比,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么你如何定义梦呢?我知道这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在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给出定义往往是相当困难的,比如说“什么是生命?”但还是让我试着问问吧,什么是梦?梦有哪些典型特征?
扎德拉: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梦的定义。一些研究者认为,梦是大脑详尽的、叙事驱动的产物,它位于大脑的某个地方,拥有时间维度,包含着情绪以及某种形式的社交互动。这些描述与人们起床之后能回想起来的梦更加接近,这种梦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中。但对于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来说,梦是指睡眠中经历的任何形式的思考或知觉要素。这往往被称为睡眠中的精神活动(sleep mentation)。
依照不同的定义方式,梦可以是相对独立的图像,也可以是思维模式。梦可以是你睡着时在你眼前舞蹈的几何图形,也可以是内容丰富的、叙事驱动的、身临其境的体验。基于不同的定义可以研究梦境的不同元素或不同的表达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当我们问“你如何定义意识[10]?是什么构成了意识[11]?”等问题的时候。存在一些意识的最小形式,例如当你早上昏昏沉沉地醒来,或当你沉浸于美妙的音乐或精彩的电影中,或在与伴侣的激烈争执中,或是当你十分投入地参与到和老板的工作中,又或者是当你处在热恋中……这些都是不同类型的意识。而且,对于盲人、聋哑人或感觉模态受限的人或瘫痪的人来说,他们同样拥有意识。但他们主观经验的范围存在巨大的差别。这对于梦来说同样适用。
斯托加茨:我们是否知道大脑是如何创造出与梦有关的图像的呢?
扎德拉:简短的回答是,不知道。更准确地说,我们正在慢慢地靠近那个答案。因为梦会发生在睡眠的不同阶段,而不同睡眠阶段大脑的活动区域差异很大,就像大脑的一般神经化学,它常常导致一些相互矛盾的观点。
但我们知道,一些最生动的梦往往出现在快速眼动睡眠中,我们知道那时次级视觉区域被激活了。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梦是高度视觉化的经验。初级视觉区域没有被激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闭着眼睛,没有视觉信息通过你的视网膜进入视觉区域。是你的大脑创造出这一切。我们还知道,你的运动皮层(大脑中控制运动的部分)也被激活了。这很可能就是让我们在梦中产生自己正在一个真实的3D物理世界中移动的感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我们的边缘系统和杏仁核也被激活了,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梦里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情绪,我们带着情绪投入其中。此外,我们还知道部分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被抑制了,这个部分位于双眼上方约一英寸左右的位置。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区域对于所谓的执行功能、判断、批判性思维、计划而言十分重要,梦境中这些因素是缺失的。
我们开始更好地了解不同的大脑区域如何一起[12]创造出了梦的一般特征。更神秘的是大脑如何选出特定的图像并把它们编织在一起,以及为何如此。
斯托加茨:梦的某些方面与对清醒时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有一种说法是,梦可以帮助我们记住一些事,但它是如何实现的呢?应当如何恰当地界定二者的关系呢?我们现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扎德拉:退一步来看,我们知道睡眠在不同类型的记忆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说,非快速眼动睡眠的不同阶段可以帮助我们巩固记忆。这通常发生在你学习一些事实并且想记住它们的时候。在快速眼动睡眠中,我们的记忆更多地与我们对世界语义上的认识相关。它更多地与你在何时、如何使用这些事实有关,而非与事实本身有直接的关联。因此,非快速眼动睡眠可以让你变得更聪明,而快速眼动睡眠可以让你更智慧。
现在,我们认为梦可能在其中一些过程中发挥作用。与七八十年代一些对梦的理解不同,神经生理学家认为,梦远非随机事件。我们的大脑明显偏爱那些清醒时所经历的有显著情绪的事件。此外,梦还能完成我们清醒时做不到的事情,它会利用这些经验并在整个记忆库中搜索能与之联系的、有微弱关联的经验。
那么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就是大脑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我们清醒两个小时后,大脑需要切断所有外部信息来源,再用一个小时处理我们在清醒时度过的两个小时中经历的事情。这部分解释了睡眠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梦是通过询问“我们今天已经经历的这些事情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用处?”发挥作用的,这意味着记忆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乎未来。这是说,你能记住事情并不是为了退休之后在门廊和老朋友喝一杯的时候可以回忆那逝去的遥远时光,“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骑车去湖边吗?”我们演化出记忆的能力不是为了这个。
记忆可以让你在路上开车时看到后视镜里闪烁的蓝红灯的时候意识到,“那是辆救护车或者警车,我应该开到右边给它让行。”记忆让你可以预测并了解你面前发生的事情,并对周围的世界作出正确的反应和阐释。
梦吸纳了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这或许是由于大脑在睡眠中(具体来说,在快速眼动睡眠中)的特定神经化学效应。它找出了这些经验之间的弱相关性。你的大脑就像是打开一个个抽屉,然后不停地问,“它能放进这里吗?它能放进那里吗?”而基于你在梦中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你做梦中的大脑利用这些信息,“是的,这是一个有用的联系。没错,这是一个合理的联系。”就是这个过程帮助我们建立起对世界的理解。所以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带着日复一日更加清晰的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理解醒过来的。
另一个我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理所应当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事情是,在我们做梦时,我们的大脑在做两件了不起的事情。当然,它会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这两件尤其特别:首先,它创造了你;你有一个身体,你看到东西,你的梦往往是第一人称视角。同时,它还创造出梦中的环境,包括你遇到的每一个人。我的意思是,你记得自己其实正在床上睡觉,你没有听到外界的声音,没有在看任何东西,但你能沉浸在梦境中,在其中与人交谈并听到他们做出回应。而就算在清醒梦(你知道自己在做梦)中,你也很难知道下一步你的梦里会发生些什么。你的大脑在向你隐瞒这些信息。在一个清醒梦中,比如说你可能可以让梦中的一个角色出现,但如果你问他们——你是谁?你在我的梦里做什么?在这之中我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并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回答你。但你的大脑知道。正是你的大脑创造出了这个角色。
所以当人们说,“噢,你可以在你的梦中做任何事”,或者说“你是梦的制片人和主演”,我并不认为这些说法是正确的。你不能控制你的梦的构建过程,是你的大脑在控制它。你的大脑还故意隐藏了关于故事情节会如何展开的许多信息。大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它需要知道你会如何对这些不断发展的叙事作出反应——梦在它的结构上也有各种转折,比如场所、地点、情节走向等。这构成了梦境本质性的奇异性。
这表明你的大脑在探索经验之间的弱关联,它试图了解你将如何作出反应。所以我们认为,梦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上起到作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记得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解读这些事情。我们对记忆之事的大多数解读是基于语义的。你知道,当我说我遇到了一起事故,“事故”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和意义。物质性对象亦是如此,像是“森林”、“玻璃杯”和“红酒”,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意义是不同的。当你梦到一个玻璃杯的时候,你的面前没有一个物理的杯子,是你的大脑创造了它。而你对这个简单的对象有着各种隐喻和联想。现在,如果我们想想人际关系,以及更加复杂的各种事物,随着梦境的展开,这些联系会变得更加宏大、复杂。
斯托加茨:你提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方向。其中最打动我的是极具神秘色彩的哲学说法,你在讲述时是用“你的大脑正在向你隐瞒些什么”这样的语句来表达的。这让我好奇这里的“你”是指谁?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大脑就是他们本身,但这里显然有一些更微妙的事情正在发生。
扎德拉:的确如此。有些人认为,这个说法也适用于我们具有清醒意识的时候,但这并不是最终的定论。但我认为,对于梦这种独特的意识状态来说,争议要少很多。
关于你的大脑如何利用你的反应、想法,并将之反馈到梦的发展中,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有时人们会有一些愉快的关于飞行的梦。梦中他们在空中翱翔,飞行过程中俯视着所经之地的风景,这真是不可思议。这时一个想法闯入脑海,我怎么会飞?这个疑问一出现,其结果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向下掉。因此,梦是你的大脑将你置身其中的环境和你对之作出的反应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我认为,这就是梦的关键功能之一。睡眠中经历的很多事不需要我们真正经历过。梦可以整合信息,分泌荷尔蒙,调节很多东西。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有意识的经验的参与。而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必须通过做梦来完成这种记忆处理工作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大脑需要通过做梦来理解这个世界。它需要了解你对它构建的梦和梦中的环境有什么反应,因为它是由你的大脑创造出来的,是你对世界、父母、兄弟姐妹、工作、自我价值以及疑问的理解。你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如何对你梦中的所思所做作出反应,你和梦中世界之间持续的、不断发展的互动(虽然被大脑向你隐瞒了)帮助你的大脑理解清醒时的种种经验。因此,前面提到的“你”只是你的大脑在梦中所做之事的一小部分。并且我相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当你做梦时,大脑向你隐瞒很多信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即便在清醒梦里也是如此。
– AMAO . –
斯托加茨:好的。让我们来聊聊清醒梦吧。我刚刚说,你前面讲的话里提到了几个方向,其中之一就是清醒梦。另一个简要提及的方向是梦的神经化学方面,以及它如何被放入奇怪的联想之类的东西之中。我对此也很感兴趣。不如就从清醒梦和与之相关的梦境工程(dream engineering)聊起吧,首先请向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清醒梦。
扎德拉:清醒梦本质上就是,你在做梦时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一旦人们有这种意识,他们就可以运用对做梦的知识尝试操纵或影响梦境的发展,这就是清醒梦的本质。清醒梦有很多有趣的特征,其中之一是它为我们在睡眠实验室中对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斯托加茨:所以清醒梦是自然而然地、自动形成的吗?还是说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做清醒梦?
扎德拉:有些人说他们自有记忆起清醒梦贯穿一生。这只是少数群体,他们中有些人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感觉很惊讶。多数人,大约一半的人,说他们在人生中至少有过一次清醒梦,往往发生在他们幼儿青少年时期。还有大概20%的人会说他们每个月会至少做一次清醒梦。
对于这些每周几乎每晚都会做清醒梦的人,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他们。而我所说的“清醒梦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并且在全世界十几个实验室都已经实现了)指的是——不管你相不相信——做清醒梦的人可以在做梦的同时告诉你(实验室里的实验员)他们在做梦,这种交流可以通过意志控制的眼球活动实现。我们在快速眼动睡眠中会有睡眠麻痹,但是我们身体的很多部位并没有被麻痹,例如你的呼吸系统,舌头和眼睛。因为即使你移动眼睛,也不会伤害到你自己;而如果你站起来跳下床,可能会一头撞到墙上。所以这种麻痹只是让我们保持相对静止就足够了。你看到的猫或者狗睡觉时身体的颤动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大规模地移动身体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你观察快速眼动睡眠中的小狗或者一个小朋友,他们的眼睛也会来回移动。所以,做清醒梦的人可以通过在梦中进行这种提前说好的左-右-左-右-左-右眼球活动来利用这一现象。实验室中用于监测他们闭合的眼皮下的眼球活动的电极可以接收这些活动。当你查看做清醒梦的人的多导睡眠图*记录(polysomnographic recordings)时,首先你会看到快速眼动睡眠中随机的眼球活动,但是突然你会看到极富规律性的左-右-左-右信号,这就是做清醒梦的人在告诉你,“我知道我正在实验室里,我现在知道我在做梦,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信号。不止如此,现在我会开始执行你让我在梦里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可能是唱歌,数到十,握紧拳头,甚至是做爱。而当他完成的时候,他就会发出第二个信号。这时研究人员就会知道,在信号一和信号二之间,被试在唱歌,或者在跑步或深蹲,然后你就可以观察当他在唱歌、数数或高潮时,大脑里正在发生什么。
*译者注
多导睡眠图(Polysomnography, PSG), 又称睡眠脑电图。主要用于睡眠和梦境研究以及抑郁症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断。多导意为其通过不同部位的生物电或通过不同传感获得生物讯号,经前置放大,输出为不同的电讯号,记录出不同的图形以供分析。
所以你在某种意义上不需要等到他们醒来再询问梦中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些人在他们开始和结束梦中的特定活动时会盖上一个“时间戳”。直到今天,这对我来说都非常难以置信,一个人可以在睡眠实验室里睡觉,很快进入快速眼动睡眠,做梦,并与你沟通。
这使得研究人员可以更多地了解身体和大脑如何对不同形式的梦的内容作出反应。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告诉我们的是,你的大脑和身体(在一个更小的程度)会对梦到的活动如你所期待的那样作出反应,这与清醒时无异。
去年,这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听起来更像科幻小说了。在多个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和做清醒梦的人之间实现了双向交流,这些实验室分散在全球,有些在欧洲和美国。他们不仅可以让做清醒梦的人给出这些眼球活动信号以表示他们是清醒的,实验人员也可以借助一些外界刺激来尝试影响梦境,就像阿尔弗雷德·莫里(Alfred Maury)在19世纪60年代所做的那样*。
*译者注
阿尔弗雷德·莫里,在弗洛伊德之前,测试了睡眠时体验到的气味和声音等感官刺激是否会影响他的梦,创造了入睡前幻觉(hypnagogic hallucination)这一术语。
举个例子,他们可以轻轻地重复一个问题,你需要找到恰好让这个问题加入梦境的点,但又不会把他们吵醒。他们可能会问8减6、8减6,或者在睡着的被试的眼皮上方闪烁一些灯光,希望这些视觉刺激能够进入他们的梦中。在第一个例子里,被试会通过两次左到右的眼球移动来回答答案是2。你可以用眼球的活动完成这些研究,你同样可以要求他们用“是”或“否”来回答问题。比如问,你喜欢巧克力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可以在梦中尝试做一个大大的微笑。如果你正在监测面部肌肉,你可以看到嘴唇周围轻微的收缩。于是你就知道这个人在微笑,也就是在回答“是的”。如果你问,你喜欢钩针编织吗?答案如果是否定的,他就会在梦中皱眉。如果你用电极监测这些面部肌肉或者眉毛周围的肌肉,当你看到电极放电时,意味着答案是“否”。
这些只是基础的步骤,但它不仅能让做梦的人向外部的实验人员传达信息,还能让实验人员向做梦的人提问,从而实现双向沟通。这就是与做清醒梦的人进行双向沟通是可能的证据。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让我们可以真的告诉人们在梦中做某件事——让他们盯着一个物体,让他们大喊,让他们在音乐会上听美妙的音乐,让他们阅读——并观察大脑和身体的反应。这开辟了研究梦境如何展开、以及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如何参与这一过程的新路径。这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它们是真正的科学。
斯托加茨:哇,你讲的这些真的很精彩。我想问一个有点像尽职调查的问题——我相信有些听众一定也想问这个问题,这所有一切有可能是一个骗局吗?人们有可能在假装吗?我确信研究这些的科学家们是负责任的,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人是真的在快速眼动睡眠中,而不是在跟我们玩什么装作睡着的把戏?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真的睡着了?
扎德拉:快速眼动睡眠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运动麻痹,这是可以被监测的。自从睡眠生理学在实验室中用一些电极(包括放在你下巴下面的一些电极)进行研究,这就已经可以做到了。在你的下巴下面有一块肌肉,就算你没有移动你的下巴,它往往也会表现出一些基本水平的活动。但在快速眼动睡眠中,这块肌肉的活动水平降到了零。而这不是你凭意志可以控制的,这是只有在快速眼动睡眠中才能观察到的现象。而在这些研究中,这些肌肉麻痹的指标是完整的。
还有一些只有在快速眼动睡眠中才会被抑制的反射,其中有一种叫H反射*。如果你测试那些反射,就能看到它们被抑制了。所有这些指标,包括他们的眼球活动,脑电图信号,或是这种肌肉弛缓,都是只有在快速眼动睡眠中才会发生的。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参与者的确是处于典型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而不是假装出来的。
*译者注
H反射测定的是感觉和运动纤维往返传导的速度,也是周围神经病变的参考指标之一。
当然,有些人可以在家里假装自己睡着了,然后说,“哦,我正在做X,Y,Z。”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我曾经在油管看到过相关的视频。但关于我刚刚讲到的研究,我们有外部的梦境专家评估这些电生理信号都是明确符合快速眼动睡眠的,被保留作数据的案例中的所有睡眠指标都是没有疑问的。
斯托加茨:你的实验室也研究清醒梦吗?
扎德拉:我们有相关的研究。此外,我们还研究清醒梦在实验室外的临床应用,比如用于治疗噩梦。但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是清醒梦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大脑是如何创作出梦中的角色的。
就我个人而言,梦中的角色是梦最让我着迷的一个方面。因为梦中的角色不仅会说出和做出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当我们问他们问题,他们会给出让我们惊讶的答案,又因为他们是由我们的大脑创造的,我认为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让我们感到惊讶。梦中的角色像是有自己的意识那样行动和回应,但我们知道其实他们没有,或者说很可能没有,因为他们只是你想象力虚构的产物。但当你在梦里遇到你的前任,他或她对你很生气,他们看起来确实很生气,他们会有面部表情展示他们对你所做的事有多生气。或者其他像是你在梦里陷入热恋或者被侵略者追赶之类的情形,这些人都会有情绪表达,他们说话的方式和语调都与我们在清醒时遇到的有意识的真实的人别无二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也许是二维的,就像是戏剧里的群众演员一样;但其他的角色真的让我们感觉他们是有感觉能力的存在,仅仅是他们看着你的样子就会让你觉得像是真的被对世界有感知的人注视着。
而我们可以用清醒梦来探索这个方面。比如说,我正在和一位运用清醒梦进行艺术创作的英国艺术家戴夫·格林(Dave Green)[13]合作,我邀请他为我表演如何让梦里的角色为他创作艺术品。当他在清醒梦里请求那些角色,“可以请你为我画一幅画吗?”他得到的回应非常有意思。有一位先生结结巴巴地告诉他,“那个,我,我不会画画。”而当戴夫问他,“好吧,为什么呢?”他说,“嗯,因为我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还询问了另一位女士,“你会画画吗?”她说,“噢,当然了。”她继续说道,“我很擅长画画,我小时候学过。”她讲述的学会画画的故事让戴夫感到惊奇。他给了她一张纸,一支铅笔,然后她画了一幅画。当他看到画时,他发现那只是一串字母数字代码。他说道,“这不是一幅画。”她说,“这当然是一幅画,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解开这串代码的钥匙。”
还有许多与此类似的有趣的例子。早在80年代,德国研究员保罗·托莱(Paul Tholey)[14]就进行了有关问清醒梦中的角色各种问题的探索。他问了这样一些问题:你会唱歌吗?你可以想出我不认识的单词吗?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梦中的角色都很不擅长数学,即便是最基础的数学问题也会让他们不知所措。如果你问梦中的角色,4加3是多少,有些角色会回答是6。这很有趣,因为作为做梦的人,你是知道答案的,但是梦中的这个角色却会出错。保罗·托莱的研究中还会出现其他的反应,当你问数学问题时,有些角色会直接跑开。在两个个案中,他们直接崩溃大哭道,“噢不,不要数学!”
斯托加茨:我们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个数学教授,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也时有发生。
扎德拉:确实。这些角色拥有着不可预测的天性。为什么他们会以这种方式行动?为什么你的大脑决定让他们做出这种反应?这又如何影响了梦的形成和发展?所以说清醒梦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研究梦的基础神经生物学,同时也是通往这些更主观也更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窗户,这与意识问题以及梦和梦中特定的角色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有关。
斯托加茨:我想确认我是否理解了你刚刚讲述的奇妙故事。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戴夫·格林本人就是一位能够做清醒梦的人?
扎德拉:是的。
斯托加茨:然后他会告诉你他的清醒梦中发生的事情,他遇到梦中的角色并且邀请他们做特定的事情,比如画画或者做数学题之类的。这就是你刚刚讲述的事情,对吗?
扎德拉:是的,没错。这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在实验室里被研究了。至于戴夫,他是一个会利用自己的梦作画的人。他会在醒来时尝试回忆梦中的事情,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它们复制出来,就像是将清醒梦作为某种创造方式。所以当我们讨论他的一些作品时,我问他,“那么,与其你自己作画,为什么不试着召唤梦中的角色,让他们画给你看,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正是我们当前的合作模式的先声。
斯托加茨:真是非常有趣的研究。我们之前还讲到了“梦境工程”,这是梦境工程的一种形式吗?
扎德拉:梦境工程和它其实关联不大。人们正在这个新兴的科学领域尝试使用不同的技术和方法来影响梦境的内容。从睡眠可穿戴设备到气味和声音的使用,这些外界的刺激环境可以对人们做梦的方式和内容产生影响。例如,从利用能够让人身临其境的VR技术让人做飞行梦到在睡眠过程中释放不同的气味,前者已经被证实为有效。我们知道,玫瑰花或者你喜欢的饭菜的味道等香味并不会直接进入你的梦,但会孕育积极的情感和梦境,就像臭味也不必然直接参与到梦中,却能够为梦境蒙上一层消极的面纱。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技术可以影响人们如何以及因何做梦。梦境工程从广义来讲大抵如此,是梦的研究中极速发展出的一个领域。
斯托加茨:我听说你和一些其他的梦境科学家和睡眠科学家签署了一封表达对梦境工程的隐忧的联名信。你可以聊聊这封信以及你们的担忧吗?
扎德拉:梦境工程真的是一个非常新并且处于起步阶段的领域。几篇关于梦境工程的最早的论文也是近几年才发表的。梦境工程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被应用于治疗、大脑研究以及意识研究,还因为睡眠和梦参与到情感记忆的处理过程中,因此梦境工程还可被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就像很多新技术一样,它也有潜在的缺点,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而言,有一些非常可怕的潜在应用。我可以举一些例子。
顺便说一下,世界各地有超过40名睡眠和梦境研究人员联署了这封信。我们的担忧并不是它当前的危险性,而是它变得危险的潜在可能,我们宁愿主动让政治家、决策者和公众早点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的担忧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睡觉时使用与睡眠有关的技术,比如苹果手机,或任何可以记录睡眠时的声音的手机。如果说你想知道你有没有打呼噜或者睡眠中是否有呼吸暂停的现象,这或许很有用。但与此同时,关于你处于哪个睡眠阶段的信息也被收集了。我们可以知道使用睡眠可穿戴设备的人的心率、呼吸频率,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他们是处于快速眼动睡眠还是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我们知道大脑在睡眠中会以和清醒时不同的方式处理信息,而就算你对睡着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没有记忆,它们仍然会影响你的行为。
我来举一个例子。在一项研究中,对戒烟有兴趣的吸烟者被带到实验室中,他们被告知,“你们可能会在实验组中,我们会释放一些气味并了解这些气味会如何影响你的睡眠;也可能被放到对照组,这时就没有气味会呈现给你。”他们需要记录来实验室之前和之后的抽烟数量以及一些其他事情。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在睡眠的一段短暂的时间中闻到了烟味、臭鸡蛋或者腐烂的鱼的气味。早上醒来之后,他们被问道,“你有没有任何与昨晚的气味刺激相关的回忆?”他们都说没有。你记得你的梦吗?他们会回答不记得。所以声称没有关于那些气味的记忆。但是一周之后,他们的抽烟数量平均减少了30%。
于我而言,最有趣的是,如果你在他们清醒的时候让他们同时闻到烟味和那些气味,这对他们的抽烟量毫无影响。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当你在人们睡眠中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相较于在清醒时做同样的事情,会更加有效且不为他们所知,因为睡眠中的大脑在用与清醒时非常不同的方式处理信息。
你也可以改变人们对糖果的偏好。你可以在他们来实验室睡觉之前问,“噢,对了,你更喜欢M&M还是Skittles?”他们可能会说,“我更喜欢Skittles。”在晚上他们睡着之后的某个特定阶段,你可以短暂地让他们听到重复着“M&M,M&M”的声音刺激。这声音不会将他们吵醒,他们对此也没有记忆。但当他们早上醒来,你再次问他们,“噢,顺便问一下,你现在更喜欢Skittles还是M&M?”超过70%的人会说:“很奇怪,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会选M&M。”但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说不出理由。
这些只是非常简单的例子,但是这种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如果你想想广告商愿意花多少钱吸引你30秒的注意力,你就能想象他们愿意用多少钱来吸引你几个小时的注意力,虽然你对这几个小时不会有记忆,但是它的影响可能比你在清醒的时候做过的任何事情都大。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但我想它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在高速公路上、在电视上、在看电影前后被广告轰炸了,睡眠应该保留为一片不受广告污染的净土。我不想我的曾孙必须每个月花10美元来选择在梦中不要听到广告。
斯托加茨:这真是一个噩梦,确实对我们有所警醒。让我们放松一下,来谈谈梦境研究的未来吧。我们来聊一聊你和你的同事鲍勃·斯蒂克戈尔德(Bob Stickgold,任职于哈佛医学院并参与到哈佛脑科学计划中)[15]提出的NEXTUP模型(network exploration to understand possibilities的缩写,理解可能性的网络式探索)吧。
扎德拉:好,这是一种尝试解释梦的核心特征的方式。许多关于梦的理论都是相当单维的,要么试图说明它们为什么很奇异,要么解释其情绪化,或者说明它们怎么依赖于快速眼动睡眠。而我们尝试提出一个模型来解释梦的整全体验,关于它们为什么会被遗忘,同时把我们已经获得研究结果融入这个模型。我们对梦的一般内容有了许多了解,关于清醒梦、噩梦、每天做的寻常的梦、重复出现的梦等等,还对做梦时大脑中发生的神经生物学活动有所了解,以及不同睡眠阶段和做梦有关的不同体验。NEXTUP的基本想法是,做梦是一种独特的依赖于睡眠的记忆演化形式。而它所尝试完成的,就是通过发现和加强我们清醒意识中那些松散的、出乎意料且此前未被探索过的关联,从已有的信息中提取新的知识。
当你慢慢进入睡眠状态,往往会有一些想法或画面出现在脑海中,它们通常与你当下的想法有关——我们认为这或许就是你大脑的某个部分尝试标记出在接下来的睡眠中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同样知道,在快速眼动睡眠中你的血清素(一种神经调节剂)的水平会下降,甚至降为0,这可能会创造出一种状态,让大脑倾向于接受梦中的关联是有意义的——这在大脑中就体现为血清素的减少。比如说,当你服用迷幻蘑菇或LSD时,这些体验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们往往使你产生充满重要性和意义的感觉,而相似的情况似乎也会在快速眼动睡眠中出现。另一种神经调节剂,去甲肾上腺素,也在快速眼动睡眠中大大减少了——而这恰恰是帮助我们保持集中、提前计划的物质。所以这可能就是梦具有超联想性、拥有奇异的元素和场景转换的另一个原因。它们再次揭示了大脑如何尝试探索可能性,为我们在白天经历的主要活动赋予意义,并探索它们如何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相符。
所以我们认为,大脑需要做梦,我们需要有这些经验来让睡眠中的大脑通过构建我们对自己和周遭世界的理解来真正理解我们居住其间的世界。这也让我们,或者说我们的大脑,为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情景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准备好在未来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反应和感知。
斯托加茨:谢谢你,托尼。这些关于梦和睡眠的想法非常具有启发性。真的很高兴今天能邀请你来我们的节目。
扎德拉:非常感谢你的邀请,我也很享受我们关于睡眠和梦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https://antoniozadra.com/en/about
[2] https://podcasts.apple.com/us/podcast/the-joy-of-why/id1608948873
[3] https://open.spotify.com/show/2FoxHraQSKwxV2HgUfwLMp
[4] https://podcasts.google.com/feed/aHR0cHM6Ly9hcGkucXVhbnRhbWFnYXppbmUub3JnL2ZlZWQvdGhlLWpveS1vZi13aHk
[5] https://www.stitcher.com/show/the-joy-of-why
[6] https://tunein.com/podcasts/Science-Podcasts/The-Joy-of-Why-p1653040/
[7]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tag/the-joy-of-why
[8] http://ceams-carsm.ca/en/chercheur-antonio-zadra/
[9] https://wwnorton.com/books/9781324002833
[10]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neuroscience-readies-for-a-showdown-over-consciousness-ideas-20190306/
[11]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anil-seth-finds-consciousness-in-lifes-push-against-entropy-20210930/
[12]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mental-phenomena-dont-map-into-the-brain-as-expected-20210824/
[13] https://dave-green.co.uk/
[14] http://www.gestalttheory.net/cms/index.php?page=paul-tholey
[15] https://brain.harvard.edu/?people=robert-stickgold
译者:肉;校对:Muchun;编辑:eggriel
原文: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why-and-how-do-we-dream-2022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