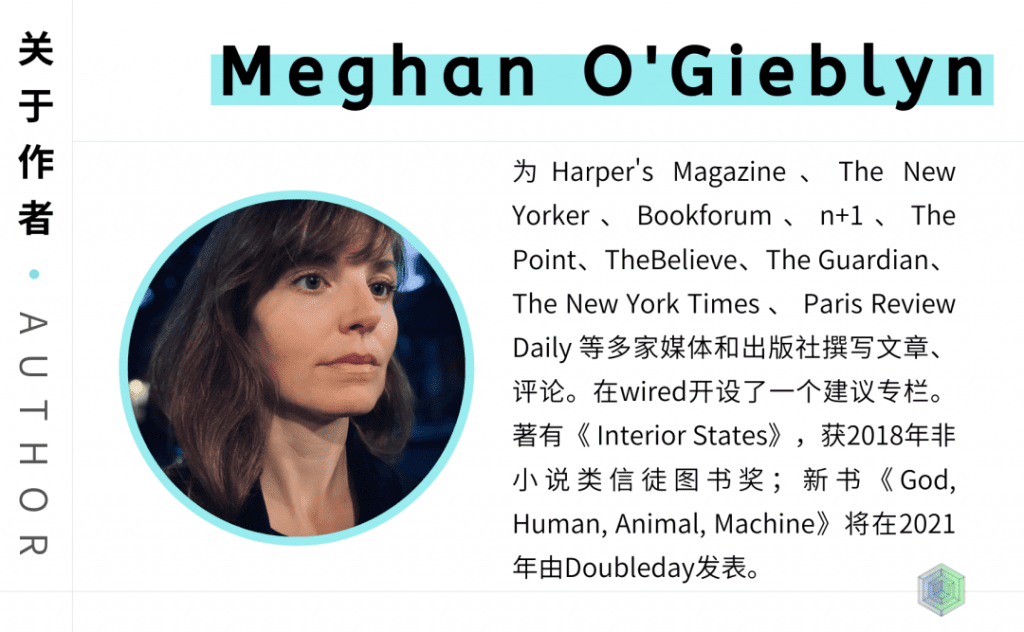请帮帮我: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虚荣的人,但是每当我参加Zoom视频会议时,我总是一直盯着自己的脸,而不是看着别人。我并不是真的在欣赏或端详自己的外貌,我只是⋯⋯单纯在看。这会影响我的个人形象吗?我应该关掉自己的画面来避免变成一个彻底的自恋狂吗?
——Seen

Seen,你好:
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可能是关掉自己的画面,但我并不建议你这么做——其实我非常反对这种做法。据我所知,看到自己的画面在参与者视图中消失,几乎总是会激起诸如愤怒、恐惧之类的情感,有时还会激起强烈的存在绝望(existential despair)——就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看到自己出生前的家庭照片时的感觉一样。换句话说,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不存在了。
而你更大的疑问——关于整天盯着自己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这超出了你是否自恋的问题。对于后者,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在临床意义上,对自恋的恐惧正说明你自己不算一个自恋者:只有那些不符合 [自恋症] 定义的人才会担心他们自恋。)不管怎样,你并不是唯一过分关注屏幕上的自己的人。而那些从来不会盯着自己的照片超过几秒的人们——就像你一样,他们报告称自己无法在虚拟课堂或家长会上从屏幕上自己的脸移开视线,这种专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我看来“虚荣心”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许更相关的问题不是平台对你做了什么,而是已经发生了什么,让你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无法控制地盯着屏幕上自己的像素图像。
当然,Zoom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镜子,或是一个普通的数码镜子(digital mirror)。它所提供的平台不是一个你可以任意涂画自己幻想和自我错觉的白板。你展现在平台上的自我,并不会摆出一些你在浴室或手机自拍中习惯见到的静态动作,而是那些真实地说笑、做手势、作出反应时的自己。

奇怪的是,这种“行动中的自我”的观察视角直到最近才变得普遍起来。在此之前,你可能会偶然在酒吧的镜子里瞥到自己在笑,或者在看到百货大楼的镜子里跟售货员说话的自己而暂时被分心。但直到一年前,我们才被迫持续地、实时地观察跟别人交流时的自己,看到我们沮丧时的表情、同情时的点头、激动时的手势,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自己的想象迥然不同——如果我们想象过的话。
“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能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这是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在1786年写的诗,表达了对客观的自我认知的祈求,而正是这种自我认知让我们大多数人感到困惑。总的来说,这个时代的科技“本领”给了我们相反的能力:让别人能像我们看自己那样地看我们。我们习惯了完全掌控自己的图像——知道最合适的角度、滤镜,并且能从几百张照片中精心挑选——然而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Zoom中无滤镜的自然状态仍然保留了某种魅力。你在Zoom中看到的形象与你期望中的自己并不一致,而是所有实体中最难捉摸的存在:你在社交场合危急关头中不假思索的自己,你的朋友、家人、熟人们所了解的自己,同时也是对你来说最陌生的自己。
*译者注: To a Louse(《致虱子》),采用王佐良译本。
这种以他人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的渴望绝不是放纵,而是形成和维持身份感的关键。抛开对理论的拘泥和对拉康不必要的引述,我简单地提一点:镜子的社会性功能体现在它提供了一种第三人称视角的方式,来将“自我”展现为另外一个人。能够通过镜子试验(婴儿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各种身体碎片的组合,而能够认出镜子里完整的自己)是儿童成长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他们已经进入了社会领域。自我是一种脆弱的幻觉,它需要不断的强化,而且这种强化通常是借由他人的凝视来发生的,这个过程在社会学里被称为“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很大程度上,我们是通过想象自己怎样出现在他人面前,以及推测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建立自己身份认同感的。
在过去,你可能将(来自其他人的)各种手势、回应理所当然地忽略掉,其中大部分都是微小的、无意识的动作,然而正是这些动作构成了你坚固而持续的自我感:当你在地铁上被一个人挤过时,他敷衍地说了句“谢谢”;当同事经过你的桌子时,你们之间发生简单的眼神交流;当你在派对上讲了一个笑话时,其他人会意地笑了。尽管你并不是被迫去观察跟别人交互的自己,但是通过这些主体间交互的时刻,你还是看到了自己。所有这些都是证明你仍然存在的真实证据,不仅仅是作为意识,而是作为这个世界上真实而具体的存在。

关于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最普遍的抱怨是感到自我被分裂和碎片化,记不得自己一天中做了些什么,这同时也是社会自我(social self)崩溃的明显症状——而这似乎并非巧合。在各种屏幕前独自度过一天中美好的时刻之后,你很容易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双在键盘上敲打的手,一双浏览新闻的眼睛,以及一个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的心灵。在Zoom上,这种“本人视图”至关重要,而移除它也就是在确证我们最糟糕的担忧——我们其实已经难以认识自己了。
所有这些都是在说,你对自己形象的痴迷很可能来源于一种自然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根本上是亲社会的。而你所试图保持的自我,正在逐渐被公共生活的中断而侵蚀。我认为,这种自我身份的维持绝非虚荣心作祟,而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从他人身上观察自我相当复杂,它需要共情,需要共识现实(consensus reality)的构建,即相信我们自己的心灵之外存在客观真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经常在一些极端的隔绝中失去辨别真实和想象的能力,而且不再能够划分自我和外在事物之间的界限。
确切而言,我不是说你应该花费更多时间在视频会议上盯着你自己,而是说这种冲动可以被当作一个提醒,它提醒人们需要相互理解——和你一起出现在屏幕上的其他人可能也感受到类似的需求。它可能会使你意识到,视频会议中的其他人也同样处于一种脆弱的身份认同感,每次登录的常规技术确认(standard technical queries)(“你能看到我吗?”;“你能听到我吗?”)可能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身份认同渴望。Zoom的一个优点在于,镜子作用是双向的。每一次点头,每一个回应时的手势,都在提醒说话的人他们是存在着的,在这个我们所有人共同居住着的世界,他们对其他人来说仍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诚挚地,
Cloud*
*编辑注: 这是wired的一个建议专栏cloud support,见链接:https://www.wired.com/tag/cloud-support/
作者:Meghan O’Gieblyn | 封面:Victor Beuren
译者:晏梁 | 校对:矛木
编辑:山鸡、Orange Soda
原文:https://www.wired.com/story/cloud-support-staring-at-my-face-on-z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