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定居沙漠之中,我才注意到雨。乌云遮蔽了夏日艳阳照耀下的光鲜。调色盘中的颜色由亮丽的琥珀色变为忧郁的蓝紫色。泥土的芳香在空气中弥漫。鸟儿歌唱和蟋蟀鸣叫不再,都被雷电轰鸣与狂风呼啸所替代。这一切猛然止歇。随后,宏伟又骇人的暴雨,像是延伸数里、密不透风的幕布,濡湿了干涸的大地。
在沙漠中,雨季迫使人们放缓生活的节奏,使干旱的大地再次充满活力。在这人们时间紧迫、忧心忡忡、心不在焉的社会,我们的脑渴求着这样的雨季。
我们的注意力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加·加塞特在1940年所说,注意力“赋予我们心智结构与凝聚力的功能”。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注意力又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每周工作超过45小时,他们之中又有八百万人自称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我们的休息时间亦不属于我们自己。在当今社会,我们每人每天从电子产品接收到的信息,几乎是1940年的90倍,等同于每周八十二小时,或是我们清醒时间的69%——这数量十分惊人。
尽管我们的脑是神经工程的史诗之作,但它依旧不能承受此般数据带来的沉重打击。我们的注意力会在集中90-120分钟之后减弱。与此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会造成一种“瓶颈”效应[1],使我们的脑无法将信息从一个区域传输至另一区域。也难怪我们47%的时间都在神游:我们每天需要付出的注意力已经令我们无所适从了。

集中注意力与神游都源自两个神经网络之间的活动。恰如一位老练的指挥使乐手们的声音和谐、调控音乐的节奏[2],脑的执行控制网络(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CN)调和、指引着各个脑区的活动[3],并以此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在中场休息时,这位“指挥家”走下舞台,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打开音乐厅的灯光[4],使我们的精神得以放松。DMN使人们能够踏上通往他们过去或未来的,愉快的逃避之行、通往小说或电影故事的,天马行空的假想航行,甚至是调控道德准则。这两个神经网络理应交替作用:中场休息并不会影响演奏的进行,演奏也不会在中场休息中唐突地开始。这种跷跷板似的配合带来了和谐的精神状态,而这又导致了创造力[5]、专注力[6]的增加,与健康的心理状况[7]。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两个神经网络并不和谐。紧张的日程安排、琐事不断的家庭生活、源源不断的负面新闻与使人上瘾的社交媒体不断剥夺着人们的注意力,扰乱了ECN与DMN之间精妙的平衡。我们生活在恒久不变的分心状态之中。在2009年,美国散文家威廉·德莱塞维茨在一场面向大学生听众的演讲中做出了警告。他声称如果人们如果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太多时间、过于沉浸于新闻的话[8]:
你就是在用世俗认知“腌制”着自己。在他人的现实中:这现实是属于他们的,并不属于你。你在创造一种噪声,而你也因此无法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当我们无法听到依赖于脑的DMN活动产生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时,已不稳定的ECN产生的旋律也不再和谐,极大地损害着人们的心理健康。
正如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慢》(Slowness)中所说,“科技革命使人类欣喜若狂,这一点正表现在这种我们对速度的永恒迷恋之中”。科技的每一个产物都闪烁着、嗡鸣着、叫响着吸引我们。在德文吉·薇弗莉卡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时写就的硕士论文中[9],她编录了数种诸如脸书或领英等网站使用的劝导式设计。下文列举了一些读者可能较为熟悉的设计,与它们生效的原因:
间歇性的通知:不定的推送时间使人感兴趣。 红色的消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令人好奇。 消息提醒上的数字:令人想要将其降至0,引发人们将无序变为有序的本性。
恰如狗得到零食作为奖赏,当我们屈服于一条通知时,多巴胺如同潮水般涌过我们的脑,为我们带来愉悦的感受。长此以往,这种令人上瘾的循环逐渐侵蚀了我们与生俱来的认知边界[10],让我们成为我们手中电子产品的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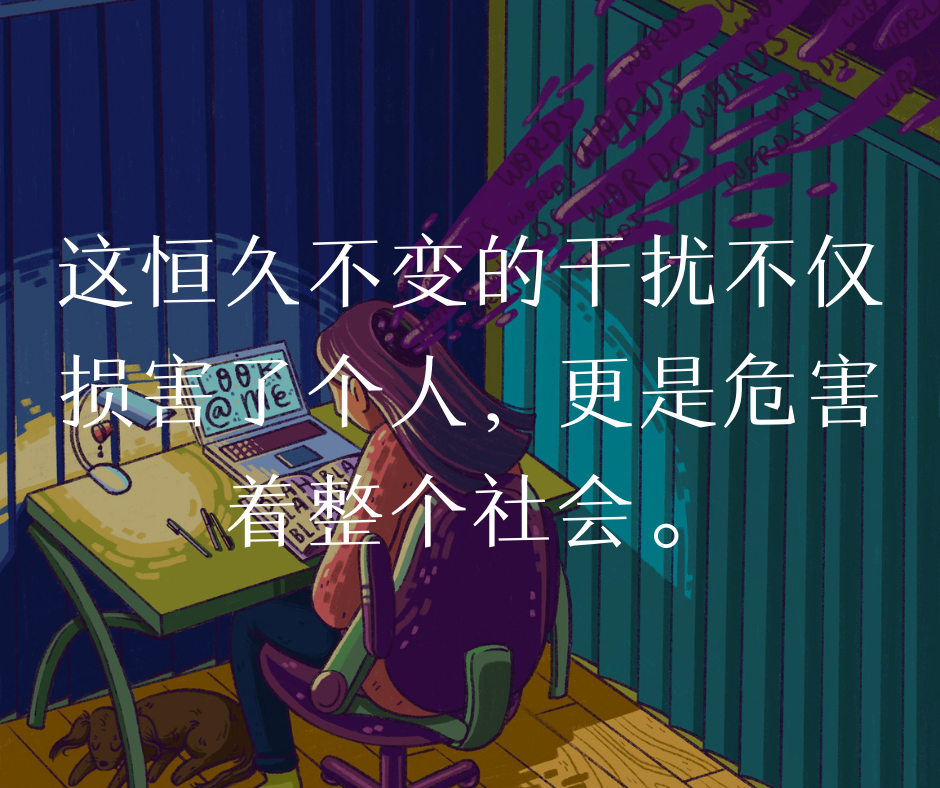
这恒久不变的干扰不仅损害了个人,更是危害着整个社会。因为一个名为注意偏向的现象[11],人们的感知会被特意挑选出的环境因素影响。举例而言,人们可以应用注意偏向,通过持续地对一个人展示使人胆寒的标语等有威胁性的刺激,来提升他的恐惧水平[12]。随后,恐惧又会影响我们的潜意识与内隐偏见[13],导致人们对他们曾认为无害的群体感到厌恶。如果我们的现实是由注意力创造,那么我们所注意的事物,就决定了我们在这现实中的活动。
在2020年3月11日,这世界癫狂的旋律止歇。很快,新冠疫情将整个世界隔离,同时为一些人提供了他们急需的,精神节奏的减缓。在所谓的“美国辞职大潮”中,数百万人辞去了他们的工作。许多人意识到了,正如奥利弗·布客曼在他的书《四千周:凡人的时间管理》(Four Thousand Weeks: Time Management for Mortals)中写到的[14],“生产力是个陷阱。提高自己的效率只会使你更加匆忙,试图清除障碍也只会使它们更快地卷土重来。”在疫情中,人们慢了下来,使DMN能够向我们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失衡之处。
在未来,世界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回归它癫狂的节奏,但我们不必如此。社会心理学家德文·普莱斯在他的书《懒惰并不存在》(Laziness Does Not Exist)中[15],从他本人的角度提及了精疲力竭这一概念,也解释道懒惰并非是需要依赖于咖啡因,或是增加工作时间来克服的缺陷;相反,它是提醒你“慢下来”的信号。在阿联酋与冰岛等国缩短工作时长[16]的同时,也有说法声称延长休息日与放缓工作日的节奏同等重要,DMN与ECN也能够借此回归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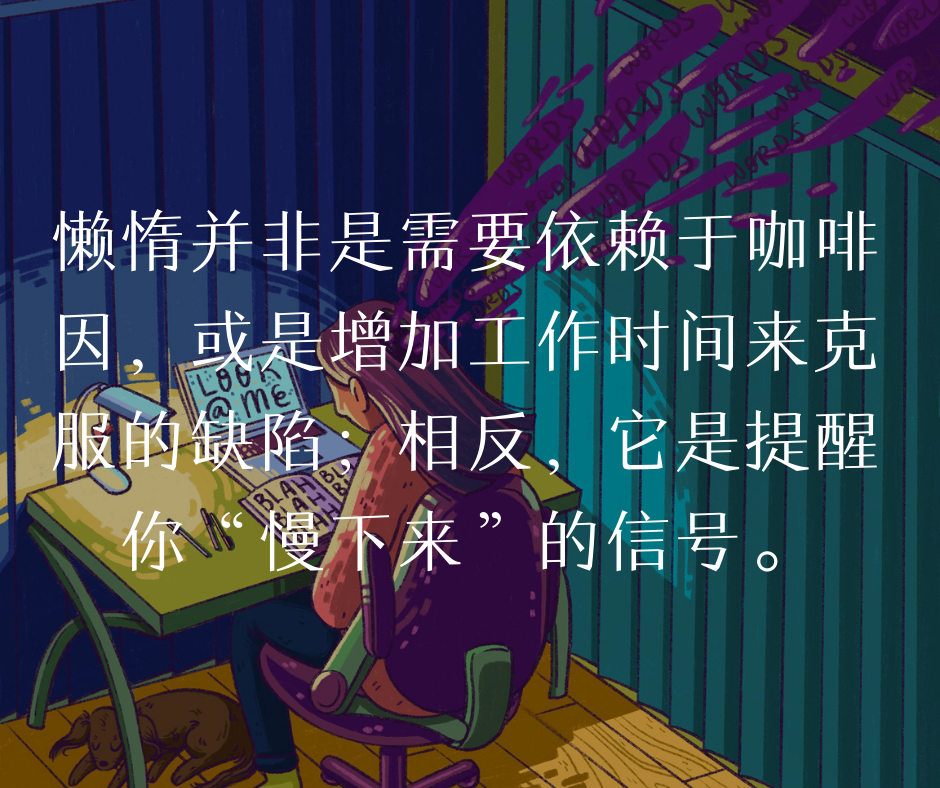
调整生活节奏的方法之一,就是与我们的感官重新结合。我们与感官的链接实在过于薄弱,以至于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身边的自然世界。艾伦·梅勒于在她的书《青绿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urquoise)中提议道[17]:
我们每个人都有五种不可或缺又令人着迷的,自然世界的投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与嗅觉。当我们——数据与诡计世界的住民——在纷纷扰扰中间解开这些将我们与自然世界相捆绑的线时,我们便缺少了这忠实又细致的向导,我们麻痹了我们的感官智能。这注意力的缺失,使我们成为无所依归的孤儿。
在大自然中[18]漫步——或者,按照日本的说法,森林浴——已被证实[19]能够降低血压[20]并帮助放松。将自己与自然的旋律相调和,能够减少与心理疾病患病风险有关脑区的神经活动[21],也启发了注意恢复理论的产生[22]——这一理论声称,自然能够恢复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通过注意力集中于在户外散步的当下,我们不再注意我们内心使人焦虑不堪的情景,也得到了我们十分需要的个人空间。
专注于当下的心境,是拥有心理韧性——在带来压力的事件(如一场全球疫情)之中或之后,对自己的情感状态进行有益调整的能力——的标志之一。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还表明[23],正念训练对心理韧性较强的人们来说,就像是在DMN将音乐厅的灯光调暗时,引导着那舒缓音乐的指挥家。深度倾听——专注于自己所听到的与在心理层面所感知到的事物——也是如此:它不仅能够培养人们的心理韧性[24],更是能够拉近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正如负面的注意偏向导致人们形成基于恐惧的感知,正面的注意偏向能够提升社会责任感,并减少情绪退缩行为。如果我们能够调控我们的注意力所在,专注于当下积极的一面,又何乐而不为呢?

艺术家珍妮·奥德尔在她的书《如何做到无所事事:抵抗注意力经济》(How to Do Nothing: Resisting the Attention Economy)中[25],描述了她预想的现实,是如何通过对分辨本地动植物的学习,逐渐被解构的:
(注意力)也可以指代对崭新的世界,与来去于它们之间途径的发现……它能够在山穷水尽时创造出通路,在未曾开拓的次元中,打造终有一日能够支持人们共同生存的环境。借此,我们不仅重塑了世界,更是重塑了我们自身。
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我们身边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心中有了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与我们对它的影响。正如奥德尔所说,“意识到了,便终将担起责任。”
在生活中,持续地保持着注意力并非易事。在定居沙漠之前,我也未曾注意过雨后的一切。温度下降,空气在沙漠鼠尾草的浓郁花香中变得清新,许多动物也从它们地下的巢穴中探出头来,使鸟啼与蛙鸣的大合唱更显得热闹。同这全新的万物一样,我也是全新的。
作者:Teodora Stoica | 排版:光影
译者:Nantu | 校对:杜彧
编辑:山鸡、光影 | 封面:Tiffany 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