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医学时代,经常有人用神经生物学术语来描述自己。这确实是个奇怪的潮流:“我抑郁是因为我的五羟色胺水平很低”、“我看电影时哭了,是因为这位悲伤的妈妈触发了我的镜像神经元”,“黑比诺红酒给我的一剂多巴胺让我来到了快乐天堂”……首先,这些说法将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过分地简单化,让江湖骗子有机可乘,靠着卖“幸福长寿万灵药”来赚钱。更重要的是,仅仅用脑活动来定义我们的行为过于片面。世界激发我们潜能的方式,就如同指挥家从乐谱中创造出音乐一样——醒醒吧,各位,你可比脑子里的神经元有趣多了!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阿瓦·诺伊(Alva Noë)提出了这一有力的观点。诺伊写了不少有趣的书,反驳了人们常常在课堂上探讨的“你就是你的大脑”的观点。他的作品包括Out of Our Heads、Strange Tools以及近期出版的Learning to Look。在Learning to Look这本短文集中,诺伊颠覆了许多从神经科学延伸出的理论。这些理论没有充分解释人们丰富的生活体验,尤其是关于艺术的体验。
过去几十年间,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受大众欢迎的神经科学书籍,这其中不乏关于“神经美学”的作品:它们用脑科学来解释艺术为何让我们感到兴奋、哪些艺术元素会让我们兴奋。“神经美学”是诺伊的眼中钉。Learning to Look一书中,诺伊写道:“假如你将‘神经美学’定义为’用神经科学来解释艺术和美学体验’的话,那么神经美学将注定失败:无论是从神经层面还是感受层面来说,艺术都不是一个需要用神经科学、心理学或其他任何经验科学来解释的现象;相反,艺术是一种质疑和探究的模式。”

对于他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对神经美学的广泛阅读使我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大脑,看看控制情感和记忆的化学分子如何影响我对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等艺术家的看法,或是解释我听到出色的乐队或管弦乐团时产生的强烈共鸣。简单地了解大脑的工作方式,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某件艺术作品对我来说会比另一件更有意义。这个领悟加深了我对艺术的欣赏,还让我对自己多了几分了解。
在最近的访谈中,我对诺伊说,神经美学可能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他并没有反对,只是纠正我说,我对于探索我所见之物的渴望是一种哲学行为。而神经美学是我在探索途中遇到的一个自命不凡的向导,想要窃取我独自找到答案的功劳。我和诺伊的谈话才刚刚开始。世界似乎都在限制我们的表达,而他为艺术的发声振奋人心:不能让科学夺走艺术的力量,解放思想的力量。

你对神经科学有什么意见呢?
阿瓦·诺伊:这么说吧,认知科学(这大体上包含了神经科学)对“人”这一概念的研究极其贫乏。“大脑是一台电脑”,“我们每个人都是缸中之脑”……就是在这些理论图景中,我们都被描绘成外星人,每个人都被描绘成自己的孤岛。神经科学非常有必要开发出更丰富、更积极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本质。
在大众科学中,神经科学似乎成为了表达自我意识的新语言。
阿瓦·诺伊:这是新的黑话。我天天听到人们说什么:“哦,对啊,我的前额叶有点问题”、“我的边缘系统没问题,但我需要很多前额叶方面的帮助。”这些话就会成为我前面所说的图景。而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真正理解了理性、决策与前额叶皮质的关系。大众科学仓促地使用之前无人问津的神经学理论去解释性格、情绪、记忆、感知、意识、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和爱情,而学界对这些领域的了解还不够成熟。虽说神经科学的文化霸权很可能是知识分子才有的顽疾,但这也是一种无知。人们对于“科学仍在发展”这一事实缺乏批评和成熟的认识。神经科学仍在发展,人们的认知也需要进步。
神经科学对艺术有什么影响?
阿瓦·诺伊:神经科在驯服艺术的同时也在摧毁它。艺术是革命性的。它是一颗种子。人类通过艺术来打破我们为自己立下的陈规。人类通过科学来验证假设。科学需要精确性、严格的定义和规则。在艺术体验的领域,神经科学就像是在学术霸凌。祭司会告诉你:“这就是关于你的真相。”神经科学也会告诉你:“这就是关于你的真相。”科学究竟有多高的威望,能让这么多人都认为:“噢,是的,这就是我,我只是一个大脑,我真的只是神经系统里一些噼里啪啦的声音。”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点似乎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信任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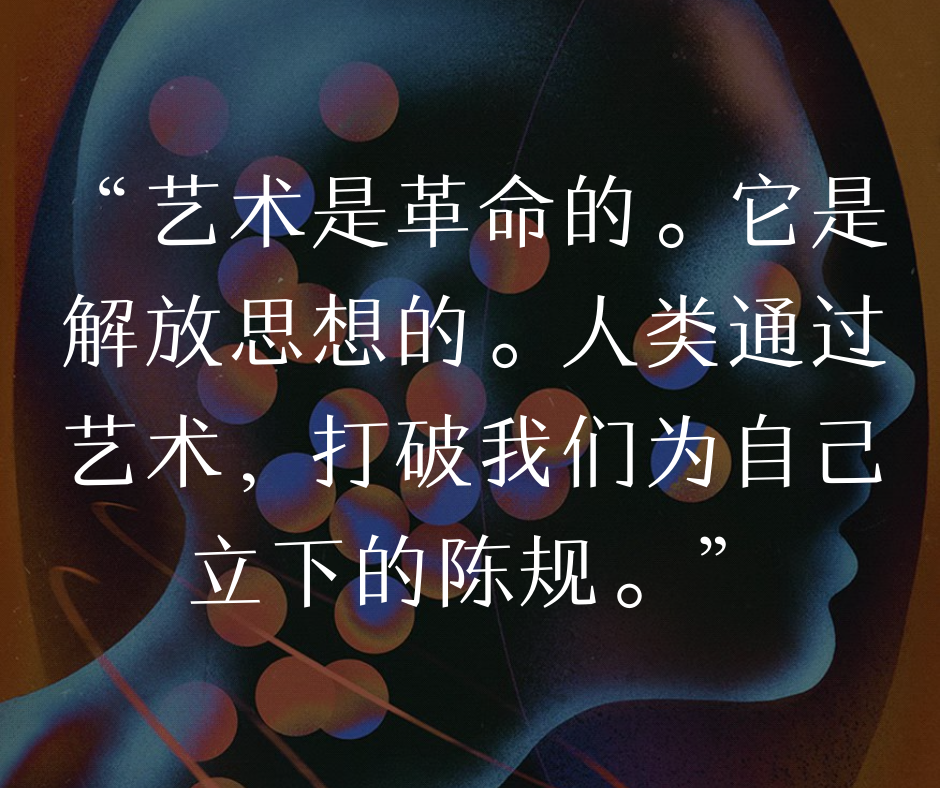
你一定比我更了解,现在书上、网上都充斥着“你就是你的大脑”、“你可以通过治愈你的大脑来治愈你的人生”这样的说法。
阿瓦·诺伊:是的。现在神经科学家试图解释并入侵艺术领域,因为他们已经解释了人类是什么。但艺术才更有可能带我们接近人类的本质。通过尝试理解艺术,我们才更有可能构想出一个更合理的、关于人类的生物学概念。
用神经科学的方式来理解艺术,有什么不对?
阿瓦·诺伊:艺术一直在提出问题,比如:“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对你很重要?”“让我成为焦点。”而神经科学,就和所有科学一样,需要定义它的术语、明确它所关注和研究的事物。神经科学的理念是,艺术触发了你身体里的某些东西,而这让艺术品沦为一个触发因素。但艺术不仅仅是触发因素而已;艺术是机遇——让一件艺术品成为焦点的机遇、让你自己成为焦点的机遇。艺术给予了人们交流、观察和思考的机会,而这正是艺术体验所在。
为什么神经美学无益于我们的艺术体验?
阿瓦·诺伊:神经美学无法区分艺术作品和其他感官刺激。本质上,它研究的就是一种被称作“艺术”的刺激。假如欣赏蒙德里安的作品很有趣是因为它可以激活我大脑里的色彩体验,那看这支荧光笔也可以啊。确实,如果我没有对色彩的感知能力,我就无法欣赏蒙德里安的画作。但我想知道,“是什么让蒙德里安的作品成为有趣的艺术品,而荧光笔却不行?”我认为神经美学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神经美学确实回答了一些艺术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它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可以触发我们的感官、情绪和回忆。
阿瓦·诺伊:一幅画可能会触发视觉系统中的简单机制,就和你看见这个世界时所触发的机制一样,迫使你去体验画中描绘的场景。但对于更抽象的作品,如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艺术或一些20世纪的实验音乐,并没有简单的信号让你进入不同的状态。你依靠你的情感联想和记忆力来感受这些艺术。但无论是传统的具象艺术,还是20世纪的表现主义艺术或概念艺术,你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它的价值源自哪里?”千万不要用记忆理论或神经处理理论来解释艺术的价值来源。
无论怎样,看待艺术的方式没有对错之分,也不存在选择立场的问题。人们讨论美学,是为了用语言描述自己的见闻与遭遇。而这种讨论本身就改变了他们对这些遭遇的体验,并且能说服其他人也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他们的遭遇。但这并不是说会有一个人拿着真理之杖坐在那里,告诉你:“这很美,而这是为什么它很美。”艺术家的性别和政治立场很重要,制作艺术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很重要,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信息。神经科学也是一样。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思考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并试图构想人类究竟是什么。但我并不认为神经科学可以做审美的仲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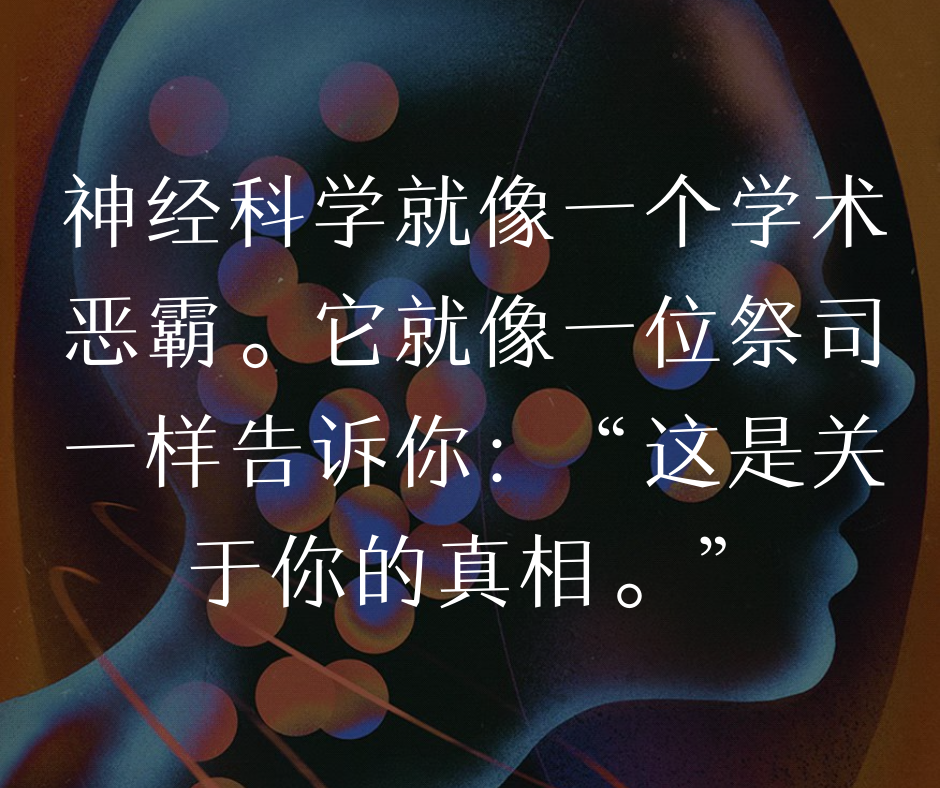
你提到了概念性作品。我不得不说,这些作品能深深地打动我。你知道艺术家罗伯特·雷曼(Robert Ryman)吗?当我走进画廊,看到他那些白色的画时,我被震撼了。
阿瓦·诺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都会说一件艺术作品有多么感人,但“我很感动”所表达的仅仅是艺术欣赏的一个方面罢了。神经科学家自然也会这么想,他们将情感反应看作是美学意义的替代品。他们在你身上放一个仪器,测量你皮肤上的电流、你的心率,或其他一些与感动有关的神经活动,然后说:“看,我们现在正在追踪艺术体验。”
欣赏罗伯特·雷曼的作品的有趣之处在于,大部分人走过他的画廊时,往往不会注意到什么。自然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些画都是一模一样的?”你需要不停问自己:“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应该看到什么?我在这里充当什么角色?”你必须努力——努力地体会自己的感知、认知与情感。你所具备的艺术史知识,将这些作品放进丰富的文化背景中。你可以将莱曼的作品看作是在说:“停下来、慢下来。当你提问时,看看发生了什么。这一墙的白色的画是什么?”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种艺术体验。它与社会、文化、知觉、情感——所有这些更宏大的话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喜欢那些表达“停下来、慢下来”的艺术。
阿瓦·诺伊:我们的一切体验都是艺术体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假如我让你描述你现在看到、听到、感受到了什么,我是在让你去理解这些事物,就像你理解一件艺术作品、试着描述它一样。即使是最简单的体验,也是十分开放且丰富多样的。如果你试着去深究它们,你就会发现这些体验之中都充满了艺术机遇,就像艺术品一样。对你的生活体验进行思考,这个行为本身就富有创造力,就像艺术体验那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阿瓦·诺伊:我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神经科学将这一切都归结为一句:“这就是当你观察事物时,你的脑子里发生的事情。”说得好像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看见”似的。我看见了蓝色背景上有一个红色色块,或者我看见了凯文……这些对视觉体验的描述都过于简单了。对我来说,这些体验具有一种隐秘的、几乎像分形一样无尽的多样性。假如我说我有过看落日的体验,那对于解构我所见之物的讨论而言,这仅仅是第一步。这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神经科学是否能解释艺术与主观体验。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艺术与美学支持着神经科学。神经科学认为它在做科学研究,而实际上它是在参与对美学的探讨。
你认为神经科学家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吗?
阿瓦·诺伊:我觉得,当神经科学家们反思他们自己的课题时,他们往往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理解。“你的意识在你的脑中,而这个世界是你的大脑运作的产物”、“你的大脑捏造出了这个我们看似’共享’的现实世界”、“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输入细胞的信号罢了”。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趋势。艺术中不存在这样的预设——艺术发掘我们心中的预设,并打破它们。艺术质疑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将美学意义与情感反应关联在一起是不合适的,因为艺术也质疑情感。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艺术原本就是社会性的。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说艺术是一个社会性行为或是指艺术被展出于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中。对于艺术的欣赏和解读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我们关于这件作品的对话。

我很喜欢你所说的:“寻找合适的词语来准确描述你的审美反应,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创作”。再展开讲讲。
阿瓦·诺伊:这就是创造性的行为。这是在赋予一件艺术品以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激活艺术品。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质疑自己。我们可能并没有察觉,但我们在打破我们思考、观察、并给事物贴标签的习惯,并试着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事物。而当我们用新的方式观察世界时,我们便成为了新的自己。我们通过艺术自我进化。
我敢说,这就是艺术的意义。
阿瓦·诺伊:我也这么认为。艺术很重要,因为艺术是让我们探索自我最高效的方法。通过艺术自我探索,不仅能让我们看清自己,而且还能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人类的所有体验中,艺术有什么特别之处?
阿瓦·诺伊:我想用一个浪漫的、听上去有点戏剧化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人生的特别之处,抑或是所有生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有组织的。生命活动是被精细控制的,是习惯性的。无论是在细胞层面、生物层面,还是文化层面,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我们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习惯性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而艺术,则是组织之轮上的辐条。艺术能解放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艺术家们之所以歌唱,不仅是为了用歌曲凝聚社会,更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歌声具有凝聚社会的力量。而一旦你开始关注这件事,你就可以去调整它,于是我们便有机会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我们不太可能从已有的习惯与组织中完全脱离出来,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改变并重新调整自己。艺术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带来了改变的可能性。
作者:Kevin Berger | 封面:Ada Zielińska
译者:Mollie | 校对:杨一森
编辑:老司橘 | 排版:平原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