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其潜伏期通常在5天左右。它的症状并不起眼,以发烧、乏力、干咳为主。出现上述症状的人群中,约有20%的病情会发生严重恶化。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难以估算,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3%左右的病例可能导致死亡。*
*译者注: 该数据发表于作者写作本文的2020年6月。
关于事实,我们暂且先说到这里。在“新冠肺炎”进入我们的词库一年多来,它已经成为了一种隐喻。和许多疾病一样,新冠肺炎被视为一场恶战中的大敌。这场疫情是一盏聚光灯,随着特朗普的频频操作,社会不平等和全球供应链的问题都被无情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它也是切中时弊的一束X射线,映射出最隐秘、腐朽的内里。正如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写道:新冠肺炎是一道“入口”,它借由大规模移民、经济破坏和威权监管的出现,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图景。
新冠肺炎或许是一种新型疾病,疾病的隐喻却并不新奇。1978年,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3篇文章;半年后她稍加修改,将其著成《疾病的隐喻》一书。桑塔格的关注点比书名所暗示的更为广泛:“隐喻”充当了一个转喻词,意指一系列象征性比喻。在书中,桑塔格追溯了在漫长的19世纪中,结核病在文学想象中留下的印记,以及20世纪人们对于癌症的幻想。书中两个相伴而生的理想是真实和健康,而隐喻是它们共同的敌人。桑塔格写道,清除自身的隐喻性思维,既是看待疾病最坦诚的方式,也是经受病痛最健康的方式。
尽管结核病具有传染性,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和其他流行病有所不同。通过在修辞上把结核病描绘成一种让人心思更为敏感的疾病,结核病可用来表达对自我的一种浪漫理想。霍乱、伤寒和黑死病的感染,是因为个体身处感染区内;相反,结核病则被理解为一种意喻着隔离和出走的疾病。这点并非偶然。从19世纪开始,在疗养院隔离,或前往罗马、山间、太平洋等地旅行,成为结核病的治疗手段,这种诊疗结果往往意味着受到家庭与社区的珍视。病体的物理隔离,有些避世绝俗的意味,被视作结核病人的内在不同于他人的外化表现。

疾病以一种使人个体化的模式被理解时,它能被纳入一种表达框架,并作为使内在实质可见的标识,以供人反向解读。这种理解也在小说中得到了印证:小说的主人公具有某种“易感染结核病的人格类型”,正是其内在本性和激情,使他们感染了结核病*。在此过程中,人们从疾病的物质现实出发,塑造了疾病的象征力量,最后病体本身被我们想象中它的对应物所覆写。结核病人呼出的气息中,会带有“腐肉的气味”,但这令人不快的现实,不过是其浪漫形象构建中一个可被忽视和擦除的细节。要当一个结核病人,就是要变得敏感、有趣、超凡脱俗。
*译者注: (前方剧透预警)比如在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中,英沙罗夫意识到自己不能重返保加利亚,因思念和沮丧而日渐病弱,染上了结核病,最后客死他乡。似乎正是因为英沙罗夫受挫的激情,使得他病入膏肓。
这种形象直到20世纪依然根深蒂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中稍加调侃了对结核病的描绘。埃斯特·格林伍德去看望她的运动员男友巴迪,他正在疗养院中准备度过这个夏天。“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期望巴迪的疗养院是什么样子。”埃斯特想,“我想我是期望见到一间小木屋,耸立在一座小小的山顶上,那里的年轻男女都面色红润,非常迷人,有着闪动着病态的双眼。”至于巴迪本人,她以为他会很憔悴,“双颊深陷”。恰恰相反,整个疗养院以晦暗阴沉、肝脏般的红褐色为主,而且巴迪还变胖了。更糟糕的是,他还有雅兴写了首诗,是关于贝壳和棕榈树的。
在桑塔格看来,当疾病的病因成谜且难以治愈时,疾病的象征意义就会变得丰富。抗生素的发现使得结核病失去了其象征作用。随着20世纪结核病的治疗方式(至少在西方)变得简单直接,结核病的象征意义被一分为二。“疯癫”(Madness)取代结核病,成为了具有艺术气质的疾病;而剩下那些缺乏美感的部分,则被另一种无法被诗化的疾病所接管,那就是癌症。

癌症的象征意义有些复杂。结核病的发展是时间性的,而癌症则是空间性的:结核病情会日渐恶化,而癌细胞可在全身范围不断增长。结核病是一种肺部疾病,而癌症可以扩散到身体的任何部位,包括那些更羞于启齿的性器官或排泄器官。而关于容易罹患癌症的人格类型,这种幻想仍未改变。结核病被解读为激情天性的流露,而癌症被视作压抑情感的代价。
疾病的隐喻有两种。我们可以给疾病取一个别称,比如“癌症是一种入侵”,或者我们可以用疾病的名称来谈论其他事物,比如“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癌症”。桑塔格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在第二种情况下,对于疾病的“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桑塔格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将过度的意义附加于疾病之上,而扭曲了病人有关疾病的经验。
不过这两种情况应当区别对待。“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癌症”是对疾病的“利用”;它通过疾病来阐明其他事物,预设了癌症比斯大林主义更为直接易懂,否则又何必要通过癌症来表述斯大林主义呢?恰恰因为把癌症说成是易于理解的,反而使得癌症本身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癌症是一种入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句话更可能被人们用来解释自己身上的疾病。奥德丽·罗德(Audre Lorde)在其回忆录中常常触及这种意象,她在《癌症日记》(The Cancer Journals)中写道:“我不仅仅是个患者,我曾走上过女性主义运动的前线,且现在依旧站在与癌症抗争的战场上。……我拒绝在自己眼里,从一个战士降格为一个受害者。”
罗德和桑塔格都在40多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两人都因乳腺癌切除了乳房;桑塔格也因此失去了胸部和部分腋下的肌肉。她们都关心,在病中和病后如何坦诚地生活。桑塔格专注于有关癌症的散文创作,而罗德审视了癌症治疗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罗德写道:安装假体让她更容易把乳房切除看作一类美容技术。反过来,这种粉饰门面的伪装反而掩盖了来自死亡的威胁。对于罗德来说,战士的形象即是“我们终有一死”(memento mori)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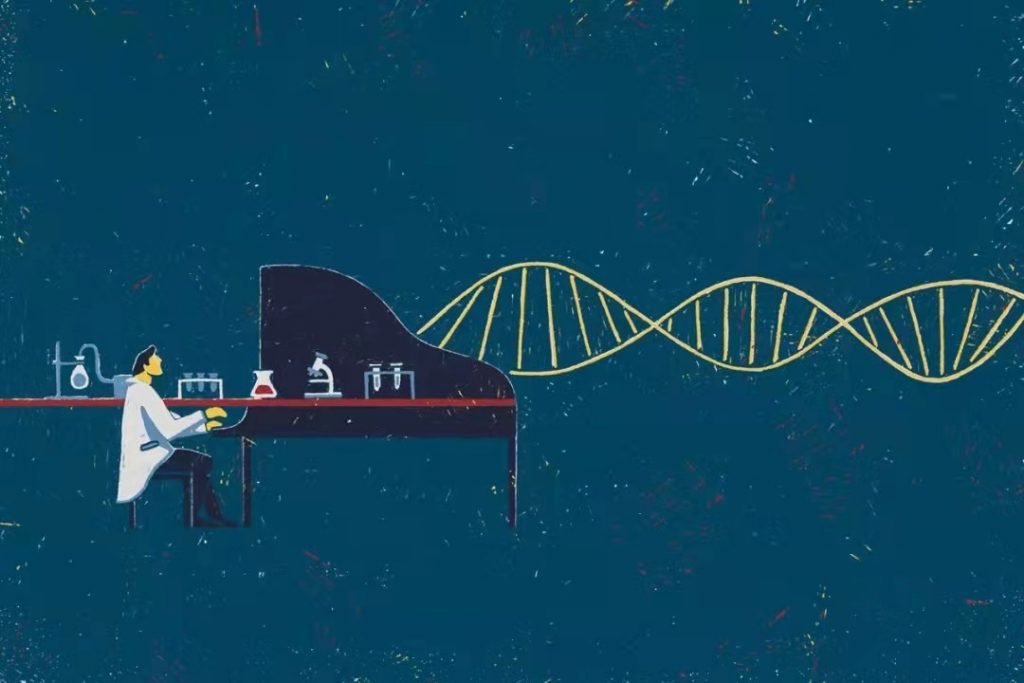
桑塔格的价值观要求一种真理:我们要看到疾病真实的面目。不过关于疾病的真理是什么呢?桑塔格有时被指责为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她认为关于疾病的真理只能用实验室和临床研究中那种冷静、客观的语言来讲述。罗德关于癌症的文章是一种自白,而桑塔格拒绝从冷静客观的分析跌入个人化的自传。(然而,女性的论作总被解读为是个人化的。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称,《疾病的隐喻》“是一本非常个人化的书,但为了合乎体统而假装是一本论著”。)《疾病的隐喻》可能是在她癌症康复后写的,但它绝不是一部回忆录。正如安妮·博耶尔(Anne Boyer)在《不死者》(The Undying)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描述乳腺癌和化疗时,桑塔格从未在同一句话里同时使用“我”和“癌症”这两个词。
桑塔格用文本的晦涩来对抗一种浪漫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身体视作不断发号施令的权威。生而为人,就是要发现自己是被他人解读和阐释的个体。无论是对于在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的“现充”还是紧张不安的“社恐”,社交总是一种在展示与隐藏之间来回切换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自我的塑造取决于我们将哪些看作密不示人的隐私。而疾病打破了这种动态。疾病的部分作用是,扰乱从我们模式化的、天生的行为中涌现的自我感知,以及我们将这种感知投射到社会环境的能力。在疾病中,我们对于身体的感知不再是“由内而外”可以把控的,而是由他人加工过的有关这具身体的经验(例如医生或朋友对于病状的描述),从外部接管并渗透了我们原本的感知。博耶尔的回忆录中戏剧化地表达了这一进程。“生命……在肿瘤学这一陌生的术语下被打破了。”她写道:
病人变成了信息……护士会询问我关于自己身体的感受。他们把我描述的感觉输入电脑,点击对应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长久以来被指定为某一特定的种类、名称,以及对应的保险种类……我把自己的感觉信息化了。是医生在解读我——或更确切地说,在解读我的身体变成了什么样子。

对于桑塔格和博耶尔来说,癌症是一种令人压抑的体验,让能够被他人解读的身体代表她们本人、甚至越过她们本人说话。只不过对于桑塔格来说,这里的身体是通过关于癌症的道德隐喻来表达的;而对于博耶尔来说,则是通过官僚化医学中苍白的词汇。在桑塔格的分析中,疾病的隐喻使得她对于他人来说变成是可解读的,而她也理所当然地对此感到厌恶。
不过也有像罗德这样的病人,在疾病威胁着要吞噬他们之后,也会使用隐喻来重塑他们对身体原本的感知。对于这样使用的疾病隐喻,桑塔格应该会如何看待呢?这很难说:虽然桑塔格告诉了我们很多,要如何不去谈论疾病,但对于我们应当如何谈论疾病,她却相对少言。有一些零散的线索:在她之后出版的著作《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她把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视为疾病写作的范例。《瘟疫年纪事》出版于1722年,为1665年在伦敦爆发的鼠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当然,这是一部纪实小说:笛福将死亡人数列成表格,否认有虚构情节;他故意巨细靡遗地描述,但却十分引人入胜。他的小说像是一块透明玻片,我们可以透过它看见鼠疫万人坑和紧闭的房屋,他们就在那里,不曾被解读。桑塔格赞同这一做法,因为他没有“进一步将鼠疫理解为一种天罚或……一场巨变”。
桑塔格与她过去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在1965年的论文《论风格》中,她写道:“所有的描述都在一种特定的风格中体现……因此严格来说,没有现实主义这种东西,除非它本身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风格习惯。”说明性的、非个人化的和平实的写作,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有选择性,就像华丽绚烂、与世隔绝或美好无缺的作品一样,是情感的投射。我们梦想着有一种可以直击事物本身的描述,但关于这种“没有风格的、透明的”描述,只是一种执着的幻想。而当桑塔格写《疾病的隐喻》时,她似乎已经陷入了这种幻想: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医学的语言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其写作越接近于纯粹的流行病学记录,也就越接近于这种渴望已久的透明性。
这听起来像是,桑塔格通过医学语言为病人们提供了一种专属于他们的表现疾病的方式:一种完全中立、不带观点的语言来描述疾病。在这种解读下(桑塔格便是被如此解读的),这样的观点很难有吸引力。毕竟,实验室和诊所并非虚幻的场所。疾病总是与人相关的,它对患者来讲是真真切切在“此处”发生的事情,或对他者而言是发生在“彼处”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德和博伊尔是在指责桑塔格对隐喻的反对忽视了疾病始终是一种个人事件,而不仅仅是医学事件。

不过,桑塔格的文章值得更细致的解读。她对隐喻的怀疑并不是要求一种剥离了个体性和倾向性的语言。准确地说,她怀疑的是幻想。她认为,我们关于疾病的语言应当起到提防幻想的作用,而非引发幻想。隐喻并不能做到这一点。隐喻的内容是可塑的、开放性的,并且难以给出确切的说明。当一个隐喻“看上去是对的”时,往往说不清这是为什么。隐喻以一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方式,重构了我们的思维。
《疾病的隐喻》既非不加评判的医者宣言,也非指导我们如何客观表达的说明书。隐喻可以被用来重构有生命的身体,但当我们这样使用隐喻时,这种重构有陷入“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风险。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其他选择?还是说生存的意志总会陷入某种形式的幻想?
桑塔格自己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1975年,当桑塔格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她的医生都很悲观。医生告诉她,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她一气之下离开美国前往法国,尝试一种在美国没有的激进化疗方案。她挺了过来,却又两次被诊断出患有癌症。70岁时,她得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诊断:白血病。一年后的2004年,桑塔格去世。
2008年,桑塔格的儿子出版了一部描述她生命最后岁月的回忆录。他写道:“我的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是那种对于真理抱有绝对渴望的人。确诊后,她依然保有这种渴望,但她渴望的是生命,而非真理。”正如她的儿子所记录下的,她对于生命的渴望,体现在她对治疗抱着一种勉强且强横的乐观态度。“为了让她相信自己会被治愈,我的母亲需要相信,她所深爱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桑塔格的一生展现了以真理为上的价值观念有着怎样的局限性。剥离了幻想的生命可能无法生存,而当面对死亡时,最平实的语言也能成为幻想的载体。最后一课是最难学习的:幻想与真理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很模糊。如果桑塔格像她的医生预测的那样,在1975年便因为癌症去世,那么她可能从一开始就像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

2013年,当我第一次读到桑塔格的文章时,我患有严重的疑病症。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恐惧,并持续了近十年。我担心最多的是癌症。我怀着近乎痴狂的心情,想象着肿瘤在我的乳房和肠道中生长。当然,阅读桑塔格的文章并不能治愈我的疑病症,但确实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桑塔格关注的是,那些因为疾病被赋予过多意义而遭受痛苦的人们。我一直都很痛苦,因为我没意识到自己对于疾病的执迷,其实是对于疾病所代表的东西的执迷。桑塔格反对对疾病的阐释,但阐释正是我所需要的:只有当我发现疾病有意义时,我才能明白我可能并不是真的生病了。
2020年3月,当疫情在英国蔓延时,我的疑病症又复发了。但这一次,我并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担心自己可能会染上新冠病毒。
对于癌症和结核病幻想的关键在于,两者从来都不是一种集体经验。而新冠肺炎不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得这种病,但我们都共同经历着这场疫情。因此,它所带来的幻想不是个人化的(不是所谓“易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格类型”),而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且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正如桑塔格在文章末尾所详细论述的那样,政治上对疾病的使用,通常是将内乱与疾病进行类比,或是将持不同政见者视作政治体中的“毒瘤”。但近来对于新冠病毒的想象有所不同。对于右翼来说,新冠病毒是一个被过度炒作的精英阴谋,是以自由之名需要与之斗争的又一股力量。对于中立群体来说,新冠病毒让人联想到的不是内乱,而是我们都必须经历的一场集体试验,病毒也许能把我们团结到新的国家、州、城市的共同体中。而在左派言论中,疫情导致了政治的破裂,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它告诉我们,我们习以为常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梦魇;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到这种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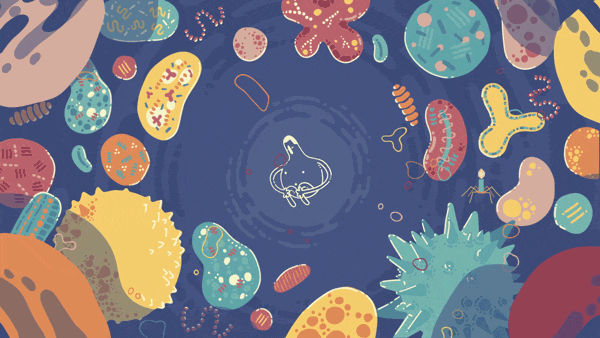
不过,为我们提供了应对近来新冠幻想的最佳指引的,也许是灾难片而非隐喻。灾难电影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它提出了有关证实(vindication)的认识论问题:灾难电影的一个常见套路是,有人察觉到灾难即将来临,但当他们试图提醒别人时,别人会觉得他们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正如天灾一样,一场危机常常被视作一个会揭露出此前隐藏着的真相的事件:对左翼而言,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与虚伪;对中立群体而言,是不应该因为身份政治而分裂的群体团结。新冠幻想借用了灾难电影的“证实认识论”(vindicatory epistemology):无论我以前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都被疫情给证实了。这种幻想最好斗的版本是,认为这场危机应当而且必须说服其他人,我们是正确的。这似乎证明,世界末日也有好的一面:它至少意味着人们不再争论。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关于证实的幻想呢?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是:抵制并揭露它们,就像桑塔格对待疾病的隐喻那样对待这些幻觉。这种方式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一个更艰难的解决方式回到了桑塔格身上,在面对死亡时,她最终被迫陷入自己对疾病的幻想:我也能挺过这次癌症。生命促成了一条奇怪的规则:人们向死而生,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有对未来注定的死亡采取某种反抗,就很难好好地生活下去,而是踟蹰于虚无主义的悲慨,或是不问前路的愚勇。
民主政治也有着类似的结构:它需要一场永不停歇、难断胜负的争论。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若非毅然坚守着这样一种幻想,认为只要我们足够善辩,虽不能骗过死神,却足以弥合分歧,那么我们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很好地与人争辩。我们需要相信自己的论证会起作用,我们的对手将会(或至少可能)甘愿屈从于我们语言的力量。为了忍受争论,我们需要幻想着,争论总有一天会结束。
作者:Rachel Fraser | 封面:Rebekka Dunlap
翻译:三木 | 审校:汉那 | 编辑:杨银烛
原文:https://thepointmag.com/criticism/illness-as-fanta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