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民粹主义怨恨情绪扰乱了美国政治,其核心是对于工作的不满。不过,这些不满不仅仅源于丢掉工作和工资增长的停滞。“工作”既关乎经济,也关乎文化。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们不仅仅在别人享受成功之时陷入挣扎,他们同时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不再获得社会认可。
二战结束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仍有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支撑全家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今天,此情此景已经很难见到。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异(经济学家称之为“高等教育溢价”)已经翻了一番。
全球化给文凭的拥有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在这场以成绩定优劣的竞赛中胜出。但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全球化却没有带来任何助益。生产力提高了,但劳动人民从他们生产的产品中获得的回报份额却越来越小。尽管自1979年以来,美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85%,但对于那些没有四年制本科学位的白人男子,他们今天的实际收入比1979年时更少。
绩优主义(meritocratic)的时代还导致了一种更隐蔽的伤害:工作的尊严受到侵蚀。认可那些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进入大学的人,也就在暗中贬低了那些没有学历证书的人。这种规则像是在说,低学历者所做的工作,既然在市场上的价值不及专业人士,那么对公共利益(common good)的贡献也就更小。
有两种相关联的趋势,共同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待“什么人配得上什么”的观念:趋势之一是以成绩定高下,这使得近几十年来,四年制大学学位几乎已经成为把握机遇的入场券,成为出人头地不可或缺的条件。趋势之二则是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主流政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接纳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市场导向的全球化。在全球化产生了大规模不平等的同时,上述两种观点(绩优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损害了工作的尊严,加剧了劳动人民对精英的不满,同时也引发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弹。

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
迈克尔·杨在20世纪50年代末创造了“绩优主义”一词,并把它当成贬义词使用。他在40年后观察到:“在一个大肆宣扬成绩(merit)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被评判为完全没有成绩,会让这个人非常难受。下层阶级像今天这样在道德上无可遮羞,这在历史上前所未见。”
2016年,没有大学学位的工薪阶层男子以压倒性优势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他们被特朗普这种愤懑的政治立场所吸引,这表明激怒他们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困难。主流分析家和政治家震惊于特朗普的当选,其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对精英阶层居高临下的常态视而不见。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绩优主义和市场导向的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导致的,但在美国人生活的角角落落也都有体现。
电视情景喜剧中的工人阶级父亲角色大多又无能又愚蠢、形如小丑,如《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中的阿奇·邦克和《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的霍默·辛普森。旧金山黑斯廷斯法学院的教授琼·威廉姆斯将矛头指向了她所说的进步人士中的“阶级无知”( class cluelessness)现象。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2016年出版了《故土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书中为工人阶级遭遇的不满提供了发声渠道:“你没法从别人对你的看法中感受到对自己的认可。你为了让自己能被看到、被尊重而费尽力气。”

为了对工人阶级面临的挫败感做出回应,首先都必须扭转居高临下的态度,与“学位证书定高下”的偏见作斗争。然后还必须把维护工作的尊严置于政治议程的中心。一旦对工作的意义进行思考,将迫使美国人民直面我们往往回避了的道德和政治议题:什么才算得上是对公共利益有所贡献?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负有什么责任?
要讨论工作的尊严,我们必须提出以下疑问:市场工资是否真正衡量了各种工作的社会价值?根据消费主义的共同利益概念,答案是肯定的。这一概念为经济政策制定者所熟悉,将共同利益定义为各人的偏好和利益的总和。以这种观点,我们通过最大化消费者的福祉来实现共同利益,实现之道一般来说便是去追求最快的经济增长。如果共同利益仅仅在于满足消费者的偏好,那么市场工资就对“谁做出了多少贡献”提供了一个好的衡量。那些挣钱最多的人很可能就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因为他们生产了消费者想要的商品和服务。
但这并不是考虑共同利益的唯一方法。一种被称为“公民观念”(civic conception)的观点反对这种消费主义的概念。根据这种观念,共同利益不是简单地将偏好相加或使消费者的福祉最大化。它也无法单靠经济活动来实现。它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偏好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与其他人一起商讨如何去实现一个公正良好的社会。
公民观念还提出了一种特别的思考工作的方式:具体而言,我们在经济中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不是作为消费者,而是作为生产方。正是作为生产者,我们累积并运用自身能力,提供商品和服务来满足其他人的需求,并赢得社会的尊重。各人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通过所获工资高低来衡量;它取决于,我们努力所服务的目的在道德层面有多重要,对公民社会有多要紧。

在电视剧《绝命毒师》里,主角沃尔特·怀特从一个高中化学老师摇身一变成为冰毒大亨。当怀特放弃课堂,拿一身本事来制备他那备受认可的冰毒品种时,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他教化学时的那点工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冰毒要比在高中教书对社会的贡献更有价值。谁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最大,不是由市场说了算。它要求我们通过民主的公民辩论来作出道德判断。新冠疫情之下,许多美国人对“谁的贡献最重要”已经有了新看法。但是这段时间里,我们所仰赖的那些“必要工种”从事者,却是社会报酬最低的那些人。
经济政策以消费为中心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要跳脱出此窠臼相当困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宣称:“消费是所有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和宗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样表达过类似想法。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也都表示赞同。但更古老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脉络却有不同的见解。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繁荣取决于通过培养并运用我们的能力,从而实现我们的自然本性。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认为,某些职业能让公民培养出赋予其自治能力的美德:先是农业,接着是工匠劳动,然后是宽泛意义上的自由劳动。
到了二十世纪,共和主义传统的生产者伦理逐渐让位于消费主义的自由观念,让位于关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但认为“工作将公民凝聚在一个作出贡献并相互承认的网络中”,这样的想法并没有消失。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对罢工的环卫工人发表讲话时就援引了这一观点。那时距离他被刺不过几个小时,他说:“归根到底,给我们收垃圾的人与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人做他的工作,疾病就会猖獗。每一种劳动都有其尊严”。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丁·路德·金,再到天主教的社会观念都认为,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赢得同胞的尊重时,我们才是最完整的人。这种观念认为,我们所最为渴望的,是被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所需要。工作的尊严在于运用我们的能力来回应他人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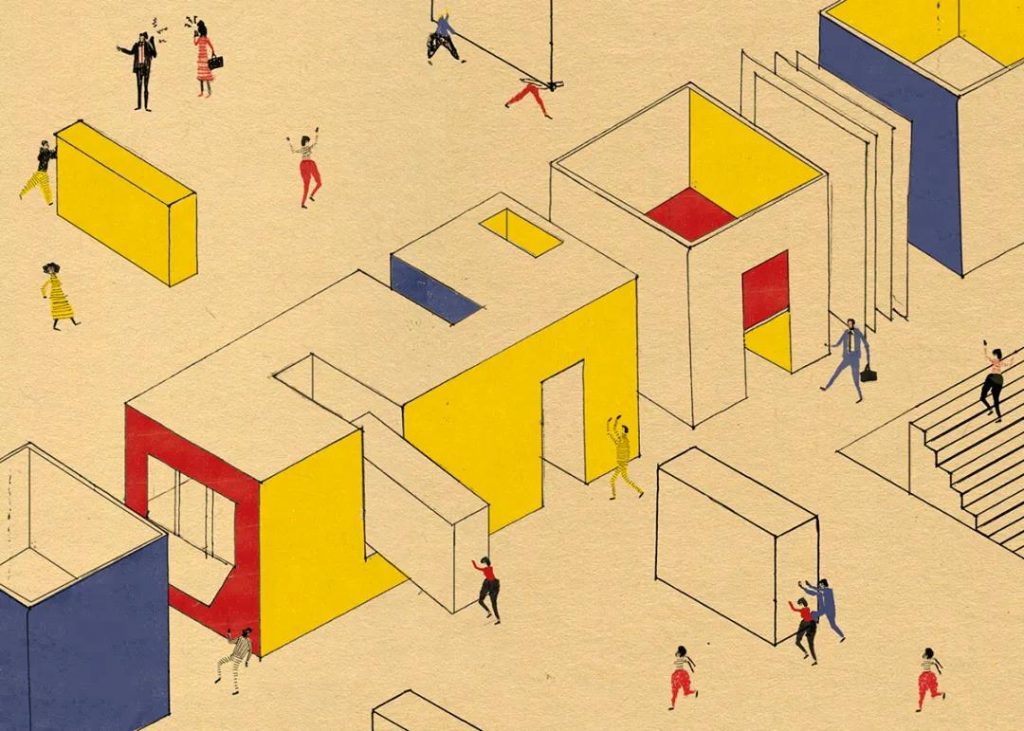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仅仅关注GDP的规模和分配的政治经济学破坏了工作的尊严,且使公民生活变得贫乏。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就明白这一点:“伙伴情谊、社区、共同的爱国主义,这些是我们文明的基本价值,光是一起购买和消费商品,支撑不了这些价值。”他继续阐述道,“这些价值的来源在于工作,那种能让人自豪地说‘这个国家的建设有我的功劳,我是国家伟大公共事业的参与者’的工作。”
今天很少有政治家会说这样的话。进步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围绕社区、爱国主义和工作尊严所构建的政治话语,转而提供一套关于上升的华丽辞藻。对于那些担心工资停滞不前、岗位外包、不平等、害怕工作被移民和机器人抢走的人,在位的精英们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建议:去上大学。让自己具备能力以应对全球化经济时代竞争,并从中争取胜利。你学了多少,就能挣多少。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这种理想主义,适合的是以成绩说话、由市场驱动的时代。它奉承赢家,侮辱输家。2016年大选尘埃落定,这种理想主义到了头。
表面上看,强调工作的尊严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想法。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它被用作支持标准政治立场的修辞。在右派中,有人将工作的尊严作为削减福利的论据,认为福利使得好吃懒做之人的生活更加艰难,主张要让这些人减少依赖。唐纳德·特朗普的农业部长桑尼·珀杜明确指出了这种联系,声称减少食品券的分发“帮我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重拾了工作的尊严”。而在自由派那边,他们试图促进分配正义——即,使得众人能更公平、更充分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算是对于政策制定素来过度关注GDP的一种修正。
但是许多劳动者更想要的是更大程度的贡献性正义——通过生产别人需要和重视之物,从而拥有机会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在我们这个观点两极分化严重的时代,当大量劳动者感到被忽视、不受重视时,当我们迫切为社会团结和凝聚力寻找一个源泉时,对工作尊严加以更有力的肯定,似乎理所当然应出现于主流政治话语之中。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一项政治方针,如果真的把贡献性正义当一回事,便会提出一些自由派和保守派听了都不舒服的问题。它将挑战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化的支持者所广泛认同的一项前提:市场的成果真实反映了人们所作贡献的社会价值。上述议程要求人们去公开辩论,什么才是对公共利益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以及市场的裁决在何处有失偏颇。这种对话不会很容易,因为何为共同利益并无定论。但是重提工作尊严,能削弱我们党派立场上的自以为是,并从道德角度去丰富公共讨论的内容。现在,随着疫情封锁将聚光灯照在各地原本“不被看见”的必要工种身上,进行上述辩论正是时候。
作为例证,试想以下两个版本的政治议程,一个保守,另一个进步。考虑为了确认它们,分别需要对市场主导之结果提出多少挑战。第一个版本来自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2012年竞选总统期间的政策顾问。在《昨日与明日的工人》(Once and Future Worker)一书中,奥伦·卡斯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应对特朗普加以利用但未能缓解的不满情绪。卡斯认为,为了在美国国内支持工作的尊严,共和党人要放弃他们对自由市场那种传统式的拥护。共和党人不应该为了提高GDP而推动企业减税、支持不加限制的自由贸易,而是应该把政策重点落在帮助劳动者找到薪酬足以支撑起家庭和社区发展的工作。卡斯认为,要建设良序社会,这比经济增长更重要。
他提出的政策之一是为低收入工人提供工资补贴——这可不是共和党一贯的思路。做法是,政府将根据时薪目标,为低收入雇员每个小时的工资收入都提供一笔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工资补贴是把工资税颠倒过来。政府不是从劳动收入中扣钱,而是增加一定数额。这里的机制或许是基于分配的,但这么做的道理却牢牢扎根于贡献性正义的理念。
新冠疫情迫使一些欧洲国家暂停了其经济活动,而这些国家此时颁布了工资补贴提案,其用意就很清楚了。英国、丹麦和荷兰没有像美国政府那样为被解雇者提供失业保险,而是替留用职工的公司支付原本工资的75%到90%。这样,在让雇主能够继续给职工发工资的同时,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来肯定劳动者的价值和工作的尊严。而美国的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雇员的金钱损失,但也只是仅此而已。
重塑工作尊严的第二种方法是强调金融业不断上升的角色,这更有可能引起政治进步人士的共鸣。在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金融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几乎增加了两倍。2008年,金融在全国企业利润中的份额超过了三成。其从业者的收入相比能力相仿的其他行业从业者高出70%。如果所有这些金融活动都是有用的,促进了经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那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估计,在英美等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5%的资金流入了新的生产性企业,其他都被用于既有资产的投机、购买花哨的衍生品。市场回报的多少和对公共利益实际贡献的高低有时离得很远,而金融业的兴起也许是当代经济中关于这点最清楚的例证。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金融业受到了公众极大的关注。随之而来的辩论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用纳税人的钱替公司纾困应符合何种条件,二是如何对华尔街进行改革。这场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现代金融的道德意涵和对公民社会的影响。政治方针若意图认可工作之尊严,将利用税收手段,通过阻止投机、尊重生产性劳动来打造一个鼓励自尊经济体。激进一点的方法是削减甚至取消工资税,并通过对消费、财富和金融交易征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稍微温和的做法是减少工资税,并通过对高频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来弥补损失的财收,因为高频交易对实体经济无甚贡献。
同样,这里的作用机制关乎分配,但这么做的道理和传达的信息在于贡献。税收不仅是保证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也是表达社会价值取向的一种方式。税收政策的道德层面为人们所熟悉。我们通常争论税收是否公平——这种税那种税更多会落在富人还是穷人的头上。但税收所传达的意义超越了公平层面的辩论,税收意味着社会做出了道德判断:哪些活动值得尊敬和认可,而哪些活动应该被阻止。
我所引述的这些提议,本身并非解决方案,而是抛砖引玉,看看把话锋转向工作的贡献与伦理会带来什么成果,看看把工作视为获取社会认可的舞台的这种思路如何。为了重塑工作的尊严,我们需要应对经济现状背后的道德问题:除了什么类型的工作值得认可和尊重,还有我们作为公民对彼此负有何种责任。这两者相互关联。如果不仔细考虑我们团体生活中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就无法确定什么算是值得肯定的贡献。而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看作社会的一员,并意识到自己受其恩惠,就不可能思考清楚共有的意义和目标。有了这种亏欠感,才会有“我们同舟共济”这样的说法——不是作为面对危机时一种仪式性的咒语,而是作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原则。
*编辑注:本文摘自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新书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作者:Michael J. Sandel | 译者:mameko
封面:Olivier Bonhomme | 校对:陈小树 | 编辑:陈小树、杨银烛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