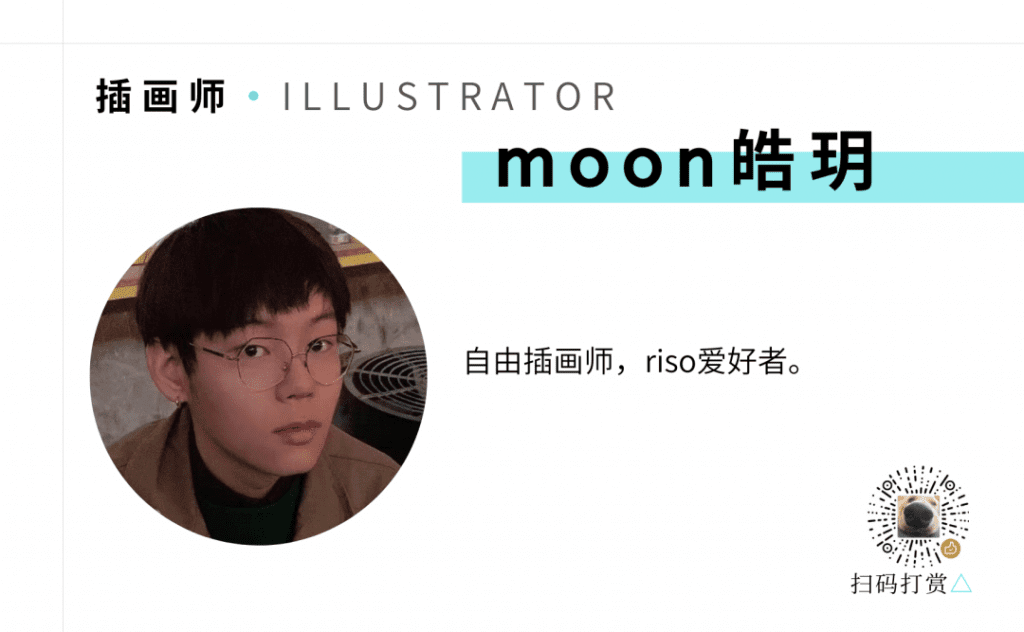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是什么样的关系?你可能会疑惑,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明显,为什么需要放到这里来讨论?我们的身体当然从属于我们大脑,受大脑的支配行动。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这个回答毋庸置疑,是因为这和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体验都是相符合的。大脑在日常生活中就像控制中心,对我们的身体发出指令,让我们做出各种行为。在生活中,我们会有“行尸走肉”这样的形容词,就是在说,倘若没有了大脑的指令,没有了“灵魂”,我们的身体就不知为何行动。大脑作为我们身体的主宰,告诉我们饿了要吃东西,不开心了要吃东西,开心了更要吃点好吃的奖励自己(毫无破绽)。
但是,如果我接着问:你觉得你的大脑是独立的个体吗?大脑的所有感觉、认知、决策都是由大脑自己完成、不受外界干扰的吗?
你可能会开始犹豫。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想要相信大脑是这样一个独立的、不受干扰的决策者。这样的想法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就已萌芽。在17世纪,著名数学家、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之一的笛卡尔就提出了著名的心身二元论。“我思故我在”这一经典语句就来自于他。在他的理论中,“思”、“心”其实都指的是英文中的“mind”,对应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与思考。笛卡尔认为,大脑的认知和身体有着非常本质的不同,并且认知和身体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大脑的认知是不受身体在物理世界的运动所影响,是独立存在的。

另一方面,和笛卡尔不同的另外一股思潮在近代科学界(尤其是认知科学界)涌动:大脑可能不是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唯一的、独立的决策者。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并不局限于内部的大脑皮层活动,也可以被外界的、物理的、世界的经历所影响。
这一理论在认知科学界被称为embodied cognition,中文大多将其译为具身认知或体化认知。其实“embodied”这个词还没有统一的译法,而笔者比较偏向“具身”一词,原因在于对”embodied“这个词本身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隐约看出“body”的影子,通俗来说就是“在身体里的,和身体相关的”。但是,不止于此。在身体这一基础上,它还表示了我们处于具体的物理世界的身体,和我们的抽象的认知之间的复杂且紧密的联系*。在具身认知的概念框架下,我们的很多认知、乃至一些重要的决策,不仅仅主动地对我们在物理世界的活动产生影响,并且也被动地被我们在物理世界的动作所影响。其影响范围涵盖之广,小到一种情绪,大到一种语言的习得和理解,乃至一个领域的发展。
*作者注: 具身认知有时非常难以界定和理解,就是因为它既非只强调身体而无视心理的一元论,也不像之前笛卡尔主张的身心分离二元论。笔者认为具身认知理论的本质,是在说一种处以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中互相融合的状态。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具身认知在意的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而是鸡和蛋直接的关系:鸡的行为如何影响蛋,而蛋又如何影响鸡。
具身认知是当前最为激动人心的前沿话题之一,但它其实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关于这个领域是否真的存在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具身认知其实并不新鲜,只是另一个可以影响认知的因素而已,只属于认知领域很小的一部分。相信具身认知力量的学者们则认为,身体感受对于认知的影响非常特殊,应该区别于其他因素的存在。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具身认知领域的实验结果还不够统一,无法在现有证据基础上宣称具身认知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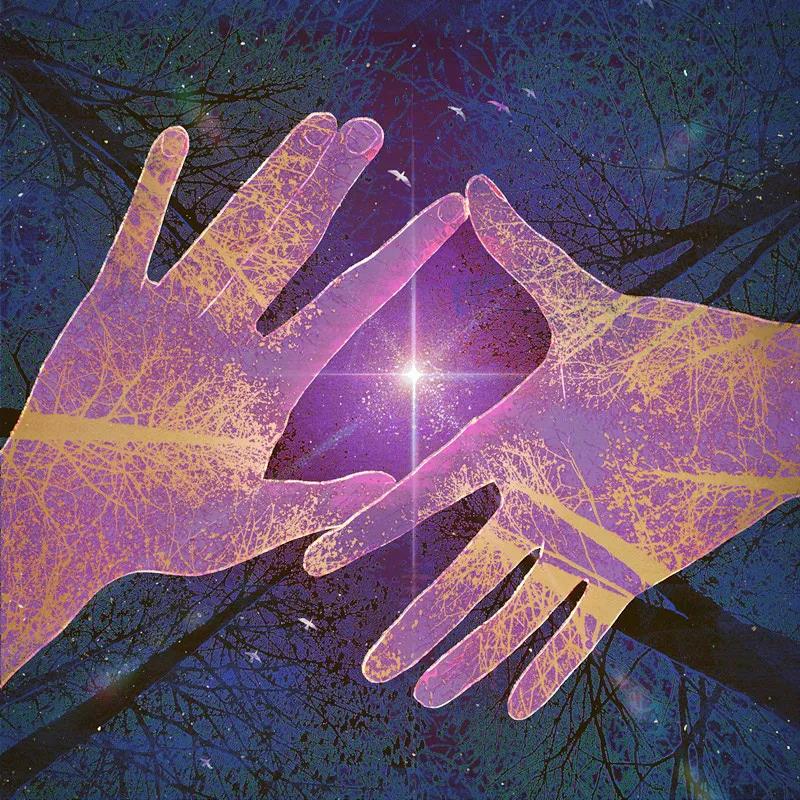
具身认知到底有何神奇之处,以至于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让我们暂且从语言、情绪和学习出发,一窥这个领域的魅力。
语言的具身化
人类语言本身就具有具身化的成分。其中,最为典型、被文献讨论最多的,就是我们语言中所运用的比喻,尤其是隐喻。
在认知语言学看来,隐喻具有普遍性,隐喻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重要的、基本的方式之一。例如,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作者提到了所谓的“方位隐喻”。方位隐喻很多时候是基于人的身体体验,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下共同存在。比如说,好的经常是在上方的、是高的;差的经常是在下方的、是低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英语中有“I’m feeling up/down today”,在中文里有“我今天情绪感觉很高昂/低落”。再比如说,已经决定了的、已知的事情是在下方的,而未决定的事情、未知的事情是在上方的。例如“Things are up in the air / Things are settled”,“事情还悬而未决/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在这些语句表达中,我们的隐喻都含有一种我们在物理世界中的体验基础。并且只有有了这样的体验基础,我们的隐喻才会被理解。所以方位隐喻的存在本身,就和我们的身体与这个物理世界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连接。
试着想象这样一个世界:0分是最高的分数,任何高于0分的分数,越高证明它越差。在这个世界里,你很可能就不会再说“好的是在上方的”了!你想要表达开心时可能会说:“我今天感觉很低落呢!”这听上去或许很荒谬。但是,你感受到的这种荒谬的认知,其实也来自对这个物理世界和语言世界日积月累的感受。如果你从小就生活在这种假想中的世界,便完全不会觉得用“下方表示好/上方表示差”这样的隐喻有什么问题了。

正如浙江大学哲学教授李恒威所说:“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概念意义的获得和概念体系的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发生的过程看,它们源于人们最初的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身体经验被用于抽象概念是司空见惯的,如Affection Is Warmth,Important Is Big,Happy Is Up,Intimacy Is Closeness……隐喻投射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人类的身体经验本身是直接的、有意义的结构。”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运用,都是来自于身体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并且,这种感受甚至不单单限于个体,它早就在时代的长河中,通过一代代人在物理世界中的积累,作用于我们的文化、语言和认知中。
情绪的具身化
情绪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存在,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是情绪的主人。这和我们想要掌控情绪有很大关系。我们都不希望情绪可以被大脑这个掌控中心,或者说个人意志以外的东西所影响。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倾向于认为,我们的身体从属于我们大脑,完全受大脑的支配行动。
然而,关于情绪的具身化研究表明,情绪是会被身体运动、身体感知所影响的;并且,这个情绪可以不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说,你对一个身体运动的感知可以影响你在意识层面觉得毫无关联的情绪。理论和研究表示,我们对于情绪的感知和处理,由体内激素对身体的影响、知觉以及重新体验情绪的活动过程共同构成。
这其实也不完全是非常叛逆的想法,早在1988年,就已经有了关于控制面部表情影响情绪认知的实验。在2007年《科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里,作者也指出可以通过控制人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来改变其对于情绪的处理和感知。实验表明,人们的面部表情会影响人们对于事物有趣度的情绪认知。在实验中,被试需要用嘴巴横着含住一支笔并观看动画片。当被试横着含笔时,嘴巴会自然做出微笑的表情,而当被试竖着含笔时,会做出严肃嘟嘴的表情(下图)。和竖着含笔相比,当被试横着含笔做出微笑的表情时,评估动画片时会认为它更加有趣。同样地,当被试含着笔看一篇文章时,在横着含笔(微笑表情)时,被试阅读理解快乐事件的句子,要比竖着含笔所花的时间更少。仿佛当你的面部表情在微笑的时候,你会更容易理解快乐的情绪。同样的实验结果如使用微小电流改变人们表情等也在其他方法中被发现。

需要注意,具身认知的一些实验确实在学术界具有争议性,很大一部分原因和可重复性危机有关——并非所有实验都能在反复试验后得到相同结果,读者诸君还需谨慎判断。
衍生一点说,我们的身体在物理世界的经历,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对其他事物的认知,有的时候这种影响可以来自于完全被动的、非自主意识的身体行为与动作。在这些具身认知对于情绪影响的实验里,人们的动作都并非自发动作,也就是说大脑并没有对人们的任意动作都进行指令,而是来自于实验的要求。并且实验并没有告诉人们,去微笑或者去嘟嘴,而是用一个含住笔的动作指令,让人做出了相应的情绪相关的动作。人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会有意识地觉得“我在微笑”或者“我在嘟嘴”,而仅仅是这样的肌肉动作,让人们的情绪和认知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其实这方面的实验还有更多,甚至包括如何通过这一理论帮助治疗抑郁症的实验。但是由于笔者之前提到的有些实验具有极大争议,本文在这里选择不对这方面的实验做过多的讨论,而是把接下来的时间放在讨论广受认可的实验发现里*。
*作者注: 这不代表笔者立场赞同或否定这些实验发现,而是希望大家用更科学批判的眼光去看这些实验发现。
学习的具身化
除了情绪之外,具身认知也可以对学习、认知、信息处理过程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认识到具身认知的作用,还可以在一些抽象领域更好地学习。也就是说,身体动作也可以有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学习新知识。在这里,有一个在整个领域看来都比较冒险且前卫的假设:我们的大脑可能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一个解决问题的认知资源(Wilson&Golonka, 2013)。我们的身体在这个物理世界中的运动和体验也可以作为一种认知资源和工具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甚至,身体的运动可以替代很多复杂困难的心理表征(也就是说,原本我们需要把很多东西同时保留在我们的大脑里,进行复杂的运算、推理、改变,但现在其中一部分,可以由我们的身体运动代劳,从而达到同样的解决问题的效果)。
比如说,Thomas和Lleras在一个实验中发现,在解决怎么把两根距离很远的绳子挤在一次的问题的过程中,被测者被要求在解决问题的过程用手臂做出一个指定的动作。当被测者被要求做的那个身体动作,和问题解决的突破口相关时,他们会比那些被要求做不相关的身体动作的被测者,要更容易找到问题的突破口并解决问题。这个实验证明了我们的身体运动可以对问题解决带来帮助,也表明了利用身体的动作来帮助人类进行抽象学习的可能性。身体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本身需要在大脑里抽象推理、演绎的过程,把这种过程具体化地展现,降低了人们的认知负荷,并且给解决问题带来了新的资源。

提到抽象领域的学习,不得不提数学。数学这个科目本身的诞生,和我们与物理世界的经历息息相关。在对数学是发现还是发明的争论中,有很多人提到公理是被发现的,然而数学的符号是人类发明的。每个文化根据自己在物理世界不同的需求,有了不同的发明和习惯。如我们在开头提到过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思想。有趣的是,早在笛卡尔身处的17世纪,哲学和数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笛卡尔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也就是数学的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哲学思考。而他本人也在数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解析几何的诞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研究人员(Martha Alibali和Mitchell Nathan)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数学在众多学科中尤为具身的两个原因:1)数学是基于我们的感知和行为的;2)数学的基础来源于我们的物理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数学这个科目尤其受益于具身化的教育和学习方式。
提到数学科目的具身化教育与学习,一个关键的概念是手势在数学学习中的重要性。许多关于手势的研究,尤其是手势在数学和统计学领域的研究,展现出了具身认知通过身体运动把抽象概念具体化所展现的作用。在文献中,手势其实分为很多种分类,从它的产生来分,有自发性的、非自发性的;从它的用途来分,又可以分为指向性手势、标志性手势、和比喻性手势。对于具身认知而言,我们更多要在意的是非自发性的手势。因为如果手势是非自发的,是被指令去做的,那更可以说明是我们的手部动作,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并且可以对于我们的利用具身认知进行教学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手势学习领域的泰斗级人物Susan Goldin-Meadow和她的同事在一个实验中,给孩子先读了一系列的数学问题,然后教他们要么做和问题的解决方法相关的手势,或者做和问题的解决方法完全没有关系的手势。她们通过这个实验发现,比起那些做了和问题解决方法无关的手势的孩子们,那些被要求做了和问题解决方法相关手势的学生表现更加突出。那些做了和解决问题相关手势的学生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学到了更多关于如何解决这些数学问题的方法,并且解决问题的表现更加优异。同样的,研究发现,当要求被测者把手和胳膊放在指定位置后,比起那些放在无意义位置的被测者们,如果被测者们被要求把手臂放在,和之后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关的位置,他们在之后的数学问题解决过程中,更加容易找到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之后,在我自己的实验中——我们在学习统计的领域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在实验中,被测者们在看一个关于统计学的视频过程中,视频中会出现红色的方块。被测者需要在看到红色方块的时候,把手放在对应的地方。红色的方块所指引的手部活动要么和视频中的统计概念是相关的,要么和统计中的视频观念无关,并且和相关的运动相反的运动。也就是说,被测者们一边看着视频,一边进行着和视频内容相关或无关的手部运动。在整个过程中,被测者是不知道自己的手部运动和他们正在学习的视频内容是相关的。他们被告知,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多线操作的实验来检测能够同时处理两件不同事情的能力。实验发现,如果被测者在看视频的过程中,被要求做了和视频内容相关的手部运动,他们的表现会比那些 1)没有做任何手部运动;2)做了和视频内容不相关,甚至是相反的手部运动的人更加优异。
这些关于手势的实验都为利用手势,乃至具身认知帮助人们学习抽象的概念带来了令人激动的前景。这些实验从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我们过去百年对于大脑的理解:大脑是人类解决问题的唯一认知资源。现在这些实验证明,我们至少有可能通过身体在物理世界的运动和感受解决问题。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你觉得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参考文献
1.Brooks, N., & Goldin-Meadow, S. (2016). Moving to Learn: How Guiding the Hands Can Set the Stage for Learning. Cognitive science, 40(7), 1831–1849. https://doi.org/10.1111/cogs.12292
2.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guest-blog/a-brief-guide-to-embodied-cognition-why-you-are-not-your-brain/
3.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13.00058/full
4.https://4think.net/你的身體如何影響了你的「思考」?/
5.https://pansci.asia/archives/47236
6.https://nyshalong.com/public/archive/20150131/20150131_ref.pdf
7.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486&do=blog&id=255602
8.Martha W. Alibali & Mitchell J. Nathan (2012) Embodiment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vidence From Learners’ and Teachers’ Gestures,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21:2, 247-286, DOI: 10.1080/10508406.2011.611446
9.Nathan, M. J., Walkington, C., Boncoddo, R., Pier, E. L., Williams, C. C., & Alibali, M. W. (2014). Actions speak louder with words: The roles of action and pedagogical language for grounding mathematical pro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33, 182–193.
10.Niedenthal,2007 https://cogsci.ucsd.edu/~coulson/Courses/200/niedenthal-science-final-2007.pdf
11.Wilson, A. D., & Golonka, S. (2013). Embodied cognition i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 Article 5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3.00058
12.Strack, F., Martin, L. L., & Stepper, S. (1988). Inhibiting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of the human smile: A nonobtrusive test of the 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5), 768–77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4.5.768
13.Thomas, L.E., Lleras, A. Swinging into thought: Directed movement guides insight in problem solving.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6, 719–723 (2009). https://doi.org/10.3758/PBR.16.4.719
14.Zhang, I., Givvin, K. B., Sipple, J. M., Son, J. Y., & Stigler, J. W. (2021). Instructed Hand Movements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of an Abstract Concept From Video. Cognitive Science, 45(2), e12940.
作者:张昀怿(Icy Zhang) | 封面:moon皓玥
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