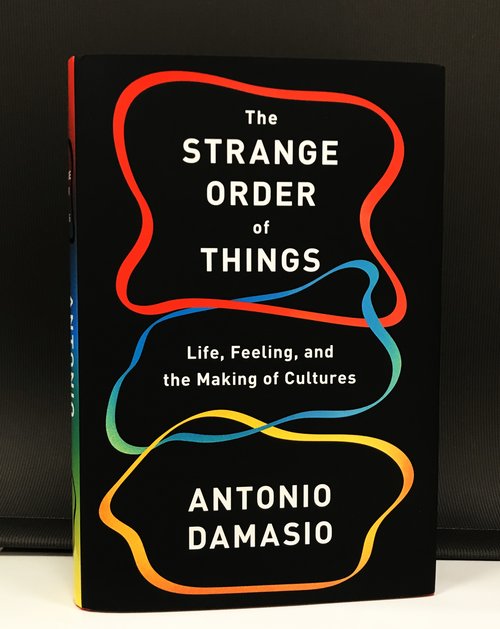
尼采会为这本错综复杂的书《事物的奇怪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而掩卷欢呼,本书既科学严谨,又兼具人道关怀,而且就尼采可以评判的范围而言,本书是革命性的。作为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的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着手研究“我们为何以及如何感受万物、表达感受、使用感受来构建我们的自我……以及大脑如何与身体相互作用来支持这些功能”。他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无形无体的炽天使,而是有思想的肉体凡胎——思想让我们变得更好。
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已经赞同头脑在“单纯”的身体之上,因此,当我们到达笛卡尔时代,人类几乎已经被视为大脑卡在棍子上(心灵囚禁在身体里)的人,像孩子手上的木马。这是达马西奥想要驳斥的人性观。对他而言,同样也是对尼采而言,身体的感觉和头脑的想法一样重要,而且,两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达马西奥坚持认为,事实上,从一开始,在最早的原始生命形式中,“情绪和感觉的世界”是驱使生物不断演化的力量,最终推动人类形成丰富的意识和创造灿烂的文化。
他告诉我们,本书阐明的观点很简单:“感觉作为人类文化繁荣的推动器、监督者和谈判者,并没有得到它们应得的荣誉。”所谓的简单,可能是作者撒下的一个小小的谎言。他陈述论点的语气是如此小心谨慎,如何客观冷静,大多数读者将跟随他的思路,点头同意。然而经过片刻的思考我们会发觉,我们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与他的前提假设是相矛盾的,并且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想要消除身体感受,让理性占上风,甚至我们可能想要消灭身体,仿佛我们是纯粹的精神存在,只不过不情愿地被束缚在百来斤的肉体上。
“感受,以及任何短暂而强烈的情绪,”达马西奥写道,“是文化会议桌上被忽视的存在”。他从细菌开始这场讨论——大多数人不会将细菌当作生物?即使在这种“没有意识的生物体中……我们也可以假设有一种只能被称为‘道德态度’的东西。”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他引证了细菌的各种行为方式,它们具有与人类社会惊人的相似性。这意味着,“人类的无意识简直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生命形态,比弗洛伊德或荣格的设想更深进一步”。达马西奥的论点是,我们不仅是从猿,而是从原始潮水潭底部的蠕虫演变而来。
整本书的关键词是“内环境稳态(homeostasis)”,他对此提供了许多定义,其中最清晰也是最早的定义是他所赞成的,他在书中用斜体将其标注了出来:内环境稳态是一种力量(这个词似乎是合理的),确保“生物体在一个有利于适应生存环境和有利于物种繁荣的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
达马西奥的著作包括《感受发生的一切》(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当自我来敲门》(Self Comes to Mind),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坚定的改革派人文主义者。他想让我们承认丰富的生活的各个维度,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他并不多愁善感。人类的状况是奋斗和维护自己相信的东西,是求胜的意志:“生命天生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反抗现状,创造未来,不管前路多么艰难。”尼采思想的阴影或光辉,再次跃然纸上。
达马西奥将斯宾诺莎也叫到了会议桌上,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斯宾诺莎的书《寻找斯宾诺莎》(Looking for Spinoza)。斯宾诺莎的重点是conatus,这是所有事情得以维持的基本力量。conatus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至关重要,它之于斯宾诺莎,正如内环境稳态之于达马西奥。
会议桌上也有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回声,他是一位受人喜爱的哲学家。达马西奥在书中讨论了一会儿詹姆斯的思想,当詹姆斯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惊叹于现代生活中所有高科技产品的复杂性时,我们仍然坐在壁炉旁边,享受着它带来的原始快感和安全感。能让詹姆斯感到欣喜的是,达马西奥过着“平淡的”生活,他准备承认我们最高级的努力是建立在非常基础的支柱之上的,例如,当他在惊奇地说:“认为肠道神经系统”——即直觉的基础——“很可能是第一个大脑,这是很有趣的。”
但是达马西奥,虽然随时准备向他的前辈和同侪致敬,却完全是忠于自己的人。《事物的奇怪秩序》来源于他的新的尝试和大胆的努力,他想要正确人类以及所有生命的真正活力和来源,其实是感觉。正如他所说的,“体弱的病人,被遗弃的爱人,受伤的战士,和追求爱情的行吟诗人,都能感觉到周围的事物。”真理是简单而深刻的;除了感觉之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