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C儿童频道有一档节目叫《美德冠军》,致力于教小观众们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在其中一集中,名叫巴里的粉眉蓝色长方形块块,因为输了足球赛而愁眉苦脸。
“我们输了。”巴里说。
“没事的呀!”卡丽说。
“都是我的错,我让对方进球了。”
“我不懂你为啥这么难过呀,忘了这茬吧!”
“我做不到!”
“为什么?这只是场比赛呀。”
“你好像没有什么同理心啊,卡丽。这意味着你要试着穿上我的鞋子(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可你的鞋子不合我的脚呀,巴里。”
按照剧情的设定,巴里其实是很有同理心(empathy)的——这意味着把你自己投射到别人的内心世界里,去感受别人所感受的。剧情会继续告诉小观众们,理解别人的感受很重要。

然而,在成年人世界中,共情的好处却并不那么明确了。尽管现在谈论共情的缺点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疫情使我们相互隔绝,意识形态斗争盛行,失控的残忍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发酵。但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错误的共情可能会对你和他人都有害处,它会导致人们变得冷漠,阻碍你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更严重的是,人们容易共情的倾向甚至可能被利用,被操纵,让人们变得好斗,残忍。所以,为了抛开共情的缺陷,我们应该用何种方式去感受呢?
“共情”这个词来源于德文词汇“Einfühlung”,创造于18世纪,可以被直译为“情感移入”。但正如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isty)的心理学家朱迪斯·哈尔(Judith Hall)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写的那样:“共情本质上是个模棱两可的词”。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理解他人的能力,或者仅仅是感到和他人有关联;而其他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他人表示担忧的道德立场。就连研究共情的学者们也未达成共识。
不过哈尔写道:“抛开概念上的不明确,大部人认为共情是——理解他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并且为其感到担心。”

而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把共情明确地定义为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去体验他人感受的这一行为。他在期刊《认知科学趋势》(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中写道:“根据以上狭义的定义来看,共情明显像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常识告诉我们,体验别人的痛苦可以激励我们去关心和帮助别人。”但是,共情也会导致一些棘手的道德困境。
为了阐释原因,保罗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主角是一位身患绝症的十岁小女孩雪莉。医生把雪莉放在等待治疗的名单中,该治疗方法可以减轻她的痛苦,并有可能延续她的生命。但这位非常聪慧活泼的小女孩得知,她可能要等待几周甚至数月才能接受治疗,这令人心碎。
想象一下这是什么感觉?这会如何影响雪莉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把她放到名单的最前面你会怎么做?

研究人员把雪莉的故事呈现给被试,以激发他们的共情,大约四分之三的人把她从名单中提前,让她能更早地接受治疗。
但是,保罗指出,这么做意味着原本在她之前的每一个孩子都要等更久的时间。这些孩子可能更需要治疗。
这就是被心理学家们称作“可辨识受害者效应(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的一个例子。当具象的受益人近在眼前,并且伸出援手可以让对方的痛苦得以缓解,人们会更愿意敞开心胸,或钱包。公益事业用一个有名有姓的孩子遭受痛苦的故事来募捐,比用数据描述1000名需要帮助的无名孩童,可能会筹得更多捐款。
20年7月,记者蒂凡尼·温(Tiffanie Wen)在BBC未来板块中写道:在新冠疫情中,该现象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陌生人的死感到麻木。现在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逐渐逼近200万,相比死亡,人们更直接感受到了个人的自由受限,因微不足道的不便而抗议封锁措施。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肉眼根本无法直击疫情期间最令人心碎的苦难。

当然,为了实现美好的愿望,用个人故事来吸引注意力无可非议。我们用“可辨识受害者效应”筹集了数十亿美元善款,但是这些资金本原本可以用在更多人身上,产生更大规模的积极效应。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尽可能多的孩子,就应该把钱花在发展中国家的驱虫项目上,这会比资助美国高昂的医疗支出,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想要为没有“可辨识受害者”的项目募捐就困难了,比如将会被全球变暖影响到的未来一代,他们都还有没有出生。
对人类来说,延展共情到抽象的陌生人身上相当困难。“oikeiōsis”这个概念最初由斯多葛学派在几千年前定义,相关理论阐明他人与我们生活的距离越远,我们的共情和亲近感越弱。想象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的图案,中心是我们自己,与之最近的圆环代表了家庭,接下来是朋友,邻居,社区,最后是国家,以此类推。
保罗提到了问题的关键:道德败坏者会利用“同情圈层”进行道德绑架,操纵我们的行为和信念。我们对这些更接近,更相似于我们的群体产生的自然共情会被人利用,从而反过来诱发我们对疏远,不相似群体的反感。

在一项研究中,本科生被试们被告知,他们隔壁房间里有一位同学,这位同学想参加数学竞赛,获胜就能得到奖金。本科生被试可以选择让这位学生的对手在考试前吃下喷火辣椒酱,影响对手的发挥。通过强调这位学生她经济困难的情况,被试给无辜对手的辣椒酱剂量会随着共情的增强而增加。
两党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都经常操弄“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利用共情和“可辨识受害者”制造政治局面。这给一些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借口,用来“抹除”特定人群,妖魔化移民的存在,甚至激起对所谓外来者的憎恶和暴力。保罗写到:在美国历史上,常常会有人大肆渲染黑人犯罪受害者的故事,在别有用心者的策动下,导致了许多针对黑人的残暴私刑。西方领导人还操纵人们的天然共情趋势来给针对平民的屠杀正名。政客们会说,如果我们在那个偏远的国家“试验”新式武器,那我们就能拯救数以万计参军“男孩们”的生命。

最后的缺点是,共情有时会导致消极的情绪效应。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曾经把共情称为“对个体的独立性的不受控破坏”。这种“破坏”尤其体现于我们观察到有人正在承受痛苦时,比如,我们爱的人。德国马普学会(Max Planck Society)的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的脑神经研究表明,当人们看到别人处于痛苦中时,他们大脑中与痛觉有关的区域会产生镜像活动。这可能是一种演化适应,帮助我们去预测和避免潜在的痛苦。
日内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奥尔加·克利梅基(Olga Klimecki)也写道:“分享快乐当然是很愉快的事情,而分享痛苦有时就会比较困难。”最坏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感到“共情压力”,这会阻止人们进一步的行动。压力还会造成冷漠,退缩,无助感,甚至对健康有害。在疫情期间,医护工作者们特别担忧“共情疲惫”问题,特别是心理健康工作人员或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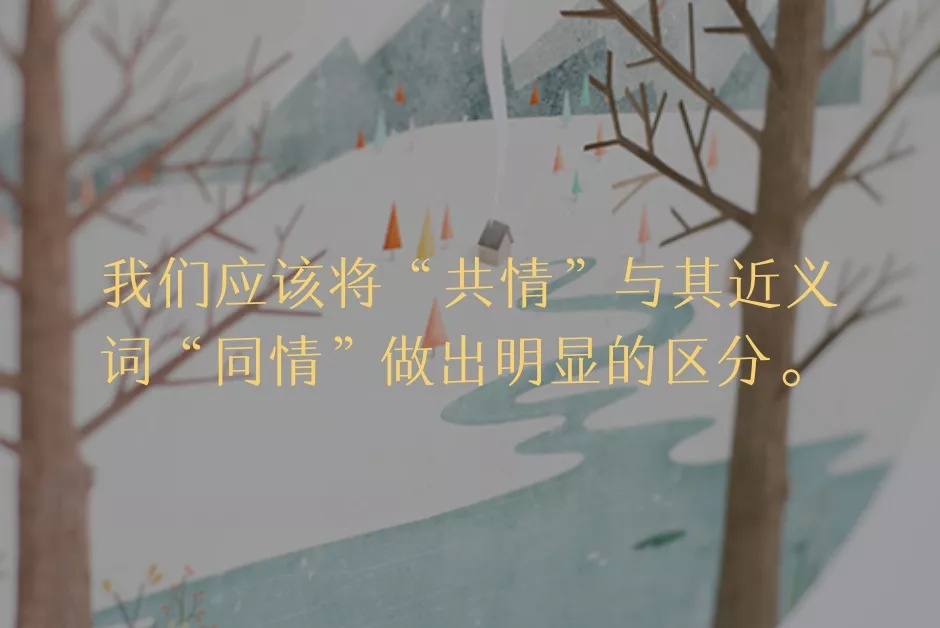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点共情都没有肯定会雪上加霜,可能会让我们离精神病态不远了。科学家们不建议我们主动地去抑制共情。有时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采取积极行动、关心帮助别人的关键性第一步。
反之,研究建议的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共情和近义词同情(compassion)在深层意义上的区别。如果共情是要去与别人感同身受,那么同情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可以理解别人的痛苦,并且愿意去帮助的感情”。有同情心,并不意味着你要和别人有一样的感受,同情更近似于给予别人关怀。
保罗用大人安慰被小狗吓到的孩子举例。是否体会到孩子的恐惧并不影响成年人去帮助孩子。他写道:“我们不必有同样的经历或者共情压力,就可以对孩子有同情心,这是一种想要帮孩子消除痛苦的愿望。”
通过扫描佛教僧人的大脑,辛格发现有可能通过简单的正念(mindfulness)训练促使人们产生更大的同情心。训练的目标是让他人产生积极和温暖的想法,而不用去过多涉及他人的体验。通过比较这种训练与其他增强共情的方法,她和同事发现,该训练会使共情压力减少,并且能增加去帮助别人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巴里的受伤情绪:他的朋友卡丽没有必要有共情地去感受巴里输了比赛的痛苦——这甚至会伤害她。但施以同情心呢?就算对方是个长方形的卡通人物,同情心也对它大有帮助。
作者:Richard Fisher | 封面:Stephan Schmitz
译者:苏木弯 | 审校:邮狸
编辑:山鸡
原文:https://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00930-can-empathy-be-bad-for-y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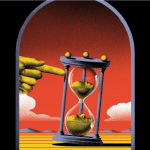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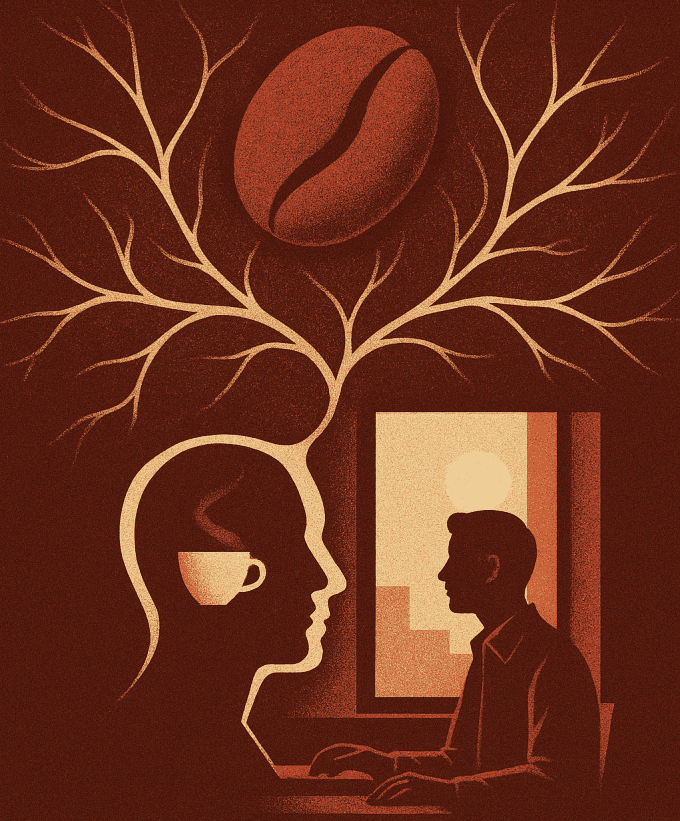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