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需要新的科学来帮助我们理解动物的意识。
穿过旧德里的人流,在中世纪集市的边缘,一座屋顶上有笼子的红色三层建筑伫立在霓虹灯照亮的摊位和狭窄小巷组成的迷宫中间,楼顶写着四个字:鸟类医院。
去年春天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医院门口脱下鞋子,走到二楼的大厅,一个20多岁的职员正在那里处理病人。一位年长的妇女把一个鞋盒放在他面前,掀开盖子,露出一只血淋淋的白色长尾鹦鹉——它遭到了猫咪袭击。排在我前面的人带着一只装在笼子里的鸽子,它撞上了金融区的一座玻璃塔。一个不到7岁的女孩从我后面进来,手里紧抓一只脖子耷拉着的白母鸡。
医院的主病房是一间40英尺长的狭窄房间,四个高大的笼子沿着墙壁放着,风扇在天花板上,其叶片周围覆盖着格栅,以免切到拍打着的翅膀。我对房间粗略视察了一番,很多笼子乍看都是空的,但靠近细看会发现有一只鸟,通常是鸽子,待在昏暗处。
医院里最年轻的兽医德赫拉吉·库马尔·辛格(Dheeraj Kumar Singh),穿着牛仔裤,戴着外科口罩,正在进行巡视检查。这里最老的兽医已经值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夜班了,还花过数万个小时从鸟类身上切除肿瘤,用药物减轻它们的疼痛,给它们服用抗生素。相比之下,辛格是个新手,但他观察鸽子的方式看起来却一点也不生疏,他用手轻快地翻转鸽子,就像摆弄手机一样熟练。我们谈话时,他向一个助手示意,助手递给他一条尼龙绷带,他将绷带在鸽子翅膀上缠了两圈,再在一声轻响中将其固定好。
鸟类医院是由耆那教信徒建造的几家医院之一。耆那教是一个古老的宗教,其最高戒律中不仅禁止对人类的暴力,也禁止对动物的暴力。医院大厅墙上的一系列绘画说明了一些信徒对这条禁令的极端尊崇。在这些绘画中,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中世纪国王透过宫殿的窗户凝视着一只接近的鸽子,它的翅膀被一只追赶中的棕鹰的爪子弄流血了。国王把这只小鸟拉进宫殿,棕鹰由于失去了一顿大餐而被激怒想要补偿,于是他把自己的手脚割下来喂它。

我由鸟类医院开始,在印度亲眼目睹了耆那教的处世道德体系。耆那教徒人数占印度人口不到1%,尽管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批评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但耆那教有时还是能获得一些权力。在13世纪,他们说服一个印度教国王改信,并颁布了印度次大陆的第一部动物福利法。有证据表明佛陀本人也受到了耆那教的影响。甘地发展出他最激进的非暴力思想,也是得益于一位耆那教朋友给了他哲学灵感。
在甘地成长的古吉拉特邦,我看到耆那僧侣在微凉的早晨为了不坐汽车而光脚行走。他们认为坐车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暴力活动,因为它会对从昆虫到大型动物的各种生灵都造成伤害。僧侣们拒绝吃块根蔬菜,以免从泥土中将它们挖出时扰乱微妙的地下生态系统。他们的白色长袍是棉质而不是丝绸的,因为丝绸会伤害到蚕。他们不在季风季节出门旅行,以避免充满微生物的水坑被踩到溅出水。早在微生物出现在西方显微镜下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于耆那教徒的假想中了。
大多数科学家同意,目前的谜团已经不是哪些动物有意识,而是哪些没有。
耆那教徒以这种温和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动物有意识,在不同程度上有着类似于人类欲望、恐惧、痛苦、悲伤和快乐的情感体验。这种认为动物有意识的观点在西方长期不受欢迎,直到最近才在研究动物认知的科学家中获得青睐,且研究的动物不局限于灵长类、狗、大象、鲸鱼等常见种类。科学家们现正在类似于外星物种的生物身上寻找意识体验的证据,这些生物在进化树上的分支离我们较远。近年来,相关报道大量出现,如一篇文章报道了一只章鱼拧开瓶盖,或将水箱中的水喷到一位博士后的脸上。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目前的谜团已经不是哪些动物有意识,而是哪些没有。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意识这么神秘。我们每一个清醒时的动作都受意识状态控制,这一感觉存在于一个充满颜色、声音和触觉的更大世界中,并被思维过滤且加诸情感。
即使在世俗时代,意识也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它被称为科学的最后一个领域,是一种超越科学推理的非物质魔法。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是世界上在这个领域最受尊敬的哲学家之一,他曾经告诉我意识可能是宇宙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和时空或能量一样。他说,它可能与量子世界的透明、不确定性或非物质有关。
这些形而上学的解释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科学家还没有对意识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知道,身体的感觉系统将外部世界的信息传送到大脑中,在那里被越来越复杂的神经层依次处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是如何被整合成一幅平滑、连续的世界图景,形成一段由流动的注意力轨迹所经历的时刻流,成为印度教哲学家所说的“见证者”。

在西方,意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件只赐给人类的神圣礼物。历史上,西方哲学家认为非人动物都是没有情感的机器。甚至在达尔文证明了我们与动物的亲缘关系后,仍有许多科学家认为意识的进化是近期才发生的。他们认为,是当我们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中分化出来后,意识之光才首次苏醒。 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在他1976年出版的《二分心智的崩塌:人类意识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一书中认为,意识是分化后才出现的。他认为,是语言的发展使我们人类进入了能够构建经验世界的深层认知状态,就像诗人维吉尔一样。
这种认为意识是近期出现的观念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开始改变,当时更多的科学家正在系统地研究地球生物的行为和大脑状态。现在每年都会有一系列新的研究论文发表,综合它们的结论,许多动物都有意识。
大约五亿年前,一些海底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军备竞赛唤醒了地球上第一个有意识的动物。第一个意识的苏醒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打开了以前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可能性。
现在来看,人类世界以外似乎存在着许多有鲜活体验的动物。科学家们值得称赞的是,他们揭示了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一新维度,哪怕只是一部分。但是他们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善待与我们共享地球的数万亿具有思想的头脑。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和大多数哲学问题一样,它将困扰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毕达哥拉斯和其他一小部分哲学家之外,古代西方哲学家并未继承思考动物意识问题这一传统。但是东方思想家长期以来被它困扰着,特别是耆那教徒,近3000年来他们一直把动物意识作为一种道德问题认真对待。
许多正统的耆那教信仰经不起科学推敲。信仰不享有通往真理的特权,不管是精神方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动物施以仁慈的文化,耆那教作为先驱深远扩展了人类的道德想象。在我看来,他们崇拜和照料动物的地方,似乎是理解当前动物意识研究前沿的好地方。
在鸟类医院,我问辛格照顾患鸟有没有给他带来麻烦。他说有一只鸟拒绝被用手喂食,甚至当他试图抓起它时会把人啄出血。他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去看那只惹人讨厌的鸟,这是一只印度乌鸦,它的羽毛乌黑,但脖子上有一圈咖啡色的羽毛。乌鸦不停地扇动一只翅膀。从附近窗户射进来的光仿佛透过百叶窗一样透过羽毛。辛格告诉我它的翅膀断了。
辛格说:“乌鸦到这里几天后,每当需要喂食时就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叫声。其他鸟类都不这样。”这并不是唯一一个鸟与人交流的例子。曾经有一只灰鹦鹉能背诵900个单词,在印度,有一些鹦鹉还曾受过背诵吠陀经文的训练。但是鸟类几乎不曾把语言符号组合成它们自己的原始句子。当然,也没有鸟宣称自己是有意识的。
这可不妙,因为哲学家倾向于把这种宣称有意识的陈述看作是另一个生物有意识的最好证据,即使在人类中也是如此。没有这一陈述,不管我盯着乌鸦的黑瞳孔看多久,希望能看到它心灵的幻象,我都不确定它是否有意识。我必须寻找间接证据。
在日本,一群乌鸦利用交通工具来打开胡桃:乌鸦在十字路口向汽车前面扔下一颗坚果,当红灯亮时,它们会俯冲下来,把压碎后裸露的果肉迅速拾起。
乌鸦拥有相对于体型来说很大的大脑,与其他动物相比,它们的神经元也很密集。神经科学家可以测量大脑活动的计算复杂性,但还没有大脑扫描能显示出关于意识的准确神经信号。因此,不能完全基于某种动物的神经解剖学而判断它是否有意识。然而,当一种动物的大脑与我们人脑非常相似时,这一方法还是有启发性的。比如灵长类动物,它们是第一类被科学界公认为有意识的动物。
哺乳动物被普遍认为是有意识的,因为它们与我们一样有相对较大的大脑体积,同时还有大脑皮层,这应该是复杂认知功能发生的地方。而鸟类没有大脑皮层。在与我们人类分开进化的3亿年间,它们的大脑进化出了不同的结构。但这其中一个结构似乎是以类似皮层的方式连接的,这说明大自然可能不只有一种方法来制造一个有意识的大脑。

尽管从进化出的无意识行为中筛选出有意识的行为是困难的,我们也可以从动物的其他行为中找到线索,工具的使用就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澳大利亚一种叫“火鹰”的猛禽有时会从森林大火中抢出一捆捆燃烧的树枝,并扔到邻近林地中以驱赶猎物。也许这意味着这些猛禽能够思考物理环境中的某些部分并创想其新用途。或许这其中也有机械记忆作用也说不定。
乌鸦是最能完成复杂工作的鸟类技术专家之一。人们早就知道它们能把木棍做成钩子,而就在去年,一种乌鸦被观察到用三个独立的棍状物体制作工具。在日本,一群乌鸦利用交通工具来打开胡桃:乌鸦在十字路口向汽车前面扔下一颗坚果,当红灯亮时,它们会俯冲下来,把压碎后裸露的果肉迅速拾起。
当我和辛格交谈时,乌鸦对我们厌倦了,又转向窗户,好像在看它模糊的映像。乌鸦科被称为“有羽毛的猿类”,2008年,它们中的一员——一只喜鹊,成为了第一只通过“镜像测试”的非哺乳动物。喜鹊的脖子上标记着一个亮点,这个地方只有在镜子里才能看到。当喜鹊看到它在镜中的映像时,它立即试图检查自己的脖子。
辛格告诉我,这只乌鸦很快会被带上楼,带到屋顶上一个放在外面的笼子里,在那里,鸟儿们有更大空间来尝试用仍然脆弱的翅膀飞翔,考虑到一片开阔的天空在鸟儿的意识中一定显得很广阔。幸运的话,它会很快恢复到野生乌鸦那般生机勃勃的状态,它们有时会在大风中像杂技演员一样玩耍,或从雪面上滑下来。(在这家医院死去的鸟儿被埋葬在德里城外的河床上,这会触动其他乌鸦,有时它们会举行葬礼,或者尸检,它们会聚集在同类的尸体周围,就像凶杀侦探在调查死因一样。)
我问辛格,当他在屋顶放生鸟儿时,会有什么感觉。他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给它们服务的。”然后他提到并非所有的鸟都会马上离开,“有些鸟会飞回来栖在我们肩膀上。”

乌鸦不会在人肩上栖息,但辛格有时会看到以前的乌鸦患者在医院附近盘旋。乌鸦能认出人的脸,所以它们可能在找他。众所周知,它们会对不喜欢的人发出恶毒的叫声,但会给它们喜爱的人送上小礼物,比如把纽扣或闪亮的玻璃碎片放在人们一定会注意到的地方,就像还愿祭品。
如果这些行为加起来能说明动物有意识,那就意味着意识要么在漫长的进化史中演化了至少两次,要么在鸟类和哺乳动物进行分开进化之前就已演化了。这两种情况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自然编排分子进入清醒大脑使之产生意识的方式可能比之前想象的更容易。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地球上,大大小小的动物都在不断地产生生动的体验,并且这些体验与我们自身有着些许联系。
参观完鸟类医院的第二天,我就乘车离开了德里,伴着来自喜马拉雅起伏山脊的亚穆纳河水,向东南方向顺流驶下。德里排出的废水把亚穆纳河的一长段染成了污黑,也因此让它成为了世界上污染最重的河流之一,沿路可见水面上漂浮着各式塑料瓶。在印度,河流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这样的污染成了一种形而上的亵渎。
在被人类科技亵渎之前,神圣的亚穆纳河中曾经活跃着数以百万计的鱼类。如今,不仅仅是亚穆纳河,地球上任何的水体都可见人类留下的痕迹。即便是海洋最深处也不能幸免——就在不久之前,人们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发现了一只购物袋。
大约在四亿六千万年前,人类与鱼类的祖先曾共享一个基因库,而后便在进化的路上分道扬镳。那之后一亿年中,我们与鸟类也渐行渐远。在这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人、鱼、鸟有亲缘关系,这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也能解释为何达尔文所描述的不断演化的世界仍迟迟未被人类集体意识完全接受。然而无法否认的是,我们的手由鳍转化而来,人人都有体会的打嗝则是腮呼吸遗留的痕迹。
科学家们有时会对鱼类有些意见,只因它们拒绝了和我们的祖先一起大迁徙,从水中离开,到陆地的空气里追求更轻松的生活。它们在混沌的生活环境中无法为长远考虑,这常被认为是一种认知障碍。但是,最新证据显示,鱼类大脑中有着丰富记忆,有些鱼类甚至能回忆起十多天前的情景。
它们似乎对骗术也略知一二。比如雌鳟鱼的”假潮”——它们会假装浑身颤抖,似乎这样就可以骗着不喜欢的追求者赶快射精了事。我们也可以看到高清的视频资料,记录了石斑鱼与鳗鱼相互配合,一起把猎食者赶出自己藏身的珊瑚礁。双方通过复杂的头部动作为行动信号。这一行为说明,鱼类有着自己的心智理论,也就是推断其他生命体精神思想状态的能力。
从多个探究鱼类是否有痛觉的实验中,我们观察到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行为。作为最强烈的意识状态之一,痛觉远非简单的对损伤的察觉。即使是结构最简单的细菌,其外膜上也分布着感受器,环境中微量的有害化学物质即可引发程序化的逃跑反应。但是细菌并没有中枢神经系统,不能将这些信号整合成个体对于身处化学环境的三维体验。

鱼的感受器可比细菌的多太多了。不论是水温的突然升高、腐蚀性化学物质,还是鱼钩穿过鳞片扎进它们的身体里,都会引起感觉神经元迅速产生电冲动。在实验室中,嘴唇被注射了酸性物质的鳟鱼即使在实验结束之后,仍然会呼吸急促地不停摆动身体,在水缸的边缘或者鹅卵石底拼命地搓揉自己的嘴唇。给它们用了吗啡之后,这些行为才会停止。
这种现象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研伦理。但是,每年有数万亿水生动物被人类从江河湖海中粗暴拽出,与它们遭受的痛苦相比,实验用鱼所经历的根本不值一提。一部分鱼在被捕捞几个小时后,被丢进昏暗冰冷的运输箱成为全球海鲜供应链中的一员时,仍然是清醒的。
鱼类所感受的疼痛,和我们的痛是不同的。在由复杂的镜像搭建起来的人类意识中,疼痛有了存在主义层面的意义。因为疼痛会让人产生想象,让我们感觉死亡仿佛巍然耸立于前,同时因为美好的未来顿时黯淡下来而无比伤感,所以我们很容易将人类的痛理解为所有苦难中最深刻的一种。但是只要知道有一个截止期限,疼痛对我们来说就不会那么难熬。鱼类可没有这么好用的认知能力,当人类把它们从水下的高压中迅速拉到水面,压力骤变会让它们的血液酸度骤升,给组织器官带来损伤,在这些可怜的生命看来,这样的极度痛苦是看不到尽头的。在甲板上,它们不停地挣扎,这很可能是一种无声的呐喊。
耆那教徒中口口相传着尼米纳什(Neminath)的故事,据说生活在远古的他对于其他动物的求救信号非常敏感。这份对动物与众不同的喜爱之情是他在家乡亚穆纳河边牧场放牛时逐渐产生的。离开德里四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来到了绍利普村(Shauripur),这片尼米纳什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尼米纳什是耆那教的24位祖师之一,这24位先知般的人物在横渡了一条象征性的河流之后,将自己从出生与再生的轮回中解放了出来,而后开始开化追随他们的普罗大众。耆那教祖师的故事往往都会强调他们非暴力的天性,据说其中一位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漂浮起来,不让羊水里皱起一点波纹,从而避免伤害自己的母亲。
耆那教的祖师中,只有几位是曾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尼米纳什只存在于传说中。耆那教徒们相传尼米纳什在他婚礼当天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村庄。那天早上,他骑上了大象,原本打算骑着它前往举行婚礼的寺庙。途中,他听到了远处传来痛苦的哀鸣,想要一探究竟,他的那头大象向导告诉他,这是那些为他婚宴而被宰杀的动物发出的哀鸣。
这个时刻彻底改变了尼米纳什。某些版本的民间传说声称他释放了所有幸存的动物,其中包括一条鱼,被他捧在手中,送回了亚穆纳河。也有人说他只是离开了。大家至少达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前半生,放弃了迎娶美丽的新娘,离开了安定的生活,向着古吉拉特邦出发,去追寻离阿拉伯海40英里的圣山吉尔纳尔(Girnar)。

天还未亮,我也踏上了自己的登山之旅。类似于常见的朝圣之路,我需要在9点之前爬完7000级依山而建的台阶,按时赶到山顶附近的古寺,参加例行的仪式。
这条山路离吉尔国家公园(Gir National Park)只有50英里,就在徒步的前一天,我在那里看到了两只亚洲狮,它们和自己的表亲非洲狮长得简直一模一样,难以分辨。曾几何时,它们是安居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后来在印度的大英帝国殖民时期,每一位到当地王宫拜访的总督例行要在附近的森林打猎,导致它们几近灭绝。它们的处境在今日虽然有所改观,但仍然是最珍稀的大型猫科肉食动物之一,甚至比它们北方的邻居雪豹更加稀有。如今雪豹的数量已经是少之又少,以至于民间有传言说,在喜马拉雅山的悬崖峭壁上看到雪豹的踪迹,相当于完成一次朝圣之旅的修行。
在黎明的黑暗中路过山底营地里一个个小木屋和帐篷时,我试着不去想这些狮子,不去想它们的行迹最近已经拓展到吉尔纳尔山林里的事实。天逐渐亮起,叶猴们也出现在山路边的大圆石上。其中一只盯着小贩架起摊子向路过的耆那教朝圣者提供饮食,趁他转身的工夫, 这只猴子冲上来拿起一根香蕉就跑。之前在吉尔国家公园里,我还看到过鹿把这些猴子当作树顶的监视系统,以及时发现可疑的信号。
猴子们会在树的高处蹲守,在雨季前森林的琥珀色和金色背景中,寻找豹和狮子的踪影。一旦发现悠闲漫步的大猫们,它们会发出特别的叫喊声。除了鹿之外,其他的动物也会利用这些信号,我当时在公园里的向导就是这样寻找狮子的。
在我向山顶前行时,不断有赤脚疾行的女人超过我,她们大多穿着各种荧光色的纱丽,闪着橘色、绿色或者粉色,伴着她们的脚步,脚腕上的精致银饰也发出清脆的声响。我走到一个路标,发现自己离寺庙还有1000个台阶要爬,干脆脱掉背包,跳上了路边的一堵矮墙,让腿随意地垂下来。
往下面走两个拐角,可以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白袍僧侣艰难地走着这条山路。他看起来很孤独,而且呼吸好像有些困难。耆那教的僧侣和尼僧需要完全隔绝尘世,所以他们会断绝所有家庭关系。在踏上修行之路前,他们会给自己的孩子们最后的拥抱,而后发誓永世不再相见,除非天意助他们在喧嚣之外重逢,因为一旦离开,他们会背着自己仅剩的身外之物,永远在少有人迹之处流浪。
我跟这位僧侣单独走了一会,四周一片寂静,只有一阵嗡嗡声传来,我发现这声音来自路边一只活跃在叶子花丛上细长的黑胡蜂。我跟这只胡蜂的最后一代共同祖先应该生活在七亿年前,这只小昆虫的样子进一步确证了我们在进化树上极远的亲缘关系——瘦长的体形,马赛克一般的眼睛带着一点雾面的质感,这些看起来不像是有意识的动物该有的样子。但是,外表是有欺骗性的:据称,一些胡蜂之所以演化出硕大的眼睛,是为了捕捉社交信号,某些胡蜂种类可以记住不同领地成员的面部特征。
实验室中的蜜蜂能够学会识别抽象概念,包括“相似”、“不同”和“无”。
胡蜂,和蜜蜂、蚂蚁一样,属于膜翅目昆虫,它们的行为有着高度的复杂性。蚂蚁在领地中遇到缺口是,会用自己的身体搭建桥梁,让整个族群顺利前行。实验室中的蜜蜂能够学会识别抽象概念,包括“相似”、“不同”和“无”。它们也可以彼此学习,如果其中一只学会了新的采蜜技巧,周围的蜜蜂也可能会模仿其行为,从而传给整个族群,甚者传给后代。
某实验中,研究者在湖中心的一艘小船上放了糖水,成功吸引了几只蜜蜂的注意力。飞回蜂巢之后,它们通过摇摆舞告诉了同伴船的位置。一般情况下,其他的蜜蜂都会立即出发去探索新发现的蜜源,但是在该实验中,它们并未行动,而是待在原地,似乎在查看意境地图,排除了湖中间有花的可能性。其他科学家并未成功重现该实验结果,但是有另外几种实验证实了蜜蜂的确能够以此种方式利用意境地图。
安德鲁·巴伦(Andrew Barron)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一位神经科学家,他在最近十年间重点研究蜜蜂大脑中的精细神经结构。他认为蜜蜂大脑对于空间信息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与人类中脑处理信息的方式相似。这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毕竟蜜蜂的大脑只有区区一百万个神经元,而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多达八百五十亿。然而,人工智能研究向我们证明了,相对简单的神经回路也可以承担复杂的任务。只有25万个神经元的果蝇,仍然有着复杂的行为。在实验室研究中,如果交配机会渺茫,某些果蝇会借酒消愁,而在自然界中,遍地是破皮发酵的果子,对于它们来说,酒精这种可以改变意识状态的物质并不稀奇。
很多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都仅仅停留在原始阶段,以分布均匀的蠕虫状神经元网络组成。在最近的五亿年间,自然选择将这些蠕动生命体中的一部分塑造成了节肢动物,给予了它们不同类型的附肢和全新功能独特的感觉器官,把它们从局限于刺激和反应的漂流生活中解放了出来。
第一批靠自己探索三维空间的动物们无疑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进化过程中意识的出现很可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拿前面那只黑胡蜂为例,它在叶子花薄如蝉翼的花瓣上盘旋时,环境中的大量信息,如阳光、声音振动、花香,会透过纤维质的外骨骼涌入它的大脑。但是这些信息流到达大脑的时间并不一致。这只胡蜂需要同步这些信号,来保持对外部世界准确而持续的感知。同时,它需要迅速纠正由自身运动造成的误差,这并非易事,因为它的一部分感觉器官所附着的身体部位本身就是可活动的,尤其是不停转动的头部。
如果胡蜂的某个水生祖先是地球上最早产生意识的动物,它的意识肯定跟我们的完全不同。
神经科学家比约恩·默克尔(Björn Merker)提出,早期的动物大脑会根据周围的世界,建立以自己身体化身为中心的内部模型来解决这些问题。默克尔认为,意识其实是在这个模型内部产生的多感官视角。这个视角略去了所有信息同步过程和我们移动时产生的干扰,好像在系统算法里藏了个会自动剪辑的斯坦利·库布里克。我们也不会体验到将欲望转化为行动的机制。如果我想再爬一次山,我只会站起来朝着山顶出发,不会去想迈出每一步时有什么肌肉在收缩。胡蜂在飞来飞去时可能也不会注意到翅膀的每次扇动,对它来说,自己可能只是靠意志在空间中移动的。
如果胡蜂的某个水生祖先是地球上最早产生意识的动物,它的意识肯定跟我们的完全不同。很可能会是黑白的画面,视野所及之物没有明显的边界;也可能是片段的,时有时无;又或许是在一片模糊中对于二元情感的粗略判断,感觉的主体是单一的,客体则是非黑即白的混沌。对于那些见识过远在宇宙另一端闪耀群星的人来说,这种存在简直难以想象,还很有可能引起幽闭恐惧症,但这不意味着意识不存在于其中。

白衣僧侣走到我坐着的墙边时,那只胡蜂离开了花丛,向着太阳飞去,我目送着它小小的身影直到消失。这位僧侣带着一副白色的面具,很多耆那教徒都会如此,以避免吸入昆虫或者空气中其他小型的生物。他走过时,我冲他点了点头,然后向后靠到了温暖的山石上。
我从墙上跳下来,带着有点僵的双腿继续向上爬时,那位僧侣已经超了我六个弯的距离,变成了远处的一个白点。距离仪式还有15分钟的时候,我终于赶到了寺院入口。寺院里的大理石地面闪耀着美丽的白光,好像被山里的太阳抚摸过。
穿过一排优雅垂下的金饰,我进入了寺院的内殿,精雕细琢的壁龛里,以及从屋顶悬挂下的平台上,闪烁着数不清的烛光。石头屋顶被雕刻成一只莲花的形状,娇弱舒展的花瓣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般纯粹、超凡的灵魂。

大约四十位耆那教徒双腿盘成莲花坐,整齐地坐在地上。女人们都换上了特意为这个重要场合带来的干净纱丽,所有的男人都身着白衣。我也在队伍后面找到了空位坐下。
在我们面前,两列柱子围起了一条黑暗的隧道,在隧道的尽头的烛光中,静坐着一具黑色大理石的男性雕像。他桶状的胸廓前,镶嵌着精致的宝石,他的眼睛也一样,如此安详,看起来像是漂浮在黑暗中的两点星光。坐在我旁边的男人轻拉了一下我的衣服,打破了这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安宁。“尼米纳什。”他冲那座雕像点了点头,说道。
传说中,尼米纳什就是在这座山上,实现了彻底的、摆脱限制的意识状态,获得了感知整个宇宙的能力,包括所有动物的思想。耆那教徒们认为,人类的特别之处在于,相比于其他生物,我们在自然状态下,最接近这种大彻大悟,没有一类物种能如此容易地洞察其他生物的意识。
朝圣者们开始低声地哼唱,之后音量逐渐提高。一个人把一面大鼓推到隧道入口旁边,用黑色的木槌击打着,另外两位一起奏响了手里的铙钹。男人和女人排成两列,分别从两侧的门走入隧道后,沿着两边向隧道尽头走去。一位身穿橘色纱丽和金色头饰的女子从尼米纳什面前走过,举起手中的容器,把混合着牛奶和圣水的液体倒在了他的头上。她离开之后,一位身着白袍的男子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歌声越来越响,朝圣者们的热情高涨,近乎狂热。他们举起双手打着节拍,速度越来越快。高潮好像呼之欲出,但就在这时,一切戛然而止。鼓声、铃铛和钹的响声突然静了下来,留下一片寂寂,最终由一声螺号收尾。
螺号低沉的声音悠长而清澈,响声飘出了寺院,笼罩着古老的山顶。随着螺声减弱,我不禁好奇,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此处是否会不仅仅局限于一座耆那教神殿。也许它会成为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场所,代表着我们从人类意识唯一性的幻象中觉醒。也许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前来此处顶礼尼米纳什,毕竟他所象征的是历史上第一位可以听懂动物哀鸣的人类。
翻译:狼顾,西子;审校:张蒙;编辑:clover honey
Scientists Are Totally Rethinking Animal Cognition
What science can tell us about how other creatures experience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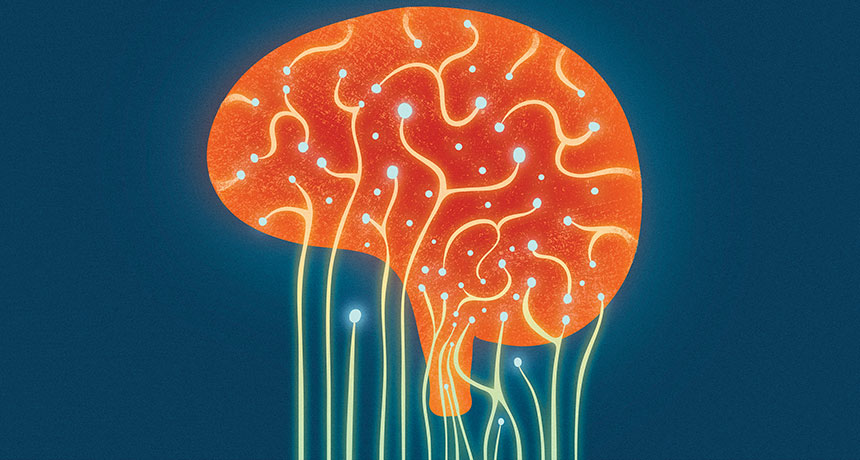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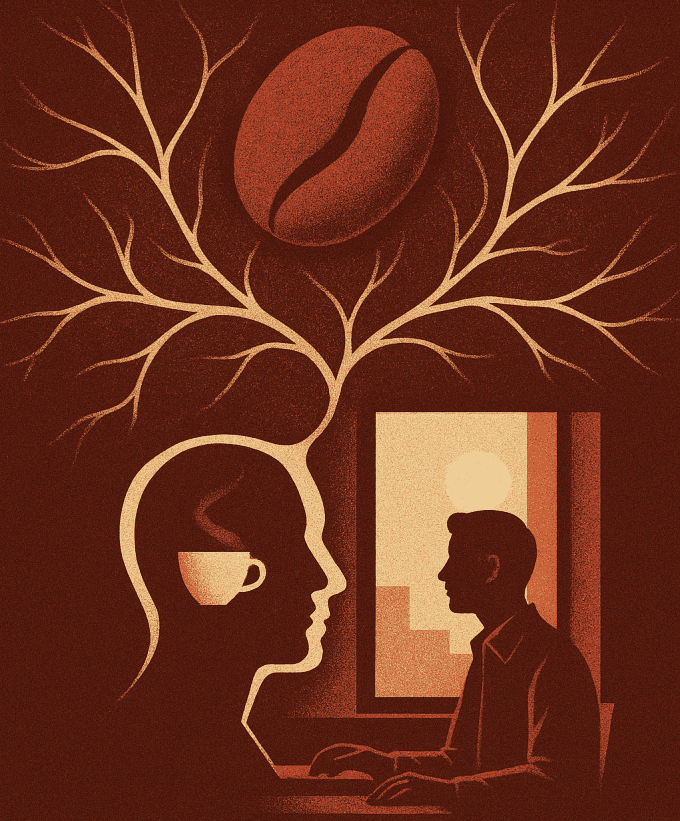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