鲸游过他死去的地方
人类用1000多年的时间,欲将海洋中的奇兽捕杀殆尽。而现在,科学家与渔民结盟,试图力挽狂澜——却发现保护比破坏要困难得多。

圣劳伦斯拂晓
“鲸曾是未来、现在和过去,皆为一体;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命运,殊途同归。”
——菲利普·霍尔《鲸》
乔·霍维特(Joe Howlett)去世的那天,破晓很美丽。舍派堪港的海面如镜般风平浪静,随着太阳浮上深蓝天空,乔掌舵着希拉号(Shelagh)——加拿大鲸研究所的科考船,驶入圣劳伦斯湾,准备开始一天的北大西洋露脊鲸考察,并对新不伦瑞克北部海湾的浮游动物进行采样。
在开阔水面,乔和船上的其他科学家早早起了床,面对金色晨光惊叹不已——途中和他们迎面相遇的三艘大帆船,正满帆而行,驶入港湾参加夏季节日。
乔,59岁,这辈子几乎一直是水手和渔夫,这些节日帆船,他看得欣喜若狂。
好天气对他们来说是多重的祝福:除了要完成常规的科考任务,希尔号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乔和菲利普·汉密尔顿(Philip Hamilton)可能会尝试在开阔水面解救被困鲸。之前的一个夜晚,他们接到了联邦海洋与渔业部(Department of Oceans and Fisheries, DFO)的电话:一头露脊鲸在他们的位置附近被捕蟹网缠住了,发现受困鲸的渔民试图靠近它时,这头鲸便发狂起来,猛烈拍击水面,它巨大的身躯交错遍布着深深的白色伤痕,这是被捕鱼用具缠绕过的典型伤痕。(世界上80%的露脊鲸一生中至少受困过一次,50%的露脊鲸经历过2次以上。现在许多的露脊鲸身披刺眼的白色伤痕,而它们原来的皮肤应该是光滑、天然墨黑的。)

求助电话打进来时,兼为新英格兰水族馆安德森·卡伯特海洋生物中心生物学家的汉密尔顿刚为小组第二天的航线做好了规划。开启鲸GPS坐标定位后,他发现受困鲸就在自己2公里范围内。他告诉渔业部:当然,我们会试着搜寻它。
这种求助对他们来说算稀松平常:乔是坎波贝洛鲸救援队的创始成员之一,这只队伍由渔民志愿者组成,自2002年开始,专门在加拿大滨海诸省对被困渔网的鲸进行施救。他是世界上曾冲在最前线的鲸解救老兵之一,无数次与重达70吨、受困痛苦的鲸亲密接触。
2017年是这种极度濒危的动物最危险的一年。渔民和研究者在圣劳伦斯湾发现了更多露脊鲸尸体,有些受船舶撞击致死,有的被渔网绞死。因为无法自由游动或进食,被渔网缠绕的鲸死于饥饿,或因渔网嵌入肉体过深,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渔网甚至割入骨骼,最后死于感染。直到2017年7月9日,希拉号接到刚才的求助电话,在短短四周内已经发现了7具鲸尸体,生物学家们已经开始将尸体拖走进行尸检。
距乔上一次解救鲸才过去5天,当时渔业部的干事们与希拉号在海湾一同施救。希拉号花了1个多小时一直在尝试靠近鲸,但这头鲸突然出人意料地停止了抵抗,无力地浮在水面上。随后,乔得以与刚抵达的联邦海洋与渔业部干事一同切除渔网,只用了15分钟,整个施救过程十分快速,解救一头鲸通常要花上数小时,而生性暴躁机敏的露脊鲸更是麻烦。
1000多年来,人类撑着小船,伺机捕杀鲸;乔则是第一代乘着小船去拯救鲸的人。
作为一名渔民,乔知道这些生物之所以受困,年复一年,是因自己生计带来的恶果。(几年前,乔工作过的渔船上的渔具正好出现在了代托纳海滩临海的露脊鲸身上。)乔选择从事拯救鲸,最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愧对这片海。他想要回馈海洋。但与旧时代的捕鲸人不同,他向往大海、对慢慢靠近世界上那些最庞大的动物感到兴奋不已。1000多年来,人类撑着小船,伺机捕杀鲸;乔则是第一代乘着小船去拯救鲸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去年7月那个夏天清晨,他那么急于出海。–
深爱着海的男人
“纵使我将它解剖,只刀入骨肉罢了;我对它一无所知,且永远无从知晓。”
——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
乔·霍维特,他的家人叫他乔伊,在新斯科舍省哈伯斯火车站长大。他的父亲是车站经理,乔每天看着乘客来来往往,自己则驻足原地。他的童年在垂钓、帆船和体育运动中度过,很少远离自己的出生地,直到1975年,那年他17岁。那年夏天,乔和他的朋友史蒂夫·克罗夫特(Steve Croft)加入壳牌公司的考察船,向北航行,为石油勘探进行地震学调查。他们行经塞布尔岛、纽芬兰、巴芬岛然后前往格陵兰岛,每6小时轮班负责30名船员的伙食——途中乔升职为甲板水手。

他们看到拉布拉多海的冰山向南漂流,北极熊游荡于海岸。他们在格陵兰岛忙活了一周,从当地因纽特人那里买了抛光坚果,雕刻成小戒指出售。夏末,他们回到哈利法克斯时,史蒂夫、乔和其他六人将船驶往该船的船籍港,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敦。日子一天天地去过,向南航行时看着美国海岸在身边延伸着,艰苦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晚上他们便聊天、给家里写信。史蒂夫说,这应该是乔过得最像度假的日子。
乔并没有回到哈伯斯完成高中学业;相反,他加入了海岸警卫队,二十多岁的那几年里,他在路易斯圣洛朗的西北通道上破冰,环绕北美航行,甚至在百慕大三角遭遇过飓风。

1986年,28岁时,乔的人生又一次被改变。那时他在贝德福德海洋研究所工作,绕着坎波贝洛绘制海床图,途径新不伦瑞克的一座小岛,有900居民,离缅因州海岸只数百米。他的船停泊在“加拿大老兵团”附近的一个码头,当时“加拿大老兵团”是这座岛上唯一的酒吧。一晚,在社区舞会上,他结识了土生土长的坎波贝洛岛民,鲱鱼渔夫的女儿,达琳·布朗(Darlene Brown)。她请求乔留下来,乔却说他做不到——最后乔在她父亲帮助下找到了工作。
乔的兄弟托尼·霍维特(Tony Howlett)回忆到:“乔说这辈子有三件事他永远不会去做,”他说过:“我永远不会搬到新不伦瑞克;我永远不会结婚;我永远不会成为渔夫。”在那一年他却把这三件事都做了。
1987年他和达琳结了婚。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泰勒,乔也成为达琳第一个儿子——查德的继父。查德的亲生父亲,迈克尔·布朗,同是这座岛的居民,成了乔最好的朋友之一。
乔安顿了下来,但他把那种水手特有的冒险精神也带给了他在小岛长大的妻子。他组建了“青蛙池勇士曲棍球队”,队员由岛民与卢贝克居民组成,卢贝克曾是缅因州的一座陆上小村庄,过桥便是坎波贝洛。
去往新不伦瑞克,途径缅因州参加圣斯蒂芬的世界青少棒球大赛的路途很长,开车要花上好几小时,但他们会绕行走乡间小路,即使夜幕早已降临,为的是不让旅程早早结束。乔曾教他的朋友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如何驾船,一有机会他们就偷偷摸摸出海。乔不管到哪都带着他的口风琴,想逮住每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就算他表演得像铲屎一样,他也玩的很开心。”他的朋友麦凯·格林尼(Mackie Greene)说。
乔与托尼最后一次遇见时,乔告诉托尼,自己的生活能变成这样还是“有点开心的”。“在这我有了孩子们,今后也要一直在这生活,”乔说,“这样挺好。”
坎波贝洛也是乔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鲸的地方。刚搬到岛上不久,乔独自一人在夜晚出海,渔船拖着一拉网的鲱鱼,他听见水下有什么东西正在跟着自己的渔船和渔网里的鱼,互相呼唤着,浮上水面在他四周游动。当乔告诉妹妹玛丽·艾伦·洛纳根他的奇遇时,她担忧不已。要是鲸靠得太近了,会不会掀翻他的小船?
“乔,你难道不害怕吗?”她问。
“梅儿,它们知道我在船上。”乔答道。
第五日
“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 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创世纪 1》21-23
放在现在谈可能有些古怪,但是在19世纪初,自然学家仍对于新鲜出土的化石困惑不已,争论着一种生物完全灭绝是否可能(被人类完全灭绝或者经自然选择消失)。美国第三任总统和野生动物爱好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道:“这便是自然的运转模式,她绝不会允许任何种族的动物灭绝;不允许她伟大工程有任何一环皴裂破碎。”换言之,生物不会灭绝,以免与上帝的完美创造相矛盾。还是将这话告诉乳齿象、野牛以及像怀俄明蟾蜍这样的不起眼的小动物。把这话讲给露脊鲸听吧。
到11世纪的尾声,巴斯克人攀登山丘与高塔,于比斯开湾高处搜寻北大西洋露脊鲸的身影。这些缓行的庞然大物于海面群聚,由于有着厚重的鲸脂层,死后就像肥大的黑色软木塞一样长时间漂浮于海上。“捕鲸人只需静坐于海岸,待露脊鲸游经,撑木舟或小船随行,屠戮,拖回。”
到了16世纪,比斯开湾的鲸群近乎被捕杀殆尽时,巴斯克人驶向更远的纽芬兰海岸,捕杀弓头鲸。
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机构生物学家,合作性、数据共享的保护组织北大西洋露脊鲸保护联盟主席,马克·鲍姆加特纳(Mark Baumgartner)说。
几个世纪以来,仅靠船桨与鱼叉,人类征服上帝的巨兽,宣示自己的统治地位。到了16世纪,比斯开湾的鲸群近乎被捕杀殆尽时,巴斯克人驶向更远的纽芬兰海岸,捕杀弓头鲸。到了17世纪,鲸油振兴了西方文明,集中在马萨诸塞的北美捕鲸业,如野火般蔓延开来。露脊鲸(right whale),其名被理解为“正确的鲸”(“right whale” to kill)而被大量捕杀,但当时人们对这种生物却一无所知。直到18世纪现代分类学创立,自然学家才得以渐渐掌握鲸物种间的差异;从前,人们对露脊鲸的称呼各不相同:巴斯克地区的人称它sardre(school),丹麦人称其svarthval (black whales),荷兰人把来自挪威北角的鲸叫做Noordkapers,冰岛人称其sletbags(smooth backs)。那时人们未曾想到,露脊鲸迁徙至全球各地,是一种遍布全球的物种。
在北美,露脊鲸被称为“真鲸”(true whale), “鲸须鲸”(whalebone whale), “七尺骨鲸”(7ft bone whale), “石鼻鲸”(rock-nose whale)。但对于内陆人来说,它们曾是可怖的海底谜兽。16世纪,艺术家们把它们描绘成有着尖牙突刺的巨型魔鬼鱼,浑身布满眼睛,甚至口器。“对于现代世界来说,鲸是在充满威胁的世界中,无辜无害的象征,” 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在他的书《鲸》(The Whale)中写道,“另一方面,大鱼吞噬了约拿,历史认为这是危险,或者辛巴德发现自己在巨鲸背上,‘鲸背已沉积土壤,自天地初树木已生于此。’”
将它们屠杀殆尽更为简单。
我们用石油制品替代了鲸油,捕杀暂时停歇了下来,但因为人类又发明了鱼叉发射器与捕鲸船,捕杀量远超海洋从前的猎捕承载能力。
到1930年,每年有5万头鲸被捕杀,而在战后的几年,鲸油作为一种廉价的材料,被用于制造人造奶油、冰激淋、肥料、肥皂等近乎所有的产品。2015年的一项研究估计,20世纪全球的鲸捕杀量接近300万。记者丹尼尔·克雷西(Daniel Cressey)在英国杂志《自然》报道此事时写道:“其他著名的动物捕杀案例可能有更大的捕杀量… …但是就纯粹的生物量而言,20世纪的捕鲸当为历史之最”。
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最终禁止了商业捕鲸(尽管少数国家,包括日本,挪威和冰岛,无视禁令)。自此,一些物种的种群数量渐渐恢复——例如座头鲸与南极小须鲸,预计到2050年,它们的种群数量有望恢复到人类捕鲸前水平。但是对所谓的“城市鲸”——露脊鲸来说,它们的栖息海域与工业化的海岸线重合,1986年露脊鲸的种群数量曾低于300头——这种消亡曲线过于陡峭,且它们栖息的水域充满了更多人为危险。–
灭绝的解药
“将军,如果我们随己所欲对待这些鲸,我们将会和灭绝它们的人类一样罪恶。”
——斯波克,《星际迷航4:抢救未来》

查尔斯·斯托米·梅奥(Charles “Stormy” Mayo)一直靠海为生。他的家人最初在1659年于科德角定居,而他却选择出海,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捕杀海里的生物,而是为了研究它们。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生物学学位并获得迈阿密海洋与大气科学学院的几个研究生学位后,他当时决定回到普罗文斯敦,在海角最远的那一端,造一艘帆船,过宁静的生活,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学术界太激进了。然而在仅几个月之内,他就和一位朋友联手,反对一项港口疏浚工程。他们的努力最终成就了沿海研究中心,一开始这个组织仅有两位活动成员,现在则变成了重要的科研与海岸管理机构。
1983年4月的一天,梅奥正在一艘科德角湾的鲸观察船上工作,恰好看见数头露脊鲸游经,在向众人解释这是多么罕见的景观时,一位年长的女性走到梅奥一旁。他们的简短对话竟彻底改变了梅奥的研究生涯。乃至35年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随着海风吹拂着她的长发,她解释道自己在楠塔基特岛捕鲸博物馆工作时,看到过文件记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科德角的捕鲸热潮并不集中在春季或夏季,而是在严冬。“我不是什么生物学家,”她说,“但是你想寻找露脊鲸的话,你应该那时候去。”第二年一月,梅奥开始了他的观察。
一月底,他在港口外就发现了第一头露脊鲸。随后,他经常同时目击2只,3只,4只鲸——那时露脊鲸是大多数生物学家眼中的谜。“那年,所有人都大开眼界。”他说。
就像捕鲸一样,鲸解救是对生命的极端狂热,冰冷海水上充满热血与肾上腺素。
约一年后,来自达尔豪斯大学和英格兰水族馆的研究人员,包括菲利普·汉密尔顿(Philip Hamilton)和莫伊拉·布朗(Moira Brown)——之后的加拿大鲸研究所领导者,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发现芬迪湾大型的露脊鲸集群。他们发展出一套识别不同鲸身份的方法,其一部分手段是靠辨认生长于鲸皮肤的突出、粗糙、独一无二的斑块——胼胝。经过数年的识别、拍摄与编目,研究人员终于可以确定露脊鲸的数量:大约270头。虽然种群数量比较少,但是出人意料地呈现出缓慢的恢复趋势。影响恢复的两大阻碍是:船只碰撞与渔具缠绕。
船只撞击造成的死亡比较容易理解。这种钝器伤,让鲸就像被车轧死的动物一样暴毙。但是被渔网缠绕更加复杂,更毛骨悚然。被渔网缠绕的鲸可能会拖着渔网数年,海水的作用将尼龙绳深深嵌入它们的肉体,甚至骨骼,随时间流逝,它们的伤口愈加暴露在水生病毒细菌之下。渔网阻力使觅食更加费力。尼龙绳有时会缠绕在鲸须上,使它们难以进食。被缠绕的鲸可能死于感染或饥饿,并且缠绕带来的心理压力甚至会造成雌性延迟怀孕,这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死亡,关键是幼崽更少。
虽然莫伊拉·布朗等人主张调整芬迪湾的航道,梅奥和他的朋友大卫·马蒂拉(David Matilla)正在尝试更加直接,更危险的方法:解绳救助——从数百年的捕鲸技术中借鉴来的鲸解救手段,于20世纪70年代由圣约翰纪念大学的鲸研究员乔恩·利恩(Jon Lien)首创。
就像捕鲸一样,鲸解救是对生命的极端狂热,冰冷海水上充满热血与肾上腺素。这与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关系相近——恰当的说,对鲸的解绳救助就像将捕鲸行为完全反其道而为之。
梅奥的父亲查理一辈子都是渔民,有时会在科德角附近捕猎领航鲸,在与他交谈过后,梅奥和马蒂拉有了想法。如果他们可以将鲸身上的渔网附上塑料浮标,把受困的鲸放在“浮筒”里(旧时捕鲸人曾用来处理木制浮标),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让鲸力竭而放弃抵抗,得以抵近剪断渔网。
救援人员不使用鱼叉,而是把爪钩拴在控制绳和浮标上,抛出爪钩钩住鲸身上的渔网。一旦救援人员足够接近,他们便用特制的鱼叉(将改造的水手刀绑在鱼叉长短的杆子上)一根一根地剪断渔网。
要拯救的生物大到无法尽收眼底,那时的肾上腺素飙升你能想象吗?
1984年10月,在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海岸边,他们准备为一头名叫艾比斯的雌性受困座头鲸首次尝试这种方法。她逃脱了救援者的第一次追踪,但一个月之后,到感恩节那一天,梅奥、马蒂拉和一组船员带着水听器和苏迪亚克充气艇出发,去录制普罗文斯敦附近的座头鲸群的叫声。抵达时,他们发现了艾比斯,她仍然被渔网缠着,和上次见她时比,消瘦很多。
小队当时没有带任何工具,在赶回去带来更多的绳索、浮标和第二艘充气艇后,他们开始了救援行动。用小船锚作钩爪,连着控制绳与浮标,钩住缠绕着鲸的渔网。就如老捕鲸人所述,艾比斯已经精疲力竭,无力逃跑,游了几分钟便停歇了。梅奥和马蒂拉依靠着小艇,用水果刀割开缠绕在她鲸须上的尼龙绳。随后她便自由了。
第一次解救之后,梅奥和马蒂拉继续与查理合作,开发了专门的工具。很快,沿海研究中心的成员开始为世界各地的人提供培训,_学员包括2002年的坎波贝洛鲸救援联合创始人乔·霍维特和麦基·格林尼。
要完成鲸救援,需要特别的人来操作,乔和格林尼分别都是不同领域的最佳人选。2000年初,他们各自运营着自己的赏鲸船,都擅长绳索操作,海上工作经验丰富。他们足够默契,足够的友好竞争让工作变得有趣。“许多时候只需要乔手指一点,”格林尼说,“我心里就明白他想让我往哪儿开。”
乔也是团队的驱动者。“他不断挑战极限,”乔的朋友、捕鱼同事、鲸解救员大卫·安东尼说。“毫无疑问,他是咱们之中最优秀的。”作为训练有素的海岸警卫队长官,乔也相当注重安全与航海技术。如果感觉实施解救太过于危险的话,他不会让船员行动。
他们刚起步时,渔业部为他们提供了一艘单人快速救援艇,新英格兰水族馆为他们临时燃油费赞助。18个月后,安东尼正式加入乔的团队。一天,在捕虾船甲板上,乔告诉安东尼,他认为他们还是亏欠大海。
今天,格林尼和大卫谈到解救这种超现实般的生物。你是否曾亲眼目睹一头座头鲸?要拯救的生物大到无法尽收眼底,那时的肾上腺素飙升你能想象吗?
网上有一段2016年乔解救受困露脊鲸的视频,你可以看到救援行动的超强体力消耗,以及精神震撼。身着红黑坎波贝洛鲸救援制服、戴着自己的签名款墨镜,乔俯身贴卧在橘色苏迪亚克充气艇舷缘——他的动作有力、专注、果断——将鱼叉或长杆一次又一次用力推入水中。视频的尾声,解救鲸后收拾器材时,你可以看到乔脸上的汗水与疲惫。(视频仅展示了解救的最后2分钟,然而乔、格林尼、布朗和前渔业部干事杰瑞·康威已经为此忙活了4个小时。)格林尼身着同样的红黑外套与白色头盔,大声欢呼并举起双手庆祝胜利。你能感受到紧张后轻松的氛围。
–
今天,格林尼和大卫谈到解救这种超现实般的生物。你是否曾亲眼目睹一头座头鲸?要拯救的生物大到无法尽收眼底,那时的肾上腺素飙升你能想象吗?格林尼说:“你无法目睹它的全貌,或许是因为它让你双腿发颤。”这两人曾经在午夜,追逐一头长须鲸,一路从坎波贝洛追到布莱尔岛。他们曾被一头座头鲸举起,离开水面。他们承认,追逐鲸就如折磨一般,却是有价值的。格林尼说:“眼前的动物正饱受煎熬,你必须有所作为。”
露脊鲸的种群数量越来越靠近灭绝的边缘,就算只拯救一头露脊鲸,也是事关重大的。但是以回报大海为理由,很难解释他们在谈及解救行动时难以掩饰的兴奋语气。体验鲸气孔的呼吸,这种感觉无法言说。也许他们之间的羁绊与他们相互的信任一样深厚。特别的人才能承担如此风险——不仅希望拯救鲸,也渴望感受野性。
每片沙滩上,都有死去的鲸
“现在,于此惊诧时刻,于不经意之间我们正决定,进化之门是继续敞开,抑或是永久地关闭。”
——伊丽莎白·克尔伯特《第六次大灭绝》

2003年,加拿大鲸研究所说服了加拿大运输部和国际海事组织,将芬迪湾和罗斯威流域的航道移出新斯科舍省南岸。一些地区的船只撞击风险降低了90%,截止2010年,露脊鲸的种群数量已提升至483。露脊鲸成为了动物保护的象征,这个物种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人类屠杀之后,近况有了些许好转。
但海面之下并不安宁,洋流开始带走大量鲸赖以生存的浮游动物,远离目前的露脊鲸栖息地,远离芬迪湾的新安全区域,远离科学家的观察区域。
芬迪湾的露脊鲸种群数量一直在上下浮动,但是2010年研究者发现,在寻常地带觅食的鲸减少了。海湾中浮游动物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一种解释是,随着缅因海湾的升温(由于墨西哥湾暖流的北移与洋流的减速,这里比全球99%的海域升温更快),且因为冷水携带更多氧气,洋流正把浮游动物带到北方水温较冷的圣劳伦斯湾。
鲸正追随它们的食物,进入新的海域:船只航速相当快的水域,每年春天,正当鲸来时,几乎牢不可破的尼龙绳和成千上万的捕蟹笼缠绕在一起,从海面到海床,变成了水下尼龙森林,缠住任何游经的物体。
截至去年6月底,托尼亚·维默(Tonya Wimmer)已经厌倦了发邮件报告海湾死鲸的情况。作为哈利法克斯海洋动物反应协会(Marine Animal Response Society, MARS)的主任,当发现受困露脊鲸时与救援队伍、研究者取得联系是她的职责。当发现死鲸时通知研究界也是她的工作,就像2017年6月18日,19日,21日,22日和23日那几天一样。她说:“所有人都困惑了,最糟糕的情形就是听到:‘伙计们,我们发现另一头,还有一头,又有一头。’”
研究人员得找出每只鲸具体的死因。首先,他们尝试从漂浮在水面的死鲸身上采集样本(基本上是大块的皮肤和脂肪)。来自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的病理学家皮埃尔·伊夫·道伍斯特(Pierre-Yves Daoust)博士甚至亲自爬上一具浮肿的鲸尸骸,切下实验室需要的样本。在使用这些手段后,显然无法得出结论,渔业部便授权协会将鲸尸体拖至海滩,使用大型政府器材进行尸检。
鲸的尸检工作至少需要30人或更多。挖掘机一条一条地剥去外层鲸脂,然后是肌肉,器官,直至骨骼暴露。一些鲸被绳索包裹,深深嵌入皮下——死因很明显:死于饥饿或感染。(早些年,人们发现一些鲸被绳索穿透了骨骼。)在其他的鲸体内发现了大块的黑灰:船只撞击造成内出血,漂浮于海上的尸体在烈日曝晒下,血块从内部被烧熟。维默说:“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加拿大沿海诸省风景甚好的海滩,可几乎每一片沙滩上,都躺着一具庞大的鲸尸体。”
去年解剖尸检的12具漂浮的鲸尸体中,2头死于渔网缠绕,4头死于钝物撞击,其余的尸体都已高度腐烂,无法确认。
其中有2具尸体,是乔·霍维特曾经救援过的鲸。
圣劳伦斯的悲剧
“……映入你眼帘
觉些许难以置信
抵苍穹之一瞬
出乎你所有想象
就如第五日生命之神话
黑暗破晓,如雨倾洒
回旋,向天际;随后
再次坠入那片漆黑丝绸
返航
一齐驶入那冷焰”
——玛丽·奥利弗《座头鲸》

7月10日,在圣劳伦斯,乔和希拉号船员收到了由观测飞机发来的受困鲸新坐标。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向北,向东,向南,向北,向东航行,来回搜索这片区域。仍然没有遇见它的运气。
约中午时分,他们与渔业部干事们会面,渔业部的人坐快速救援舟与乔一行人会和。本周稍早些,乔和汉密尔顿与这些干事们非常高效地协作救助了一头受困露脊鲸。会面期间,他们得知另一架观测飞机于16公里外定位了那头鲸。希拉号行驶得太慢,乔和汉密尔顿跳上联邦海洋与渔业部的船,急速前往。
上午10点后他们很快找到了4123号露脊鲸,一头6岁大的雄性鲸,情况不容乐观。一圈又一圈,渔线紧紧地把它的身体和鳍缠住,嘴里的鲸须更是缠绕了十多圈。汉密尔顿和乔向干事们解释道,这次行动不会和第一次一样轻松。汉密尔顿警告他们:“乍一看露脊鲸好像不会屈伸,但其实它们的尾巴可以一直拍到头部。”
乔站在船头就位,手里捏着他的鱼叉准备就绪。汉密尔顿居后,站在驾驶室边以便指挥渔业部的船长行船。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4123,鲸却以3-4节的稳定航速逃离了追逐。站在船上,乔可以看到鲸背部的一些渔线缠得并不紧,留有些许空隙,以便剪断。快艇追上了4123,船长掌舵让小艇与巨鲸并排航行。看鲸并没有转向,也没有下潜的意图,乔便猛推鱼叉,剪断了一根渔线。4123,或许是感到焦虑和疼痛,拍打着它的尾鳍,把水溅到了船上。
船长放缓速度,好让4123平静下来,随后他们又一次尝试抵近。又一次尝试,乔将鱼叉推入缠结的渔线,第二团纠缠的线被成功钩住。汉密尔顿记得他目睹鲸潜入水下,掉头向小艇游去。乔的反应一如通常,随着4123消失在船头之下,他仍然用力拉扯着渔线。乔用力的拉啊拉——随后鲸在汉密尔顿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渔业部的船长能看到。乔转身,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并对着船员们竖起一个大拇指。他成功剪断了渔线。但是船长发现4123突然毫无征兆地从乔身后浮出水面,它的尾鳍正要砸落下来。汉密尔顿及时转身,却只看到露脊鲸的尾巴从充气艇一侧弹开。随后,所有人发现乔瘫坐着,倚着舷缘,面朝驾驶舱。
汉密尔顿冲了过去,看见乔急促地吸了几口气,不知他的意识是否清醒。“我急切希望刚才乔是在呼吸,但是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不,乔根本没有呼气,”汉密尔顿说。他想确认乔的心跳,却没有发现跳动。汉密尔顿问船员是否有镜子,放在乔嘴前确认他是否还有呼吸。一名渔业部干事递过一部手机。“有那么一两分钟,我真的不想承认事情的严重性。我真的不想承认这是真的。”
船员们扶住乔,让他躺在船的甲板上。由于担心脊柱受伤,汉密尔顿在乔脖子下垫了一件夹克,随后开始做心肺复苏。一名渔业部干事呼叫了希拉号。随后他们紧急返航。
希拉号的船员并不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带出来一些创可贴。渔业部的船到达后,接受过高级急救训练的滑雪救护队队员,汉森·约翰逊(Hansen Johnson)带着他的心脏除颤器跳上甲板。跪在乔身边,小心翼翼地将乔的头向后倾斜,抬起下巴,保持呼吸道畅通,汉密尔顿则继续做心脏按压。
来回重复的急救让船员们近乎恍惚,忘记了自己有多疲惫。他们无助地重复着急救,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渔业部干事通过无线电组织好了紧急救助,以最快、最稳的航速前进,平静的海面被急船一刀切开。最终他们与海岸警卫队快艇集合,随后又花了90分钟赶往码头。
他们最终达到舍派堪时,急救小组已经将码头的一侧封锁隔离。医疗小组把乔接到便携式心电图仪上,经过几次测试后,医生宣布,乔在船上死亡。
约翰逊说:“如果你在做心肺复苏,伤员仍然没有心跳,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保持器官运作,还有复苏的机会。因为一旦放弃,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接受现实
“假设上帝远行归来,微笑着问我们,是否对宇宙万物有了些许头绪。恐怕上帝想问,我们是否终于想到要不要请教鲸。随后稍环顾四周,说道:‘话说回来,鲸们去哪儿了?’”
——科马克·麦卡锡《人与鲸》
2017年7月15日,来自坎波贝洛和鲸保护界的400多人齐聚岛上的小教堂,追悼,纪念乔的一生。这是坎波贝洛居民记忆中最大的一场葬礼。麦基·格林尼说:“有些人在岛上住了20,30年,但他们仍不是真正的岛民。乔是这座岛真正的居民。乔可以到任何人家里串门,不用敲门或打招呼;他就直接走进别人家,到冰箱里拿一瓶啤酒。如果茶几上有食物,他可能会吃一些。他早已融入这座岛,他是我们的家人。
加拿大运输部下令暂停鲸解救行动,并对事故进行了调查。托尼·霍维特这样形容他的兄弟:“如果这次事故发生在别人身上,他不会考虑自己,乔会开着自己的船,独自出海。他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事故发生后,格林尼提心吊胆地继续运营他的鲸观光生意,有孩子在船上时,他总担心鲸靠得太近。“鲸在船底时,我只想着逃离,”他说。
到2017年底,加拿大水域已经发现了12头死鲸,在美国水域发现了3头。2017年10月5日,加拿大野生动物健康合作组织公布了露脊鲸尸检报告,证实了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的事实:鲸死于船只撞击和渔线缠绕。同月,在露脊鲸保护联盟的年会上,马克·鲍姆加特纳和美国东北渔业科学中心的皮特·科克龙(Peter Corkeron)向与会者宣布,他们已经完成了估算。还有约100头可繁殖的雌性露脊鲸存活,每年至少有4-5头死亡。这意味着要保持种群数量稳定,每年必须要有4-5头露脊鲸幼崽出生。据我们所知,2018年,没有幼崽出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鲍姆加特纳说,“未来二十年内,露脊鲸将彻底灭绝。”
2018年3月,加拿大政府宣布实施正式、存有争议的保护计划。他们重启露脊鲸解救行动。格林尼和安东尼,一旦接到电话,将立刻出发行动。飞机和海上监视将会增加,加拿大运输部规定,途经圣劳伦斯湾西部,大型船只限速。
海岸警卫队试图在4月破冰,以便捕蟹渔民早日撒网(不巧,天公不作美,渔季迟来)。今年春天,在目击露脊鲸的海域,联邦海洋与渔业部禁止捕蟹作业。捕雪蟹的渔季也会在6月30日结束,较通常提早两周结束,几名渔人向渔业部提交了申请,测试新式无网螃蟹笼。所有的这些措施,虽饱受争议,但都实质性上改变了传统捕鱼方式,且对今年雪蟹的收成有很大影响。
希望,让我们在危机面前凝聚,但它也会助长叛逆。世界被塑料埋没,循环利用一小部分垃圾又有什么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攀升,减少开车又有什么用?格林尼和安东尼接替了乔,他们的工作并不是无足轻重——它很及时,且至关重要,可最终,也只是权宜之计。
如果鲸重新繁盛起来,为它们种族的延续争取到了时间,我们才算成功。曾经给它们带去末日的人类,若不做更多的干预,我们这辈子,恐难看到此景。现在我们远看着,撤走渔网,故意躲开它们。现在最好的假设也只是不会灭绝。梅奥说:“我必须向你强调,当种群数量非常低且呈下降趋势时,想要挽回,难度极大。”
我们在这颗星球留下的烙印太深,她已遍体鳞伤。想要彻底拯救,抚平伤痕已无可能。

帝王蝶迁徙
“人类的精英们被关爱诅咒,即使我们的视野模糊不清,笨手笨脚还不死心,无论如何都想要保护任何看上去美丽的东西。”
——乔恩•莫阿拉姆《野之物》
2017年春天,乔的兄弟托尼和他的妻子珂赛特在后院种了乳草,试图吸引帝王蝶。托尼说:“乔正在拯救鲸,我们就种些乳草来救帝王蝶。”
7月的一个下午,珂赛特第一次在外头发现这些蝴蝶,正当她仔细打理乳草时:两只鲜艳的橙色蝴蝶互相纠缠着,在花园扑翅翻飞。她立刻开始拍照,过于着迷甚至忽略了家里的手机铃响。“家里电话打不通就打我手机,我最好快去接电话。”她想着。一只手接着电话,一只手用相机拍蝴蝶时,她却听到了乔的噩耗。
“帝王蝶在墨西哥是死亡的象征,”今年3月托尼告诉我:秋寒潜入加拿大时,帝王蝶就开始它们的长途迁徙,南飞至中墨西哥的山脉。有阿兹特克神话如是说:橙色蝶群,每年于死亡之日以遮天之势而来,是逝世亲人之魂魄。
乔去世后约一个月,珂赛特和托尼留意到一条鲜艳的毛毛虫,正在木架下爬行。两人每天观察着它,这只蠕动的小生物随后变成了显眼的绿色蛹。8月25日早晨,珂赛特前去查看蝶蛹,透过外壳,她看到了蝴蝶斑斓的橙色翅膀,已是完全半透明,随时准备孵化。因为珂赛特还有工作要做,所以托尼代为静坐在蝴蝶旁,手机随时准备录像。他在那儿耐心等待了七个小时,直至帝王蝶破茧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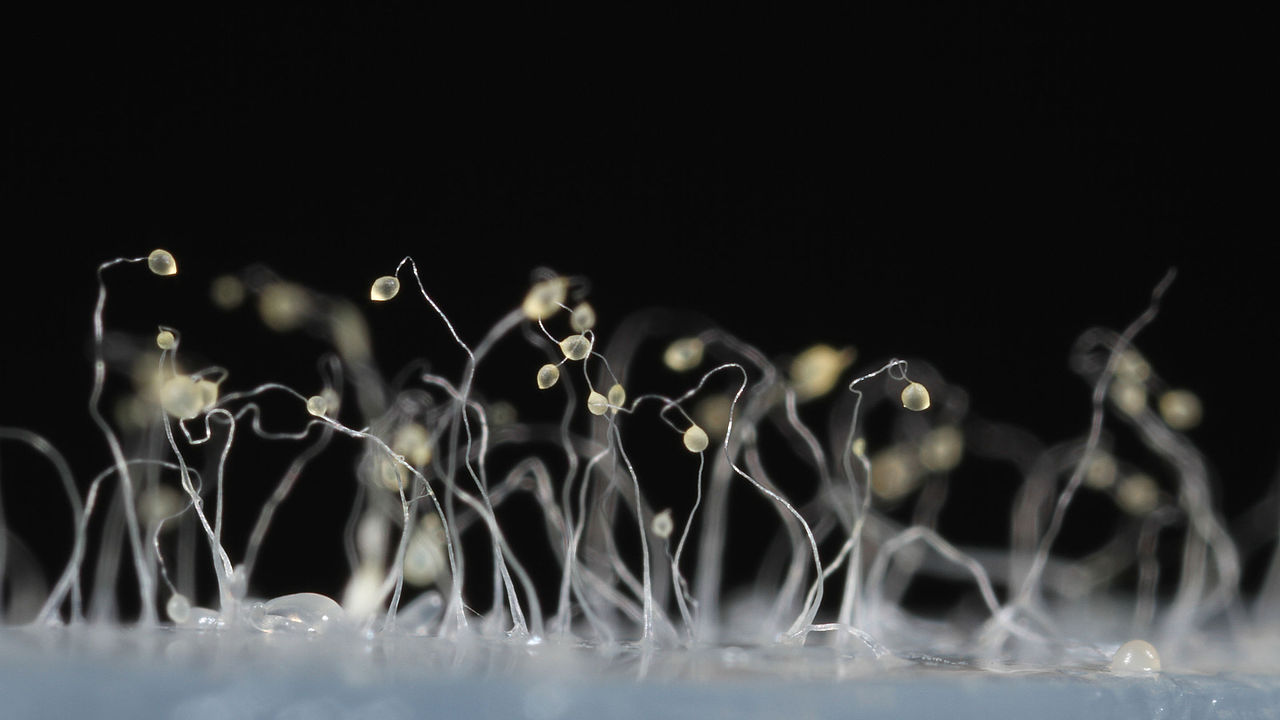

感到渺小,感到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