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解对方,
——尼采,欧若拉(Aurora)
即在自己身上模仿他的感受
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将自己置于
内部模仿,
在某种程度上,
在我们心中涌现出类似的情感
凭借古老的联系
运动与感觉之间的古老联系……
镜像神经元怎么了?
2006年1月10日,一则题为“读心神经元”(cells that read minds)的报道赫然占据《纽约时报》头条新闻位置。这则新闻宣布了大脑中存在一种特殊神经元,可以让灵长类动物模仿他人心理活动和预测其行为。事实上,在登台《纽约时报》亮相之前的十几年,以及之后的七八年间,这些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一直年复一年地出现在数百项科学研究中,也出现在众多报刊、新闻广播、书籍和 TED 演讲中——镜像神经元的讨论一直主导着读心、社会认知和交互主体性的话题。许多媒体的过度爆料一度让镜像神经元声誉日隆,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相信镜像神经元的活动有可能为我们人际交往的方式提供最佳解释。在学术界,动作模仿和读心只是被认为是这些所谓镜像神经元激活所致的几个话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300多篇文章将镜像神经元的功能延伸到了:意图理解、共情、商业管理、语言理解与产生、文学叙事、审美体验、述情障碍(alexithymia)、自闭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精神分裂症。许多学者对此反应强烈:“我预测,镜像神经元对心理学的作用就像 DNA 对生物学的作用一样:它们将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帮助解释迄今为止仍然神秘莫测、无法进行实验的大量心理能力。”(Ramachandran, 2000)。
遗憾的是,过度的媒体曝光和科学界爱蹭热度的陋习导致镜像神经元研究的声誉受损。至少从学术出版物的数量来看,人们对镜像神经元的兴趣2013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逐年下降。之于镜像神经元,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相较于前十年的进展,研究者已经能够借由分子生物学在因果层面上了解镜像机制的起源和功能。然而,镜像神经元这一研究选题在科学界受到了不公允的、过度严苛的审查与偏见,以至于研究者正在使用其他代名词来称呼它们,例如“动作观察网络”(action observation network)。
2022年,一篇发表《心理科学视角》(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的评论文章《镜像神经元怎么了?》(What happened to mirror neurons?)指出:“镜像神经元发现的影响在过去十年达到了顶峰,我们现在正在目睹它的衰落……这种神奇的神经元正在失去吸引力”(Heyes & Catmur, 2022)。然而,我们认为,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并非真正“盛极而衰”,通过追溯历史并追踪该领域的前沿动态,不难发现,镜像神经元在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内部的影响力依旧巨大。新的强健证据澄清了某些污名化的质疑,重新发现神经科学的原始文本中的那些证词。这些都进一步提醒我们反思,不必要的认知偏见与过分炒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秩序。
“心理学DNA”的意外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同他的导师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带领的团队正在记录猕猴前运动皮层中单个神经元的活动。他们希望区分猴子在观看物体时放电的神经元和猴子抓取物体时放电的神经元。然而,在实验过程中,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猴子观察到科学家抓取物体以重设实验时,一些原本在猴子抓取物体时发射的神经元再次放电。不管是猴子还是科学家在抓握物体,这些神经元都在放电。这种重复放电一直是仍然是镜像神经元的决定性特征。有趣是,早期的研究发现,镜像神经元需要生物效应器(手或嘴)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被视觉刺激触发。单独看到一个物体、看到一个模仿者的动作或看到一个人做出非及物性(非目标对象指向)手势都是无效的。物体对猴子的意义对镜像神经元的反应没有明显的影响。抓住一块食物或一个几何实体产生的反应强度相同。在没有视觉信号的情况下呈现与动作相关的声音信号也能激活镜像神经元的活动(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因此,加莱塞大胆假设,镜像神经元的活动反映的不仅观察者对动作视觉信息的编码,而且还对动作的意义(或意图)进行了编码:“当我们将观察到的动作的视觉表征映射到我们对同一动作的运动表征上时,我们就能理解动作。”(Gallese, 2005, p. 34)
随后,多种神经生物学与脑成像技术形成的收敛性证据链证实,与猴子的镜像神经元一样,人类镜像神经元广泛分布在经典顶叶-额叶回路(腹侧前运动皮层和顶下小叶)和非经典区域(背侧前运动皮层、顶上小叶、前脑岛、小脑、辅助运动区、内侧颞叶与基底神经节等)。由此,很多研究人员开始对这类在动作观察和执行中做出反应的神经元,会对于灵长类动物的生存适应会有什么“好处”产生兴趣——即,镜像神经元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进军心灵哲学和现象学
1998 年,帕尔马团队最具哲学家气质的神经生物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和哲学家阿尔文·戈德曼发文支持一种关于镜像神经元功能的假说:模拟理论(simulation theory)。该理论本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一种旨在解释读心加工过程的解释理论。按照模拟论的观点,读心就是归属给对象的状态被看作是归属者对那种状态进行示例、经历或体验的结果。这与镜像神经元的活动特征存在惊人的相似。鉴于传统的模拟论一般都将心理模拟视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想象+投射的过程,加莱塞和戈德曼认为:“镜像神经元可能是读心基础的模拟启发式(simulation heuristic)的原始版本,或者可能是种系发育的前体(precursor)”(1998, p. 498)。随后,加莱塞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具身模拟论(embodied simulation)。通过镜像神经元与具身模拟,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动作,一种情绪,或一类情感。与观察到的社会刺激的感觉描述对等的是观察者所产生的与动作、情绪和情感有关的身体状态的内部表征,就好像他做了相似的动作或体验了相似的情绪和情感。加莱塞认为具身模拟与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观点如出一辙:“动作的沟通或理解是通过我的意向和他人的动作、我的动作和在他人行为中显现的意向的相关关系实现的。所发生的一切像是他人的意向寓于我的身体中,或我的意向寓于他人的身体中”(Gallese, 2005, pp. 47-48)。
很快,来自人类fMRI的实验证据开始支持具身模拟论。体验厌恶和目睹他人面部模仿厌恶表情都会激活相同的神经结构——前脑岛。这种神经结构的损伤会损害体验厌恶和识别他人厌恶的能力(Wicker et al., 2003)。这表明,至少对于厌恶情绪而言,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对特定情绪的体验是由共同的镜像机制支撑的。当我看到一个特定的面部表情时,这种感知会让我把这种表情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但我并不是通过类比论证来完成这种理解的。他人的情感是通过产生共同身体状态的具身模拟来理解的。正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共享的身体状态促成了直接理解。相反,如果他人被观察到的行动与观察者自身的运动技能库(motor repertoire)匹配不了,那么其行动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就也无法被识别和理解 (Gallese, 2001)。
那么,具身模拟从何而来?这就涉及到对镜像神经元起源问题的回答。对此,帕尔马团队诉诸于进化立场,又称“适应说”(adaptation account)。类似的观点诸如“镜像神经元机制具有重要进化意义,灵长类动物凭此理解其同类做出的动作”(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 p.172);“在镜像神经元的基本属性中,它们构成了相对简单的动作知觉机制,这种机制在动物的进化过程中被多次运用(Bonini & Ferrari, 2011, p.172)。学术界普遍将这些观点视为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暗示了镜像神经元是与生俱来的(Cook et al., 2014)。
百口莫辩与被迫“误入歧途”
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在接下去的十五年里开始“井喷”。有关镜像神经元的科学论文数量加速增长,2013 年达到顶峰,仅当年就发表了 300 多篇论文。这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实验报告,但也充斥着很多蹭热度的假说、扭曲的科学普及与夸大其词的新闻报道。这期间,一些研究者尝试提基于联想学习提出了镜像神经元起源和功能的竞争理论。联想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是动物通过接触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学习的一种形式。该理论认为,镜像神经元系统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和过程,而并非是进化筛选出来专门服务于灵长类读心的神经相关物。对这一理论至关重要的是证据来自卡罗琳·卡特穆尔(Caroline Catmur)等人在 2007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镜像神经元系统可以在短短一小时内接受训练,在不同的线索下发生与原来不同的反应。在这项研究中,人们看着一只人类的手移动食指,但被要求移动他们的小手指作为回应。这种训练导致镜像神经元系统发生转换:原本在观察食指时出现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激活,后来只在观察小指时才激活。如果镜像神经元是一种基因适应,某些进化结构应该可以预测镜像神经元的发展对那些妨碍其适应功能的环境扰动具有抵御或“免疫”能力。
2014年,语言心理学家格雷戈里·希科克(Gregory Hickok)出版了一本名为《镜像神经元之神话》(The Myth of Mirror Neurons)的书,详细描述了数百篇科学论文中的逻辑谬误和相互矛盾的数据。同年,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理论生命科学高级研究员塞西莉亚·海斯(Cecilia Heyes)及其同事在系统整合来自联想学习理论的所有研究基础上指出,镜像神经元并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特殊读心能力。相反,镜像神经元是出生后在大脑中形成的,是对反复同时做和同时看同一个动作的反应,就像在同步舞蹈或被父母模仿时发生的那样(Cook et al., 2014)。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镜像神经元研究最为炙手可热之际,里佐拉蒂就曾冷静地反思:“我认为,‘镜像神经元和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得不好。镜像神经元并没有特定的功能作用。镜像神经元的特性表明,灵长类动物大脑具有一种将高阶视觉区域对动作的图像描述映射到其运动对应物的机制。这种匹配机制可能是多种功能的基础,这取决于所观察到的动作的哪一方面被编码、所考虑的物种、镜像神经元所包含的回路以及镜像神经元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连接。”(Rizzolatti, 2005, p. 419)然而,科学的吊诡之处在于:谨慎的判断无人理会,喧嚣的言论深入人心。
拨开浮云见长安
事实上,《镜像神经元之神话》一书甫一出版,就有多位知名学者对对希科克的观点进行系统批评。南加州大学的计算神经科学家迈克尔·阿尔比布(Michael A. Arbib)认为,该书的书名刻意挑衅,有吸引读者眼球之嫌。更准确的书名应该是《关于镜像神经元的神话》(The Myth about Mirror Neurons)。这是因为:(1)镜像神经元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被称为从“A到Z”(意指过度延伸的对镜像神经元功能的解释)一切的神经原因;(2)一些科学论文提供了出色的数据,但对这些数据的解释却不那么出色。这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物理学上有着严格的使用语境、内涵和限定条件,但公众甚至修养不佳的研究者会将其泛化使用,赋予其各种各样“无中生有”的解释力,由此出现的相对论的污名化不应由爱因斯坦及其理论来背锅。希科克在质疑帕尔马团队及其相关工作时,存在大量选择性报告和解释的嫌疑,这事实上是一种科学解释上忌讳的“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甚至是“采樱桃谬误”(cherry picking)。例如,本书在第 44-45 页,希科克谈到了里佐拉蒂和科拉多·西尼加利亚(Corrado Sinigaglia)(2010)对乔瓦尼·布奇诺(Giovanni Buccino)等人(2004)的观察结果的解释。即当人类观看狗叫视频片段时,fMRI 显示人类镜像神经元系统在口面部动作方面没有活动。里佐拉蒂和西尼加利亚(2010)断言:“这些数据表明,对他人运动行为的识别可能仅仅依赖于对视觉方面的处理。……(但只有当)观察者和行为者共享目标的运动表征时,才能真正理解动作。”(2010, p. 7)
希科克狡黠地反问:“养狗的人……可能会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Hickok, 2014, p. 45)。做出这个判断本身并非难事(现象学家舍勒曾在一个世纪前就对此有过精彩的评论)。一个人可以真正理解自己剧目之外的行为,而镜像神经系统之外的活动可能(至少有时)是理解的关键。但希科克没有注意到,布奇诺等人确实发现了人类观察者在观看人类说话的(无声)视频片段和猴子做出口面部交流姿势的(较少)视频片段时,镜像神经元系统都会产生活动。因此,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镜像神经活动的意义是什么?”此外,希科克指出,盲人可以识别狗叫声的意图,他认为这是对具身模拟论的反驳。然而,他不可能不清楚帕尔马团队关于“视-听镜像神经元”(audiovisual mirror neuron)的报道(其中一项实验发表2002年于《科学》杂志)——如果一个动作有独特的声音(掰花生、撕纸),那么即使看不见,也会有视听镜像神经元对动作的声音做出反应(Keysers et al., 2003)。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盲人的镜像神经元会对动作的声音做出反应。众所周知,听觉反馈对动作的成功执行起着关键作用。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值得严肃反思的残酷事实——帕尔马团队对镜像神经元研究的结论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事实上,早在2007年,加莱塞就曾明确指出,具身模拟并不是支撑社会认知的唯一功能机制(Gallese, 2007)。他人在不同情境下做出的相同动作,会让观察者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个女士拿起桌上的咖啡杯,下一个动作,可能是要喝一口咖啡,但也可能是要泼向有欺骗行为的渣男。只有理解前因后果的人,才能对女士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猕猴中的实验证明,镜像神经元,确实有根据不同运动背景(抓握-进食,抓握-放下),在放电频率上区分相同抓握动物的能力(Fogassi et al., 2005),fMRI研究人类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也有类似的区分功能,可以区别抓取动作是用于喝水或清理(Iacoboni et al., 2005)。
社会刺激也可以通过利用先前获得的关于待分析情境相关方面的知识,在对其情境感知特征进行明确认知阐述的基础上加以理解。我们将错误的信念归因于他人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最复杂的读心能力,很可能涉及到我们大脑中大量区域的激活,其规模肯定大于假定的和特定领域的心智理论模块。然而,具身模拟和目前仍鲜为人知的更复杂的心智认知技能并不相互排斥。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具身模拟可能是最古老的机制,它是以体验为基础的,而第二种机制的特点是对外部事态进行反思性、推理化的认知描述。很有可能,具身模拟为以语言为中介的命题式读心机制提供了支架。
里佐拉蒂等人(2014)明确强调了镜像机制并非是理解所有读心现象的必要条件:“镜像机制在理解他人行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机制参与这一功能。有些机制可能依赖于特定刺激与其效果之间的关联。例如,人们可以理解一个传达威胁的手势,但不一定要将其转化为运动形式。当猴子看到实验者向它投掷石块时会感到害怕,即使投掷石块的方式与猴子投掷石块的方式并不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里重要的是被石块击中的痛苦效果,而不是精确的手势镜像。”(Rizzolatti et al., 2014, p. 681)
不幸的是,这些声音全部被淹没在“镜像神经元之神话”这样的标签之下,它给读者造成了“镜像神经元的研究都只能当作故事来听”的思维定势,从而使读者在阅读后续章节时产生不应有的偏差。虽然镜像神经元的热度随着恶意炒作的落空而消退,而苛责的批评者往往也会在恰当的时候转移焦点,但它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举例来看,围绕以海斯和帕尔马团队为代表的阵营,虽然对镜像神经元的起源和功能提出了多种理论,但这些证据并不具有判决性意义,相关的假设检验陷入了僵局,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有关镜像神经元的核心问题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马克-让纳罗认知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皮尔·弗朗西斯科·法拉利(Pier Francesco Ferrari)认为,究其原因是当时缺乏分子水平的神经生物学实验模型来描述其机制,也没有操纵它的可能性。可喜的是,近十年来一系列高质量的实验研究坚实将该领域最初的争论推向纵深(Ferrari et al., 2023, p. 315)。
2019年,里佐拉蒂曾经的博士后、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Neuroscience)的克里斯蒂安·凯瑟斯(Christian Keysers)带领的团队首次在大鼠前扣带皮层(ACC)(人类研究中被认为是产生共情的主要脑区)找到“情绪镜像神经元”,它们能帮助大鼠以与亲身疼痛体验相同的编码方式对观察到的同类疼痛进行编码。研究人员还通过蝇蕈醇显微注射技术(muscimol microinjections)暂时灭活对扣带皮层的神经元活动进行暂时抑制,进而发现该脑区活动消失后,大鼠在观察其他同类被电击产生疼痛时不再出现冻结(freezing)行为。该行为一般出现在啮齿类动物感受到恐惧时出现的本能反应(Carrillo et al., 2019)。
2023年,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尼劳·沙阿(Nirao M. Shah)及其团队使用光纤光度记录法(Fiber photometry, FP)在雄性小鼠的下丘脑中发现了一组攻击镜像神经元(aggression-mirroring neuron),当小鼠身为打架“当事人”或“旁观者”时,这组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但激活机制有所不同。反过来,如果激活这组镜像神经元,也可以加强小鼠的攻击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即使是对于一只从来没看过也没参与过打架的雄性小鼠来说,观看别的小鼠打架时或在自己的首战中,VMHvlPR神经元也会被激活,这说明视觉输入而不是社会经验对于这些神经元的镜像反应才是必要的(Yang et al., 2023)。至少小鼠下丘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不是“后天学习”的产物,而是一种先天本能。这也为重启早先关于镜像神经元的“联想学习说”与“适应说”之争了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
而今迈步从头越
过去三十年,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历程如同过山车般惊心动魄。镜像神经元这个标签是否真的像海斯声称的那样“失去吸引力了”?对此,帕尔马团队中的第三代翘首学者卢卡·博尼尼(Luca Bonini)在长篇综述《镜像神经元30年之后:意义与应用》中给出针锋相对的回应:“镜像神经元研究的推进驱动力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不断发展”(Bonini et al., 2022, p. 767)。
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出于各种目的,通俗科学与网络媒体在传播科学信息之时,总是喜欢使用夸大的标题来吸引眼球,让公众对科学发展的轨迹产生严重误解,认为科学发展遵循的总是一个“大跃进”模型(great-leap model),即某一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某个关键实验得到解决,或者是某一个重要的灵感成就了理论的进步,并彻底颠覆了先前众多研究积累的全部知识。在科学史上,这种大跃进模型的确出现过(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典型的代表),但这仅仅是科学发展中的少数个例。即便是这种大跃进出现,也依旧不可能完全脱离科学研究的两大原则:关联性原则(connectivity principle)与收敛性证据原则(principle of converging evidence)(Stanovich, 2018)。前者是指任何新的科学理论必须与先前的已经确立的实证事实建立关联。换言之,这种理论不仅要能解释新的事实,还要兼容旧的事实。无论相对论的概念多么新颖,它都并非脱离牛顿力学,进而还解释了新的物理现象。后者是指任何科学研究不可能一次性解决该领域内的所有问题,只有一系列的研究才能逼近并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相对论的证明过程依靠的正是一系列严谨的收敛性证据,尤其是与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之间长期争论与互相质疑中积累的证据。这两个原则决定了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遵循的是一个渐进综合模型。之于镜像神经元研究及其相关理论学说,亦应作如是观。我们可以依稀看见附着在它光环背后铭刻着一连串伟大名字:威廉·詹姆斯、胡塞尔、特奥多尔·利普斯(Theodor Lipps)、梅洛-庞蒂、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 Gibson)……
无可争辩的是,镜像神经元领域内这样一种渐进综合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按照Web of Science最新的统计(截止2024年7月30日),镜像神经元研究发表数量已经达到4780篇,累计被引用次数更是达到惊人的264997次。正如加莱塞所说的:“动作理解的镜像神经元理论……即使是错误的,也为该领域带来了大量新发现、新观点和新反思”(转引自Lemon, 2015, p. 2111)。是的,即便是错的,它不过是帕尔马团队遭遇的小小挫折,但却是人类读心科学事业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Bonini, L., & Ferrari, P. F. (2011). Evolution of mirror systems: A simple mechanism for complex cognitive function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225(1), 166–175. https://doi.org/10.1111/j.1749-6632.2011.06002.x
Bonini, L., Rotunno, C., Arcuri, E., & Gallese, V. (2022). Mirror neurons 30 years later: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6(9), 767–781.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22.06.003
Buccino, G., Binkofski, F., & Riggio, L. (2004).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and action recognition. Brain and Language, 89(2), 370-376.
Carrillo, M., Han, Y., Migliorati, F., Liu, M., Gazzola, V., & Keysers, C. (2019). Emotional Mirror Neurons in the Rat’s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Current Biology, 29(8), 1301–1312. https://doi.org/10.1016/j.cub.2019.03.024
Catmur, C., Walsh, V., & Heyes, C. (2007). Sensorimotor learning configures the human mirror system. Current Biology, 17(17), 1527–1531. https://doi.org/10.1016/j.cub.2007.08.006
Cook, R., Bird, G., Catmur, C., Press, C., & Heyes, C. (2014). Mirror neurons: From origin to function.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7(2), 177–192.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13000903
Ferrari, P. F., Méndez, C. A., & Coudé, G. (2023).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mirror neurons sheds light on their functions. Current Biology, 33(8), R313–R316. https://doi.org/10.1016/j.cub.2023.03.028
Fogassi, L., Ferrari, P. F., Gesierich, B., Rozzi, S., Chersi, F., & Rizzolatti, G. (2005). Parietal lobe: from action organization to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Science, 308(5722), 662–66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06138
Gallese, V. (2005). Embodied simulation: From neurons to phenomenal experience.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4, 23–48.
Gallese, V. (2007). Embodied simulation: From mirror neuron systems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ovartis Foundation Symposium, 278, 3–12.
Gallese, V. (2001). The ‘shared manifold’ hypothesis: From mirror neurons to empathy.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8(5-6), 33-50.
Gallese, V., & Goldman, A. (1998). Mirror neurons and the simulation theory of mind-read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2, 493–501.
Heyes, C., & Catmur, C. (2022). What happened to mirror neuron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1), 153–168.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21990638
Hickok, G. (2014). The myth of mirror neurons: The real neuroscienc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WW Norton & Company.
Iacoboni, M., Molnar-Szakacs, I., Gallese, V., Buccino, G., Mazziotta, J. C., & Rizzolatti, G. (2005). Grasping the intentions of others with one’s own mirror neuron system. PLoS Biology, 3(3), e7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bio.0030079
Lemon, R. (2015). Is the mirror cracked? Brain, 138, 2109–2111. https://doi.org 10.1093/Brain/Awv131
Keysers, C., Kohler, E., Umiltà, M. A., Nanetti, L., Fogassi, L., & Gallese, V. (2003). Audiovisual mirror neurons and action recognition.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153(4), 628–636. https://doi.org/10.1007/s00221-003-1603-5
Ramachandran, V. (2000). Mirror neurons and imitation learning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treat leap toward in human evolution. Edge, 69, 5–31.
Rizzolatti, G. (2005).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and its function in humans. Anatomy and Embryology, 210(5-6), 419–421. https://doi.org/10.1007/s00429-005-0039-z
Rizzolatti, G., & Craighero, L. (2004). The mirror-neuron system.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7, 169–19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neuro.27.070203.144230
Rizzolatti, G., Cattaneo, L., Fabbri-Destro, M., & Rozzi, S. (2014). Cort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organization of goal-directed actions and mirror neuron-based action understanding. Physiological Reviews, 94(2), 655–706. https://doi.org/10.1152/physrev.00009.2013
Rizzolatti, G., & Fogassi, L. (2014). The mirror mechanism: recent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9(1644), 20130420. https://doi.org/10.1098/rstb.2013.0420
Rizzolatti, G., & Sinigaglia, C. (2010). The functional role of the parieto-frontal mirror circuit: interpretation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1(4), 264–274. https://doi.org/10.1038/nrn2805
Stanovich, K. E. (2018). 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Pearson.
Wicker, B., Keysers, C., Plailly, J., Royet, J. P., Gallese, V., & Rizzolatti, G. (2003). Both of us disgusted in My insula: the common neural basis of seeing and feeling disgust. Neuron, 40(3), 655–664. https://doi.org/10.1016/s0896-6273(03)00679-2
Yang, T., Bayless, D. W., Wei, Y., Landayan, D., Marcelo, I. M., Wang, Y., DeNardo, L. A., Luo, L., Druckmann, S., & Shah, N. M. (2023). Hypothalamic neurons that mirror aggression. Cell, 186(6), 1195–1211.e19.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3.01.022
关于作者
蝙蝠Chin:心理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研究员,同济大学心理学系、澳门城市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渐变、扎染、金属色系等等一切迷幻主义色彩爱好者。
索麻Soma(刘童玮):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反神经狂热主义的神经科学爱好者,哈利波特迷,喜欢收藏各种吗喽表情包。
Landowph:德国图宾根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中德转化医学协会理事会成员,国内某创业公司神经再生高级研究员,快乐的段子手,偶尔写个诗,希望以后能撸猫、遛狗~
心理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研究员,同济大学心理学系、澳门城市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渐变、扎染、金属色系等等一切迷幻主义色彩爱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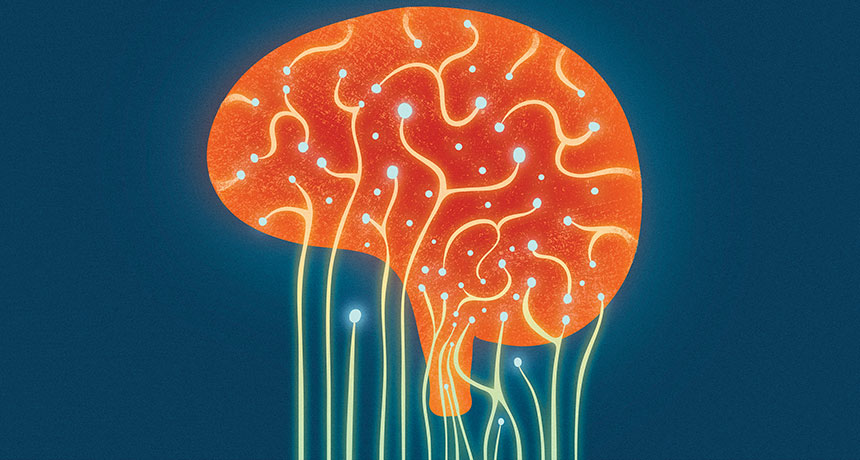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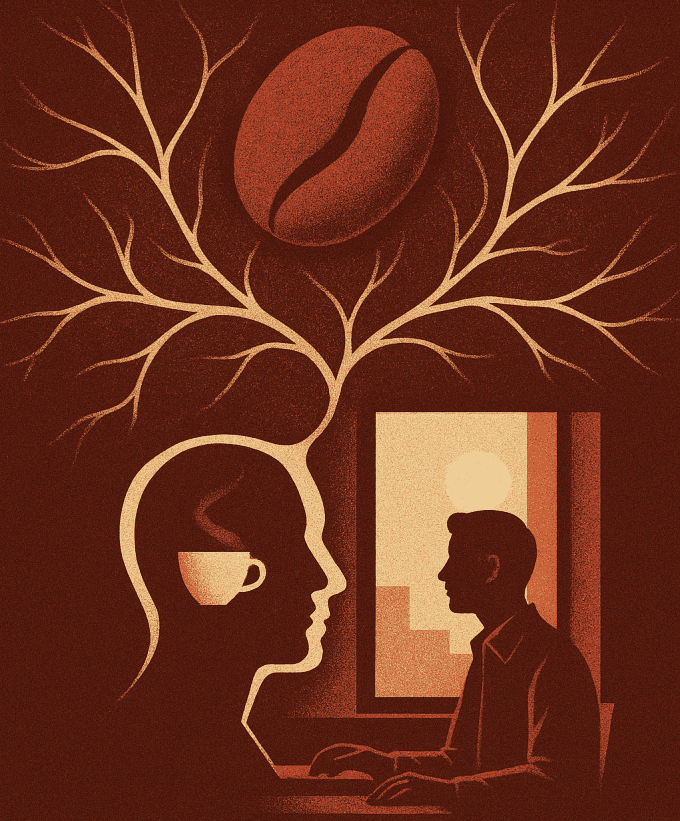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