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在一辆公交车上醒来,周身堆着你的随身物品。几个同行的乘客瘫在你旁边浅蓝色的座位上,脑袋靠着车窗。转头,你看到一位怀抱儿子的父亲。几乎所有人都酣然入睡,除却一个留灰白胡子穿卡其布背心的男人。他站在车末,正直直地盯着你看。你坐立不安,瞥向司机,想知道他能否在你需要的时候救你于水火。当你再次回头,那个留胡子的男人已经靠近,现在离你只有几步远了。你一惊,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但随后提醒自己没什么可担心的。摘下Oculus,你意识到自己回到了现实,在斯坦福大学的杰里米·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的虚拟人机交互实验室里。

对于越来越多的硅谷人来说,一趟冗长而危险的巴士之旅不是一场模拟,而是现实。脸书和谷歌发源之地圣克拉拉县坐拥全美第二密集的财富。这里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只有富人才有能力安顿下来。在美国科技中心帕洛奥托,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在两年内惊人地增长了26%,其中大多是有孩子的家庭。这些人投奔避难所、露营地,而在更艰难的时候,22路公交车是他们的家。
斯坦福的校园一片田园风情,而就在1.6公里外,22路公交车从帕洛奥托驶往圣何塞,整夜穿梭于两城之间。硅谷的无家可归者常到这里寻求安全和庇护,次数如此之多,以至于这里被亲切地称为”22号旅店“。几十个人往返于两地度过午夜,组成一列井然有序而精疲力竭的队伍。他们用90分钟从一地坐到另一地,下车,随后立即回到车上。22路公交车的司机深谙此事。从第一站出发后,一位司机会用车内对讲机广播,“不要躺下,不要把脚放在座位上……尊重下个上车的乘客,因为他们要去上班了。让我们有个美好、安全的旅程;不要出任何差错。任何人想捣乱的话,你知道后果的。”
帕洛奥托的皇家大道上,一辆特斯拉2019年款候在专卖店里,等着被新的千万富翁捞走。沿这条路,一排排房车停放了好几天,里边住着刚遭遇生活变故的家庭。当这样的对比无法再震撼我们,便意味着我们已经对无家可归者的苦难视若无睹了。有时我们完全忽视他们的人性。在一项研究中,神经科学家向人们展示了来自不同群体的照片,包括生意人、运动员和父母,同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他们的大脑。面对大多数群体的照片时,人们大脑中与同理心(empathy)相关的部分都被激活,只有无家可归者的照片例外。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同理心经演化而来。为了更容易地感受彼此,我们几千年来变了许多。我们的睾丸酮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脸庞柔软下来,也不那么好斗了。我们演化出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多的眼白,以使我们更容易地追随他人的目光,我们还演化出复杂的面部肌肉来更好地表达情感。我们的大脑不断发展,让我们更精确地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随之而来的是极强的同理心。我们不仅能进入朋友和邻居的大脑,知晓他们的思想,还能知晓敌人、陌生人,甚至电影或小说中幻想人物的思想。这让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善良的物种。与人类相似的物种——比如黑猩猩,它们虽一起行动并在困难时刻抚慰彼此,但它们的善意比起人类来更有限。它们很少分享食物,而且它们的善意仅留给自己的族群,对其他族群则充满敌意。
相较之下,人类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合作者,对彼此的帮助远胜于其他物种,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作为个体,我们很渺小,但合作起来,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超级有机体,上能捕猎猛犸象,下能建设斜张桥,统治整个星球。
现代社会已然让善意举步维艰。2007年,人类跨过一条伟大的里程碑——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越了非城市人口。到2050年,将有三分之二人类居住于城市。但我们也因此愈发孤立。1911年,5%的英国公民独居;一个世纪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1%。城市年轻人的独居比例上升得最明显——在美国,18至34岁的人现今的独居比例是1950年的十倍。巴黎和斯德哥摩尔的居民有一半独居,在曼哈顿和洛杉矶的部分区域,90%的居民独居。
随城市扩大和家庭缩小,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认识的人却更少了。那些让我们定期与人接触的仪式——教堂礼拜,团队运动,甚至是买杂货——已经让位于个体追求,而这种追求通常通过互联网完成。街角商店里,两个陌生人或寒暄一二,谈到篮球,学校体制,或者电子游戏,渐而了解彼此的各种琐事。互联网上,有关陌生人,我们首先知道的也常常是我们最不喜欢的部分,例如对方令你反感的意识形态。这让人们在有机会成为人之前,先成为了敌人。
要是你打算设计一个泯灭同理心的社会制度,你几乎不可能比我们所创造的社会做的更“好”了。在某种程度上,同理心已经泯灭了。不少科学家认为同理心是渐渐消失的。过去四十年心理学家测量了人们的同理心,而情况不太乐观。同理心已然稳定减弱,在21世纪尤甚。平均而言,2009年的我们比1979年75%的人更缺乏同理心。
现代社会的地基是人与人的彼此连接,而我们的上层建筑正摇摇欲坠。过去十二年里,我研究了同理心如何运作、如何影响我们。但在今天做一个研究同理心的心理学家,和做一个研究极地冰川的气候学家没什么两样:我们逐年发现它的价值,而它逐年在我们身边消失。一定得这样吗?
无家可归者成了测试同理心最难的关卡。承认这些人的存在是令人痛苦的;这会引发内疚;这会打破人们想象中的公正世界。在同理心的拉锯战中,逃避终成胜者。杰里米和我在斯坦福着手研究的是,我们能否用沉浸式技术使关心边缘人群更容易,更自然,甚至无法逃避。
十多年前,杰里米的实验室这样的技术仅存在于科幻小说。几年前,这样的技术专有、昂贵而且错漏百出,只是个撩人却缺乏实用性的想法。几年后,它爆发了,2014年,脸书以近20亿美元收购了Oculus VR。同时,一系列便宜便携的设备,价格从10至300美元不等,使虚拟现实对普通人来说触手可及。杰里米表示这并非是在媒介领域的跃进。“虚拟现实技术比之前任何媒介在心理层面都强大。”他写道。它的秘密武器就是杰里米所说的“心理在场”(psychological presence)。书籍和电影将我们带入故事,但读者和观众仍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故事之外。虚拟现实则完全包裹住人们,让他们置身于故事,以至于忘记媒介本身。他们会将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混淆,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虚拟经验对他们来说非常真实。
许多被驱逐的穷苦工人最终住在汽车里。作者发现,在虚拟现实中经历无家可归的体验有助于参与者不再非人化无家可归者。
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了幻想,而且几乎肯定会定义游戏与色情作品的未来。但“心理在场”也能让我们在真实经验中有所突破。杰里米表示,这就是这项技术的真正力量所在。橄榄球四分卫借助它提升对运动场地的视觉感知,而医学生用它练习复杂的手术。虚拟现实技术在两类情况皆促进快速、深入的学习。
虚拟技术也能让人们亲身体验成为老年人、其他种族或色盲是什么样的。杰里米和他的同事发现,这些经验减少会人们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这些发现让艺术家克里斯 · 米尔克(Chris Milk)称赞虚拟现实为“终极共情机器”。2014年,米尔克制作了虚拟现实电影《西德拉上空的云朵》(Clouds Over Sidra),它讲述了约旦扎塔里难民营中一个12岁女孩的故事。当时,约旦约有8.4万名叙利亚难民。观众和西德拉“见面”,花时间与她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并探索沿途的营地。米尔克最近把这部电影和观看这部电影所必需的Oculus设备带到了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这些人,”他沉思道,“他们本来或许不会坐在难民营的帐篷里……但在某个下午,在瑞士,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在那儿。”米尔克说,那种“在那儿”的感受很重要。他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解释道,”你不是通过电视屏幕旁观,而是和她坐在一起。当你往下看,你正和她坐在同一片土地上。正因为如此,你能从更深的层面感受到她的人性。你会以更深的方式同情她。”
这个想法简单而有力。的确,科技让我们更难看到彼此。但换个角度,它能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
米尔奇的电影生动地描绘了虚拟现实的力量,然而,对于沉浸式技术是否真能建立同理心的实验研究寥寥无几。我们有理由心存怀疑。想象你告诉某人他有机会在难民营里待上一个小时,谁会同意,谁又会摇头走开呢?那些不想与人共情的人,很可能压根不想进入一个“共情机器”。的确,虚拟现实技术可能会让已经关心着他人的人更进一步,而问题在于,它是否不过如此。
大约三年前,杰里米和我,还有我们的学生费尔南达和艾瑞卡,决心找出答案。我们设计了一套虚拟现实体验,以帮助湾区的居民以全新视角看到他们无家可归的邻居。使用Oculus Rift,“观众”能探索各种场景,走进无家可归者的故事。观众首先在他的公寓“醒来”,面临着被驱逐,他接着被要求清算家当以维持开销。这一幕后,观众发现自己住在车里。一名警察发现他非法滞留并扣押了车辆。观众最终来到了22号旅店。在这最后一幕中,他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乘客的情况。如果他“点击”旁边的父亲和儿子,一个声音会解释道,“这是雷,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名叫伊桑。伊桑的母亲患有慢性病,最近去世了。她留下的医院账单让雷负债累累。他们在家庭收容所的候补名单上。因此,在有空位出现之前,他们晚上都睡在公交车上。”

杰里米和我相信,让人们在无家可归者的虚拟生活中走一遭会让他们产生同理心。但是,虚拟现实会比传统方法建立更多的同理心吗? 为验证这一点,我们在实验中分组,让一些人完成我们的虚拟现实练习,同时让其他人通过阅读同样的故事ーー被驱逐、扣押、 22号旅店ーー同时想象主人公的想法和感受。在许多研究中,这类设身处地的练习已经成功地增强了同理心,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实验中,虚拟现实技术面临挑战。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和杰里米打赌,虚拟现实技术并不会比技术含量较低的媒介带来更多同理心。
我错了。一开始,这两项活动都增加了人们对无家可归者的同理心,甚至使他们更愿意向当地收容所捐款。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测试他们的关怀时,差异就出现了。我们向参与者介绍了一号提案,这是一项无记名投票法案,将扩大旧金山湾区的社会福利住房改革计划,同时略微增加税收。参与我们实验的人说他们支持这项措施,但是当我们给他们机会签署支持这项措施的请愿书时,那些完成虚拟现实的人更有可能同意这项措施。这项技术创造的同理心也更持久。在参与研究一个月后,经历虚拟现实的参与者仍然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投票倡议,并且比其他参与者更不倾向于非人化无家可归者。
杰里米和我都不相信虚拟现实是完美的共情机器。有些经历根本无法模拟出来。我们可以让某人在22号旅店待上几分钟,但我们没法让他们感受到长期饥饿下无止境的绝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虚拟现实可以提高人们的好奇心ーー这促使他们更多地了解那些本来会被忽视的人。杰里米和他的团队已经在湾区附近的商场和博物馆安装了我们的“22号旅店”VR装置,已有几千人体验过。在《杀死一只反舌鸟》(To Kill a Mockingbird)中阿提克斯 · 芬奇(Atticus Finch)给斯科特(Scout)的提议是,“你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设身处地……除非你披着他的皮囊行走于世。”随着虚拟现实技术愈发普及,数百万人将有机会“设身处地”。
翻译:汉那;审校:Ziming Yuan;编辑:兔毛
Can We Revive Empathy in Our Selfish World?
An experiment shows how to rebuild human compa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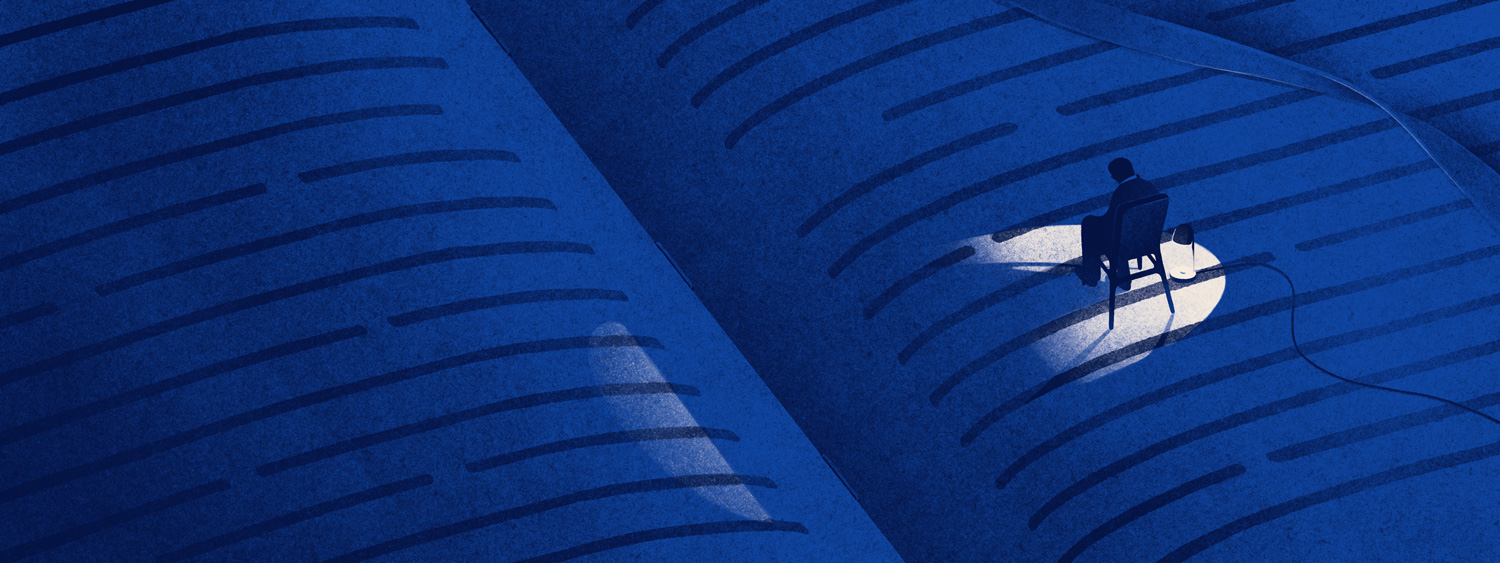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