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取电话号码并将其键入手机之间的间隙,你可能会发现你对这些数字的记忆出现了错乱——即使你已经将第一个数字烙印在记忆中,最后一位数字仍可能莫名其妙变得模糊。6是在8之前,还是之后?你能确定吗?
视觉工作记忆保证我们能将这类信息碎片保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备后续调用。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工作记忆的容量限制来自何处:是由于工作记忆只能同时存储几个项目,还是因为我们对于记忆细节的存储空间有限。换句话说,大脑到底是把容量分布给了几个清晰的记忆项目,还是更多个模糊的记忆碎片。
根据纽约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人员最近发表在《神经元》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工作记忆的不确定性可能与大脑监测和使用模糊性(ambiguity)的方式有关。通过使用机器学习,研究员分析了人们完成记忆任务时的大脑扫描结果,他们发现,信号编码了人们认为自己看到的东西的估计,而信号中噪声的统计学分布则编码了记忆的不确定性。感知的不确定性可能是大脑回忆表征中的一部分。不确定性可能有助于大脑就如何使用记忆做出更好的决定。
*译者注:Li, Hsin-Hung, et al. “Joint representation of working memory and uncertainty in human cortex.” Neuron 109.22 (2021): 3699-3712.
纽约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克莱顿·柯蒂斯(Clayton Curtis)说,这项研究表明“大脑使用了这种噪音”[1]。
这项工作结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看似不擅长理解统计学,大脑却能通过概率解释其对世界的感官印象,包括当前的和回忆的。这一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我们对不确定世界的感知赋予了多少价值。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当我们回想一段记忆时,对这段记忆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被提取出来。| Myriam Wares
基于过去的预测
视觉系统中的神经元会对特定的环境刺激做出反应,例如某种角度的线条、特定的图案,甚至是汽车或面孔,然后向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释放信号。但就其本身而言,单个神经元是嘈杂的信息源,因此“大脑不太可能通过单个神经元(的信号)来推断它所看到的东西。”柯蒂斯说。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大脑拼凑了来自神经元群体的信息。因此,了解这个过程的运作方式很重要。例如,大脑可能对来自各个细胞的信息取均值。如果某些神经元在看到45度角时放电最强,而其他神经元在90度角时最强,那么大脑可能对它们的输入信号进行加权平均,以表征视野中的60度角。或者,也许大脑有一种赢者通吃的方法,它能够将最强烈放电的神经元作为感知的指标。
“(但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运用贝叶斯定理。”柯蒂斯说。
对纽约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克莱顿·柯蒂斯来说,最近的分析表明,大脑使用其神经电信号中的噪声来表示其编码的感知和记忆中的不确定性。| Clayton Curtis
贝叶斯定理以其开发者、18世纪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的名字命名,由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独立发现并推广。这个理论将不确定性纳入处理概率问题的方法之中。贝叶斯推断可以用来分析根据已知情况,人们对于期望结果的置信程度。当应用于视觉时,这种方法可能意味着大脑通过构建一个似然函数来理解神经信号。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就变成了,根据以往经验的数据,最有可能产生该放电模式的景象是什么?
拉普拉斯认为,条件概率是探讨任何观测的最准确的方式。在1867年,医生和物理学家的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将条件概率与我们的大脑在感知过程中可能进行的计算联系起来。然而,直到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神经科学家们才开始关注这些想法。那时研究人员刚刚开始发现人们在行为实验中进行了类似概率推断的过程,贝叶斯方法也开始在一些感知和运动控制模型中被证明是有用的。
“人们开始认为大脑具有贝叶斯性质。”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这篇论文的另一位作者马伟基(Wei Ji Ma)说[2]。
在2004年的一篇评论中,亚历山大·普吉(Alexandre Pouget)(现为日内瓦大学神经科学教授)[3]和罗切斯特大学的大卫·尼尔(David Knill)讨论了“贝叶斯编码假说”,该假说假定大脑使用概率分布来表征感官信息[4]。
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马伟基(Wei Ji Ma)提供了一些最早的实证,证明神经元群体可以执行最优贝叶斯推理计算。| Wei Ji Ma
扫描记忆
在那时几乎没有来自神经元研究的证据支持这个假说。但在2006年,罗切斯特大学的马伟基、普吉和他们的同事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5],表明模拟神经元群体可以执行最优贝叶斯推断计算。马伟基和其他研究人员在过去十几年的进一步工作中使用名为贝叶斯解码器的机器学习程序来分析实际的神经活动,从电生理和神经影像中进一步证实了该理论适用于视觉[6]。
神经科学家已经能够使用解码器来从人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中预测人们看到的内容。可以对程序进行训练,以找到呈现的图像与人们看到图像时大脑中的血流和神经活动模式之间的联系。贝叶斯解码器不会做出类似“被试正在注视85度角”的单一的猜测,而是产生一个概率分布。这个分布的平均值代表了对被试最有可能看到的东西的预测。描述分布宽度的标准偏差被认为反映了被试对景象的不确定度(是85度抑或是84度或86度?)。
在最近的研究中,柯蒂斯、马伟基和他们的同事将这一想法应用于工作记忆。首先,为了测试贝叶斯解码器是否可以追踪人们的记忆而不是感知,他们让fMRI机器中的被试盯着一个圆圈的中心,圆圈的外围上有一个点。圆点消失后,志愿者被要求将视线移到他们记忆中圆点所在的位置。
工作记忆的含义和不确定性 | Samuel Velasco
研究人员将记忆任务期间记录的10个涉及视觉和工作记忆的脑区的fMRI图像输入到解码器中。该团队观测了神经活动分布的平均值是否与被试所报告的点的位置的记忆一致,抑或是反映了点的实际位置。在其中六个区域中,均值确实更接近于记忆中的位置,这使得第二个实验成为可能。
贝叶斯编码假说认为,至少应该有一部分脑区中的分布宽度反映了人们对记忆内容的置信度。柯蒂斯说:“如果分布非常平坦,那么你将以同样可能性从极端值或中间值中提取记忆,因此,你的记忆应该会更加不确定。”
为了评估人们的不确定性,研究人员要求被试对记住的点的位置下赌注。被试有动机去记忆得更精准——如果他们猜到的位置范围更小将会得到更多的分数,而如果他们错过了真实的位置就没有分数。这些赌注实际上是被试对其不确定性的自我报告测量,研究人员可以以此寻找赌注与解码器分布的标准偏差之间的相关性。在视觉皮层的两个区域,V3AB和IPS1,分布的标准差与被试的不确定性的大小表现出了一致的相关。
嘈杂的测量
这些观察到的活动模式可能意味着,大脑使用相同神经元群体编码对某个角度的记忆的对该记忆的置信度,而非将不确定性信息分别存储在不同的脑区中。“这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柯蒂斯说。“这真的很了不起,因为它们被共同编码在一起。”
尽管如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实际上这种相关性非常低。”剑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保罗·贝斯(Paul Bays)说[7]。保罗也研究视觉工作记忆。与视觉皮层相比,fMRI扫描的粒度非常粗,每个数据点都代表了数千甚至数百万神经元的活动。鉴于该技术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完全能够在这项研究中观察到各种现象已经非常不容易。
纽约大学柯蒂斯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Hsin-Hung Li 使用脑部扫描仪测量与工作记忆相关的神经活动,然后评估研究对象对记忆的不确定性。| Hsin-Hung Li
纽约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新论文的第一作者Hsin-Hung Li表示[8]:“我们正在使用一种非常嘈杂的测量方法来梳理一个非常小的东西。”他说,未来的研究将通过在任务中制造更大范围的不确定性,让被试对其中一些图像非常确定,而对另一些图像非常不确定。这种处理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明确其中的相关性。
尽管研究结果很有趣,但对于如何编码不确定性的问题,这项研究只提供了初步和部分的答案。“这篇论文正在论证其中一个解释,即不确定性实际上是被编码在神经元组中的活动水平中的。”贝斯表示,“但是利用fMRI可以揭示的的现象依然非常有限。”
其他解释也是可能的。也许记忆及其不确定性是由不同的神经元存储的,这两组神经元的位置可能极为相近。或者也许除了单个神经元的放电之外,有其他东西与不确定性的相关性更强,只是目前的技术无法解决。理想情况下,各种证据类型例如行为的、计算的和神经元的都应该一致指向相同的结论。
我们四处走动时大脑中一直进行着概率分布表征,这个想法非常美好。根据普吉的说法,这种结构可能不仅仅只适用于视觉和工作记忆。他说,“这个贝叶斯理论非常普遍。”当大脑进行决策时,无论是在评估你是否饿了还是进行导航,“这个通用的计算因素都在起作用。”
然而,如果计算概率是我们感知和思考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人类会因不擅长概率而闻名呢?众所周知,来自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估计方面犯了无数错误,导致他们高估了某些危险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而低估了其他事情的发生。“当你要求人们明确地、口头地估计概率时,他们的表现会非常糟糕。”普吉说。
但“这种可以在文字问题和图表中表达出来的概率估计依托于大脑中的另一个认知系统,该系统比本研究中着眼的系统演化时间更晚。”马伟基说。感知、记忆和运动行为已经通过更长的自然选择过程得到磨练。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发现捕食者或错误判断危险就意味着死亡。长久以来,对记忆中的感知做出快速判断的能力[9],也许包括对其不确定性的估计,这些使我们的祖先得以存活下来。
参考文献
1.https://as.nyu.edu/faculty/clayton-e-curtis.html
2.https://as.nyu.edu/faculty/weiji-ma.html
3.https://www.unige.ch/medecine/neuf/en/research/grecherche/alexandre-pouget/
4.https://www.cell.com/trends/neurosciences/fulltext/S0166-2236(04)00335-2?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166223604003352%3Fshowall%3Dtrue
5.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n1790
6.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n.4150
7.https://www.psychol.cam.ac.uk/people/paul-bays
8.https://www.cns.nyu.edu/malab/people.html8(3), 293-305.
9.https://www.cell.com/neuron/fulltext/S0896-6273(08)00803-9?_returnURL=https%3A%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ieve%2Fpii%2FS0896627308008039%3Fshowall%3Dtrue
作者:Veronique Greenwood | 排版:平原
译者:Jiatong | 校对:山鸡 | 编辑:山鸡
原文: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neural-noise-shows-the-uncertainty-of-our-memories-20220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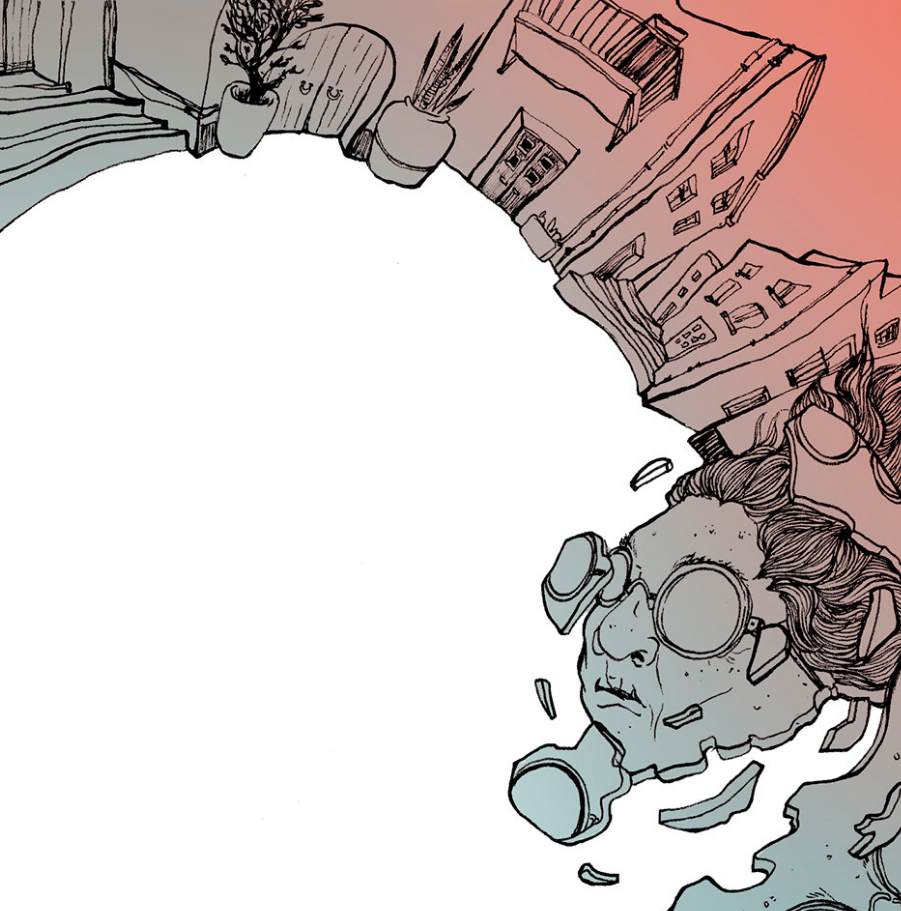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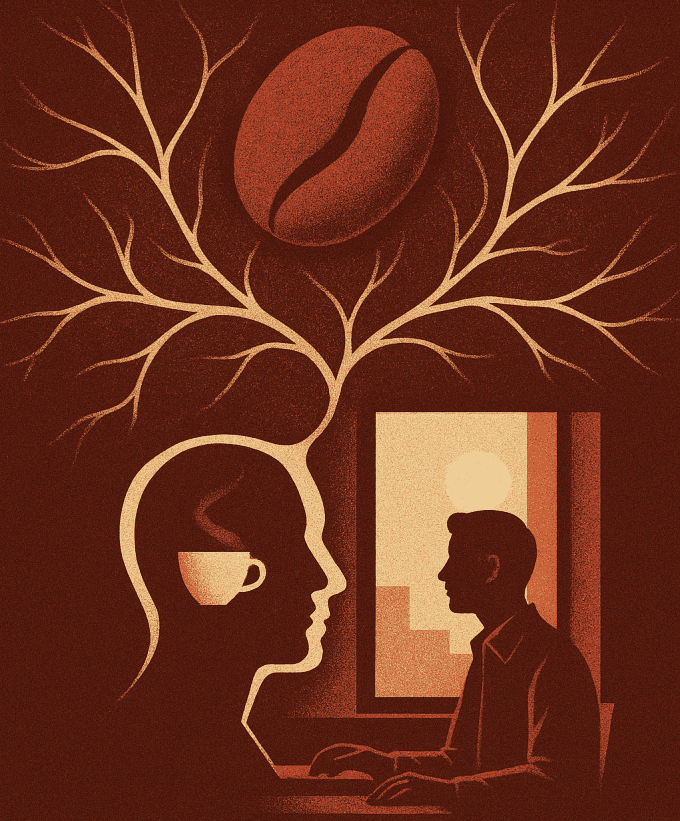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