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向神经现实的读者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你们好,我叫埃里克·蒂埃森(Erik Thiessen),2004年受聘于卡耐基梅隆大学,现担任心理学教授。我于2004年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取得发展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婴幼儿的语言习得。
第一个问题:一些婴儿学会说话较早,而另一些则较晚,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基因决定的,还是说婴儿的性格也有一定作用?
好问题。这种语言习得开始时间的差异,可能是婴儿语言习得过程中最容易注意到的事情了。最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在婴幼儿期要比在成年期显著得多。例如,十二个月大时,一部分婴儿会说话,而另一些则不会。但等到了十二岁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说话了。所以早期的显著差异大多会在之后的人生中均化。
从另外一种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考虑特定型语言障碍(Specific Langauge Impairment)的情况。当儿童的语言习得速度处于最慢的10%时,就会被诊断为特定型语言障碍。被诊断为这种障碍的孩子并没有身体畸形或者神经功能的缺陷,与其他孩子的区别仅仅在于原因不明的语言发展缓慢。绝大多数有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孩子,随着慢慢发育成熟,可以正常交谈。所以就算是处于学习语言最慢的10%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可以自行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研究语言习得的差异时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对这些差异进行区分:在童年早期出现的这些差异中,到底哪些差异是会贯穿孩子一生的。换句话说,一些早期差异只是随机噪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失。但另外一些语言则有可能会贯穿整个童年,甚至持续到成年后。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语言习得受到遗传因素影响。例如,如果你被确诊为持续性特定语言障碍(Persistent Specific Language Impariment),相比没有被诊断为语言障碍的成年人,你的孩子更有可能被诊断为特定性语言障碍。我们通过研究双胞胎和家谱遗传分析(e.g., Tosto et al., 2017),能够确定语言习得受遗传因素影响。
语言习得受性格因素影响吗?也许吧。婴儿时期的“性格”与成人时期的“性格”,指代的并不是一个东西。 因为婴儿无法像成人一样表达很多行为和意见,所以它们的“性格”结构更简单。我们经常用另一个词来指代婴儿时期的性格影响——气质(temperament)。它基本上就像一个简化版的性格,只有两个维度。你是快乐还是暴躁?你对变化的反应是好奇还是消极?事实证明,这一气质矩阵确实能勉强预测语言习得。如果控制其它因素,面对社交挑战时更外向、更有韧性的孩子们会稍快地到达语言上的里程碑。
不过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是语言输入的影响。语言输入可能是影响语言习得中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所谓语言输入,就是指你听到多少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听到这种语言的场景是什么?例如,同样的一句话,如果是你的父母在和你对话,努力与你沟通,就是能够给你提供有用信息的。相反,如果这句话发生在两个成人之间,而非成人对婴儿,那么对婴儿来说,这句话所提供的信息可能要少得多。这是因为当大人和宝宝说话时,大人会努力确保两个人的注意力都在同一个环境对象上。然而,当两个大人互相交谈时,成年人没有努力让宝宝注意力集中在对话主题上,宝宝很有可能就会把注意力投射到别的事物上。相比较而言,从一个别人真正关注你,并试图谈论你所关注事物的环境中学习,要比从一个人们泛泛交谈,但并不明确关注你的环境中学习,容易得多。
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当我们和婴儿交谈时,我们使用的是婴儿指向言语(Infant Directed Speech)吗?
注:婴儿指向言语,也指”宝宝语“,特指成年人在与低龄幼童和婴儿说话时使用的语音语调,有用词较简单、音高声调曲线较大的特征”。
婴儿指向言语很重要。婴儿从他们听到的婴儿指向言语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他们从比成人指向言语(Adult Directed Speech)中更多。但这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当大人与宝宝交谈时,他们会对宝宝所做的事情做出反应。当宝宝看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成百上千的东西——爸爸妈妈是怎样谈论那些成百上千的东西呢?他们谈论的是宝宝正在看的那些。
所以,如果宝宝正在看一个球,爸爸妈妈则更可能谈论那个球。爸爸妈妈对孩子关注的东西做出了回应,也就使得语言输入更适合宝宝学习的信号。
这与共同注意(Joint Attention)有关吗?
对,我们说的就是共同注意。在成年人间,共同注意像是协商。比如你想聊那个蓝色的东西,而我想聊那个红色的东西。我们需要“协商确定”到底聊哪个东西。我们互相“出价”,“兜圈子”,互相协商并弄清楚最终要谈论的是哪个东西。而婴儿和成人间并不会如此“讨价还价”。相反,在一个真正高质量的语言环境中,往往都是宝宝提出要求,而父母满足要求;婴儿看东西、指东西、做事情,而父母对此作出回应。这对于宝宝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当成年人之间协商时,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你想谈谈红色的东西。我想谈谈蓝色的东西。如果你说服我谈论红色的东西,我可以把注意力从蓝色的东西转移到红色的东西上。我能这么做,因为我能控制我的注意力。
婴儿没有同样的能力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所以,如果宝宝想:“我想看红色的东西。”同时也听到成人说:“让我们来聊蓝色的东西。”宝宝没有能力把注意力从红色的东西转移到蓝色的东西上。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你想教宝宝们一些他们不关注的事情,你就必须先努力让他们关注这些事情。相反,如果你想教宝宝一些他们已经关注的东西,你就已经剩下了大部分的工作。成年人的协商过程对于宝宝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成人是通过只谈论婴儿正在关注的事物来适应这种情况。
所以这就像是,宝宝太不善于控制注意力了,所以需要成年人不“仗势欺人”?
是的。
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宝宝是否有可能理解语言,有内部言语(inner speech),只是无法表达出来?
首先要说,宝宝不仅可以理解语言,而且是先理解,然后才能产生语言,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知道这一点的一个原因是,就像几分钟前我说的,十二个月大的宝宝几乎都可以说出第一个词了。宝宝的第一个词一般在12个月左右被出现,但如果你教宝宝手语而不是口语,即使教的内容相同,宝宝的第一个词也会出现在宝宝六到七个月大的时候,而不是十二个月左右。原因就是,如果宝宝听到你在说话,想模仿,却不能看到自己的嘴,所以就不能很轻松地模仿你的口型。相比之下,如果你使用手语,且举起一些手指,宝宝就可以看着自己的手指,模仿做出同样的交流手势。
这是否意味着宝宝们有内部语言和心理语言?嗯,这真的很难知道。即使是成年人,我们也不能很好地设计实验来验证。但对于成年人,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指导。我们可以测量像反应时间这样的东西,但许多这样的实验都无法在婴儿身上实行。
不过虽然这样,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宝宝们,甚至那些还不会说话的宝宝们,都具有拥有精神生活(mental life)时需要的重要能力,即,象征不存在的世界状态的能力。换句话说,这种能力可以具体体现为:我想要一些东西,我需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使之发生。我们发现,宝宝们能够完成相当复杂的方法-结果(means-end)任务。
所谓”方法-结果任务“指的是一个有目标的任务,宝宝需要做的就是想出实现目标的方法。但是当然,你并没有办法给宝宝定一个目标。你不能对宝宝说:你要这么做。所以在设计实验的时候,你必须利用他们的目标。他们可能有一个目标,比如,宝宝喜欢把一些东西放进嘴里。所以你把它放在那里,然后你对宝宝说:好吧,我知道你想把这东西放进嘴里,你现在打算怎么做?然后,你给他们一个有障碍的环境,让那个东西不能简单地被拿出来。宝宝可能需要摸索试探,没准需要拉开这个障碍、去抓那个东西。实验证明,宝宝们是有能力完成这类任务的,这表明他们能够想:“我想要这个,现在我该怎么做?“他们是用语法结构清晰的英文句子来思考这些状态吗?不,恐怕不是。
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宝宝不能理解语言,而是他们不能产生语言,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嘴是如何动作的。这对他们来说需要很长时间。
第三个问题是,宝宝是如何从单纯地模仿成人说话,过渡到能够理解语言的?这种转变的潜在机制是什么?比方说,一个宝宝能模仿很多单词,但很显然他(她)压根不知道这很多些单词什么意思。家长怎么做才能帮助婴儿理解语言,超越简单模仿呢?
很好的问题。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我们能够测试的最小的小宝宝里,模仿的的确确是语言习得的重要部分,但即使是在最小的时候,模仿也不是语言习得的全部。发展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同事基恩·博科·格里森(Jean Berko Gleason)做过一个经典实验,叫做“Wug任务”。在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向孩子们展示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新物件,比如一个布娃娃,或者小玩具之类的。实验人员告诉他们,这是一个wug,然后给他们看第二个wug。然后说,现在有两个啦。现在有两个_?
Wugs?
没错。孩子们之前从没听过这个单词,所以他们肯定不是在简单模仿,而是在归纳推理了。孩子们把“复数就是加个s”这个已经习得的模式运用到了新情境中。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做这种泛化(generalization)了。
不过泛化和模仿处在一种持续的竞争关系中。你之所以会模仿别人,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会错,或者至少很自信自己是对的。如果你模仿一个说话很糟糕的人,你知道自己说得也很糟糕。不过一般来说,模仿别的语言使用者是个不错的方案,因为大多数人说话都没毛病。但是,模仿在根本上是有限制的,因为你只能模仿你听到过的东西。但我们常常需要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这样一来,泛化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如果你泛化过头了,你的说话方式肯定也就不正确了。
比方说,我从来没有听过mouse(老鼠)这个词的复数,我很可能会说成“mouses”,但其实应该是“mice”。小孩子们经常犯这种错误。这种现象叫做过度规则化(over regularization),是语言习得早期阶段的常态。孩子不需要刻意学习如何摆脱简单模仿,他们会自己尝试超越简单模仿。他们似乎意识到了语言的复杂程度。在模仿的时候,你会想准确模仿其中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你只会大致模仿,而不是逐字逐句。当然,还有一部分你干脆忽略了。就好比我说英语的时候,我不想和你说得一模一样,我不想效仿你的音色或口音。因为这些方面最无关紧要。所以,对于在学说话的小孩子们来说,重要的挑战是弄明白,我到底想要模仿语言的哪些方面呢?哪些方面又处于模糊地带,让我想要部分模仿、部分泛化呢?
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做得更好?其实和任何技巧一样。如果我想学会做某件事,我就先反反复复地做。然后我再尝试那些更有挑战性的。比如我想学习某个字母的发音,我一开始只练习它在单词特定位置的发音。我先学会/D/在单词开头怎么念,比如doggy、daddy、diaper这些词,就只先练习单词开头的发音。如果我想进阶一下,就把它放到单词末尾,慢慢地,孩子就能领会不同情况下的发音。
我认为这是学习如何泛化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学会辨认,下一步再领会各种不同情境,这些不同情境能帮助你判断哪些方面是关键的,是一直需要重复的,或者至少是需要尝试重复的;同时你也会明白哪些方面依情况而变,需要从中抽象出规律并泛化。
下一个问题有关统计学习。提问者去年读了一些有关统计学习的书,她有一个很基本的疑问。在行为研究和神经成像领域都有许多证据表明统计学习的有效性,但她注意到猴子也能成功地完成统计学习,而猴子并没有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即使我们承认统计学习对语言是有意义的,统计学习也无法全部解释人类的语言系统。统计学习领域的研究者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这位提问者真的很专业。
嗯,非常专业。我先为不熟悉统计学习的读者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吧。统计学习的意思是通过探测环境输入的哪些方面总是一起出现,来判断环境中的单位。比如说,你听到“pretty baby”(漂亮的宝宝)这个词组,你是怎么知道“pretty”和“baby”其实是两个单独的词的呢?一种方式是通过听爸爸妈妈说话,在英语中,爸爸妈妈在和宝宝说话时,没准有95%的情况下发出“pre”这个音之后会紧跟着发出“ty”这个音。毕竟爸爸妈妈跟小孩子交流的时候不会经常说“predilection”(偏好)、“prevaricate”(搪塞)、“precaution”(防范)这类复杂的词。但在“pretty”这个词之后可以跟很多不同的词。你的确可能会说“漂亮的宝宝”,但你也可能说“漂亮的眼睛”、“漂亮的鞋子”、“漂亮的衣服”等等。单词中的音节能准确地相互预测,而单词末尾的音节无法预测下一个单词,因为每个单词之后可以跟许多不同的词。所以一旦你发现哪些音节能相互预测,就能判断这些音节属于同一个词。
所以关注事物如何相互预测或许是语言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用各种预测关系来描述语言。当我说“pre”的时候我很可能会接着说“tty”,就成了“pretty”。当我说定冠词“the”,接下来很可能就是一个名词,因为这种词组构成要求跟一个名词。所以说语言中有许多预测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统计学习。
我们认为统计学习与语言习得息息相关,首要原因当然是语言充满了这种预测依赖关系,而且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原因是个体差异和统计学习的关系。统计学习的能力能预测语言习得成果的个体差异。换句话说,和那些不擅长统计学习的婴儿来说,擅长统计学习的婴幼儿的词汇量增长更快。
不过这位读者很好地指出了一个难题。其他动物的确也会统计学习。尽管我们认为统计学习对语言很重要,可是其他物种也能够这么做,但却没有发展出了人类的语言。这该如何解释呢?提问者在问题中其实已经暗示了第一种解释,那就是,统计学习可能无法完全解释语言习得。也就是说,统计学习虽然对语言有用,但光有统计学习是不够学会语言的,人类还得有其他能力。像猴子等物种,可能只有统计学习。
也就是说,之所以人类只有拥有语言,是因为只有人类同时拥有统计学习和其他那些必要的能力。关于其它必要的能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学界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有些人认为要拥有语言,在统计学习之外还需要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意思是你需要意识到他人可能拥有和你不同的想法。如果你不知道别人可以想得不一样,你会假设每个人都和你想得一样,那么你也就没什么理由去跟别人交流想法了。这样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许这正是人类是唯一拥有语言的物种的原因,因为语言不仅要求统计学习,还需要某种人类特有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假设统计学习可能确实全面解释了语言习得:只要有了统计学习,就能有语言。而其他物种学不会语言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缺乏关键的学习机制。它们拥有统计学习,满足语言习得的所有要求,但问题是它们统计学习的内容是错误的。刚才我提到当你听到“the”,接下来就会听到一个名词,这可能是比较简化的说法。在现实情况中,“the”之后跟着的并不一定是名词:事实上当我说完“the”,只要最终跟上一个名词就够了。我可以说“the dog”(这条狗),但我也可以说“the big dog”(这条大狗)、“the big fluffy dog”(这条毛茸茸的大狗)甚至“the big red fluffy dog”(这条毛茸茸的大红狗)。“The”意味着最终将出现一个名词,而不一定是名词相邻着出现。语言中充满了这种非相邻统计关系。
人类似乎更擅长探测这些非相邻的规律性。而动物,至少当它们接收语言信息的时候,似乎只关注相邻关系。因为我们自然地对这些远距离关系更感兴趣,或者说更擅长,所以人类的统计学习对语言更有效。动物不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心灵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能力不够发达,导致它们只能注意到紧密相邻的东西。这样一来它们更难学会语言。
还有一种解释关乎人类和其他动物另一个可能的差异,就是在学习机制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二者对不同的事物感兴趣。我们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还知道几乎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都更愿意听自己物种的同伴的声音,而不愿听其他物种。所以有可能动物和人类统计学习的方式是一样的,但它们不关心人类说话,它们不像我们一样觉得语言交流很有趣,所以没法发现我们在语言中发现的那种规律性。
可见,这里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分歧。动物没有语言是因为它们不具有统计学习之外的那种必要能力吗?还是因为它们虽然和人类一样运用统计学习,但是方法不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还是未知的。
我明白了。还有一个略微相关的问题。有没有脑损伤研究发现病人缺乏统计学习能力?
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而且既往研究成果有些相互矛盾之处。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要损坏统计学习能力,好多脑区都得受损。统计学习的神经机制分布非常广泛。我认为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人脑中几乎所有神经元都能够做类似于统计学习的工作。这个系统极为分散。不过中脑里的海马体,一个对记忆至关重要的结构,似乎在统计学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确有一定研究发现海马体损伤的病人的统计学习能力也受损了。
不过我必须再强调一下,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一些研究发现海马体受损病人的统计学习能力不足,但其他研究没能复制他们的结果。因为你不可能为了做实验而把志愿者的海马体切掉,没有海马体就没有记忆了。你只能在海马体自然受损的人身上做实验,而每一个病人的海马体受损情况都不一样,于是他们的表现也就不一样,更别说他们受伤之前海马体结构的个体差异了。目前基于这些研究,我们至少可以断定统计学习面对损伤是非常稳健的。即便海马体受损导致统计学习能力下降,这些人依然能够在某些领域或任务中进行统计学习。所以我应该再次强调,统计学习是一种分布极为广泛的过程,而不是集中在某一脑区。
下一个问题就又回到了婴儿的语言学习,这位读者想要知道人在孩童时期是如何区分不同的方言的。有一些成年人可以在方言和普通话间切换自如——在中国大陆,普通话是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方言版本的语言。但是有些人就会很难把方言和普通话两者区分开。这是否与童年时期不同的家庭环境有关呢?
这个问题还挺有挑战性的。不同的成年人这方面的能力会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人会说两种语言或者两种方言,他们在讲任何一种语言时都非常自然,好像完全没有口音。而有些人可能会不止两种,甚至是三种或者四种语言,不管他们用得多好,还是可能摆脱不了口音。他们的方言会不断地影响所用的语言。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有些有些人只要说话就会带口音,也有一些人在学语言的时候一点口音都没有。开始学习语言的年龄的确对口音有所影响,越年轻,就越容易像当地人一样说话,而不是别人一听就能认出来的外国人。
我们认为这种能力也有着个体差异,很有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有些孩子就是能学会去很好地控制他们的发音器官,用嘴巴、下巴、舌头和嘴唇精巧地合作,让说出来的词句听起来特别地道。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与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和成年人相比,婴儿们学习起来会容易很多。婴儿们能够捕捉到的语音非常丰富,基本可以涵盖世界上所有语言所用到的语音元素。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宝宝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听周围人说的语言,所以在大概一岁的时候,他们就能感知出母语中使用的语音,忽略母语外的语音。举个例子,在英语里,我们有r、l、ra、la的区分,但是日语并不会区分r和l。在刚出生后,英语环境中和日语环境中的宝宝都可以区分/r/和/l/,但是到了12月龄的时候,日语环境中的宝宝就不能识别这两个音了,因为他们的语言并不会用到这个。
所以,沉浸在A语言的环境中时间越长,你的这种语言能力就越强,同时,当你接触到B语言的时候,你的学习就会出现更多的偏倚。如果你的A语言已经用的非常好了,你就会很容易用既有的语言去理解新的语言。同理,如果你已经学会了一种方言,在接触新语言的时候,很容易在所讲方言的基础上去进行学习。相反,如果你是同时学习这两种语言,并不会出现其中一个强于另一个的情况。因为并没有主导的一种语言,所以对两种语言的习得可以相对独立。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容易在两种地道的语言,或者口音和没有口音之间自由切换。
那么,人们是如何对口音进行测量的呢?
这个其实很难做到,因为你并不能提前判断好某个口音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起来不是什么样子的。你需要真正地沉浸在相应社群的语言环境中,才能明确地了解当地社群的语言中会有什么样的语音,这样再去决定某个人的语言有多地道。其实最简单最靠谱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短的语音样本放给该语言的母语使用者听,由他们来打分,以此衡量这些样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他们身边的人,同时有多大的可能性会是非母语使用者。
有意思。下一个问题是,婴儿语言学习和镜像神经元是否相关?
其实呢,我们并不知道。我先给那些还没有读过相关文献的读者解释一下镜像神经元这个概念。镜像神经元会在看到其他人做出某种行为时,产生与自己做出该行为时一样的反应。这种神经元有可能对于学习语言有帮助,因为语言的学习需要使用者之间进行一定程度的模仿,或者是一致性。你有了一个想法,然后你想要把这个想法传递给另一个人。某种程度上讲,镜像神经元可能提供了一种天然的翻译机制。如果我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发现你也有一样的想法,这是可能就是镜像神经元在作用:我和别人在想着同样的事情。
但是据我所知,目前并没有文献证明有着更多镜像神经元的孩子会更擅长学习语言,或者没有镜像神经元的孩子就对语言一窍不通。还没有很多的文献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系。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说,镜像神经元可能和语言学习有关系。我们只是在进行合理的猜测而已。
所以现在大部分关于镜像神经元的文献还都局限于肢体的运动吗?
是的。
这是不是说,如果你如果真的想把镜像神经元往语言上边靠,你得特别注意说话的人的嘴是怎么动的?
对,这是一种说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嘴唇的运动,因此模仿对方发声器官的运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学习,这种联系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我得再次强调一下,据我所知,我们还没有任何神经影像学或者行为科学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推论。
棒棒的。下一个问题也是这方面的,宝宝是如何察觉语言中情绪的部分呢?我们是否可以说,语言学期的早期阶段其实是一种对于情绪和表达的学习呢?
好问题。首先,宝宝们是如何捕捉语言中的情绪呢?我觉得我们专业领域中的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种能力并非是宝宝们后天习得的,而是听觉系统先天具有的。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们一起来想一下人对着一只不懂人类语言的动物说话的场景。
如果你想夸一夸你的狗,你可能会温柔地说一句“乖狗狗”,而不是恶狠狠地喊出来:好狗!我爱你!狗!你是我的狗!
我这么跟我家里的狗试过,它被吓得够呛。
是吧。似乎大部分哺乳动物的听觉系统都有这样的能力,讲得慢的低声细语往往是比较舒服的,太高的声调会导致不安情绪,大声快速的词句就是警告信号。我们认为婴儿们天生带有这样的识别能力。这是哺乳动物的听觉系统进化了好长时间的自然结果,这样婴儿们就不需要费力去学习如何辨别情绪了: 他们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被各种轻声柔和的语言包围,比如说:哦、好棒呀、真好。一切都平静祥和。然后他们一旦听到很快很高调的声音,就会自然地想到,天呐,我受到了惊吓。这是耳朵听到声音后很自然的反应。
然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早期的语言学习就是一种对于情绪和表达的学习。对于情绪的理解似乎是先天具有的。表达方式还是需要后天的学习。试想一下,特别特别小的小孩子,往往并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只有两种情绪状态,好和不好,大部分时候是不好。他们不开心的原因可能是自己饿了、生气了、需要换尿布了。不开心的原因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认为,婴儿表达情绪的能力的确会随着生长发育逐渐改善,可能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能很好地理解情绪信号,所以他们最终可以学着模仿那些信号,以服务于自己的情绪管理系统。
我们刚刚提到了先天的情绪识别能力,这个是所有物种共有的吗?
至少在哺乳动物的听觉系统中是挺普遍的。我没看过蜥蜴或者鸟类的资料,但是哺乳动物们处理和回应语言中的情绪信息的方式还是挺相似的。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个特别专业的,主要是关于跨国领养的孩子们早期的第一语言学习。比如说,某个被领养的孩子在婴儿时期曾经历过中文的语言环境,被一个法国家庭领养了之后长期居住法国,完全忘记了怎么说中文。然而,她或他在做语音工作记忆的任务时,脑区活动会更接近中法双语者,而非单纯的法语使用者。所以,发展早期接触到的语言真的会留下所谓的痕迹的?
首先,答案的确是肯定的,早期经历的语言的确会留下印记。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毕竟我们的任何经历都会影响到大脑结构。所以,如果小时候听了几年中文没有改变任何神经反应,这才应该觉得奇怪。在你举的例子中,不可思议的应该是即使他们把中文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的大脑还是更接近于会讲中文的双语者。虽然他们连听过中文这件事都不记得了,大脑还是会好像他们掌握了中文一样做出某些回应。如果你让他们试着识别声调,他们肯定会比只接触过法语的人要厉害。
所以,早期经历对于大脑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就算有,也非常小、非常微妙。目前的确有一些研究证明,对于在出生后一两年在中文环境中生活的国际领养儿,如果后来彻底忘记中文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来学习的时候,相比于生活早期没有接触过中文的法语单语者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优势。所以,语言虽然忘记了,但是仍然留下了一些非常细微的痕迹。
这样的改变在功能上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得,所以这时候我们面对的难题就是,大脑为何要做出这种形式的适应呢?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14岁的讲着法语长大的孩子,不论你是否在出生之后一两年体验过中文环境,功能上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你还是会说一口地道的法语。只不过在其中一种情况下,你的大脑中会留下一点点中文的影子。为什么这样的痕迹不会有任何行为上的影响呢?又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定的影响呢?我们目前正是想就这些问题寻求答案。
采访:曹安洁
翻译:狼顾、有耳、西子
审校:曹安洁、E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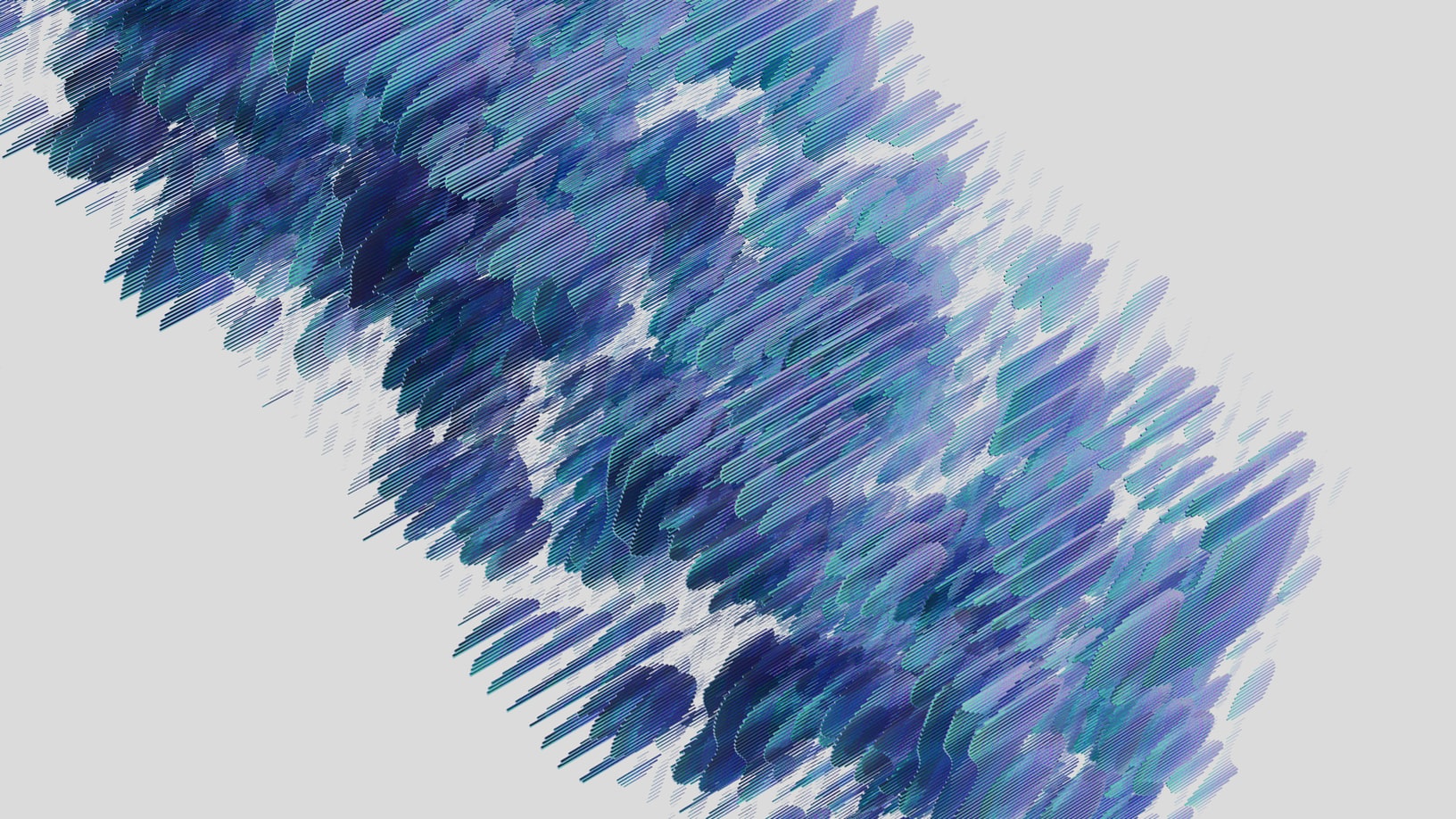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