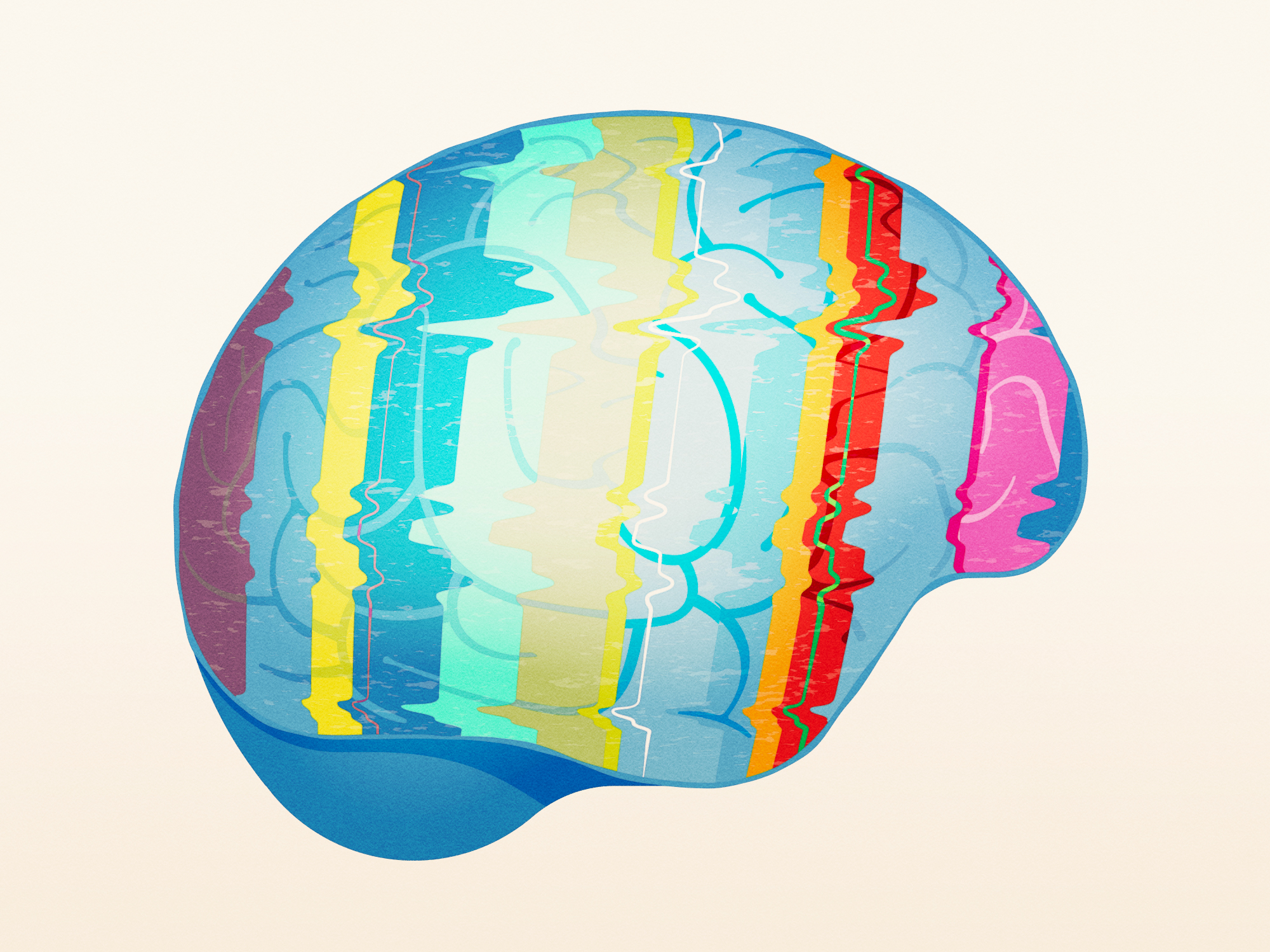
在食品业的世界,颜色就是金钱。食品公司用特制的色度仪扫描生产线上的产品,以确保产品的色调数值保持一致。运输过程中,水果、蔬菜被封装在化学“改良”过的气体中,因为“水果的颜色和茎秆的样子越好看,就能卖越贵”——控气(TransFresh)运输公司的官网上说。在整条生产、运输链中,食品要经受接连不断的检色标准的考验。例如,美国农业部就有一套橙汁颜色标准,橙汁的色调必须据此严格校准(A级浓缩还原橙汁要求做到“成色逊于标准5号色,但又远胜于6号色”)。在联邦监管机构的眼中,几乎没有比“欠染的”(undercolored)浆果命运更悲惨的了。
橙子和浆果还只是故事的序曲。色彩标度公司孟塞尔(Munsell)出售的颜色标准囊括了薯条、番茄、南瓜、橄榄、糖浆、蜂蜜、樱桃等食品。孟塞尔的一位管理人员阿特·施莫林(Art Schmehling)告诉我,像酒渍樱桃(maraschino cherry)这样的产品其实有两套颜色标准:樱桃首先要漂成一种暗淡的黄色,这是为了之后能成功地染成标志性的亮闪闪的红色;第二套标准才是那种红色。
人们如此痴迷颜色,绝不仅是表面功夫:虽然我们总是谈论舌头和颚,眼睛却可以称得上是最重要的味觉器官。牛津大学跨通道实验室的主任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指出,我们大脑皮质中超过半数的“不动产”都致力于处理视觉感受,却只有1-2%关乎味觉官能(我们是哺乳动物中的异类)。这不仅导致颜色会给我们的期望添油加醋,事实上,颜色改变了我们如何品尝食物。
198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把被试的眼睛蒙上,给他们喝一种饮料,然后问是不是橙子味的。仅1/5的被试能够辨识。但当他们能够看到饮料时,所有人都“喝出来了”橙子味。而当被试喝一种调色成橙色的青柠味饮料,一半人认为这是橙子味的;当青柠味饮料是绿色的,没有人犯错。
不只是饮料本身的颜色事关重大。另一项实验中,人们认为白色马克杯中的咖啡尝起来没有透明杯子或蓝色马克杯中的那么甜,而七喜的包装上黄色越多,尝起来越有黄柠和青柠的味道。甚至餐盘的颜色也可以改变我们对味道的感觉:被试称白色圆盘上的草莓慕斯比黑色方盘上的更好吃。
专家的舌头也难逃眼睛的诡计。比如,康奈尔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视觉缺席时,训练有素的品鉴者很难辨别牛奶中的脂肪含量;对牛奶的“见证”这条线索的重要性,让任何口中的感觉都难以望其项背。“期望(expectation)无孔不入。”斯宾塞说。
觉得这款葡萄酒不好喝?调整一下灯光吧。想让这杯饮料甜一些?请把颜色弄浅些。
葡萄酒酿造工艺学教授温蒂·帕尔(Wendy Parr)及同僚做过一个著名实验:品酒专家们被要求描述两杯葡萄酒的气味,分别是一款霞多丽干白和一款黑皮诺干红。他们不知道干白里添加了无臭无味的红色食用色素。当他们用不透明的玻璃杯品尝红色干白时,结果比较准确。然而,如果换成透明的玻璃杯,他们却用通常用来形容干红的语汇来描述这款干白;仅仅是看到了红色,就触发了他们对于干红的滔滔学识。可惜,他们懂得越多,洋相出得越大。
食品公司都会常规地进行内部品尝试验,所以他们知道颜色是个多么调皮的捣蛋鬼。食品公司的专家品鉴组在红色的灯光下评估新产品,这样他们的鉴别力就不会被通常的颜色-口味期望扰乱。美赞成公司的感官科学家简妮·德尔维奇(Jeannine Delwiche)说(她也曾受聘于百事),在食品研发的早期阶段,“颜色一般是悬而未决的”。食品最终加工过程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它的外观。“我们假设两方面可以分开处理。”她说,“你先得把味道搞清楚。”她告诉我红光迫使专家组将注意力放在外观之外的因素上,比如质地和口味。
当某人因为饮料的颜色有欺骗性而辨别错口味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仅仅是因为被试无法完全尝出味道,不得已依赖视觉信号帮助做出决断吗?还是说,颜色其实改变了品尝的感受?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白颜色对于期望有什么作用。“舌头之后的第一步是初级味觉皮层。”斯宾塞说。然而,“连那里的大脑活动也受到期望的调节。”人们曾经以为“所有通过眼睛、耳朵、舌头输入的外界信息从低阶皮层一路通往高阶,信息在每个阶段上都经过浓缩”,他说,“然而真相是,有更多由内向外的通路。”
大脑就像一台预测引擎。如果亮红色的水果总是尝起来更甜,你下次吃一个看起来是亮红色的水果时,就会产生一个“反向投射”(back projection),斯宾塞解释说,“你神经系统中临近外界的部分(比如,靠近眼睛或舌头)的初步活动就可能受到反向投射的限制。”
2014年《神经心理学》(Neuropsychologia)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证据产生前和积累过程中两个阶段,期望都会左右感觉经验的表现。”文章指出,成像研究“在选择性接收所期望的刺激的感觉区域,检测到了预期性信号或基准线迁移(baseline shifts)”。嗅觉中最简单的基准线迁移现象之一,是当气味与期望(这一期望大部分是由颜色构成的)符合时,大脑嗅觉系统“编码”气味信息的速度更快。至少在我们的杂食小伙伴大鼠那儿,只要联想到从前体验过的一种味道,似乎就能刺激味觉皮层产生与真实品尝那种味道相同的“神经元集群”(neural ensembles)。
头部失状切面。气味分子进入鼻腔激活嗅觉受体,嗅觉神经细胞传递信息到嗅小球,在送至嗅皮层。每一级都有信息整合过程,由来自高级中枢的其他神经元调控。
正如此,当我们凝视一杯据称是草莓榨成的的深红色果汁时,就会产生一种习得性联系:它的风味如何,它喝起来应该是甜的。一个甜草莓味道的“模板”(template)被激活了。或者用《神经心理学》那篇论文的术语说,“最底层刺激模板”发送了一个“前馈预测错误信号”。如果舌头感受到的甜度较低,大脑高低层次之间的往复通信依然会使得大脑倾向于判断这是甜甜的草莓汁,毕竟这种想法处于宰制地位。
我们生来嗜甜,但我们天生并不知道甜的食物长什么样。
我们的眼睛第一个动叉子(We taste first with the eyes),这句老话一点没错。颜色和口味之间的通路是双向的。《乳业学报》(Journal of Dairy Science)的一篇文章指出,消费者们喜欢好看的切达奶酪(美国农业部的标准是“中橘黄色,明亮均匀,光泽诱人”)。然而,如果味道不太对,“消费者的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奶酪的色泽上”。既然尝起来不好,那么很可能看起来也不好。一项成像研究显示,当被试的味觉期望被违反时,视觉皮层的一些区域受到抑制,似乎是大脑在说“等等,这会儿就别管眼睛怎么想了”。
洛克菲勒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查尔斯·吉尔伯特(Charles Gilbert)称,虽然有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自上而下影响与周围神经系统的感觉输入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我们的大脑中时刻进行着。”他指出,在麦古效应(the McGurk effect)等类似展示中,被试看到影像里的人发出了不同的音素(phonemes),虽然声音其实从来没变过。单靠视觉指引,就足够让他们感知到不同音素。“你听见什么,取决于你看见了什么。”吉尔伯特说。“我们才刚开始了解何种信息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传递的,以及自上而下的影响如何在各个皮质层表现,但我打赌每个阶层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个过程。”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火星上的人类学家》(An Anthropologist on Mars)一书中讲述了“I先生”(Mr. I)的故事,这位画家遭遇车祸后失去了辨别颜色的能力。虽然他知道记忆中事物的颜色,却再也看不出来了。“番茄汁是黑色的。”书中写道。这些新联系渐渐变得根深蒂固。当他吃番茄的时候,只好闭上眼睛,“可这并没多大用,”萨克斯写道,“因为番茄在他脑中的心灵印象和眼睛看上去一样黑。”绝望的I先生开始只吃黑白的食物,比如黑橄榄、酸奶,至少它们看起来还是应该有的样子。
这个例子诠释了视觉主宰味觉的另一方面意义:我们可以利用视觉喜欢上新的口味。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颜色与口味的关系是绑定的。我们生来嗜甜,但我们天生并不知道甜的食物长什么样。
斯宾塞说,大脑“从环境中选取数据”,于是我们学会了,比如说“绿色的水果是未成熟的、酸的,等成熟变成红色时才能为我们提供大量能量”。我们无需品尝绿色的草莓,就知道它的味道不讨喜。
萨克斯的故事提示了我们这些联系能多么快地改变。斯宾塞说,几十年前,食品工业认为蓝色食品卖不掉是自明之理,因为自然界鲜有蓝色食物。然而,如今超市柜台上充斥着“劲爽蓝”佳得乐和“蓝莓风味”冰爽饮料。他说,我们是被教会这些联系的——当人们开发了某种新口味的食物,甚至发明了一种口味,就是这一机制大展身手的时候了。糖果和软饮料似乎特别容易成为颜色实验的对象,德尔维奇称。“它们就像食品王国的晚礼服,而不是办公室着装。”怪异的颜色已经悄然侵入了儿童食品市场,儿童尤其看重新奇感,他们脑中的习得性联系还没有僵化。亨氏(Heinz)在本世纪初卖掉了许多绿色、橙色甚至蓝色的番茄酱,后来这些颜色也变成了陈词滥调。
如果我们可以学会喜欢食品的新颜色,那么颜色也可以促使我们喜欢上新食品。超肉(Beyond Meat)公司(生产植物蛋白“人造肉”)产品研发部门的副部长蒂姆·杰斯林格(Tim Geistlinger)称,消费者目前还不能接受因为叶绿素而呈绿色的汉堡。“除非变质了,没有肉是绿色的。”他的工作便是将绿色变成褐色,虽然技术上很复杂,这样做的最终目标很简单:让人造肉和它希望取代的肉(不管生的还是熟的)看上去一样。“我们的产品必须让人有种熟悉感,否则没人会买。可辨识的颜色是人们挑选产品的第一要义。”
觉得这款葡萄酒不好喝?调整一下灯光吧。想让这杯饮料甜一些?请把颜色弄鲜亮些。你的茶太烫了?用玻璃器皿装就好了。眼见为“信”,此言不虚。
大脑仿佛一个隐形的乐团指挥,熟练地协调整合着从不同感官输入的信息。这种“多感官统合”(multisensory integration)通常给人行云流水般的感觉,但如果你留心一瞥它工作的样子,又会觉得不安,那就像是《黑客帝国》中的涟漪。服下让人觉醒的红药丸,你就会发现视觉在俯瞰、主宰着每一种感官(虽然视觉本身也能被影响,比如在一个实验中,一次闪光伴随着两声“哔”,看上去就成了两次闪光)。
视觉凌驾于其余感觉之上的力量是“不对称的”、无可比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似乎仰仗心灵印象,或言“视觉皮层处理”,才能知道事物给我们怎样的感觉。
1964年的一次著名实验中,科学家厄文·洛克(Irvin Rock)和杰克·维克多(Jack Victor)让一些人看一些被实验操控的小物体;它们其实是正方形,但看上去像长方形。第二组被试蒙着眼睛触摸物体,第三组被试则两者都做。然后,他们被要求画下自己体验到的东西。不出意料,第一组画了长方形,第二组画了正方形。可是,既看又摸的第三组也画了长方形。达斯汀·斯托克斯(Dustin Stokes)和史蒂芬·比格斯(Stephen Biggs)这两位哲学家认为,视觉凌驾于其余感觉之上的力量是“不对称的”、无可比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似乎仰仗心灵印象,或言“视觉皮层处理”,才能知道事物给我们怎样的感觉:“我们经常借助视觉印象来了解某些触觉刺激,但我们极少,甚至从不借助触觉印象来了解视觉刺激。”味觉给人不可侵犯的感觉,因为它发生在我们内部;仿佛某种隐秘的记忆,我们所品尝到的,便是它真实的模样——味觉怎么会背叛我们?可是,嘴巴还没动,眼睛已经给食物调味了。
翻译:有耳;编辑:夏明明
Nautilus | Science Connected
Nautilus is a different kind of science magazine. Our stories take you into the depths of science and spotlight its ripples in our lives and cultures.
美国记者,作家,现居纽约布鲁克林,《连线》、《户外》和《艺术论坛》特约编辑,他写设计、技术、科学和文化等。最新著作《Traffic:Why We Drive the Way We Do (and What It Says About Us)》是《纽约时报》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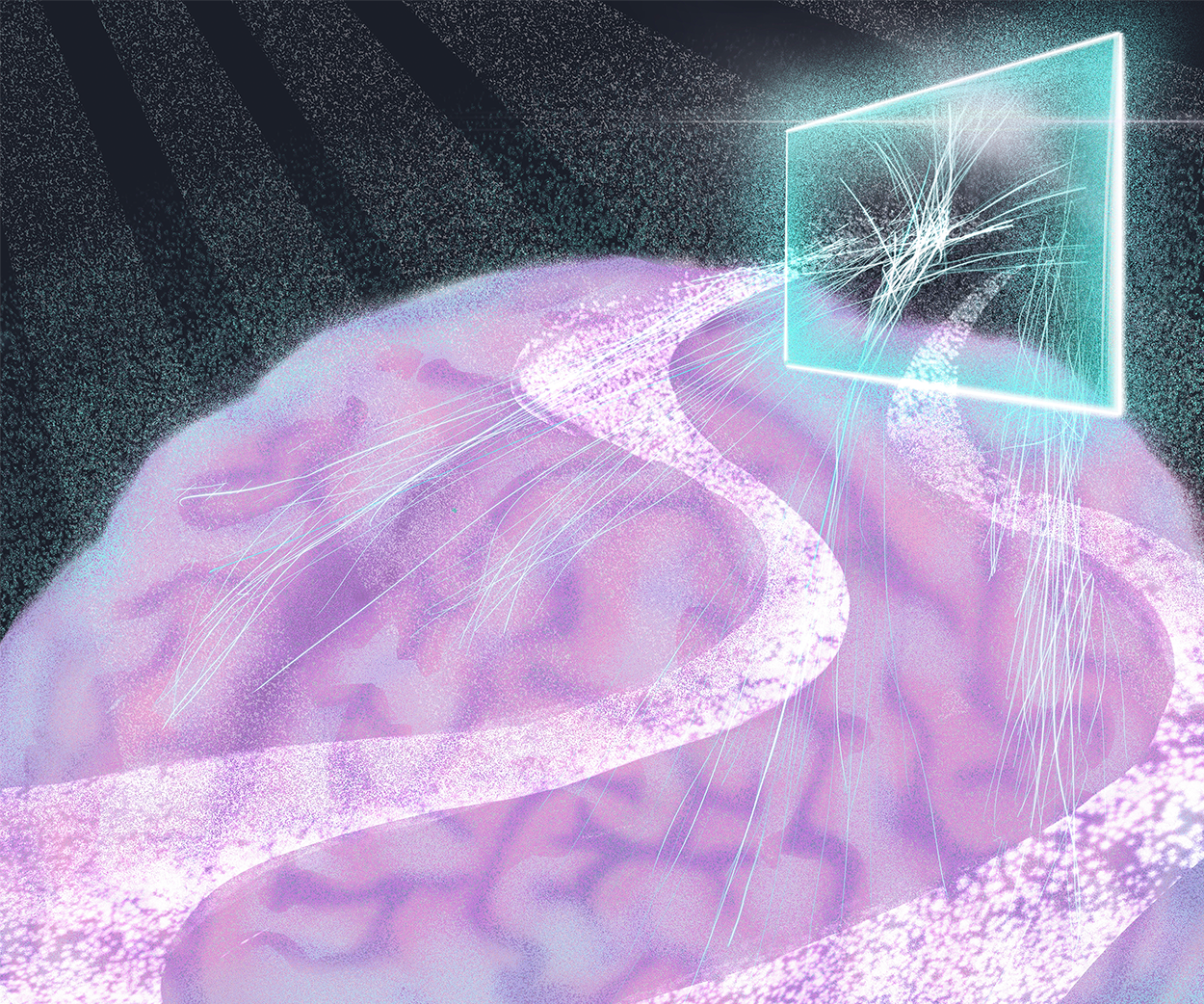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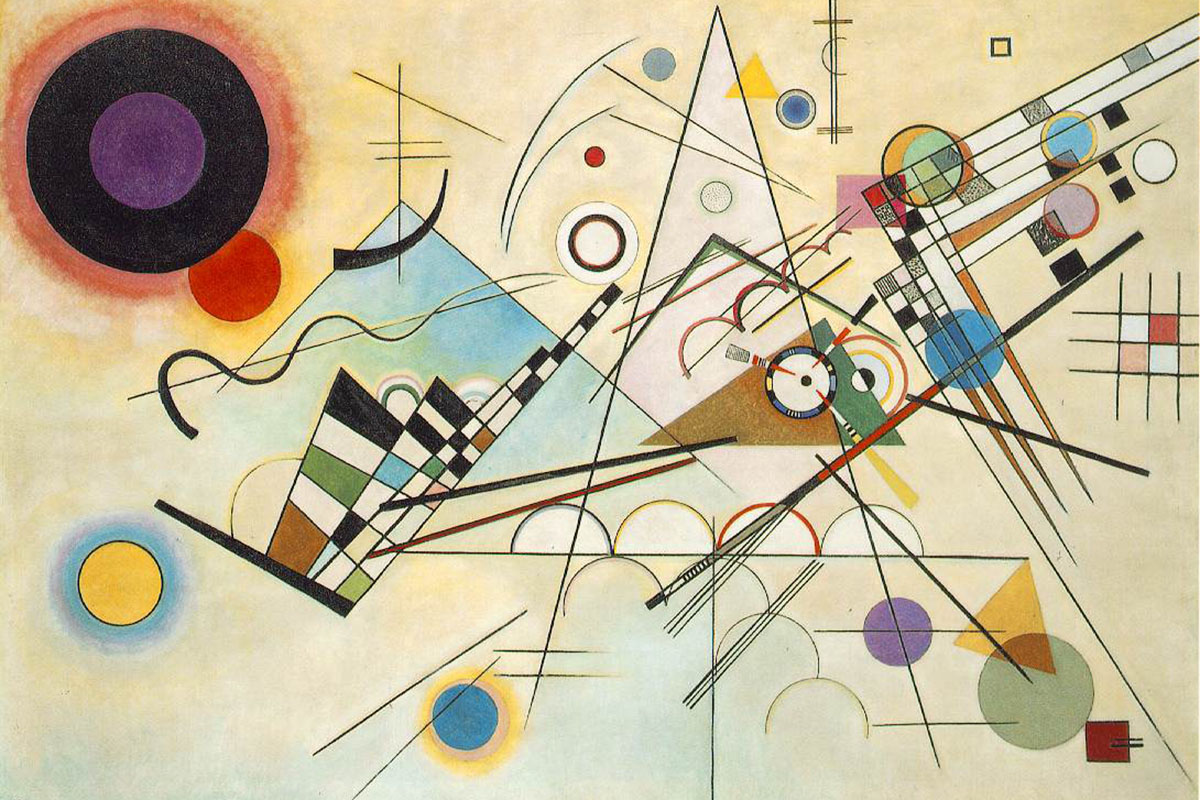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