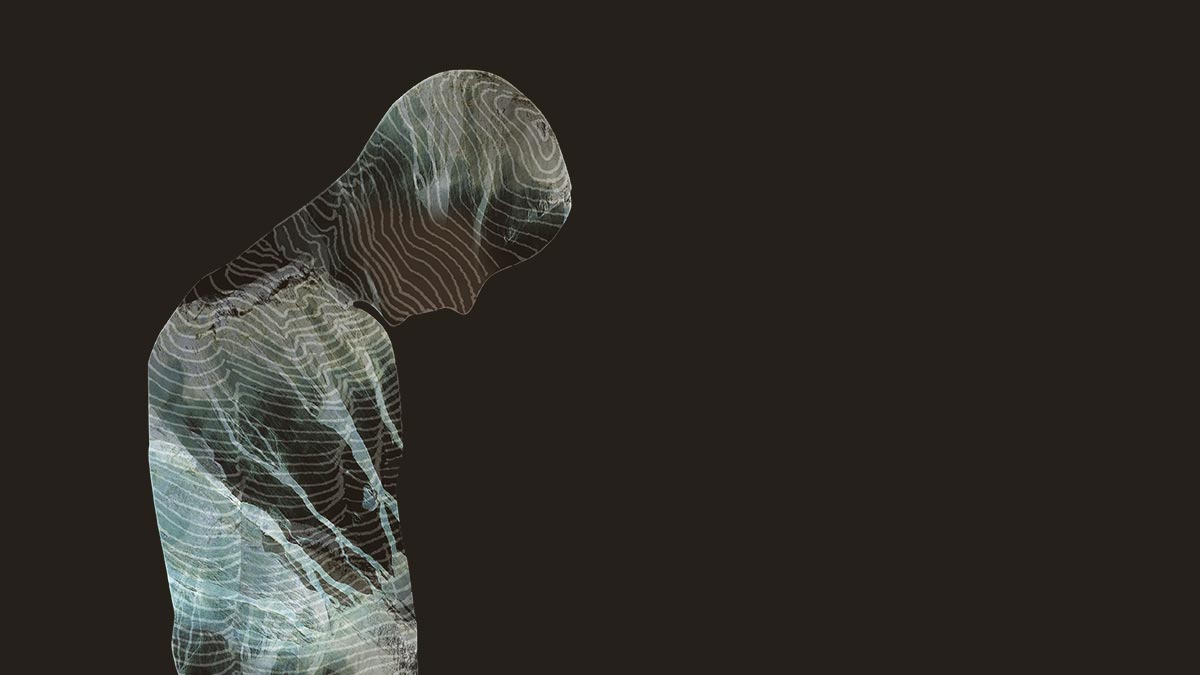
哥哥去世后,我开始频繁地看见他。他出现在我眼前,不是鬼魂般的幻影,也不是梦境中的虚像。他总依附在陌生人身上出现。车流如织的路口,一个男人在等待人行绿灯亮起,为了看清路标,他把帽子向上顶了顶,帽檐下若隐若现的是哥哥的脸。他是地铁入口的检票员,也是那个在市中心食肆里独自喝汤的人。
我无法预见这些“神显”。它们的出现毫无征兆,更无规律可循。那些被我覆上哥哥形象的人,都只拥有他的丝缕影子——深色头发,有些溜肩,胡子浓密,戴厚框眼镜。这并不奇怪,因为我根本不了解我的哥哥。我出生的时候哥哥已经11岁了,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孩提时,他只在周末和另一个兄弟一起来我们家。成年后,我们的生活很少有交集,所以我对他的记忆囿于童年。这些记忆如浮光掠影,又纷乱如麻。直到他死后,我才发现他的大名应该是约瑟夫(Joseph)——他母亲起的。但他出生后人们都用中间名称呼他,“约瑟夫”便渐渐被遗忘了。我是在为他写讣告时,才从父亲那儿知道这件事的。在与哥哥相识24年后,我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这让我感到惊愕,甚至羞耻。我不知道哥哥的名字,更不了解他是怎样的人。我在无知无觉中失去了他,这是多么悲惨而恐怖。我想,这就是他死后我经常看到他的原因吧。他在世的时候,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却从未相遇。
哥哥去世时,我刚开始新闻专业研究生第二学年的学习。当时,我很年轻,怯生生的,还没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我一度以为自己不会重返校园了,也不再会写作了。置身于枯萎的葬礼花束和用心烹制的丧仪宴席中,我迷惘了,感觉萦绕在我们周围的哀伤将永远无法散去。然而只过了两周,我就离开了乡下的父母回到城市,继续学业,重新开始了生活。我走进公寓的时候,楼上的邻居迎上前来献歌一曲,他还以为我门口堆积的花朵和卡片是祝贺我生日的。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回归了往日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一如从前,内心却已地覆天翻。
我已记不清第一次看到哥哥身影时的具体情形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自那以后的许多年,我都经常在陌生人身上看到哥哥的影子。起初,我没有追问自己为什么会“看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直到17年后,我才迈出第一步。现在我年近中年,有了孩子,也自信了很多。我从实习生成长为了一个新闻记者,也成为民俗学研究者。我采访人们的超自然体验,无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陷得多深,我都尊重他们的信念。正因如此,现在的我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终于可以将探索的目光转向内心,审视自己了。
····
看见已故之人是哀悼过程中常有的事情,精神病学、宗教研究、社会学、老年学和人类学都探讨过这一现象。不同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享着这一体验。生活在城市的人并不会比生活在乡村的人少看见逝去的挚爱,而且性别和教育水平差异也不会对拥有这一体验产生什么影响。据称,看见逝者的人中女性居多,但这大概是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而且我读过的那些报告大多聚焦于寡妇的经历。虽然直到20世纪才开始有此类研究报告发表,但是在神话与寓言中一直有阴阳两隔的爱人重聚的故事——从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Orpheus)恳求冥王冥后让妻子欧律狄克(Eurydice)死而复生但终成徒劳,到北欧古诺斯语神话中已故的新郎与新娘私奔。民间传说讲述着人类情感的每一个侧面,悲恸也不例外。

按照精神病学的术语,这种“目睹”被称作“悲恸/丧失亲友幻觉”(grief-/bereavement-hallucinations)或“丧失亲友幻觉体验”(post-bereavement hallucinatory experiences,简称PBHE)。而“眷殒见”(idionecrophany)这个新词以更加温和的方式描述了这一现象——它把希腊语中表示私密和死亡的词与动词“出现”结合起来,从字面上看,它没有断言那些“目睹”是真实还是虚幻的——是一个中性的术语。因为声称一样事物是真实的——我们所相信的——可能具有高度主观性。也许我信仰精灵,而你信仰上帝,也许有人觉得我们俩都不可理喻,考虑到这些判断中隐含的非真即假的二元对立逻辑,谁又有资格来评判我们孰对孰错呢?超自然体验的内在矛盾之处就在于,信仰上帝在北美社会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看见你已故的哥哥在公园遛狗,却成了禁忌、怪异,甚至病态的。
对超自然体验的污名化言论,或许就是人们不愿说出目睹亡者经历的原因。3组来自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哀悼者研究不约而同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曾以某种方式看见他们已故的挚爱,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人提到他们看见的是活人。这些丧失亲友的人在采访中说,他们害怕被嘲笑或吓到亲友,甚至害怕因此招致厄运和更多悲剧。和这些参与研究的人一样,在我哥哥去世后的几周、几个月,甚至很多年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遇见过他,原因多有类似:朋友们不太可能相信我曾见到已故之人,而且我担心这会给悲伤的家人再添烦恼。然而,我最大的顾虑是,忧心的亲友们会强制我去接受一些医疗干预。让我感到恐慌的不是看见哥哥本身,而是这可能意味着我产生了幻觉,甚至出现精神紊乱。
我已记不清第一次看到哥哥身影时的具体情形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自那以后的许多年,我都经常在陌生人身上看到哥哥的影子。起初,我没有追问自己为什么会“看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直到17年后,我才迈出第一步。
2012年,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他的《幻觉》(Hallucinations)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幻觉常被视为疯癫或大脑严重受损的一种预兆——虽然绝大多数幻觉并未引发不良后果。伴随着强烈的耻辱感,病人通常不愿承认有过幻觉体验,他们害怕朋友和医生会认为他们疯了。”
萨克斯写的是普遍的幻觉,可是那些产生于丧恸(日常的,而非创伤性的)的幻觉,却一直被笼统地归类于精神疾病系统。然而,最新一版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后文简称《手册》)已删去了这种错误提示。《手册》将丧失亲友后幻觉列为“持续复杂性丧失亲友障碍”的一个子项,并将其描述为“以为死者在场的幻觉”。2015年,米兰大学的学者们在一篇关于PBHE的文献综述中总结道:“鉴于目前对一般人群精神错乱体验连续性的研究尚无定论,我们依然不清楚它们是否应该被视作病理性的。”

回头看来,我的丧亲体验是复杂的。至少,围绕着哥哥之死出现的诸多细节让我的感受盘根错节、累屋重架:他酗酒,因此可能患有精神疾病;他死于酒精成瘾的时候,还非常非常年轻;还有,他的死亡被烙上了耻辱的印记。如果是别的疾病,我们会说他与疾病“抗争”或“战斗”过,然而酗酒者与这种歌颂英雄的辞藻无缘,我们只会说他是屈服于令自己上瘾的恶习。哥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背水为阵,在这场战役中,他输掉了最爱的女人、他的创造力、工作,还有亲情。看似单调平庸的生活,对他来说,每天都是撕心裂肺般的挣扎,但我们这群旁观者却总是觉得,为生活拼命是理所应当的。
我不怎么了解哥哥的童年,但全家福照片上的他看起来是个快乐的孩子——虽然表现出一丝警觉。哥哥在我父亲第一段婚姻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这段婚姻持续了十多年。这段婚姻结束后,我的两个哥哥留在他们的母亲身边,两个姐姐随父亲搬到附近的一个城市——那儿的一所大学聘父亲做视觉艺术教师。而我的母亲,比父亲小15岁的年轻寡妇,在几年后走进了他们的生活。那之后两年,我出生了。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存在于故事和相片里:我两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姐姐化为涂着蓝色眼影,永远保持着愤怒状态;我们那只名叫减震器(Buffer)的狗精神错乱,经常对着报童狂吠,在访客的身上撒尿;我的两个哥哥,当时还没到青春期,会在周末拜访我们;作为周末郊游,我们一家七口会像戏班小丑一样挤进狭小的勒卡家用轿车,到附近的中餐馆吃饭;如果狗逃走了,我们就集体出动对街坊邻里地毯式搜查——狗逃走是常有的事。
到我7岁时,两个姐姐都已结婚并搬了出去,哥哥们也不太来了。在那段愈发凝滞、寂静的日子里,我成了集万千关爱、特权于一身的独女。我一直很清楚,我的生活比哥哥姐姐们容易。我的父母一直在一起,我几乎不需要谋求家长的关注,而且养育我的母亲不酗酒。哥哥是家中第三代酒精成瘾者。我曾经为了写书采访过一个远亲,她把我和某个姐姐搞混了。“你祖父是个敏感、善良、有同情心的人。”她说,“但他被酒精毁了。”她指的是我哥哥姐姐的外祖父(他们母亲的父亲),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她的这番描绘倒是很符合我哥哥。
不过,我想给哥哥的肖像再加上几笔:他大笑时会冒出假声;他曾是个消瘦而焦虑的少年,会将我扛在肩上;等我上了高中,我的那些小男朋友看见他都会夹着尾巴逃跑;我们偶尔也会向彼此袒露心声。他长大后成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是大师级别的制图师,也是一间装裱工作室的责任经理,他在那儿用木材、琉璃和镀金制作画框。现在,我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他留下来的艺术作品——一幅油毡浮雕,阴影中有两个苹果;一幅钢笔速写,画的是一只破烂不堪的皮质公文包,它敞开着,里面空空如也;一幅精妙的迷你自画像,铅笔画的,因日久年深而微微泛黄,还带着因放在钱包里而留下的折痕,哥哥如带驾照一样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哥哥的这些艺术作品挂在我父母家的墙上,当我去拜访他们,时而会发现自己盯着其中一幅看,期望某些隐含的东西会自我显现。然而,除了我自己映在玻璃上的镜像,那里空无一物。
····
2001年9月一个冷得出奇的日子,我们举行了哥哥的葬礼。我们于正午聚集在墓地。豆大的雨点从天空坠下,雾气弥散在漫山遍野的墓碑间,一种阴郁的气氛笼罩着这里的一切。一个穿黑色礼服、体型健硕的男人伸开双臂为送葬队伍引路,仿佛在收集下落的雨水。凹凸不平的砂砾小路穿过墓地,汽车在上面曲折缓行。哥哥的墓旁,一顶黑色的伞棚遮在我们头顶,地上铺着一块粗麻布。我、活着的哥哥姐姐们,还有父母,围在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地坑旁,它也就比鞋盒稍微大些——从泥土上整整齐齐地切下去。它太小了,仿佛我们埋葬的是后院里的一只小鸟,而不是哥哥的骨灰。

之后,我们又去往一个教堂的地下室,那里有条灰色的地毯从室内一直延伸到外面。一路行来,漫天的雨把每个人都打湿了。走进教堂,角落里挂满湿漉漉的大衣,我们的鞋底沾满污泥。女人们穿着黑裙子,男人们穿着黑西装。人们吃着牙签穿起来的小三明治,喝着泡在塑料杯里的苦咖啡。我站在地下室的一角,端着一个堆满食物的纸盘子,一口也吃不下。人们排着队和我说话,再一次自我介绍,有些人还拥抱了我。我母亲的一个表亲向我表示哀悼,又闲聊了几句。她问我住在多伦多的哪条街道。我咽了口唾沫,看向脚下。我张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我深吸一口气,感觉心砰砰跳,血涌到脑子里。我以为自己病了。一时间我想不起自己住在哪,我的脑海中有家门的样子、附近公园的样子,但无论我如何苦思冥想,就是想不起街道名。“我记不得了。”我没辙了,只好这样告诉她。
····
我无法掌控自己会于什么时间在拥挤的酒吧或公交车上看到死去的哥哥,但我是个擅长白日做梦的人。我曾在幻想中为哥哥书写不同的结局,同时在他的这些生命旅途中赋予自己不同的角色。在这个想象的、不可能实现的未来,我看见多伦多的一家咖啡馆,冬日的阳光扫过杂色的木地板。高高的窗上结了霜,有人闷声咳嗽,身后那桌人的轻声谈话溜进我的耳朵。我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这只是我叙述的未来中的一个随机场景。这是一次平常的约会,我最年长的哥哥走进门,他迟到了一会儿。他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嘲笑了一番这个地方——这里的陈设有些粗糙,又有些小资,环境精致而陈旧。他说这是“波西米亚风”,正符合我的风格。(当然是我的风格!是我找到了这个地点,布置了场景,挑选了内部装潢,还雇了群众演员。这是我的幻想啊。)
这些是他应该做过的事:在多伦多的某个艺术学校当老师,住在西区离有轨电车站不远的公寓里。他离世时留下的印刷社,依然是他的(现在搬到父亲的工作室了)。或者,按照另一个剧本:他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装裱工作室,在那里,他拥有许多客户——他们都是本地的艺术家,其中一些是父亲的老朋友,还有一些是他生命中的新角色,他凭一己之力俘获了这些年轻的主顾。这一切不是天方夜谭。他是个有条理、一丝不苟并且对财产负责的人——他死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的生活多么节俭。他才35岁,却有足够分成四份的遗产;一份留给他的母亲,其他三份给她的另外三个孩子。我拒绝了我那份遗产。倒不是说我多么高尚,只是出于迷信。
我们让死者重生。我们翻新他们的房子,重新搞一遍装修,还添置新家具。每一次讲述我想象中哥哥的另一种未来,故事总有不同,但一个细节始终如一——因为这不可以改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任何未来的生活都不可能存在,无论是在想象里还是在现实中——那就是:他不酗酒。此外,他还在做艺术。哥哥的这两个侧面紧贴在一起,失去了其中一面,另一面也灰飞烟灭。他因酗酒耗尽了自己,最终再也不能创造艺术。然后,他就死了。
哥哥死后的那段愁云惨淡的时光,几个月仿佛折叠成了一天。我把我的幻想浓缩成了一句话,告诉了母亲。
“如果他接受治疗,不再喝酒,我们会不会成为朋友?会不会一起喝咖啡?”
“不太可能。”她说。
母亲是小说家,根据我的观察,虽然虚构文学作家在想象的领域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靠幻想吃饭。想象的世界里充斥着现实主义。如果哥哥是小说中的人物,加入“12步计划”戒除酒瘾、改变生活,读者会相信吗?我们之间从来不是那种“出来喝杯咖啡吧”的轻松的关系,所以母亲说的很对,我们往后的人生也不太可能变成我想的那样。你不能强迫别人建立感情,即使是家人;也许,尤其是家人。

我可以为哥哥设想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但我知道,若他活着,到今年53岁生日时,他更可能面对的是因长期酗酒带来的惨淡现实。去年冬天我在城里一家运动鞋店外看到一个男人,他对着人行道呕吐,手里紧攥着一瓶威士忌。那时是12月,临近午夜,寒气刺骨。我想到了哥哥。我想知道这个男人今晚会睡在哪。我回忆起哥哥葬礼过后,父母在从葬礼回去守灵的路上迷路了,我们只能慢慢地开车经过镇上一片破败的街区。我们看到人行道上有两个人像幽灵一样踉跄前行,褴褛的衣衫被早先的雨淋透了,脑子也被什么东西搞坏了——是酒精还是毒品,我也不知道。“至少他没有落得这样的下场。”前排的母亲对父亲耳语道。
····
哥哥死后仍在这座城市里漫游,这可能和他生前的经历有关。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民间传说中,那些未享安宁的死者会在生者的生活中游荡。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死者的灵魂回到世间,是为了完成未竟的美好的心愿。但在另一些时候,他们以鬼魂的形式归来,目的是纠缠他们认识的人。有个故事讲了一个男人的灵魂回到世间想和曾经交恶的邻居和好,而在另一个故事里,一个孩子的鬼魂纠缠着父母,因为他们没有把裹尸布好好地缠在他小小的尸体上。死者像信使,通报沉船的灾难,诉说台风的肆虐,但他们有时候也会为一些生活琐事归来。“不要卖。”已故的母亲向难以定夺家庭农场命运的儿子建议道。有些人死于自杀,尸体不能埋葬在宗教墓地里,他们被迫游荡,直到他们本该“自然死亡”的那一天。
如果人们以悲惨的方式死去,走得突然,或英年早逝,那么爱着他们的生者更可能“看见”他们。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从未看见过祖母。她是在过路的修女或几个等公交车的叛逆少女的见证下安详地离开的,享年96岁。灾难发生的地方,尤其是那些罹难者数量巨大的,是鬼魂滋生的土壤。比如,海啸后的日本。受灾后数月的一天,日本福岛市石卷车站附近,一个年轻女子坐上了出租车,司机是个50多岁的男子。她让司机送她到南浜町,他说不行,因为那里什么都不剩了。
“我死了吗?”女人问。
司机有点恼火,转身看向乘客。可是,她不见了,车里没有人。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工藤優香记录了7件这样的“鬼乘客”事件。通过研究她发现,所有的鬼魂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对自己的死亡尤为悲伤,因为他们再也无法与爱人重聚了。”她写道,“为了传达这种痛苦,他们可能选择出租车……作为媒介。”
或许我哥哥的心愿仍未完成,又或许和海啸后的鬼魂一样,他的现身是为了表达失望。让我更加难受的是这样一个念头:是我关于哥哥之死那些没解开的心结,让他无法彻底离开生者的世界。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与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的畅销书《论丧亡与哀悼》(On Grief and Grieving)中有一句话:“鬼魂出现包含着重要的暗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线索追溯源头。它们有时代表了某些未竟的心愿,并可以给他人带来宽慰。”精神病学家威廉·福斯特·马切特(William Foster Matchett)认为看见死者或与之互动可以提供“化解过往的冲突,以及修复甚至重新掌控破裂的关系的场域”。那么,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哥哥或许使得我开始了解他,比他生前更深入。我在镇上那些过着各自生活(甚至快乐的生活)的陌生人的脸上和身上,追寻着四处漫游的哥哥的踪影。同时,难免想起哥哥的孤独生活和悲惨死亡,但他的“出现”缓解了我心里的苦涩,这是一种奇异而珍贵的安慰。
我无法掌控自己会于什么时间在拥挤的酒吧或公交车上看到死去的哥哥,但我是个擅长白日做梦的人。我曾在幻想中为哥哥书写不同的结局,同时在他的这些生命旅途中赋予自己不同的角色。
大多数关于丧失亲友后出现幻想与幻觉的研究发现,这些体验令人愉快并帮助他们减轻痛楚,但也有例外。比如,2002年《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聚焦于两个丧子的母亲——看见孩子的幻影对她们来说是痛苦且具摧毁力的。其中一个母亲的女儿死于海洛因吸食过量,这个母亲不断听到女儿向她求救的呼声:“妈妈,妈妈,我感觉好冷。”这当然让人痛苦难耐。

古往今来,丧子之殇是被不断吟唱的主题。《悲伤的力量》这首于17世纪记录下来的瑞典民谣,描绘了一个丧子的母亲看见一群小孩子列队经过,不禁伏在如茵的草地上啜泣。她在那群孩子中间寻找自己的儿子,他竟真的在那儿,一身白衣,脑袋低垂,手里提着沉重的铁罐。母亲问他为什么不像别的孩子一样欢笑舞蹈,他说,罐子里装满了母亲的泪水,只要母亲不停止哭泣,他就没法加入小伙伴们。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可以追溯到15世纪,在北欧和中欧都曾流传,英国民俗学家詹姆士·柴尔德(James Child)将这一版本的民谣命名为“78号:不宁的坟墓”,并收录在案。在格林童话的《丧衫》(The Burial Shirt)版本中,一个死去的小男孩没法安睡在坟墓里,因为他母亲的泪水不停地落下,打湿了他的衬衫。他将此事告诉母亲后,她便不再恸哭。在苏丹的民间传说中,造物主阿约克(Ajok)让一个孩子起死回生回到母亲身边,却激怒了孩子的父亲。他将妻儿双双杀害。于是,作为惩罚,阿约克废除了一切永生的可能,死亡变成了永恒的状态。这个故事的寓意蕴含在古今各个文化的叙事中——死者不可能真正复生。还有一个附加警告:避免表现出过度的悲伤,或者按照我的理解,至少不要告诉别人自己很悲伤。
现代社会有一个地方甚至鼓励你肆意流露情感,那就是心理医生的诊疗室。在哥哥死后我回到新闻学院后,曾短暂地接受过一个悲伤顾问(grief counsellor)的治疗。她看起来太年轻,一副紧张而犹疑的样子。911恐袭事件发生后,许多心理治疗师被派遣到我们学校,她是其中之一。恰好在这么一个全球性创伤事件后,哥哥的死接踵而至。在一场吞噬了整个世界的大火中,哥哥的生命燃尽了,只留下小小一抔灰烬。我们这代人会永远铭记那件事:听到消息时我们在哪,是谁告诉了我们,还有那树桠间闪烁的秋日暖阳在人行道上撒下斑驳的影子,都将永远刻在心里。我认为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哥哥还没有离开。这可能是他最后看到的景象——高楼在燃烧,绝望的人们一跃而下,坠入死亡。
我知道哥哥的死因是酗酒导致的食道静脉曲张,意思是他的食道里有一根膨胀的血管爆裂造成了大出血。但是,我跟悲伤顾问说过,没有人知道他的死亡时间和当时的情形,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尸体在房间里躺了多久。所有这些不确定逼着我想象他的死亡过程,怀着恶心和极度的悲伤拼凑出一幅幅场景。我没有把这些想象告诉过任何人,家人、男友、朋友,一个都没有。
那个治疗师建议,每当那些想法闯入脑袋,我可以专心欣赏一件艺术品——我学过几年艺术史,桌上堆满了图集,可以随手挑一张看。她说这个方法还有额外的好处,可以把我和身为艺术家的哥哥联结起来。我曾试着想象一间华丽的艺术画廊,新古典主义,欧式风格,有锃亮的木地板和高高的壁画穹顶。在我的脑海中,我漫步在画廊间,然而当我走近那些最著名、最美的艺术品,我只看到不安和忧伤。大卫那双苍白的、雕刻而成的眼里,有一种疏离的悲伤。透纳画笔下的那些暴风雪,都仿佛预示着沉船的灾难。艺术的装饰性意义,在它阴森、黑暗以及拷问灵魂的力量面前不值一提。我只见了那个悲伤顾问两次,从未跟她提及那些对亡者的幻觉。我简直不敢想象她会怎么诠释这一现象。那时候,保持沉默似乎是最安全的方案。
许多年前,我还不像现在这样“全副武装”。当时我刚踏上求知之路,这条路奠定了我毕生事业的方向——先是一名记者,然后成为学者。后来,我学着去质疑我们对现实的感觉。我开始采访那些超自然或魔幻性事件的亲历者,并给予尊重——我不会问他们这是不是真的,而是认真倾听他们的描述和解释。现在的我懂得了很多,终于明白我在哥哥死后的反应其实很正常。短期记忆丧失在人极度悲痛时属于常见情况。全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可能在生者身上看见死去的爱人,无论是古老的民间传说还是新近的科研成果都证明了这一点。丧亡之痛毁坏大脑。逻辑思维分崩离析。你哀悼着死去的亲人——他是你认识的那个人,也是你创造的人,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最终融为一体。
哥哥的中间名是马什(Marsh,有沼泽之意),从一个家人的姓氏演变而来,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用“马什”来称呼他。是啊,他死后我才知道他大名叫什么,但我已经不是年轻时的那个自己了,我不再为此感到羞耻。从前我从来没有想到,除了马什,他还会有别的名字。我有什么理由去想呢?然而,名字还是很重要。我们往往将意义和历史包裹在一个名字里,虽然有时候,我们仅仅是因为喜欢它的写法或读音而取的这个名字。人们不是在悲伤中起名的,也从不奢望用名字去塑造、禁锢一个人。起名,充满无尽的可能,又转瞬即逝。人们怀着爱意起名。于是,当我生下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时,我在他姓、名的中间加上了约瑟夫。约瑟夫源于希伯来语,涵义不太确切;它的一个意思是,将第二个儿子带来人世间。它抑扬顿挫,读音优美,但我选用它的原因还是,它纪念了我的哥哥——不是他的死亡,是他拥有过的人生——我希望他的人生能够重来。
如今,马什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我也不再在街头“偶遇”他了。我知道我很可能已经和他见了最后一面——这件事自然是令人悲哀的。这份创伤已经被时间磨去了锋利的棱角,我也不再沉溺悲伤、止步不前。我甚至原谅了自己对哥哥的一无所知。当他消失时,我多么想念他,但现在,应该不必了吧。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不再产生悲恸幻觉,但我还有一个平行理论,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民间信仰以及日本海啸后那些现身的鬼魂类似:哥哥的灵魂,曾因未竟的心愿,一度处于不安中,也许有十几年之久,但现在他已经求得平静。如今,我们沿着不同的道路,同时继续前行。
翻译:有耳
校对:邮狸
编辑:马小鸽
https://longreads.com/2018/08/20/giving-up-the-ghost/
记者,民俗学家,著有《Beyond the Pale: Folklore, Family and the Mystery of our Hidden Ge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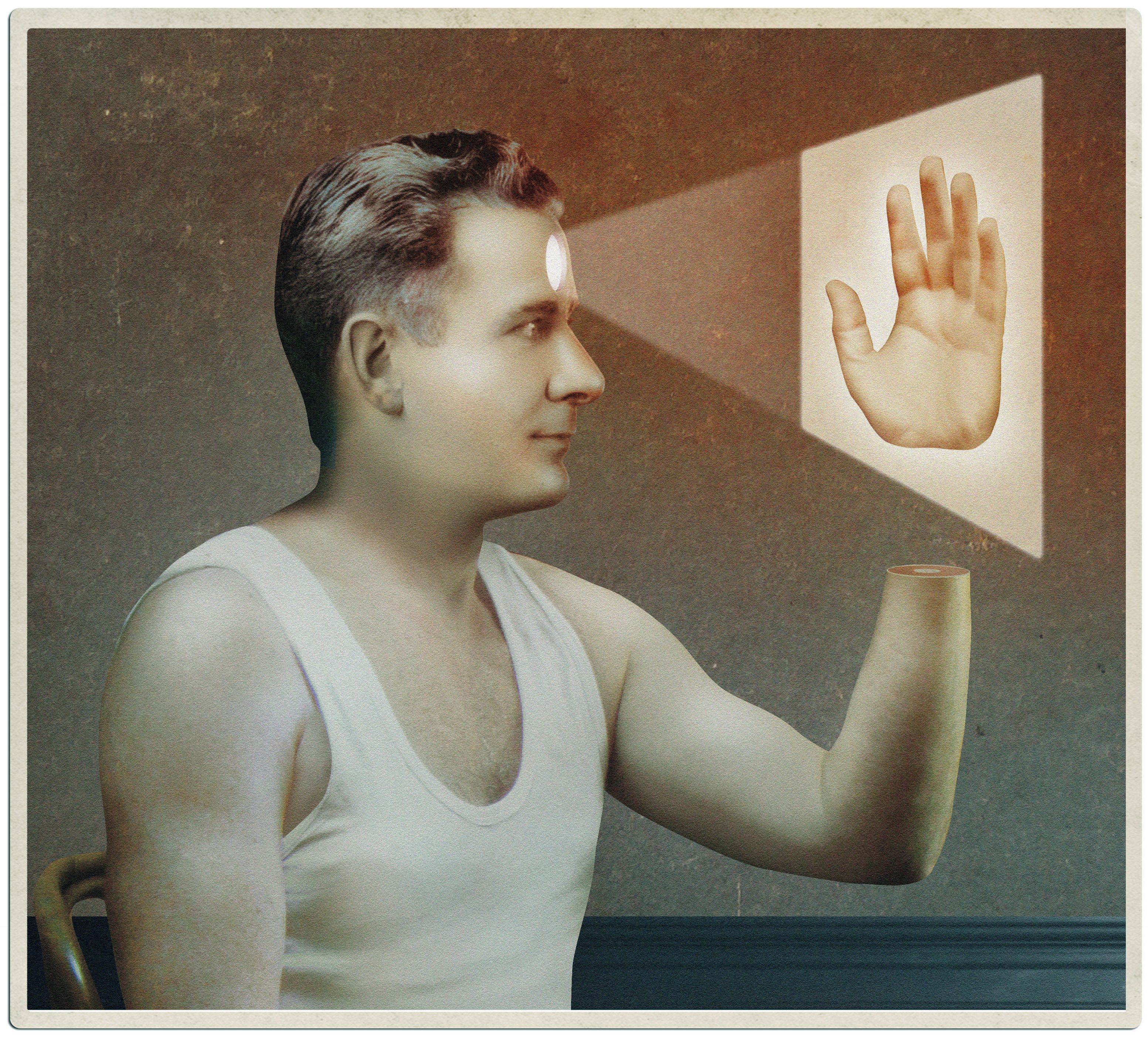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