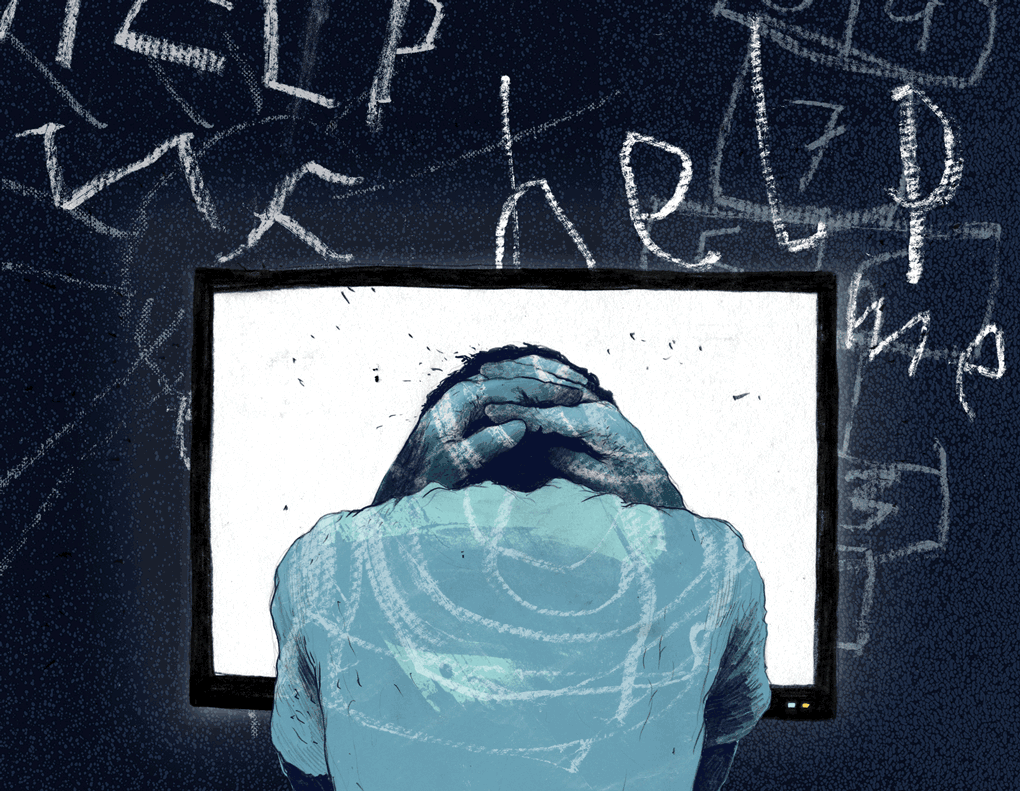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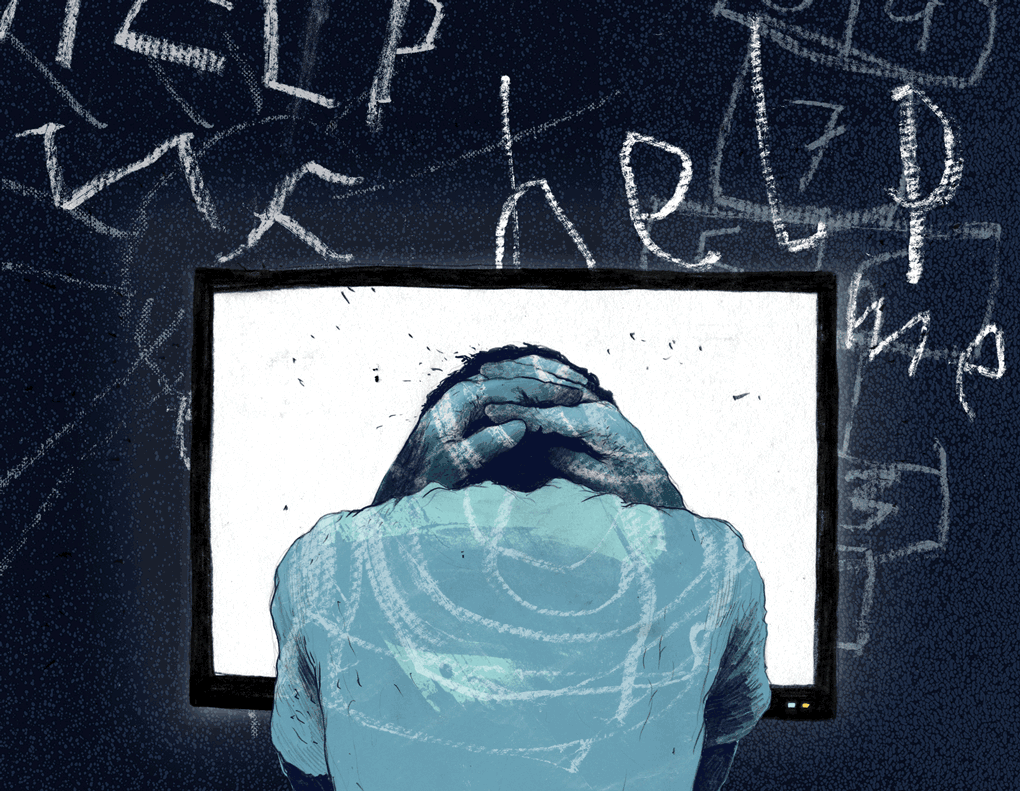
任何名人的死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一种可预见的行为模式,以及在社会上引发一系列独特而令人不安的现象,包括公众哀悼和寻求关注等。
最近,瑞典著名DJ艾维奇(Avicii)、时尚设计师凯特·斯派德(Kate Spade)和厨师兼美食记者安东尼·布尔丹(Anthony bourdain)相继自杀身亡,就已经引发一系列的讨论——救助资源和预防热线的分配、对死者精神状态的猜测、与精神疾病作斗争的经历以及对去污名化的呼吁。
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意,我们只是日益习惯于聚集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所有事情。但不可避免的是,网络上也会有粗鲁的回应。
谈及自杀,互联网的不正当刺激机制在遇到人类冷漠的天性时可以导致荒唐的闹剧,比如,YouTube网红Logan Paul发布拿自杀者尸体开玩笑的视频,或者媒体对名人自杀事件发表不负责任的、没有深度的报道,无耻地蹭热点和追捧流量。
在最近的这类案件中,《新闻周刊》2018年6月1日对布尔丹之死做出了一系列回应,报道的标题类似于《谁是安东尼·布尔丹的女儿,阿里安?一代名厨逝于61岁》(后来似乎被改成了《安东尼·布尔丹的女儿阿里安如何评价他的厨艺》),难逃标题党骗流量的嫌疑。
关于死亡的新闻总是有些混乱而难以理解,自杀更是如此。这是一个广泛且正在变得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每位自杀者和有自杀念头的人都不尽相同,自杀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精神疾病是其中之一,但疾控中心还发现,人际关系问题、经济问题、住房损失和药物使用等也有可能导致自杀。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人们对不幸的反应也是多样的,随处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一切使得谈论自杀成为一件困难的事。
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的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汀·穆捷(Christine Moutier)说:“我们经常将心脏病类比于自杀,因为在很多方面,两者非常相似。除了生物风险因素,来自生活的压力源、环境、吸烟、肥胖、压力和人际关系冲突都与心脏病有关。这和自杀是一样的。只不过自杀是众多复杂因素导致的行为结果,旁观者很难理清头绪。”
人们担心用错误的方式讨论自杀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是合理的担忧。研究表明,媒体对自杀的报道可能导致他人模仿自杀的行为。Netflix的电视剧《十三个原因》(13 Reasons Why)在2017年因为对自杀生动的描述而受到抨击,有些人称它美化了剧中青少年的自杀行为。
事实上,后来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该剧上映后的几天里,谷歌上与自杀相关的搜索量有所上升。出于这个原因,记者在报道自杀时通常会遵循谨慎的指导方针,包括避免详细描述自杀的方法,不要过分简化自杀的原因,避免拍摄悲伤的亲人的照片,也不要用耸人听闻的报道方式。
“人们对谈论自杀感到不安,因为这种谈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便于模仿的脚本。”印第安纳大学研究自杀和精神疾病污名化的社会学教授柏妮丝·佩斯科索利多(Bernice Pescosolido)说。但她指出,当人们听到彼此与精神疾病或自杀念头做斗争的故事时,会减少对自身想法的羞耻心和不适,并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并不孤单。社交媒体为这些有益的对话提供了机会,正如为有害的对话提供了机会一样。
“我认为我们现在肯定处于过渡阶段,” 穆捷说,“社会既有巨大的进步,同时一些陈旧的观念和判断也仍然存在。我指的是人们责备自杀者的懦弱,或者认为自杀发生处在一个突然的、不可预知的失去理智的阶段。这真的与科学背道而驰。”
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可能会令人尴尬,因为随着羞耻心的逐渐消退,人们变得更愿意谈论自杀,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知道如何谈论自杀。例如,佩斯科索利多说,她看到她的学生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精神疾病经历,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分享”。
类似自杀干预热线的资源是重要的工具,但它们不是有自杀想法的人们谈论遭遇的唯一途径,而且也不可能吸引每个需要帮助的人来求助。
2018年6月初,安东尼·布尔丹去世的那天,Twitter上的许多人都在强调,向那些似乎有自杀危险的亲人或者仅仅是那些痛苦挣扎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是极其重要的。
模特克丽丝·泰根(Chrissy Teigen)写道:“当我陷入最深、最黑暗的产后抑郁中,我从来没有私下拨打过自杀干预热线。”
当我陷入最深、最黑暗的产后抑郁中,我从来没有私下拨打过自杀干预热线。如果约翰(John)或我的医生当时不联系我,我将永远不会知道我的病情有多严重。这真的是一个孤独的洞穴。关照你爱的人,不要害怕说出你的担忧。
——克丽丝·泰根(@chrissyteigen),2018.06.08
留意你的好朋友。
留意你那些安静的朋友。
留意你那些“快乐的”朋友。
留意你那些有创意的朋友。
互相留意吧。
——劳伦·沃伦(@iamlaurenp),2018.06.08
佩斯科索利多有一个理论,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9世纪晚期关于自杀的著作,即《自杀论》(Le suicide)。佩斯科索利多说,人们轻易地把自杀归咎于孤独和缺乏社会融合。“另一个我们往往会忘记的维度是,自杀者身边人是如何引导他的行为的,如何监督和看管,当自杀者把事情搞砸时耐心提醒、劝诫,帮助自杀者走上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你生活中的社会支持网络。”她说,她想知道“自杀者的家人、朋友或社交网络引导、帮扶自杀者的能力是不是正在减弱甚至消失,而不是彼此间缺乏联系和沟通。”
我们有时有一种限制性的礼貌,即不好意思打扰对方,这会在人际之间筑起一道墙,尤其是在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朋友可能会收到多少其他短信、电子邮件和Facebook通知的时候。佩斯科索利假定社会已经开始关注个人的权利,而削弱人们对彼此的义务。她说:“我认为这是以社会成本为代价的。以前的社会有太多的禁忌话题,比如自杀,现在它们已经不再是禁忌,对它们的污名化也已经减轻,但是人们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转变。”
“在20世纪50年代,你不会告诉任何人你得了癌症,”她说,“现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社会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思想、大脑和人际关系的问题是最后的边界,它们是我们最后需要学习如何谈论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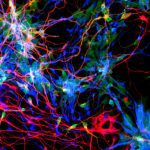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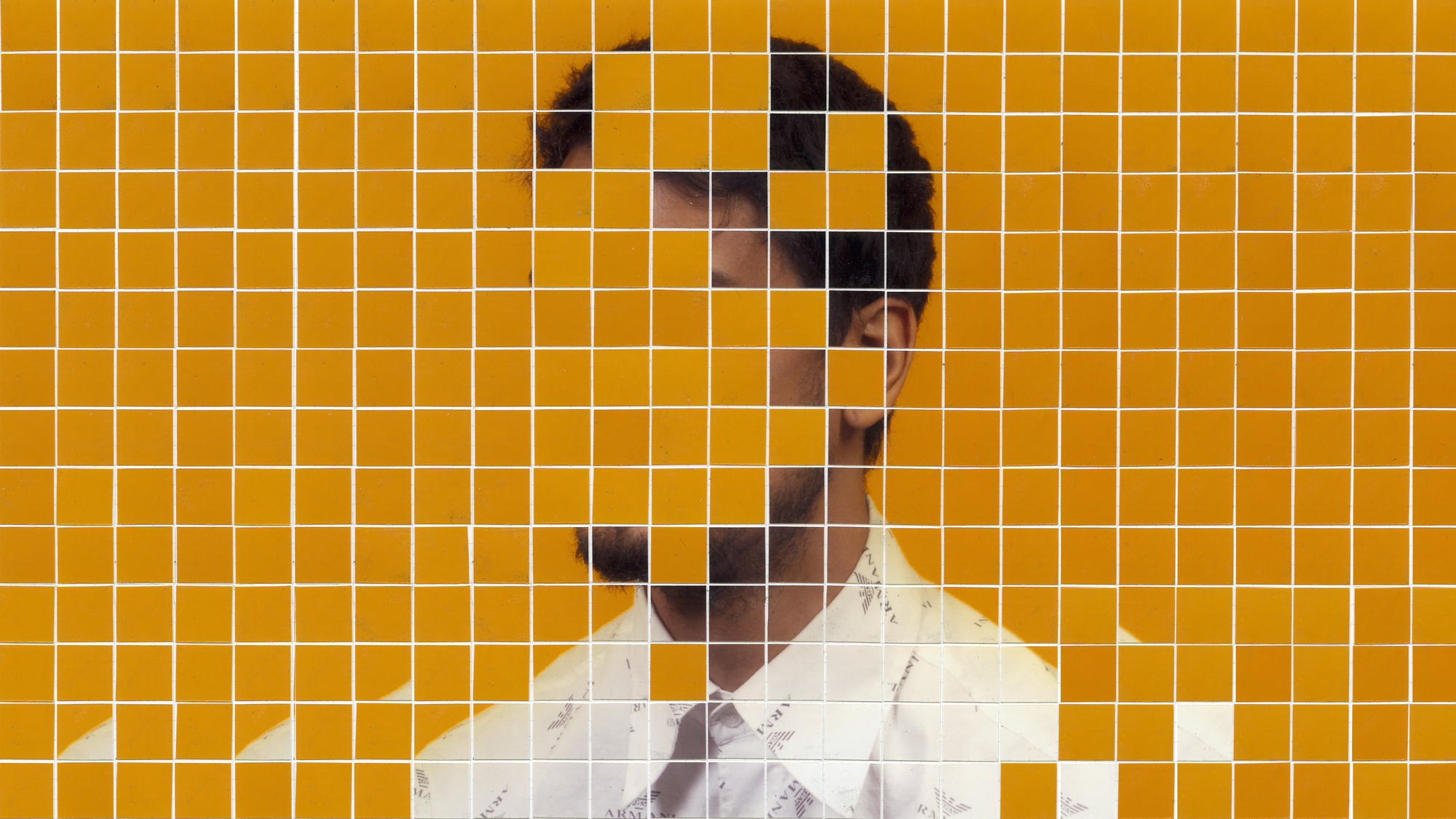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