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马斯·内格尔和丹尼尔·丹内特都是美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在意识究竟为何物这个问题上,两人的观点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这篇文章发表在去年3月的《纽约书评》上,是内格尔为丹内特关于意识问题的新书《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 The Evolution of Minds》所写的书评。
五十年多来,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一直在参与一项有关如何理解人类世界的宏大启蒙运动。他用科学知识的进展,将人们从对心智问题的迷茫中解脱出来:意识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很难被驱逐,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现象。《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是他的第18本书(其中有13本是独著),丹内特在书中提供了一种富有价值的、十分明晰的整全世界观。尽管书中的内容得到了很多科学数据的支持,但他也承认,他的很多观点仍然属于假说,既没有得到经验的证明,也没有得到哲学的证明。
丹内特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对科学知识有着极强的求知欲。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最擅长于清晰而深入地传播科学知识,并解释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的文字既充满才智,又十分优雅。在这本新书中,他的观点十分鲜明,试图竭力理解并反驳与其相反的观点。但他又承认,他希望我们所相信的观点是相当违背直觉的。我最终将会解释,为什么在我看来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不成功的。但首先还是让我从他的论证开始,这其中包含了很多真知灼见。
该书采用了历史叙事结构,将我们从前生物世界带到了人类心智和人类文明阶段。历史的演变基于自然选择所发生的进化,这种进化具有不同的形式,自然选择既发生在生物层面又发生在文化层面,而这些进化形式正是我们解释世界的最重要的方法。丹内特在全书一开篇就坚信这样一种假设:我们只是物质实体,任何看上去与这种假设相反的现象都一定可以通过某种解释的方法,与这种假设相一致。巴赫或毕加索的创造性天赋,我们听到巴赫的《第四勃兰登堡协奏曲》或看到毕加索的《镜子前的女孩》(Girl Before a Mirror),这些现象都来自于一系列前后相继的物理事件。在单细胞生物出现之前,这些物理事件是从地球表面化学成分的演变开始的。丹内特知道,在历史演变的时间进程中,仍有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古老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新近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文化起源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没有妨碍丹内特提出自己的假说。
丹内特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在哲学家威尔弗雷德·塞勒斯(Wilfrid Sellars)所作的著名区分的框架内来解释尚待解释的现象。塞勒斯区分了“显现影像”(manifest image)和“科学影像”(scientific image)——两种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丹内特写道,根据“显现影像”,世界
充满了其他人、植物和动物、家具和房子以及汽车……颜色和彩虹以及落日、声音和理发、酒店经营和美元、问题和机会以及错误,还有其他种种事物。我们很容易辨识、指认、爱或恨这些纷繁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能够操控甚至创造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属于人类的世界。
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影像”,世界
充满了分子、原子、电子、引力、夸克,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暗能量?弦理论?膜理论?)?
在丹内特看来,“科学影像”的世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世界。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解释分子的世界如何变成了一个产生了诸如人类这样的生物的世界。在人类看来,每一样复杂的物质实体,包括人类自身,与“科学影像”的世界比起来,都显得如此不同。
丹内特大大拓展了塞勒斯的观点,他观察到,“显现影像”的概念不仅可以适用于人类,而且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生物,直到最低等的细菌。所有的有机生命都有生物感官和物理反应,这让它们可以探测环境并对环境的某些特征作出恰当的反应——丹内特把这些特征称为“环境赋使”(affordances),包括营养物、有毒物、安全、危险、能量的来源或繁衍的可能性、潜在的天敌或猎物。
对于每一种有机生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这些环境特征定义了它们“眼中”的世界。对它们而言,这些特征既明显又重要,而其他特征则完全可以被忽视。无论根本的生理机制是什么,“显现影像”的内容通过有机生物的行为和它们与环境互动的方式显现了自身,我们没有必要认为有机生物是有意识地知觉到了它们的环境。不过,这的确是意识的早期形式,是通往人类意识的第一步。
····
产生了“显现影像”的进化有着漫长的过程。最初,进化发生在生物层面。然后,就人类社会而言,进化又发生在了文化层面。只有到了近现代,人类心智和人类文明的独特性,才使得进化部分受到了人类智能设计的影响。不过,正如丹内特所说,从一开始生物领域就充满了自然的设计——从隐含在DNA中的基因编码到单细胞生物的新陈代谢,再到人类视觉系统的运转——这种设计不是有目的的产物,并不依赖于人类的认知能力。
丹内特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人类和其他有机生物为什么能得以生存,并与这个世界和其他生物发生互动,以及为什么生物会繁衍,关于这些问题,有很多是人类或其他生物无法理解的。这些现象的发生根本不需要意识,而是一种自然能力。这一点对于像细菌和树这样的生物来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因为它们完全没有意识。但是,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像人类这样的生物能够有意识地理解很多事物。在丹内特看来,大部分人类行为和人类身体的行为——消化肉食、移动某些肌肉抓住门把手、将作用于耳膜的声波转化为有意义的语句——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人类能有意识地让这些行为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而是出于丹内特所谓的“自由独立的”(free-floating)原因而存在,是自然选择的压力才让这些行为和过程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自然选择模式的出现和存在一定有其原因,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原因。但是,我们不必非得知道这些原因,我们就能够知道导致人类行为的那种自然能力。
而且,我们也不必非得理解自然能力背后的机制。丹内特用了一个鲜活的比喻来表明:“显现影像”描绘了我们每日生活于此的这个世界,但这些影像是由一系列的用户幻觉(user-illusions)所构成的,
就像单击并拖动图标会产生的那种很自然的用户幻觉,有些文件被拖放到了文件夹,而有些经常使用的文件则被拖放到了电脑的“桌面”。发生在“桌面”背后的运行机制异常复杂,但用户不需要知道这些机制,因为,聪明的电脑界面设计者会将可视物简化,让人类的眼球非常容易捕捉这些可视物,并增加声音效果,以帮助用户集中注意力。而在电脑的内部,却没有任何简洁而明了的东西可以对应于屏幕所显示的“桌面”文件夹。
他说,每种生物的“显现影像”就是“一种由进化所精巧设计的用户幻觉,而这种幻觉能够满足该用户的需要。”尽管使用了“幻觉”一词,但丹内特并不希望简单拒绝事物存在的真实性,而正是这些事物构成了“显现影像”。我们所看见、听见并与之互动的事物,“不仅是虚构的,而且也是现实存在(也即真实模式)的不同版本”。然而,根本的现实存在——一种自为的存在,一种不以人类或其他生物为目的的存在——只能被“科学影像”精确呈现,也即是说,最终是用物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理学的语言来呈现。
····
类似电脑“桌面”上的小图标那样的用户幻觉,并不是由聪明的界面设计师所创造出来的。几乎所有类似的幻觉——诸如我们关于他人的影像,他人的面孔、声音和行为,感觉到某些东西好吃或舒服而另一些东西令人恶心或危险——都是“自下而上”的设计产物,这种产物只能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来理解,而不是通过人工的“自上而下”的设计来理解。达尔文通过丹内特所谓的“反常的逆向推理”(strange inversion of reasoning)向我们表明了,如何拒斥人们的一种直觉倾向——人们总是用人类能力去解释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各种能力和设计——以及如何用自然选择的解释去替代人类能力的解释,而自然选择是由偶然变异、复制和差异化生存所形成的一个无意识过程。
在计算机的发明者阿兰·图灵看来,无意识的机器并不需要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有能力实现完美的数字运算。基于这样一种新的“反常的逆向推理”,我们现在对“自下而上”的运作机制就有了一般性的了解。这种机制可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计算和程序控制,既包括自然系统,也包括人工系统。因此,能力的产生并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理解行为。丹内特认为,当我们将这两种系统放在一起来理解时,我们就能明白这个世界的所有智力和意识最终都来自于没有意识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混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形成更有能力的——也因此是更有意识的——系统。这的确是一种反常的逆向过程,推翻了前达尔文时代相信“意识出现在前”的神创论,替之以“意识出现在后”的进化论。作为智能设计者的人类,是经过了长期进化才形成意识的。
他还补充道:
图灵本人就是“生命之树”的一个细小分枝,他的发明创造,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都是盲目的达尔文式进化过程的间接产物,就跟蜘蛛会织网,海狸会筑坝一样……
进化过程最重要也是最高级的阶段就是文化的进化。丹内特相信,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一样,背后的很多东西是不为人知的。他援用了彼得·戈德弗雷-史密斯(Peter Godfrey-Smith)的定义,从该定义出发,进化的概念显然可以用于更广阔的领域:
经由自然选择的进化也发生在人类社会中,因为(i)人类社会中不同成员的特征产生了变异,(ii)这种变异导致了不同的繁衍比例,(iii)这些变异是可以遗传的。
就生物的情况而言,变异是由DNA的变异造成的,并通过繁衍、交配或其他方式得以传承。但同样的进化模式也适用于并非由基因导致的行为变异,而这种行为变异之所以能传承下去,只是因为人群中的成员复制了这种变异行为,无论它是一种游戏、一个词汇、一种迷信,还是一种穿着风格。
····
这就是理查德·道金斯所谓的令人影像深刻的“文化模因”(memes)所要表达的观点。丹内特认为,“文化模因”这一概念在描绘信息和文化进化方面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他将“模因”重新定义为:
它是一些行为(广义上的)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被复制、被传播、被记忆、被教导、被避免、被谴责、被炫耀、被嘲讽、被模仿、被审查、被神圣化。
“文化模因“包括了如下一些模式化的行为:将棒球帽反着戴在头上,或者,以某种形状修建一扇拱门。然而,“文化模因”的最佳例证是我们的语言。一个词汇,就像一个病毒,需要一个寄主来繁衍。一个词汇只有最终传播给他人,而他人通过模仿习得该词汇,它才能存活下来:
就像一个病毒,它被设计出来(主要通过进化)激发和增强它自身的复制,它所产生的每一个标记,都会出现在它后代身上。传承自上一代的一系列标记形成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就好比是一个物种。
“类型”(type)和“标记”(token)的区分,来自于语言哲学:“tomato”(番茄)这个词属于一种类型,而任何关于它的发音、文字和观念都属于一种标记。不同的标记在物理形态上也许非常不同——你可以说“tomayto”,我可以说“tomahto”——让这两种不同发音指向同一种类型的,是不同的人所共有的感知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用不同的口音说同一种语言,或者用不同的字体写同一种文字时,人们还能理解彼此所说所写的原因。
当 一个孩子开始学自己的母语时,他并不理解语言是如何运作的。丹内特相信,很可能,语言同样是由未经人工设计的方式产生的,也许,它最早产生于人们无意识地将声音与前语言的思想相结合(而且不仅是声音,还包括身体语言:正如丹内特所观察的,我们发现我们说话时很难不摆动我们的手臂。这表明,最早期的语言也许有一部分是无声语言)。最终,这些模因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语言。有着丰富表达能力的语言具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却被大量的人群所共用。
语言允许我们在表达不在场的事物时超越时空限制,允许我们积累共享的知识体系,允许我们通过写作在个人脑海之外存贮知识。语言的这些作用带来了广泛的共同知识和实践,而这些知识和实践散布于创造了人类文明的诸多心智和人群之中。语言还让我们得以将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思想,并由此有意识地自上而下地发展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科学、艺术、技术和制度设计。
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和进步只有深植于一种能力才是可能的,而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文化进化的结果。丹内特并没有贬低个人才能的贡献,他只是告诫我们,不要忘了这一切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有着必不可少的前置条件,不要忘了数千年来相互竞争的模因之间的“军备竞赛”——完全未经设计的进化以及语言的产生和消灭正是这方面的例证。
当然,人类大脑的生物学进化,以及大脑与文化在过去五千年的同步进化,让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然而,在当前这个时点,我们仍然只能猜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丹内特引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大脑的构造是神经元自下而上竞争和相互作用的产物——神经元的运作方式部分应合了模因的影响。但是,无论神经元运作的细节是什么,如果丹内特关于我们是物质实体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有的理解能力、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感知能力和思想观念都是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得以表征,既呈现给我们“显现影像”,又能让我们形成“科学影像”。
····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意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丹内特持有一种不同的而又明显矛盾的观点。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显现影像不仅包括物理身体和中枢神经系统,还包括我们具有精妙特征的意识——感知、情绪和认知——也包括我们对他人和其他非人类生物的意识。为了与他的“显现影像”观点保持一致,丹内特坚持认为,意识不是现实的一部分,至少不是像大脑那样的现实,而是一种特别明显和有说服力的用户幻觉,这种幻觉是我们与他人互动以及约束和管理我们自身行为的必要条件。总之,意识就是幻觉。
你可能会问,既然每一个幻觉自身都是一种意识体验——与现实不相符的一种体验——意识又怎么可能是一种幻觉。因此,对于我来说,我不可能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具有意识:正如笛卡尔那个著名的观察,我自身意识的真实性是唯一一件我不会受到蒙骗的事情。丹内特回避了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将我们带到了他的观点的核心之处:在意识和一般意义上的心智方面,他拒绝承认第一人称视角的权威性。
这一观点非常怪异,很难用语言表达,但它与上世纪中叶在心理学中流行的行为主义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们拥有主观内在生活——不能仅仅用物理术语去描绘——的有意识的生物,丹内特相信,这种想法是一种有用的虚构。这种虚构可以让我们预测有意识的生物是如何行动的,也可以让我们与那些生物进行互动。他发明了一个术语“heterophenomenology”来描述(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现象:我们每个人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颜色、形状、味道、声音、家具影像、风景等等——归咎于与他人的互动,而这种互动还包含了他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表征。
在丹内特看来,现实是一种表征,这种表征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而我们却对这种在神经结构中发现的表征所知甚少。同样,我们对于我们心智的概念也所知甚少。那种概念没有捕获到内在的心智现实,而是把心智当成了我们需要与他人就我们不同的能力和性情(有时,也是为了掩盖这些能力和性情)进行沟通的一种结果。这是一种粗糙而便于理解的看待心智的方式。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关于我们心智的第一人称视角与我们关于他人心智的第二人称视角并没有太大不同:我们无法看见、听见、感觉到我们大脑中复杂的神经机器是如何搅动的,但我们不得不对心智给出一种简明而易于理解的版本,而用户幻觉的概念对于我们是如此之熟悉,以至于我们不仅把用户幻觉当成是一种现实,而且还当成是所有已知现实中最不可能被还原和最紧密的一种现实。
问题在于,丹内特不仅得出结论说,在我们行为能力的背后还有很多不为第一人称视角所知的东西——这当然是正确的——还得出结论说,无论第一人称视角向我们揭示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神经机器运作的一种产物。换句话说,当我看见美国国旗时,在我看来,我的主观视野中出现了一些红色的条纹,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仅有的现实发生在我的视觉皮质中,这是一个我无法描述的物理过程。这就是关于意识的“一个简明而易于理解的版本”。
我记得马克斯兄弟(译注:美国著名喜剧演员)说过一句台词:“你会相信谁?我,还是你撒谎的眼睛?”丹内特想让我们无视再明显不过的现象——在意识状态中,我们能够立即意识到真实的主观体验,包括颜色、气味、声音、触觉等等,这些体验即便的确是由神经运动形成的(或者,也许既有神经方面的原因,也有体验方面的原因),也不可能全部用神经术语来解释。另外,他之所以想让我们无视这些现象,是因为这些现象的实在性与科学上的物理主义不相容。在他看来,物理主义为现实设定了外在边界。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丹内特是在“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一个论点”。
如果我对他的理解是对的,他就是在要求我们用行为主义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自身:当我似乎拥有一种主观的意识体验时,这种体验只不过是一种信念,它呈现在我将要说出来的话当中。在丹内特看来,当我看到美国国旗时,出现在我视野中的红色条纹只不过是那种信念的“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 object),就像圣诞老人是孩子过圣诞节时在脑海中浮现出的信念的意向性客体,而没有哪一个意向性客体是真实的。回想一下,丹内特认为,即便树木和细菌也有自己的“显现影像”,这种影像只能通过它们的外在行为而得到理解。同理,人类也是如此:“显现影像”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影像。
····
我们没有理由以科学的名义去接受这种对心智的歪曲理解。而正是将心智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自17世纪以来物理学才有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进展。这个世界存在着比物理学所能解释的更多类型的实在,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一种神秘主义:这只不过是承认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解释所有事物的理论,科学将不得不扩展它的边界,以解释与当前的物理学所能解释的事物完全不同的事物。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想法会带来极端的后果,尤其是给丹内特所钟爱的自然科学和生物学带来极端的后果:当前的进化理论,在形式上仍然是一种纯粹的物理理论,正如丹内特所想的那样,如果意识不是一种幻觉,进化理论就必须将非物理因素整合进对意识的解释之中。物理主义仍然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科学不会因为用人为裁剪的数据去迎合流行的理论而得到进步。
书中还有很多内容我没谈论到,比如,教育、信息理论、生命起源之前的化学反应、意义的分析、可能性的心理学角色、心智种类的分类、人工智能。对于人工智能历史和前景的反思、我们应该如何管控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如何与之相处,丹内特给出的回答是明智而有益的。他总结说: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不是机器比我们更聪明,从而篡夺我们掌握自身航行之舵的能力,而是我们过分高估了对最新的这些思考工具的理解,在机器还远不具有我们的能力之前,我们就过早把控制权交给了机器。
我们应该让新的认知假体(也即人工智能)继续成为人类的仆人,成为人类的工具,而不是人类的合作者。人工智能的“天生”目标是由它的创造者决定的,它应该透明而积极地回应用户的需求。
关于人类心智的真实属性,丹内特在某种意义上持有一种古老的观点,这种观点要追溯到笛卡尔时代。他对笛卡尔抱有敬意,提到了他称之为“笛卡尔引力”(Cartesian gravity)的力量,一种从第一人称视角去看待事物的能力。他把产生幻觉的意识领域称为“笛卡尔剧院”(Cartesian Theater)。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推进对意识的理解的唯一方式,是让相关研究者尽可能充分地发展和捍卫他们相互竞争的概念——正如丹内特在书中所做的那样。即便读者认为他的新书的整体观点并不令人信服,但他们还是会在书中发现很多有趣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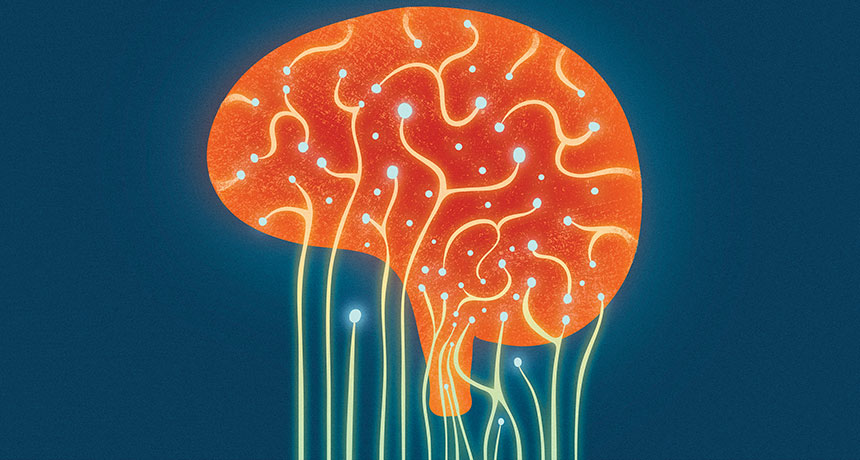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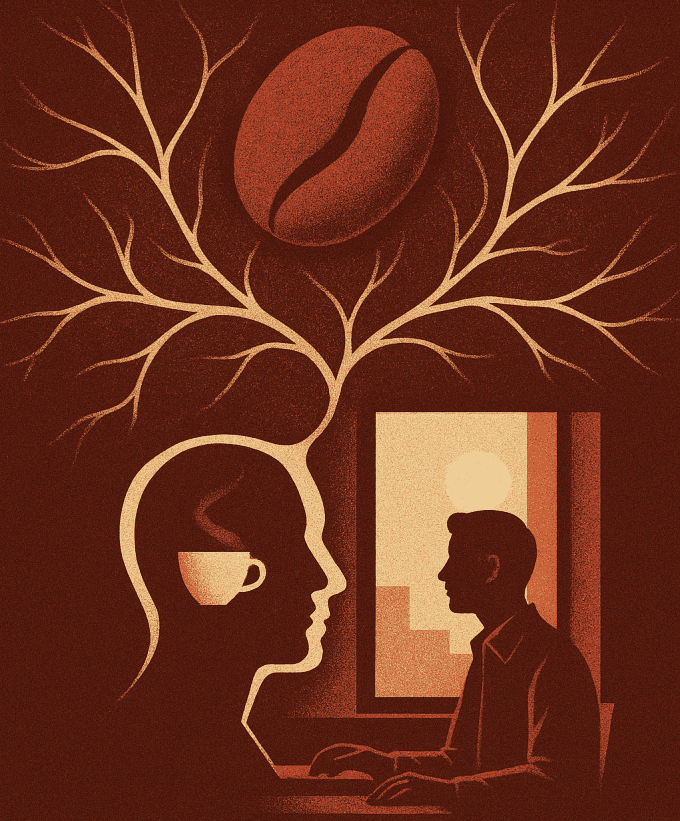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