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难想象,如今我们竟然要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寻找例证。很长时间以来,这些稳固的价值观定义了我们的现代生活。多数人都以为,抨击这些价值观的人来自极端右翼分子:他们是进步主义的敌人、是反科学宗教运动的先锋、是封闭心智的代表。
然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还有另一类人,对启蒙遗产的攻击影响更大,他们来自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当进步观的支持者看到如此之多的灾难、倒退、颠覆、新战争揭开了老伤疤、新秩序叠加了旧不义、作为进步副作用的新破坏超过了进步的好意图,他们就对进步观产生了信任危机。悲观主义者怀疑,进步观是否能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愤世嫉俗者则怀疑,今天的生活是否真的比往昔更好。科学和技术是否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妙,或者当科技的巨轮滚滚向前,它是否又给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就像在《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的那台永不停歇的机器?
这些问题并不新鲜。在启蒙运动发生的巴黎,让·雅克·卢梭问过这些问题;在令人胆寒的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浪漫主义运动分子问过这些问题;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问过这些问题。而就在过去几年,这些问题再次以某些新的方式被提了出来。
于是,身为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的史蒂芬·平克开始问答这些问题,他捍卫了如下一些观点:人类的确取得了进步;今日的生活比过去更好;我们的未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超越今日。正如平克所说:“我们能够运用理性和同理心增加人类的福祉,这样的启蒙原则似乎已经变得理所当然,甚至陈腐和老朽了。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表明,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平克的新书《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系统论证了衡量进步的各种标准,用图表展示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进步,包括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厌恶、欺凌、交通事故、石油泄漏、贫困、闲暇、妇女权利等方面的进步。在这些变化中,有一项是出人意料的:在美国,无神论者正在增长,而宗教信徒正在减少。我们很容易从图表上找到一些瑕疵:比如,有图表显示,1945年以后每年死于战争的人数呈下降趋势,然而这一趋势似乎看上去还不如从1600年开始的下降趋势那般明显。但如果你能公正地看待这些图表,就会发现,平克提供的大多数数据和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一再坚定地描绘了进步的图景。
对于一本书而言,叙述啰嗦、立场鲜明很难说是好的品质,但就这本书而言,却是它的优点所在,因为平克所要寻找的例证是如此重要、如此困难,以至于任何细微的证据都他不能放过——在当下的历史时期很多人都不相信乐观主义。平克借用了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译注: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提出了平行宇宙概念,著有《真实世界的脉络》、《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对乐观主义信念的看法,认为“乐观信念的所有失败——所有魔鬼——都要归结于知识的不充分……”尽管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是第一次重大的反启蒙运动,但平克认为1960年代也出现了一些反启蒙的浪漫主义情绪。他提到了某种宗教倾向,由于人们专注于来世,这就与推动此世进步或者深度关注此世产生了冲突。他提到了民族主义和其他运动让个人利益或者所有人的利益屈从于特殊利益集团。他提到了环境保护主义的一种他所谓的新浪漫主义形式,它提倡让人类服从于自然生态,寻求绿色发展之道,但不是通过技术进步,而是通过谴责当今技术和生活方式来实现。他还提到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衰落叙事,一种预见了我们所在时代正在上演的衰落论或末日论,这种衰落要么通过核战争,要么通过科技毁灭,要么通过现代社会的虚无和堕落得以实现。
面对几十年来的这些怀疑,人们可能还会补上这样一个事实:人性的缺陷从来没有像在21世纪那样暴露无遗。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健康、贫困、平等、生态、正义。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挫败,通过数字媒体对负面新闻不间断地、连篇累牍地报道,并强烈呼吁采取行动,让它们变得更扎眼了,也耗尽了很多人的期望。
在过去两年中——之前从未发生过——很多学生在我的课堂上表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不平等“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过”。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回答则是,“不,过去要糟糕得多,让我告诉你们1950年之前的生活……”然而,这样的回答似乎并没有让学生感到满意,尤其是当学生的愤怒和痛苦被现实所印证的时候。对于这样的问题,平克提供的大量清晰而科学的数据是一种更好的工具,比起我所讲述的前现代生活的不堪往事,更能重燃人们的希望。
在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之后,该书用三个章节捍卫了平克所推崇的人类三大工具: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在关于理性的这一章节,他将政治偏见和极端化视为是理性实践的新的重大威胁,其中包括他称为学术圈“对自由主义一边倒”的现象。为了驳斥人类在根本上是非理性的这一信念,他正确地指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只是表明了,人类有能力做到理性,而不是声称人类总是理性的,而践行理性是有价值的、有益的。在这里(在关于平等权利和进步的未来等章节中),平克对“特朗普主义”(Trumpism)和相关现象做了最有力的批判,但即便如此,他仍不忘持守理性,呼吁理性的拥护者抵制愤世嫉俗地把这个世界视为是后真相世界。他坚信,事实和逻辑是一种累积的力量,是具有说服力的。他观察到,事实证明,揭穿谎言的报道是很能吸引读者关注的,而且这类报道的数量和受欢迎程度都在上升,编辑们已经发现了这一趋势。
平克对科学的推崇是直言不讳的:他认为科学的成就超越了诸多艺术、音乐、文学巨著,是至美、健康、财富和自由的来源。他审视了那种反科学的论调,这种论调试图把科学局限在物质和技术领域,而将伦理、价值观、文化等领域视为非科学。他尤其批驳了把社会丑恶现象归结到科学身上的观点,强调我们需要区分科学本身与科学被人为用于歧途、被误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源头、造成性别不平等等现象。有些人认为,性别歧视和社会不公等现象是得到了科学结论支持的,但平克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他正确地指出,社会正义运动能够从科学研究中受益,科学是它的同盟而不是敌人。
然而,科学很容易被误用于非正义或破坏行为。对于这种危险,平克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人文主义。它能阻止科学成为进步和幸福的敌人,他认为,要发挥科学做善事的力量,阻止它行破坏的力量。
人文主义定义繁多,但平克的定义是我们所谓的现代世俗人文主义,他把它理解为“追求人类福祉——生命、健康、幸福、自由、知识、爱、丰富的体验——的最大化”,并且“没有排除对动物福祉的追求”,人文主义要“倡导意义和道德的非超自然基础:没有上帝的善(good without God)”。他将这种人文主义与《美国独立宣言》中推动现世社会进步的价值观、与启蒙运动和后启蒙运动关于人权的思想联系起来。平克审视了他所认为的人文主义的智识威胁:比如,那些将人文主义看成是冷冰冰的功利主义的人;那些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宗教信仰需求的人;那种常见的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典型批评:没有上帝,就没有善或美德。有些读者可能会对该书感到不满,这本350页的书所提供有价值的、令人信服的数据,大多是信仰中立的,它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只有真正的无神论才能确保科学进步会造福人类,而不是伤害人类。然而,平克的世俗人文主义不像当今很多无神论者的言论那样激进。他关心现世的福祉,而不是谴责宗教。他得出的结论是很多有神论者能够并且已经接受了的:进步只是意味着要求我们珍惜生命而不是死亡、珍惜健康而不是疾病、珍惜富足而不是贫穷、珍惜自由而不是压迫、珍惜幸福而不是痛苦、珍惜知识而不是迷信。
平克还简要审视了人们将感性(爱、激情、感受)置于理性之上的信念。但他认为,这种信念是自败的(self-defeating):只要人们试图相信感性至上的信念,他们就需要为这一信念提供理性论证,而这种论证恰恰证明了理性论证是信念最坚实的基础。然而,当我反思平克的这一论证时,我想起了在科学发展历程的关键时刻,科学曾经以同样的方式遭遇了自败。
作为一个主动的、由人类行为驱动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进步观是由弗朗西斯·培根在17世纪初期第一次做出全面阐述的。当时他认为,人类对经验的协作探索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真理,从而彻底改造人类文明,让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可以逐渐比前辈过得更好。这种进步观似乎没有得到众人的响应,因为培根没有拿出证据,证明这一史无前例的进步观可以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即便他掌握了证据,人们还是没有能力用合乎理性的证据去证明,合乎理性的证据具有证明的效力。那个时候,时常会出现一些新的发现——木星的卫星、各种昆虫、血液循环——然而,把这些发现投入到实际的应用却进展缓慢。
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曾经说过的那样,直到19世纪培根的信念才得到了认同:如果培根的同行们将金钱和生命投入到科研中,他们就会获得财富,以及能够改变人类境况的技术。正如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关于因果和事物神秘运动的知识能够扩展人类社会认识一切能够认识的事物的认知边界。然而,在鼓动起人类对理性和科学的热情方面,培根的确成功了。我曾向我的学生们提到过他的一个论证,令他们颇感惊讶:培根诉诸于上帝的性质,认为一个卓越的造物主不可能既将欲望置于人类的身心,又将人类置于荒野,而不提供满足他们欲望的工具和办法。因此,理性必定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独特礼物,也必定是人类想要并且能够获得的东西。
培根的这一论证时常——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会让世俗科学的信奉者感到尴尬。作为无神论者,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追随者意识到,早期的科学没有世俗的证据支持他们对于理性和证据之力量的信仰,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人们不禁要想知道,培根所在的时代会如何看待平克所提供的这些丰富证据呢?培根自己也许会很高兴地看到,他所预言的未来得到了实现。但当他手里捧着平克的这本书时,他也许会感受到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横亘于自己的内心:一种是他所确信的观点:认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能让我们的今日胜过往昔,并且还能让我们的未来胜过今日;另一种是他不那么确信的观点:无论其论证有多么雄辩和充分,平克坚信,能将我们的才智转化为善并摆脱邪恶的那种人性和富有同理心的人文主义,必定是世俗主义的。
如果不循环诉诸于科学和理性,平克对于科学和理性之力量的证明就不会比培根做得更为成功。然而,对于那些始终相信证据的说服力的人而言,他们很难想象还有一种辩护,能比平克对于进步的事实和可能的辩护做得更成功了。
翻译:王培
编辑:EON
原文:https://harvardmagazine.com/2018/03/steven-pinker-enlightenment-now
芝加哥大学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史的助理教授,获得过奖项的科幻小说家。她与詹姆斯·汉金斯合著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复兴》(The Recovery of Ancient Philosophy in the Renaissance: A Brief Guide),还著有《在文艺复兴时期阅读卢克莱修》(Reading Lucretius in the Renaissance),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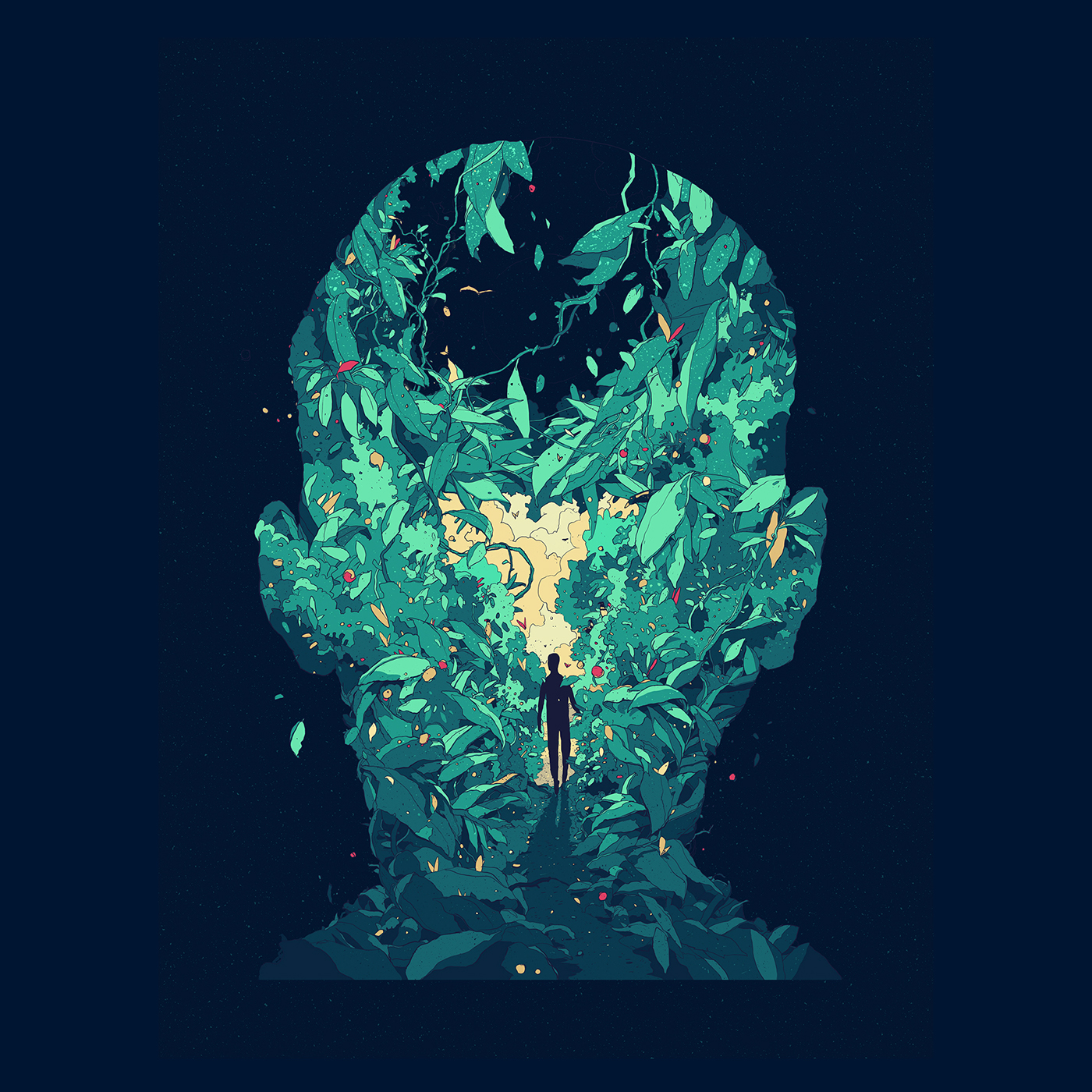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