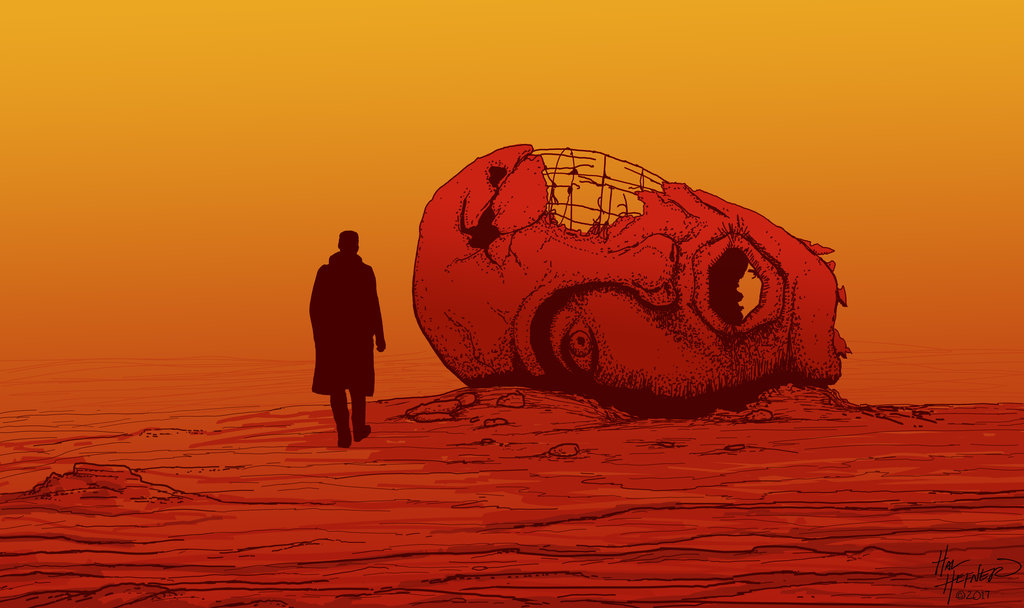

在《银翼杀手2049》的世界里,地球已经不再是2017年那样了。美国的圣迭戈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垃圾场,农作物无法在户外生长,一家独大的企业垄断着所有的农业和工业。洛杉矶的天空布满了烟雾,街道上满是喋喋不休的流浪汉和伺机而动的帮派(好吧,也许有些事情没有改变)。
然而,最大的变化有点难以窥见。2049年的世界是由人类和复制人组成的,这是一种与人类几乎没有区别的生物机器人,被人类当作奴隶种族。它们出生的时候是发育完全的成年人,滑动着,颤抖着,脚先从一个黏糊糊的塑料袋里伸出来,然后在4年内逐渐走向死亡。在其他方面,它们就像人一样,一样说话,一样行动,有人类一样的身躯,甚至像人一样流血。它们唯一可观察到的与人类不同的生理差异是他们眼皮下眼白的序列号,只有在紫外线下才看得见。
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表现得像人类,甚至像人类一样思考,仅有一些明显的例外。首先,它们对人类有绝对的忠诚,不能违背他们的任何命令。其次,它们通常不会在短暂的一生中产生同理心和强烈的情绪。这些钝化的情绪特征是唯一能帮助我们检测2049年的复制人的可靠方法。复制人需要通过“Voight-Kampff”测试,回答一系列问题——它们冗长且混乱、而且需要复制人快速反应,还带有侮辱性的陈述和情绪挑衅性;检测者注意复制人的反应时间和瞳孔的扩张,这两种对情绪反应的测量其实也是现实中的科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1,2]。
第三个区别是迄今为止最值得重视的,它支撑了另外两个区别。2049年的复制人在出生之前就被植入了一组错误记忆(通常被许多复制人分享),然后模拟它们记忆中的生命。这些记忆被设计来“缓冲”复制人的情绪,使它们的情绪反应迟钝,并教导它们完全服从和忠诚于人类。
这些记忆定义了它们的“个性”,确立了它们的怪癖和行为习惯,并创造了一系列用来引导它们处理周遭情况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虚假的记忆会从头开始创造新的身份,使这些复制人不仅仅是血肉堆砌的自动机,更是与人类几乎没有区别的存在。
2049年是遥远的未来,那时的科技只存在于幻想中。这些复制人的错误记忆就像飞行汽车、全息广告或者殖民外星球——我们有生之年从未见过。记忆会是错误的,这种未来构想只存在于虚构中,而非现实。
不,在现实中即可实现。
1980年,米歇尔·史密斯(Michelle Smith)写了《米歇尔回忆录》(Michelle Remembers),这是一本畅销书,记录了她在五岁时被邪教所虐待的仪式。本书包含了大量骇人听闻的细节,详细描述了可怕的外科整形手术、强奸和猥亵儿童、以及对圣物的亵渎。然而,史密斯并没有按照人们所想的那样准确记住这些情节。她的治疗师(后来的丈夫)劳伦斯·帕兹德(Lawrence Pazder)却“找回”了她的记忆。因为她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承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和紧张,这段记忆显然被压抑了很久。

几年后,一场道德恐慌爆发了。很快,数百人(大部分是父母)站出来,声称孩子们在社会工作者和日托工作人员的手中遭受了类似的苦难。史密斯的书似乎揭示了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的、涉及性侵的撒旦邪教,它渗透到了全球的托儿所。警察几乎完全基于这些孩子的证词,展开1万多起调查,法院审判了100多起案件(半数被定罪)。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图斯(Elizabeth Loftus)对这些记忆有些怀疑,并怀疑这些记忆是否真的存在。1996年,她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是否有人记得一件从未发生过的具体事件?为了找到答案,她和一个名叫克里斯(Chris)的少年以及他的直系亲属展开工作[3]。在这个实验中,克里斯的童年生活是由他的家庭提供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的家人写了一个听起来很真实的故事,即克里斯在当地商场的一家玩具店里迷路了,他害怕得哭了,后来他被送回家人身边。
当他被要求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这些经历时,克里斯最初持怀疑态度,但最终他开始越来越清楚地回忆起这段经历。在这个实验后,他的错误记忆比四种真实记忆中的一些内容更清晰,他可以提供他的家人最初没有提供的故事细节。他可以详细地描述那家玩具店、他和其他人穿的衣服,以及他当时的想法,尽管这些细节都没有出现在最初的故事里。换句话说,他根据最初的故事场景形成了一个记忆,并在自己的记忆中填满了缺失的细节,而没有意识到记忆是假的。当洛夫图斯在其他家庭中重复这一实验过程时,她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产生了错误记忆,就像克里斯一样。因此,米歇尔·史密斯和其他心理学家们对“撒旦式的性虐待”的记忆可能是暗示的结果,而不是真实的回忆。
之后,警方的最终报告显示,父母和孩子提供的证词是唯一实质性证据,不足以判罪(警方还没有发现关于性侵仪式的法医证据),而且进一步的调查还发现,帕兹德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邪教有着长期浓厚的兴趣;这两个发现都证实了洛夫图斯的假设。更多不一致的结论开始堆积,大多数涉及证据不足或证人不可靠,而且引人注目的是,后来许多卷入案件的人被无罪释放(最明显的一个案件是在1990年,持续了六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刑事审判)。被妖魔化的性虐待仪式逐渐褪下虚构的外衣,大多数原被定罪的人最终被释放。
然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米歇尔·史密斯或其他孩子的个性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在“记住”这些性侵事件之后应该会产生创伤体验并需要从中恢复。虽然错误记忆可以被植入,但可以肯定的是,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利用这些错误记忆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这是一种在遥远未来可能诞生的技术,对吧?
不,你现在就可以用这项技术。
如今,虚假的记忆可以用来改变一个人的未来行为,就像真实的记忆一样。例如,许多人(但是当然不是我)无法喝至少一种类型的酒(比如某些人不能喝火龙肉桂威士忌),因为他们曾经在喝了这种酒之后做出了令人尴尬或恶心的事(比如他们在晚上1点观听Drake的歌《马文的房间》后给所有前任发短信)。
鉴于这些事是常见的,并且可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洛夫图斯的小组试图利用这些事件的错误版本改变酒精偏好[4]。在这项研究中,他们使用了与购物中心事件相同的实验设计,但是他们用喝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烈性酒后生病的故事代替了在商场迷路的故事。如果一个人成功地获得了这种错误记忆,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比其他人更喜欢这种类型的酒了。同样的程序也可以修改食物的喜好,这表明制造错误记忆可以作为改变行为的一般过程[5]。
虽然这种高度具体的、情境性的行为,与绝对忠诚那样的行为大相径庭,但是它们仍然表明,哪怕是一段记忆中的一段情节,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会对我们目前的行为、个性和偏好产生强大的影响。如果这就是植入一个错误记忆的效果,想象一下植入许多错误记忆的潜在影响。也许,像忠诚或勤奋这样的整体品质在将来某一天也可能会被技术操纵。
我们的记忆是身份的基础,因此虚假的记忆可以真实地改变我们的身份认知。在遥远的2049年,植入的记忆可以编织出一个人的个性,创造出丰富但却虚构的自我,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的记忆反映了真实的事件,真实的记忆构建着我们真实的身份,无论这种身份是更好还是更差。或者,事实并非如此。
参考:
Bradley, M.M., Miccoli, L., Escrig, M.A., Lang, P.J. (2008). The pupil as a measure of emotional arousal and autonomic activation. Psychophysiology. 45: 602-607.
Dresler, T., Mériau, K., Heekeren, H.R., van der Meer, E. (2009). Emotional Stroop task: effect of word arousal and subject anxiety on emotional interference. Psychol. Res. 73: 364-371.
Loftus, E.F., Pickrell, J.F. (1996). 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 Psychiatr Ann. 25: 720-725.
Clifasefi, S.L., Bernstein, D.M., Mantonakis, A., Loftus, E.F. (2012). “Queasy does it”: False alcohol beliefs and memories may lead to diminished alcohol preferences. Acta Psychol. 143: 14-19.
Bernstein, D.M., Laney, C., Morris, E.K., Loftus, E.F. (2005). False memories about food can lead to food avoidance. Soc. Cogn. 23: 1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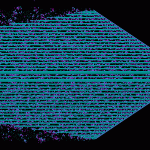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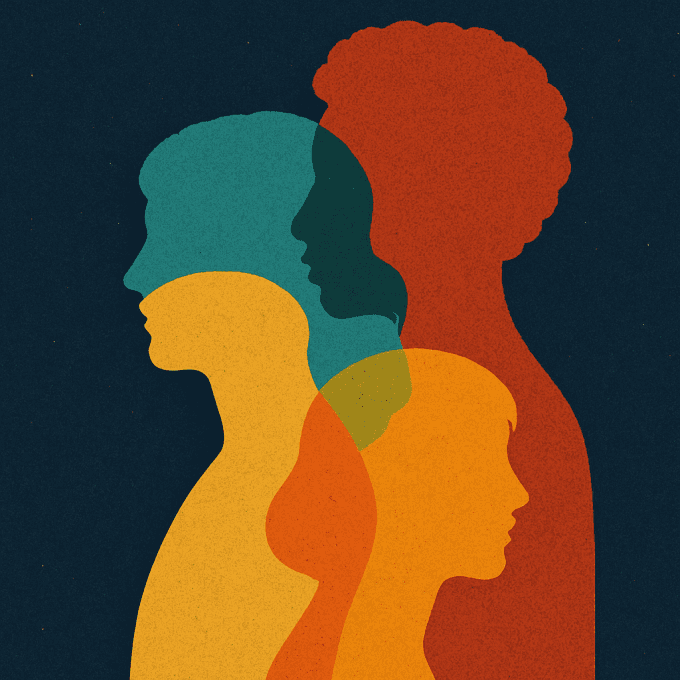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