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兔隐喻:大脑如何决定你的认知?
我们通过感知这扇窗户对世上万物形成认知,但这些认知像镜头一样,只聚焦在我们想看见的事情上。

1951年,普林斯顿帕尔默场上举行的足球秋季赛中,不败老虎队对阵达特茅斯队。老虎队有着明星后卫迪克·卡兹麦尔(Dick Kazmaier),他擅长传球、带球和踢悬空球,带领队伍以破纪录的分数击败达特茅斯赢得海斯曼奖杯。普林斯顿在点球赛中领先大绿队,但也为此付出代价——十来名球员负伤,卡兹麦尔的鼻梁也被打断,并有脑震荡(但还是象征地完成比赛)。“这场球赛踢得十分艰难,”《纽约时报》还算温和地报道,“两队都指责对方恶性踢球。”
这场比赛不仅出现在报纸的体育版,还登上《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杂志》。比赛后不久,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 和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采访了一群学生并给他们看了比赛视频。他们想知道:“你认为哪队先挑起了这场恶战?”
Nautilus | Science Connected
Nautilus is a different kind of science magazine. Our stories take you into the depths of science and spotlight its ripples in our lives and cultures.
学生都有自己偏爱的球队,因此给出的回答必定有所偏颇,这使研究者得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这些数据表明,人们不只是单纯地观看比赛。”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的比赛。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或许这就是“认知失调”之父里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所指出的:“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和解读会与他们已经相信的事物符合。”(译者注:即我们俗话说的“人们只会听他们想听的话,并且自动忽略所有与他们认知相悖的现象。”)
学生们在观看解读比赛录像时的表现,跟看到著名的“鸭兔图”(下图)时的孩子们类似。当给孩子们在复活节看这幅图时,更多的孩子看见兔子,而在其他日子他们更容易看到鸭子。[1]这幅图片本身就有两种解读,而且从一种切换到另一种得费点儿力气。

–当我把“鸭兔图”给我五岁的女儿看并问她看见了什么时,她回答:“一只鸭子。”当我问她有没有看见“其他东西”时,她额头皱起,往近靠了靠。“可能还有另一种小动物呢?”我提示道,尽量不把这搞得像重点高中的入学考试一样。突然,她灵光一闪,随即微笑道:“一只兔子!”
我不该为此感觉糟糕,艾莉森·戈普尼克(Allison Gopnik)及其同事的实验表明,3-5岁组的儿童里没人能自己看出”花瓶脸”图的两种形象。[2]另一组年纪稍大一些但仍算“稚嫩”的受试儿童中,有三分之一能成功辨别图案。其余大部分孩子能够在模糊的提示下辨别。有趣的是,那些自己辨别出两种图像的孩子,正好在进行“大脑理论”测试时表现更好,该理论检测精神状态随世界变化的能力(例如,给孩子们一个装着蜡烛的蜡笔盒,然后问他们觉得其他孩子会认为盒子里是什么)。
就算你不能一眼辨别出鸭兔图或是其他图形切换,也无需担心,研究中大量数据显示,一些被作者划为“应当有着强大表现力”的成年人也没能成功辨别。对“鸭兔图”也没有什么正解:虽然整体趋势略偏向兔子,但看见鸭子的人也不在少数。也尚未有研究证明这与惯用手有关。我的太太看到兔子,我看到鸭子,而我们都是左撇子。
虽然每个人在某些提示下都能最终看见鸭子又看见兔子,但却没人能一下子同时看见鸭子和兔子,无论你多努力。
–
–
我们是否也活在某种隐喻的鸭兔世界中?当我向东北大学跨学科情感研究所的所长丽萨·费德曼·巴瑞特(Lisa Feidman Barrett)如此提问时,她很快答道:“我甚至觉得这不是‘隐喻’。”她指出,大脑结构决定了这一切,因为神经元之间的固有连接较输入感官信息的连接要多得多。大脑在那副不完整的图片里填充细节,从模棱两可的感官信息中得出意义。(译者注:大脑将外部感官信息添加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决定外部感官信息的意思。)
她说大脑是一个“推理生成器”,描述了逐渐得到证实的“预测编码”假设,根据该假设,感知由我们大脑驱动,再由感官输入修改。不然,要接收的感官输入就太多了。“这不高效,”她说,“大脑必须找到别的工作方式。”所以它总是通过预测来完成。当“接收到的感官信息不符合预测时,你要么改变预测,要么改变你接收的信息。”
我们通过感知这扇窗户对世上万物形成认知,但这些认知像镜头一样,只聚焦在我们想看见的事情上。
研究者们在实验室里观察了感官输入与预测形成认知之间的连接。一份发布在《神经心理学》上的研究表明,当人被要求判断一份有关物体颜色的陈述是否为真命题时(例如香蕉是黄色),被激活的脑区和我们感知颜色时激活的区域相似。这就如同想象一根黄色香蕉和真正看见黄色并无二致——在唤起回忆时发生了某种再感知(虽然研究者也提醒“感知和知识呈现并不是同一种现象”)。

我们通过感知这扇窗户对世上万物形成认知,但这些认知像镜头一样,只聚焦在我们想看见的事情上。今年纽约大学心理实验室进行了一项实验,一组被试需要观看一段45秒的短视频。[4]短片讲述的是一位警官和一个未武装平民间的暴力事件。警官在尝试逮捕拒捕人员时是否行为不当还有待争论。
在观看视频前,实验对象们被问及对警察群体的认同度。被试的眼球活动被秘密监控,事后再被问及对罪责的看法。结果并不意外,对警察认同度低的群体提出了更重的刑罚。但这仅限于在观看期间时常注意警察的人们,那些并不时常看向警察的人作出的决定与对警察的认同度无关。
艾米丽·巴尔赛提(Emily Balcetis)是纽约大学社会感知行为与动机实验室的头儿,也是该研究的共同发起人。她告诉我,我们通常把决策看作是偏颇的核心。但“认知的哪一部分在进行这项重大的判断呢?”她提议注意力可以被看作“你允许你的眼睛看到的地方”。
在警察短片中,“你的眼动决定对案件事实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些更反对警察的人在看视频时,也花了更多时间在警察身上(根据兔鸭假设,他们不能同时关注警察和市民)。“如果你觉得他不跟你是一路人,你会多看几眼。你会看向你觉得会产生威胁的人。”巴尔赛提说。
但是什么左右着这项评估呢?没有标准答案。大量研究显示,人们看见群体中同族人的图片时会产生一种偏见神经信号。但如果现在告诉他们,图片里的人和他们分在同一个小组里,结果会怎样呢?你是在看一个跟你同组的人?亦或是一个不同种族的人?
“在最初的100毫秒左右,我们面前摆着的是兔鸭问题。”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杰·范·巴维尔(Jay Van Bavel)说。在范的试验中,小组性在那一瞬间压倒了种族性,获得了更多积极神经活动。(就像在兔鸭问题中,我们在某些时刻只能有一种解读一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某种意义上看,几乎所有事物都有多种解读”的世界,巴沃尔说。因此,我们永远在鸭兔之间进行抉择。
–
–
我们对自己的抉择深信不疑。在一份向鸭兔实验致敬的研究中,巴尔赛提和她的同事给实验对象展示了一系列描绘“海洋生物”或是“农畜”的图片。他们被要求辨别这些图片。每次辨别都会加分或减分。如果游戏结束时分数为正,则奖励果冻豆。分数为负?“局部解冻的罐头豆。”但每个实验者最后都会看到同一张图:马/海豹图(海豹要稍难辨别一些)。为了能拿到好豆,被试需要看出能让他们得分的图。他们大部分也做到了。但如果他们实际上看到了两种图但只汇报了能得分的那张呢?
研究人员又以新的对象进行了一次实验,这次他们加入了眼部追踪。那些需要看见农畜的人倾向于先看标记着“农畜”的方框(在点击后会出现下一张动物图片),反之亦然。对“正确”框(至少他们这么认为)的一瞥就像拿到自摸牌一样,揭示了他们在无意识计算下的意图。他们的视觉倾向于挑选有利图片。
但当实验假装发生了系统错误并告诉实验者,“啊,不好意思,其实是选海洋生物才能避免喝豆汁”时,绝大多数实验者都纠结在了已形成的感知里——哪怕现在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目标。“他们无法重新解读已经在脑内定性的图片,”巴尔赛提说,“一旦你试图搞清模棱两可的图片,那么它的双重性就已经消失了。”
我们的大脑也许潜意识记录了这种图片的模糊性,但决定不走漏风声。
卡拉菲德梅尔(Kara Federmeier)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显示,我们的记忆形成过程中也发生了相似的事情。[5]他们以某些对政治候选人有所误解的人为例,比如大多数人都以为“教育总统”是迈克尔·杜卡其而不是乔治·布什提出的一样。他们通过EEG研究实验者的大脑活动发现,人们对记错和记对的信息的“记忆信号”基本相同。他们把这种解读固化为真理。
这个固化过程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一篇发表在《儿科学》的研究中,超过1700名美国家长收到用于消除人们对MMR疫苗危害性误解的宣传材料。[6]据汇报,没有一份宣传材料能够让家长有注射疫苗的倾向。从最不愿接种的家长开始试验,宣传资料的确改变了他们认为MMR会导致自闭症的看法,但也使他们更拒绝接种。而给人们观看患有麻疹和腮腺炎的小孩的图片——这便是不接种疫苗的危害性——只会使人们更坚信疫苗有着危险的副作用。
这种固化如何产生,以及如何使人们改变思维和对兔鸭图的理解依旧未知。是什么让人们可以反转图像理解,这样的辩论一直存在且仍在继续。有种观点是,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也许是呈现给你鸭子画像的神经细胞累了,或者“饱足”了,导致兔子突然跃然纸上。也可能是和图像的绘画方式(鸭喙“弹出”)或是呈现方式有关。
另一个相反的观点是“自上而下”,大脑之上还有其他物质使我们倾向反转:我们已经得知了这种双重性,并且满怀期待地积极寻找它。被指示不逆转图形的人更难发现图片的反转,而催促人们快些发现会提升逆转率。[7]其他论点还包括混合模型,这种理论质疑是否有自上而下或与此相反的区分。[8]
德国弗莱堡的前沿领域心理学及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尤根·科恩梅尔(Jürgen Kornmeier)及其同事提出的混合模型质疑这种区分。据科恩梅尔描述,最先发生的眼部活动以及早期的视觉系统就反驳了“自上而下”说——而且信息流也绝无可能是单向的。他们认为即使人们自身没有发现兔和鸭,大脑也许在潜意识记录了这种图片的模糊性,但决定不走漏风声。依这种观点看来,大脑也参与了这次欺骗。你是那个唯一被蒙在鼓里的傻子。
仅靠提供给人们准确的信息不预示着政策讨论或其他争论可以得到解决。耶鲁大学的法律和心理学教授丹·可汗(Dan Kahan)提出,诸如气候变化的讨论中的两极分化,不是由于一方在理性分析,而另一方处于无知状态或坚持偏见而发生。[9]相反,是因为那些在测试中 “认知反思”和科学素养得分最高的人,更容易表现出被称作“意识形态驱动认知”的行为。他们花费最多的注意力去找他们已知的鸭子。
参考:
1. Brugger, P. & Brugger, S. The Easter Bunny in October: Is it disguised as a duck?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76, 577-578 (1993).
2. Mitroff, S.R., Sobel, D.M., & Gopnik, A. Reversing how to think about ambiguous figure reversals: Spontaneous alternating by uninformed observers. Perception35, 709-715 (2006).
3. Granot, Y., Balcetis, E., Schneider, K.E., Tyler, T.R. Justice is not blind: Visual attention exaggerates effect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legal punish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14).
4. Van Bavel, J.J., Packer, D.J., & Cunningham, W.A. The neural substrates of in-group bias. Psychological Science19, 1131-1139 (2008).
5. Coronel, J.C., Federmeier, K.D., & Gonsalves, B.D.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vidence suggesting voters remember political events that never happened.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 358-366 (2014).
6. Nyhan, B., Reifler, J., Richey, S. & Freed, G.L. Effective messages in vaccine promotion: A randomized trial. Pediatrics (2014). Retrieved from doi: 10.1542/peds.2013-2365
7. Kornmeier, J. & Bach, M. Ambiguous figures—what happens in the brain when perception changes but not the stimulus.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6 (2012). Retrieved from doi: 10.3389/fnhum.2012.00051
8. Kornmeier, J. & Bach, M. Object perception: When our brain is impressed but we do not notice it. Journal of Vision 9, 1-10 (2009).
9. Kahan, D.M. Ideology,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cognitive reflec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8, 407-424 (2013).
翻译:小铁 校对:罗杏红 编辑:EON
美国记者,作家,现居纽约布鲁克林,《连线》、《户外》和《艺术论坛》特约编辑,他写设计、技术、科学和文化等。最新著作《Traffic:Why We Drive the Way We Do (and What It Says About Us)》是《纽约时报》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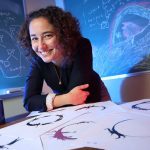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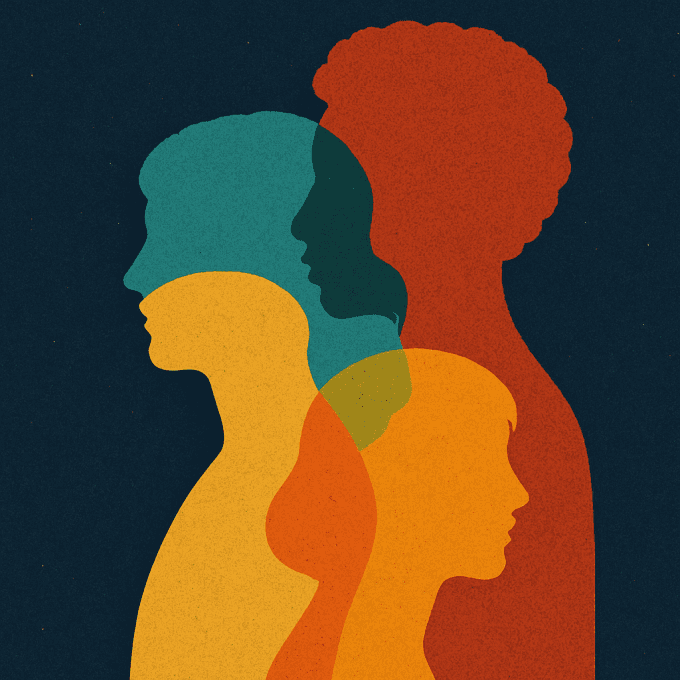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