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毒师》第四季开头有这样一幕: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愤怒地看着一个新手制毒师,他正仿制自己标志性的蓝色冰毒。沃尔特害怕被暴徒老板格斯除掉,于是拼命想让他相信,没有沃尔特就没有“产品”。当“业余毒师”维克多自称深谙所有步骤,沃尔特咆哮道:“行啊,那劳烦您提醒我,催化加氢反应要用质子性溶剂还是非质子性溶剂?我记不清了呢。如果还原反应不是立体特异的(stereospecific),我们的产品又怎么可能是对映体纯净的(enantiomerically pure)?”
科学知识救了沃尔特一命。维克多则被残忍的格斯用一把开箱刀割了喉。
随着《绝命毒师》剧情发展,沃尔特从一个窝囊的化学老师逐渐蜕变成了野蛮的罪犯。然而,无论他变得多么形容可怖,观众都忍不住对他报以同情与关爱。这种共情感很大一部归功于主演 布莱恩·克兰斯顿(Bryan Cranston)精湛的演技,他让一个忧虑重重的“居家男人”形象跃然屏上,而剩下的功劳则属于构思了这个角色的文斯·吉里根(Vince Gilligan),《绝命毒师》的创造者兼主编剧。在文斯的想象中,这个科学家的疯癫是本质的,而不是创造者强加的外部属性。

沃尔特讨喜的原因之一,是他懂科学。“文斯尽可能确保片中有关化学的内容准确无误,以增加可信度。”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化学教授唐娜·纳尔逊(Donna Nelson)说。作为《绝命毒师》的科学顾问,纳尔逊帮助吉里根达成了这一目标。(她最喜欢的场景是沃尔特对维克多尖刻而嘲讽的反驳。)虽然他们小心地避免让观众看到制作冰毒的准确、完整的“菜谱”,片中的化学反应是绝对真实的。如果你想要通过改变其他物质的结构来合成甲基安非他命(冰毒),你必须保证最终产物是对映体纯净的:甲基安非他命的三维结构在大脑中发生特定反应,你才会“嗨”,相同分子组成的对应映体(镜像)却没有用。
除了《绝命毒师》,近些年还诞生了许多以科学家为主人公的热剧,比如《西部世界》、《黑色孤儿》、《性爱大师》、《犯罪现场调查》、《识骨寻踪》、《豪斯医生》和《生活大爆炸》等,这些剧中的科学家性格复杂,形象多元,他们和我小时候看的那些80年代电影中的科学家有着天壤之别。那些在地下车库里捣鼓着古怪装置,让试管咕咕冒泡的孤僻天才,已经从荧幕上消失。如今,这些虚构的科研工作者在真实的实验室工作,使用高端仪器,而且,他们还有同事呢。他们的言谈总是夹杂着最新的科学词汇,他们的性格设定也富于深度,撑起了整个剧情。
一些传播学专家称,从电视节目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管窥现今科学家的形象和影响。虽然近些年的头版头条总是充斥着假借传播科学知识之名,兜售个人意识形态私货的家伙,调查显示民众对科学家还是极为尊敬的。现在的观众渴望并要求看到真实的科学家,而观众要什么,好莱坞就给什么。结果就是,荧幕上的科学家不再囿于刻板形象和反派设定,而更多地成为了可信且正面的角色。此外,科学家希望通过自身形象的传播促进科普工作,也促成了这一转变。
····
过去60年间,主要得益于医疗进步和技术发展,美国人对于科学的益处持愈发肯定的态度。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美国民众认为科学利大于弊。尽管人们从未停止担忧科学的风险和危害,但与被核恐慌支配的70年代及80年代初相比,现在的公众情绪已经大大缓和。据说,以美苏核战的余波为题材的《浩劫后》(The Day After),自1983年播出以来至今,一直是评价最高的电视电影。
198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教授乔治·葛伯纳(George Gerbner)对电视上的科学家角色及其文化影响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指出,科学家的形象有着聪明而理性的特点,但在荧幕呈现的各行各业当中,科学家们最不善交际;而且,1/6的科学家是反派。报告总结道,“只有当我们将科学家与医生等职业相对照,而非孤立考察时,才能发现他们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这种形象总带点邪恶、麻烦、危险的意味,仿佛预示会有坏事要发生。”这些角色显然对观众,尤其是每天看电视超过四小时的“重度观众”,施加了不良影响,让他们排斥甚至厌恶科学。
然而,这些邪气逼人、见佛杀佛的电视科学家似乎正逐渐销声匿迹。2011年,安东尼·葛伯纳(Anthony Dudo)及其同僚对等人研究的未尽之处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在《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发表了成果。经过比较2000年至2008年间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上各行各业的角色形象,他们发现只有3%的科学家以“坏人”面目示人,该比率低于其他任何职业。文章指出,不仅电视上的科学家非常正面,而且大量观看这些节目“有助改善那些有经历与剧情相似的人对科学的态度”。
怎么回事呢?新南威尔士州大学文学、媒体和表演艺术学院的副教授罗斯琳·海恩斯(Roslyn Haynes)通过研究虚构作品对科学家形象的描绘,发现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60年代;在那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脸谱化的科学怪人或滑稽的配角。现如今,人们有其他事情要担忧:政治腐败、恐怖主义、气候变暖……海恩斯说:“我们不再需要科学家扮演坏人了,因为现在满大街都是坏人。”现在,科学家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人。“我们知道科学家可以修补这个被我们糟蹋得满目疮痍的世界。假使尚有一线生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深谙危险并能设法克服它们的科学家。而过去,我们认为科学家本身就是危险。”
除了世道变迁,海恩斯认为人们对科学家的态度转变还与媒体对科学的大量报道有关。五六十年代前,极少数人见识过科学家。人们主要通过报纸和广播了解重大科学发现,偶尔有公开讲座或科学演示可供大众观摩。除非你自己是科学家,或者私下里认识一个,你这辈子都不太可能常常撞见他们。然而,电视改变了一切。
除了世道变迁,海恩斯认为人们对科学家的态度转变还与媒体对科学的大量报道有关。
二战后不久,英国的科学界人士渴望参与 BBC 科学节目的制作。伦敦大学学院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教员让-巴蒂斯·古永(Jean-Baptiste Gouyon)告诉我们:一开始BBC是拒绝的,直到一些制作人看到了“非专业听众”对科学的渴望,他们才回心转意。BBC大众科学系列纪录片《地平线》(Horizon)于1964年开播。根据当时的内部记录,这档节目旨在“提供一个平台,让那些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将他们的好奇、观察和反思广而告之,并将他们最前沿的宇宙观注入人们的常识。”
通过自然历史类节目展示科学,是 BBC 的另一大法宝。1979年至今,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曾主持多档节目,带领观众们踏上旅程,一同惊叹路遇的奇观。这些节目让八九十年代的大众对科学家的印象大大改观,就像海恩斯所说,“爱登堡可是国民祖父,你会怕你的祖父吗?”
卡尔·萨根(Carl Sagan)则是美国电视上的“科学之友”。他的节目《宇宙:一次私人漫游》(Cosmos: A Personal Voyage)于1980年播出,并一度成为美国公共电视史上观看人次最多的节目,直到被《南北战争》(The Civil War)超越。和爱登堡的节目一样,萨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对科学的惊叹和赞美展。他将“我们都是星尘”(we’re made of star stuff)铭刻在一代人心中,还发挥了前几年《太空竞赛》和《星球大战》等电影的余热,使得美国人对太空科学的激情愈发高涨。
科学纪录片从此成为电视台的常规节目,而近来它们对观众的吸引力甚至有增无减。古永说:“回顾《地平线》的历史,你会发现在90年代末到2001年前后,其呈现科学的方式有所转变。这档节目不再使用批判、调研式的口吻,而代之以对科学的歌颂。”
同时,这些节目中的科学家和主持人充满热情,平易近人,又富于探险精神;他们多数比较年轻,其中也有一些女性。“这些特质让人们觉得科学家是英雄,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海恩斯说,“他们和30年代科幻题材方兴未艾时的那些英雄不太一样——后者的故事往往惊世骇俗,点燃了一整个时代孩子们(主要是男孩子)的火箭科学梦——但前者也的确展现了科学家独具魅力、激人奋进的形象。”
····
顺应着这种新态度的潮流,荧屏上的虚拟科学家们很快迎头赶上。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的埃米特·布朗(Emmett Brown)博士发明疯狂的时光机的八年后,《侏罗纪公园》中的科学家们用远古生物震惊了游客。然而,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布朗博士滑稽古怪的形象在1985年仍是可以接受的,而1993年《侏罗纪公园》中的古生物学家们可要高级多了。他们的工作基于观众在现实中接触过的东西:恐龙、DNA、整洁的实验室和专业的记录本。虽然从困在琥珀中的蚊子身上提取恐龙血液中的存留的DNA这样的神操作并不切实际,但这种想法倒是在情理之中。就在这个月(本文发表于2016年12月),现实生活中的古生物学家在琥珀里发现了一块长羽毛的恐龙尾巴碎片,并在血液中检测到了铁元素的痕迹。
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传播副教授,2011年《好莱坞的实验室大褂》( Lab Coats in Hollywood)一书的作者大卫·柯比(David Kirby)指出,《侏罗纪公园》标志着电影领域中科学现实主义的开端。这部电影的视觉特效绝佳,而镜头中的科学细节都出自专家之手。票房大获成功后,其他影片纷纷效仿,着重进行现实主义的细节刻画。既然观众喜欢,何不如法炮制呢?
柯比还解释说,这其实是目前在所有电影类型中都愈发显著的“现实主义”潮流的一部分。“当我们谈论虚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在意的不只是角色佩戴的手表是否犯了年代错误,或者某项科学作业是否用对了仪器。现实主义应该是整体的,包括角色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身处的情境。”柯比认为电影制作人“巨细靡遗地实践着这种现实主义,以求向观众呈现宛若真实世界的感觉。”

柯比回忆起与《犯罪现场调查》和《识骨寻踪》等法医学题材电视剧的制片人的交流,他说:“他们经常说观众希望看到真实的东西;他们未必有证据来证明这点,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观众越来越精明了,从前那套滑稽古怪的科学画皮已经骗不过他们了。”
虽然2000年至2008年间电视网络展示了正面的科学家形象,观看这些节目却几乎无益于科学知识普及。
对于包含科学元素的电影,这就意味着以下两方面愈发重要:让片中的科学设定尽可能真实,以及让科学家角色像真正的科学家那样行动。
这股现实主之风也吹到了电视作品中。一部电影充其量也就几个小时,然而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可以每周播出,持续数年。《识骨寻踪》的粉丝已经陪伴着那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法医人类学家整整十二季了。《犯罪现场调查》的四个子剧集共800多集中,科学家们侦破的案件不计其数。《生活大爆炸》中的那些逗比带给观众的欢乐时光,也已经超过九年了。总而言之,虚拟科学家们在电视上亮相的时间要长得多。
也许较之于电影,电视节目面向更为多广闻博识的观众,于是肩负着更多责任感。《生活大爆炸》的科学顾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和天文学教授大卫·萨尔茨伯格(David Saltzberg)说:“你可以一边刷剧一边谷歌剧中内容。而且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介,电视剧的制作团队会收到海量的反馈。”
《生活大爆炸》剧组一开始就找到了萨尔茨伯格,从此他一直负责确保剧中的物理知识尽可能准确无误。每一集背景中白板上正儿八经的物理公式就是他的手笔,他还帮助编写台词中的科学讨论。“他们总是让我给一段故事情节点缀些科学元素。有时候他们只需要一个半秒钟说完的梗,或者一闪而过的镜头;有时候一整集内容都离不开科学。他们把故事主体部分写好后,我再想出五六个润色方案供他们选择。”
然而,这些“崭新”的荧幕科学家的教育意义并没有得到传播学者的肯定。根据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普罗大众的科学知识水平在过去二十年间并没有显著提升。2001年以来,美国人在九道基础科学知识题中平均只答对了5.8道。杜多等人的研究指出,虽然2000年至2008年间电视网络展示了正面的的科学家形象,观看这些节目却几乎无益于科学知识普及。
可是,这些节目的积极意义的确有迹可循。2011年,英国物理学会的一位代表告诉《卫报》,修读物理系课程的人数激增部分得益于《生活大爆炸》剧集的风靡。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犯罪现场调查》最火爆的时候,一些大学和学院不得不加设法医科学课程,以容纳那些梦想模仿剧集借助 DNA 证据破案的学生的雄心壮志。“《犯罪现场调查》效应”在电视剧停播后逐渐消失了,但这足以显示年轻观众如何受到电视节目影响。

乔恩·米勒(Jon Miller)作为密歇根大学科学素养提升国际中心的院长,在过去40年间一直关注着大众对科学的接受度。在一项始于1987年的时序研究中,他跟踪观察了一群七到十年级的学生,在他们成年进入职业生涯后依然持续。“电视往往是带领孩子通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米勒说,“在你生长的家庭、社区,可能无法接触到科学家和律师,你身边可能没几个人上过大学。”所以电视是“让年轻人了解未来从事各色职业之可能性的重要途径。”但米勒也告诫我们,对科学感兴趣不必然导致一番事业;成为法医学家或物理学家的学术之路是非常严苛而坎坷的,而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充足的准备。”
社会调查研究也证实了,在提升公众的科学知识与理解这方面,没有什么能取代学校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电视节目启发兴趣的功劳,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主义风格的科学家角色功不可没。
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真正的科学家们也要推波助澜。美国科学、工程和医药学院一直留意着影视作品中那些良莠不齐的科学家形象和科学元素,并最终于2008年开设了“科学与娱乐交流热线”,让制作人和编剧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与科学家交流。该组织的副执行主管安·莫查特(Ann Merchant)说:“我们左顾右盼——谁的号召力最强呢?谁最能点燃大众的热情和兴趣?好莱坞啊!”
沃尔特的蓝色冰毒产业也提醒了我们,虽然电视上的科学家们总体转向了英雄式的角色,此人是个凶犯这一点毋庸置疑。
科学家们说,他们之所以拨冗指导这些电视节目,是因为他们在乎自己的虚拟化身以何种面目示人。他们知道一档流行节目的受众,要比自己的最新论文不知道多到哪去了,而且他们希望观众了解真正的科学是怎样的,更别说,观众还可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当然,无论科学家多么乐意给他们的职业打广告,节目内容的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好莱坞或许意识到了观众喜欢现实主义胜过令人出戏的胡诌,但有时候科学事实的绝对精确必须让位于叙事。
在与《绝命毒师》的创作者吉里根沟通时,纳尔逊便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文斯问我,你觉得蓝色的冰毒怎么样?我只好回答,我反正不想吸蓝色的。”虽然纳尔逊从未亲自制毒,但她的化学知识告诉她冰毒应该是白色的,绝没有蓝色的。冰毒的任何原料或终产物都不会反射光谱的蓝色部分,所以如果你的冰毒是蓝色的,肯定掺了别的东西。吉里根没有听劝,纳尔逊则表示理解。“那是剧情需要,得体现出沃尔特·怀特的冰毒与众不同嘛。后来有人向我抱怨蓝色冰毒,你懂的,我只能告诉他们《绝命毒师》不是纪录片!”
沃尔特的蓝色冰毒产业也提醒了我们,虽然电视上的科学家们总体转向了英雄式的角色,此人是个凶犯这一点毋庸置疑。纳尔逊说:“我没听说过有那个科学家像他这样。”而另一方面,他和传统虚构作品中的坏蛋科学家也不一样。柯比描述他为“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罪犯”,还说:“把他推向邪恶深渊的不是科学。他最初是受了金钱的驱使而犯罪的,后来则是傲慢之故。”那些性格缺陷可以出现在任何人身上,而不是科学家特有的。——这不恰恰证明了,荧幕上的科学家们已经变成真实的人类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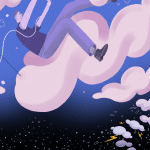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