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心智问题已被研究了上千年,但关于大脑的研究直到最近100年才开始,其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神经生物技术的重大革新。正如布伦纳(Sydney Brenner)所说:“科学的进步取决于新技术、新发现和新思想,科学的发展也可能遵循着这个顺序。”
看见:基于观察的神经生物学技术
最早的神经技术源于英国医生威利斯(Thomas Willis),他通过解剖大脑和相应的循环系统,于1664年详细绘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幅大脑解剖图。这象征着神经生物学的开端,Neurology一词也由此产生。
近200年后,1857年,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用高尔基染色法绘制出精细的神经细胞和大脑结构。在他的画中,大脑好比灌木丛生的森林,但其中的缠绕蜿蜒并没有让他迷失。他从中总结出了一套“神经元学说”,认为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一团无序的网络,而是由相互分开的独特的处理单元—神经元组成的。1906年,发明高尔基染色的科学家高尔基(Camillo Golgi)与卡哈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对揭示神经系统结构的贡献受到了瞩目,卡哈尔也被后世称为“神经生物学之父”。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卡哈尔笔下的神经元是通过简易的显微镜看见的。今天,这一技术已经发展成为多项神经生物学不可或缺的技术:最基本的光学显微镜能把物体放大1000倍,让我们看到细胞内部的结构;荧光显微镜能聚焦到特定的亚细胞结构中;电子显微镜理论上能把物体放大100万倍,甚至能看到神经元内部单个蛋白质。不过,显微镜的发展并没有理论上说得那么容易。光学显微镜面临的一大难关是1873年阿贝(Ernst Abbe)提出的理论限制—在光学显微镜中,我们无法观察到光波长1/2(约0.2微米)的物体。但获得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三位物理学家巧妙地绕开了这一理论限制,另辟蹊径地提出了受激发射损耗技术(STED)。2006年前后,超分辨荧光显微镜技术终于成熟并开始广泛应用。此后,“显微镜”变成了“纳米镜”,1纳米的小分子都能被这种高分辨显微镜捕捉到。超分辨率显微镜面临的另一个难关是如何与电子显微镜技术相关联。电子显微镜的问题在于,电镜的电子束能量很高,需将样品真空脱水,但对生物分子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杜博歇(Jacques Dubochet)、弗兰克(Joachim Frank)和亨德森(Richard Henderson)利用冷冻电镜技术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并因此于201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离1968年三维电镜重构技术诞生已经过去将近50年。
听见:基于记录的神经生物学技术
除了看见神经细胞,听到它们的活动更重要。1991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德国科学家尼赫(Erwin Neher)和萨克曼(Bert Sakmann),以表彰他们发明了革命性的膜片钳(Patch Clamp)技术让人类第一次“窃听”到了细胞表面离子通道里各个离子进出的电信号。这项技术的想法很简单:将一个极细的玻璃小管的一端紧紧连在细胞表面,如果幸运的话,玻璃小管正好包裹一个离子通道,细胞内外的离子就可流进小管,被另一端的电极检测到。有了膜片钳技术,我们就能了解不同的离子通道如何像门一样,通过开关来调控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并进一步了解离子通道在受精、心脏跳动、胰岛素分泌、肌肉收缩等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
膜片钳技术记录的是体外的细胞,要想记录活动状态下大脑内部的细胞,就得依靠单通道、多通道体内记录。体内的记录原理同样简单——将一个金属电极放在神经细胞旁边,神经细胞的放电活动就能被检测到。胡贝尔(David Hubel)和威塞尔(Torsten Wiesel)便是通过体内细胞记录技术,共同攻克了世界上最难解的大脑谜题之一:神经元如何编码大脑从眼睛获得的信息。他们也因此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体内和体外的细胞记录获得的是单个或少量细胞的信息,如果想听到大脑细胞群体协奏的“交响乐”,就需要更宏观的技术—脑电图(EEG)。最早的EEG要追溯到德国精神科医生伯杰(Hans Berger),他发明了将电极连接到头皮的装置,并于1924年在一个17岁男孩的神经手术中记录到了大脑信号。[1]如今,EEG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对癫痫、脑损伤、脑瘤、睡眠障碍的检测以及确认脑死亡等。与EEG类似的还有脑皮层电图(ECoG)技术,不同的是,ECoG的电极直接放在皮层外,信噪比更高,信息更丰富;而EEG的电极直接放在头皮上,优点是不会对大脑造成伤害。
除了基于电信号记录的神经生物学技术,另一类基于光学的记录技术——钙信号成像技术(Calcium imaging)发展迅猛。由于神经细胞内的钙信号与神经元放电直接相关,如果将钙成像和显微镜技术结合起来,科学家就可以同时看到成百上千个神经元的放电活动。自1980年钱永健(Roger Tisen)发表钙指示剂的论文后,[2]钙信号成像技术快速迭代,从基于化学原理的钙指示剂到基于基因编辑的钙指示剂,后者已广泛应用于各神经研究领域。[3]
最后,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在神经生物学记录技术领域独树一帜,也不得不提。PET和fMRI通过检测大脑的血流、耗氧量和血糖代谢动力学,可以准确地反映大脑的活动。1928年,富尔顿(John Fulton)报道了一个名叫沃尔特 · K(Walter K.)的病例。沃尔特的视皮层有血管畸形,他告诉医生,当他用眼睛看物体时,大脑背部感觉到的一个噪声就会增强。富尔顿发现这种增强只发生在大脑的视皮层,这是第一个证明视觉皮层的血流会对刺激产生增强反应的例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家凯蒂(Seymour S. Kety)和他的同事才第一次开发出定量研究人类大脑血流代谢的方法,这也是PET和fMRI
技术的早期基础。[4]
1991年,麻省总医院的罗森(B. R. Rosen)团队利用fMRI技术在不同视觉刺激下检测到7名被试大脑的血氧动态,标志着世界上首次通过fMRI观察到大脑活跃地图。如果将fMRI的大脑活跃地图和与MRI(磁共振成像)的大脑结构地图结合起来,科学家就能无创地精准定位人类某一脑区在进行认知任务时的活动情况。[5]从此,fMRI自成一派。科学家也因此发现了很多有特别功能的脑区,比如坎维舍(Nancy Kanwisher)发现了对人脸有反应的面孔识别区(Face Patch),她的得意门生萨克斯(Rebecca Saxe)发现了与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相关的右侧颞顶联合区(rTPJ)等。现在,MRI和PET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检查身体器官、骨骼以及肿瘤等。
遇见:基于调控的神经生物学技术
除了看见和听见,精确、定时定点地调控大脑的功能是神经科学家们多年以来的梦想,为此他们不惜采用电、化学物质或其他任何方法。早期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由于缺少调控技术,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通过某一脑区损伤的病例得到的。最有名的例子是铁路领班工人盖奇(Phineas P. Gage),在一次工作事故中,一根长1.1米、直径6.6毫米的夯铁棍从他的左脸颊插入,从颅顶出来。神奇的是他并没有当场死亡,但当伤口愈合后,医生和熟悉他的人都发现他的性格完全变了。他没有失忆,但智商有所下降,变得像小孩一样任性无常,对他人的意见不耐烦,并且满嘴脏话。当时盖奇的案例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直到10年后科学家费里尔(David Ferrier)对猴子进行的实验重现了盖奇的症状,学界才肯定了前额叶脑区对于注意力、性格和智力的重要作用。除了盖奇,还有癫痫患者H.M.为治疗癫痫被切掉双侧海马区,从而失去短期记忆的例子。这些病例为我们理解大脑的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脑损伤的病例很难重复,而且损伤的脑区一般不局限于一处,因此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大脑的功能仍有限制。
18世纪末,意大利科学家伽伐尼(Luigi Galvani)发现,如果用铜线和铁质解剖刀同时接触离体的青蛙腿,腿上的肌肉就会抽搐。这或许是最早用电调控神经的故事,伽伐尼之后,通过电刺激来调控神经反应成为主要的神经调控方法之一。1874年,美国医生巴索洛(Robert Bartholow)在病人拉弗蒂(Mary Rafffferty)脑中植入了一个刺激电极,并通过电刺激大脑直接引发她的肢体和身体活动。该研究第一次证明了大脑的躯体运动兴奋性。[6]100多年过去了,电刺激技术的安全性如今已有了极大提升,广泛应用于研究和临床领域。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脑深部刺激(DBS)被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其原理也是将电极植入大脑的某一区域中,通过产生一定频率的电流来调节大脑的异常活动。DBS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建立脑机接口来控制身体活动。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能解码来自大脑的编码信号,就能预测大脑在想什么,从而调控瘫痪病人的肢体活动,或者帮助失语患者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比如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的科学家在瘫痪病人科切瓦(William Kochevar)的大脑运动皮层和手臂上分别植入电极,通过读取大脑信号给手臂、手掌下达指令。现在科切瓦已经能通过意念控制自行吃饭、挠头。这是人类第一例通过大脑控制完成手部动作的壮举。近来马斯克(Elon Mask)成立的Neurolink公司给猴子植入脑机接口,让它们通过意念打乒乓球(Mindpong)游戏采用的也是类似的原理。当然,目前脑机接口技术还在实验研究阶段,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真正应用于临床治疗。
由于伦理和安全问题,目前在人体内完成的神经调控技术仍然屈指可数。但很多无法在人身上完成的技术,在动物身上却已轻松实现。科学家借此能够精准地控制大脑某一个位置的某一类细胞,从而产生特定的行为。这些技术包括基因克隆技术、光遗传学技术、化学调控等。
基因克隆技术并不起源于神经生物学。当1953年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自然》杂志发表跨时代论文,提出DNA双螺旋结构以后,分子生物学的时代就开启了。随着分子克隆技术不断进步,科学家终于能在动物大脑内改变某个基因的功能,筛选出会产生异常行为的基因并进行研究。比如本泽(Seymour Benzer)和科诺普卡(Ronald Konopka)通过基因突变的方法在果蝇中筛选出了与生物节律相关的基因,与该基因相关的研究也获得了201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年来,科学家又发明了被称为“分子剪刀”的CRISPR/Cas基因编辑技术。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和卡彭特(Emmanuelle Charpentier)也因在基因编辑技术上的突出贡献,获得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有了这些基因操作工具,我们不仅能够通过突变基因来了解特定基因对大脑的作用,还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复遗传疾病(如孤独症、早发性老年痴呆症、精神分裂症等)中突变的基因。
如果说分子生物学技术并非脱胎于神经生物学,那光遗传学技术则是一项神经生物学沃土上“土生土长”的革命性技术。人类的眼睛是一个光信号—生物信号的光电转换系统,但人眼系统很复杂,需要十几个蛋白共同协作,而光遗传学只需要一个光敏蛋白ChR2—ChR2吸收光子以后发生构象变化,打开细胞表面的离子通道,从而让细胞兴奋。除了ChR2,类似的还有让细胞抑制的光敏蛋白嗜盐菌紫质(NpHR),结合定点定位的基因克隆技术,就可以做到定时定点调控神经活性。2002年,米森伯克(Gero Miesenbock)把其中一种光敏感蛋白表达在果蝇的肌肉细胞上,再把果蝇的头砍去,当光打在果蝇身体上时,无头果蝇竟拍起了翅膀!三年后,斯坦福大学博士刚毕业的博伊登(Ed Boyden)与戴瑟罗斯(Karl Deisseroth)实验室的张锋等人合作,首次发表了将光敏感蛋白表达于哺乳动物细胞的论文,揭示了光遗传时代的来临。[7]光遗传技术有准确的时效性,并且可操作性强,如果与显微镜成像系统结合,就能为了解神经系统的活动机制提供非常有力的武器。当然,光遗传作为侵入性的技术在人体上的实验,目前仅限于局部脑区相关疾病的治疗,比如2015年美国FDA批准了光遗传治疗失明的临床试验。
化学调控也是调控神经元的主要方式之一。早期科学家在自然界的动植物中找到了很多天然的神经毒素,比如河豚毒素可用于抑制神经放电等。此外,结合基因克隆技术的化学遗传学技术DREADDs,可通过药物达到类似光遗传技术的抑制或兴奋神经元的目的。由于不需要植入光纤,DREADDs技术在基因治疗方向有着巨大的潜力。
可以说,神经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诺贝尔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奖史。它推动着我们对大脑的理解深入,也使得我们离最终目的——治疗疾病,造福人类,并且了解我们何以为人这一终极问题——不再遥远。技术爆炸的当下已然是神经生物学最好的时代,它的前方会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见证。
参考文献
[1] INCE R, ADANIR S S, SEVMEZ F. The Inventor of 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 : Hans Berger (1873—1941) [J]. Child’s Nervous System, 2021, 37(9) :2723-2724.
[2] TSIEN R Y. New Calcium Indicators and Buffers with High Selectivity Against Magnesium and Protons: Design,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Prototype Structures[J]. Biochemistry, 1980, 19(11) : 2396-2404.
[3] ZHOU X, BELAVEK K J, MILLER E W. Origins of Ca2+ Imaging with Fluorescent Indicators[J]. Biochemistry, 2021, 60(46) : 3547-3554.
[4] RAICHLE M E.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 Brain Mapping[J].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2009, 32(2) : 118-126.
[5] BELLIVEAU J W, KENNEDY D N, MCKINSTRY R C, et al. Functional Mapping of the Human Visual Cortex b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J]. Science, 1991, 254(5032) : 716-719.
[6] HARRIS L J, ALMERIGI J B. Probing the Human Brain with Stimulating Electrodes: the Story of Roberts Bartholow’s (1874) Experiment on Mary Rafferty[J]. Brain and Cognition, 2009, 70(1) : 92-115.
[7] BOYDEN E S, ZHANG F, BAMBERG E. NAGEL G, DEISSEROTH K. Millisecond-timescale, Genetically Targeted Optical Control of Neural Activity[J]. Nature Neurosci, 2005, 10: 1263-1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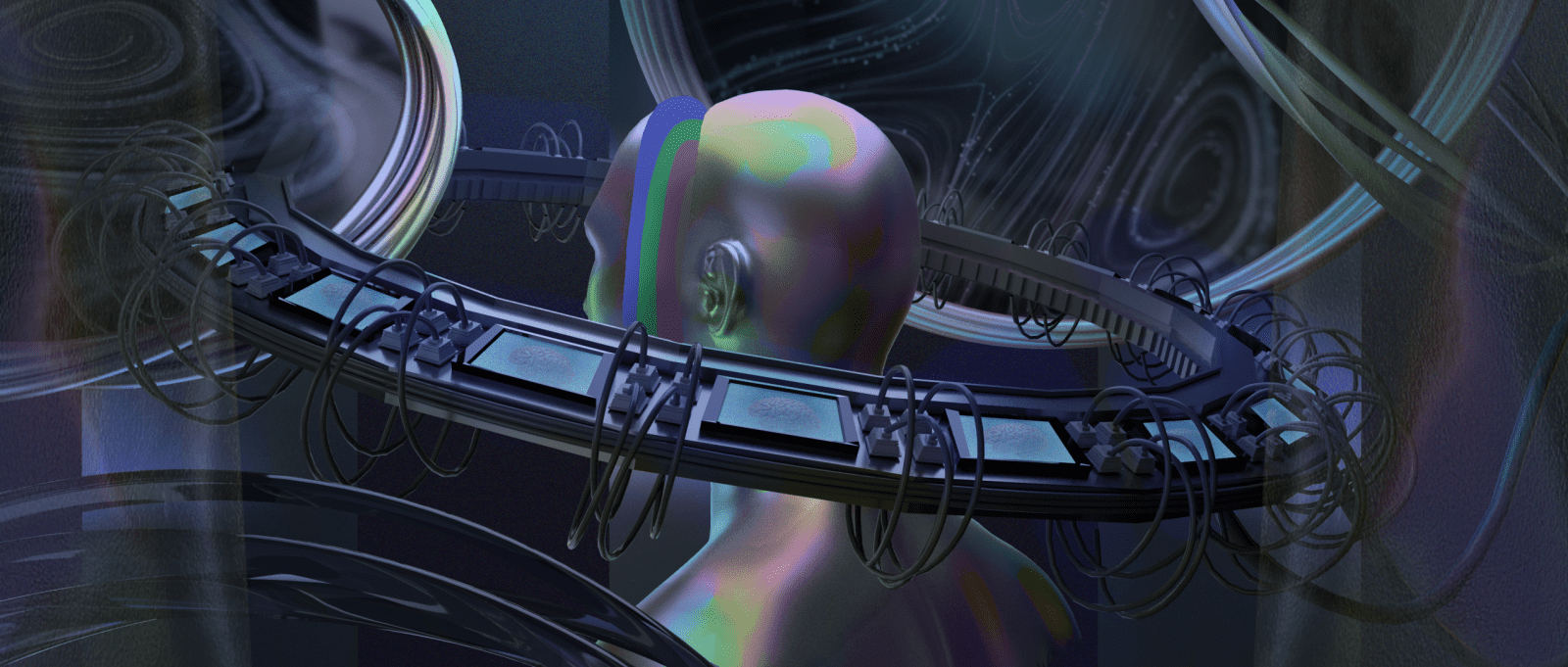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