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问题上,心理学家应该闭嘴吗?
想要维护实然或应然纯粹性的希望注定破灭;当道德心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呈现他们的本事时,实然和应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

心理学和人类道德是否相关?这个问题最近(又再次)流行了起来。表面上看,这点似乎没什么值得讨论的——“我们实际如何”与“我们应当如何”之间,难道会没有关系吗?但事实上,这一问题长盛不衰,道德哲学家们对其已经探讨了几个世纪之久。
因此,我们带着一种讨厌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开始了毫无新意的讨论。但前些年,塔姆辛·肖(Tamsin Shaw)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纽约书评》网站上的观点交锋,迫使我们以现代眼光重新思考这一古老的观念,即认为人类心理并非对道德毫无意义,只不过心理学家关于道德的论述对道德本身无关紧要罢了。
通常,对于这种观点的支持更多是来自影射,而非论证。心理学界被指陷入了危机:心理学家在实验中同谋犯案,践踏人权!编造数据,学术不端!心理学实验更是无法重复,结论不可靠!
是,是,是。有的心理学家愿意干些道德上可疑的活儿;有些心理学家学术造假;有些心理学实验无法重复。注意是“有些”。但这些以偏概全的推论,往好了说站不住脚,往坏了说则是满怀恶意。心理学界良莠不齐,正如其他事物也都有好坏之分,一笔抹煞并不能帮助我们做出区分。
若仅仅因为,在美国心理学会这个一个庞大且多样的专业协会中,有一两个人参与了小布什任内的刑求项目,而全盘否认所有心理学家的成果,那和因为一些纳粹分子着迷尼采学说而无视尼采学者的所有文章,又有什么差别呢?毫无疑问,不是每个学科领域,每个知识分子,都能称得上是文化上的宝藏。他们中的有些人凭什么能称为宝藏,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通过含沙射影或者论战攻击来找到严肃的答案。
是否还有其他更为实质性的理由,将心理科学排除在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呢?最有力(尽管未必成功)的反对意见是以“规范性”的语言展开的。对哲学家而言,规范性陈述就是立规矩,分黑白:与之相对的是描述性陈述,仅仅想要说明世界是怎样的。规范性陈述则是说,我们对世上的事情我们应当怎么做。而有些哲学家所论证说,这两种陈述之间永远不会有交集。
尽管哲学家们尚未在类律归纳(lawlike generalisation)*的引证上取得令人惊羡的突破,但休谟法则(Hume’s Law)可谓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成就。休谟法则禁止人们随意从描述性陈述推导出规范性陈述。正如我们常说的:“实然并不蕴涵应然。”(is doesn’t imply ought.)
*译者注:类律归纳是指,该假设能够通过对相关实例的归纳得到证实,这类假设也被称为“类律假设”,例如“铜能导电”。与之相对的是“偶适假设”(accidental hypotheses),例如“这个房间里有人是独生子”。
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休谟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实然和应然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推论的壁垒”,以至于从描述性到规范性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逻辑蕴涵关系。与此同时,道德哲学作为最常出现规范性陈述的哲学子领域,却经常充斥着描述性的主张;在许多粗制滥造的期刊和大学出版物中,道德论证的根据往往是关于对人类和世界的经验观察。
哲学家对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法则视而不见,如此频繁而无忧无虑地乘风破浪,这似乎有些令人惊讶;但我们怀疑,这对于那些未经休谟“荼毒”的路人来说可能尤为意外。在讨论开始之前(甚至之后),是否会有人认为应当对大型烟草公司采取的措施,与吸烟对健康和死亡率的实际影响完全无关?道德哲学是一个棘手的领域,它很少(如果有的话)在演绎上达到无懈可击:实然并不蕴涵应然,但是关于人类如何思考和行动才是最合理的,其答案却处处离不开那些思考和行动实际所处的环境和心理。

一些道德哲学家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哲学只应从事某种“理想的”理论)。自古典时期起源之后,道德哲学便一直坚持“实然”与“应然”的两分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例如上述“实然”与“应然”并非完全泾渭分明的观点,很可能遭到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而除了道德哲学的研究通常是如何展开的,更重要的是,道德哲学的研究应当如何进行: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中的最佳理论,可能是事实和价值混合的产物。事实上,这一假设也可以在道德哲学领域的经典论断中找到依据,即“应然蕴涵能够”(ought implies can)。这个论断通常被认为是康德提出的,它的意思是:认为一个婴儿应该(ought to)在饥饿的时候忍住不哭,这不合情也不合理,因为我们并不能合理地期待婴儿能够(can)做到这点本身。
在建立道德理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事实,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得出结论,认为道德哲学所关注的所有事实都源自心理科学上的发现。这一观点的确立,首先必须厘清科学事实是什么,以及理解这些事实如何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的建立。也就是说,需要在哲学和心理学两边进行详细的讨论,而这一跨学科的努力目前已积累了大量文献。尽管这一方法论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心理科学能够为伦理学思想提供信息,但他们并不主张心理科学能够取代伦理学思想(这点可能是不言而喻的)。更不太会有人认为,心理学家应当被奉为“道德专家”,而我们其他人也应当对其“顶礼膜拜”(顺便一提,我们从未听到我们认识的心理学家表达过这种愿望)。他们的信念很简单,确信对人类心理的科学研究能够丰富对人类道德的探讨。
考虑一下心理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这种观点认为,所有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出于我们自身的个人利益。相反,心理利他主义(psychological altruism)认为,某些人类行为的最终动机是为了他人的幸福。在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为利己主义提供的论证被许多人认为是极具说服力的,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有两位伟大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社会变革者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们确信享乐主义才是对人类动机的正确解释,其作为利己主义的一个翻版,认为人类只有两个最终目的——体验快乐、避免痛苦。
但是,当然,功利主义者也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成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而,根据功利主义者的心理理论,其规范性理论常常要求人们以似乎不太可行的方式行事。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在密尔的回答中有提到,我们应当着手开展严酷的社会工程,通过灌输对于“宇宙之主”的不满的恐惧,来约束人们对于功利主义道德的实践(尽管密尔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译者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功利主义的理论需要提供能够规范人们去做出利他行为的理由。密尔认为我们应该强化这样一种情形:每个人出于害怕不被“造物主/宇宙的主宰者”青睐而做出利他的行动。

如果利己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功利主义者(也包括康德主义者和其他学派)的规范性图景将大为不同。但真的是这样吗?自霍布斯以来的四百年间,哲学家借由轶事、直观和先验论证来争辩这一问题,但几乎无人信服。接着,大约40年前,实验社会心理学家转而投身于心理利己主义和心理利他主义之间的争论。这是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如何使设计的实验能够为心理利他主义或利己主义提供有力的证据,这是个充满挑战的课题。然而,时至今日已经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相关的精彩讨论可参见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的Altruism in Humans一书。这些讨论表明,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心理利己主义者们是错误的。人类具有纯粹的利他动机,而社会干预可以激励这种利他行为,也可以造成阻碍。你也不得不同意,这些大量的实证研究无疑在规范性理论的建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近的一个论述来自约翰·米哈伊尔(John Mikhail)的重要著作Elements of Moral Cognition。米哈伊尔是一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和人权法领域的法学教授,并在十余年间专注于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早期的开创性研究中提出的道德悖论。在格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中,他通过脑成像技术来研究道德推理,并提出了各种道德困境中的道德推理。由此,米哈伊尔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但又充满争议的论点论据:所有正常人类共享一套重要的内在道德原则。然后,基于约翰·罗尔斯那个影响深远的解释,即关于道德原则在何时是被辩护的。米哈伊尔认为,如果存在一种泛文化的内在道德原则,那么在罗尔斯关于“证成”的阐释下的证成(justification)策略下,那些道德原则是被辩护的。*
*译者注:作者没有明确说是哪个“罗尔斯的影响广泛的解释”,校对推测是指“反思平衡的方法”(the method of reflective equilibrium),这是一个非常符合直觉的(也很“归纳的”)方法。简单来说,一个原则可以通过“它具有的解释我们最有信心的那些判断的能力”被辩护。
米哈伊尔的结论是,对于二战结束以来作为国际法核心的普遍人权原则,他的解释为其提供了亟需的知识基础。那么他是正确的吗?不出所料,大家各执己见。但如果仅仅因为米哈伊尔的成果依赖于心理实验,就认为他的研究不应被视为关于人权的规范性理论,那也过于武断了。

科学研究为公共政策提供支持的另一案例,是在厌恶心理的领域。前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里昂·卡斯(Leon Kass) 在其著名论文The Wisdom of Repugnance(1997)中提出:“在重要的情况下,厌恶是深层智慧通过情感的表达,这是理性的力量所无法充分表达的。”简单来讲,在卡斯看来,厌恶是一种道德感觉,它可以在哪怕是缺乏依据的情况下,识别有违道德的行为:人们可以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即使他们无法理性地阐明这些东西不对在哪里。值得注意的是,有其他人也通过类似的论证,来为他们对同性恋的谴责和对同性婚姻的反对进行辩护,当然我们无意将这些观点归咎于卡斯。
最近的实证研究就厌恶的智慧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在丹尼尔·凯利(Daniel Kelly)的著作Yuck!中,对30年来针对厌恶的心理学研究进行了细致的综述,认为当代人类的厌恶反应源于两种不同机制的融合:一种是用来辨别有毒的食物,另一种则是用来识别寄生虫传播的渠道,包括微生物和病原体。
凯利认为,这种对隐含中毒或污染风险之迹象所采取的保护性反应,其实与其他方面的心理活动形成合力,其中就包括道德判断心理。然而,厌恶仍然可以由社会习得的中毒污染迹象所引发:这些本能(visceral)暗示的影响,使得厌恶心理扭曲了道德判断,导致我们将文化中认为“恶心”的事物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事物混为一谈。再一次,我们仍无法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点,即基于心理学的理论不应在规范性思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论结论如何,是否存在可信的论证,能够排除一些考虑因素,像是凯利在争辩“厌恶的智慧”时所提出的那些?
除了阐明现存的道德问题,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也能使我们发现新的道德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所有人都有着各种各样令人惊讶的内隐(或者说无意识的)的偏见。而许多人,包括那些致力于种族平等的人,也可能会有偏见的念头,比如将黑人面孔与消极词汇联系在一起,将白人面孔与积极词汇相联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内隐偏见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尽管我们常常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道德哲学家长久关注的一个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人们理应对他们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而这方面探讨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是,无知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如果这些倾向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那么我们是否对这些受内隐偏见影响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这个问题已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果不去参考心理学家得出的实证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也不可能负责地提出这个问题。

除了仔细研究心理科学之外,也许大多数当代道德哲学家的第一要务,是探讨道德方面的品格与德性,正如我们建议他们所应当做的那样。伦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良好的品格是持久抵御恶行的坚固堡垒,也是善行的可靠来源。人们很容易认为,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会太残忍,即使受到了干扰或挑衅,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个人代价,他们也会表现出适当的善意。问题是,许多心理学表明,有悖道德的行为是极易引发的,最著名也是经常被重复的例子,便是米尔格拉姆实验:极为轻微的情境压力,也可能让一个正直的普通人做出不那么正派(甚至骇人听闻)的事情。这种心理学使得像我们这样的“品格怀疑论者”开始质疑道德思想中为品格保留的特权地位,无论是学术哲学中的“德性伦理学”传统,还是通俗政治文章中关于品格的许多探讨(这些文章呼吁人们为品格高尚之人投票)。
我们也愿意承认,并非一定要接受这种怀疑论。恰恰相反,这种思想是极受争议的:目前已经有大量文献围绕此问题展开了激烈论辩。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如果道德哲学家严格禁止对所有心理科学的接纳,那么这些属于规范性伦理学领域,或与之相关的文献也就不可能出现。可以说,关于道德品格的哲学探讨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蓬勃发展。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因为人们普遍愿意认真对待心理科学。
想要维护“实然”或“应然”纯粹性的希望注定会破灭;当道德心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呈现他们的本事时,实然和应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正如在我们举出的几个例子(以及其他许多例子)中所展现的那样,忽略实然——尤其是实证心理学所揭示的实然——往往会导致关于应然的灾难性理论。
我们确信,心理学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好。同样我们可以肯定,哲学亦是如此。想要做到这点,去固化的学科界限是没有用的,学科划分不过是出于管理之便,关键是以包容心态仔细思考,取各学科之所长。

后记
三木:这篇文章解答了一个我非常好奇的问题:实然和应然这两个范畴,在现实生活中具体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就我受到的哲学训练而言,更侧重于强调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如何不同,应当在哲学分析中尽量避免混淆,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似乎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规范性问题从来不是一个高悬于云端的飘渺之物,不仅在于它对生活有着某种指导性的作用,而且随着生活经历的不断更新,我也在不断修正许多价值观念。可是这种修正过程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我却一直没有去好好地厘清,有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感觉。我想这篇文章给出的一些实例,确实回答了我的(或许也是一部分读者的)疑问。
阿歪:你去参加了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的效用”的研究,你担任的是老师的角色。学生在你的隔壁房间,你们只能通过声音交流。实验者告诉你,如果你的学生答错了,你可以对他施以电击,电压可以被设置在75V到450V之间。实验中,当电压达到120V的时候,你的学生开始尖叫、敲打墙壁,说他想退出实验。而你也开始萌生退意,但实验者坚持让你继续,你会怎么做呢?
上述实验就是本文提到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担任教师角色的被试不知道的是,隔壁房间的学生并没有真的受到电击。而这个实验有着令人错愕的结果,62.5%的被试都实行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
米尔格拉姆实验为我们思考本文涉及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垫脚石。阿道夫·艾希曼,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军官,在耶路撒冷审判中为自己申辩:他只是单纯服从了法律和上级的命令,他从来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
米尔格拉姆在1961年,使用这个心理学实验来回应和审视这个沉重且艰深的关于人性和道德的命题。我们会发现,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东西,和艾希曼的审判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一样,止步于事实。刻画具体的事实是当代科学心理学的学科规范,是心理学建立其科学性的方式。但是一个事实会敞开无数种解释,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目的出发,我们从一个或一系列事实中会给出无数种不同的对“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的答案。
从事实跨向解释的这一步,往往就是从心理学跨向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这一步。做现代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局限在一篇论文的一亩三分地;但当我们对一个问题进行思考,思考本身是无限广袤的,它的每一步不受限于所谓的学科边界。读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也一样迈一步就到米尔格拉姆实验在耶鲁大学。
作者:John M. Doris, Edouard Machery, Stephen Stich | 译者:三木 | 审校:陈小树、阿歪 | 封面:Andreea Moise | 排版:光影 | 原文:https://www.philosophersmag.com/essays/153-can-psychologists-tell-us-anything-about-phil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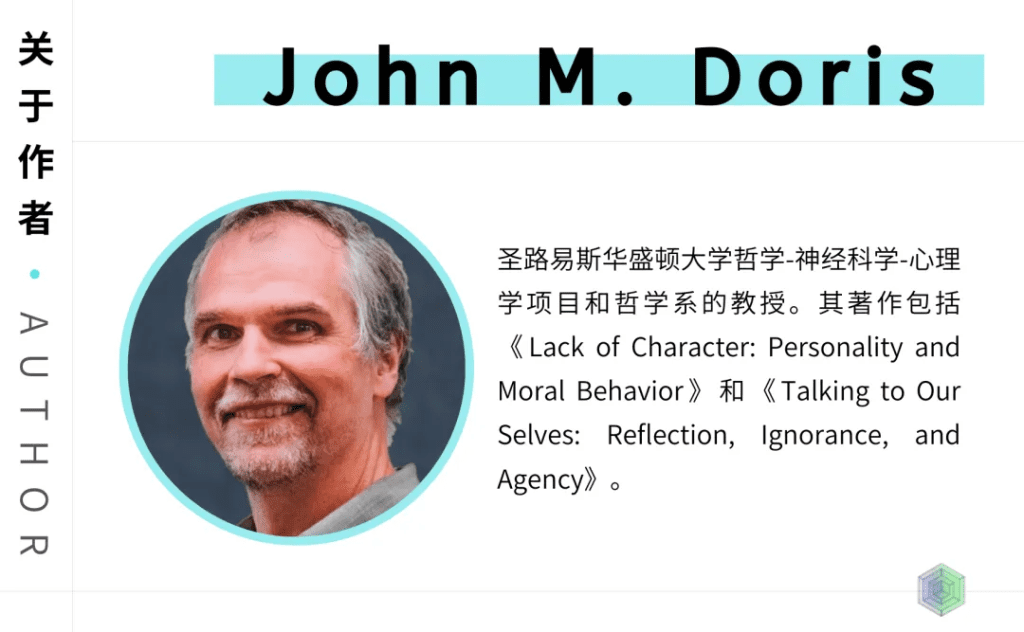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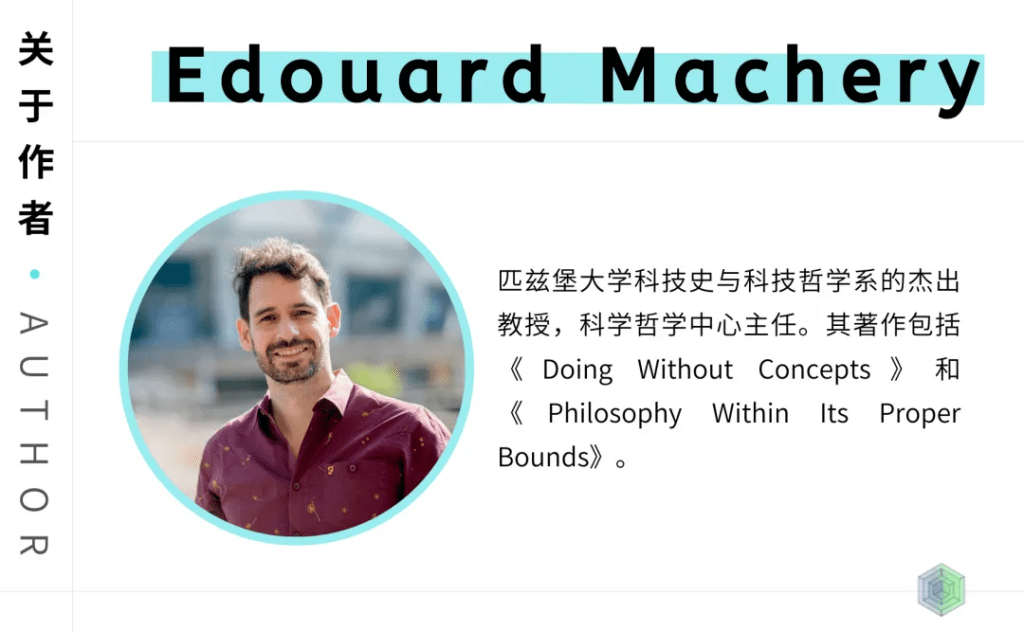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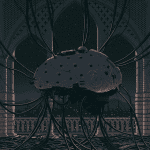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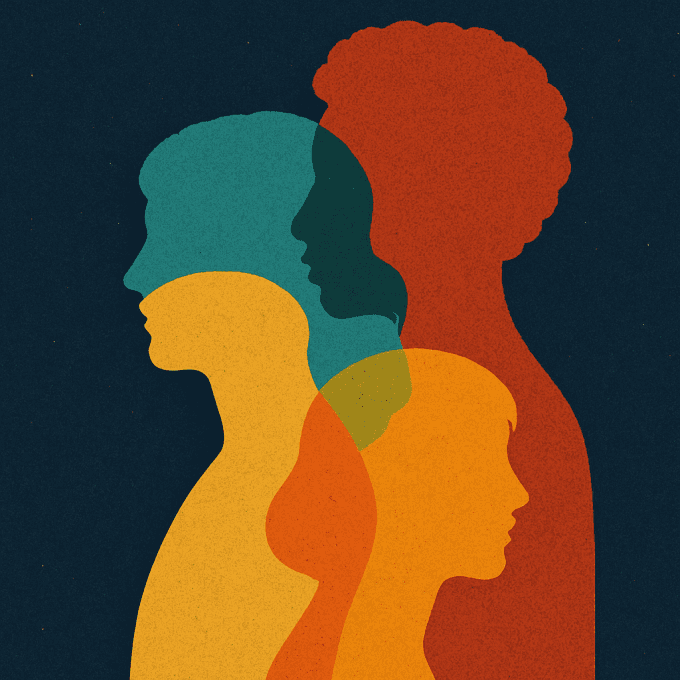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