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早期,第一次收到“待在家中”命令,我对那天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前一刻还想着这像一个不用出门工作的下雪天,下一刻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作为一个本质上十分外向的人,一个不愿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的人,这样的转变其实是相当艰难的。但是你知道吗?我竟渐渐对此习以为常。尽管疫情无疑对一些人生活的影响比对另一些人更大,但它的确以我们永远难以遗忘的方式对我们每个人都产生了影响。两年之后的现在,我想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与疫情之初有了很大不同。
因为这正是我们的大脑运作的方式。大脑被我们的经验塑造,因而我们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即便是那些不那么好的情境。
这实际上是我们大脑最为人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根据当代一些人类演化的观点,我们的祖先经历了一场“认知革命”,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适应环境。有证据表明,在不稳定的极端天气过后,我们祖先大脑的尺寸也有所增大。我们的大脑拥有非凡的灵活性,对此一种颇受欢迎的解释是,那些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原始人类无法存活。换句话说,现代人的大脑是凭借学习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被挑选出来的。
然而,这种非凡的灵活性的主要代价之一是,人类生来就对事物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如果你与某人谈论一件你们共同参与的事件,由于二人讲述的故事差别实在太大,以至于你可能觉得你们中的一个人在妄想。如此一来,你便会明白你的经验如何塑造了你对周遭世界的理解。这一点让人极其沮丧,因为我们一直坚信大脑给我们构建的个人现实世界。还记得那条蓝黑白金裙吗?尽管当某人对现实的看法与你截然不同时,听起来像是一种“煤气灯操纵”。然而,你们对现实不同版本的陈述完全可能是共存的。归根结底,人们记住一个故事的方式反映了人们经历原始事件的方式之间的差异。对这一现象的科学解释被归结为视角差异(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
经验塑造大脑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是赫布型学习(Hebbian learning)。从本质上讲,赫布型学习是一种生物学机制,允许大脑保存关于环境中特定事情发生频率的数据集。这与运动团队保存运动员的统计信息类似,这些信息会在决定谁去首发、谁被交换时使用。你的大脑能够“计算”不同类型事件的发生频率,并在接收的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使用这个系统弄清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什么。
幸运的是,你的大脑获取数据的方式并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计算。与此相反,这一工作发生于神经元交头接耳的联结中——在这里神经元们会决定谁与谁交流,以及以多大的声音交流。时机对于组织这样的交流而言至关重要,事实证明,这对于学习来说也十分重要。当两个近在咫尺的神经元几乎同时被激活,它们之间的联结会变强,从而提高了其中一个神经元的信息被另一个神经元获取的可能性。尽管赫布型学习的实际法则比这更加微妙,但我始终记得我在本科习得的顺耳易记的口诀:“若共同发放,则携手相连*”。共同发放得越频繁,神经元之间的联结会变得越强。这就是大脑融会贯通的方式。大脑的这一运作方式表明,如果事件A和事件B实际上总是同时发生,它们就是相同“神经事件”的一部分。一旦这样的事件发生,即便你的大脑只获得A即将在世界中发生的证据,它依然可能假设B也会发生,并为你创造相应的体验。
*译者注:赫布定律(Hebb’s rule),一般表述为“同时激发的神经元,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会随之增强(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目前的翻译参考自顾金涛译作《我们如何看见,又如何思考》(原作名 We Know It When We See It)。
在你的观念逐渐形成时,什么可以“算作”一个经验呢?简单来说,你从所有的神经经验中学习。从大脑的视角出发,在神经元间流动的信号来自于何处都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你在外部世界看到的某些事物,或是一个白日梦般的幻想,还是一个关于自己潜在未来的自由联想。每一个与之相应的“脑电风暴”都会塑造你大脑数据库的景观。
一种所有人都有的经验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它被认为对我们的心智和大脑有普遍影响。这是因为语言对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十分重要,以至于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使用语言。
如果你只会一种语言,或者你的第二语言知识十分有限,又或者你习得第二语言的时间较晚(例如青春期之后),相较于拥有多种语言经验的情况,你的大脑更容易局限在母语中。这样的好处是,相比于那些学习多种语言的大脑,你的大脑会更好地为使用单一语言做准备。大致来讲,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在使用统计数据来理解或产生一种语言时,有更多的备选项需要考虑。在使用特定的语言之前,他们需要消除不同语言之间的竞争。这意味着即使是他们最精通的语言,他们也会花费几分之一秒的时间才能通达需要使用的语言信息。
广泛地接触不同类型的数据也有益处。学习多种语言的人不仅有更丰富的行动可供选择,并且他们在决定如何行动时也可能考虑到更多的信息,例如哪种语言最适合当前的语境。但是考虑各种情况,以“自然”的方式来应对,其代价肯定会更大。但简而言之,拥有一个有着多种经验的大脑会减慢在特定环境或情境中作出回应的速度,但它也使得一个人为更多情况做好准备。
我们都知道,在孩童时期学习一门语言比成年之后容易很多。这一现象不禁让我们好奇:在生命的早期有多少学习在发生,在之后的生命中又有多少可以为适应环境而发生变化?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大脑的不同部分的发展适应有着不同的特定时期。基于对经验的开放程度和持续时间,可以简单地将大脑区域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几乎全是由负责调控和维持生命的功能区域组成,与经验无关。这些区域是调节呼吸、心率和体温的核心功能区,在不同的环境中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此外,我们还有期待经验的脑区。这些区域的任务是学习解释关于外部世界的特定类型的信息,因为它们生来就是为了接收来自感官的信息。例如,在正常发育的婴儿身上,通过眼睛抵达的光线会传送到大脑后部的枕叶皮层,通过耳朵传导的声音传送到位于大脑两侧颞叶的听觉皮层,通过鼻子获得的气味信息会被位于大脑前底部的嗅球处理。事实是,我们需要学习辨认我们看到、听到和闻到的东西,这些信息使得人类婴儿在出生的环境中发展出专门知识。
然而,许多期待经验的脑区也有接收刺激输入的“关键期”。在生命的初期,它们只是等待着数据输入,并且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可塑性。但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这些区域积聚了关于周围世界的大量信息,它们处理它们所期待的事物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受到外部世界的新经验的影响越来越小。
幸运的是,某些大脑区域在我们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可塑性。这些便是依赖经验的脑区。其中大多是皮层“联合”区,包括我们在一生中习得新词汇的区域。依赖经验的最核心脑区之一位于额叶,它支持着人类适应性特征中表现出灵活性的行为。基底核也依赖于经验。事实上,它们常常被视为最具适应性的脑区,因为它们包含丰富的多巴胺交流信号,能够增强神经可塑性。这对大脑的决策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幸的是,这些依赖经验的区域也会将我们引进死胡同:例如,它们塑造了我们对事物的隐性偏见,包括但不限于种族、年龄、性别或性取向。这些偏见通常涉及到我们学习那些高层次概念相互联系的方式,这些概念总是同时出现,或者在上下文中高度相关,但是这些偏见还是会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早期的知觉理解。
举个例子,相比于白人的面孔,当一个模糊的物品出现的时机或位置与一张黑人面孔临近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报告他们看到了武器——这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不同的人群中、以及各种情境下被反复验证。这一效应由基思·佩恩(Keith Payne)首次提出。在两组实验中,佩恩向60位非黑人参与者展示了一系列工具或手枪的黑白照片,这些图片会在屏幕上以五分之一秒为间隔快速闪过,并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这两组实验的关键点在于,在每个需要辨认的物品出现之前,都会有一张黑人或白人的男性面孔短暂呈现。研究的参与者被告知那些面孔仅仅是预示着事物即将出现的线索,而非与事物的关联性。事实上,研究者们也并没有这样做,黑人和白人面孔在工具和手枪被展示之前出现的概率是相等的。尽管如此,佩恩的实验结果表明,基于参与者的反应时,手枪在黑人的面孔之后出现更容易被辨认。在黑人面孔出现之后,手枪也比工具更容易被辨认;但当二者出现在白人面孔之后时,辨认的难易度没有差别。
尽管这项研究的效应量相对较小,但它依然表明学习对于参与者的大脑而言至关重要。在黑人面孔之后呈现的手枪是该实验中最容易辨认的事物,这一事实表明,平均来看,参与者的神经数据库中包含着黑人面孔与手枪之间足够强的连接,以至于他们的大脑中产生了一条连接两者的捷径。换句话说,为什么人们能够更快地辨认出黑人面孔之后出现的手枪,对这一事实最直截了当的解释是,当仅仅看到黑人面孔时,他们的大脑已经开始填补空白,构建出武器这一概念。
不幸的是,这项原创研究没有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修正它?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弄清楚驱使偏见产生的数据来自何处。尽管许多每个人拥有枪支,仍然很难相信该研究中的普通大学生有许多(或任何)关于黑人持枪的真实经验。那么,这些捷径是如何产生的呢?简单来说,你在真实生活中关于特定类型的人、地点和事件的经验越少,你大脑的数据库就越是容易被在电视上看到的、在新闻中或社交媒体上读到的、或是在虚构的描述的信息所占据。因此,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的黑人更可能拿着手枪而非听诊器,你的大脑便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情况,并将之融入基于经验、你与你所见世界之间的滤镜中。这对于任何一个能从新闻中获取资讯的人来说,结果都不堪设想。
如此一来,当我们与其他人眼中的现实交流碰撞时,我们大脑的自然而然也会被来自于社会的系统性偏见所塑造。这些偏见会使我们以非常快速且不经意的方式产生对世界的理解。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重要区别,即参与这项研究、并在大脑中搭建了这种捷径的人,他们不一定对什么样的人会携带枪支拥有有意识的、明确的想法。事实上,你的明确的信念和你经验数据库之间完全可能是彼此冲突的。
你可以认为隐性偏见是一种过度适应的结果。当你生活的环境比你所希望的狭隘得多,但你大脑对这一环境的依赖已经积重难返的时候,这种过度适应可能就发生了。当我们开始从比过去更狭隘的、受疫情隔离影响的偏见中挣脱出来时,意识到这种过度适应的影响似乎更加有意义。为了修正大脑中已然形成的捷径,我们可以接触更多样化的真实世界的经验,并允许来自不同视角的观点来塑造我们的大脑。如果能够有意识地选择一些经验来滋养我们的大脑,我们便可以凭此来塑造未来自己适应世界的方式。
翻译:Muchun;校对:物离;编辑:eggri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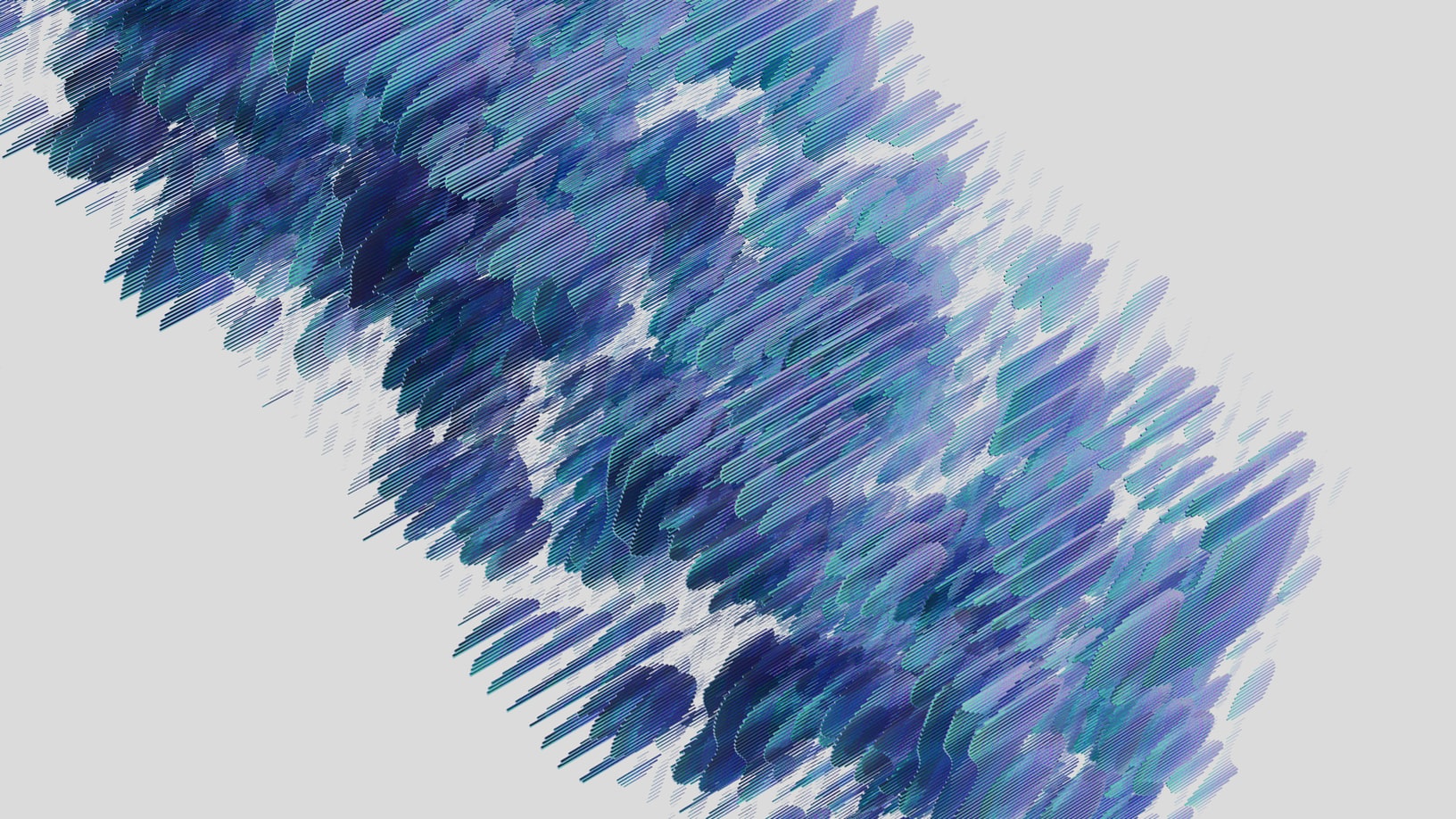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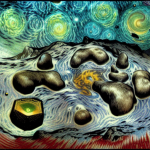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