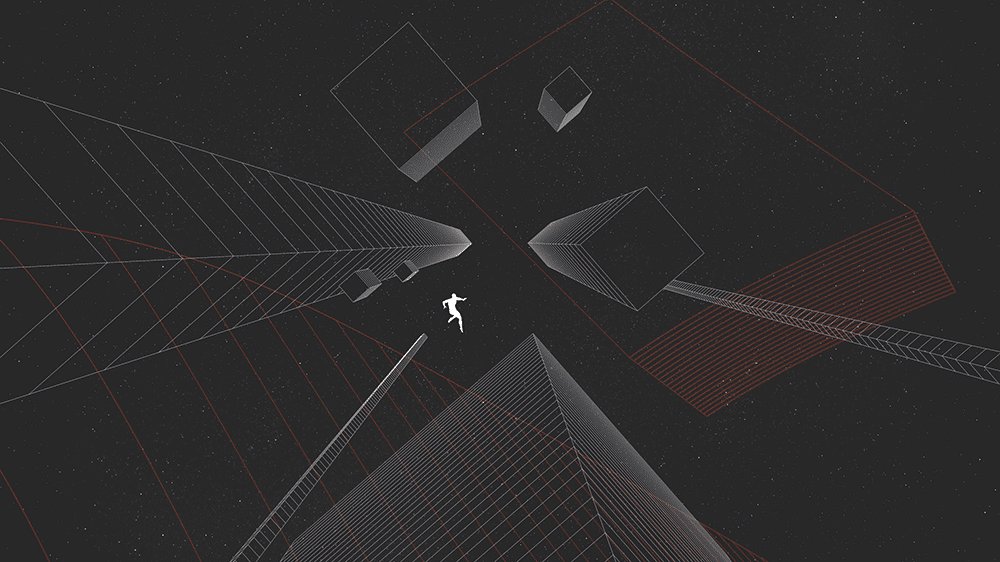
人类喜爱规律,追求可预测性。但就像宇宙演化离不开熵一样,我们需要无序才能繁荣。
在印度南嘉寺(Namgyal monastery)有一种仪式,佛教僧侣会在仪式中创作图样精美复杂的彩色沙画曼陀罗(mandalas)。每一幅曼陀罗的直径长达三米,如此巨作需要耗时数周才能完成。作画期间,几个身着橘袍的僧侣们弓着身子跪在一个平台上,刮擦金属小瓶。沙子从小瓶的细孔中喷出,一次只有几颗沙,落入由粉笔准确勾勒的区域里。慢慢地、慢慢地,古老的图案绘制成了。等到大功告成,僧侣们念一段经,停留一小会儿,然后五分钟内把沙画全部抹掉。
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过这个仪式,但是我在东南亚旅游的时候见过不少曼陀罗。在佛教里,曼陀罗的创造和毁灭象征了尘世的无常。这一仪式也让我想起有序(order)和无序(disorder)在世界核心玄妙的共生关系。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无序不只是存在于大自然,无序更是大自然的养料。植物、星星、生命甚至时间之矢都依赖着无序。我们人类也一样——尤其是当我们把随机性、新奇性、自发性、自由意志和不可预测性等概念与无序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概念都归类为超自然的。与无序对立的有序,则与系统、规律、理由、理性、模式、可预测性等概念相近。虽说这两个概念集的关系不像黄昏与黎明那样对应,但它们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从现代美学就能看出,我们本能地被有序和无序同时吸引着。我们喜欢事物具有对称性与有规律可循的模式,但我们也渴望一点不对称。英国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认为,虽然人类心理在深层次上偏爱有序,但绝对有序的艺术却很无趣。“无论我们怎么分析规则与不规则之间的区别,”他在1979年的《秩序感》中写道,“我们最终不得不解释审美经验中最基础的事实——愉悦感总是介于乏味和困惑两者之间。”当太多有序的事物摆在面前,我们就不再感兴趣。而太多的无序,也无法让人感兴趣。我妻子是个画家,她习惯在画布的一角抹上一道色彩来打破平衡,好让作品更吸引人。可见,我们的视觉甜点(sweet-spot)介于乏味与困惑之间,介于可预测性和陌生感之间。
对于有序/无序的联结,人类总是很矛盾的。我们有时倾向有序,有时又会渴望无序。我们尊重原则、规律和有序。我们探求事物背后的成因,讲究逻辑上的论据。我们追求可预测性。不过,不是所有时候。总有一些瞬间,我们也看重自发性、不可预测性、新奇性和不受束缚的个人自由。我们喜爱西方古典音乐的结构,也喜欢爵士乐无拘无束的急奏(runs)和信手拈来的韵律。我们着迷于雪花的对称感,也迷恋着天上云朵捉摸不定的形状。我们喜爱纯种动物的规律性特征,同时也赞叹“混血儿”的美丽。我们会尊敬那些循规蹈矩、秉公正直的人。但我们也尊重打破陈规的生活方式,并颂扬自己那些狂放不羁、出人意料的行为。我们人类真是奇怪而矛盾的生物。而我们的宇宙也同样奇怪。
从科学与艺术的对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序/无序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在公元前250年,阿基米德构造出了浮力原理——任何浸没在液体中的物体(不管是完全或部分),都会受到一个向上的作用力,且这个作用力与排出液体重量相等。作为史上最早的量化自然定律之一,它预示着科学时代的到来。这条定律也可以表述成,当排出液体的重量等于物体的重量时,放入液体中的物体便停止下沉。为了证明这一定律,阿基米德想必曾经不断重复实验,探究不同形状、体积的物体和各种液体(比如水和水银)所产生的影响。(古希腊的集市上已经有天平了,用来称小麦、咸鱼、玻璃、铜块和银块。)
显然,质量与力构成的物理世界是逻辑、理性、可量化和可预测的。然而两个世纪以前,苏格拉底——这个身材矮壮,长着蒜头鼻和鱼泡眼的不停游荡的智者,在柏拉图等人口中“比起人类更像萨提尔(satyr)”*——却颂扬疯癫的创造力:“那个灵魂没有被灵感击中过的人,来到神庙前,以为可以靠艺术的帮助入殿;我说他和他的诗都不准进来;与疯人相较,理智的人永远无法望其项背。”
*萨提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羊男,性情快活而粗鲁好色。
我们经常把创造力与标新立异、惊奇以及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所谓的发散性思维(divergent thinking)联系在一起——发散性思维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即用自发和无序的方式探索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与之相对的聚合性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则用更逻辑、更有序、按部就班的方式解决问题。法国数学家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就曾在1910年称,他某个数学发现的酝酿过程,就是在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来回切换:
有那么15天,我竭尽全力想证明,不存在其他与我所谓的福克斯(Fuchsian)相似的函数。那时候我特别无知;我每天坐在写字台前,待上一两小时,尝试各种组合却一无所获。有一天晚上,我打破了生活规律,喝了杯黑咖啡然后失眠了。想法源源不断地涌出来;我感觉它们不停碰撞,直到环环相扣,换句话说就是产生了稳定的组合。到第二天早上……
毋庸置疑,是发散和聚合两种思维方式协同作用,点燃了我们部分创造力。
自苏格拉底颂扬疯癫诗人后的两千年里,都没有人详细阐述过无序在自然中的关键角色——直到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1822年,克劳修斯生于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一个德国波兰两国分占的地区,并在柏林大学接受教育。或许是受到教士父亲的宗教影响,克劳修斯过着很有原则的生活。在鲁道夫1888年去世时,他的兄弟罗伯特回忆道,“他最显著的性格特点就是真诚和精确,任何程度的夸张都违背他的本性。”
和爱因斯坦一样,克劳修斯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也就是说,他的所有成就,包括他在无序问题上的开创性成果,都是由纸笔创造的数学功绩构成的。1850年,克劳修斯成为了柏林皇家炮兵与工程学院的物理学教授。同年,他发表了关于无序的伟大论文《论热的动力》。在文中克劳修斯表明,物理世界的变化与从有序到无序的必然运动息息相关。若是没有无序的潜能,宇宙的万事万物就永远不会变化,就像整整齐齐竖好的一排多米诺骨牌,或是一幅锁在保险箱里的佛教曼陀罗,南嘉寺僧侣的扫帚永远碰不到它。
克劳修斯论文的标题出现了“热”这个词,因为人们经常把无序的增加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的热传导联系起来——但这个概念其实更宽泛。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克劳修斯发明了“熵”(entrophy)这个术语来量化无序的程度。这个词是由希腊语里意为“在里面” 的ἐν(en),和意为“转变”的 τροπή(tropē)构成的。于是熵增与世间的转变、运动和变化联系起来了。无序越多,熵就越多。《论热的动力》的最后两句话是:
- 宇宙的能量是恒定的。
- 宇宙的熵趋向于最大值。
有序不可避免地屈服于无序,熵不断增加直至无法再增加。是这一运动推动着世界的运作。干净的房间蒙上灰尘。庙宇逐渐坍塌。随着我们变老,骨头变得脆弱易碎。恒星终会燃尽,将它们的热能尽数献给宇宙的寒冷——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为周围的行星带去了温暖和生命。无序的无情增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养料。
无序也是这一深奥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
甚至连时间之矢这样基本的事实都是由有序到无序的运动决定的。如果你觉得这种说法很荒谬,请想象一个玻璃高脚杯从桌子上掉下来,摔碎在地板上——这是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变最明显的例子。如果你在电影里看到这么一段,会觉得很正常。但如果你看到地板上的碎玻璃一跃而起,自动拼合成了一个完整的高脚杯,停留在桌子的边沿上呢?我们会认为这段电影是倒放的。为什么?因为随着我们向未来进发,一切都从有序变得无序。甚至可以说时间流逝的方向就是无序的增加。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根本没法分辨这一刻和下一刻;也就不存在钟表,鸟儿也不会飞,树叶不会划过空气从树上掉下来,更没有呼吸。宇宙会是一张绝对永恒的静态照片。
无序也是这一深奥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是有(something)而不是无(nothing)?(这类问题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夜不能寐。)为什么会存在任何形式的物质,而不仅仅是纯粹能量(pure energy)?从科学角度上看,这个问题与反粒子的存在有关;科学家们于1931年预测到了反粒子,并于1932年发现了它们。每一个亚原子粒子,比如电子,都有一个反粒子孪生兄弟——除了电荷相反和某些其他性质的差异外都一模一样。至于这对兄弟的哪一个叫“粒子”哪一个叫“反粒子”,只是约定俗成罢了,就像南极、北极那样。当粒子与反粒子相遇,它们将彼此摧毁,除了纯粹能量什么都不剩。
假如在宇宙诞生之初,粒子与反粒子的数量相等,就能推断出在这样一个完全对称的宇宙中,一切物质早在几十亿年前就应该被摧毁了,只剩下纯粹能量。没有恒星,没有植物,没有人类……一切有形的物质都不存在。那我们又为什么在这儿?为什么所有粒子没有和它们的反粒子兄弟一起消失呢?
这个让物理学家头疼的问题,在1964年终于有了答案。通过一系列在当时极为精密的实验,人们发现粒子和反粒子的行为方式并非完全相同。二者与其他粒子作用的方式表现出细微的不对称性,所以在宇宙创生之初产生与摧毁的粒子和反粒子数量其实不等。在大批粒子与它们的反粒子携手湮灭后,一些粒子会留下来,就像在舞会上落单找不到舞伴的男同学,孤独地坐在长凳上。这些被剩下的粒子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不对称性,便是我们存在的原因。
无序不仅存在于物质如何构成自身的细枝末节里。在生命本身的深层结构中也有无序的踪迹。无序在生物学中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是基因的“洗牌”——通过基因突变,或者病毒及其他生物体的基因转移。藉由这些随机过程,生物体得以尝试各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的身体构造。这些基因“轮盘赌”的旋转可不是安排好的,它们的结果也无法提前预料。假如没有“洗牌”,生物就会受限于少量死板的设计。很多生物会灭绝,因为它们无法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也会大大减少。
生物学中另一种与无序有关的著名过程叫做扩散(diffusion)。扩散指的是不平整的物质或能量团会被原子和分子的随机碰撞“抹平”。你可以自己实验一下,比如把一桶热水倒进装着冷水的浴缸里。一开始,浴缸中心会形成一块高温区域,周围则是凉的。然而热水很快与冷水混合,直到温度均匀分布。这就是扩散。借用克劳修斯的话来说,扩散不消耗任何能量,但它能增加无序——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混合热量——从而引发转变和变化。要是没有分子的随机碰撞,扩散就不会发生。热水和冷水就会各自占据浴缸的一边,互不相干。
扩散也是将维持生命的物质运输到全身的一种关键机制。用氧气这种制造能量时不可或缺的气体举例吧。我们每一次吸入空气都在肺里聚集了高浓度的氧气。遍布肺部的微小血管中的含氧量则相对较低。这就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气体从肺里“扩散”到血液中。这种定向运动其实是随机碰撞所导致的,因为后者趋向于将氧气分子从高浓度区域运输到低浓度区域。如果没有这些随机的“敲敲打打”和“横冲直撞”,肺里的氧气就会被困在原地,体细胞也就窒息而死了。
在神经元间穿梭的电信号也是生物体中扩散现象的实例。当带正电荷的钠原子和钾原子跨过神经元的细胞膜时,神经元会产生电脉冲。而这样的过程是由高浓度的带电离子朝低浓度区域随机“洗牌”并平衡浓度所导致的。说来很讽刺,个体原子的随机碰撞竟然导致了神经冲动的有序向前传导。这就是身体自我交流的机制。
可是这些微观领域的例子,包括克劳修斯关于熵的深刻洞见,都没能解释人类为何悖论般地同时着迷于有序和无序——我们又喜欢老实体面人,又爱特立独行者。我们的灵魂深处似乎有某种原始的冲动,早在克劳修斯或苏格拉底之前的远古时代就已印刻下来。或许这种对矛盾属性的接纳,赋予了我们数百万年前的祖先一种适应性优势。
这一推测听起来很可靠。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有序意味着可预测性、模式和可重复性——它们都使得我们能够做出准确预测。当我们想知道猎物什么时候会穿过树林,庄稼应该什么时候种下的时候,可预见性就很重要了。显然,可预见事物的确定性对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帮助。或许更出人意料的是,关注惊喜、随机和新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如果我们过得太安稳,就无法应对变化:比如老虎突然出现在一条我们走过一千遍而从未遭遇意外的路上。而且我们也不愿冒险了,总害怕偏离我们熟悉的日常。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演化得既渴望可预测的事物,又渴望不可预测的事物了。
既然有序和无序都对人类有好处,我们得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总是把事物分成极端对立的两极。
如果渴望新奇事物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生存优势,那么我们应该能在基因中找到证据。研究者最近发现了一种叫做 DRD4-7R 的(等位)变异基因;它还有个更酷的名字,“漫游癖(wanderlust)基因”。20%的人口拥有这种基因,它似乎与人们喜爱探索和冒险的癖性有关。这与我们希望部落的大部分成员待在家里、循规蹈矩、脚踏实地是符合的。但我们也需要一小部分人踏上危机四伏的征程,寻觅新的狩猎场所和意外的机遇。“有证据表明,与追求新奇、冲动等性格特征相关的那些等位基因,也与金融投资的风险行为有关。”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教授、DRD4-7R 研究的领导者之一理查德·保罗·爱波斯坦(Richard Paul Ebstein)说,“有这种基因的人似乎更倾向于冒险。”不过,其他生物学家也正确地指出,不太可能是某个单一基因控制了冒险和追求新奇等性状,而更有可能是一组基因的协同作用。
既然有序和无序都对人类有明显的好处,我们得反思一下我们(至少是西方人)总喜欢把事物分成极端对立的两极的倾向;而且我们还预设了价值的高低,掺杂了默认的偏好——高产和懒惰、理性和非理性、热和冷、光滑和粗糙、白和黑。或许我们其实应该把这些对立看作一种有效的平衡。
丹麦物理学家、量子物理的先驱之一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曾说过,一个深奥真理的对立面也是真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比如古代儒家就有“阴阳”的概念:所有事物都是作为不可分割的矛盾对立存在的。“阴”与女性、黑暗、北面、衰老、柔软、寒冷联系在一起,而“阳”则代表男性、光明、南面、年轻、坚硬和温暖。阴阳的标志是两个纠缠着的漩涡,一黑一白,大小相等,两个旋涡中间都包含着对方颜色的一个圆点——这意味着阴阳和谐共生,没有哪个能主宰另一个。与之相反,典型的西方人思维则是试图通过二分法,简化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在某个阶段是有效的,直到我们凑近观察潜伏在这背后的真实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最终得以站在更高的维度,就会重新找到简单和和谐。宇宙歌唱着有序,但它也歌唱着无序。我们人类寻求可预测性,但我们也渴望新事物。拥抱这些必然的矛盾吧,玻尔和孔门弟子说。
写到这里,文章也将收尾。我正在听奥地利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第九交响曲》,他从1887年开始创作这首作品。交响曲的开场渐次展开主题。而第二乐章“谐谑曲”(the Scherzo)听上去很邪恶,好像隐瞒着什么黑暗的秘密。第三乐章“慢板”(the Adagio)中的几段则深深吸引了我。在一段连绵不绝的悦耳弦乐后(也许在许诺即将揭示秘密),声音变得越来越不和谐,音量也越来越大,直到我们听到雷鸣般的号声,粗粝而刺耳,然后是更多的撞击声,就像浪潮奋力拍打海岸。然后是一段寂静无声。弦乐再次渐起,宁静而抒情。这种悦耳和刺耳间的切换循环往复,直到乐章结束。
我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与不和谐紧挨在一起,和谐的那几段还会听起来那么美吗?没有黑暗作伴的明亮呢?没有粗糙作伴的光滑?还有,失去了表面上无序之物作伴的有序?当然还有布鲁克纳自己,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不过是巧合中诞生的——细胞在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随机碰撞,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生命。
翻译:有耳;审校:Root;编辑:EON
The music of all time is a duet between order and disorder | Aeon Essays
Humans love laws and seek predictability. But like our Universe, which thrives on entropy, we need disorder to flourish
小说家、散文作家和物理学家,MIT 人文实践教授。著有 Einstein’s Dreams、In Praise of Wasting Time 等。现居波士顿。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