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和硅谷的职场卷王,正在靠“嗑药”压榨大脑
华尔街和科技圈正在向我们展示一种畸形的工作生态,依靠处方药物来强行突破人类生理极限,满足无止境的效率和竞争需求。

在美国企业界,特别是华尔街和科技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高管和普通员工为了应对激烈的职场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开始依赖各种药物。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咖啡因或能量饮料,而是处方药物如阿德拉(Adderall)、万思达(Vyvanse)等ADHD药物,甚至包括氯胺酮和迷幻药等更具争议性的物质。
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初级分析师和助理银行家们常常面临每周90至100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些年轻的金融精英们每天清晨踏入办公室,往往又直到凌晨才能离开,而第二天清早又必须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客户面前。为了应对这种近乎不人道的工作强度,许多人转向了处方兴奋剂,并将它们视为职场生存的必需品。
马克·莫兰的经历就是典型案例。作为一名在纽约瑞信实习的年轻投资银行家,面对即将到来的每周90小时工作量,他向同事寻求建议。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令人震惊却又在业内习以为常:去华尔街的一家健康诊所,告诉工作人员你难以集中注意力。
莫兰按照建议前往诊所,只花了五分钟填写了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回答诸如”是否难以保持条理”、”是否拖延”等问题。随后的医生问诊更像是例行公事,医生直接草率地宣布他的答案表明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毫不犹豫地开出了阿德拉的处方。整个过程快速而机械,反映了美国医疗体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精神类药物的过度处方和获取的便利性。这些精品健康诊所和远程医疗平台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惊人地容易,它们通常不接受保险,收取高额费用,却提供极为宽松的药物处方标准。
“他们给了我处方,几个月内,我就上瘾了,”莫兰回忆道。”你开始依赖它才能工作。服用阿德拉后,我能连续工作数小时,甚至对年轻投资银行家的一些单调任务产生兴趣,比如在PowerPoint上对齐公司标志或在Excel中格式化单元格。”这种药物让他能够在极端工作条件下保持专注,但同时也开启了依赖的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已经在职场公开化。在旧金山富国银行医疗保健投资银行部门工作的乔纳·弗雷描述,有同事会在公共办公区的办公桌上直接吸食碾碎的阿德拉药片,而周围没有人对此有异议,仿佛这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正常手段。在杰富瑞集团休斯顿办公室,分析师们在制作财务模型和PowerPoint幻灯片时,一次会放两个Zyn尼古丁袋。空容器通常在公共办公区堆成金字塔,成为工作强度的另一种象征。
更极端的是,在休斯顿有银行家会一口气喝下”魔爪炸弹”——一杯装满魔爪能量饮料再加入一支超强版5小时能量饮料的混合物,相当于一次性摄入近五杯咖啡因的量。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不断推高极限的文化,仿佛不靠药物和刺激物就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成了行业默认的规则。
而在科技行业,另一种趋势正在形成:使用氯胺酮和迷幻药物如裸盖菇素(魔术蘑菇)来增强创造力和专注力。保险经纪公司Frontier Risk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惠特科姆在氯胺酮体验后,创建了一种特殊的团队视频会议形式,让12人团队每周聚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彼此工作,没有议程。他承认,清醒的自己本会认为这种共同沉默的坐着太过”神神叨叨”,不适合职场,但在药物影响下,他认为这可以激发即兴的协作。
佩吉·范德普拉什在疫情初期她的金融咨询公司陷入困境时,开始服用小剂量的魔术蘑菇,发现自己能长时间专注于重要任务。她将这种体验称为”生物黑客的下一个层次”,并进一步表示说”如果我在两小时内比旁边的人在八小时内更有创造力,那就是一种优势”。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科技行业对效率的极度追求,以及将人体视为可以被”黑客入侵”和”优化”的系统。
这些行为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动机。在华尔街,初级银行家的薪水可达20万美元,而成功晋升可获得七位数年薪。纽约精神科医生塞缪尔·格拉泽指出:”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渴望表现出色。巨大的经济回报可能会促使人们使用药物来提高业绩。”
获取药物的途径也变得更加便捷。像纽约的Trifecta Health这样的精品健康诊所以及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远程医疗网站,都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异常简单。拥有并经营Trifecta的精神科医生爱德华·弗鲁特曼承认,他的客户中有50%来自华尔街。这些客户转向他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高能工作几乎不可能在没有药物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任何人类真正能产出和做的事情都是有限度的,”这些医生还借口说工作困难可能是未经治疗的ADHD的迹象。这种说法模糊了正常人类能力的界限与病理状态之间的区别,为药物的过度使用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这种追求效率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阿德拉和万思达被归类为二类管制药品,与可卡因和阿片类药物并列,因为它们有很高的滥用潜力。滥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脏病、体重急剧下降、失眠和精神问题。
莫兰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从阿德拉换成了万思达,剂量稳步增加到每天70毫克,这是该药物的最大日剂量。在纽约的精品投资银行Centerview Partners工作期间,他曾在办公室为客户准备推介材料直到凌晨5点,回家换衣服后,大约上午9点又回到办公室与客户会面,途中服用了万思达。那天上午,在调整一个财务模型时,他开始出现心悸,感觉就像刚跑完800米冲刺,”只不过我是在Microsoft Excel上而不是在跑道上。”那一刻他意识到必须停止使用这些药物。
银行家弗雷的故事更突显了药物依赖的恶性循环。他开始服用阿德拉是为了应对在旧金山办公室凌晨4点开始并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工作日。当他在纽约找到新工作后,工作量至少增加了两到三倍,医生提出增加他的剂量,他欣然同意。”我开始早上服用一次,下午再服用一次,一开始是一周五天,然后变成了一周七天,因为我大多数周末都在工作,”他回忆道。
随着时间推移,弗雷开始忘记是星期几,因为药片使他陷入不间断的高效狂热中。他失去了食欲,体重下降了约25磅。最终,他在2022年辞去了工作,停止服用药物,搬回父母家。大约一个月后他才感觉恢复正常:晚上会出现冷汗,要么连续睡12个小时,要么根本不睡觉。”我开始时了解使用阿德拉的风险,”他说。”但回报是成为董事总经理并获得七位数的薪水。我觉得我必须有一个优势才能成功。”停药后,”我基本上必须重新学习作为一个在社会中运作的人类的基本知识,而不仅仅是去办公室工作到死。”
药物依赖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会改变使用者的性格和社交能力。一位在纽约古根海姆合伙人工作的前银行家表示,他每天早上服用50毫克的万思达,有些晚上服用20毫克的阿德拉,这远高于格拉泽医生所说的典型起始剂量(每天30毫克的万思达或5毫克的阿德拉)。他发现药物让他感到反社会和孤立,阻碍了他在工作中进行随意交谈的能力。“我觉得药物使我变得像机器人一样,高度交易性,无法接受与陌生人社交的想法——因为我看不到即时的价值增加。”这种描述令人不安地展示了药物如何剥夺了使用者的人性,将他们转变为纯粹的生产工具。
在美国企业界,特别是华尔街和科技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高管和普通员工为了应对激烈的职场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开始依赖各种药物。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咖啡因或能量饮料,而是处方药物如阿德拉(Adderall)、万思达(Vyvanse)等ADHD药物,甚至包括氯胺酮和迷幻药等更具争议性的物质。
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初级分析师和助理银行家们常常面临每周90至100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些年轻的金融精英们每天清晨踏入办公室,往往又直到凌晨才能离开,而第二天清早又必须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客户面前。为了应对这种近乎不人道的工作强度,许多人转向了处方兴奋剂,并将它们视为职场生存的必需品。
马克·莫兰的经历就是典型案例。作为一名在纽约瑞信实习的年轻投资银行家,面对即将到来的每周90小时工作量,他向同事寻求建议。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令人震惊却又在业内习以为常:去华尔街的一家健康诊所,告诉工作人员你难以集中注意力。
莫兰按照建议前往诊所,只花了五分钟填写了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回答诸如”是否难以保持条理”、”是否拖延”等问题。随后的医生问诊更像是例行公事,医生直接草率地宣布他的答案表明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毫不犹豫地开出了阿德拉的处方。整个过程快速而机械,反映了美国医疗体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精神类药物的过度处方和获取的便利性。这些精品健康诊所和远程医疗平台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惊人地容易,它们通常不接受保险,收取高额费用,却提供极为宽松的药物处方标准。
“他们给了我处方,几个月内,我就上瘾了,”莫兰回忆道。”你开始依赖它才能工作。服用阿德拉后,我能连续工作数小时,甚至对年轻投资银行家的一些单调任务产生兴趣,比如在PowerPoint上对齐公司标志或在Excel中格式化单元格。”这种药物让他能够在极端工作条件下保持专注,但同时也开启了依赖的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已经在职场公开化。在旧金山富国银行医疗保健投资银行部门工作的乔纳·弗雷描述,有同事会在公共办公区的办公桌上直接吸食碾碎的阿德拉药片,而周围没有人对此有异议,仿佛这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正常手段。在杰富瑞集团休斯顿办公室,分析师们在制作财务模型和PowerPoint幻灯片时,一次会放两个Zyn尼古丁袋。空容器通常在公共办公区堆成金字塔,成为工作强度的另一种象征。
更极端的是,在休斯顿有银行家会一口气喝下”魔爪炸弹”——一杯装满魔爪能量饮料再加入一支超强版5小时能量饮料的混合物,相当于一次性摄入近五杯咖啡因的量。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不断推高极限的文化,仿佛不靠药物和刺激物就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成了行业默认的规则。
而在科技行业,另一种趋势正在形成:使用氯胺酮和迷幻药物如裸盖菇素(魔术蘑菇)来增强创造力和专注力。保险经纪公司Frontier Risk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惠特科姆在氯胺酮体验后,创建了一种特殊的团队视频会议形式,让12人团队每周聚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彼此工作,没有议程。他承认,清醒的自己本会认为这种共同沉默的坐着太过”神神叨叨”,不适合职场,但在药物影响下,他认为这可以激发即兴的协作。
佩吉·范德普拉什在疫情初期她的金融咨询公司陷入困境时,开始服用小剂量的魔术蘑菇,发现自己能长时间专注于重要任务。她将这种体验称为”生物黑客的下一个层次”,并进一步表示说”如果我在两小时内比旁边的人在八小时内更有创造力,那就是一种优势”。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科技行业对效率的极度追求,以及将人体视为可以被”黑客入侵”和”优化”的系统。
这些行为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动机。在华尔街,初级银行家的薪水可达20万美元,而成功晋升可获得七位数年薪。纽约精神科医生塞缪尔·格拉泽指出:”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渴望表现出色。巨大的经济回报可能会促使人们使用药物来提高业绩。”
获取药物的途径也变得更加便捷。像纽约的Trifecta Health这样的精品健康诊所以及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远程医疗网站,都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异常简单。拥有并经营Trifecta的精神科医生爱德华·弗鲁特曼承认,他的客户中有50%来自华尔街。这些客户转向他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高能工作几乎不可能在没有药物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任何人类真正能产出和做的事情都是有限度的,”这些医生还借口说工作困难可能是未经治疗的ADHD的迹象。这种说法模糊了正常人类能力的界限与病理状态之间的区别,为药物的过度使用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这种追求效率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阿德拉和万思达被归类为二类管制药品,与可卡因和阿片类药物并列,因为它们有很高的滥用潜力。滥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脏病、体重急剧下降、失眠和精神问题。
莫兰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从阿德拉换成了万思达,剂量稳步增加到每天70毫克,这是该药物的最大日剂量。在纽约的精品投资银行Centerview Partners工作期间,他曾在办公室为客户准备推介材料直到凌晨5点,回家换衣服后,大约上午9点又回到办公室与客户会面,途中服用了万思达。那天上午,在调整一个财务模型时,他开始出现心悸,感觉就像刚跑完800米冲刺,”只不过我是在Microsoft Excel上而不是在跑道上。”那一刻他意识到必须停止使用这些药物。
银行家弗雷的故事更突显了药物依赖的恶性循环。他开始服用阿德拉是为了应对在旧金山办公室凌晨4点开始并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工作日。当他在纽约找到新工作后,工作量至少增加了两到三倍,医生提出增加他的剂量,他欣然同意。”我开始早上服用一次,下午再服用一次,一开始是一周五天,然后变成了一周七天,因为我大多数周末都在工作,”他回忆道。
随着时间推移,弗雷开始忘记是星期几,因为药片使他陷入不间断的高效狂热中。他失去了食欲,体重下降了约25磅。最终,他在2022年辞去了工作,停止服用药物,搬回父母家。大约一个月后他才感觉恢复正常:晚上会出现冷汗,要么连续睡12个小时,要么根本不睡觉。”我开始时了解使用阿德拉的风险,”他说。”但回报是成为董事总经理并获得七位数的薪水。我觉得我必须有一个优势才能成功。”停药后,”我基本上必须重新学习作为一个在社会中运作的人类的基本知识,而不仅仅是去办公室工作到死。”
药物依赖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会改变使用者的性格和社交能力。一位在纽约古根海姆合伙人工作的前银行家表示,他每天早上服用50毫克的万思达,有些晚上服用20毫克的阿德拉,这远高于格拉泽医生所说的典型起始剂量(每天30毫克的万思达或5毫克的阿德拉)。他发现药物让他感到反社会和孤立,阻碍了他在工作中进行随意交谈的能力。“我觉得药物使我变得像机器人一样,高度交易性,无法接受与陌生人社交的想法——因为我看不到即时的价值增加。”这种描述令人不安地展示了药物如何剥夺了使用者的人性,将他们转变为纯粹的生产工具。
参考来源:
The Drugs Young Bankers Use to Get Through the Day—and Night
They Say Drugs Make Them Better at Their Jobs. Are They Tripping?
The Long Nights and Drug Addiction That Drove a Banker to Insider Trading
Generation Xanax: The Dark Side of America’s Wonder Drug
编译:李泽伟,胡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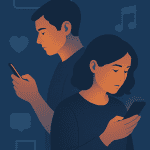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