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瑞克·内斯特勒(Eric Nestler)在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研究精神病与神经科学。他的实验室用小鼠研究抑郁——小鼠抑郁的表现与抑郁的人几乎无异。它们会无视陌生的同类,独自在笼子里静静地坐着;它们对糖水也提不起一点兴趣;甚至就算是把它们扔到水里,它们也不会挣扎,而是任由流水摆弄着它的躯体。
用术语来说,它们是“社会挫败应激小鼠模型”。换言之,更年长、更大的小鼠曾多次对它们宣誓主导地位,这种社会挫败的压力进而诱发了它们的抑郁症状。在实验室里,这是一种诱发小鼠抑郁的常规操作。不过内斯特勒的团队发现,如果一只小鼠幼年经受过创伤,那么,相较于其他小鼠,它会对霸凌更为敏感。
内斯特勒说:“根据这些小鼠和大鼠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幼年时受过精神压力的个体,在年长时抗压能力也会更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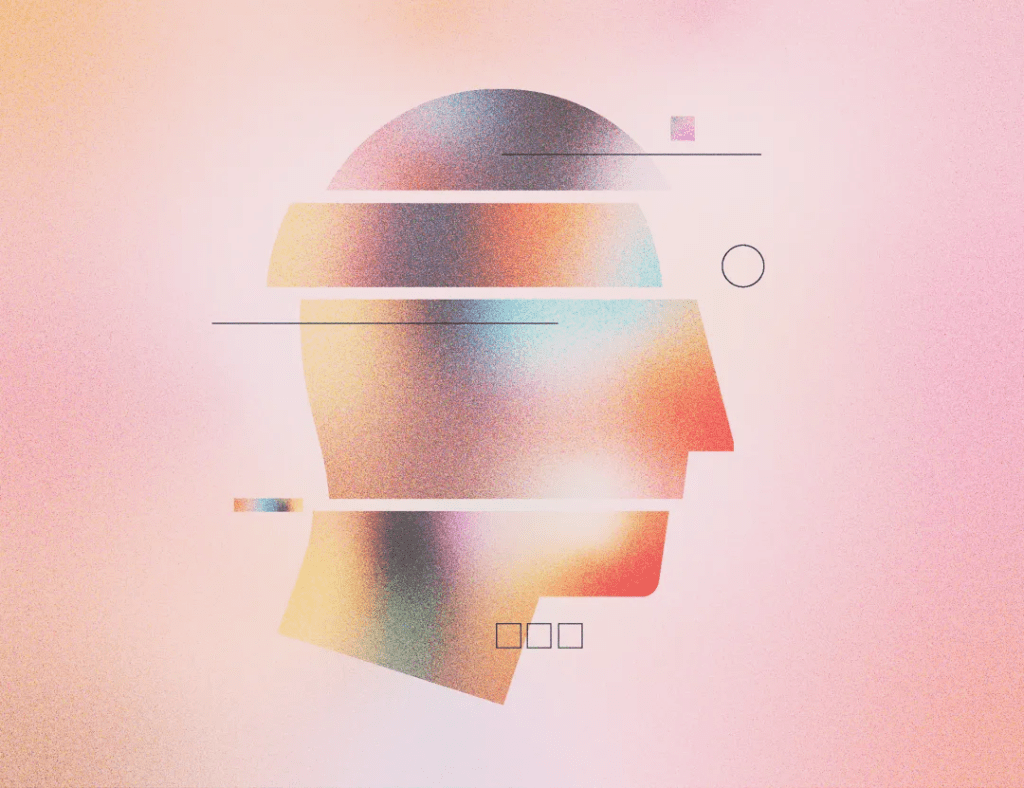
– Antlii 🇺🇦 –
以表观基因组为针线,我们也许能用物理手段缝补过去的伤痕。
这一结论看起来对人类也是成立的。详细的机制尚不明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把矛头指向表观基因——改变基因功能、但不修改DNA序列本身的那些过程。很多研究者认为童年的创伤性经历会从生物水平上改变我们,调控我们的基因表达,让我们精神健康的防线更为脆弱。
如果以上观点无误,那么它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新疗法。考虑到基因编辑在心脏病和癌症治疗中展现了光明的前景,有人认为以表观基因组为针线,我们也许能用物理手段缝补过去的伤痕。
悲惨的童年有时确实铸就了一些孩子坚韧不拔的性格。但内斯特勒坚持道:“童年的创伤性经历是以抑郁和焦虑为代表的精神问题的最大风险因子。”2010年,有团队发布了一个覆盖21个国家、超过5万名成人志愿者的大型研究[1]。
他们发现,无论是父母离世还是有家人滥用成瘾物质,几乎任何童年创伤性经历都会显著提升TA以后得精神病的概率。有趣的是,如果那个人可以想办法摆脱这段回忆的影响,那么TA得精神病的概率就会降低近1/3。

在实验中,一些早期暴露于压力下的小鼠,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更大的压力易感性——这一现象似乎对人类也是如此。
—
Alamy
但要揭示其下的生物学机制,我们需要进行动物对照实验。正是在这些实验中,研究人员观察到,早年逆境会导致表观遗传修饰。我们需要用动物对照试验来,而表观遗传修饰正是实验所揭露的。这种修饰就像在DNA上或DNA周围贴标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调控基因表达,即转录和翻译*。哈佛大学社会与精神流行病学家艾琳·邓恩(Erin Dunn)说:“如果把基因比做一首音乐,作曲者为得到想要的效果而做出的修饰性调整,便是表观基因修饰。”
*译者注:原文为“基因读取的难易程度以及是否产生对应的蛋白质”。
在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以亲自“作曲”,让幼年小鼠经历创伤,引导出表观基因变化。内斯特勒和他的团队曾每天将刚出生的小鼠和它们的母亲隔离几个小时[2],并且发现竟然有几百个基因在抑郁相关脑区的表达变得不一样了,而这些小鼠也会更快地在社会挫败压力实验中展现出抑郁行为。
但问题是,我们无法对人类被试进行同样的实验。让小孩经历创伤,切片他们的脑组织,然后去分析表观基因改变?这有悖人伦。不过马克斯普朗克精神病理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伊丽莎白·拜德(Elisabeth Binder)说:“人脑尸检似乎揭示了类似的发现。”
她提到了一个对自杀者大脑的研究[3]。作者对比了在童年遭遇过虐待和没有遭遇虐待的人,发现他们与压力有关的基因受到的表观基因修饰有所不同。这是个不错的证据,但为了解自杀者童年的创伤情况,这个研究的作者需要去询问自杀者的亲人,而这样问来的信息并不总是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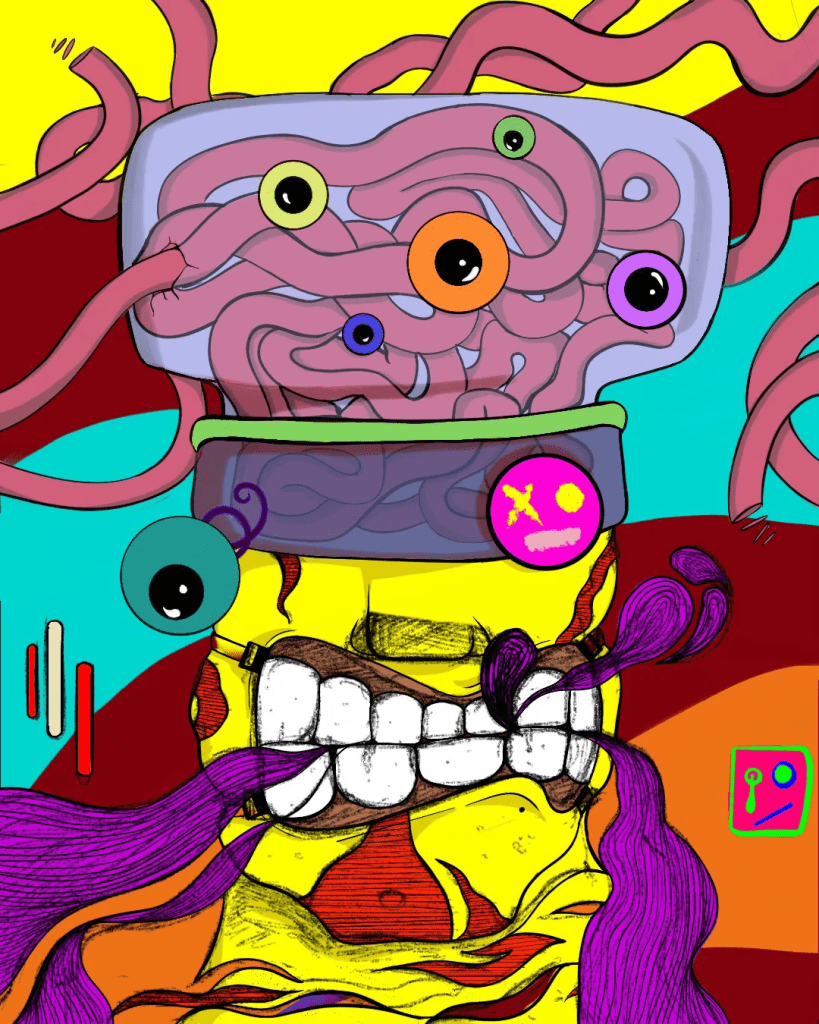
– Abhishek Anand –
所以研究者们希望直接研究活人。既然不能提取脑组织,就只能退而求次:采集唾液或血液样本来进行表观基因分析。没人知道这些样本能反映出多少人脑的变化,但也别无他法。尽管如此,这些样本还是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表观基因改变不只是“伤痕”那么简单,它是演化出来的极端生存策略。
表观基因钟(epinegentic clocks)是一种日益热门的研究表观基因改变的途径。一些表观基因会随着衰老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通过表观基因的变化来测算人的“生物学年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生物学上是衰老得快了还是慢了。
拜德首次针对有被虐待史的3-5岁儿童使用了表观基因钟[4]。她发现,那些产生了抑郁和焦虑倾向的被虐儿童在生物学上要比同龄人老三个月。这个差距相对于他们的年纪来说可不小。遭受过的虐待越是残酷,他们的生物学年龄就会越老。

表观遗传学可以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来标记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有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特殊风险。
—
Alamy
基于这个研究,我们很容易认为加速衰老纯粹是损伤性的变化。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珍妮弗·萨姆纳(Jennifer Sumner)觉得事实可能并不是如此简单。
她把创伤分成两类:威胁和匮乏。她解释道:“威胁,也就是遭受暴力、外伤的可能,跟生物学年龄的加速增长尤其有关。”她的研究还发现[5],受到威胁的儿童会更早进入青春期。但如果受到诸如缺乏关照等匮乏性创伤,儿童则会更晚地进入青春期,生物学年龄也不会受到影响。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合理的。在一个充满威胁的环境里,个体很有可能寿命更短,因此加快成熟可以让个体提早拥有繁殖能力。但如果处于资源不足的匮乏环境,萨姆纳表示:“在这个特殊的时段发育、繁殖,可能不是最优解。”
所以,这些创伤后的生理改变或许是演化的选择。大自然只在乎物种的繁殖,并不关心我们的福祉。“加速发育可以提高繁殖能力,但代价是牺牲长远的身心健康。”萨姆纳说。
对于今天把生活看得比繁殖更为重要的人来说,这笔买卖并不划算。既然这些表观基因是后天获得的,那我们可否逆转这些改变呢?

– Nan Cao –
长话短说,这是有可能的。新型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9的一种版本中剪切DNA的Cas9酶没有活性,这让科学家可以用这一工具来编辑表观基因组[6]。“它并不会剪切基因或者加段什么东西进去。”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神经科学家苏巴斯·潘迪(Subhash Pandey)说。它只是找到正确的基因位点,然后增减修饰基因的标签。
在2022年的一个研究中[7],潘迪利用针对表观基因的CRISPR-dCas9技术逆转了大鼠青少年时期酗酒导致的表观基因变化。他先前的研究[8]将大脑的恐惧中心杏仁核中的这种表观基因变化与成年人的焦虑情绪和饮酒行为联系了起来。

神经科学家Elisabeth Binder发现,创伤会导致儿童加速衰老。
—
Max Planck Institute
在青春期注射过酒精的大鼠比起没有接触过酒精的会更为焦虑。但是,当潘迪逆转了这些表观基因变化之后,它们的焦虑水平又回到了正常值。反之亦然,人工引入这些变化也可以让没接触过酒精的大鼠更为焦虑。
在表观基因编辑用于临床(酗酒)治疗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潘迪相信它“在未来有着很高的潜力”。他表示,毕竟所有的新疗法都要经过繁琐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验证。
然而,当涉及到抑郁和焦虑障碍时,内斯特勒则没那么有把握,因为这些疾病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基因决定的。他说:“每个人抑郁的原因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找到正确的治疗靶点就成了第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治疗的方式:潘迪通过手术给大鼠植入了一根管子。没有这根管子,CRISPR就无法编辑杏仁核的基因。对于大多数的临床障碍,内斯特勒评价道:“要治疗人类,我们需要更可行的办法。”一个替代CRISPR的办法是服用专门去除特定表观遗传修饰的药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经批准了此类药物用于某些癌症的治疗。虽然人们对它们的副作用仍心存疑虑,但内斯特勒表示:“我们对它控制抑郁症状的潜力非常感兴趣。”
另一些人认为,我们不能由于药物和基因编辑而忽视掉表观遗传学的本质:它是随环境改变的。“这些基因变化是我们生活环境的动态结果。我们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控制人们的精神健康风险。”邓恩觉得,抑郁症的预防重于治疗。
她认为,我们应该在患者被诊断之前就弥补他们童年的创伤经验,但不是利用针对精神健康的CRISPR技术,而是通过社会支持与心理治疗。而表观基因,则可以仅仅作为生物标记物用于筛查高危儿童。

– Majid Alammari –
一些人会觉得,我们并不是非得用表观遗传检测来筛选需要帮助的经历过创伤的儿童。对此邓恩答道:“我们可以有同样的遭遇,但这些遭遇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生物学效应。”在公共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将真正受创伤影响的人与有心理韧性的人区分开来可能是值得的。
内斯特勒的小白鼠证明了邓恩所言不假,同样的创伤会给不同的个体带来不同的效果。幼年晚期的创伤经历最容易在以后诱发抑郁,而幼年早期经历创伤的小鼠更容易复原,这可能是因为幼年早期的小鼠有更多的时间从创伤中恢复。
但即便是表观遗传药物和编辑内部,也有一些相对的捷径。内斯特勒最近发现了一套增强抗压能力的基因网络[9]。表观遗传调控可以增强这套网络的表达,也就是说,成人有可能通过服药来增强这套基因的表达。他说:“近几十年,大多数人都在想着怎么去消除压力的消极影响,但我们也可以尝试激活人类天生就有的恢复力。”
将来这些基因针线肯定不会短缺。问题是,我们会愿意用这些针线缝补我们的脑子吗?
后记
Benson:自医师这个职业诞生以来,他们都有着“审判”一个人是否病态(illness)的“生杀大权”。当这病以生理病变为主导原因时,循证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让医生可以做出越来越准确的诊断,这个权力并不会带来问题。可是到了精神疾病上,麻烦就来了。
什么样的情绪、思想和行为是需要干预的?如果需要干预,那么医院与规训机构(学校、监狱等)承担的角色又如何不同,分界线应当在哪?答案是,诊断权和处方权的边界并非由专业知识,而是由社会观念划下——比如说,上世纪LGBT的去病理化并不是医生带头的。19-20世纪的精神病院黑历史证明了,这样会带来一些很不好,很不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只有把精神问题还原到生理层面,才能让诊疗的边界归还给医学本身,避免医疗权力被社会滥用。fMRI,EEG,病理切片,基因测序……大家为此做了很多,但还不够好。随着表观基因与精神创伤的关联被发现,我不禁惊喜于未完的拼图又补上了一块。
参考文献
1.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the-british-journal-of-psychiatry/article/childhood-adversities-and-adult-psychopathology-in-the-who-world-mental-health-surveys/321448F043CF54632354A940AAB9E94E
2.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an4491
3.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44040/
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352289521001028
5.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326868/
6.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6-020-00620-7
7.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2319300307
8.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2319300307
9.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713580/
作者:Ida Emilie Steinmark | 译者:Benson | 审校:Soda | 编辑:M.W. | 封面:Nan Cao | 排版:骐迹 | 原文: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3/feb/26/does-gene-editing-hold-the-key-to-improving-mental-heal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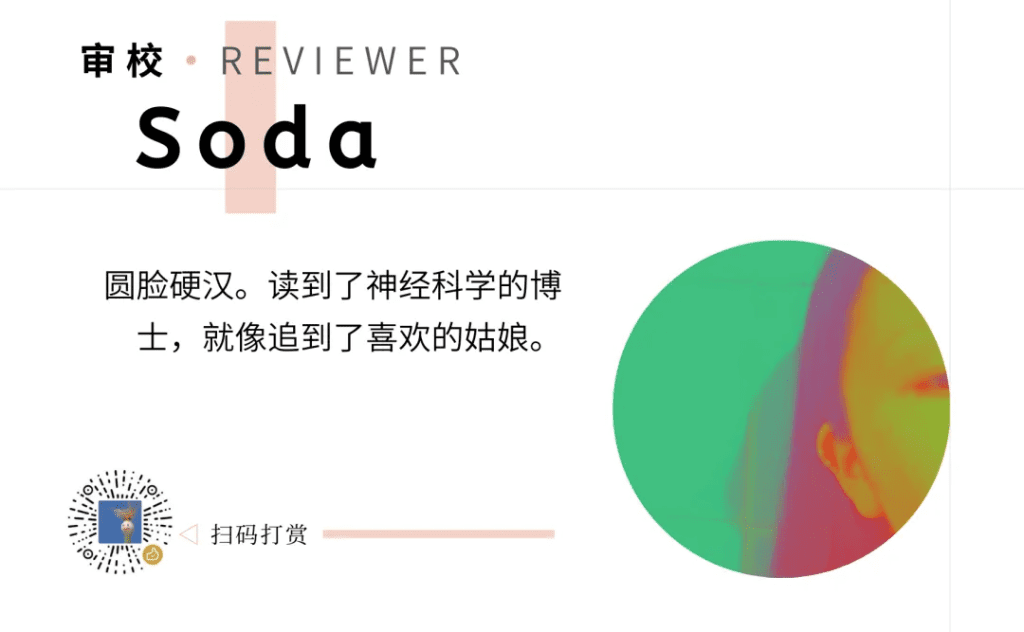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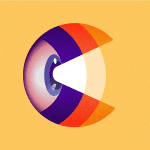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