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然,你告诉自己,一定存在着符合逻辑的证据。但是,无论多么努力地寻找,你都无法找到符合你所知现实的答案。当魔术的最后一幕上演时,观众看到了不可能的事情:一只鸟凭空出现,一个人开始在空中漂浮、飞翔,一个人的思想像书中的文字一般被读出。魔术师在做着观众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错觉的力量。就像美国魔术师西蒙·阿伦森(Simon Aronson)在1980年说的那样:“在观众不知道某事是如何完成的,与他知道某事无法完成之间,存在天壤之别。”但是魔术不仅仅是一种与不可能的相遇,还是与拼合现实世界的知觉机制的碰撞。
魔术的神经科学,本质上是对这些相遇和碰撞的研究。错觉在艺术中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被当做一系列聪明的小把戏,但是在这从不可能到可能的神奇转变背后,蕴藏着对哲学与认知科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解答,即揭示了我们于多种拼合的现实的生活方式的答案。
关于不可能之事的研究,都基于一种转瞬即逝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惊讶,即对标志着期望和现实之间差异的意外之事的回应。惊讶可能是痛苦的,比如当我们得知一个好朋友的溘然而逝;惊讶也可能伴随着喜悦,比如当我们中彩票的时候。无论惊讶的情绪效价是好是坏,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可以让我们直面意外的发生,促使我们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或者令我们不知所措,迷失在不确定的海洋中。要想见证惊讶的力量,最好的途径便是坐在魔术师面前,观察那沉浸在魔术中的观众。对研究魔术的神经科学家来说,惊讶揭示了魔术师是如何对我们大脑的功能加以利用的。而对于魔术师来说,惊讶则是他们用来交换不同形式的现实之间的货币。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艺术家德里克·德尔高迪奥(Derek DelGaudio)的节目——正在消失的砖块。在他最近的一个节目中,他讲述了自己六岁时的回忆——关于彼时得知自己的母亲是同性恋的故事。当他们那个保守的小镇里有人发现此事后,他母亲的车窗遭到了一块砖头的袭击。
德尔高迪奥一边讲述着这个故事,一边从身后的布景处拿了一块砖头,并通过纸牌搭出的一座房子将其逐渐隐匿。他优雅且随意地处理着每一张牌。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我们几乎可以预测他的行为、言语、动作和肢体语言。纸牌被慢慢地搭接起来,将砖块藏匿。没有什么能够为这故事带来波澜,也没有什么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对我们的预测做出挑战。总之,没有什么能挑战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这即是魔术师的职责:带领我们沿着充满确定性的寻常路走下去。
我们可以用阿瑟·叔本华[1]在《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中描述旋律的方式来描述魔术:一个“由始至终意义深远的有意铺排”。当然,直到一个似乎不可能的结局打破我们所有的期待。这就是惊讶!通过一个动作,德尔高迪奥推倒了纸牌屋。砖头不见了。观众瞬间呆住了,因为他们体验到了不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对于研究魔术的神经科学家来说,所有复杂的人类认知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场景中。尽管我们体验到的世界是一个连续的、无缝连接的整体——固体物体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但魔术和错觉表明,这种现实体验并不是事物真正的运行方式。世界不是严丝合缝的:我们生活在多重被拼合的现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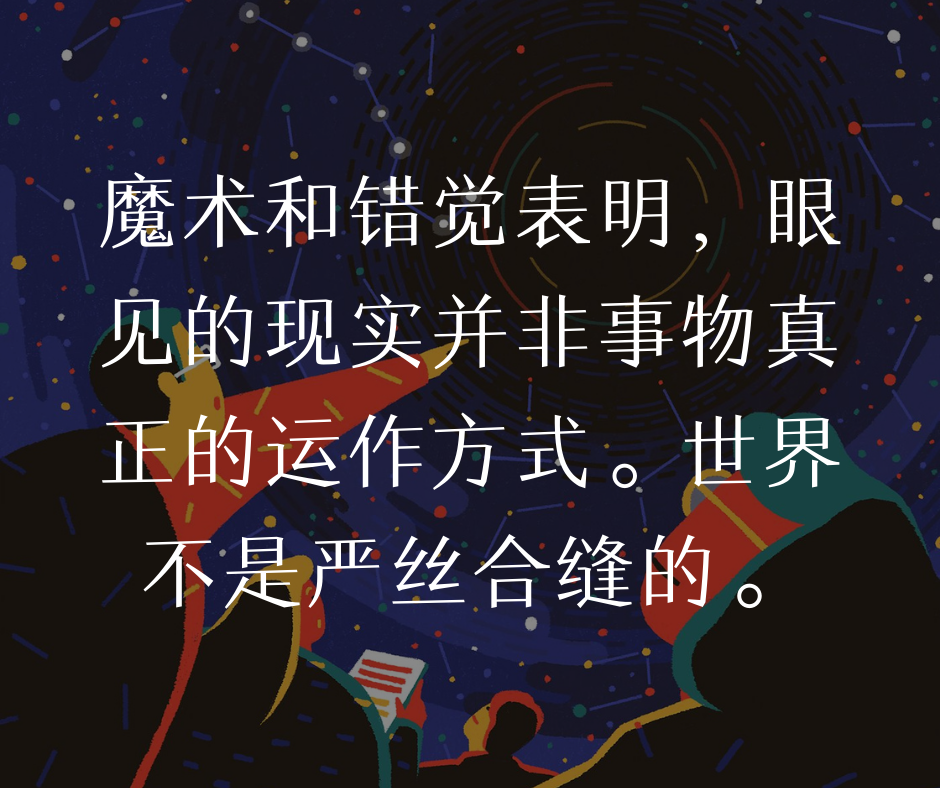
大多数神经科学家认为,视错觉或认知错觉,比如德尔高迪奥的消失的砖块,揭示了我们大脑回路的局限性。从这个角度来看,错觉(和惊讶)应为不可避免的错误。若非如此,我们由感觉接收到的知觉信息,应能重构出这个世界的完美心理意象。然而,现在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我们并非仅通过流入大脑的信息感知这个世界,我们似乎还会拼合并创造现实。我们主动地寻找、选择、忽略或改动大量接收到的感觉信息,意图依照我们所体验的世界构建出一个关于现实的心理版本。根据英国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2]所言,知觉是一个主动的、动态的过程[3]。当我们接收无缝流入的信息时,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期待正不断地进行着校准和更新。我们的知觉不过是我们用来解释我们所见的最佳猜测、假设或者预测。这些解释有赖于许多基础:不仅包括我们对这个世界物理特性的了解、对物体以及物体间动态关系的理解,还包括我们透过物种的演化历史、文化教育、个体经验和记忆所习得的每件事。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这些可能和不可能,均来源于这些解释。
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可能与不可能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位于我们拼合现实的概率连续体的两极。我们认为真实或可能的事,其实只是我们感知下最可能发生的事。这关乎于我们基于解释[4]而做出预测的能力。当我们没能正确地预测某件事——我们的最佳猜测偏离目标十万八千里时,我们会异常惊讶,这时常发生在魔术表演中。魔术师运用了这一点来干扰我们基于知觉所做出的预测。通过这么做,魔术师揭露了我们心照不宣地解释真实世界应当如何运转的方式。从某些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他们的一种“把戏”。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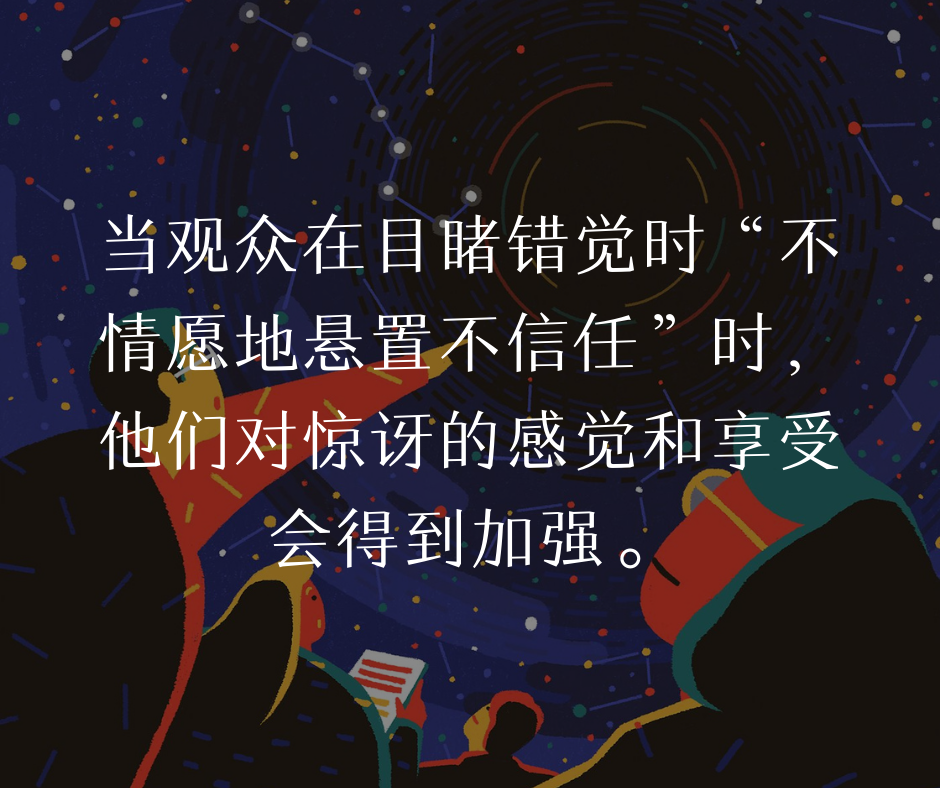
每个魔术师都栖居在两种现实世界中,一种是供以观众感知的,另一种是通过操控以成功制造错觉的。这两种现实永不相交,因为魔术师必须成为掌控物体可见与不可见的大师。难怪德国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玛克斯·德索(Max Dessoir)在1893年写道:魔术是一种对观众产生巨大影响的艺术,在观众面前,魔术师可以做任何事而不被察觉。魔术师能够骗过观众,是因为作为同类,他们与观众共享着人类的内隐知识——关于世界的规则、环境的物理学,以及对人类和社会习俗的深刻认识。魔术师能够骗过我们,因为作为观众,通过我们高效的预测能力,我们认为自己能够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仿佛我们才是在舞台上表演戏法的人。令我们惊讶的是,魔术师必须始终将环境与社会的知识牢记于心。他们必须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从而悬置我们的这种不信任。
小说作家、电影导演和演员经常做同样的事:他们要求人们暂时推迟对故事可能性的置评。但是这些艺术形式和魔术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美国魔术师特勒(Teller)是这样解释的:
在典型的剧院里,一个演员举起一根棍子,你会认为它是一把剑。但是在魔术中,那把剑必须看起来百分百真实,即使它百分百是假的。它必须染上鲜血。
对泰勒来说,戏剧包含着“愿意悬置不信任感”,而魔术则包含着“不愿悬置不信任感”——魔术是描述不可能事件的一种方式,仿佛这些事件真实发生着。我们用来预测现实的规则因目睹了错觉而开始遭到破坏。对于一个艺术家、作家或者魔术师而言,这种戏法其实就是了解该如何令人信服地打破这些规则。亚里士多德说,当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他们应该倾向“似是而非的不可能”甚于“似是而非的可能。”要使一种可能的情况看起来似是而非,只需要让其符合我们对世界的预期即可。在小说中,不可能的事情通过富有逻辑性和逼真性而变得似是而非。
1817年,英国诗人和哲学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提出,如果作家能给一个荒诞的故事披上现实的外衣,读者便会悬置他们的批判能力,并忽视故事的不可能性。小说家J·R·R·托尔金(J R R Tolkien)在他的文章《论童话》(On Fairy-Stories, 1939)中更进一步论述,他认为一个不可能的故事不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显得可信:它只需与作者所创造的虚构世界中的“第二现实”相符即可。读者或观众保持沉浸在那个第二现实中,如此一来,读者那基于对现实世界的预测得来的评断力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在特勒看来,这些都是“愿意悬置不信任”的例子,在其中我们允许自己接受第二现实。但当观众在目睹错觉而“不愿意悬置不信任”时,惊讶的感觉和享受就会增强。这便是魔术师通过创造一个第二现实所实现的事,但不同于小说中对不信任的悬置,这个第二现实不会打破对现实世界的期待——直到最后一幕。
要体验魔法,观众必须相信他们看到的是不可能但足够真实的东西,为此可产生丰富的情感体验。他们必须相信,他们所目睹的既不是幻想,也不是梦境,甚至不是错觉。当我们看到彼得·潘(Peter Pan)在电影中飞翔时,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是虚构的。然而,当我们看到美国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在舞台上飞行时,我们却会觉得飞行是真实的,尽管我们知道这并不可能。通过魔术,观众不必想象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种不可能已被体验为了真实。没有任何其它艺术形式或人类活动可以像魔术这样,为我们提供这种奇妙的体验。
译者:群山回唱;校对:Zen;编辑:eggriel
原文:https://psyche.co/ideas/for-neuroscience-magic-opens-a-doorway-to-multiple-realities
参考文献
1.https://psyche.co/ideas/what-arthur-schopenhauer-learned-about-genius-at-the-asylum
2.https://aeon.co/videos/your-body-is-scanned-destroyed-then-reproduced-do-you-live-on-the-copy
3.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097-017-9525-z
4.https://aeon.co/essays/consciousness-is-not-a-thing-but-a-process-of-infe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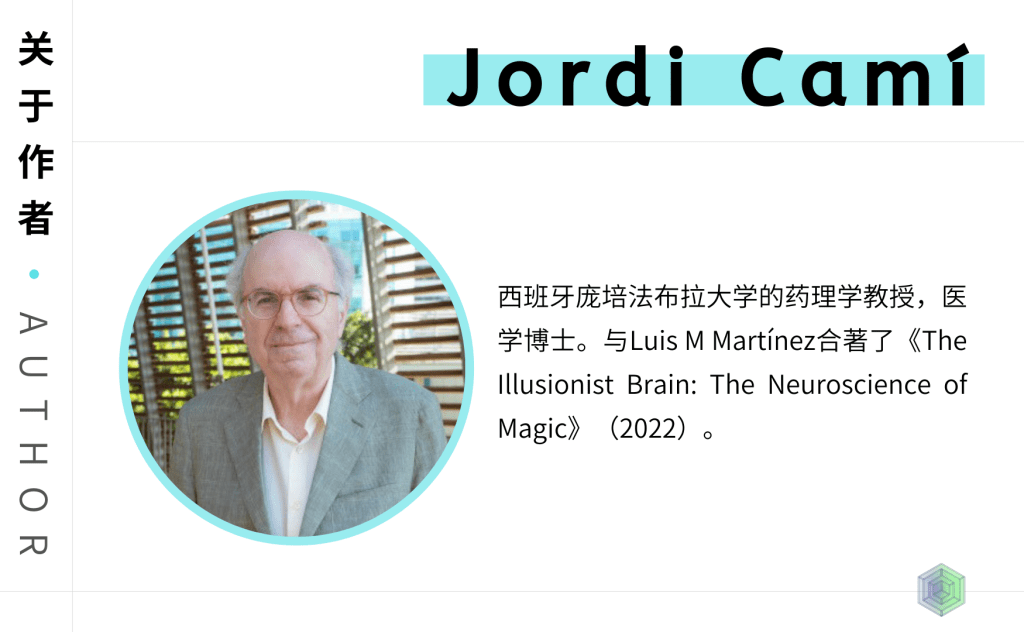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