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Summary
音乐不只是声音的序列,更是内部主观性以声音这种形式进行的有序表达。通过统筹节奏,和弦与旋律,音乐承载了我们的思绪波动,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行动。
每种已知的人类文化都拥有独特、带有节奏感的音乐。音乐组织时间,活跃人的身体,让人群在舞蹈、做音乐、工作时腾挪于时间。[1]和其他人协调配合动作可以带来纯粹的快乐,而音乐的律动(pulse)就是达成此事的一种方式。及时感知音乐的律动并随着节奏舞动我们身体的能力看似简单,但其下暗藏的复杂性不仅让音乐家着迷,还引来各类科学家的关注。这其中潜在的神经机制惊人地复杂,为揭示大脑如何塑造着我们的现实并连接感知与运动提供了新视角。溯流追源,本文整理这一机制几种可能的演化学源头。
那么,节拍是何时出现,又是如何出现的?我们的世界四处可见重复的规律;日落月出,昼去夜来,这些律动与生命相伴相生。跟踪和预测节律,如白天或黑夜的到来,对生物有适应的好处。而纵观自然界,将自身节律与昼夜周期同步十分常见。大多生物体会产生自己特有的节律,如运动系统、呼吸和心跳的节律。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振荡和同步,这种将运动输出与听觉输入同步的能力(比如人在跳舞、表演、或随音乐用脚打拍子)在其他动物中是极为罕见的。菲奇(W. Tecumseh Fitch)称这种现象为“节奏的悖论”。[2]
这里的罕见体现在至少两个层面上:首先是基本且常被注意到的——我们有神经连接使得听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相关联,然而这种对同步至关重要的连接似乎不存在于大多数动物中。这一连接赋予我们感觉运动同步(Sensory Motor Synchronization, SMS)的能力。但这不能完全解释人类所具备的带有节奏性能力。据认为,听觉系统与运动系统是双向影响的,这种理论为解释内部的节奏感知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也就是内在的节拍不仅影响我们对节奏的回应,还影响我们主动感知节奏的方式。[3] 我们认为这是人类节奏能力的第二个关键成因,称之为丰富节拍的感知和同步(rich Beat Percep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rich BPS)。两者不同于后一种能力可能包含更多步骤。它们之间的区别在文献中并不总是很清楚,而且大多数做比较和演化研究的都集中在基本的感觉同步上,而据我们所知,丰富节拍的感知和同步的存在尚未在其他动物中找到证据。
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着重于一个更深层次的起源问题:有哪些成因使我们祖先演化出了这些能力?将声音和运动联系起来是否因为它对我们的祖先具有生存价值从而演化而来?它是我们具有复杂情感和社交的大脑的副产品,还是一种能够带来愉悦甚至推动我们的思维发展的技术发明呢?
我们不能轻易下定论。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事实上是十分有限的,最早的乐器骨笛可以追溯到40000年前,这表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已经开始演奏调性音乐(tonal music)。[4]尽管如此,在研究音乐节律起源的理论时,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可供借鉴。它们包括在人类和其他动物身上进行的行为和神经科学研究——用以了解动物们有哪些及为什么会与我们有着相近的节律行为;文化间的对比研究——通过剥离我们的技术和文化发展,从而瞥见音乐和舞蹈如何在过去的人类社会中发挥作用。
丰富节拍的感知与同步(Rich BPS):
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观点
首先,我们要解释的是什么?这里我们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明(这些内容对于打击乐手或许是熟识的基础知识,只是用词略有不同)。归根结底,声音的节奏模式存在于外部世界本身,而节拍则完全是我们大脑内部的产物。我们的大脑能够找到声能时间模式的规律并进行预测。这些预测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感知和行动。也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的音乐和节奏是我们的大脑与外部声音互动的产物。我们的感受取决于感受者而不是外部信号本身。类似地,不同频率的光是因为经过眼睛和大脑的处理才成为颜色,所以我们看到的颜色与蜜蜂看到的颜色很不一样。节奏也一样,它的周期性取决于我们的感受。因此,关于节奏的认知科学研究都专注于从我们内部运行机制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预测能力。
节拍感知
众所周知,对于人类来说,当时间模式稍微具有一些不严格的时间特性,如有音符的持续时间成简单比例,或者有某种程度的周期性或重复,就能引发我们的律动(pulse)。律动让我们拥有一种特殊的时间感知——节拍感知。[5]这种对周期性输入或律动的连续感知是人类节奏体验的节奏核心方法。
律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我们对外部声音的处理过程中相对于我们的内在律动感知进行加工。面对一个听觉上相同的声调,我们感知上可以完全不同。内在律动让它们有不同的感知特征和不同的表现实现。节拍相关的感知也帮助记忆这些模式。这么看来,节拍不是全由声音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我们控制的。当我们听到高度切分音的旋律,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并且随着音乐律动用脚打拍子。尽管音乐有复杂的顺序和音符持续时间,很多可能一开始没有“在节拍上”。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用内部律动创造出高度切分节奏。当一组表演者共享一个内部律动的时候,他们可以协调他们感知和创造的节奏。
下面我们将梳理和展示一系列越发复杂的特征,它们组成了丰富节拍的感知与同步。我们将它们和感觉运动同步(SMS, Sensorimotor Synchronization)区分开,并记录哪些特征在非人动物中有所展现。
基础感觉运动同步
对节奏感知和创造的现代科学研究已发展超过一个世纪。[6]我们至今大部分工作的最基础方向和正统范式就是和等时声音的一拍一次的感觉运动同步,即每听到一声就动一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即使没有受过专门的音乐训练,在匹配动作(通常是手指打拍子)和节拍器的平均节拍时,都能达到只有百分之几的误差的卓越表现。有两个观察指出了内在律动的存在。首先,同步并不是一个反应过程,而是一个预测和提前行动的过程。同步动作往往在节拍器的节拍之前发生。此外,一开始与节拍器同步的动作在节拍器被拿走之后还能继续。
甚至简单地和他人同步也带有很强的情感和社会元素。同步是亲社会的,也就是说,同步的搭档会对彼此产生正面的倾向。小朋友更可能去帮助一个和他们产生同步的大人。[7]基础同步的能力基本上在四岁被发展出来。[8]在这之前。小朋友可能会对音乐有动作反应,但是不会同步。[9, 10]
基础同步的动物证据
大部分对于基础形式的一拍一次的感觉动作同步研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比实验上,并且已经在一些动物中发现,包括可以“同步合唱”(synchronous choruses)的一些品种的昆虫和青蛙。[11]对比试验的结果发展出了几种对于集体同步的起源解释,因为同步合唱的优势是可以增加空间上呼叫的范围,为了吸引配偶或者防御入侵,所谓的“灯塔效应”。[12]反之,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只表现出基础同步的有限的一些方面。
训练后的恒河猴可以匹配声音和视觉节拍器的节拍,但是没法和测试片段同步,打出的节拍永远在节拍器之后。这与人类的可以做到的和节拍器同时同时甚至在节拍器之前打节拍形成了差异。这个结果显示,尽管恒河猴能够按照规律性做出一些预测,他们对于有时间规律的声音的反应时间比起对随机的声音的要短[13](作为参考,虎皮鹦鹉如果使用相似的训练方法被训练也会有相似的结果),但他们并没有和达到人类一个水平的预测。[14]大猩猩可以被训练交替用键盘上的按键打节拍,但是他们的自发的打节拍较弱地受到节拍器的影响,只有对于他们一开始的自发打节拍节奏接近的有反应。[15]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被训练到会同步。对照实验的结果启示了一些理论,比如声乐学习假设(接下来讨论)还有“逐步音动演化假设”(gradual audiomotor evolution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我们的灵长类亲戚的感觉动作同步尚处于演化的初步阶段(相对人类而言)。[16]
节拍和分拍
和动物相比,人类在基础感觉运动同步上就有可观的灵活性:1)人们可以与一个广泛范围中的节拍同步,大概在30 bpm到300 bpm之间,[17]还可以预测性地跟随节拍变化。2)人类普遍可以改变同步的模式,从跟随节拍器的一拍做一个动作到随着一拍分成的小节拍做动作或者一拍做多个动作(打节拍)。比如说,两次一拍,或者每两拍打一次(我们称之为m:n同步)。二分法的分拍或者一拍多动作通常对非音乐背景的人来说也不难,[18]但我们的系统还完成更复杂的分拍,如复合节奏(polyrhythm)。[19]让输入输出之间存在一些机械上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中律动被选择和调整,使得输入不需要完全取决于输出。
复杂的时间模式,等级结构
第二个角度涉及到可以被表征和产出的输入输出模式的复杂度。与复杂的多部分音乐同步是表征的一个例子,而按照节拍音轨打出复杂的鼓点则是产出的一个例子。当然,复杂音乐伴随着复杂的动作,这是最常见的配置。但是,重要的是把它们连在一起的内部律动的存在。基础的声音感知做的处理包括声音分组,区分不同的声源,测量时间的频率。这样基本的处理在动物和人类新生儿中就普遍存在,[20]所以本身不是感觉运动同步的必要特征,而更像是一个提供了更多可以同步的声音呈现,使感觉运动同步拥有更丰富的附加功能。[21]
一个全面的呈等级结构的,具有韵律的节拍系统(体系)可能更进一步地需要人类的大脑处理语言的核心区域。假设认为这个区域更普遍的功能是设置了动作的嵌套等级结构,[22]同时也需要运动系统复杂性的关联发展。[23]对于动物来说,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和现实中的音乐同步的这个能力目前只在美冠鹦鹉[24],鹦鹉[25],和加利福尼亚海狮[26]中发现。其中至今只有美冠鹦鹉可以呈现有等级结构的动作模式——随着不同的韵律等级移动身体的不同部位(头,鸟嘴,脚),像人类跳舞一样。[27]
主动感知
第三个方面,我们认为对更全面的丰富节拍感知与同步有关的一系列行为至关重要,就是运动律动对声音感知的影响。负责运动准备的脑区的神经元会在大脑感知强节奏律动时被激活,有时甚至在动作缺失的时候也会激活,这一发现佐证了听觉和运动的模糊边界,[28]并意味着这个脑区对内在律动产生的重要性。通过研究对于一个模糊旋律的多种韵律诠释,我们发现律动可以影响声音反应。[29]我们提出了作为听觉预测的动作模拟(Action Stimulation for Auditory Prediction)这一假设来正式地形容这个观点。也就是动作系统对感知有因果关系,通过声音和动作律动的在顶叶皮层的互相转化。人类会有这一能力的原因就是在神经网络中存在活跃的双向连接。[30]律动对声音感知的主动的影响至今没有在其他任何动物中发现,尽管被测试的只有几个物种。[31]
人类专家和训练
尽管前文所述的所有机制都是人类所共有,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受隐性经验或训练的影响,这些能力的效能也会不同。比如说,对大多数非专业音乐人士,要让自己和一个节拍器、简单的分拍、简单且很有节奏的模式分别进行同步都很简单,而和更切分的模式同步要更为困难。[32]同样的,更复杂的m拍n个的多旋律的同步比例通常需要额外的学习才能掌握。通过主动感知,我们的内在律动影响我们听到的旋律。这种主动感知在我们听其他文化的,不熟悉的旋律时通常会受到挑战。只有通过经验的积累,我们才能开始理解那个音乐本意的律动结构。[33]很多初次尝试萨尔萨舞或西非舞蹈的舞者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主动使用身体来学习如何倾听律动。音乐的才能诠释人类建立、维持以及确定一个内在律动感觉的能力,甚至在那些有着复杂、流动时间关系的视听输入,主要的律动并非直接被表达和强调。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会进入其他层次的讨论,例如短期和长期记忆的参与,又如嵌套的旋律模式中的句法结构,以及关于旋律的感知与创造。值得注意的是,往往是这些方面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音乐,因此在人类音乐律动的演化起源中,它们最经常被直接讨论。
节拍感知与同步的起源
关于节律感知与整合的起源,适应论和非适应论的观点已拉扯许久。想要解开这个谜团,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的音乐行为是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得到了进化(演变)。整合节奏的能力是否为我们的祖先赋予了一些健康或生存优势,使那些具有感知节奏技能的个体能够更好地生存,并将他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另一方面,如果节拍感知与同步不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那么它会是一种源自其他适应却被我们用于感知声音的副产品么?
非适应论观点
最著名的非适应观点非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的“听觉的奶酪蛋糕”理论 (1999)[34]莫属。他认为音乐和节律是人类的一种技术革新,是为了刺激现有的听觉敏感性(对声音情感、语言、听觉场景分析等),就像发明芝士蛋糕是为了刺激我们对高脂肪和高糖食物的渴望。在这种观点下,音乐是一种毫无生物效用的奇技淫巧,感知节律是通过借用我们处理语言和其他听觉信息的神经环路实现的。但平克的观点因过于根植于现代西方世界人与音乐的关系而受到批评。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主要听取录制好的音乐。诚然,禁止一个人从iTunes,Spotify,或其他媒体接触音乐对个人的生存没有影响。然而考虑到音乐普遍用于激励和情绪调节,这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福祉以及在世俗事务和繁衍上的成功。而且在留声机出现之前的世界里,亦或在那些音乐和舞蹈表演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文化中,音乐只是快感技术的观点更不站得住脚了。
认知心理学家帕特尔(Aniruddh D. Patel)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35]。他认为尽管音乐是非适应性的,音乐对个体生存有显著影响。在帕特尔看来,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快感技术,而是一种“思维变革技术”,它对注意力和语言等更普遍的认知功能产生影响,并通过利用现有的奖励机制来引发情绪,例如奖励正确的时间预测。音乐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人类文化中的普遍性可以用人类对火的控制来解释。
*译者注
对火的操控技术可见于每种人类文化中。火提供了人类普遍重视的东西,包括烹饪食物、保暖和提供光源;一旦一种文化习得了这种能力,魔盒就此打开(there’s no going back),变革技术为人类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音乐也是如此,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以及身份认同的形成。(Patel, 2008)
关于节奏,帕特尔的“发音学习假说”解释了节拍感知与同步的出现是一个副产品,为了适应发音学习而出现;我们需要节拍感知与同步在听觉和运动系统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从而能模拟身随音动的调谐。[36]帕特尔认为,如果有种回路能够延伸到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声带肌肉组织,那么它就可能成为节拍感知与同步的基础。该假说预测只有能学习发音的物种(包括鹦鹉和海豚)应该有节拍感知与同步的能力。这排除了其他不学习发音的灵长类动物。
这个假设最初被证实,因为发现了第一种能与音乐节拍同步的非人类动物,一只名叫雪球的葵花鹦鹉*。雪球能不时地将头部的摆动与不同节拍的音乐同步,展示了从音乐中提取脉冲、并结合进运动的能力。[37]随后的证据来自一项对公共视频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为数不多能与音乐同步的动物有凤头鹦鹉、鹦鹉和大象,它们都是发音学习者。[38]而相对来说,非人灵长类动物无法做到这样的同步,这同样符合假说。加利福尼亚的一只海狮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同步能力,但这种动物不是已知的发音学习者[39],这可能与发音学习假说相矛盾;不过,由于海狮和属于已知发音学习者的海象、斑海豹有着密切的关系,矛盾是否存在还有争议。
*译者注
若想一睹雪球芳容,请移步油管BirdLoversOnly https://youtu.be/cJOZp2ZftCw
Bilibili 【葵花鳳頭鸚鵡「雪球」的舞技可能比你強!《國家地理》雜誌-哔哩哔哩】 https://b23.tv/2wUmXWJ
非适应性观点只占少数,这或许出乎意料。首先,这种观点不符合小规模文化中音乐的使用现象;小规模文化主要在仪式中使用音乐,如果音乐的发明是为了认知益处,那这似乎是一种相当迂回的认知转变方式。除此之外,不持非适应性观点的思想家似乎不论如何都无法抗拒这样一种观念,即音乐必须是一种适应,具有明显的生存或繁殖优势,因为音乐在人类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因为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音乐是人类所独有的,它的某些方面似乎是人与生俱来,而且与情感和团体紧密相连。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解释。
演化的简史
达尔文把自然选择定义为“变异有用即保留”这一原则。[41]在这里,“有用”指的是一种性状(trait)的变异可以延长个体存活的时间为繁衍后代创造机会。这一概念的背景是个体之间存在着自然发生的变异,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生存竞争ーー由于种群的几何增长,许多个体将无法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在当前环境中生存相一致的性状将在种群中变得更加丰富。(“自然选择”用“自然”对比诸如人工培育的“人工”。)那些适应生存的性状通常被称为适应性变化(adaptations),并被认为是由环境选择的,不过,这两个术语过于含有主动意味而不大能准确描绘演化的现象,我们应该在抛开词中通常意义上的能动性和目标导向的含义来理解它们。这个简单原则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在任何程度上放大性状(只要这些性状可以被遗传)。
达尔文接下来将性别选择定义为一种“不那么严格”的选择形式,不是根据生死,而是个体获得配偶的机会。雄性和雌性的性别选择性状往往不同,包括那些涉及性别直接竞争的性状(例如雄鹿角的大小)和涉及吸引异性的性状(例如孔雀的羽毛)。两种额外的选择形式经常被讨论,但是没有定论:一种是亲属选择,这解释那些以个体的利益为代价让亲属获益的性状;还有团体选择,这解释那些让大团体带来获益但可能不直接帮助个体的性状。团体选择很有争议,因为它认为团体是选择、突变和繁衍的单位(即,团体产生新的团体)。不过本文将回避这个有趣的论点。
我(J. Iversen)认为性状是可以在多种尺度上产生影响:人类个体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团体相连,因此可能有一部分性状可以提高个体在团体中的能力;如果这些性状对其所有者的适应能力总体上是积极的,那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到头来人不过是能够繁殖和提供变异的个体。事实上,达尔文指出,在自然选择的背景下,“在社会动物中,[自然选择]将调整每个个体的结构,以利于社会;如果每个个体能从这些有选择的变化中获利的话。”[42]这一解释对于我们理解节奏的社会属性来说,就足够了。
个体适应性理论
性别选择论
达尔文早先便预见了平克的怀疑,对此他回应:“就人类的日常生活习惯而言,创造乐符的能力和乐趣都不与一个人的正常生活有直接联系,因此创造音乐的能力必定是一个个体所具备能力中最神秘的能力之一。”借鸟类的歌唱,他认为音乐在我们祖先的求偶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文化的发展消除了两性之间的差异。米勒重申了这样的观点:音乐是一只聪明的群居类人猿通过复杂的声音表演而跌跌撞撞进入不可控的性别选择进化时产生的。音乐之于人就同达尔文理论中的孔雀尾巴之于孔雀。”就此米勒有趣地运用了一个比喻——摇滚小子们性生活丰富,但他们的寿命并不比一般人长(这么看,音乐对生存或许没有好处)。在生育控制出现之前他就推断这类强力手段将增强繁衍成功率。音乐表演成了伴侣质量的一个指标(但在演化中受限于“先前就存在的知觉与认知偏好”)。高超的音乐知识和记忆体现着耐力、身体协调能力和创造力(爱好新奇事物的物种尤其在意这个)。
反对性别选择理论的人认为这一说法太过严格,毕竟事实是两性都有音乐天赋(而大多数性别选择的性状只在一个性别中出现)。这不是大问题,因为如上所述这种差异可能在历史中被消除,又或者配偶选择是双向的。在许多小型社会中,性别选择理论不能解释音乐在团体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性别选择支持者倾向于追溯到音乐更多是单独活动的时代,这似乎是说法的主要缺陷。不过这个反对意见也不中要害,因为谁不同意音乐和舞蹈能以亲密的方式把我们介绍给一个人,创造吸引力,不论是在独自一人还是在团体之中?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吸引力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在一个团体中脱颖而出的能力,同时表现出与团体中其他人合作的能力。与一对一的交流相比,团体音乐制作可以成为在更大的团体中寻找配偶的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自然选择论:为适应生存
罗德勒(Juan Roederer)[45]认为音乐是一种声-情感模式感知训练工具,可以在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中提高婴儿大脑的复杂听觉模式感知,以适应语言和情感关系所需。缺乏这一必要能力的母亲和孩子在社会中将处于不利地位。这种观点并没有明确地涉及节奏或同步,但解释包含情感元素的音乐或能通过平衡和同步情绪来维持团体凝聚力。这种观点与帕特尔的思想变革技术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基于两足运动的理论
一些理论认为两足行走的特殊发展是节奏同步现象出现的原因。两足行走有许多生存优势,包括释放手和手臂以完成支撑身体以外的任务。与四足动物的运动不同,两足动物最高效的步态是等时的,有严格的左右交替。[47]因此,所有人类都永远能发出和听到等时节奏,并且能平稳地调节节奏。这可以解释同步的运动基质,也可以解释人类对步行节奏同步的偏好。不过,这并不能立即解释为何我们把运动和声音同步的现象。
里格尔(Mark Riggle)[48]的解释是同步的产生是奖励前庭和听觉的周期性输入的系统的副产品。这个奖励系统激励婴儿开始行走,奖励他们走出稳定的步态。拉尔森(Matz Larsson)[49]认为,双足运动为团体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的步行和跑步步态相匹配,以减少不同步的脚步所造成的连续听觉掩蔽。步态同步能留出安静的时间窗口,这样其他重要的捕食者和猎物的声音可以被听到。步态同步允许潜行,掩蔽团体,使团体更加隐秘地移动,这是生存优势。
基于照顾婴儿的理论
两足行走同样带来了劣势,骨盆的限制使得人类发展出了更小的产道,让尚处于早期发育阶段的婴儿无法自理。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yake)[50]提出,为确保双足母亲们能给予她们未成熟的婴儿所需要的长期照顾,一个鼓励机制得以演化,这种演化上的选择压力产生了一种结构化的有节奏的情感纽带。而这种纽带的建立要求个体能够预测他人的行动时机,并与之产生联系。这个最初的假设解释了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音乐性互动的持续使用,并且例证了一个更宏大的整体起源假说。嵌入在仪式和模仿的多模态框架中的节奏同步是整合情感、社会性和节奏的整体机制中的一部分。
团体适应性理论
节奏,社会群体的协调者和标识物
音乐通常是团体活动。布朗(Steven Brown)[51]认为,音乐的核心特征,如鼓励群体对一时间结构的同步,是实现这一点的有效方式。在小规模的文化中,音乐的共同参与使用强化了这种音乐中心使用的概念。因此,那就不意外了——许多关于音乐的进化论者都强调音乐能够创造有凝聚力的团体,有些人甚至认为音乐能够协调一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关键里程碑,[52]它使早期的人类能够形成更大的团体,利用共同协调的力量来缓解不可避免的社会紧张,避免早期的团体分裂。[53]
与音乐服务于团体这一观点并行的理论是音乐可以体现团体的质量,因为团体的合声大代表食物充裕,吸引雌性。默克(Bjorn Merker)[54]认为等时性群同步的出现是从黑猩猩“狂欢表演”的行为而来,这是在寻找果树时一种喧闹的团体狂欢。他认为,如果黑猩猩和人类的某个共同祖先能使发声同步化,那么总和起来的团体合唱就能向迁徙中的雌性更广泛地宣传自己食物充裕,吸引她们加入。这种“灯塔效应”也被用于解释其他物种的团体合声。他进一步假设,由于呼吸、发声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这种合声的速度可能与现代人能同步的步行速度差不多。[55]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灵长类动物的“鼓声”表演仅仅是个体发出的声音,通常以生物物理学上最快的频率发出(会让人想到一只圈养动物摇动笼门的样子),因此同步能力不太可能是以此发展而来的。
哈根(E. H. Hagen)和布莱恩特(G. A. Bryant)[56]认为,音乐是人类社会组织更高层次的核心: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情况下,音乐能凝聚团体。他们认为,音乐和舞蹈既是一个团体的标识,又是一个可靠的团体质量指标,能帮助一个团体与其他团体形成互利的联盟,从而支持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音乐和舞蹈表演的准备时间要比表演时间长得多,因此一个短小的表演可以即时、可信地传达团体的稳定性和协调行动能力。只有那些有足够时间和传统的团体才能准备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览。这个说法也解释了为什么有良好音乐性和鉴赏能力的人类将更好地传达一个群体的质量。这个论点与性别选择假说非常相似,只是基于团体。这种说法使用令人信服的人种学证据解释音乐和舞蹈在争取其他团体结盟上的作用,但似乎与大脑变革技术 (TTM,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of the mind)等非适应性说法同样吻合,认为生物适应性在演化中被基于先前能力而产生的文化创新取代了。
此后的方向
我们已经尽可能广地列出能解释人类以节拍感受节奏的假说。这些假说尽管显然不完整,但都十分迷人。每一个似乎都有不少于一次论证上的跳跃,并且大多数只专注于可获得的部分证据。我们得出一个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的结论,即所有假说都或多或少有正确之处:音乐和丰富节奏的感知与同步是许多单独成分的复合体,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描述简化了这一点。
每一种说法,甚至是非适应性说法,都假定音乐的功能方面是演化而来的,但对于是什么选择性压力在做选择意见不一。除了音乐的适应方面之外,人类显然还发明各式各样的传统音乐和舞蹈作品用作他途。解释人类的丰富节奏感知与同步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概念框架仍需完善,这些组成部分的神经机制也尚待发现。这里非常欢迎大家贡献自己的想法。
最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解释对丰富节奏的感知与同步如何演变的理论,并确定这一现象的各部分是可分离且各有各的演化目的,还是最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当然还有许多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如果团体性音乐活动能带来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这一现象没有在演化上出现得更频繁?是因为连接听觉和运动系统所需的神经变化很难进化,还是因为其他物种缺乏社会环境和必要的先决条件,使得这种联系具有任何价值?我们希望读者进一步阅读,并与我们一起探讨。
作者:John R Iversen; 译者:苏木弯、yy; 校对:汉那; 编辑:eggri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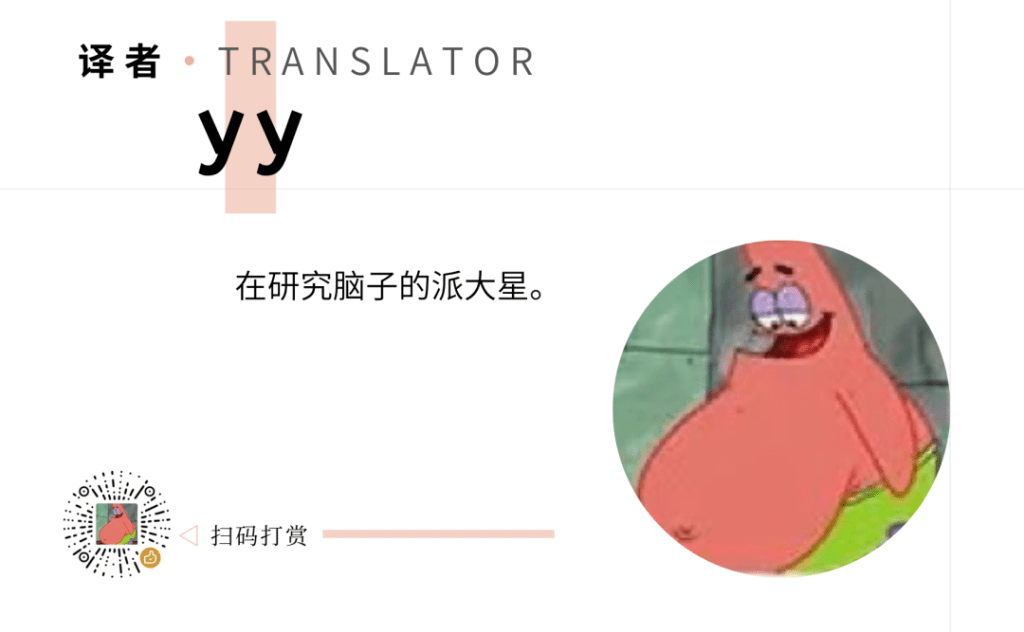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