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物种起源》(1859)中描绘了一幅生命演化图景的长卷。这幅长卷从生命的萌芽开始,沿着生理和心理,即身体和心灵,两条基本的轴线展开。他写道,所有生命(而不只是部分),在“肉体和心灵”方面都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发生演化的。达尔文预言,当心理学接受这种自然观时,心智科学“将会建立一个新的基础之上”,即“每种心智能力”必然会随着演化而得到发展。
达尔文猜测生命起源于单一的祖先“形式”,并推测它只有单个细胞。不久之后,德国、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们开始通过研究微生物来寻找其存在“心智能力”(感知、记忆、决策、学习)的证据。这三个小组的研究组长都注定会成就显赫。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是设计了第一个实用智力测验的心理学家,赫伯特·詹宁斯(Herbert Spencer Jennings)奠定了数学遗传学(mathematical genetics)的基础。这两位组长根据自己的研究承认达尔文是正确的:即使是微生物的行为也可以表明心智演化的存在,就像身体的演化那样。然而,马克斯·弗沃恩(Max Verworn),德国生理学界的巨擘,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继而,一场关于心智演化连续性的激烈争论被触发。这种连续性观点认为心智(人类意义上的“心灵”,其他动物中的“认知”)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发展和变化(实际上是数十亿年)。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20世纪初期兴起的行为/主义将行为作为唯一可接受的科学数据,并在此后几十年里避免直接讨论心灵从而削弱了这场争论。当“认知革命”在世纪中期兴起之后,支持不连续性的观点便被牢牢地确立下来。人们的普遍共识是,在演化的某个时间点上(并且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认知能力好像“噗”的一下就出现在一些动物身上。而在此之前,作为除语言外唯一认知指标的行为,就应该是完全天生的、机械式的、反射性的。尽管其看上去是由认知驱动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直至目前,这仍然是主流观点,并且完全基于人们“直觉上的”合理性。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是最早引用演化论的认知哲学家之一,他将自然选择称为“达尔文的危险想法”*,因为它表明在自然界中设计的出现不需要设计者,不管是神灵还是其他。就像他的很多哲学家与科学家同事一样,丹尼特不承认心智演化的连续性。然而,我认为达尔文这一被忽略的见解其实是他最激进的想法。这个想法可能在认知科学中引发彻底的哥白尼革命,并且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位置。
*译者注
Dennett, Daniel C. “Darwin’s dangerous idea.” The Sciences 35.3 (1995): 34-40.
哥白尼革命开启了一次人类视角的转变。1400年来,欧洲学者们一直抱持着普通人的观点,认为地球是天空围绕旋转的不动点。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将太阳、月亮、恒星和其他行星放置在围绕地球的嵌套水晶球中运动。1543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发表了一个详细的替代方案,用太阳取代了地球。我们的星球被罢黜了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与其他天体“漫游者”一同围绕太阳运动,而现代天文学也就此诞生。
同样地,达尔文的激进思想也废黜了人类与其他大脑在(西方)认知宇宙的“直觉显然”的中心位置。而在这个位置,达尔文放上了一个不断演化、具有认知能力的生命,它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变化条件下,努力生存和繁衍。从以智人(Homo sapiens)为参照的大脑中心论,到将生物学和生态学事实考虑在内,这一视角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结果是为这一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带来更精确有效的解释,而这对理解我们怎样成为人类以及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至关重要。

认知是什么?像很多其他心智概念一样,人们也没有在这一术语的定义上达成共识。这在130年前曾激怒过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此后也偶尔惹恼其他人。我是这么定义的:认知包括生物体熟悉、评估、利用和逃避周围环境特征的方法,以此来保障其生存繁衍。下面我从自己经历入手来阐述这一问题。
21年前,我还是一名做亚洲研究的博士生,我的研究集中在四个佛教命题上。我致力于将其纳入到辩论性西方哲学和科学分析当中。这些命题中隐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佛教心智观:心灵是什么、如何实现、它在无知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它经过训练后可以做什么。我在当时被称为认知科学(还只是独一门时)的领域内寻找西方文化中相应的比较对象……但什么也没找到。
除了四箱书和一部装满文章的笔记本电脑,我还收集了一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观点和相关的一系列争论,但这些都没能为拥有心智,或心智在行为中的作用提供现实经验上的解释。正如神经生物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在1998年意识到的(并且什么都没改变),神经科学已经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但却没有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它们。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仍然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尽管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那时的认知科学被三个(几十年前的)参考框架所统治,这几个框架构成了“认知主义”范式的基础:1)人脑;2)认为大脑是一个计算机器的信念;3)“认知是对表征的计算”的观点。第三个信条固执地拒绝简单解释,因为其核心概念所伴随的含混性也进入了该领域内(就好像原本还需要更多)。这一观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大脑中有一些可辨识的东西“代表”着世界的方方面面,就像是词语在句子中的作用。这些信息由尚未被发现的算法“处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考、计划、决策等等。除了对表征的加工外,不存在其他心智活动;认知就是这种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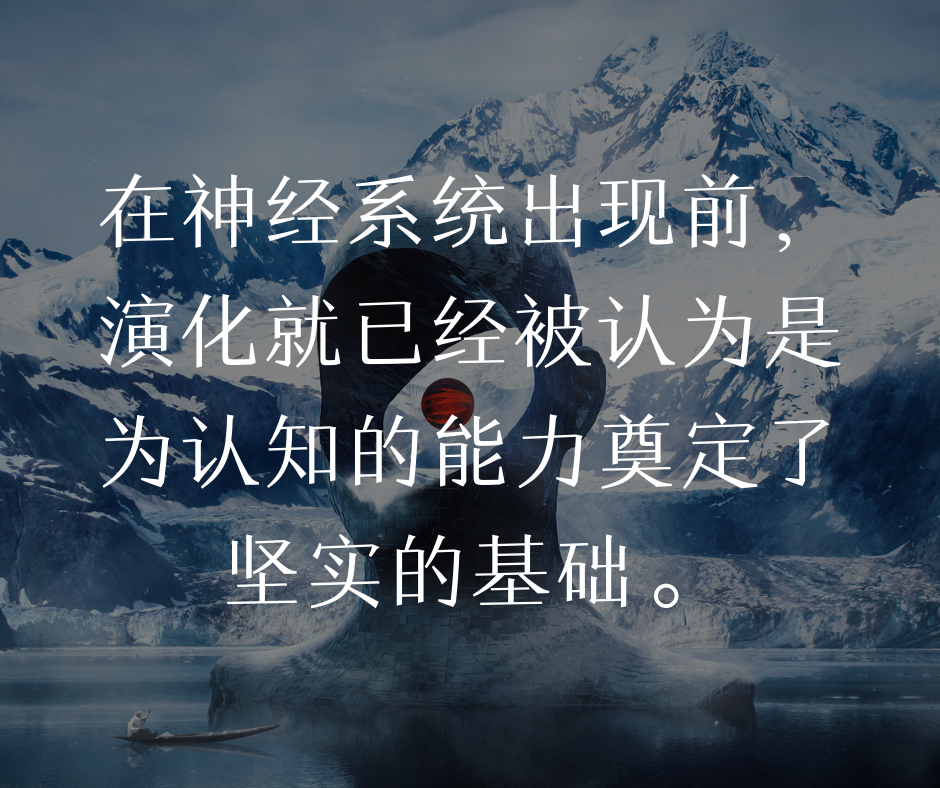
生物学和演化论,这两个我认为极为重要的视角,几乎没有一席之地;生理学、情绪和动机也是一样。那些认为动物行为研究对认知科学有所帮助的研究者们,才刚刚开始在这一领域发表文章,并且也没有受到同行们的欢迎。“具身”和“情景”(situated)认知正在获得关注,但更多是对理论显著性的承认,而非对整个连贯体系的认可。还因为缺少鉴别标准,生物学分类的任何特征都可能被当成认知。
但我仍然需要一个比较对象。我决定开始调查生物学,看它是否具有我认为必须持有的答案。我选择从生命之树的根基——细菌开始,来看看它们是否具有能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作“认知”的活动;20年过去了,我仍然在这片沃土上寻觅。
受一位非传统的澳大利亚生物学家所荐,我最初的理论导师是动物学家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和神经科学家翁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冯·尤克斯库尔的感觉世界(Umwelt)概念(1934年在英语中普及)让我理解了生物体周围世界的特殊性:生物体特有的诸种感觉构造了其周围的世界,并且生物体为这个世界中的元素赋予价值,而这个世界也会依赖于生物体的生存方式而发生演化。例如,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会吸引蚊子寻找血液,但对多数人类来说则会导致短暂的呼吸困难、眩晕和轻微焦虑(就像疫情期间佩戴口罩的体验)。马图拉纳的《认知生物学》(Biology of Cognition,1970)使我意识到,与地球上其他任何物理系统相比,生命是多么奇特。
在马图拉纳看来,生命是自生产的,而不仅仅是自组织或者自我维持。如果一架空客A380有着相同的能力,它就可以从环境中寻找、获取燃料并将之转化为物质和能量来源,以及制造其在飞行过程中正常运作(滑行、起飞、飞行、保持内环境稳定、着陆)所需的各种组件。这还没有谈及繁殖。马图拉纳对认知的说明集中在生物体与环境持续交互的需要上,这种交互使其具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能力。对马图拉纳来说,这一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域”就是认知,以至于“生命过程就是认知过程”(原文斜体)。我已经在细菌上满意地确证了这一断言。
认知主义要求作为交互域的认知发生不早于大脑的起源,而且很可能是在大脑起源很久之后才发生的。在马图拉纳看来(他是一名神经科学家),认知交互域发端于单细胞生命。神经结构只是增加了认知生物体和可利用环境的复杂性,但并不因此产生认知。支持马图拉纳观点的证据正与日俱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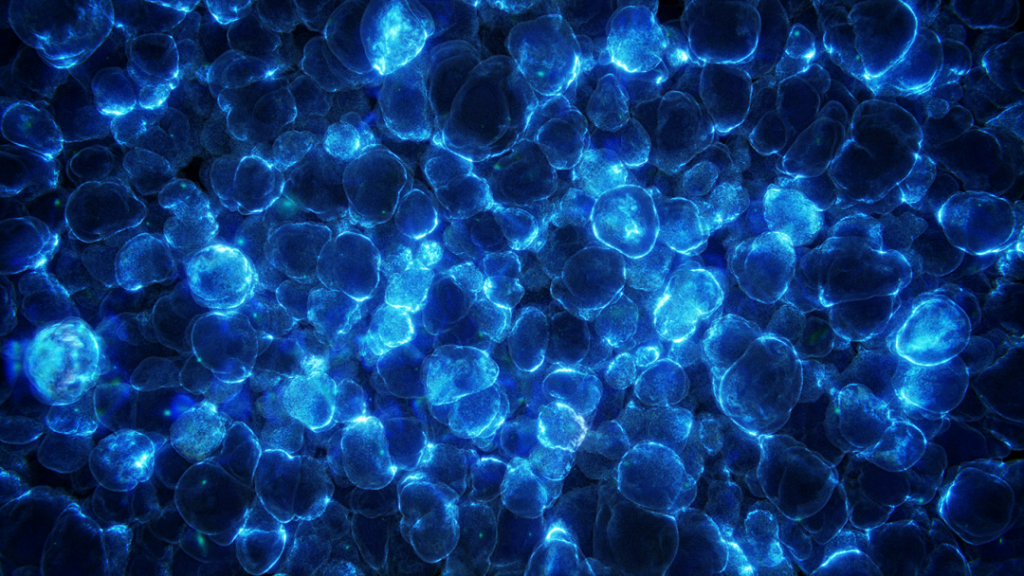
基础认知(basal cognition,研究不具有神经或具有简单神经系统的生物体的认知能力*)还是一个新生的研究领域。然而,已经有证据表明**,在神经系统出现前,即约5亿至6.5亿年前,演化就已经被认为是为认知的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感知、记忆、效价、学习、决策、预期、交流——所有这些原本被认为是人类的特质,都在各种各样的生命中被发现,包括细菌、单细胞真核生物、植物、真菌、不具有神经元的动物、具有简单神经系统的动物以及大脑。
*译者注
*Lyon, Pamela, et al. “Reframing cognition: getting down to biological basic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0 (2021): 20190750.
**Levin, Michael, et al. “Uncovering cogniti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on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1 (2021): 20200458.
然而,再多关于基础认知的证据也不能说服一个顽固的神经中心主义者。(你说的记忆、效价、决策是什么意思?这难道不就是一个定义问题吗?)达尔文的激进思想必须解决一些认知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哥白尼模型也是如此,直到日心说模型解决了托勒密模型所面对的不能预测或解释的发现,它才成为一场革命。这需要第谷细致完善的天文学观察,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基于光学望远镜改进后获得的观察所提出的理论,牛顿建立在前人工作(“巨人的肩膀”)基础上的引力定律。这总共花费了144年。
达尔文关于心智进化连续性的理论比这更古老,但也更接近人类身份的本质。毕竟,“智慧”就在我们物种的拉丁名中(“Homo sapiens”中的“sapiens”意为智慧)。拥有一个聪明的、理性的心智,被认为是人类的定义特征。相比起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心理学,接受一个日心说的宇宙可就算不上什么了。但其实,我们或许并没有选择。
认知神经科学要想理解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必须克服它目前所面临的几个挑战,而这是理解认知能力何以从这些系统中产生的先决条件。下面概述了三个挑战。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需要的是更简单的模型系统,以便帮助我们发现生物体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驱动因素,而这些发现可能意味着其背后存在更基本的原理,并且能够在更复杂的生物体中进行验证。
神经科学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与大脑或神经系统的“功能单元”有关。一个多世纪以来,单个神经元一直是大脑活动的结构单元和功能单元。认知科学的先驱者们将神经元学说作为大脑假定的计算能力的基础,每个神经元被认为是一个类似逻辑门的开关,可以将信息“数字化”(变成1或0)从而进行“编码”。单个神经元被假定执行复杂的编码任务,包括空间中的地点/场所、朝向、位置;一项诺贝尔奖曾被授予此领域的研究*。
*译者注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John O’Keefe、May-Britt Moser和Edvard I. Moser,获奖理由是“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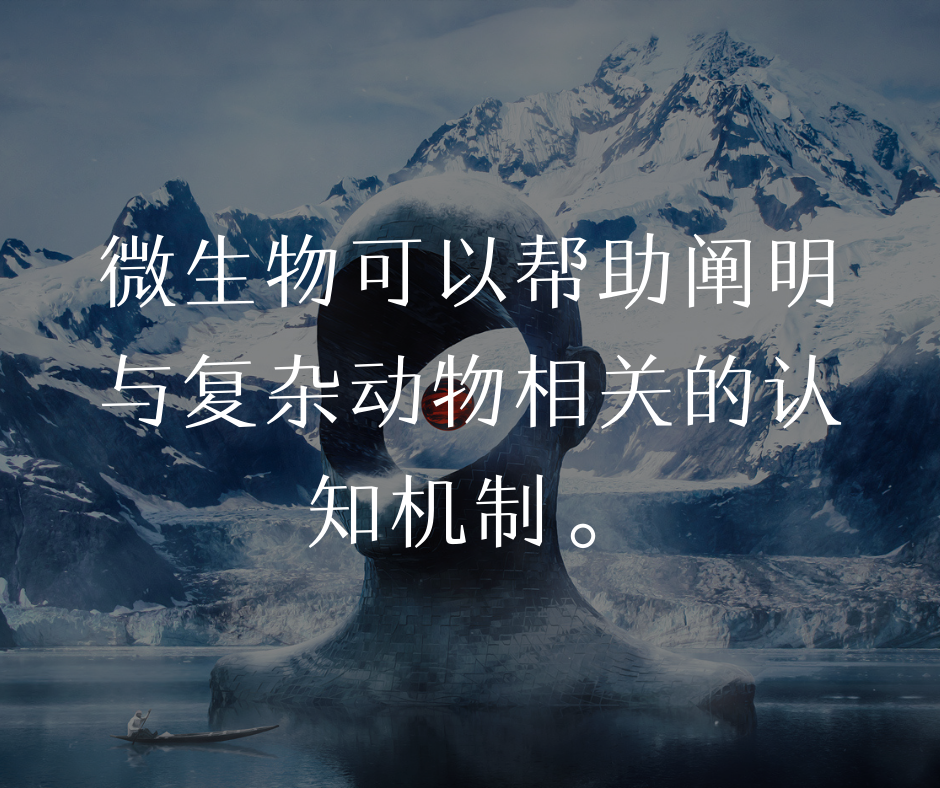
但有两个发现动摇了这一说法。一个是人类大脑内不同类型细胞的数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存在不少于75种不同的细胞*:24种兴奋型、45种抑制型以及6种非神经元型。它们有什么功能以及怎么交互仍然不清楚。另一个是现在已经清楚的观点,即神经元群(集合、网络和/或回路)更可能是功能活动的单位。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定义一个神经元集合、网络和/或回路,以及理解它们怎么形成和交互、它们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怎样以及是否嵌套在层级中、怎样产生行为。这些都是仍在进行中的主要工作。
*译者注
Hodge, Rebecca D., et al. “Conserved cell types with divergent features in human versus mouse cortex.” Nature 573.7772 (2019): 61-68.
要理解神经元回路的形成和功能,需要将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其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神经科学家拉斐尔·尤斯特(Rafael Yuste)将水螅(Hydra vulgaris,一种具有已知最简单神经系统的淡水动物)作为模式动物来研究神经元回路。这一决定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当这种微小动物伸展触手去捕获食物,或者收缩成一个小球时,它的整个神经网络就会同时被视频成像*,这样不同的神经回路就会对应到不同的行为上。得益于水螅的再生能力,研究者们通过对离体细胞再生的观察,已经识别出水螅从神经元生长到全身多个神经网络整合的不同阶段渐进序列。然而,水螅行为的生态学意义仍然晦暗不明,要理解某些行为(对生物体)的意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神经活动的动态(生物学)逻辑。
*译者注
Entire nervous system of an animal recorde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y neuron in a hydra has been seen firing. The breakthrough helps us understand basic behaviour and could lead to us unlocking the secrets of our own brains. Read more: http://ow.ly/7ePi30aLPhe
细胞集群内的协调活动既需要认知,同时也有可能构成认知——虽然说这一观点的转换并不容易与认知主义的信条“对表征的计算”相一致,但这在生物学中已经获得了普遍支持。对于细菌(例如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黄色粘球菌[Myxococcus xanthus])和阿米巴虫(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这类生物,研究者们已经就由数千个相互作用的自主细胞协调的复杂行为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在枯草芽孢杆菌菌群上,研究者们发现了借助于离子通道实现的长距离电信号传递(同样也是神经元电信号传递的机制),这为微生物帮助阐明与复杂动物相关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这一研究结果也进一步导致了原先未知的细菌集体行为的发现。这种集体行为类似于大脑活动的某些认知类型,包括记忆。对由电信号介导的细菌行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细菌信号转导蛋白之间的网络活性在25年前首次被描述。到今天,信号蛋白大型阵列的网络特性已经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这种特性常见于那些依赖鞭毛在化学梯度间定向移动(趋化作用)的细菌。在高度保守的进化过程中,这种结构被比作“纳米脑”并不夸张,因为它以一个网络的模式工作,能够处理大量信息,对环境中的微小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它位于细胞的前端就像是细胞的“头”,虽然这个头会随着细胞方向的改变而变换位置。
这些阵列所能处理的信息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多。最近发现*,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会拒绝垃圾食物,因为那会让它们生长延缓。趋化作用(即趋向或远离某些状态)是大肠杆菌最消耗能量的行为之一;但令人困惑的是,它们会放弃跟前的食物(即谚语中的“在手之鸟”)转而在其他地方继续寻找更有营养的——这种策略通常是有效的。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一种具有小型脑的蠕虫)也会这么做。如果它过去是以高质量的食物为食,那么它也会舍弃低质量的食物并期待找到更好的。这样的发现在当时是相当震惊的,因为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需要一种“更高阶”的决策能力。
*译者注
Ni, Bin, et al. “Growth-rate dependent resource investment in bacterial motile behavior quantitatively follows potential benefit of chemotax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1 (2020): 595-601.

神经科学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由一个史诗般的科学成果带来的,它揭示出了“令人震惊的失败”。秀丽隐杆线虫大脑的接线图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起始于认知主义鼎盛时期的项目*。线虫的302个神经元间的连接被绘制出来,并且定义了与大多数细胞类型相关的行为。然而,这一惊人的成就并没有揭示出线虫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如此行动——这原本是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据神经科学家科里·巴格曼(Cori Bargmann)的说法,秀丽隐杆线虫的研究“表明(神经)接线图并不是一套明确的指令,我们不可能直接阅读它。”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译者注
2021年发表于Cell的文章。参考Taylor, Seth R., et al. “Molecular topography of an entire nervous system.” Cell 184.16 (2021): 4329-4347.
首先,在更真实的生态条件下,生物体的行为方式有悖于以往通过基因敲除在特定神经元(感觉、运动、整合)和特定行为(前进、后退、进食)之间建立的因果联系。相反,单一行为可能由几个不同的神经回路引起,而一个回路可能会在不同情景中触发不同、甚至相反的行为。总之,一个接线图要比原来所设想的表示更多潜在的行为方式。
其次,环境和生物体的内部状态对行为的影响要比最初认为的重要得多。环境和内部状态的信息被认为由生物分子(神经递质和神经肽)进行传递,尽管具体机制并不清楚。这些信号分子(大部分由神经元自身产生)可以改变神经元功能,从几秒到几分钟、几小时不等;可以与其他目标(其他神经元、肌肉细胞、腺体)作用;以及激活或抑制整个回路。秀丽隐杆线虫会产生100多种这样的分子。
在细菌和单细胞真核生物(相比于细菌有明确的细胞核)中,成千上万个体间的协调活动——相当于多细胞水平的行为,也要借助于信号分子。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感应。群体感应分子也被比作是激素,因为它们通过类似的机制来改变生物体的行为。就像动物和植物当中的激素那样(神经递质和神经肽的活性没有区别),微生物细胞产生的信号分子通过四种方式诱导行为改变:1)作用于产生信号分子的细胞内部;2)通过细胞接触作用于相邻细胞;3)作用于细胞周围区域;4)作用于远距离外的细胞。单细胞信号分子其实有很多,只是要远少于多细胞生物。

神经科学面临的第三个挑战不是范式的失败,而是来源于意料之外。传统观点认为,认知过程完全是反应性的:外部世界的某物作用于生物体(输入),导致其作出反应(输出)。这种输入-输出观点正是认知主义的基本思想。上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在缺乏外部刺激时,大脑也存在自发的、持续的活动,这在最初被认为是成像技术造成的伪迹,之后被看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现在则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被定义为,大脑内在清醒静息状态下活跃、在任务导向行为时不活跃的功能连接区域。黑猩猩和老鼠就表现出默认模式活动。在人类当中,默认网络失调则与精神障碍有关。这也意味着它对认知功能的重要性。
大脑内的自发振荡远不止默认模式网络。神经科学家尤里·布扎基(György Buzsáki)——他正在努力吸引人们对“大脑节律”的注意*,他认为这种大脑活动并不是系统噪音,相反它“实际上是我们认知能力的来源”,并且可能是大脑对“神经元信息的基本组织者”。自发低频振荡不仅在水螅上被检测到,还存在于许多生物体上,包括植物、单细胞真核生物、细菌,以及多种动物。如果这种振荡是生命活动的中心组织者——就像艾莉森·汉森(Alison Hanson,尤斯特实验室的驻院医师)所猜想的那样**,那么显然,神经元就不会是产生振荡的必要条件。
*译者注
*Buzsaki, Gyorgy. Rhythms of the Br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nson, Alison. “Spontaneous electrical 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 a possible role in Hydra and all living system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0 (2021): 20190763.
振荡是由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产生的,这种现象被发现遍及整个生命界。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的实验室已经证明*,离子通道产生的生物电在动物身体再生的“模式记忆(pattern memory)”中起着关键作用。无头涡虫可以再生大脑,蝌蚪可以再生尾巴,成年青蛙可以(借助诱导)再生功能型后肢,电刺激还可以让一些部位长在它们不该在的地方——例如让蠕虫的第二个头长在其尾巴的位置处。对莱文来说,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接受即使组织中的细胞也继承了其单细胞祖先的某些决策能力这一观点——他称之为“认知透镜(cognitive lens)”,可以为发育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科学、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领域等诸多领域带来新的转变。
*译者注
*https://ase.tufts.edu/biology/labs/levin/research/index.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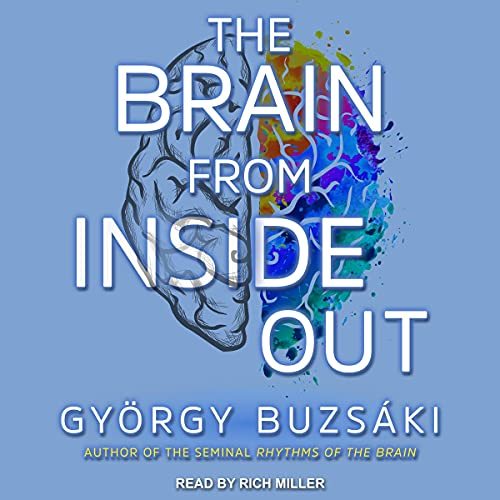
我们需要的是视角的转变。在《从内向外解析大脑》(The Brain from Inside Out,2019)这本书中,布扎基认为很多神经科学面临的困难问题根本上受制于“人类构建的关于心/脑怎样运作的观念”,这些根据几千年来的哲学和科学猜想建立起来的观念,现在则被用于解释观察到的大脑活动。这就是他称之为“由外而内”的视角:“主流神经科学的主导框架表明,大脑的任务就是感知和表征世界、处理信息,以及决定如何反应……一种‘由外而内’的方式”。这也是马图拉纳所说的“观察者依赖”,从观察者的视角出发而不是被观察的系统。自发活跃的大脑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布扎基认为,从系统的视角去解码其产生活动的逻辑(即“由内而外”)应该是神经科学的主要任务,而不是将人类的猜想对应到神经元的观察结果上。
我在15年前做了一个类似的区分。我把基于人类经验和反思所形成观念的认知视角称为人类启始(anthropogenic)进路,也就是布扎基说的“由外而内”。尽管认知主义断言,认知可以被不同的物理形式所实现(包括机器人),但这种方法仍然是人类启始的,因为它源于人类的算数能力。与之相反,我称为生物启始(biogenic)的进路则将生物存在模式作为认知的来源,这意味着“由内而外”的视角*。
*译者注
Lyon, Pamela. “The biogenic approach to cogni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7.1 (2006): 11-29.
如果理解人类认知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这种生物启始的进路才是最有前景的方向,它会带领我们超越现在这条蹒跚难行,又望不到头的歧路。在过去70年间,大量公共和私人基金被投入其中,更不必说人们的才能、时间和精力,到如今我们本应该获悉更多关于认知是什么、怎样工作的理论知识,而不仅仅是来自于大脑活动的简单数据。想想自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社会发生了多大的转变。有多少教条已经崩溃和废止?在这么多领域中,我们学到了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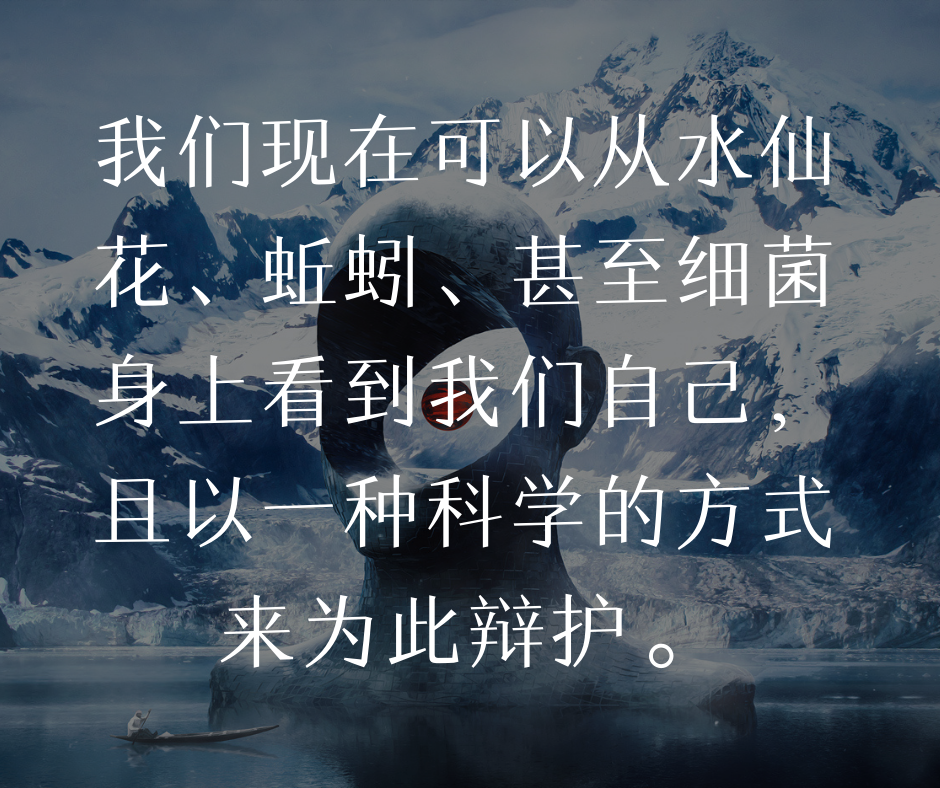
人类基因组计划本应该产生一个基因的“蓝图”,但当第一份草图在21年前发表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还有那么多是我们未知的。例如,有太多所谓的“垃圾DNA”确实是垃圾;人类与植物基因组有着惊人比例的重合;在我们的基因组中还携带着单细胞生物转移来的基因。随着整个基因组越来越多地被比较,我们发现在自己与植物所共享的基因中,有一些与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有关,也包括我们人类。此外,对人类生存最重要的系统之一,也就是在个体细胞层面自主运作的免疫防御机制,同样在大约数十亿年前继承自细菌或者其姐妹王国,古菌。事实证明*,记忆和学习的正常功能依赖于神经元与免疫刺激因子(细胞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真正的,不测。20世纪50年代(以及之后),大脑一直被认为具有“免疫特权”;免疫系统不能监视大脑。
*译者注
Lyon, Pamela. “Stress in mind: a stress response hypothesis of cognitive evolution.” Developing scaffolds in evolution, culture, and cognition. MIT Press, Cambridge (2013): 171-190.
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掌握认知的基本原理:不同感觉是怎样整合成一个世界的;记忆在哪里以及如何储存,是否能保持稳定,检索如何改变记忆;如何做出决定,以及指挥身体行动;如何评估效价。
效价是生物体为自身和/或周围事物所处环境赋予的价值,如有利、危险或中性。效价在情绪中的核心作用已经被确立。正在形成的共识认为,人类情绪从根本上参与了身体对其基本功能的调节。近50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了细菌会朝向特定(有利)物质移动,并且设法躲避其他(有害)环境。理由细菌行为的效价机制,会有助于阐明在更复杂生物体中情绪是怎样引起行为的吗?除非我们对此开展研究,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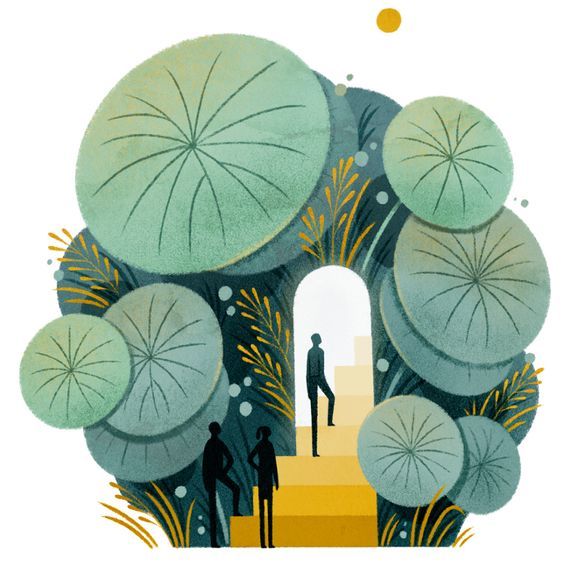
在《物种起源》的结尾,达尔文描绘了一个“树木交错的河岸”(tangled bank):在那里,演化进程中的自然选择法则,与当前动植物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这两个因素看似毫不相关,实则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了生命。达尔文认为,所有生命在深层次上都是彼此相关的。我们现在以一种达尔文只能够想象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们拥有着不可比拟的复杂工具,有着对进化原理更为丰富的理解——包括发育可塑性、表观遗传、全基因组改变,以及单基因突变,是这些为自然选择机制的奏效提供了遗传变异。
“这种视角下的生命当是伟大的。”达尔文这样写道,他说得没错。我们现在可以从水仙花、蚯蚓、甚至细菌,还有黑猩猩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并且是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为此辩护,而不需要任何神秘的面纱或拟人化。我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共同的基因,我们通过共同的机制来亲近这个被感知到的世界并为它赋予价值。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存,相互依赖,茁壮成长并繁衍生息(对其中一部分来说)。我们都生活在这座星球上,尽管它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太阳系也不是,但它是我们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
是时候接受达尔文的激进思想了,就像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从更简单形式的身体演化而来一样,我们的心灵也由更简单的心灵演化而来。身体与心灵一同演化至今,并将继续如此。
作者:Pamela Lyon | 排版:济一
译者:晏梁 | 校对:eggriel
编辑:杨银烛 | 封面:Shahan Keu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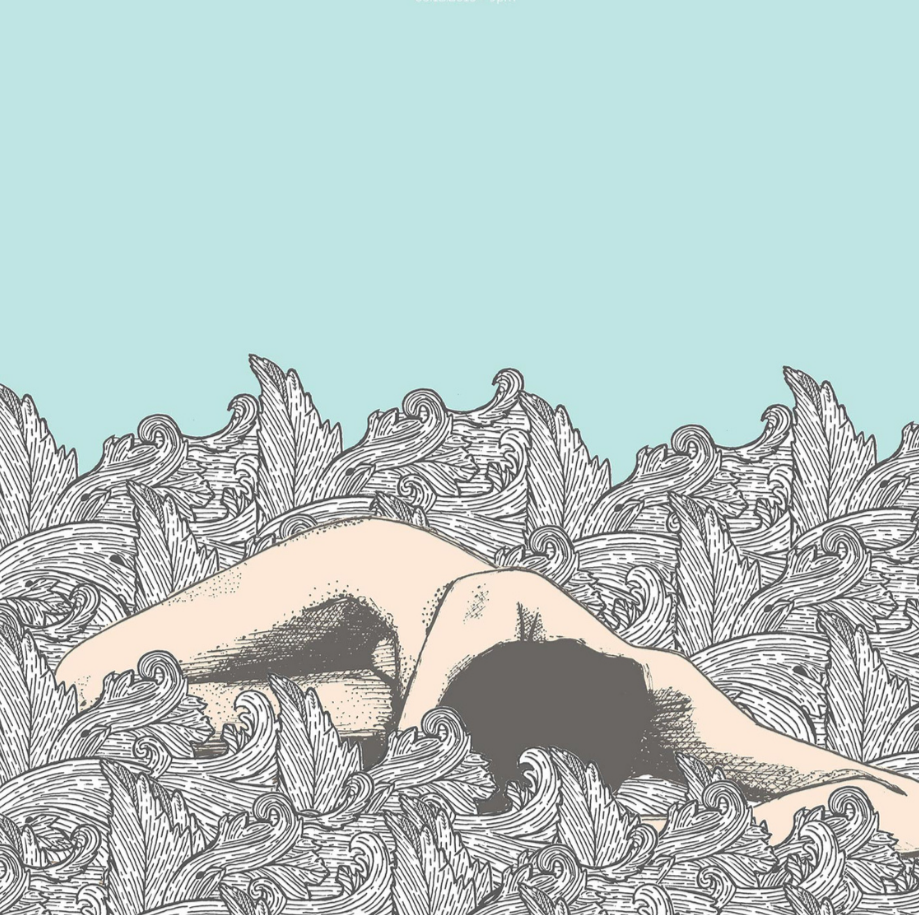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