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之意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思想和社会互相塑造,并形成了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它也许能为女性主义提供一个突破性的新视角。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思想和社会互相塑造,并形成了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它也许能为女性主义提供一个突破性的新视角。
我们被生命的痛楚与颠簸所束缚, “生活就如同骑在野马上挣扎” ,维吉尼亚·伍尔夫在她1931年的作品《海浪》中这样写道。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有人不这么认为。
出生在俄国的科技创业者,瑟尔基·法吉(Serge Faguet),自称是一名“极端生物黑客”。他想要像驯服一匹野马一样,驯服自己体内的生物化学机制:通过长生不老药一般的药品、植入物、医疗监测装置以及行为学“奇技”,来最大程度地优化自己身体中的生化反应。他的个人追求是成为“摆脱生物学极限,遍布宇宙的不朽后人类神”之一。在这场个人征途中,法吉自称已经花掉了将近二十五万美元。他的开销中,还包括花钱“与时装模特性交,这样就可以省下约会时间,把精力放在其他更要紧的事情上”。
对法吉的这种做派不屑一顾很正常:他这样显摆特权的荒诞作风,像瘟疫一样席卷硅谷。除了法吉之外,企业家伊隆·马斯克,谷歌的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以及哲学家尼克·波斯托姆(Nick Bostrom)等“超人类主义”信徒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翘首以待“极乐升天”。
这些超人类主义者心目中人类的理想状态,如同达芬奇画笔下的《维特鲁威人》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版本:一个装备着认知强化、躯体强化的超级人类个体,已经升级进入了一种力量与权力均无懈可击的状态。这个超级人类斩断了一切依靠,甚至无需劳烦女性就可以繁衍后代。在这些超人类主义者的蓝图中,“不朽”听起来就像是大男子主义横行到了未来一样。
但是,超人类主义者的警示意义并不在于它暴露了富有白人男性的傲慢。而是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范式案例:当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思想沉积而成的特定心态登峰造极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对于肉体的恐惧、对于超脱肉体的渴望,深深吸引着自柏拉图起世世代代的哲学家们。这样的渴求与对女性的恐惧、对控制女性的欲望齐头并进。

在对话录《蒂迈欧篇》(Timaeus)中,柏拉图将他心目中理想的、非物质的形式比作纪律严明的父亲。这位父亲将秩序强加于所有难以管控的物质的“事物”。然而这些事物,正好是“所有被创造的、可见的、可觉察的事物的母亲与载体”。在这一段论述中,柏拉图使用了一种陈词滥调来抑制对于肉体的焦虑:把心灵(理性的、超然的、神圣的、符号意义上象征男性的),从肉体(情感的、混乱的、孱弱的、符号意义上象征女性的)上凿下来。
柏拉图的精神遗产流传到了中世纪,而形式与物质之间的分裂也奠定了基督教的道德特征。人们认为,人类拥有不朽灵魂。这颗不朽的灵魂受到理性与克制的庇护,免受尘世欢愉的堕落影响。作为男人性欲的假定目标,女人与女性肉体则自然背负着符号学意义上的罪恶重担。比如说,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就惩戒过自己,因他年轻时曾反复屈服于淫欲冲动。他在《忏悔录》中写道:“那个不检点的女人看见我魂不守舍,用肉欲之眼引诱了我。”
随着现代性与启蒙运动,这种超脱物质的渴望演变成了一种科学与理性的自觉探索。精神上的超越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如何在自然世界中“一览众山小”。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博学家,也是科学方法论的先驱。他尤其喜欢使用带有性隐喻的意象来捕捉自然与其观察者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心灵与自然之间建立一段贞洁合法的婚姻”,他在1608年出版的《哲学的反驳》( The Refutation of Philosophies)中这样写道;自然,毫无悬念是这段婚姻关系里乖巧的妻子。对于培根来说,“优秀的科学家是一位殷勤的追求者”。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哲学家吉纳维夫·劳埃德(Genevieve Lloyd)也曾在1984年出版的《理性的人》(The Man of Reason)里写道,自然是“神秘的、冷漠的,但最终无论如何,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可知的、可控的”。
这也难怪女性主义思想家们常常对“理性至上”表示怀疑。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按照一张性别色彩浓重的蓝图修筑的。不过,这些思想之间的和解也许近在咫尺了:在女性主义者对心灵与物质的二元分割进行批判的同时,一些哲学家与科学家正在试着把这两者重新联结在一起。关于人类认知的新发现与新理论都表明,像肉体、情感与欲望这些被部分女性化的领域,不仅仅影响了我们思考的方式,它们同时也是组成思想本身的重要元素。所以,尽管有些人可能依旧在期望逃脱我们充满缺陷的肉体,但我们至多只能达到美国生物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说的“接纳烦恼”:不用逃离、不用超脱,与我们麻烦的身体好好相处便可,然后慢慢突破身体的限制。
在女性主义者对心灵与物质的二元分割进行批判的同时,一些哲学家与科学家正在试着把这两者重新联结在一起。
我们对“思想”的看法是充满政治色彩的。这一点在现代心灵研究的伊始就有所彰显。1643年,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在写给勒内·笛卡尔的信中质疑了笛卡尔对于认知的解释。她那种自轻自贱的姿态,每个曾大胆批驳权威的女性都很熟悉:她们都知道,开始争辩的最佳方式通常是先安抚他们的自尊。
不幸的是,伊丽莎白认为她家庭生活的节奏根本不允许她拥有冷静的沉思;笛卡尔宣称,这种冷静的沉思是哲学研究成功的关键。伊丽莎白写道:
家族的生计(我决不能忽略),人与人的交流,还有我的社会责任(我无法避免),在我脆弱的心灵上施加了太多的烦恼与倦怠,长期以来我都无暇顾及其他事情。若我无法领悟您的思想,使您倍感失望,希望您能原谅我的愚蠢无能。
但她对笛卡尔的回复言辞之犀利,恰是弱智愚蠢的反面。在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尔声称心灵与身体由两种不同的实质组成。一种是非物质的、自足的,而另外一种是物质的、向外界延伸的。
伊丽莎白发现了这种二元论中潜藏的问题:像心灵(即“我思”)这样漂浮的、无形的东西,如何让身体这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做出各种举动呢?笛卡尔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提供一个解释,认定心灵与身体之间存在某种媒介使二者可以互动;要么就承认心灵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从物质中诞生的。第一个选项看起来有点儿奇怪,而且展开而论过于庞杂;而后者则剥夺了心灵活动的一切效力,因为原则上说任何心灵活动都可以由底层的物理过程来解释。
在今天,这种理解心灵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在对心灵的哲学、科学研究中,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如今,“物质”的领域指向大脑:身体感知外界环境,把信号输入大脑,并对外界作出反应。而与之相对的“心灵”,如今则被认为是一些难以阐明的现象,比如心理特征与意识。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以及实验者开始使用“计算”这个隐喻来解释笛卡尔的二元论。大脑就像一台有章可循的机器,其机制可操控抽象符号与内部表征:这些符号、表征以某种方式,通过我们的感知从外部世界进入觉知中。这些感知被转化成信念、意向或欲望等内部状态,然后再由算法转化为行为。可以肯定,大脑需要身体,但大脑需要身体的方式就如同寄生虫需要宿主,或者软件需要某种硬件来运行一样。
生物黑客创业者法吉抓住了这种观点的精髓,他这样写道:“你是一个由演化打造的生物学机器人,可被破解,可被程序控制。你只是在执行一些程序。这就是你,接受现实吧。”
但是心灵与物质的割裂,与后继的“认知与计算”,并不是试图理解思想本质时逻辑推导的必然结论。它们更像是出发点,或者一种基础的直觉,而且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直觉。比如说,伊丽莎白就告诉笛卡尔,相比二元论,她更倾向于物理还原论:“我宁可承认灵魂属于物质,有广延,也无法接受非物质的东西能够导致身体动作,或受到身体作用。” 她关于家务事的小插曲也是狡猾的批评。通过亲身经历,她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所需要承担的繁杂劳务会削弱她的身体,并影响到她思考的能力。
伊丽莎白曾在比利时的一座温泉小镇卧病,两年后,她也曾写下相似的内容。她的生病经历让她开始怀疑笛卡尔的断言:美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否服从理性的冷酷指挥。“ 一个人真的能仅仅凭借完全取决于意志的东西,到达你所谓的至福境界吗?对此我依然深深怀疑。”她如此说道。伊丽莎白相信,要做好一件事,有很多条件我们无法掌控,比如说:没有太多负担,良好的教养,以及健康的身体。
伊丽莎白不只是简单地否定笛卡尔的观点,她此前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非一味重申主观意见。这是因为她特定的生活经历使她倾向于发展出与笛卡尔不同的直觉,这些直觉给了她很好的理由去质疑二元论是否可信。就像牛津大学的哲学家阿米亚·司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所说,我们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偶然性——曾塑造我们的人,我们克服的挑战——无一例外地塑造了我们的判断直觉:什么样的言论有说服力,什么样的言论是值得怀疑的。
在我看来,伊丽莎白作为女人的经历让她无暇忧虑身体与物质之间的巨大割裂。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她和很多女人、历史上被压迫的人们一样,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弥合紧闭的内心世界与遥远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巨大分歧。相反,伊丽莎白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被世界不断索取的同时,“保存”内在的自我;如何维护自身权利来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并拥有多项截然不同的事业,以及如何在剥削制度的社会中,开辟出一片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天地。
哲学家们常常沉浸于把人类和“非我族类”者(僵尸、蝙蝠、人工智能、章鱼和外星人等等)进行对比。但与此同时,他们更难注意到那些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复杂生命。这些复杂生命跟他们一样,会走路,能说话,也能描述自己的主观体验。但直到最近,她们都未被给予完整的、真正的人格(personhood)。将女性边缘化有诸多害处,危害之一是,它可能导致未经审视的设想和未经质疑的理论盛行。而女性主义理论关心的是父权社会的运作和女性的解放,也正因此,它可以成为揭示这些害处的有力工具。
法国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经典作品《第二性》中,就用女性主义的策略,向启蒙哲学的基石——“有知的人类主体”——发出了宣战。她在书中这样解释同时期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话:“人不是一个自然物种;人是一个历史概念。”德·波伏娃认为:“人类主体”并不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普世概念——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社会对女性系统性贬压带来的副产品:
对女性的贬压象征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时期,因为女性的特质对应的不是她本身的正面价值,而是男性的弱点;她象征着自然中那些令人不安的谜团。当男性将自己从自然中解放,他同时也将自己从女性的掌握中解放。换句话说:女性是“人类”的衬托。她是“她者”,拥有着“非人”的特质;因此,男性可以指着她,并窃窃私语:感谢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她们。
所以,德·波伏娃那句常常被引用的名言,“一个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性,她是‘成为’了女性”,并不只是在说女性的思想和自我是社会建构的。实际上,她是在更有力地指出: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正是为了让男性可以成为人类。人类有能力进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考,知晓真相,清晰洞察,而“她者”则与非理性、情绪化和含糊不清相伴。人类拥有文明和教养,而“她者”则与自然和物质紧密相连。人类有着锋利且强大的思想,而“她者”则只有肉体。德·波伏娃写道:
男性自傲地忘记了一点:他的身体还包括了激素和睾丸。他将自己的身体视为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直接且正常的连接,也相信他对世界的理解是完全客观的。然而,他眼里的女性身体就是障碍,是牢狱,被自己所有的女性特质所拖累。
美国哲学家玛莎·纳斯邦(Martha Nussbaum)在2013年出版的《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中进一步展开了德·波伏娃的分析。纳斯邦引用儿童和发展心理学中的例子,指出人类境况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对自身脆弱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改变和控制现实的渴望。她认为,这无法逃脱的束缚使任何人都自然倾向于自恋、自恶。我们厌恶自己必然死去的肉身,厌恶自己作为生物的有限和脆弱。因此,我们使人顺从,以此将我们想要否认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质,都映射到别人的身上——她们是卑微的、动物性的、“她者”的;而我们则超越了这一切,成为了伟大的、真正的人类。
带着这些论据,女性主义者们似乎就要面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主张提升女性被贬低的地位,从而上升到完全解放和理性的人类境况;这是一种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这样典型的自由女性主义者会采取的策略。正如男性的身份不由身体定义,女性也该如此。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也可以拒绝承认“人类社会充满绝望的腐败和父权”这样的主流观点,并提出我们应该拥抱“女性”属性中的特质。
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用的就是后一种策略,她在1982年出版的女性道德推理研究著作《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指出:在思考道德问题时,女生的考虑会倾向于涉及关怀和情感关系,而男生则会透过正义、理性和个人主义来分析问题。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则采取了一种更激进的策略:他们将“地球母亲”的哺育能力与具象的、“母性的”特质(例如生殖和抚养能力)联系了起来。但美国演化论学者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犀利地提出:在当下这个生态环境并不稳定的人类世,我们其实更应该将盖亚——我们的地球母亲——描述成“坚韧的泼妇”。但不论采用哪种策略,我们都掉入了同一个陷阱:我们将身体当成了原始的、不变的物体——一种基质、一种不能被改变或质疑的“既定情况”。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陷阱”帮助女性主义将性别(gender)和性(sex)分开:性别是鼓励女性去扮演的一系列社会角色和行为,而性则是生物意义上的。将女性境况分割成性别和性,让激进分子们有途径去论证社会规范的作用,并迫使政治权威放弃“与生俱来”的论点。
毋庸置疑,这个策略是变革性的,但它也有它的代价。例如,“身体”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物体:它有深刻的重要性,同时又被遮蔽着。女性主义者讲述了她们的身体是如何被审查,被表现,和被符号化的,但这让我们无法公开地用科学、客观的语言来讨论与具身化有关的问题,仿佛这样做会把决定论这个魔鬼从罐子里放出来。批评者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生物和科技都已经被多次用作武器,只为满足男性的需求和欲望。这些做法当然是需要质疑和批评来纠正的,但这些质疑和批评最终却从内部削弱了女性主义对科学进程的影响。此外,如果女性主义者想要革新男女关系的某些方面(例如抚育后代、职场关系和性别取向),就只能将追咎的矛头指向性别,而非性。就这样,从自然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我们焦虑的对象变了,可两者都是站不住脚的论断。
将女性境况分割成性别和性,让激进分子们有途径去论证社会规范的作用,并迫使政治权威放弃“与生俱来”的论点。
与此同时,正当女性主义者们认为我们的生物性是“无可救药”的,因而将注意力从生命科学上移开时,生物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们则继续拓展他们的影响力,吸引大众和政客的眼球。性,变成了女性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如美国生物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在2005年写道:
我们曾以为性别是我们的的盟友,所以把性降低到了生物和医学的领域,但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们却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把性拓宽到了性别的领域。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激素使得生来就更独断的男性占领职场的顶峰;强奸是极难改变的行为,因为它已经以某种方式固化在了男性的大脑中;精子和卵子的相对大小决定了男性生来就倾向于一夫多妻,而女性则生来就习惯一夫一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换句话说:女性主义对身体——尤其是生物角度上‘性的身体’——的工具主义科学解释心存疑虑是可以理解,但这种存疑是缺乏远见的。
面对这些由“性”引申出的棘手问题,福斯托-斯特林认为女性主义者们迎来了全新的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完全否认所有关于身体的生物学解释;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认可这个由细胞、神经和组织构成的身体,但与此同时,不忘批判性地审视身体吸收文化,并被文化雕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理和社会、先天与后天,都在不断地塑造彼此,以至于我们无法将两者分开讨论。
想象一下:假如有人给了你和你的朋友一个箱子,并叫你们轮流把它抬起来。根据思考的计算模型,你的大脑会录入关于箱子重量的感知信息;这些信息会告诉你当你抬起那个箱子时,会感觉有多重。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同样强壮的话,你们对箱子重量的感知应该是近似的。
但2014年一项由剑桥大学的李恩熙(Eun Hee Lee)和西蒙·施纳尔(Simone Schnall)开展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她们发现:感觉自己在社会上更有权势的人,相比社会权势感更低的人,会更容易低估物体的重量。在类似的研究中,有朋友陪伴的登山者,比独身的登山者,更容易低估山坡的陡峭程度;饮用了葡萄糖的登山者,比喝了相同卡路里糖水的登山者,会更易低估斜坡的陡峭程度;而带着负面情绪的登山者,会比积极的登山者更高估斜坡的陡峭程度。
当下,计算模型仍然主导着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领域。但是,新的前沿理论也正在浮现;这些理论不再把身体单纯看作扛着大脑的机器人。由此,这些理论便有机会与像福斯托-斯特林一样的女性主义者们联手。
具身认知可以帮助女性主义者,或者任何批判性社会理论家,推翻被误用的、不公的社会阶级制度,走出性和性别的泥淖。
在一个叫做“具身认知”(名称仍有争论)的广阔领域内,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科学家和理论家们认为精神生活不仅仅取决于身体状态,而更是由身体状态构成的。借用哲学家迈克尔·基尔霍夫(Michael Kirchhoff)的隐喻来说:心灵从一台笛卡尔式的计算机,变成了一个放在转轮上的陶坯。湿润的陶土在转动的圆盘上疾旋,被陶工的手、臂和肌肉塑造,再塑造;与此同时,陶工的手、臂和肌肉也在感受着陶土的运动。心灵既被外界,也被内在的力量塑造;同时,心灵与外部世界和身体也有着联系,形成一个大体稳定的单一动态系统。
只需要一点前瞻性,我们就不难认识到具身认知的政治潜力:它可以帮助女性主义者,或者任何批判性社会理论家,推翻被误用的、不公的社会阶级制度,走出性和性别的泥淖。具身认知让我们得以承认生物性对我们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不会忽视权力或政治的影响力。
在1980年的论文《像女孩儿一样投掷》(Throwing Like a Girl)中,美国哲学家艾利斯·马瑞恩·扬(Iris Marion Young)引用经验研究指出:参加体育活动时,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认为一个飞来的球是“带有侵略性地飞过来”,而非单纯地“飞过来”;她们也更不信任自己的身体,并把自己的四肢当作“尴尬的累赘”,而非帮助她们实现目标的“工具”。
扬引用了德·波伏娃的作品,并提出女性的身体体验源自于女性“将自己的身体视作物品——一件易碎品;这件物品必须被强迫、被激励着运作;它是为了被欣赏和被操纵而存在的”。但是,扬不认为这样的状态是自然的,也不认为它来源于女性生理中某些内在因素。反之,她指出:想要以女性角色生活,其副产品之一,就是会有这样的感受。由此可见,即使不能找到一个对“女性”的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到具身的重要性,也能明白它和社会文化之间如何互相塑造的。
虽然具身认知在近些年才流行起来,它的历史其实比当今主流的大脑计算模型还要悠久;它源于反笛卡尔流派的哲学心理学。虽然德·波伏娃常常被人认为是深刻地反生物性的女性主义者,并早在性和性别被定名之前划分了两者,但是这样的表述忽略了马丁·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对具身现象学(embodied phenomenology)的贡献(德·波伏娃本人明确地表达过具身现象学对她思想的影响)。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坚决维护身体的重要性:它并非单纯存在于世的物体,而是每一个生命理解现实的基础和源泉——身体即思考之工具。
“世界于每个人呈现了不同的样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感受世界的工具,而世界的样貌随着每个人不同的感受而变化,”德·波伏娃写道,“身体不是物体,而是处境:它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也是我们人生的项目大纲。”
在现象学中,身体是个人体验的参照点。它不只是单纯地记录或呈现抽象表现形式,让这些表现形式以各种形状压印在无生命的石膏上一样;更准确地说法是,它将生物在某个瞬间觉得有意义的环境要素及时地唤起。海德格尔最中意的例子,是一个锤子。意识到它是一个锤子——意识到它是什么、有何功能——取决于你此前与锤子有关的身体经验。只有当你此前使用过与之类似的东西,你才能判断它对一个任务来说是太重还是太轻。认出一个锤子,等同于理解它对你在那一刻的意义,这需要你已有的“使用锤子”的感受。
麦克·梅(Mike May)是一名美国职业滑雪运动员;他的案例或许揭示了海德格尔理论的现实意义。梅三岁时,煤油灯爆炸让他的左眼失明,右眼虹膜也受了伤。通过虹膜移植,在1999年,四十六岁的他奇迹般地恢复了视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真正地“看见”。大多数人眼中的车、猫、人和树,在梅的眼中就只是移动的线条和斑驳的色块。
为什么梅在经历了四十年的黑暗之后无法“看见”物体,缘由并不明朗;毕竟他似乎和视力正常的人一样,能够接收到视觉信息。用心理学家路易斯·巴雷特(Louise Barrett)和神经科学家莫什·巴尔(Moshe Bar)的话来说:“这些想法暗示着一个有趣的可能性:仅仅暴露在视觉信息中,并不足以提供视觉经验。”
他们认为,梅的问题未能消除是因为,他在儿时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错失了将各种物体的样子和其他身体感官联系起来的机会。他们认为,我们人类并不会用我们的感官来建立对外界物体的抽象模型,然后再转化成我们对这些物体的感受。反之,我们在看到物体时,就已经有了感受:我们之所以能学会认出一棵树或者一只猫,是因为我们将它们与自己身体感知的历史联系起来了;这些身体感知包括它们的味道、触感和我们看见它们时唤起的情绪。我们在思考时并不会抽离自身,而是会带着自己的身体与外界物体的互动历史来理解世界。
与海德格尔类似,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认为我们在探索世界时会产生身体状态的潮汐与湍流,而我们的核心认知过程则是这些潮汐与湍流的残像(afterimages)。以恐惧为例,詹姆斯在1884年指出:如果没有“心率加速、呼吸急促、嘴唇微颤、肢体颓弱、鸡皮疙瘩和内心焦躁”,我们就不能理解“恐惧”这个概念。类似地,“如果没有眼泪、抽泣、缺氧心痛、胸口阵痛”,我们就无法理解“悲伤”。与笛卡尔的想法相反,身体的确会思考;它正是意识理解事物之意义的工具。
虽然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主宰主流心理学已然几十年,但是关于心灵,这一股情感和具身理论形成的逆流,一直都在水下默默湍动。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J·吉布森(James J Gibson)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直观功能(affordances),并开创了后来被称作“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的领域。吉布森认为,将感知理解为操纵着装有(外界)物体之模型的计算机式心智,是错误的。他指出,我们演化并学会去感知周遭环境的某些性质(例如红绿、软硬、轻重,甚至生死),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些性质曾给我们“提供”(afforded)过一些机会,使得我们可以做出某些提高我们生存几率的行为——换个表述就是,这些性质对我们而言具有直观功能。见过红色和绿色浆果,也许曾帮助我们判断浆果是成熟的,还是有毒的。用手提起过石头,也许曾帮助我们分辨煤块(用于点火)和花岗岩块(用于制造工具)。
用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说,环境中的这些性质,是“能够带来差异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处在特定情境中,或追求特定目标的生物有着重要意义。它们并不需要“我思”中任何抽象符号来作为媒介;它们的存在源自于我们联系和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换句话说,直观功能的存在,与我们行为的意义和目的息息相关。
由此可见,直观功能的建立,与生物具体的实时目标和能力——包括身体目标和能力——息息相关。水,为鱼提供呼吸的直观功能,但对火烈鸟没有;楼梯,为腿脚健全的人提供行走的直观功能,但对坐轮椅的人没有。前文提到的那些实验也与之类似:当你感觉自己很强壮,有同行者的支持,或者刚吸收了卡路里时,一座小山坡的行走直观功能可能更明确,你也因此感觉不那么陡峭,且更容易攀爬。
另外,外部世界能提供给你的直观功能,取决于你的个人历史:取决于外部世界曾提供过给你的那些直观功能,取决于你在个人经验中习得的直观功能。也就是说:感知和行为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一本笔记本,对作家来说,提供了记笔记的直观功能;对于画家来说,提供了素描的直观功能;而对于一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文盲来说,笔记本很可能没有任何直观功能。借用前文中扬的例子:与男生不一样,也许飞来的球对女生来说,并没有“接住”的直观功能;这是因为在普世教育中,关于如何与世界进行身体交互,男女生接触的教育不同,培养强化男女生的某些策略截然不同。扬发现:“年轻的女孩会学到很多带有‘女性风度’的微妙习惯——‘像女孩一样走路’、‘像女孩一样歪头’、‘像女孩一样站和坐’、‘像女孩一样做手势’。女孩会主动学着去约束自己的动作。”
具身理论中最前沿的热门话题是,期望如何塑造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多的认知科学研究指出,我们并非用感官数据“自下而上”地描绘着外部世界的样子,而是通常会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能让我们对外部世界做出预测的模型。
对有些人来说,例如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的哲学家雅各布·何威(Jakob Hohwy),关于“预测模型”的讨论是在向曾经笛卡尔式的、与身体脱离的“我思”致敬;但对其他大部分人来说,例如爱丁堡大学的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这些预测必然需要实际经验的基础,更与行动、具身性密不可分。
我们的预测和实际感觉状态之间,存在着一个误差,而这个误差会在我们的觉知中留下印记;作为生物,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个误差(或“惊喜”)最小化。宽泛地说,“看见一只猫”就相当于预存了猫的模型,并且这个模型可以预测一只猫的存在,随后感官数据再和这个模型进行匹配。如果根据吉布森式的认知观,我们预测的实际上是外界环境中众多持续变化的直观功能——外部世界中的那些真切且有意义的方面;而我们能够感知、预测到这些方面,并借此促成我们自己的行为。
这些预测模型由两方面构成,分别是反馈回路和筛选机制(它能筛去不符合我们期望的信息)。也正因为此,我们的行为倾向于让感觉材料和期望匹配。这让人不禁想起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62年在瓦尔登湖的自然研究——他提到了一种“激动且期盼的心情”:
“物体不为我们所见,并非因为它们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而是因为我们未将自己的心灵和眼光聚集于它们……如果想要看到某物,我们就要为它着迷;这时,除了它,我们就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这些关于期望和直观功能的讨论,可能会让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浮出水面:认知与政治之间再也无法划出一道清晰界限了。如果我是黑人,一名警官给我的直观功能或许会与给我白人朋友的直观功能不一样,而且我们面对这名警官时的反应和感受也会截然不同。要消除这些(也许对我个人来说是合理的)期望,不仅需要改变我相信的事情,而是必须改变长期形成的具身反应。类似地,作为一名女性,我不会觉得一条漆黑的废弃街道对我而言,有在夜晚散步的直观功能,但我的男朋友也许就能完全放心地夜游。我打心底里感觉自己是脆弱的,这就意味着我会避免将自己带到这样的环境里,也因此,我的期望会被默默固化。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具身世界,就是由这种自我固化的因果循环构成的。
我们女性主义者想要一份女性解放的处方;这份处方要能避免在不羁的人类共性和刻板的“女性”形象之间做出尴尬的抉择。具身认知是否给我们开出了这样的处方呢?当前,我们的确能捉摸到一些线索,以追求更有可塑性和创造力的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在《神农毒瘾:性、药物与生命政治》(Testo Junkie)一书中,西班牙活动家和作家保尔·佩西雅多(Paul Preciado)¹讲述了他非法进行局部睾酮注射的故事,读来令人瞠目结舌。
¹译者注:旧名Beatriz Preciado,曾经是生理上的女性,在改变生理性别(性)后自认为是跨性别者。
佩西雅多讲得非常清楚:他想要的不是任何从一个性/性别到另一个性/性别的“标准”过渡;他并没有把女性的外壳剥去,来展露所谓被隐藏的、真正的“男性本质”:
性的真相,并不需要我们去揭露;它是一场关于性的设计……我并不想改变我的性,也不想宣称我觉得我的性有多么不自在。我不想要让医生来决定:多少睾酮比较适合改变我的声音和让我长出胡须;我不想让人摘除我的子宫和乳房。
身体成了一种可塑的基质,佩西雅多可以摆弄、修补它,而不是控制它,或改变其构造。
佩西雅多所表现出的,既不是对生物不可塑性的怀念,也不是某种忽视身体重要性的高科技迷痴。他自我描绘的形象类似于前文提及的哈拉维的“赛博格”:一个由科技和生物、思想和感情、物质和精神构建出的嵌合体;它们通力合作,共同演化。诸如此类的嵌合体,与硅谷里流传的“半神”形象截然不同。相反,哈拉维的“赛博格”享受着自己模糊的边界,沉醉于生物和科技元素之间的交融和污染,享受着与其他生物的纠缠与依赖,以及自身的缺陷和不可预测。“不仅‘神’(god)死了,‘女神’(goddess)也死了,”哈拉维欣喜而道,“消除生物和机器之间的界限会带来很多新的可能性,而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公开明确地接受这些可能性,则会带来许多好处。”
如果没有具身认知理论,未来的女性主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要么接受基于女性身体刻板印象而建立的政治生态,要么可能通过强迫女性遵守所谓“普世”的社会规则,来压制女性的个性。具身认知绕开了这些选择,它将女性的境况描绘为生物和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循序渐进地构建、重塑,使自己与自然、物质纠缠融合。与法吉想象的那个无敌且万能的“超人类”不同,具身女性主义可能创造出的形象类似于加泰罗尼亚艺术家穆恩·里巴斯(Moon Ribas)——她在手臂上永久植入了传感器,可以感受到任何地方发生的地震。
意识到我们的身体被社会文化所包围和塑造,也就意味着要接受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我们极易被操纵和控制。电子设备入侵我们最私密角落,让我们越来越难相信自己真的拥有自主、有界、独立的思想。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对这种新情况保持过度警惕,而是可以把它当作历史给我们的通行证——我们可以开始尝试新的共情、新的身份,和一系列更有意思的嵌合自我。
翻译:曹安洁、阿莫東森;审校:邮狸、有耳;编辑:语月
原文:Women’s minds ma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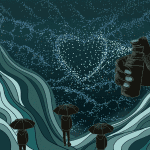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