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爱意不能相等,就让我成为爱得更多的人。”
1957年,W.H奥登将自己对爱情的期待总结凝练成一行美丽的诗句。这位当时已年过半百,同时也是同性恋者的著名诗人,曾在致友人的信里不无惆怅地写道:“婚姻是他现在唯一的主题。”然而直到大半个世纪后的2015年,美国才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对同性婚姻的禁令。而在全世界,目前已有将近三十个国家与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认可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但是,同性婚姻合法性的推动,只代表着性少数群体诉求权益保障之路上前进的一小步。即使是在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仍然面对着各种各样隐性或者显性的歧视与区别对待。
在一些国家,人们仍然会因为发生同性关系而被关入监狱或者判处死刑。哪怕是在美国这样已经实现合法化的国家,根据独立研究组织NORC开展的调查显示,2018年仍然有31%的人认为同性别成年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永远错误”的。除此之外,在性少数群体(LGBTQ)中,不同字母所代表的不同人群仍然面对着不同的挑战。比如调查发现,美国对跨性别者的包容程度远远不如对于同性恋者高。
对于很多生活在信息比较流通地区的人来说,这样的现状也许是使人惊愕与困惑的。
惊愕之处在于,如果自己的生活中都是支持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一个人就很容易忘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性少数群体仍然置身于连基本权力仍然都缺乏保障的困境之中。而困惑之处在于:抛去政治、社会、宗教和经济等因素不谈,为什么一个人类会对另外一个人类抱有这样强烈的偏见——在对方仅仅是想去拥抱自己真正的身份,仅仅是想去爱自己真正爱的人的情况下?
对性少数群体抱有的偏见,从何而来?
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里高利·M·赫里克(Gregory M. Herek)提出“性偏见”这个概念。
他将性偏见定义为“由于性取向而对一个人产生的负面态度” 。赫里克认为,这个词应该取代“同性恋恐惧症”, 因为它比同性恋恐惧症更具有描述性,并不隐含对于这一现象成因的推测。而且,早有证据表明,对于一些自认为是“同性恋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的生理反应也并不能完全满足真正临床意义上恐惧症的发作生理标准。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性偏见”这种消极的态度具有什么样的心理机能呢?毕竟,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事物抱有某种态度,这种态度对于这个人来说一定是有一些心理上的意义的。可对于性少数群体抱有偏见,又能在何种层面上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一种解释是社会表达功能。比方说,通过抱有这样的态度,一个人可以强化自己与自己比较重视的群体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功能常常表现为受到宗教原因的影响,在信仰较为重要的群体之中,人们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接受程度往往较低。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信仰与性偏见之间不存在因果性。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并不是所有对于宗教信仰带来的看法都会演变成性偏见。有很多信徒能够很好地区别对待“教义上”“道德上”与日常生活及立法进程中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
另外一种解释是价值表达功能。与社会表达功能不同的是,价值表达功能的主要目的是捍卫处于一个人自我概念核心地位的价值。比方说,有调查研究表明,男性对于男同性恋的反感程度,与他对于男性气质的支持重视程度呈现负正相关性。也就是说,一个越持“男子汉大丈夫”这种观点的男性,也就越容易产生性偏见。而因为男性气质与女性的自我概念的关联性不强,这种相关性并没有体现在女性身上。即使一个女性对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十分认可,她们也不会因此而产生反对男同性恋的倾向。
“恐同皆深柜”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当然,赫里克也指出,对于一些人来说,性偏见这种负面的态度也许与表达无关,而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来对抗自己的焦虑而存在。这样的说法起源于精神动力学,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这种强烈的偏见都是来自于一种担心自己无法抑制住自己对同性产生欲望的焦虑。换句话说,就是“恐同皆深柜”。
那么,这样的说法有实验证据支持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很有争议的实验。在实验中,他们招募了35名自称是“同性恋恐惧症”的异性恋男性与29名没有“同性恋恐惧症”的异性恋男性。为了测试这些异性恋男性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否与他们潜在的同性恋倾向有关,这些实验人员给这些男性播放了三段色情影片,这三段影片分别包括男男性行为,男女性行为与女女性行为。
根据“恐同皆深柜”的理论,这些实验人员预测自称为“同性恋恐惧症”的男性,在观看男男性行为的影片时应该也会出现性唤起。而他们的实验结果确实表明,这些“同性恋恐惧症”组的男性,有54%的人出现了生殖器充血,远高于“非同性恋恐惧症”组中出现生殖器充血现象的24%。
但是,这样的实验证据真的印证了“恐同皆深柜”吗?并不尽然。
早有证据表明,焦虑情绪会增强男性性唤起的程度。而单从这一项实验中,我们并不能解读出这种焦虑的来源。也许,焦虑来自于参与这项对隐私性有极大挑战的实验本身;也许,焦虑来自于观看刺激性较强的影片,这些可能性都导致我们无法判断这种充血现象的原因。之后试图复制这项实验的研究人员也屡屡失败。一项2011年通过测量惊恐条件反射(startle response)的研究指出,现有的证据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恐同皆深柜”的理论。
更有趣的是,一项2013年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不仅一个人对于性取向的态度与这个人对于同性吸引力程度无关,而且一个人的内隐态度往往与这个人的显性态度形成正相关。所谓的内隐态度,就是指一个人对于某种事物的潜意识里的判断。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是女,对于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何种态度,他们在明面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都能很好地预测潜意识中的态度。这样的正相关,恰恰与“恐同皆深柜”所预测的相反。
不过,这项实验中用来测量内隐态度的“内隐联结测验”的信度与有效性,也是具有一定争议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至少目前来看,并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支持“恐同皆深柜”的理论。
生来如此
在关于性少数人群权益的讨论中,常常有这样一种声音:“我不反对LGBTQ,但我也不支持LGBTQ,我持中立态度。”
这样的态度使人无可奈何。表面上,说这话的人看起来确实纯良无害,十分开明,其实在这种言论的背后仍然是对性少数群体持反对态度的。有些人之所以会这么说,往往是出于保持“政治正确”或者“避免争执”的消极态度,其实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于性少数群体根深蒂固的误解。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论是性取向也好,还是性身份认同也好,几乎都是生来如此,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遗传学家们就发现,如果双胞胎中的一个人拥有非异性恋的性取向,那么双胞胎中的另外一个人出现非异性恋性取向的概率也会增高。在被研究的这些双胞胎兄弟中,如果两人是同卵双胞胎,那么两人同时是同性恋的概率为52%,而如果两人是异卵双胞胎,两人同样是同性恋的几率则为22%。
除了基因以外,也有人猜测表观遗传学的的因素也会对性取向的形成产生影响。
在同卵双胞胎中,同性恋出现的概率仍然远远低于纯粹由基因决定的特征所出现的几率。所谓的表观遗传学因素就是指,即使两个人的基因序列核苷酸序列完全相同,因为环境的影响,这个基因所表达的特征也会出现不同。比如说,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女性,在胎儿时期常常处于高雄激素的环境下。虽然激素水平在出生之后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降回正常水平,但是相比于没有经历过高雄激素的环境中的对照组来说,这些女性出现非异性恋倾向的概率会增高。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表观遗传学上的解释仅仅是一种假说。激素水平与性取向的相关性并不能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挂钩。比方说,也有可能是同性恋的基因触发了高雄激素的水平,或者是相关基因同时导致了同性恋与激素水平的改变。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链条,在现阶段的科学研究当中,都尚处于模糊的摸索阶段。
没有人需要为爱愧疚
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于性别和性向的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无论是来自遗传学还是神经科学的解释,都会逐渐帮助我们更好、更科学地理解这些现象。不过这样的科学证据也带来一些潜在问题,它们常常会被纳入性别与性向的本质主义框架内。
无论本质主义者对同性恋持何种态度——要么,认为同性恋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生物属性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要么,认为这样表现形式是生理上的病态——他们的解读都忽略了这个个体所生活的社会世界背景。如果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都是在个体与社会之间不断互动的结果,所谓的“真实的本质”并不存在,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人们对于性别与性向的理解受制于自身所处的话语体系内,单纯地强调“生理因素”“科学解释”,也有可能成为性多数群体遏制性少数群体的工具。
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的张晓冰博士的话来说,“不管是理论研究抑或是同性恋群体本身,从一开始都认为同性恋是生来如此,是一种不可改变论。这种理论隐含着一种愧疚感,会导致同性恋者在拒绝矫正的要求时只能说‘我没办法改变’,而不是说’我不愿意改变’”。
但人不需要为选择什么性别、爱什么性别的人感到愧疚。“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 无论是同性恋也好,还是异性恋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爱的本质都没有区别。
那些说“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人,应该意识到,在关于爱与自我的问题上,他们没有权力表达反对或支持。所谓“不反对也不支持同性恋”,就像在说“不反对也不支持三角形”“不反对也不支持彩虹色”一样是无稽之谈。对于性多数群体来说,应该做的只有尊重:无论是异性恋也好,还是同性恋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这些标签背后都是一个个同样活在阳光下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个体。
编辑:E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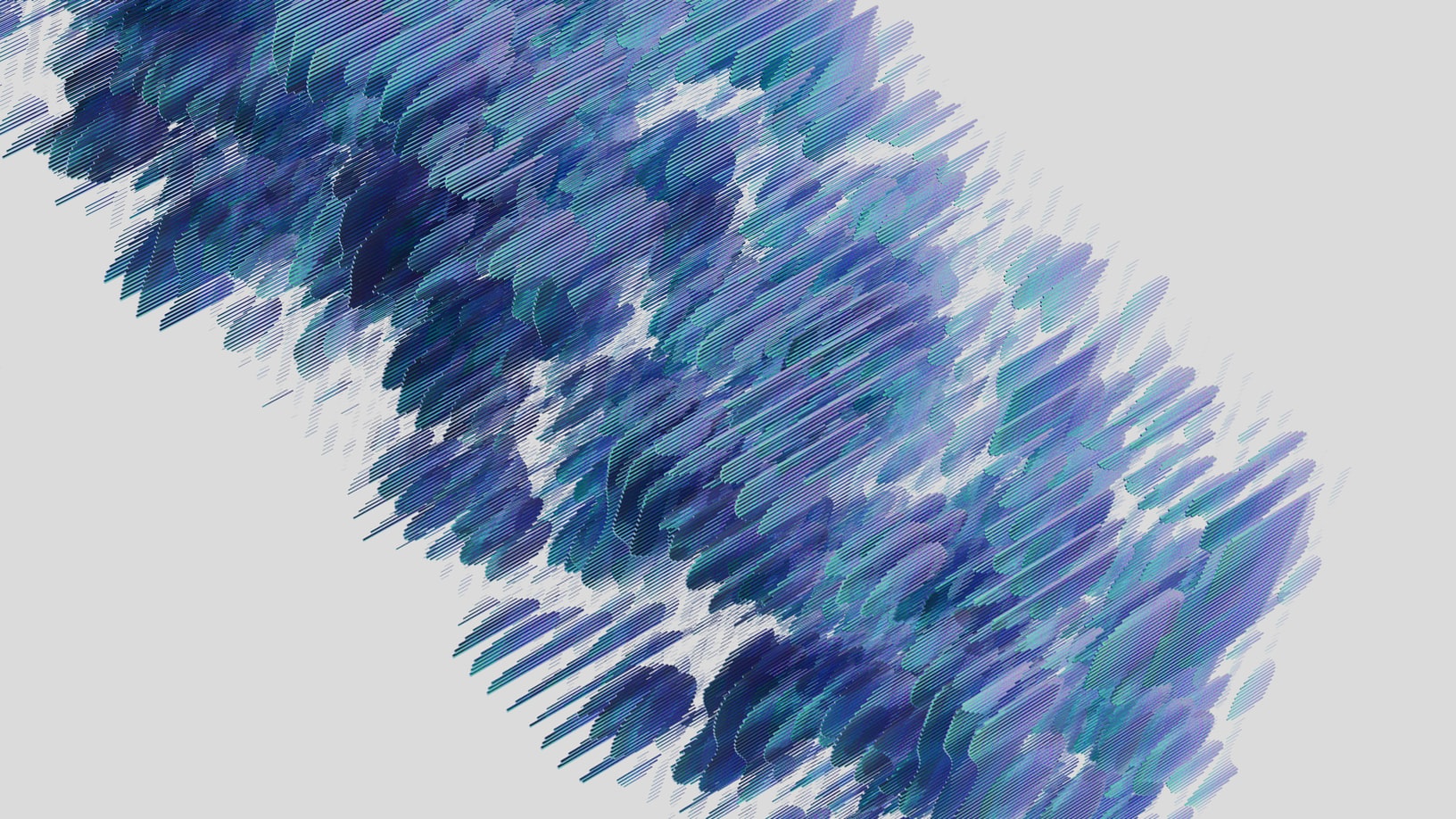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