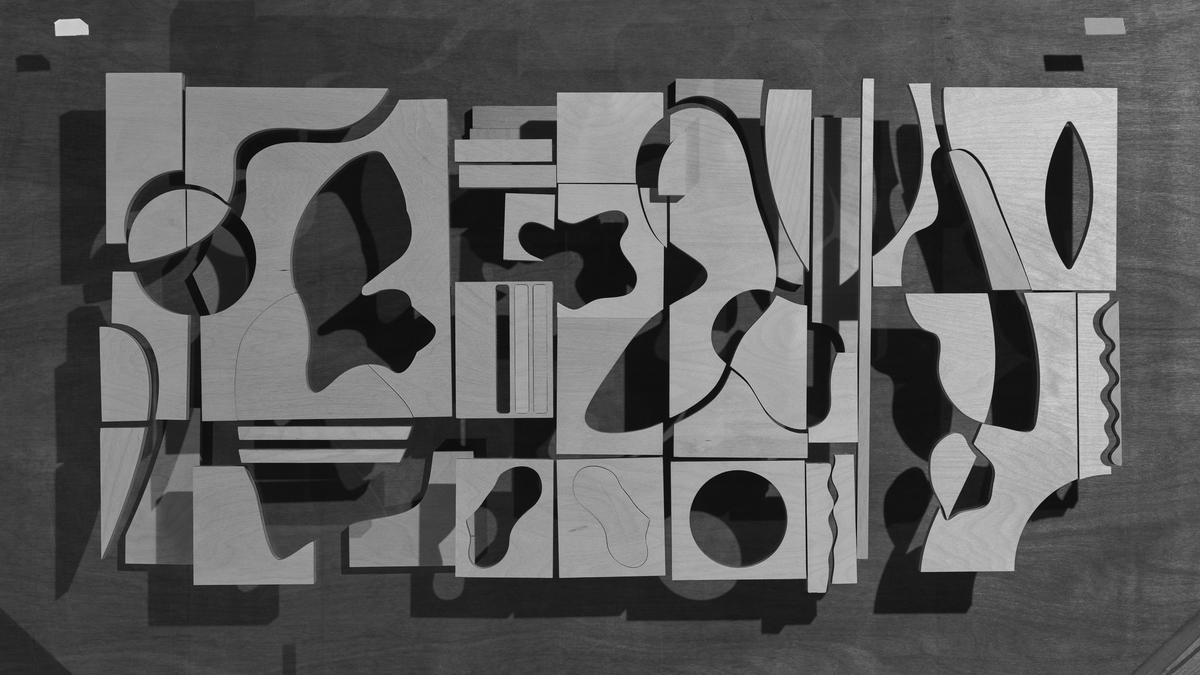
康妮·德·沃斯(Connie de Vos)把手垫在身下坐着。2006年,她首次来到巴厘岛本卡拉村(Bengkala)住下。每晚访客们都会来到她的房子,坐在前院的地板上,喝喝茶,吃吃水果味或榴莲味的糖果。现在就有大约八到十个人在那里双手纷飞,用当地的手语卡塔克洛克(Kata Kolok)聊着天:下一场纪念仪式在哪里?下一次葬礼是什么时候?谁死了?
大约120年前,卡塔克洛克语于本卡拉村被创造出来,它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比如伸出舌头表示在动词上加上否定。与使用美国手语(Amerian Sign Language,简称ASL)时人们无声地做口型不同,使用卡塔克洛克时,你需要轻轻拍打嘴唇,发出微弱的爆裂声,表示某个动作已经结束。
“如果你在六点钟,人们准备洗澡和吃饭时穿过村庄,”德·沃斯回忆说,“你可以在整个村庄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第一次来到本卡拉村时,德·沃斯还是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欲成为第一个找出卡塔克洛克语法规律并列出所有手势的语言学家。她说,由于该手语出现在一个聋人数量相对较多的孤立社区,所以那时还“未受影响”。与2000年起开始被发现的一些类似的“乡村手语”一样,卡塔克洛克是丰富的研究材料。德·沃斯知道,如果能抢先将之研究透彻,那将是她的一大成就。
但是研究任何现象都有将其改变的风险。考古学家知道,在古墓中呼吸会提高古墓的湿度,而动物学家用食物吸引野生黑猩猩有可能会改变整个族群的政治。
语言是如何涌现和演化的?而所有语言的共同起源又是什么?新出现的语言为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扇窗口。但是一些语言学家担心研究环境的纯净度,害怕研究一种可能只有少数使用者的手语会带来外部影响,从而改变其发展。
这就是德·沃斯为什么把手垫在身下坐着的原因——她是在故意避免使用其他语言的手势。如果她改变了卡塔克洛克的发展进程,她的研究有效性就会降低,与语言自然演化研究的相关性也会减弱。唯一的问题是,为了科学利益而将像卡塔克洛克这样的语言隔离起来可能并不符合其使用群体的最佳利益。“
语言是如何涌现和演化的?而所有语言的共同起源又是什么?
“每个这样的社群都像一场自然实验。如果让你用我们现代人的大脑来开发一门语言,它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已是荷兰拉德堡大学语言学助理教授的德·沃斯问道。“而我们有机会看到多个现代语言产生的案例,这是很有价值的。”
从泰国的手语Ban Khor到加纳的Adamorobe,语言学家已经记录了大约24种这样的语言,并猜测还有更多类似的语言存在。一些研究人员称它们为“年轻的”或“新兴的”语言,特别是当关注的焦点在于它们是如何进化时。另一些人则称其为“乡村”手语或“微型”手语,这反映了这些语言所在社群的规模之小和孤立性。“共享”手语这一称法虽然不太常见,但用来描述这些语言也非常恰当,因为听障者和听力正常者都经常使用它们。
这些语言往往出现于地理或文化上孤立的社群。由于表亲联姻,这些社群中耳聋群体画患病率通常较高。在这些地方,正规教育和全国通用手语并未普及。因此几十年来,人们发明了这些手势和连接这些手势的语法。
由于使用人数太少,这些脆弱的语言出现之日就面临着威胁。一些有钱有势之人意欲使它们消亡,或让手语者改用其他语言。有时,这一强大的幕后推手是聋人协会,他们蔑视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一切事物。
而且,由于手语者对于某些手势的意义和使用方式无法总是达成一致,这些语言可能看起来半生不熟。然而,它们本身毫无疑问就是语言,因为手语者一生都在用它们进行日常交流。
对这些语言的研究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手语的看法。例如,人们通常认为,所有手语,不管覆盖面大小,都使用身体周围的空间以相同的方式表示时间:手语者身后表示过去,身前表示现在,再往前则是将来。但是乡村手语通常略有不同,以卡塔克洛克为例,它根本没有一条时间线。“
有时,这一强大的幕后推手是聋人协会,他们蔑视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一切事物。
但德·沃斯会很快解释说,卡塔克洛克使用者仍然在思考和谈论未来和过去,只是没有指定的语言结构来谈论它们,除了诸如提及他们都知道的事件外。
研究乡村手语清晰地揭示了手语的独特性。但是,由于绝大多数乡村手语只诞生了30到40年,仅足以经历三代人的演化,它们也为实时见证一种语言的诞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研究人员可以跟踪研究诸如词序这样的语言结构是如何出现的,还可研究从第一代开始的语言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是人类语言能力所固有的,还是另有出处?
探寻这些问题的机会激发了语言学家对乡村手语的兴趣,此外“发现”一种新语言的诱惑也是难以抗拒的。
鉴于这些脆弱的语言受到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很大、风险也很高,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在争论该如何对待它们。
南缅因州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朱迪·克格尔(Judy Kegl),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遇到尼加拉瓜手语(或被称为Idioma de Señas de Nicaragua,简称ISN),当时没有任何研究先例可供她参考。
1980年左右,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一所学校的聋哑学生用他们的语言直觉把从自家习得的手势拼凑在一起,创造了这门语言。
克格尔说,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她一直没有使用ASL。“我努力只使用手势。学生们真的扮演了教师的角色,通过使用手势而非ASL,教会了我使用手语。如果我一来就用ASL,这些就不会发生。如果他们没有看到我想要学习他们语言的坚定目标,他们可能就不会教我了。”
她的目的不是保护语言,而是确保语言的发展方式不会因她改变。克格尔引用科幻作品《星际迷航》里的术语,称她也有一套“最高指导原则”:“你不应自以为是地参与并影响其他文化的决策。”
如果人们自己偶然学会了ASL,她不会阻止。但如果当地语言纯洁性遭到破坏,受到污染,她说,“至少保证这影响不是我们带来的”。“
她的目的不是保护语言,而是确保语言的发展方式不会因她改变。
而局外人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建议最好让这些社群积极融入更广泛的聋人文化,包括教他们更成熟的手语。1999年,克格尔的研究被收录在一份对新兴的尼加拉瓜手语的简介中,随后布朗大学哲学教授菲利西亚·阿克曼(Felicia Ackerman)对此写了一篇尖锐的评论。
阿克曼写道:“显然,[克格尔]宁可让这些孩子无法与外界交流,扼杀他们的人生前途。”(我问阿克曼她是否现在仍这样想,她没有回答。)
对于一些语言学家来说,觉得一种语言会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这种想法太过简单了。他们的这一观点也能支持那些认为人类过于轻易便能拥有先天能力的争议性理论。批评者认为,尼加拉瓜第一代手语者和其他手语之间可能有一些早期的、看不见的接触。为了避免受到这种怀疑,后起的语言学家,如康妮·德·沃斯,也坚持严格的“最高指导原则”。
德·沃斯知道本卡拉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孤立,但她想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语言污染迹象。她懂国际手语、英国手语和荷兰手语,不希望这些语言中的一部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头几个月,我一直坐在自己的手上,直到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不会再使用太多自带的手势,”她说,“我尽量不过多影响他们。”她担心人们可能会无意中习得她的手势,这样她也不能声称那是Kata Kolok的自然演化结果。
这并不是保证语言纯净起源的唯一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找到一种在一个真正隔离社群中使用的乡村手语。
2012年的一天,来自土耳其的年轻学生拉比雅·埃尔金(Rabia Ergin),正与塔夫茨大学的其他研究生一起在教室里听讲。她来美国主要是为了学习研究土耳其语句法,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她不久便改变了方向。他们当时讨论的主题是家庭手语(home sign),也就是由听障者和他们的家人之间发明且由他们共享的一系列手势。家庭手语并没有一套既定的造句组词的规则,它真的可以被算作是一种语言吗?
埃尔金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跟其他同学提起了自己远在土耳其的大家庭,其中一些有听力障碍的家庭成员自己发明了一种手语,然后村里所有人都学会了用这种语言和他们交流。
她的同学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可是,就这样,埃尔金风轻云淡地描述出一个大家闻所未闻的、仅存在于孤立社群环境中的乡村手语。
不久之后,她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她所提到的这种手语,也就是托罗斯中部手语(Central Taurus Sign Language,简称CTSL)。埃尔金告诉我:“我和这种语言来自同一个社群,并且共同成长,这个故事因此更具情感冲击力。”
当埃尔金真正着手开始研究时,CTSL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加入了一些全新的结构,包括更明确的表现动词的方式。这无疑是非常宝贵且激动人心的经历——她有机会亲历一个语言发展和改变的过程,而且因为前代的手语者仍然在世,她还可以在时间线上回溯得更远。
CTSL仍然是个非常年轻的语言,但是她认为这并不代表她的存在会对其造成很大的影响。她说,这些手语者们,特别是老几代的长辈们,并不会轻易地从其他语言中采纳新的元素。她常看到人们用CTSL在生活各个方面进行沟通,大家总能毫不费力就把意思表达清楚。她说道:“这个语言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CTSL非常灵活,没有规则束缚,以至于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CTSL版本,也就是说,该语言某些方面在使用者之间是共通的,剩下的就靠当场即兴发挥。而且,手语者们也可以不断变换自己的表达方式。
因此,虽然CTSL起源的环境与外界隔绝,这一语言仍然在迅速地发展变化。
埃尔金目前在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工作,她跟踪研究着一个均为聋人的五口之家,他们都是CTSL手语者,几年前搬到了安那木尔旁边的某个城市。这次举家搬迁之后,他们的手语中逐渐浮现出一些土耳其手语的痕迹,也开始偏离以前村庄里核心CTSL群体的表达方式。此外,埃尔金的某个表亲和另一个镇子上某位听障男士喜结连理之后,她的CTSL也在不断改变。
埃尔金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努力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以免错过最好时机。”4
最近一种新的研究策略也应运而生,以全新的方式对待乡村手语。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乌尔丽克·泽山(Ulrike Zeshan),是第一位将乡村手语完全当作ASL一类对待的语言学家。也就是说,乡村手语不享有特殊待遇,并不需要被视为处于萌芽阶段的半语言形态,我们也不必去悉心照看或者保护它们直至它们发展成熟,而是可以直接将它们与其他手语做对比。
正是在这样不同以往的思维方式下,我们才能认识到,某些公认的手语“一般规律”在乡村手语中可能并不成立,所以并不算普遍适用。比如,大部分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在一个手语系统中,身体前方的这片空间好似一个舞台,而双手就是舞台上的牵线木偶。在表达“牛在车前过马路”这句话时,大部分手语都会展现出“牛”、“路”和“车”在手语者身体前方的互动。
但是在某些乡村手语中,手语者的角色并非会置身舞台之外,以牵线木偶表演者的角色来操纵这三者。加纳地区的某种手语会从手语者自身的视角来描述牛、路和车之间的关系。所以,语言学家们需要打开脑洞,开拓手语中的各种可能性。
然而,语言学家们仍然要负责地行事。几年前,泽山和一些同事决定写一篇学术论文,专门为可能有机会邂逅乡村手语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建议。
但是,他们在考虑研究者的伦理责任时遇到了瓶颈。研究兴趣对于乡村手语意味着什么?研究者们需要与政府当局进行沟通吗?万一当地政府接到消息之后给手语者们送来助听器,或是采取其他技术层面上的干预呢?他们是否会强制村民使用国家通用手语?这些可能的回应在失聪人士的世界观中都是极具冒犯性的,因为它们不仅侵犯了人的身体自主权,还威胁到了当地的语言。
“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在伦理方面达成一致。”泽山说。最终这篇论文就被搁置了。
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会与许多尚未被发现的语言失之交臂呢?泽山承认,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对于她来说,伦理比科学知识本身更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研究时造成不良干预,与没有拿到成果相比,会对于一个人的良知造成更直接的打击。”她说。
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们仍然没有明确的伦理准则可以参考,他们只能自己去衡量与其他语言打交道的方式。
但是随着乡村手语研究发展成熟,研究者们发现他们作为个体对于语言的影响并不如担忧的那么大。有的时候,他们正是在自己犯错误时领会到了这一点。5
2012年,丽娜·霍(Lina Hou)和凯特·梅什(Kate Mesh)正在研究查提诺手语(Chatino Sign Language),一种使用于墨西哥瓦哈卡州内两个小社群中的乡村手语。霍目前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语言学系任助理教授,是一位听障人士,而任职于以色列海法大学的梅什并不失聪,但与霍一样,都是ASL手语者。
“我们开始的时候尽量用文字信息交流,避免在该手语社群中用ASL。”梅什说,但是这两位经常一不小心就露馅。
他们实在藏不住,社群中的很多成年手语者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的外来语。那么,当地人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他们觉得[ASL]很好玩,”梅什回忆说,但是她又说道,除了与彼此讨论两位研究者的举动之外,当地人根本不会去用这些新奇的手势。之后,她和霍在当地的成年人面前就放松了下来,交流起来更省力了,也并没有影响查提诺手语本身。
她在用查提诺手语时会不经意间融入一些ASL的使用习惯。有一天,她正与一位手语者讨论村子里的篮球赛,球赛的奖金是由参赛者共同筹集的。
“所有人都要交钱吗?”梅什问道。在抛出这个问题时,她用的是查提诺手语中的手势,语法却来自ASL,她在身体前方两个不同位置打出两次“支付”的手势,来表示支付者不止一人。
查提诺手语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达结构,因此,跟她交谈的那位男士喊来了自己同为手语者的妻子,跟她模仿了一下梅什刚刚的动作。他还表示自己蛮喜欢这个方式的。但是梅什说,这之后,自己再也没看到过他用那种方式打过手语。对她来说,这件事证明了,手语者们也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影响的。
玛丽·科波拉(Marie Coppola)是康涅狄格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她指出,所有语言都有其缺口,即使是像英语、意大利语和汉语这样的大语种也不能幸免。英语中过于简单的亲属称谓语便是个很好的例子,此外,网络上也经常能找到有关一些有用概念的列表,而这些概念在英语中都找不到对应表达。
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大语种使用者甚至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语言的限制,而小众的手语使用者们也一样。“他们只知道信息在传达过程中是会出现错误,但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平常的,”科波拉说道,“他们也没有其他语言可以拿来对比。”
成年人们尤其抗拒改变,就算外界语言可以帮他们解决日常沟通中的问题,他们也不会轻易接受。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学习新语法会越来越难,虽说学习新词汇反而相对容易一些。
然而,梅什发现,即使作为个体出现的外来人员难以动摇新兴手语,社会文化环境中总体流行趋势仍然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力。当原本比较孤立的偏远社群逐渐与外界建立联系,手语者们也会让他们的语言去适应新的环境,有些人甚至不会再用原本的语言,甚至不会再教给后代。
此外,当代生活环境对于小语种越来越不利。2012年,康尼·德·沃斯重回本卡拉,与她六年前首次拜访时看到的景象相比,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年有成百上千的游客涌来参观这个出了名的手语村,他们的食宿费用为村庄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
旅游经济兴起之后,本卡拉的村民们人人都有了一辆摩托车,很多人因此可骑车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工作,这也意味着年轻男子比以前更容易娶到外村的媳妇。一些听障孩子开始在学校学习BISNDO,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官方手语。来自游客们的影响力如此巨大,远非单个研究者的微薄之力可以企及的。讽刺的是,很多游客本身就是听障人士。
Kata Kolok能逃过一劫继续存在吗?在人类语言发展的历史上,不乏昙花一现的美好。接下来这个乡村手语的故事则告诉我们,对于某些语言来说,正因与世隔绝,语言才得以留存,一旦这一状态被打破,人们需要采取新的策略才能维持其活力。
矢野羽衣子(Uiko Yano)从小就开始学习使用宫洼手语(Miyakubo Sign Language),该语言在20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左右起源于日本爱媛县大岛,而在筑波技术大学读研究生的矢野成为了第一个将宫洼手语带入科研世界中的语言学家。
她说,以前看的一部关于卡塔克洛克手语的纪录片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所有人也都用手语交流。在手语翻译的帮助下,她告诉我:“在那样一个社群里,不管是否有听力障碍,所有人都会很自然地用手势交流,这还是挺少见的。”
宫洼手语是由15个一起在渔船上工作的人发明的,因此,这个语言的计数系统止步于30或40,整数不会超过200。矢野曾经问自己的父亲:“你是怎么表达225的呢?”
父亲告诉她:“我们就打’超过200’就好了。”
“万一你想告诉别人你有223瓶果汁,”她问道。“要怎么办呢?”
“你要那么多果汁干嘛?”父亲回答。
矢野说,近些年,不断有来自日本本岛的聋人协会联系父亲和他同为听障者的兄弟姐妹们,但是都被他们拒绝了。
父亲告诉矢野说:“我们不需要修改我们的手语,也不需要别人跑来讲我们用自己的语言都会出错。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标准做了,我们就无法跟祖父母辈交流了。”
数十年来,从大岛到主岛的唯一途径就是每天几班的轮渡,大家等轮渡的时候会聚在一起,边说话边用手语交流。
然而,2004年时,一座连接两岸的桥梁取代了轮渡。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上网,有了自己的电脑和智能手机,也有更多人与来自岛外的另一半喜结连理。
诚然,这些改变意味着大岛上约7000人口整体上和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但同时,用宫洼手语的听障者更被孤立起来了。没有轮渡,就没有跟其他人见面交换信息的机会,网络的便捷也省去了向彼此求助的麻烦。随着听障者们逐渐离开本地去寻找工作机会,岛屿上的手语者总数也越来越少了。
现在,岛上还有约15位听障人士。矢野常把自己在东京的朋友带回自己的家乡,向他们展示自己生长的地方,可她70多岁的姑姑却总觉得有些伤心。
她告诉矢野:“看到你们的时候,我总会觉得孤独。”矢野忙问为何。
“因为每次有人从东京过来,我们都只能用他们的手语,好让他们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姑姑回答。
外面的世界让她原本美好的海岛生活不再平静。“以前,我们可以随意交谈,大家都能很自然地理解彼此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但现在,没人会用我们的手语了,陌生的词汇层出不穷,我根本就不知道其他人在说什么。”
大家想到年轻人的时候,似乎总是想到容易受外界影响、易冲动而不负责这样的特点,但是年轻的手语并非如此。语言虽年轻,使用者却是很现实的,他们与自己所了解的世界不可分割,专心于自己当下的生活。语言学家们常常担心新兴的语言会受到外界过多的影响,这样的考虑更多是把语言作为科学研究的客体,而脱离了使用者本身的经历和感受。
但是所有人类语言都是在商业往来、工作娱乐和婚姻等等各种社会活动中逐渐演化的,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交流。各种语言都可以向彼此借鉴词汇,甚至是语法规则。随着我们的地球村越变越小,语言学家们也正在学习如何跟上加速变化的脚步,这些变化在影响语言的同时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语言学家们常常担心新兴的语言会受到外界过多的影响,这样的考虑更多是把语言作为科学研究的客体,而脱离了使用者本身的经历和感受。
回想起来,康妮·德·沃斯觉得自己刚开始跟村民们在一起时坚持不用自己的手语,的确是有点反应过度了。
后来,她坦诚地跟当地人谈了谈可能会改变他们所用语言的外界影响。“更重要的其实是去告知他们,提高他们意识。”她想告诉他们,世界各地都有听障者,不同的人群所用的语言都可能有所不同,而她想要看看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
最终,她在当地帮着建起一座学校,用Kata Kolok手语为孩子们提供教育。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太过小心了。”她说,不过她认为,可能正是因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坚持只用Kata Kolok工作,她才能从当地人那里听到一些外人很难接触到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有一个是讲为什么本卡拉有这么多听障者的。传说中一对夫妇求子不得,就到一个埋葬婴儿和胎儿的公墓祈福,住在此地的一位鬼魂帮他们实现了愿望,但是因为这个鬼魂听不到声音,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后也就成了听障者。
年轻的手语急切需要年轻的手语者们。在大岛上,矢野听力正常的侄子是目前宫洼手语最年轻的使用者。她希望他不会是最后一个用自己母语的人,也在不遗余力地想办法让宫洼手语得以延续下去。
“你觉得自己需要为这个语言承担起责任吗?”我问她。
她停下来想了想,然后打起手语,通过手语翻译回答了我。“岛上的人们不会过多地去考虑宫洼手语本身。表面上来看,这个语言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一部分人内心明白它对我们来说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的确想要守住它,把它留在我们的生活中,永不分离。”
翻译:狼顾,西子;审校:张蒙,子铭;编辑:酒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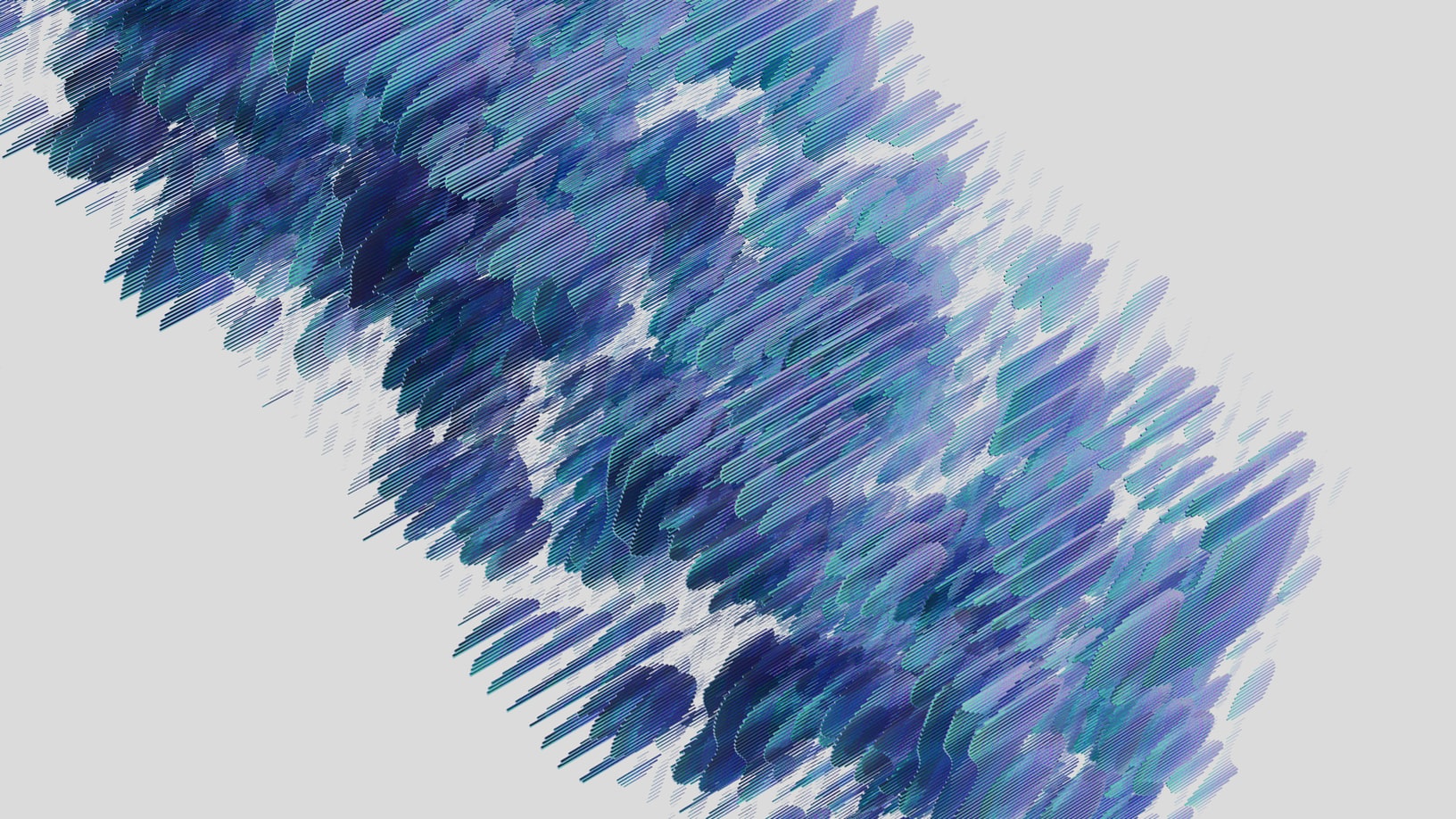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