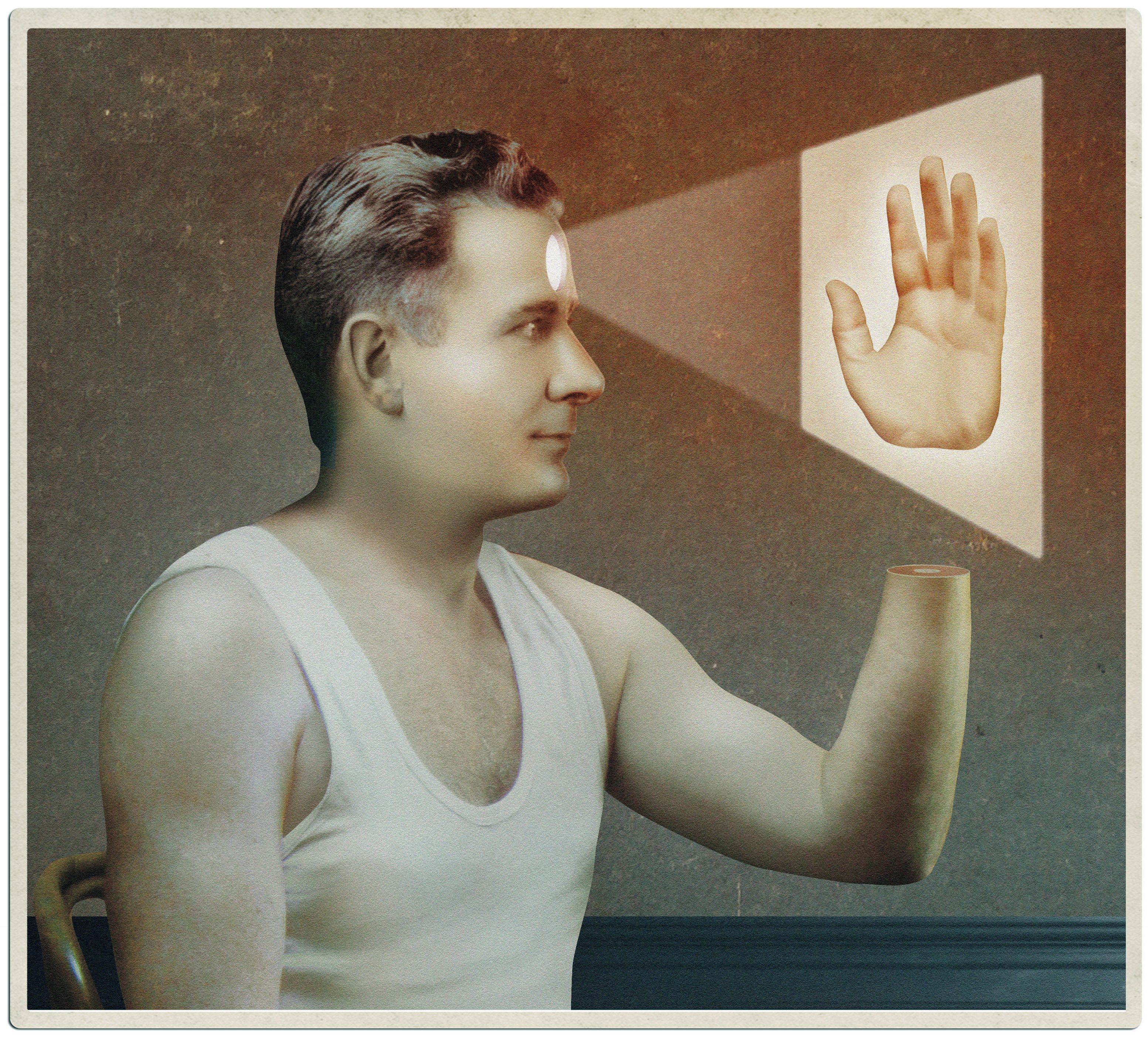
您永远也不可能从您身体投出的影子中认清您自己,或者从其影像,或您在梦中所看到的身体,或从您的想象中认清自己。因此您也不能从这个活着的身体中认清您自己。
——尚卡拉(Shankara)(788 — 820年),《吠陀经》
当有一位记者问著名的生物学家霍尔丹一个问题:他的生物学研究对他认识上帝有什么帮助时,霍尔丹答道:“如果确有造物主的话,那么他一定特别喜欢甲虫。 ”
这是因为甲虫的种数比任何其他生物群的种数都要多。按照同样的理由,神经病学家也可以断言上帝是制图员。他必定特别喜欢图,因为随便您看脑的哪个部位,都有大量的映射图。例如单就视觉而言就有超过30个不同的映射图。对触觉或是体感来说,也就是触觉、关节和肌肉感觉之类,它们都有许多映射图,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彭菲尔德侏儒,这是脑两侧纵向皮层条上的映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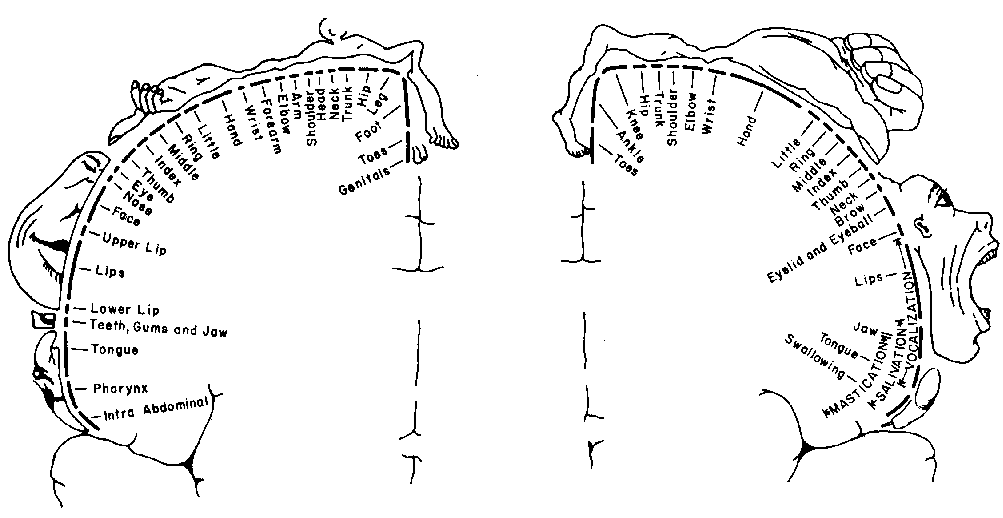
这些图在整个一生中是相当稳定的,从而有助于保证知觉通常是精确而可靠的。但是也正如我们看到过的那样,作为对异常的感觉输入的反应,这些图也经常会进行更新和细化。请回想一下,当汤姆的手臂断掉以后,对应于其已失去了的手的一块很大的皮层就会被从他脸上来的感觉输入所“接管”。如果我摸汤姆的脸,这时感觉信息就到达两个区域 ——原来的脸区(本该如此),同时也到达原来的“手区”。脑映射图的这种变化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手断掉以后不久汤姆就会产生幻肢现象。每当他微笑或是当面神经上有某种自发活动时,这些活动就会刺激他的“手区”,由此使他误以为他的手还在那儿。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故事。首先,这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许多幻肢病人声称他们能够随意地动他们“想象中”的肢体。这种运动错觉的根源是什么?其次,也没有解释这些病人为什么有时会在已经失去了的肢体上感到剧痛,这种现象被称为幻肢痛。再次,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没有一只手臂,那又会怎么样呢?在他的脑中也会发生映射图重组吗?还是在他的皮层中根本就没有发育过手区,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过手。他会有幻肢的体验吗?会有人生来就有幻肢吗?
这些想法听上去似乎很离奇,但是如果说我在这些年里懂得了一件事,那就是神经病学中充满了惊奇。就在我们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幻肢的文章几个月后,我见到了一位25岁的印度研究生米拉贝尔·库马尔(Mirabelle Kumar),她是由森(Sathyajit Sen)医生让她转诊过来的,因为这位医生知道我对幻肢感兴趣。米拉贝尔生来就没有双臂。她只有两条短短的残肢从肩部垂下。X射线检查发现这些残肢内有肱骨(上臂骨)头,但是没有桡骨或尺骨的任何痕迹。她也没有手上的小骨头,虽然在她残肢中确实有原始的指甲。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米拉贝尔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的脸由于爬了三段楼梯而发红。这是一位迷人的、高高兴兴的年轻女士。她的脸上极明显地显现出“请别可怜我”的神气。
当米拉贝尔坐好之后,我开始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她是什么地方人?她在哪儿上的学?她对什么感兴趣?如此等等。她很快就不耐烦了,并说道:“请说吧,您到底想知道什么?您是想知道我是否有幻肢,对吗?我们不要说废话了。 ”
我说道:“好吧!是的,事实上我们在对幻肢做实验。我们感兴趣的是……”
她打断我说:“没错。绝对如此。我从来就没有手臂。我所有的就是这一些。 ”她敏捷而熟练地用下巴帮着脱下假臂,假臂掉在我的桌子上砰然作响,并且举起她的残肢。“从我童年能记事时开始我就有非常生动的幻肢感。”
我有些怀疑。是否有可能这只是米拉贝尔出于希望才这样想?也许她有潜藏的欲望想要变得正常。我开始有点像起弗洛伊德来了。我怎么能确定她不是在编造呢?
我问她:“您是怎么知道您有幻肢的呢?”
“是这样的,因为就在现在我和您谈话时,它们正在做手势呢。正像您的臂和手那样,当我指点东西的时候,它们也在指点这些目标。 ”
我向前靠了靠,完全给迷住了。
“医生,关于它们还有件有趣的事,这就是它们并没有它们该有的长度,它们短到只有6到8英寸。 ”
“您是怎么知道的?”
米拉贝尔直视着我说道:“这是因为当我带上我的假臂时,我的幻肢要比它应有的长度短得多。我的幻手指本应和假手的手指相配,就像戴手套一样,但是我的幻臂短到只有6英寸长。我对此感到非常沮丧,因为这种感觉很不自然。通常我最后会要求假肢匠减短我假臂的长度,但是他说这看起来太短了而显得滑稽可笑。所以我们最后采取了折衷方案。他给我的假肢比绝大多数假肢都要短,但是没有短到异乎寻常而使它们看起来十分奇怪的程度。 ”她指了指落在桌面上的一只假臂以使我明白。“它们比正常臂要短,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对我来说,这证明米拉贝尔的幻肢并非是她希望要而想出来的。如果她想要像别人一样,那么她为什么会要一只比正常的要短的手臂呢?在她的脑中一定发生了些什么,使她产生了生动的幻肢体验。
米拉贝尔还有另一个论点。“医生,当我走的时候,我的幻臂并不像正常臂那样晃动,就像您的手臂那样。它们僵在身旁,就像这样。 ”她站了起来,让她的残肢笔直地垂在身体两边。她说道:“但是当我讲话的时候,我的幻肢会做手势。事实上,现在我讲话时,它们就正在活动。”
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神秘莫测。当我们走路时负责流畅而协调地晃动手臂的脑区和控制做手势的脑区是不同的。如果没有后天从肢体上连续不断地发来的反馈的话,或许负责手臂晃动的神经回路就不能存在很久。当失去手臂以后,这种回路就废弃掉了或者不再发育。但是负责在讲话时激发起来做手势的神经回路可能是在发育过程中由基因决定的。(有关回路可能先于口头语言之前就有了。)值得注意的是,米拉贝尔脑中产生这些命令的神经回路似乎一直是完整起作用的,尽管在她生活的任何时候她都没有从这些“手臂”上接收到过视觉或运动感觉的反馈。她的身体一直在告诉她:“没有手臂,没有手臂。 ”然而她依然一直体验到在做手势。
这说明负责米拉贝尔身体影像的神经回路一定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不是严格地依赖于运动和触觉经验。有些早期的医学报道声称出生时就没有肢体的病人不会有幻肢体验。然而我从米拉贝尔那儿所看到的却表明我们所有人在出生时就有内在硬件布好线的有关身体和四肢的影像,这种影像可以一直起作用,甚至在遇到感觉上有矛盾的信息时也是如此。除了自发地做这些手势之外,米拉贝尔也能用她的幻肢做随意运动,成年后失去双臂的病人也是如此。和米拉贝尔类似,大多数这种病人也能“伸”幻肢出去“拿”物体、指点、挥手告别、握手或是做一些精巧的动作。他们明白这听上去像是疯了,因为他们理解到他们没有手臂,但是对他们来说,这种感觉体验却是非常真实的。
····
在我遇到约翰·麦格拉思(John Mc Grath)之前,我一直未能领会这种感觉上的运动有多么逼真。这是一位手臂被截的病人,他是在看了一部有关幻肢的电视新闻故事之后打电话给我的。约翰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业余运动员,他在三年以前失去了肘以下的左臂。他笑着说道:“当我打网球时,我的幻手就会做它本来应该做的动作。当我发球时,它就要把球扔出去,而在我打一个高难度的球时,它就想帮我保持平衡。它总是想去接电话。它甚至在餐馆中招手要账单。 ”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求约翰伸手去拿杯子,但是在他的幻肢碰到杯子之前,从他那里把杯子拿开又会怎样呢?
约翰有一种称之为望远镜式的幻手(telescoped phantom hand)。感觉上这只手好像就直接连在残肢上,中间并没有手臂。但是如果某样物体,比如说一只茶杯放在离残肢一两英尺之外,他可以试着伸手去拿它。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幻手就不再留在残肢处,感觉上好像被拉伸了出去去拿茶杯。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求约翰伸手去拿杯子,但是在他的幻肢碰到杯子之前,从他那里把杯子拿开又会怎样呢?幻肢会不会就像卡通人物的橡皮手臂那样被拉长了呢?或是它就停在自然手臂的长度处?在约翰说他够不着之前,我能把杯子移多远呢?他能去拿月亮吗?对真实手臂适用的物理约束是不是对幻肢也同样适用呢?
我放了一只咖啡杯在约翰前面,并要求他去拿它。就在他说他正伸出手去拿的时候,我突然把杯子抢走。
他高叫起来:“喔,不要这样! ”
“怎么回事呀?”
他重复说:“不要这样,您抢走杯子时我的手指刚握住杯子的把手。这真的很疼。 ”
请停一下。我突然从幻手指中抢走一只真的杯子,而病人叫喊起来,哇!当然啰,这些手指只不过是些错觉,但是疼痛却是真的,而且还那么痛,因此我再也不敢重复这个实验。
通过和约翰打交道,我开始考虑视觉在保持幻肢体验中的作用。为什么仅仅“看到”杯子被夺走就会造成疼痛?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考虑为什么人会体验到幻肢运动的问题。如果您闭上眼睛而动您的手臂,您当然能很生动地感觉到手臂的位置和运动,这部分地是由于有关节和肌肉中的感受器。但是不管是约翰还是米拉贝尔都没有这种感受器。事实上他们连手臂都没有。那么他们的这些感觉又是打哪儿来的呢?
说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关于这一谜团我最初得到的线索来自我理解到有许多幻肢病人(或许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不能动他们的幻肢。当要他们动他们的幻肢时,他们说:“医生,我的手臂灌了水泥。 ”或是“它冻在一块冰块中了。 ”我们的一位病人艾琳(Irene)说道:“我想动我的幻肢,但就是动不了。它不服从我的意志,它不听我的命令。 ”艾琳用她的好手臂模仿给我看她的幻臂的位置,给我看它是如何僵成一种古怪而扭曲的姿势。它那样已经有一整年了。当她进门时,她总担心会撞到她的幻肢,这会使它痛上加痛。
幻肢(并不存在的肢体)怎么会瘫痪呢?这听上去好像是自相矛盾的。
我查了病历,发现有许多这类病人从脊髓进到手臂的神经原来就有病变。他们的手臂以前就是瘫痪的,用吊带悬起来或是固定了好几个月,后来因为它们经常碍事而被截掉了。有些病人是被劝说截肢的,或许误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臂痛,或是纠正由这些瘫痪的手臂或腿所造成的姿势异常。在手术之后这些病人常常生动地感到有幻肢,这是无足为怪的,但是使他们极端失望的是他们的幻肢还是像在截肢之前一样僵在老地方,就好像对瘫痪的记忆继续传到了幻肢上去。
这样我们就碰到了似乎荒诞而实有其事的情况:米拉贝尔在她的整个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过手臂,但是她却能动她的幻肢。艾琳只是在一年前才失去了她的手臂,但是她的幻肢甚至一动也不能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仔细地看一下人脑中运动和感觉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请想一下当您或我闭上眼睛做手势时会怎么样。关于我们的身体、四肢的位置及其运动,我们都有生动的感觉。有两位杰出的英国神经病学家布雷恩(Russell Brain)爵士和黑德(Henry Head)(没错,这些都是他们的真名)造了一个术语“身体影像(bodyimage) ”,以此来表示这种和身体对应的(vibrant)内心构造出来的体验集合,也就是有关随时空变化的自己身体的内心影像和记忆。为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产生和维持这种身体影像,您的顶叶皮层就必须把来自许多来源(肌肉、关节、眼睛和运动命令中枢)的信息结合在一起。
当您决定要移动您的手的时候,首先是在额叶皮层上,特别是在称为运动皮层的一纵条皮层组织上发生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运动。这条皮层正好在把额叶皮层和顶叶皮层分隔开来的沟裂前面。就像感觉侏儒正好就在这条沟裂后面占了一条皮层区域一样,运动皮层也有整个身体的一个倒立的“映射图”,不过这一映射图是发信号到肌肉去,而不是从皮肤接收信号。
实验表明初级运动皮层主要是和一些简单的运动有关,例如动动手指或是咂咂嘴唇。就在其前面有一个称为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的脑区,它似乎负责挥手告别、抓住扶手等比较复杂的技巧。这个辅助运动区就像是某种仪式的主持人,它向运动皮层发出一连串要加以执行的运动的特定指令。驱使这些运动的神经脉冲就从运动皮层传送到脊髓,再到对侧身体的肌肉,这样就使您得以挥手告别或是涂口红。
每当有“命令”从辅助运动区送到运动皮层时,它进一步到达肌肉并使它运动。与此同时还有两份同样的命令信号也传送到另外两个主要的“加工”区,也就是小脑和顶叶皮层,告诉它们想做的是什么运动。
一旦这些命令信号送到肌肉之后,就有一条反馈环路起作用。肌肉在收到运动命令之后就运动起来。接着从肌梭和关节发出的信号又通过脊髓送回到脑,并通知小脑和顶叶皮层:“是!命令已经执行无误。 ”这两个结构帮助您对您的意向和实际执行结果进行比较,这就像伺服环路中的温变自动启闭装置那样起作用,根据需要而修正运动命令(如果太快了,就制动;如果太慢了,就增大运动输出)。这样意图就转换成了流畅的协调动作。
····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病人,看这一切和幻肢体验究竟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当约翰要动他的幻臂时,他脑中的额部依旧在发命令信息,因为约翰脑的这一特定部分并不“知道”他的臂已经丢掉了,尽管约翰“本人”无疑知道这一事实。顶叶也在继续监视这一命令,并感到是在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是幻想出来的幻臂运动。
因此幻肢的体验看来至少依赖于来自两个来源的信号。首先是映射图重组,请您回想一下从脸和上臂来的感觉信号激活了对应于“手”的脑区。其次,每当运动命令中枢发送信号到已经没有了的手上时,有关命令信息也送到了包含有我们身体影像的顶叶。从这两个来源来的信息会聚在一起,这就产生了在任一给定时刻和有关幻臂动态相对应的内心影像,当臂在“运动”时,这种影像也在不断更新。
对于一条真实的手臂来说,还有第三个信息来源,那就是从该手臂的关节、韧带和肌梭来的脉冲。幻臂当然没有这些组织,因此也没有来自它们的信号,但是奇怪的是这一事实似乎并未使脑免于受到愚弄,它还是以为肢体在动,至少在截肢的头几个月或头几年里是如此。
不管从生理学上怎样来解释,当以后手臂被截去后,病人还依旧保持着这种更改过的影像:有一只瘫痪了的幻肢。
这使我们回到了前一个问题。幻肢怎么还会瘫痪呢?为什么在截肢之后幻肢还会继续“僵”在那儿?有一种可能性是当真的肢体瘫痪时,它用吊带或支架固定起来,脑还在发送其通常发的命令,要手臂和腿动起来。顶叶监视这些命令,但是现在它收不到适当的视觉反馈。视觉系统告诉病人:“不!手臂没有动。 ”这一命令又重复了一次:“手臂,动起来! ”视觉系统再次回复告诉脑手臂没有动。最后脑终于知道手臂不会动,而在脑的线路里留下了某种“习得性瘫痪(learnedparalysis) ”的印记。这一切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还不得而知,但是这可能有一部分是在运动中枢,也有一部分是在和身体影像有关的顶叶区域。不管从生理学上怎样来解释,当以后手臂被截去后,病人还依旧保持着这种更改过的影像:有一只瘫痪了的幻肢。
如果您能习得瘫痪,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使您不这样呢?如果给艾琳送去她的幻臂“现在动起来了”的消息,那又会怎样呢?而每当如此时,如果她都收到幻肢在动的视觉信号,不错,幻肢听从了她的命令,那又怎样呢?但是如果她连手臂都没有,那么她又怎么能得到视觉反馈呢?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欺骗她的眼睛,使她以为真的看到了她的幻肢呢?
我考虑起虚拟现实来。或许我们可以造成一种视错觉,使病人以为又有了手臂,而且还能服从她的命令。但是这种技术的价格要在50万美元以上,一下子就会把我的整个研究经费都用光。幸而我想出了用一面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普通镜子做实验的方法。
为了使像艾琳那样的病人能知觉到她们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手臂真的在运动,我们做了一个虚拟现实箱。这个箱子是把一个纸板箱的顶部去掉,然后在它里面垂直地插一面镜子。在箱子的前面开两个洞,病人可以把她的“好手”(譬如说,右手)和她的幻手(左手)从这两个洞中伸进箱子。因为镜子插在箱子的中央,所以右手在镜子的右侧,而幻肢则在镜子的左侧。然后要求病人看她的正常手在镜子中的像,并让她把右手稍微动一下直到这个像就好像叠加在她所感到的幻肢的所在处。这样她产生好像看到了两只手的错觉,其实她只是看到了好手在镜子中的像而已。如果现在她向两臂都发命令,要它们做镜面对称的运动,就像在指挥交响乐或拍手那样,当然这时她也“看到”了她的幻肢也在动。她的脑接收到了视觉反馈,证实幻肢正在按她的命令正确地动起来了。这样是否对她能随意地控制她的瘫痪了的幻肢有所帮助呢?
····
菲力浦·马丁内斯(Philip Martinez)是探索这一新世界的第一人。1984年菲力浦从他的摩托车上被抛了出去,当时他正以45英里/时的速度沿圣迭戈高速公路疾驶。他飞过中线,掉在一座混凝土桥的桥脚,他晕头晕脑地站立起来,但还有神志检查了一下是否受伤。头盔和皮夹克使他幸免于难,但是菲力浦的左臂在近肩处给剧烈地拧坏了。就像庞斯博士的猴子那样,他受到了臂撕裂(brachial avulsion),支配手臂的神经给从脊柱上撕了下来。他的左臂完全瘫痪了,了无生气地吊在吊带上有一年。最后医生劝告他做截肢手术。这条手臂只会碍事,而再也不会恢复功能了。十年之后,菲力浦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当时他已经三十好几了,他的残疾反而使他作为一名落袋台球戏玩家而名声大震,朋友们称他 为“独臂大盗(one-armed bandit) ”。
菲力浦从当地新闻中听说了我对幻肢所做的实验。当时他很绝望:“拉马钱德兰医生,我希望您能帮助我。 ”他往下看他失去了的手臂。“我在十年以前没有了手臂。但是打那以后,我的幻肘、腕和手指一直剧痛不止。 ”以后又做了进一步的面谈,我发现在过去十年中,菲力浦一直未能动他的幻臂。它总是固定在一个古怪的位置上。菲力浦是不是得了习得性瘫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虚拟现实箱子通过视觉让他的幻肢“复活”并恢复运动?
我要求菲力浦把他的右手放到箱子里镜子的右边,并想象他的左手(幻肢)在镜子的左边。我命令他说:“我要您同时动您的左右两臂。”
菲力浦叫道:“喔,我做不了呀,我能动我的右臂,但是我的左臂僵住了。每天早上当我起身时,我总是想动动我的幻肢,因为它位置不当,我想动动它也许能缓解一点疼痛。但是, ”他向下看了下他那无法看到的手臂,继续说道:“我从来也未能动这只手臂,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
“好吧,菲力浦,无论如何试一试吧。 ”
菲力浦转动身躯,移动肩膀,把他那没有生命的幻肢“塞进”箱子里。然后他把他的右手伸到镜子的另一边,并试图让它们同步运动起来。当他看镜子的时候,他喘了口气惊叫起来:“啊呀,天哪!啊呀,天哪,医生!真不敢相信,真是想不通! ”他就像个孩子那样跳上跳下。
“我的左臂又接通了。我就好像回到了过去。多少年以前的所有这些记忆又都涌回到我的头脑里。我可以再动我的手臂了。我能感觉到我的肘在动,我的腕在动,又都动起来了。 ”
等他冷静下来一点以后,我说:“好吧!菲力浦,现在请闭上您的眼睛。”
他很明显失望地说道:“啊呀,天哪,它又僵住不动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右手在动,但是幻肢不动了。 ”
“睁开您的眼睛。”
“喔,是的,现在它又动起来了。 ”
这就好像是菲力浦暂时抑制或阻断了通常使幻肢运动的神经回路,而视觉反馈则去除了这种阻断。而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手臂运动的体感一下子就恢复了,尽管这在前十年中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过。
尽管菲力浦的反应令人振奋,并对我有关习得性瘫痪的假设是某种支持,那晚我回家自问:“这又怎么啦?我们让这个人又能动他的幻肢了。但是如果您仔细想想,这种能力完全没有什么用处,这正是那种我们医学研究人员中许多人所责备的对一些神秘现象的研究。 ”我完全明白是决不会因为使一个人移动一只幻肢而获奖的。
但是习得性瘫痪可能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真实肢体瘫痪的人(比如说,由于中风造成的)也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为什么人在中风之后会用不了一只手臂了呢?当供脑的血管堵住之后,从脑的额部到脊髓去的神经纤维缺氧而受到损伤,结果就使手臂瘫痪了。在中风早期,脑发生肿胀,使有些纤维死去了,但是还有些纤维只是暂时性地失去作用,打个比喻说就是“离线(off-line) ”了。此时,手臂丧失了功能,脑接收到视觉反馈:“不行呀,手臂动不了了。 ”在肿胀消退以后,病人的脑还可能继续有某种形式的习得性瘫痪。那么是否可以用镜子那样的小玩意至少部分地消除由于习得这部分因素所造成的瘫痪?(当然了,对于由于纤维受到真正毁坏所引起的瘫痪,想用镜子恢复其功能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在我们能对中风病人进行这类新的治疗之前,我们需要确定这种效果并非像幻肢运动那样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错觉。(请回想一下,当菲力浦闭上双眼之后,幻肢运动的感觉就消失了。)如果让病人用这种箱子练习好几天,以不断地接受视觉反馈,那会怎么样呢?有没49 有这样的可能,脑可以消除习得的损伤了的知觉,而使运动得以永久性地恢复?
第二天我回到办公室,并问菲力浦:“您是否愿意把这个装置带回家去练习?”
菲力浦答道:“当然啰,我很愿意带它回家。我对我能再动我的手臂感到非常兴奋,即使只是一会儿。 ”
因此菲力浦就把镜子带回家了。一星期后,我打电话给他。“情况怎样?”
“喔,很好玩。医生。我每天都用它十分钟。我把手伸进去,到处挥动,看看到底有什么感觉。我的女朋友和我一起用它来玩。非常好玩。但是当我闭上双眼,还是不行。如果我不用镜子,那么也不行。我明白您想要我的幻肢能再次运动,但是如果不用镜子就是不行。 ”
又过了三个星期,直到有一天菲力浦来看我,既激动又兴奋。他说道:“医生,没有了。 ”
“什么东西没有了?”(我还以为或许是他丢失了镜箱呢。)
“我的幻臂没有了。”
“您说的是什么呀?”
“您要知道,是我的幻臂呀,我都有了十年了。再也没有了。我现在只有幻手指和幻掌就悬在肩下。”
我当时的反应是,喔,不会吧!我好像已经用一面镜子就永久性地改变了一个人的身体影像。这会对他的精神状态和心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菲力浦,这可使您感到烦恼吗?”
他说道:“不!不!不!不!不!不!正相反,您知道我肘部一直以来的剧痛吧?每个星期它总要折磨我好几次。好了,现在我没有了肘部,我再也不痛了。但是我还是有手指,它们就垂在肩下,还是发痛。他停顿了下来,显然是要让我理解这一点。他接着说:“不幸的是,您的镜箱不再能起作用了,因为我的手指位置太高了。您能不能把设计改变一下,好消除我的手指?”看来菲力浦把我当成某种魔术师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助菲力浦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我认识到这大概在医学史上还是首次得以成功地“切除”了一只幻肢!这个实验表明,当菲力浦的右顶叶同时得到两种相互冲突的信号时(视觉反馈告诉他手臂又能动了,而肌肉告诉他根本就没有手臂),他的心智就采取了50 不承认的态度。他那受到困扰的脑对付这种离奇的感觉冲突的唯一途径就是说:“真见鬼,根本就没有手臂! ”作为巨奖,菲力浦也连带不再感到幻肘部的疼痛了,因为大概不大可能再在一只不再存在的幻肢上感受到无所附着的疼痛。还不清楚为什么他的手指还在,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手指在体感皮层上受到了过度的表征,就像嘴唇在彭菲尔德的映射图上很大一样,因此可能更难于否认。
····
关于幻肢运动和瘫痪的问题就够难于解释的了,许多病人在截肢后不久所感到的剧痛就更令人不解了,而菲力浦则使我直面这个问题。有哪些生物学上的条件合在一起才会引起在一只根本就不存在的肢体上的疼痛?这有好几种可能性。
这种疼痛可能是由疤组织或是神经瘤(神经组织在断面上所形成的卷曲小团)引起的。脑可能把对这些团块和受到磨损的神经末端的刺激解释为已经不复存在的肢体的疼痛。用外科手术切除神经瘤有时也能消除幻肢痛,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它们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又去而复回。
疼痛也可能部分来自映射图重组。请记住映射图重组通常是有模态特异性的:这就是说,触觉通路管触觉,温觉通路管温觉,如此等等。(正如我指出过的那样,当我用棉球签轻触汤姆的脸时,他感到我在碰他的幻肢。当我滴冰水在他的脸颊上时,他就感到他的幻手上有冷的感觉,而当我滴热水时,他的脸部和幻肢上都感到热。)这大概意味着映射图重组并非是随机的。和每种感觉有关的纤维一定“知道”到哪儿去找适当的靶体。因此在绝大多数人中,其中包括您、我和截肢病人都没有交叉布线(cross-wiring)。
但是如果在映射图重组过程中发生了些许错误(在蓝图中有些小错),因此使得有些触觉输入碰巧输入到了痛觉中枢,那又会怎样呢?每当擦到病人脸部或上臂的一些区域(而非神经瘤)时,甚至只是轻轻地擦到,病人都有可能感到剧痛。轻轻一触就可能产生剧痛,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由于有一些纤维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
坦白说,我们真的还不知道脑是如何把神经活动模式翻译成有意识的体验的,不管是疼痛、愉快还是颜色都是如此。
映射图的异常重组还可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引起疼痛。当我们感到疼痛时,根据需要激活了一些不但传导而且还同时加强或减弱这种感觉的特殊通路。这种“音量控制(volume control) ”[有时也称为门控(gate control)]正是使我们在有不同需求时得以有效地调整我们对疼痛的反应的原因所在(这也许可以解释针麻为什么能起作用,也可能解释为什么有某些文化背景的妇女在分娩时并不感到疼痛)。在截肢病人中完全有可能由于映射图重组而失去了这种音量控制机制,结果产生了一种像回声那样的“哇哇(wha wha) ”回响,并对疼痛加以放大。其次,映射图重组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病理过程或者说是一 种不正常的过程,至少在失去肢体之后发生大规模重组时是如此。很可能触觉突触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重布,它们的活动很可能是混沌的。脑的高级中枢于是把这些不正常的输入模式当成了垃圾,并知觉为疼痛。坦白说,我们真的还不知道脑是如何把神经活动模式翻译成有意识的体验的,不管是疼痛、愉快还是颜色都是如此。最后,有些病人说就在他们截肢之前所感到的肢体疼痛成为一种疼痛记忆而保存了下来。例如,手榴弹就在自己手中爆炸的士兵常常报告说他们的幻手总是在某个固定的位置,紧握着手榴弹,正准备扔出去。这种手痛是钻心刺骨的,和手榴弹爆炸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永久地烙在他们的脑中了。有一次,我在伦敦遇见一位妇女,她告诉我说,在她童年时她曾经有好几个月老是感到她的拇指有一种像冷天时冻疮那样的疼痛。这个拇指后来变成坏疽而被截掉。现在她有一个幻拇指,而且每当天转冷时总感到是生了冻疮。另一位妇女则说在她的幻关节上感到有关节炎痛。她在截去手臂之前就有这个问题,但是在不再有真的关节之后问题依然如故,当天气变得潮湿和寒冷时疼痛就会加剧,这就和关节在被截去之前一模一样。
我所在的医学院中有一位教授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发誓说这是件真事,这是一件关于另一位医生 ——一位卓越的心脏病学家的故事,他由于血栓闭塞性血管炎(Buerger’s disease)而在腿部发生阵发性的痛性痉挛(pulsating cramp),这种病使动脉收缩,并在腓肠肌中产生强烈的阵发性疼痛。
尽管经过多方治疗,始终未能止痛。这位医生完全绝望了,因此决定截去他的腿。他再也不能忍痛活下去了。他找了位外科医生同事并安排了手术,但是令外科医生惊异的是,病人说他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在截掉我的腿之后,您是否可以把它泡在一瓶甲醛里面给我?”
说得最轻,这一要求也是离奇古怪的,但是这位外科医生还是同意了,截掉了腿,把它放在一瓶防腐液中并给了这位医生。他把瓶子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并且说道:“哈!我最终还是得以看着这条腿并嘲笑它说:‘我最终还是摆脱了你!’”不过笑到最后的却是那条腿!阵发性疼痛又回到了幻腿上以资报复。我们那位好医生无法相信地瞪着漂浮在瓶中的肢体,它也反过来瞪着他呢,就好像在嘲笑他想摆脱它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流传有许多此类故事,这类故事说明疼痛记忆的惊人特性,当肢体被截掉后它还会表现出来。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如果在手术之前就对要截去的肢体进行局部麻醉的话,这样就有可能降低截肢以后疼痛的发生率。(确实也试过这种方法,并取得了某些效果。)
····
在所有的感觉中,痛觉是了解得最少的感觉之一。疼痛常常使病人深为沮丧,连医生也是如此,疼痛还常常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从病人那儿经常能听到的特别令人不解的一种抱怨是,他们的幻手不时地 变得紧握成拳,手指深掐进手掌,其力量就像一位职业拳击手在准备挥出决定性的一击时那样。
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是一位聪明的工程师,55岁时,由于癌症而使他截去了肘上6英寸的左臂。我遇到他是在他截肢7个月之后,他非常生动地感到有一条幻肢,这条幻肢经常不由自主地紧握到痉挛。罗伯特说道:“就好像我的指甲要掐进到我的幻手里面去一样。痛得无法忍受。 ”即使他全神贯注想松开这只看不到的手,还是一筹莫展,无法缓解它的痉挛。
我们想知道是否也可以用镜箱帮助罗伯特消除痉挛。就像菲力浦一样,罗伯特朝箱子里看,把他好手的位置摆得使其镜像正好和幻手相重,先用好手握拳,然后试着同时松开两手。罗伯特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就宣称他的幻拳随着好拳一起松开了,这完全是由于视觉反馈53 的作用。更好的是疼痛也随之而去。有好几个小时幻手就一直张开着,直到后来又自发地产生新一轮的痉挛。要是没有镜子的话,他的幻手会抽痛40分钟或更长时间。罗伯特把箱子带回了家,每当他又握拳而痉挛的时候,他就故技重施。如果不用这个箱子的话,即使竭尽全力,他也无法松开拳头。如果他用了这面镜子,手一下子就松开了。
我们对十几名病人试过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大概对一半病人有效。他们把镜箱带回家,每当发生痉挛时,他们就把好手伸进箱子松开手,痉挛也就随之而去。这真是一种治疗吗?很难搞清楚这一点。痛觉极易受安慰剂效应的影响(说服的力量)。或许只要有精巧的实验室设备或是一位治疗幻肢的名医在场就足以消除疼痛了,可能这根本就和镜子没有关系。我们对一位病人检验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给了他一只没有什么害处的电池盒,它可以产生一点电流。我们要他在产生痉挛和姿势不当时,就转动他那个“皮肤电刺激器(transcutaneouselectrical stimulator) ”上的转盘,直到他开始感到在他的左臂(他的好臂)有刺痛感。我们告诉他这会立刻恢复他幻肢的随意运动,并解除痉挛。我们还告诉他这种方法对一些和他有同样问题的病人很有效。
他说道:“真的吗?哇,我恨不得立刻就试。 ”
两天以后他回来了,显然非常恼怒。他叫道:“一点用也没有,我试了5次,就是没有用。我把它转到了头,虽然你们告诉过我不要这样做。”
同一天下午我给他镜子试试,他立刻就能张开他的幻手了。痉挛也没有了,指甲深掐到手掌里的这种感觉也消失了。如果您仔细想一下,这是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这里讲的是一个既没有手,也没有指甲的人。这个人怎么会把并不存在的指甲掐进也不存在的手掌里面去,还由此产生钻心刺骨的疼痛呢?为什么一面镜子就能消除这种虚幻的痉挛呢?
当有运动命令从前运动皮层传送到运动皮层去握拳时,请想想看您脑中发生了些什么呢?一旦当您把手握成了拳,从您手中的肌肉和关节发出的反馈信号通过脊髓回送到脑,并告诉脑:“慢一点,够了。进一步握紧就要握疼了。 ”这一本体反馈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度自动起制动作用。 然而如果肢体没有了,也就不会再有这种制动反馈了。因此脑继续发送命令,再握紧点,握紧点。运动输出甚至得到进一步的放大(直到远远超过你我所曾经达到过的最大水平),这种过度的运动输出或者“竭力感(sense of effort) ”本身可能在感觉上就成了疼痛。镜子的作用可能是提供视觉反馈使手松开,因此也就消除了紧握产生的痉挛。
但是为什么有指甲深掐的感觉呢?只要想一下当您握起拳头而感觉到您的指甲掐入手掌的无数次经历。在您的脑中,这些经历一定在握拳的运动命令和明确无误的“指甲掐入”感之间建立起某种记忆联系[心理学家把这称为赫布联系(Hebbian link)],因此您很容易就在您的心智中唤起这种景象。但是尽管您可以把这种景象想象得非常生动,但是您并不会真正有这种感觉,并且说道:“啊,痛呀。 ”为什么呢?我相信其原因就在于您有一个真的手掌,而这个手掌的皮肤告诉您并不痛。您可以这样想象,但是您不会这样感觉,这是因为您有一只正常的手在发送真实的反馈,在现实和虚幻发生冲突时通常总是现实胜出。
但是截肢病人并没有手掌。从他手掌上并没有发出取消信号以禁止产生原来存储着的疼痛记忆。当罗伯特想象到他的指甲正掐入手掌时,他得不到来自皮肤表面的相反信号告诉他:“罗伯特,你这个傻瓜,这里并不痛呀。 ”事情确实如此,如果运动命令本身和指甲掐入感联系到了一起,那么可以想象如果把这些信号加以放大,就会使和这些信号连在一起的疼痛信号也被相应地放大了。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疼痛会如此难以忍受。其中的含义非常深刻。即使是短暂的感觉联系,就像握拳和指甲掐入手掌之间的那种联系都会在脑中留下永恒的痕迹,并且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表露出来,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感觉到幻肢痛。此外,这些理解还意味着疼痛是对机体健康状态的某种评价,而不只是对损伤的一种反射性反应。在脑中并没有从痛觉感受器到“痛觉中枢”的直达热线。与此相反,在不同的脑区之间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例如那些和视觉与刺激有关的脑区就是如此,只要在视觉上看到拳头松开了,这种信息就会回过来一路馈送到病人的运动通路和触觉通路,并使病人感到拳头松开了,因此消除了在一只并不存在的手上的疼痛错觉。
····
如果疼痛是一种错觉,那么像视觉之类的感觉对我们的主观体验有多大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对我的两个病人做了些多少有点不那么正规的实验。
当玛丽(Mary)走进我的实验室时,我要求她把她的幻肢右手巴掌向下伸到镜箱里面。然后我要求她在她好的左手上带上一只灰色的手套,并伸到箱子的另一边的镜像处。在确定她感到舒服之后,我要我的一名研究生藏身在一只用幕布遮蔽起来的桌子底下,并把他戴有手套的左手伸进箱子中玛丽的好手所在的同一边,放在她手上面的另一个台面上。当玛丽向箱子里看时,她不仅可以看到研究生戴手套的左手(这只手看上去和她自己的左手一模一样),此外还可看到这只手在镜子中的像,就好像她正在看她自己戴手套的幻肢右手。当这名学生握拳或是用他的食指垫(pad)去摸他的拇指球(ball)时,玛丽生动地感到她的幻肢也在动。和我们的前两个病人一样,单靠视觉就能骗她的脑感到她的幻肢在运动。
如果我们愚弄玛丽,让她以为她的手指处在一个解剖学上不可能的位置,那又会发生些什么呢?用镜箱就可以试试这种错觉。还是让玛丽把她的幻肢右手手掌向下伸进箱子里面。但是这次学生做的动作和上次不一样。他不是把他的左手伸到箱子的另一边和幻肢成镜面对称的地方,而是把右手手掌向上伸了进去。因为手上带有手套,它看上去和她的“手掌向下”的幻肢右手一模一样。然后学生屈曲他的食指去触摸他的手掌。玛丽向箱子里看时,就好像她的幻肢食指向后翻转去触摸她手腕的背部,方向完全错了!她的反应会怎么样呢?
当玛丽看到她的手指向后弯时,她说道:“医生,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感觉应该很奇怪,但是并非如此。感觉上手指好像就是向后翻转,而不像人们认为它应该弯的方向。但是感觉上既不古怪,也不痛,或是诸如此类的感觉。”
卡伦(Karen)是另一位受试者,她苦着脸说道弯转的幻肢手指很疼。她说道:“感觉上就像是有人在抓住我的手指拉,我感到剧痛。 ”
这些实验很重要,因为它们和下列理论完全不相容:这种理论认为脑就像是为了应急而临时组织起来的一队人那样由许多自主模块组成。由于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大力宣传,人们普遍相信脑就像是一台计算机,它的每一个模块都执行高度特异化的工作,然后把它们的输出传送给下一个模块。在这种观点看来,感觉信息处理只有从皮肤上的感受器和其他感觉器官到脑高级中枢的一条串行的信息单行道。
但是我对这些病人所做的实验使我懂得脑并不是这样工作的,其中的联结异常多变并随时间发生变化。知觉是从感觉多层次结构中不同层次之间信号的回响中涌现出来的,这种回响甚至可能跨越不同的感觉。视觉输入可以消除一只并不存在的手臂中的痉挛,并且消除了连带产生的疼痛记忆,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了这些相互作用可以有多么广泛和多么深刻。
····
对幻肢病人的研究使我对脑的工作机制有了深刻的了解,这远远超越了4年前当汤姆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开始问的那些简单问题。我们确实见证到了(直接或间接地)在成人的脑中如何产生出新的联结,不同的感觉信息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感觉映射图的活动是如何关系到感觉体验的,而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是:脑怎样不断地更新它内部对现实世界的模型,从而对新遇到的感觉输入作出反应。
最后的这一观察对所谓的先天—后天之争给出了新见解,它使我们问下列问题:幻肢现象主要是来源于像映射图重组或断面神经瘤这样的非遗传因素呢,还是它们只是在精神上要求维持某种生而有之的、由遗传决定的“身体影像”的一种表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是:幻肢是从这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我要讲5个例子给您听,来说明这一问题。
当截肢病人截去的是肘下部分时,医生有时候会把断面劈成像龙虾螯那样的两半,用以代替安装标准的金属爪。病人在手术之后学着用他们断面处的“螯”去抓东西,使它们转向,并以新的方式操控物质世界。有趣的是,他们的幻手(离残肢几英寸处)在感觉上也分成 了两个,在残肢的每半片上都有一或几个幻肢手指,它们都能逼真地模仿所在那片的运动。我知道有一个病例,医生截去了病人的螯形残肢,结果却永久性地留下了分裂的幻肢,这是一个惊人的证据说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可以对幻肢进行解剖。在最初把断面劈开的手术之后,病人的脑一定重塑了他的身体影像,其中包括了两片螯状物,否则他怎么会感到幻螯状物呢?
还有两个故事既有趣又有教益。有一个女孩生来就没有前臂,她感到在她的残肢下6英寸处有幻手,还常常用她的幻手指进行计算和解算术问题。有一位16岁的女孩,生来她的右腿就要比左腿短2英寸,她在6岁时接受了一次膝下的截肢手术,结果使她产生了有4只脚的奇怪感觉。除了那只好脚和另一只预料之中的幻脚之外,她还有两只额外的幻脚,一只正好就在截断处,而第二只脚则连着腿肚一直向下延伸到地板,要是这条腿不是先天就长得短的话,它就本该是这个样子。虽然研究人员曾经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遗传因素在决定身体影像方面的作用,但是人们也可以同样用这个例子来强调非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基因对一条腿要指定三个分开的影像呢?
说明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第四个例子要回到我们对许多截肢病人体验到有生动的幻肢运动的观察,这些运动既有随意的,也有非随意的,但是这些运动最后大多数都消失了。最初感到这些运动是因为脑在继续向截肢之后已经不再存在的肢体发送运动命令(同时也在对它们进行监视)。但是或迟或早由于缺乏视觉上的确认(呀,手臂没有了)就会使病人的脑否决这些信号,因此也就不再感觉到有 运动。但是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又怎样来理解像米拉贝尔这样生而无臂的人会一直有生动的肢体运动错觉的现象呢?我只能作这样的猜测:正常成年人都在一段时间内保有视觉和运动感觉反馈,这使得脑甚至在截肢以后依然期待着有这种反馈。如果这种期望落空,脑感到“失望”,最终就不再有随意运动的错觉,甚或完全失去了幻肢本身。但是米拉贝尔脑的感觉区从来就没有接收到过这种反馈,其结果是根本就没有习得的对感觉反馈的依存性,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的运动感觉可以持续25年之久而毫无变化。
最后一个例子来自我的祖国印度,每年我都要回去一次。在那里可怕的麻风病依然相当普遍,这种病常常使病人不断致残以致失去四肢。在韦洛尔(Vellore)的麻风病院里,人们告诉我这些失去手臂的病人并没有幻肢的感觉,我也目睹了一些病例,并证实了这些说法。对此的标准解释是这些病人逐渐“学会”了利用视觉反馈把残肢融入他的身体影像中,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又如何解释截肢病人一直感到有幻肢呢?或许这是由于逐渐丧失四肢,或者是由于麻风菌也同时逐渐损伤神经,它们以某种方式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这或许让他们的脑有更多时间去重新调节他们的身体影像以适应现实情况。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这种病人的残肢是由于坏疽而切除了有病的组织之后,他们确实也有幻肢现象。但是这个幻肢并非是原来的那个残肢,而是整个幻肢手!这就好像脑有双重表征:一个是由遗传决定的原来的身体影像,另一个则是与时俱进的不断更新的影像使之能把以后的变化也吸收进来。由于某些还不知道的原因,切除手术打乱了这种平衡,而使原来的身体影像又复苏了,这种身体影像一直在想赢得注意。
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些离奇古怪的例子,是因为它们意味着幻肢是由遗传因素和经验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涌现出来的,关于这两种因素贡献的相对大小只有通过系统的经验研究才能得以阐明。正如许多先天—后天之争一样,要想追究哪个因素最重要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在文献中一些极端的说法与此正好相反。(说实在的,问这样的问题并不比问下列问题更有意义:水的潮湿性主要是由构成水分子的氢原子呢,还是氧原子?)但是好消息是通过做恰当的实验,您可以把这两者分开,研究它们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研究出治疗幻肢痛的新方法。即使仅仅只是思考您有可能用视错觉来镇痛都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是请记住疼痛本身也是一种幻觉,它和其他任何感觉一样都完全是在您的脑内构成的。用一种幻觉去消除另一种幻觉看来毕竟不那么令人吃惊。
本文节选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推动丛书:生命系列”之《脑中魅影》(Phantoms in the Brain), 转载已获授权。《脑中魅影》由V. S. 拉马钱德兰和S.布莱克斯利合著,顾凡及教授翻译,各大网店、新华书店有售。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脑和认知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拉霍亚(La Jolla)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副教授。著有《脑中魅影》等,主编有《人类行为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Human Behavi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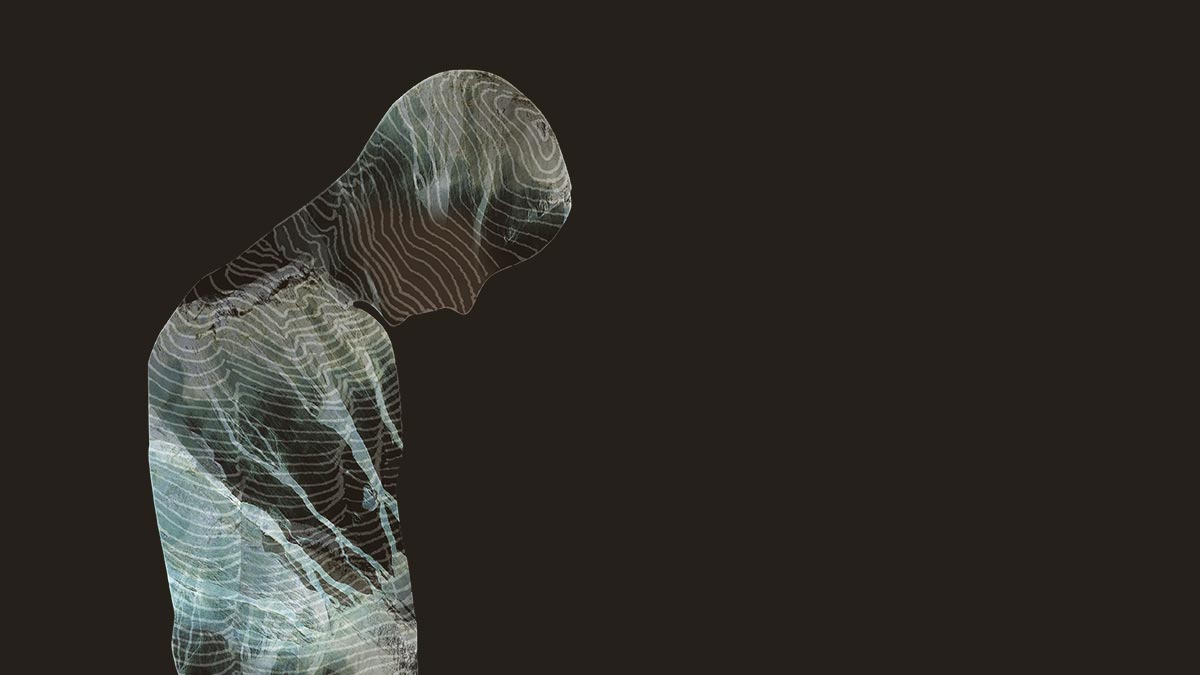


这期干货满满,虽然长了点,看了我半个多小时,但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