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发现亨廷顿舞蹈症的相关基因25年后,一项治疗方案有望治愈这种毁灭性疾病。
“这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詹姆斯说。他们以为是父亲的膝盖出了问题,因为他总觉得膝盖不舒服,一直移动他的膝盖。“他去看病,医生说是骨关节炎。所以他就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但事情没有结束,他父亲的病情恶化了。另一个全科医生说:“别担心你的膝盖了,为什么你总是要动它呢?我把你转到专科医生那里吧。”詹姆斯和他母亲这时才意识到,父亲的行动与膝盖是否有病变无关。
这只是烟雾弹,根本原因其实是亨廷顿舞蹈症。
美国内科医生乔治·亨廷顿(George Huntington)在1872年首先发现了亨廷顿舞蹈症——地球上最残酷无情的杀手之一。该疾病由HTT基因突变导致,会产生一种有毒蛋白质,逐渐摧毁大脑的主要神经束,最终消除患者所有的精神功能。这种突变基因是显性的,意味着只要两个基因拷贝之一突变,就可导致亨廷顿舞蹈症。如果父母一方得此症,孩子有50%的几率遗传它。

对那些有患病危险的人而言,生命是一场在痛苦中等待的游戏。没有特效药,症状一般在40多岁显现,发病后15年左右死亡。确实,发现该疾病的100多年来,那些有一半几率遗传的人要想知道自己是否患病,唯有等待。
直到大约50年前,情况才有所转机。1967年10月3日,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在纽约死于亨廷顿舞蹈症。几个月后,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米尔顿·韦克斯勒(Milton Wexler)的妻子莱昂诺尔·韦克斯勒(Leonore Wexler)也被诊断为亨廷顿舞蹈症。
米尔顿·韦克斯勒和格思里的遗孀马乔里都是有权有势之人,他们一起建立了基金会,来帮助亨廷顿舞蹈症患者,希望提升公众认识并激励更多研究。不过,在有关亨廷顿舞蹈症的科学研究中,最伟大的先驱者是莱昂诺尔和米尔顿的女儿南希·韦克斯勒(Nancy Wexler)。莱昂诺尔死后,米尔顿便开始筹集资金,征集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工作。南希随后接过这项任务,并在国家神经障碍与中风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任职。
查理斯·萨宾(Charles Sabine)曾是战地记者,后来成为普及亨廷顿舞蹈症的社会活动家——他也是一名该疾病基因的携带者。他很确信:“没有韦克斯勒和格思里家族对这一疾病的关注,我们不知道会在何处幸存,指不定会同50年前一样活着。如果没有他们,这个疾病仍是不为人知的秘密。”
的确,找到亨廷顿舞蹈症的发病基因是件难事,毕竟这需要在大规模样本中检测患病与不患病的基因差异。因此,当南希发现委内瑞拉北部的马拉开波湖附近有一大群患者时,她想方设法赢得他们的信任。1979年以后,由韦克斯勒家族领导的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研究项目,从马拉开波取得血液和组织样本,用于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研究。
多亏韦克斯勒家族的努力,1983年,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被定位于4号染色体;10年后更精确的基因序列被找到。
尽管自那时起,患者们就等待着疾病研究能进入下一阶段,但他们失望地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有所突破”的“黎明”。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个靶向基因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初步结果显示,毒性蛋白首次被成功减少。
像詹姆斯这样的家庭也许终于能够改变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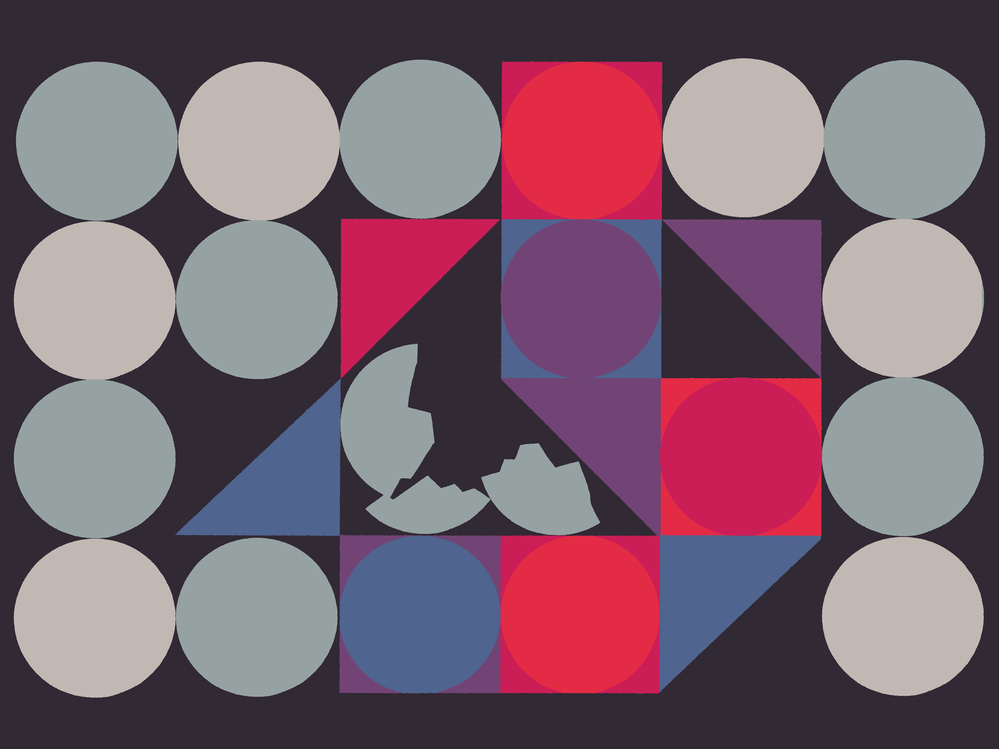
····
“非凡的”,“开天辟地的”,“有突破的”。2017年12月11日,临床试验的结果公布,新闻标题就充斥着这样的字眼。对医学研究的新闻报道,一般泼点冷水是明智的;然而即使是在学术圈,大家的兴奋没比公众差多少。
“我真的认为,这很有可能是过去五十年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最大的突破。”伦敦大学学院(以下简称UCL)的神经科学家约翰·哈迪(John Hardy)对BBC说,“这听起来有点夸张,也许我一年后就会对这种说法感到尴尬,但此时此刻我就是这种感觉。”
UCL的亨廷顿舞蹈症研究中心的项目负责人、这项研究的领导者莎拉·塔布里兹(Sarah Tabrizi) 同样感到兴奋:“自从1993年发现这个疾病的致病基因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系列的希望。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告诉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家庭,治疗方法会出现的。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的进步已经赶了上来。”
在某种程度上,塔布里兹继承了南希的衣钵,成为亨廷顿舞蹈症科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她有热情、活力、能量和信念。她的日程已经排满,将要把这个科学进展好消息告诉全世界。
她的骄傲是很合理的。研究人员自1993年以来一直在研究HTT突变基因。他们早在2000年成功在小鼠体内证实这一突变基因存在,但是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对应的药物、评估在小鼠和除人之外的灵长类动物体内的疗效,才达到这一成就。这是25年来艰辛努力的结果。
ASO可以与携带疾病相关蛋白基因信息的信使RNA结合,然后摧毁这个RNA,防止蛋白的产生。
这个药物IONIS-HTT(Rx),由总部在加州的爱奥尼斯制药公司(Ionis Pharmaceuticals)和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共同研发。目前有很多很有希望的研究正在进行,但是爱奥尼斯的药物是一种反义寡核苷酸(ASO),这是首款被认为可能对抑制病情有效的药物。ASO可以与携带疾病相关蛋白基因信息的信使RNA结合,然后摧毁这个RNA,防止蛋白的产生。
爱奥尼斯的团队想要减少突变亨廷顿基因产生的蛋白质,防止其伤害大脑。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是需要只针对突变的蛋白,还是要全面下调所有HTT蛋白(正常和突变的)的表达。研究显示,后者是正确的策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唐·克利夫兰(Don Cleveland)实验室与药厂的合作研究在小鼠体内证实了这一观点。
下一步就是从几千种ASO中筛选可以安全有效下调人类HTT蛋白的候选药物。“我不喜欢用‘基因沉寂’这个词,因为ASO不是这样的机制,”塔布里兹说,“还需要留下足够的HTT蛋白来执行功能。”
筛选ASO之后,UCL的临床试验证实了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以通过脊髓注射下调脑脊髓液中的HTT蛋白水平。这个结果的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它的生物效果:在人体中下调蛋白表达的成功,“是超出我预期的,”塔布里兹说。
····
受到亨廷顿舞蹈症影响的人们也有了强烈地希望。但是直到治疗可以普及之前,他们面临的选择仍然很有限。虽然有一些药物可以缓解症状,如抑郁、情绪不稳定和非自主运动,但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减缓病程。
生病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茫然困惑和体重下降。记者夏洛特·瑞文(Charlotte Raven)已经发病7年了。她很瘦,还能大声说话,但是她再也不能阅读:“那些字我就是读不进去。”作为一个作家和编辑,她深切体会到这个疾病的伤痛。她不能继续运营热闹的杂志社,因为策划和协调活动太难了。“我只能坐下来听广播4台。戏剧我是听不进去的,但是新闻可以。”

对于像夏洛特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上一个重大突破是检测方法的出现。一种准确率为90-95%的检测方法是在1983年HTT基因被定位之后出现的,需要几个家庭成员帮助来做诊断。1993年基因序列被确定之后,几乎100%准确的方法出现了。但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加深了悲剧。
詹姆斯说道:“当疾病被发现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自己会病如山倒,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想想吧,你为什么会想要知道诊断结果呢?”没有治愈方法,做检测只是把一个人50%的希望变成100%的悲剧。很多人决定观望。直到今天,英国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高危人群做了这个检测。
只有在想建立家庭时,人们通常才会想到去做这个测试。这也是为何这个疾病的治疗始终没有受到关注。
伊丽莎白·罗瑟(Elisabeth Rosser)是伦敦大奥蒙德街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的一名临床遗传学顾问,储存了一些与疾病检测相关的心理态度的数据。牛津郡的80个人被邀请参加这个完全可靠的检测,他们之前通过那个90-95%准确率的检测为阳性。当她让我猜有多少人选择做这个测试,我猜有十个,她说太多了。只有一个人接受了这个检测。
“他们宁愿要5-10%的疑惑和希望。”罗瑟解释说,就是这一点点诊断错误的可能。相反地,那些之前检测阴性的人也不想接受这个新的检测,“他们怕莫名其妙地失去几乎是确定的没有疾病的结果。”但是这一治疗带来的兴奋足以改变这些。在症状开始之前及早治疗总是好的。
只有在想建立家庭时,人们通常才会想到去做这个测试。这也是为何这个疾病的治疗始终没有受到关注。在疾病检测方法出现之前,那些有风险患病的人选择不要孩子——他们的自我否定有50%的可能是不必要的。另外有一些人选择赌一把。但在这个测试可行之后,这些人有了第三个选择——着床前胚胎遗传学诊断(以下简称PGD),尽管这个方法也有局限。
PGD需要体外受精,把没有HTT基因变异的胚胎筛选出来。从2013年开始,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下简称NHS)为有患病风险的伴侣免费提供3个疗程的PGD。附带条件是,假如成功,NHS不会继续为下一个孩子的基因诊断买单。在私人机构做PGD的价格大约是15000英镑,也就是一个兄弟姐妹的价格。
这项检测、对于生育的渴望、PGD以及治疗方法的缺失,这些在不同家庭中以各种排列形式出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想要个健康的孩子,虽然PGD可以明确父母是否患有亨廷顿舞蹈症,但詹姆斯夫妇和其他有着这一疾病家族史的家庭一样,都不想知道结果。PGD是通过应用一项被称作排除测试的程序来实现对疾病的检测。它的原理是看子代的胚胎染色体是从哪个祖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在詹姆斯这个例子中,任何携带来自詹姆斯父亲的4号染色体的胚胎可以被排除。
这对詹姆斯和他的妻子是有价值的,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宝宝在12周时夭折了。 “这对我的妻子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说。他们想再次尝试,但他们渐渐明白有个健康的宝宝是不可能的。有患病风险的詹姆斯成了问题的症结,最终他们分手了。詹姆斯决定,如果他想要再开始一段婚姻并生育,去做一下这个检测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在2017年9月,他收到了结果:他没有亨廷顿舞蹈症。顿时他感觉未来一片光明。
而对于路易丝和西蒙来说,事情有着相似的开头,但结局却大不相同。“我们直到父亲被诊断出疾病之前都不知道家里有这种病,”路易斯回忆道。她和她的姐姐现在处于高危状态中,是否接受测试的选择题搞得她们“团团转”。但路易斯说,“PGD是我们能做出的最佳的选择。”像詹姆斯和他妻子一样,路易丝和西蒙选择了排除测试。结果很成功,他们现在有了一个男孩。
但是路易丝明白,如果她需要治疗的话,她将采取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它决定着我的人生。如果我需要治疗,我会去积极了解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所以如果我的检测是阳性的,我可以尽快开始治疗。”
詹姆斯夫妇、路易斯和西蒙选择这一检测的情况很特殊——他们对PGD的可用性以及对所有可能干预措施的了解都很少。伦敦南部圣乔治医院的临床遗传学家爱安娜·拉系里(Nayana Lahiri)报告说,自1993年突变基因测序可行以来,英国的产前检测一直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每年平均只实施20多项检测。现在PGD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英国,2015年至少完成了50个疗程,但这只代表近期的大幅度增加。从2002年推出这一项目到2009年,疗程的平均完成数从未超过20次。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该疾病是无法治愈的,但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对待疾病的方式。夏洛蒂·拉文有个女儿安娜,2005年,就在安娜的父亲被诊断为亨廷顿舞蹈症的前几个月,她决定接受测试,结果是阳性的,接踵而来的是“多年的痛苦”。夏洛蒂担心安娜“太过孤独”,所以她和她的丈夫决定再生一个孩子。“我记得我考虑过自己去测试胚胎,”她说,但最终她并没有去“治愈这一切”,而是决定不去尝试。正如她在《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胜过了忧虑,我们的儿子在安娜的妹妹出生五年后也出生了。”然而,两人都必须等到18岁才能去测试他们是否继承了错误的基因。
····
PGD会使一些家庭忧心于遗传亨廷顿舞蹈症,但它也只能做这么多了。显然,在未来某一天突然出现这个病,这不仅仅是家庭总是尝试掩盖它的结果,它的本质就意味着突如其来。在突变的HTT基因中,特定的DNA碱基三联体CAG异常复制。在两个HTT基因中,如果CAG低于26组,你就不会得这种疾病,但如果其中一个有超过40组,你得这种病的几率会随着异常复制的增加而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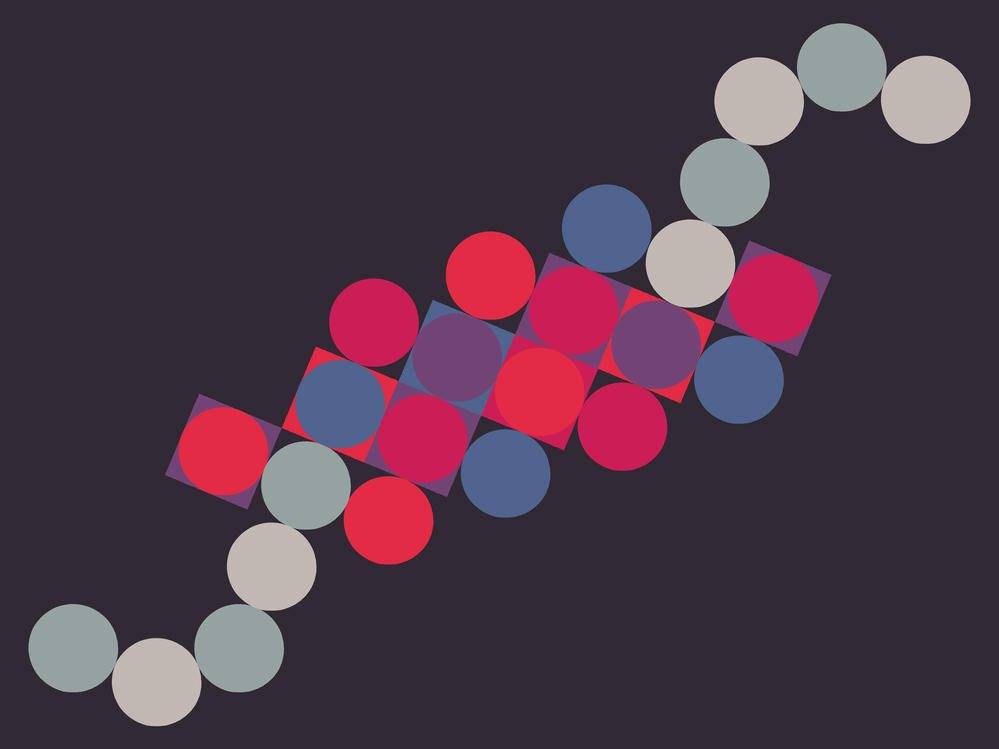
在CAG复制26-40次中间,有两个灰色地带。如果你有27-35次的复制,你不会得亨廷顿舞蹈症,但你的孩子可能会得,因为基因复制在隔代中变得不稳定,一般情况是复制此处增加,特别是在男性后裔中。复制36-39次,你有可能会得这种病,但是无论你得不得,你的孩子都会面临更高的风险。一旦你复制达到36,在下一代增加复制次数的趋势尤为明显。
在英国,估计有6千到1万人患有亨廷顿舞蹈症,另有2万5千人有患病风险。但如果把2016年加拿大疑似病例研究(36-39次重复)的患病率数据放在英国,英国还有约15万人可能会将更高的风险遗传给子女。
米兰大学的艾琳娜·卡塔内奥(Elena Cattaneo)绘制了HTT基因的整个生命历程(这一基因可以追溯到十亿年前),以此来探求为什么CAG复制的数量会有这种从一代到下一代增加的特点。该基因的第一次出现(没有复制)是在单细胞变形虫盘基网柄菌中。然后在海胆中开始出现第二次复制,然后在动物进化过程中复制逐渐增加。
亨廷顿舞蹈症可怕的破坏性实际上可能是“最终使我们成为人类的生物过程的支流”。
这一基因的复制率在人类中是最高的,并且有证据表明,接近“危险区”的复制次数可以实现更高的认知功能。佛罗里达中央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安博·索斯维尔(Amber Southwell)说,核磁共振研究表明,接近安全范围最大值(多达35个CAG重复序列)的人群比那些重复序列少的人群具有更多的大脑灰质。
的确,HTT基因中增加CAG的复制可能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这有助于将人类的智力提高到超过其他动物的智力。正如卡塔内奥和她的同事基亚拉·祖卡托(Chiara Zuccato)所说,这揭示了这种疾病的潜在悖论:亨廷顿舞蹈症可怕的破坏性实际上可能是“最终使我们成为人类的生物过程的支流”。
CAG序列复制次数的上升仍在继续。 “无论你的生育规划有多好,都不能消除亨廷顿病的突变,”索斯维尔总结说。或者正如查尔斯萨宾所说的那样,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未来的疾病”。
····
在宣布UCL试验成功的那一天,瑞士制药巨头罗氏(Roche)宣布将花费4500万美元将IONIS-HTTRx推向下一阶段:一项III期试验,涉及数百名患者的长期评估,观测它是否能改善症状。在这个阶段,仅能够表明它能够对抗亨廷顿病的成因(基因转录),而与疾病本身没多少关系——尽管爱奥尼斯及其合作者已经使用ASO改善了小鼠的症状。
虽然得到这个结果已经足以使人感到兴奋,但莎拉·塔布里兹依然十分谨慎:事情的发展依然需要时间。“我们预计这项研究的规划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然后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善。在这些研究中,如果该药在保持良好安全性的同时为亨廷顿病患者提供临床益处,罗氏将申请批准上市。”最终,这将决定一个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能够最终被实现。
一些专家认为,使用爱奥尼斯药物的非选择性方法来同时降低正常和突变亨廷顿蛋白是一种不稳定的方法。虽然有研究表明,减少亨廷顿蛋白,甚至完全敲除它,在成年的小鼠中耐受性良好,但索斯维尔认为,风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明确:“我认为你无法在九个月的时间内得出结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对人类几十年的治疗。”
这将成为临床试验的主要关注点:IONIS-HTTRx在历经多年的使用后仍然能保证安全吗?通过什么途径注射呢?通过将药物注入脊髓使药物进入大脑,这意味着大脑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药物浓度更高。在几十年的治疗过程中,想在病变的位置降低突变型亨廷顿蛋白和在无病变的地方降低正常蛋白质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
除了所有这些技术之外,我们真正希望能做的是剪掉那些额外的CAG重复序列。
因此,我们正在积极寻求其他治疗方法。单独针对亨廷顿舞蹈症突变的蛋白是索斯维尔首选的方法,但它需要一些创新支持:迄今为止我们开发的所有复杂的遗传工具都不是很擅长计数。让这些遗传工具挑选具有40个CAG重复序列并抑制HTT基因,同时仅保留35个CAG重复序列的正常优秀基因是极具有挑战性的。但有一种方法可以。
基因是以模块为单位遗传的,这些模块被称为单倍体模型,它们大多随染色体一起运动,而亨廷顿舞蹈症的变异仅伴随着几个这样的典型模块。这意味着不必计算CAG重复序列数据以区分正常或受到抑制的HTT基因;相反,可以在附近的遗传物质中寻找变异信号——单倍体模型之间不同的DNA碱基,我们把它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使用这种技术来研究靶向突变基因正在朝着人类临床试验迈进。
另一种选择是AMT-130,一种由荷兰UniQure公司研发的基因疗法,该技术使用工程病毒干扰RNA进入细胞以抑制突变基因表达。这是项很超前的技术,因为它可能一次剂量终生治愈,临床试验将于今年开始。
最后,还有另一种策略是由UCL亨廷顿舞蹈症中心的主任吉尔·贝茨(Gill Bates)领导的,他是1993年发现HTT基因的研究人员之一。有一种使突变的亨廷顿蛋白毒性增加的物质,它是由HTT发生错误时产生的一种蛋白。贝茨的工作是研究如何防止这种蛋白质的生产。
对其他疾病的治疗,比如癌症和艾滋病,往往会涉及多个公司,所以这不是一种竞争。 塔布里兹设想了将上述方法和其他方法在未来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由病毒传递的干扰RNA可以被传递到纹状体(大脑受亨廷顿舞蹈症严重影响的部分),一种类似于爱奥尼斯的药物可以针对皮质进行靶向治疗,而一种小分子药物可减轻这种疾病对人体的影响。
但是,除了所有这些技术之外,我们真正希望能做的是剪掉那些额外的CAG重复序列。由于基因编辑工具CRISPR的存在,这个项目所必须的技术手段已经就位了。CRISPR自2012年被发现以来,已被用于针对小鼠中HTT基因的靶向治疗,并成功恢复了正常功能。但它的主要困扰在于,无论它在基因组中发现哪一个DNA序列,它便会将那个DNA序列作为目标,但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的CAG重复序列。除非我们确保不会出现脱靶效应,否则CRISPR仍存在风险。这一风险一旦产生,遗传变化是不可更改的,也就是说出现任何不可预见的后果都不能再逆转。
因此,为了解决亨廷顿舞蹈症的问题,有很多正在进行的大有前途的工作正在努力寻找治疗方法。但是,UCL亨廷顿舞蹈症中心的临床科学家艾德·怀德(Ed Wild)说,“新闻稿中存在很大的炒作问题。”这也是他参与创立了博客HDBuzz的原因——以此在该领域研究中传播“更切合实际的叙述”。(夏洛蒂·拉文有另一个名字:HDBuzzkill)。对于先进的治疗方法:爱奥尼斯药物,强调了关键的III期试验的必要时间周期:可能需要三到四年,再加上成功拿到许可的时间,所以大概共需要五到六年。
尽管如此,塔布里兹仍然充满信心。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自1993年HTT基因发现以来,很多家庭一直坚持接受亨廷顿舞蹈症的治疗。“现在我们可能能够提供更精准的药物,改善每个受影响者的生活。”她说。其他人也都信心满满。约翰·哈迪认为,爱奥尼斯药物可能是治疗许多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测试案例。甚至连HDBuzz都声称爱奥尼斯2017年12月所得到的结果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最好的早期圣诞礼物”。
但最后一句话应该留给受影响的那些家庭成员去讲。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试用的成功非常激动。詹姆斯虽然很兴奋,但同时也有他的担心:“当他们设法许可试用药物并进行进一步测试时,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的父亲现在已经处于疾病的晚期阶段。
但对于年轻女性杰西卡·威尔逊来说,她的测试结果为阴性,但她有两名家庭成员患有亨廷顿舞蹈症,并且其他几个人仍处于患病风险之中,不过她很期待地说:“可以说,如今我将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担心疾病出现,如今我将永远不会像之前那样受到测试结果的打击。这个世界已经让我们遭受最困难的经历。”
翻译:张瀚桢,赵赫
校对:肖荷
编辑:EON
原文:Mosaic, How close are we to a cure for Huntington’s?
科学作家,文学编辑,现居伦敦。他主要写生物学和医学等话题。他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评论,例如《卫报》、《金融时报》、《万古》和《自然》等,著有《Dazzled and Decei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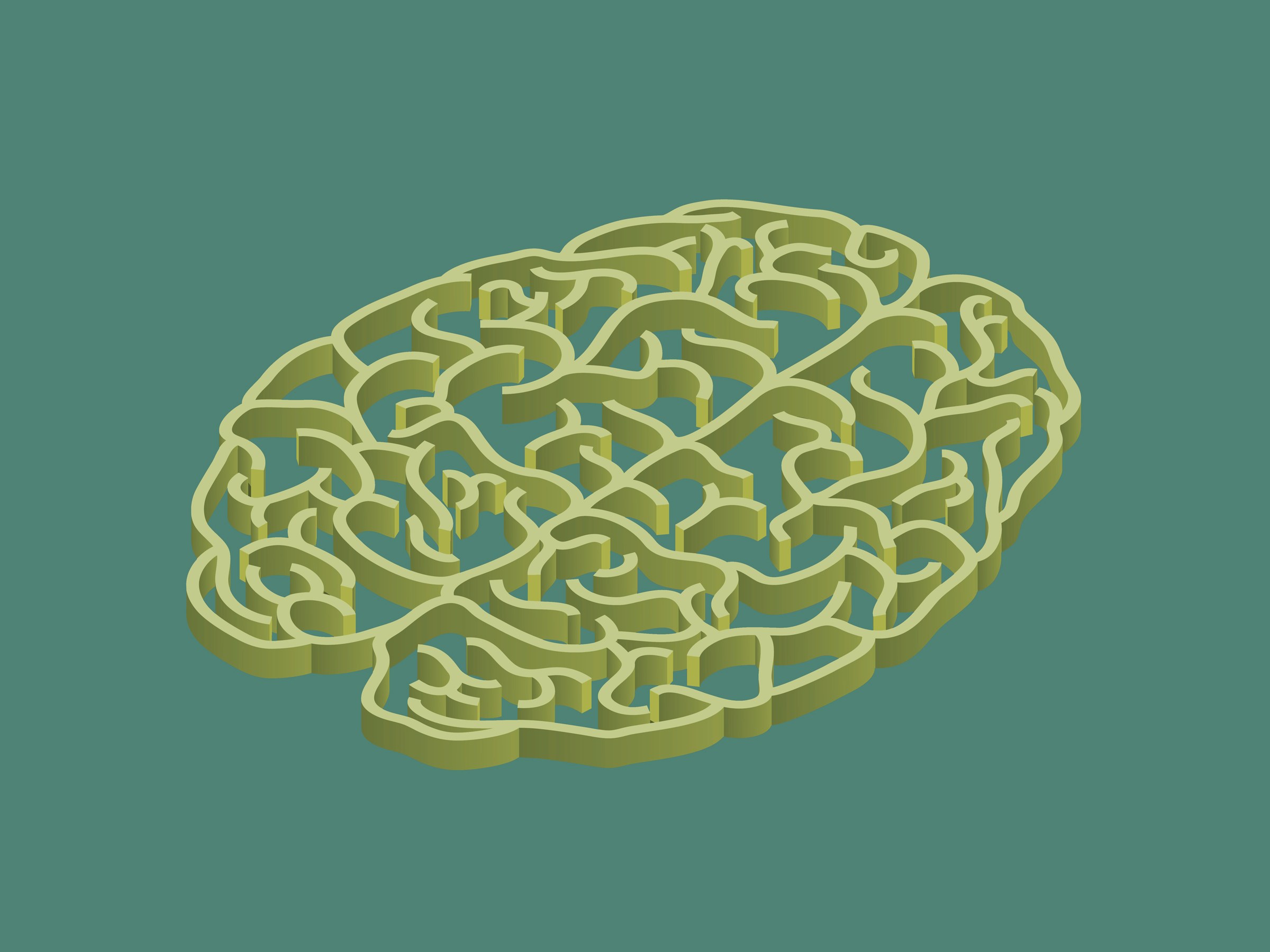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