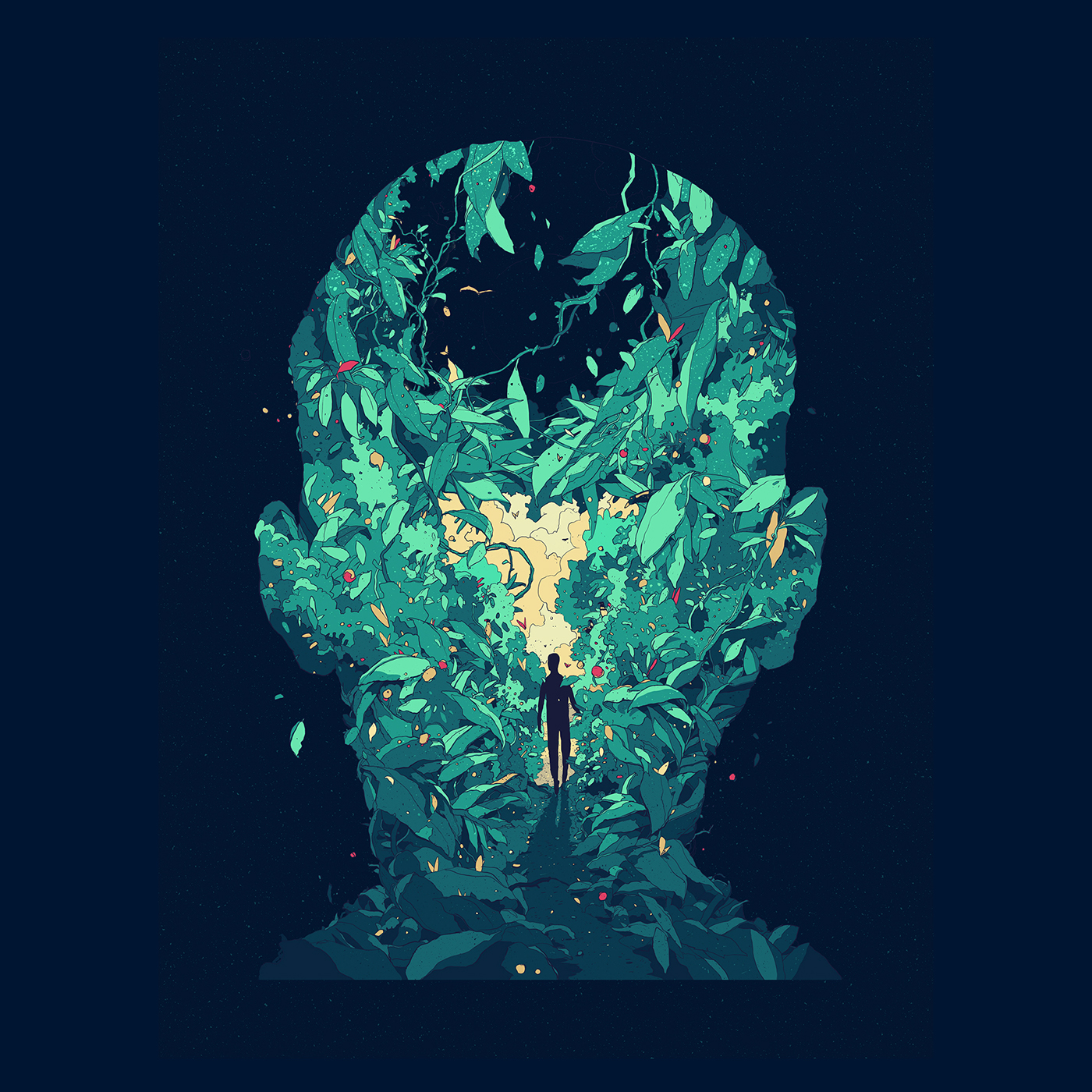

2015年冬季,奥利弗·萨克斯在去世前六个月,给《纽约时报》写了一份类似于讣告的文章。他表达了对自己的一生、对相识的朋友以及对所追求的学术生涯的感激之情。 他写道:“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从全局角度俯瞰了自己的人生,对于它各个局部相互之间的联系有了深刻的认识。”
从广角镜头看待事物,将看起来不相关的细节连接起来,这种能力极大地辅助了萨克斯,也使他拥有诸多头衔——内科医生、神经学家、作家,甚至是过去半个世纪最有名的非虚构类作家。他很擅长书写大脑和心智领域的奇闻轶事,并在描述案例研究方面极具洞察力和同情心。 (《时代周刊》称他为“当代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虽然擅长调查神经系统失常,但他的兴趣要更广泛一些。《意识之河》(River of Consciousness)收录了他之前发表的10篇论文,该书篇幅不长但涵盖多方面内容。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 萨克斯描写自然的角度如同达尔文或者是奥杜邦,他也能够涉猎到物理领域又不失可信度,他能够很精确地探索科学历史,精确程度在学术界外的确罕见。(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假使萨克斯感兴趣的话,可能会编写一些像西方思想史上六位著名思想家的传记,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威廉·詹姆斯。)

萨克斯从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如实描写他的所写所想就已足够。该书的第九篇文章中这样告诉我们,他当时只是坐在第七大道上喝咖啡,慢慢地看着眼前的世界:
我的注意力来来回回,有时候停留在一个经过的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或是溜着一只顽皮的狗的男人,太阳(最后!)从云端里出现。还有其他不仅仅是视觉上出现的事物,例如汽车开引擎的声音,邻座借火点起的香烟味,这些都是一瞬间吸引我的事物。
这些足够提醒我们,意识体验虽然平凡常见,但是身处意识的体验过程却是很令人吃惊的。但我们下面要说的才是需要探讨的:为什么在众多可能获得的感知之中,我们唯独抓住了这些?
到底是为何呢?大脑——由三磅极其复杂的灰质和白质组成的结构,通过感官接受到大量信息,无数电化学信号中,最细微的一些信息流找到了进入我们意识世界的方式。萨克斯并没有提出一种全新的意识理论,但他是罗列问题、定义术语、提醒我们谜团在哪里的高手。由于视觉相对比较容易探测,长期以来都是意识领域研究最常见的入口。威廉姆斯·詹姆斯将视觉感知比作万花筒中闪烁的图像;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则把它比作电影帧通过投影仪时短暂闪烁的光芒。
最近以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他的支持者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在研究感知和意识的“神经相关区”。同时一名生物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也提出了“神经达尔文主义”的意识理论,他的理论关注神经元群的行为以及它们随时间出现的变化。萨克斯通过自己的理解研究进一步发展了他们以及其他思考者的观点:我们的大脑会以某种方式将一些片段编织成经历,再将经历串成记忆,记忆逐渐形成自我。(我还是很好奇如果萨克斯之后是否有读到物理学家朱利安·巴伯(Julian Barbour)1999年的作品《时间终点》(The End of Time),因为巴伯提到只有片刻是真实存在的,其他的都是幻想。)
长期以来,我们发现爬行动物可能是第一批拥有类似“意识流”的生物。两栖动物可能没有这种体验。(当一只苍蝇在视线范围内时,青蛙会反射性地展开它的舌头,但它不会像壁虎或变色龙那样到处看看吃东西。)萨克斯是自然主义者也是神经科学家,但萨克斯同时也是历史学家。这让我们想起达尔文,那个好奇蚯蚓是否有心智的人。
意识的本质是让萨克斯着迷的谜团中最深奥的一个,但时间知觉和记忆机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萨克斯出生在伦敦郊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是个孩子。在写第一部自传《钨舅舅》时,他剖析了自己的战时记忆,生动地描述了两次德国的轰炸袭击(记载于《记忆也会犯错误》的短文中)。在第一次袭击中,炸弹没有爆炸。他的家人和邻居“悄悄溜走…..很多人还穿着睡衣……带着用红色绉纸降低亮度的手电筒。”在第二次袭击中,“一枚燃烧弹,一颗铝箔炸弹落在我们家后院,燃起一股可怕的白热烟气。父亲拿出手摇泵,哥哥们拿了水桶,但在这股地狱之火面前,水似乎毫无用处。
《钨舅舅》出版之后,萨克斯震惊地发现其中一个记忆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两件事都发生了,但他只亲眼看到了第一件事。就像他的兄弟迈克尔解释说,第二次袭击发生时,他和萨克斯在农村,但他的“回忆”却与他们的哥哥戴维在信中的描述完全吻合。戴维的描述最终形成萨克斯的记忆。如果没有迈克尔的提醒,萨克斯是否会发现错误的记忆? “精神分析,或者说,大脑投影能够察觉出这种差异吗?”
但当一国总统出现这种情况时,这种“记忆”则要面对更细微的检查。萨克斯指出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竞选总统时说道,二战期间敌方的炮火摧毁了我方的一架轰炸机,有名机组人员受伤严重无法逃出,飞行员选择在飞机旁死去。但这也不是真的,这是1944年一部片子《飞行之翼》中的片段。(我在08年《探索时间之谜》一书中谈及到布什总统也有关于“9·11袭击”残缺的记忆,他“回忆”说曾在电视上看到第一架飞机袭击世贸大楼,但这不可能,这是之后才出现的画面。当然特朗普对阿裔美国人在新泽西庆祝911袭击的“回忆”也是虚构的,这或许是来自以色列占区的一个片段。)
萨克斯写道:“尽管一些我们最珍视的回忆可能从没发生过,或可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意识到这件事仍让人无比惊奇。奇怪的是,这种异变情况比较少见,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记忆是那么可靠可信。”
萨克斯在2015年《纽约时报》的那份讣告中的结尾表达了这样的感激之情:“最重要的是,能够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成为一具富有感情的生命体,成为一种能够思考的动物,于我,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荣幸和冒险之旅。”但是,读过《睡人》或《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的人都知道,也正如这些文章提醒我们的那样,能享有这份荣幸并参与到这场冒险的是我们所有人,应为此心怀感恩的也是我们所有人。
翻译:JH
校对:tangcubibi
编辑:EON
原文:https://undark.org/article/book-review-sacks-river-of-consciousness/
科学新闻记者,奈特科学新闻学者,著作有《莎士比亚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hakespeare),畅销书《探索时间之谜》(In Search of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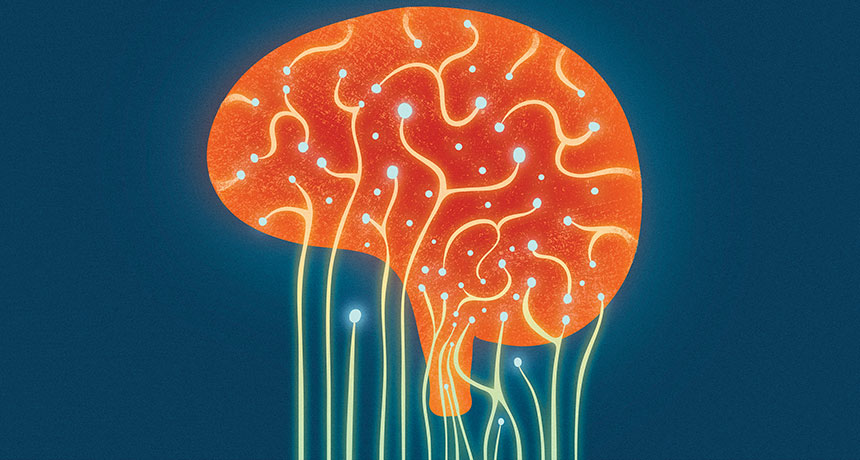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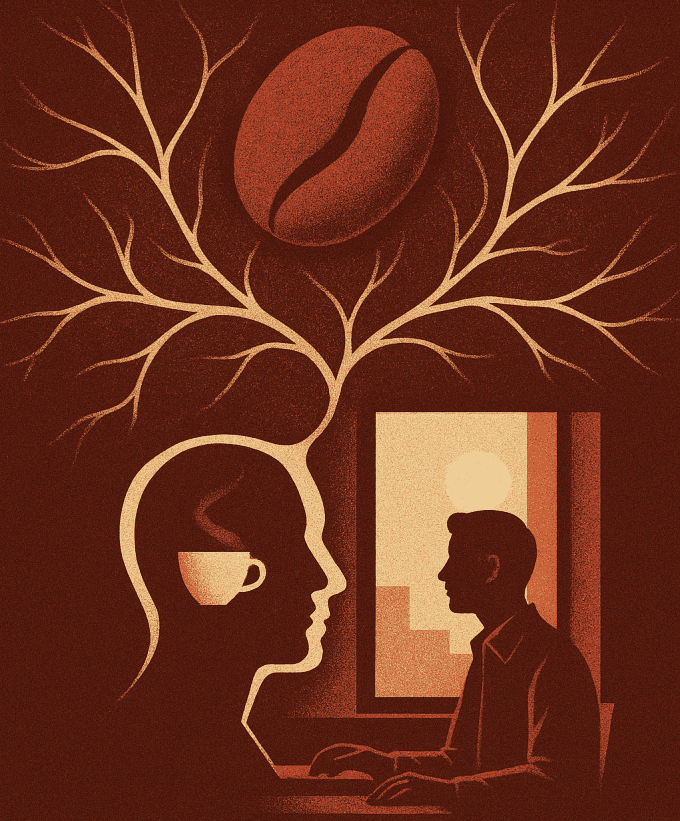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