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个没有自杀的世界,可能吗?
儿子18岁那年自杀后,一位父亲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在越来越多的精神卫生专家的帮助下,他试图降低全世界的自杀率,最终实现零自杀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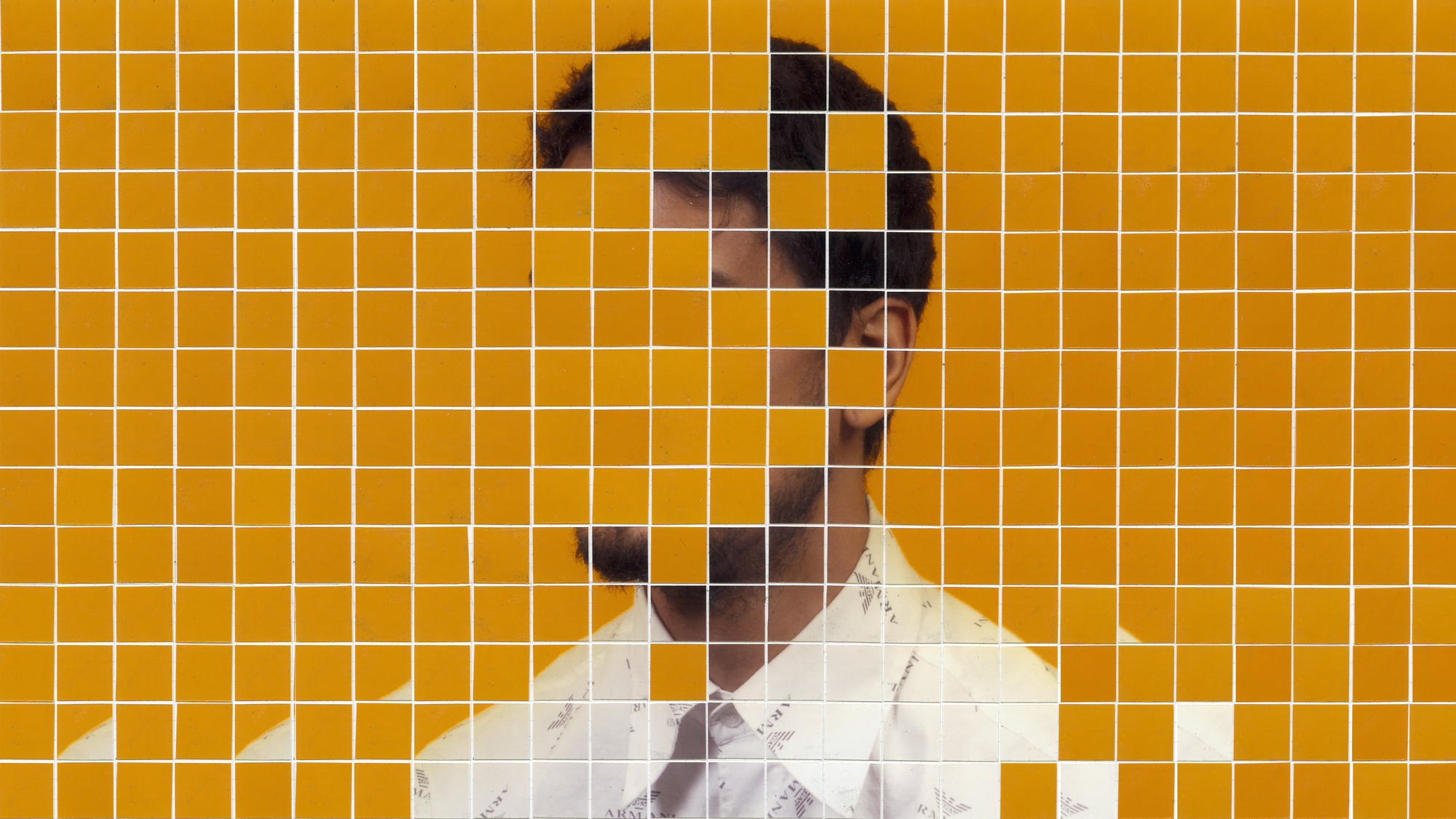
儿子18岁那年自杀后,一位父亲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在越来越多的精神卫生专家的帮助下,他试图降低全世界的自杀率,最终实现零自杀的目标。
史蒂夫·马龙(Steve Mallen)认为,他的儿子不再弹钢琴时,就已经出现自杀征兆了。18岁的爱德华(马龙的儿子)是个音乐天才,很小的时候就通过了钢琴八级,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热衷于练琴。然而,随着成长,爱德华变得异常繁忙。他获得了剑桥大学地理专业的录取通知,并为英国高中课程考试努力复习。在学校,爱德华是学生代表,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他的弟弟妹妹们也很崇拜他。
“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有多重要。”马龙觉得儿子中断弹琴这一行为仅仅类似于音乐中的一个停顿,“我们只是想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弹了这么多年钢琴了,他太忙了……’我现在才知道,那些在正常生活中如同涟漪一般、不被注意的小事,有可能非常重要。”
爱德华停止弹钢琴的三个月后,剑桥以南十公里的梅尔德雷斯小镇,警察敲开了马龙家的门——就在两周前,爱德华刚向老师递交了他的一篇英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老师视作她读过的最棒的作品。警察上门时,马龙独自在家。
“你非常痛苦地意识到,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了,”马龙回忆道,“警察对此表示同情并下达了一份死亡通知,你逐字逐句地读完,他们就离开了。仅此而已。突然间你眼前仿佛出现了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深渊。”
马龙再次听到儿子弹奏的钢琴声,是在充满了音乐的圣三一教区教堂。教堂距离爱德华每天早晨乘火车去上学的车站一英里,2015年2月9日,他在那里自杀身亡。史蒂夫说有500人来到爱德华的葬礼,朋友们组建了一个音响系统来演奏过去用手机拍摄下的他的表演。“我的儿子在自己的葬礼上演奏了音乐,”马龙在伦敦市中心的一间咖啡厅里喝了一杯茶,回想着那天的场景,“这真是做梦都想不到。”
我第一次和马龙聊天是在2016年11月,爱德华去世后的第21个月。马龙52岁,一头白发,穿着海军蓝外套,白衬衫上佩戴着代表纪念的罂粟花。他用一种商务式的语气措辞完美地跟我谈话。显然,他并没有跨过那道深渊。他说生活总是如此。但生活同时也变成了一种使命,儿子自杀后的两年里,马龙从一个商业地产顾问变成了一名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心灵的感召者。他赢得了首相的倾听,并向健康委员会提供了相关证明,他的书房里堆满了文件和研究论文。
“作为一个父亲,我只有一件事要做,可我却失败了,”他的声音变得哽咽,“不论我是怎么教育孩子的,身为父亲有多爱他们,我的儿子就在我面前逐步走向死亡,我却毫不知情……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内疚感。我想要做的就是从回溯中拯救我的孩子。我站在教堂旁的棺木边上,那里挤满了社区中为他感到疲惫、心碎的人们。在那里我向他公开承诺,我会调查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会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一代年轻人寻求心灵上的改革。

“坦白说,我只是一个履行对儿子承诺的人。这可能是你能想到的最大动机,因为我不会再让他失望。”
····
爱德华是2015年记录在案的英国的6188名自杀者之一。在英国,平均每天有17人、每3小时有两人死于自杀。自杀是35岁以下女性和50岁以下男性的主要死因。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5年全球约有77.8万人因自杀而死亡。在一些地方,每40秒就有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科学在进步,政治和舆论对精神卫生日渐重视,英国的自杀率在过去几十年中下滑得并不明显,仅从36年前的0.147‰下降至2015年的0.109‰。
一个简单的信念驱使着马龙:爱德华本可以活着,在他抑郁症快速发作的几个阶段,他的死亡是可以预防的。马龙和越来越多的精神卫生专家认为,这适用于所有自杀式死亡。他们认为,有了资金充足、协调更好的策略,社会各方(包括学校、医院、警方和家庭等)的态度和方法都会发生改变。而这有可能或至少有望预防每一起自杀。
他们称其为“零自杀”,这是十多年前一家底特律医院为减少自杀放出的豪言,现正被纳入几个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下简称NHS)信托基金。自我们初次见面后,马龙充分赞同这个计划,并在今年5月与默西护理(Mersey Care,已经着手实施“零自杀”策略)举行了会谈。马龙的计划还处于早期阶段,他正在着手建立一个零自杀基金会。他希望基金会能在英格兰55个精神卫生信托机构中确定良好的自杀预防措施,并创造出一种适用于全世界的新策略。
即使你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根除自杀,我们也必须竭尽全力。
“零自杀”是一个积极的策略,旨在确定和关注所有可能存在自杀风险的人,而非在患者到达危机点才做出反应。它重视强有力的领导能力、优化的培训机制、更好的患者筛查,利用最新数据和研究及时并果断地做出改变。这是一个联合战略,挑战关于“自杀是一种必然”、“自杀是一种耻辱”这样的旧观念,反对“如果整体的死亡率降低了,个别人员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这种观念。“即使你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根除自杀,我们也必须竭尽全力,”马龙说,“如果‘零’不是正确的目标,那什么是呢?”
“零自杀”不是激进的,它结合了现有的预防策略。但是,这个计划是全新且大胆的,它揭示了人们态度的转变有多么缓慢。在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的作品《工人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中,他回顾了自己在利兹的成长,书中以半自传式叙述的方式对1950年代的文化剧变进行审视。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说有人自杀,无论男女,都把他们的头放进煤气炉里。” 他写道,“自杀不会在每个月、每一季度固定发生,也并非所有试图自杀的人都会死去;但如果发生的次数足够多,自杀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很诧异人们是如何“怜悯但没有一丝责备”地接受“自杀是可以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他的这种诧异也反应了社会对自杀的普遍态度——自杀也是一种犯罪。195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613人因为“企图自杀”而被起诉,其中33人被监禁。直到1961年,法律才被更改,但污名依旧存在。撒玛利亚会(The Samaritans)和精神卫生专家建议放弃使用“主动寻死”(commit)这个词修饰自杀,他们更倾向使用“死于自杀”(die by)——但“主动寻死”这个词仍常出现在报纸的头条上。持同样态度并发声的人强烈反对自杀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从而催生了这样的想法:自杀的根除,或者至少大幅度的减少,是有可能的。
编注:撒玛利亚会是一间注册志愿机构,以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为基地,为情绪受困扰和企图自杀的人提供支援。
····
传统意义上,自杀被认为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与选择。因此,精神卫生系统往往倾向于用两种方式来对待存在自杀倾向的病人。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大卫·卡温顿(David Covington)是“零自杀”的先驱,他说:“有些人处于危机之中但无法停下。但他们会故意让你听到‘你无法阻止一个执意想要自杀的人’这类描述。所以存在一种奇怪的逻辑:你无法阻止那些自杀的人,因为他们不会去寻求照顾,也不会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而那些与我们交谈的人,他们的内心是矛盾的,因此兴许是可以被挽救的。你会留意到我们提到“手势”这个词。是的,我们有一套特别的语言,通过使用这套语言试图将风险降到最低。”
卡温顿是RI国际(RI International)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RI国际是一家位于凤凰城的精神卫生团队,在美国有50多个急救中心和其他项目,此外它还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有一家分支机构。卡温顿是一位杰出且精力充沛的演说家,同时也是美国自杀组织协会的董事长候选人,该协会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慈善组织,并发起了一项国际“零自杀”倡议。二十多年前,当他开始接触精神卫生时,他对自己在系统中发现的训练和思考方面的差距感到沮丧。直到最近,突破才出现,卡温顿以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并推动人们摆脱自杀宿命论、令人耻辱的思维——当我们根除疾病并处理好其他威胁(例如道路交通事故和吸烟)时, 我们发现“自杀是必然的、令人羞耻的”想法是减少自杀行为过程中取得进展的最大障碍。
卡温顿认为一本书和一座桥梁加速了这一转变。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托马斯·乔伊纳(Thomas Joiner)在其书《为什么人们死于自杀》(Why People Die by Suicide)中利用幸存者的证词、大量研究和他父亲的去世来颠覆人们的观点。他提出了自杀者的各种心理压力:药物滥用、精神疾病的遗传易感性、贫困,同时也指出所有高危人群中存在的三个因素:一是虔诚但非理性的信仰,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周围人的负担,二是孤独无助的感觉,三是一种违背我们与生俱来自我保护本能的倾向性,这种倾向伤害了我们自己。(这些都指向了一种自杀方式,乔伊纳将其称为“习得性无畏”(learned fearlessness),卡温顿则把它称作“习得的能力”。)卡温顿说:“这本书的内容为干预自杀的努力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并且是我们完全闻所未闻的。它就像一道曙光,使自杀预防的整个领域都开窍了。”
钢网的设计目的不是为了抓住人们,而是为了阻止他们从桥上纵身跳下。
另一个驱动因素是金门大桥,或者说2006年拍摄的关于金门大桥自杀事件的纪录片。在这座桥上拍摄的特写镜头中记载了人物的自杀片段以及随后对家属的采访。影片的上映引起了轩然大怒,公众的怒火指向了导演,而非金门大桥记录的死亡人数和丧亲之痛。导演艾瑞克·斯蒂尔(Eric Steel)面临着残酷的指责。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令人厌恶的电影。”影评人安德鲁·普尔弗(Andrew Pulver)在《卫报》上写道。然而,斯蒂尔的目的是让电影起到震慑作用,并以此作为例证,揭露社会对于自杀的典型态度。卡温顿说:“它触及了公众心理,以一种极强大的方式挑战了核心价值观中对社会自杀现状固有的观念。”
20世纪70年代,当地媒体开始了对第500位死者的倒计时(自桥1937年竣工以来,每两至三周就会有一人在此处自杀身亡)。1995年,一位电台主持人答应给第1000个受害者的家属一箱斯奈普(Snapple)饮料。最终在警方的介入下,官方的计数停在了997。
几十年来,桥梁的董事们一直以财务和美学为理由,拒绝在行人通道(有一道低矮的栏杆)和高于水面75米处建造一道安全屏障。1953年,一位桥梁监管员认为,跳桥自杀要比跳楼自杀落在人行道上更好。而在1978年,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名誉教授的理查德·西登(Richard Seiden)发现,在1937年至1971年之间,515名从金门大桥上跳下的人中,94%的人仍活着或自然死亡。
这项被卡温顿称为“被忽视了25年的研究”,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仅仅通过消除危险渠道,并找出一个“习得性无畏”的出口,简单的干预也可以大大降低自杀率。这一观点也加强了在这座无法持续巡视的大桥上建设安全网的呼吁。2008年,桥梁董事会通过了这一提议。施工于当年5月开始,预计2021年完工,将在人行道下方六米处放置钢网。它的设计不是为了抓住人们,而是阻止他们向下跳。
爱德华·马龙的“金门大桥”是他每天上学的火车站。他的父亲史蒂夫永远不会知道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那些企图自杀却幸存下来的人在争取进一步理解中受到欢迎——他们继续谈论它(自杀)。2005年,在斯蒂尔的纪录片上映的前一年,只有26人在以7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击金门大桥下的水后幸存。那些受伤(骨折、器官穿刺)的人,通常不是死于猛烈撞击,而是淹没于剧烈疼痛。而那些被发现的尸体痕迹表明死者曾遭受鲨鱼和蟹类的撕咬。
19岁的凯文·海因斯(Kevin Hines)患有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2000年9月,他乘上了去金门大桥的汽车。海因斯的家人知道他患有精神疾病,他也正在接受治疗,但是这个年轻人的大脑中经常出现声音,并伴有幻觉,向他灌输自杀的念头。这些声音告诉海因斯,他对周围的人是一种负担,如果他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痛苦程度,他就会被关起来。
“当你长期处于自我厌恶状态之中并开始相信这些声音时,你便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自杀也就成了一种选择。”凯文在亚特兰大的家中通过电话说,“当人处于那种状态时,他们无法分辨出这种声音其实是虚假的——它是大脑化学递质失调而产生的虚假现实……他们认为周围的人对他们没有同情心。”
凯文曾遭受亲生父母的忽视,他们吸毒且存在心理方面的问题。寄养前的新生儿期,他们将他一个人留在旧金山一家汽车旅馆的混凝土地板上,给他喝可乐和偷来的变质牛奶。《美国预防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曾于1988年发表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由撒玛利亚会发表的一份2016年3月的报告中引用了这一研究。报告表明,经历4次及以上“童年不幸经历”(ACEs,包括身体虐待、母亲遭受暴力、药物滥用的环境以及被父母监禁)的人在之后成长过程中的自杀倾向性是普通群体的12倍。
凯文的养父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帮助他接受治疗,但凯文把所有人都蒙在鼓里。他告诉医生,他正在执行一个新的计划,并且正在服药,实际上他只是偶尔服用,并经常喝酒直至昏厥。“我曾是一名州际摔跤冠军,一个足球运动员,外界都认为我表现出色。”在自杀之旅之前,凯文状态持续变差。他回忆说:“就在那时,我决定去那座桥。”
凯文反对“选择”自杀这一说法。“自杀并非是主观的选择,而是有一个不属于你的声音在你的大脑中拼命地尖叫着,‘你必须死,现在就跳吧!’”他还质疑自杀是一种自私行为的说法,因为处于极端状态下的个体深信自己是一个负担,活着更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也记得2000年的那个早晨,外界只要给予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就能阻止他自杀。
“我和自己订立了一个协议(许多幸存者在后来也提到了这个协议),如果那天有人对我说,‘你还好吗?’或者‘有什么不对吗?’或者‘我能帮你吗?’这三句话,我就会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情,并请求帮助。”他依旧记得自己坐在公交上,对着声音哭着喊着叫它停下来,可当时周围并没有人对此说些什么。“我还是感到困惑,为什么人们对痛苦中嚎哭的人视而不见,也不说任何关心的话。”凯文说。
当凯文沿着桥梁走过铁轨时,他以为靠近他的一位女性是来帮助他的。“但是她拿出一台相机,请我为她拍照。她有着德国口音。她可能是迎着光,或许因此没有看到我的眼泪。我帮她拍了5次后归还相机,她感谢完我后就离开了。那时我对自己说:‘根本没人在乎我。没有人。’那个声音说:‘跳吧’,于是我跳了。”
在我的手离开围栏的那一刻,我后悔了。
从金门大桥跳下到落入水中五秒钟都不到。“在我的手离开围栏的那一刻,我后悔了。”凯文回忆到,“可是已经太晚了。”他在深水下睁开了双眼,他的脊椎也折断了。“我只想活下来。我当时在想,在我浮上水面之前,我不能死在这里。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没人会知道其实我并不想死,我犯了个错。”
海岸警卫队来营救时,凯文挣扎着维持身体漂浮。他花了几个星期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时表示自己花了数年时间才做到坦诚地面对自身的心理问题。他依旧努力地使自己保持状态稳定,并以研究员、作家和演讲者的身份成为自杀预防的强大发声者。“从金门大桥跳下后还活着的25至26人中,有19人表示自己的手一离开围栏就感到后悔了。”凯文说,“自杀的行为与想法是彼此分离的。”
消除自杀的途径已经成为现代自杀预防策略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无论它们是否带有“零”标签。本世纪初,英国卫生部要求曼彻斯特大学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杀和谋杀的全国保密调查”项目,提供一种降低患者在精神病院自杀的方法。“从现有的数据上看,就好比说解开绳子上的结,这样就没有人能够以上吊的方式自杀。” 路易斯·阿普比(Louis Appleby)回忆说。阿普比是一名精神病学教授,也是这项调查的负责人,此外他还领导了英格兰的自杀预防战略。
到2002年,病房被要求拆除浴室和床周围的不可折叠窗帘轨道。2012年,阿普比团队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病房内“上吊自杀”案例从1999年的57起下降至2007年的15起。“这带来更广泛的影响,随着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住院部(精神病院)似乎变得更安全了。”阿普比表示。而在医院之外,则通过具体有意或无意的方式减少自杀,例如立法降低扑热息痛的产量(有意),以及上世纪50年代天然气取代了煤气炉(无意)。
····
爱德华·马龙和凯文·海因斯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但是,凯文自杀的重要原因来自刚出生前几个月受到的创伤,爱德华并没有不利的童年经历。他的父亲并不清楚自己家族有抑郁症病史,只能推测也许是某种基因缺陷造成了致命的化学混合物迫使他结束生命。
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正在发展。2016年,麻省总医院的科学家们通过对30多万人DNA数据的分析,发现了17种可能增加抑郁症风险的基因变异。这一发现发表在了《自然·遗传学》杂志上。格拉斯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罗里·奥康纳(Rory O’Connor)是自杀行为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他说:“我们都有一些弱点,其中一部分受到遗传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凯文和爱德华在寻求精神疾病治疗时都传递出试图自杀的讯息。根据“精神疾病患者自杀和谋杀的全国保密调查”,在2016年,超过四分之一的自杀者都与精神卫生机构有过接触。停止弹钢琴后不久,爱德华已经明显不太好了。史蒂夫记得儿子不断衰弱。他脸色苍白,看上去不太健康。他告诉他母亲苏珊娜,他的状况很不好,但从未向父母透露出自杀的想法。
在爱德华去世前的两周,他会见了全科医生,医生立即将他转介给了NHS危机干预小组,建议对方于24小时内对其进行评估。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与爱德华交谈的护理人员经验有限,他降低了风险,建议等五天。此外,虽然爱德华生前再过两个月就满18岁,他允许护理人员告诉他的父母自己的自杀念头,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这并非只是个例。
在2016年6月的调查之后,剑桥郡和彼得堡的NHS信托基金会发表了共同声明:“虽然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有一些因素可能的确无法预见,但信托基金会本可以做得更好。他们进行了内部调查,编写了一份独立报告,并正在执行报告中的建议。”
马龙在一封邮件中写道,他儿子的案件“是一场过程混乱的偶然惨败,是不明确的责任和曲折悲剧后的争论,而那些争论极大地加深了一个家庭的痛苦”,他补充道,“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这并非只是个例。”
“零自杀”最初是为了减少精神卫生系统中的死亡人数。2001年,在亨利·福特卫生系统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负责管理底特律的医院、诊所和急诊室的埃德·科菲(Ed Coffey,同时出任该机构的行为健康服务的CEO)提议共同讨论同年美国医学院发表的报告——呼吁进行全面医保改革。该报告引发了一场关于“完美护理”的讨论,科菲想知道这对精神卫生意味着什么。科菲说:“我记得一名护理人员举起她的手,说:‘好吧,假设我们为抑郁症患者提供了完美的护理,我们的病人都不会自杀。’”(科菲现在是休斯敦的一家精神病医院门宁格诊所(Menninger Clinic)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科菲视其为一项挑战,并着手改革亨利·福特卫生系统,以实现一个新的、零自杀的目标。这一举措涉及改善获得护理机会以及限制使用自杀工具。任何精神疾病患者都被视为具有自杀风险,他们在每次咨询中都会被问到两个问题:“在过去的两周里,你的失落有多频繁?”和“你在做事时,感到些许的快乐又有多频繁?”高分数会触发关于睡眠不足、食欲减退和自残等的新问题。系统筛查将为患者制定个人护理和安全计划,并让家人参与其中。每一个死亡案例都会被当作“学习机会”。
亨利·福特系统报告的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99年,精神疾病患者的年自杀率是0.11‰。接下来的11年里,共有160人自杀,但自杀率下降到0.036‰。而在2009年,患者的自杀率第一次达到零。数据很惊人。但这种策略也遭到了批评,部分原因是员工认为它让医务人员被财富绑架,许多人因此饱受指责。路易斯·阿普比也指出,这项策略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撑。不过,他确实相信它足以提高自杀预防的公共曝光度,并迫使精神卫生部门反省自己的做法。
卡温顿在RI国际工作之前,曾将“零自杀”引入到麦哲伦卫生服务部门,后者在过去10年中将自杀率下降了50%。“我们社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刚开始时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承认,“但是一旦阻力被消除,’零’的概念就进入了人们的脑海……一旦这颗种子开始生长,人们对此报以无比积极的期待。”
····
2013年,科菲在默西护理讨论了自杀预防的相关内容。这家机构雇佣了5000多名员工,在西北地区对超过1000万人提供了服务。2014年,“零自杀”策略得到批准,同时承诺在2020年之前消除自杀行为。2015年,默西护理每年接待4万名患者,成为英国首个采纳该策略的机构。
在利物浦东部商业公园的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简·伯兰德(Jane Boland),她是一位卫生行政人员,也是默西护理的自杀预防临床主管。她说,18年前她刚开始做精神卫生临床医生时,关于自杀的干预训练并不存在。
“我们并没有被教导如何与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进行沟通。她回忆道,”这(患者自杀)被认为是一种职业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默西护理新策略的一部分,伯兰德负责向所有员工提供培训,从资深临床医生到接待员和清洁工。
她说:“这5000名员工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在城市里,在火车上,关注着那些感觉不太好的人们。”
培训以在线课程进行,旨在帮助员工寻找人们痛苦的迹象。它同时挑战了关于自杀“宿命论”且“令人羞耻”的旧观念。伯兰德发表演讲,并邀请那些遭受自杀影响的人分享亲身经历。她甚至说服自己的丈夫谈论他16岁那年,21岁姐姐自杀身亡的故事。伯兰德说:“他和我谈过这件事,但我没有意识到,他只告诉过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现在,他告诉成千上百的人,他每一天都在思念着姐姐,现场鸦雀无声。”
默西护理的计划还包括更方便的危机护理、更好的患者个人安全计划、在死亡或出现自杀意图后更迅速地调查,计划的重点是学习而不是责备。2017年5月,该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乔·拉菲蒂(Joe Rafferty)告诉我,这项政策还不能对自杀率产生影响。目前每10万个接触到的患者中有5.5人死亡。(拉菲蒂说这相当于平均每两周发生一次死亡,也让默西护理成为自杀率最低的20%的精神卫生信托基金机构中的一员。)
“但最伟大的胜利在于文化和态度上的转变。”拉菲蒂说,“就在两年前,我和上级谈论自杀时,谈话通常以“别担心,我们处于最低的五分之一”或“我们拥有非常有利的基准”结束……最大的变化就是转向了一种绝对的观点,即将基准值设为零。”
拉菲蒂认为,他与史蒂夫·马龙讨论过的零自杀基金会可以将这种想法传播给其他信托机构,以及任何愿意改变现状的组织。默西护理已经在努力帮助70%的自杀受害者,这些人在死前一年并没有与精神卫生机构接触。伯兰德与当地政府合作,并向利物浦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自杀预防培训。默西护理正在商洽向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提供培训。
NHS的临床网络也采用了“零自杀”战略的一个版本,将其覆盖到英格兰西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这种做法的推广与对自杀迟来的政治关注不谋而合。2015年1月,时任副首相的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发起了一项新的精神卫生倡议,呼吁NHS开展“零自杀”运动。同年早些时候,卫生特别委员会对“零自杀”试点表示欢迎。仍需指出是,该战略尚未得到更广泛的采纳,其结果有待评估。最近发表的保守党宣言中没有提及自杀,但重申了政府致力于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承诺。政府目前的目标由精神卫生特别工作组独立制定,到2020年将自杀率减少10%。与此同时,精神卫生倡导者正在努力争取更好的研究资金,而这仅仅只是身体健康状况(如癌症类)研究资金的一小部分。
····
身为商人的史蒂夫·马龙发现,如果道德状况没有阻碍自杀预防,很难理解为什么资金支持没有让自杀率的降低更快一些。
“我们正在失去许多将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马龙说。他希望在学校、家庭和全科医生的手术中进行早期干预,重点关注危机来临之前的问题,并提高心理健康素养。他说:“在爱德华的家庭、朋友圈和中学里,没有人注意到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当我回想起来,他自杀的征兆有迹可循。”
爱德华的死使家庭遭受重创。马龙说:“他很善解人意,懂得分享,有教养。”马龙不愿说出其他两个孩子的名字,他们现在还未成年。“我们从来没有吵过一场。他还让我和苏珊娜保持着好脾气。他有着超出年龄的智慧。失去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困难的,就像心脏被人撕裂一样,十分痛苦。”
马龙和我与交谈的精神卫生专家一样,不相信能够完全根除自杀。自杀比小儿麻痹症更复杂。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自杀行为会大幅度减少,而且必须被降低,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降幅表明能够实现。如果有一件事要先改变,那就是人们的态度。
“我儿子为什么不寻求帮助呢?”马龙一边说,一边前往火车站,坐火车回家去剑桥。“如果我的儿子接受过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就像他在饮食、公民身份和身体健康方面接受的教育那样,他就会明白,感觉一团糟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尽管他才华横溢,但他并没有接受此类教育来帮助他前进。在他停止弹钢琴的那8周里,如果他说‘爸爸,我想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我们一定会帮助他。”
在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可以拨打116 123联系撒马利亚会,美国自杀预防热线是1-800-273-TALK/1-800-273-8255,北京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010-82951332。
翻译:黄佶滢
校对:亦兰
编辑:Spring
审校:EON
原文:https://mosaicscience.com/story/zero-suicide-mental-health/
自由特写作家,现居伦敦。他为《GQ》、《Vogue》、《金融时报》、《卫报》和Buzzfeed等撰写文章。《独立报》的前编辑,2017年获得英国新闻奖的年度旅行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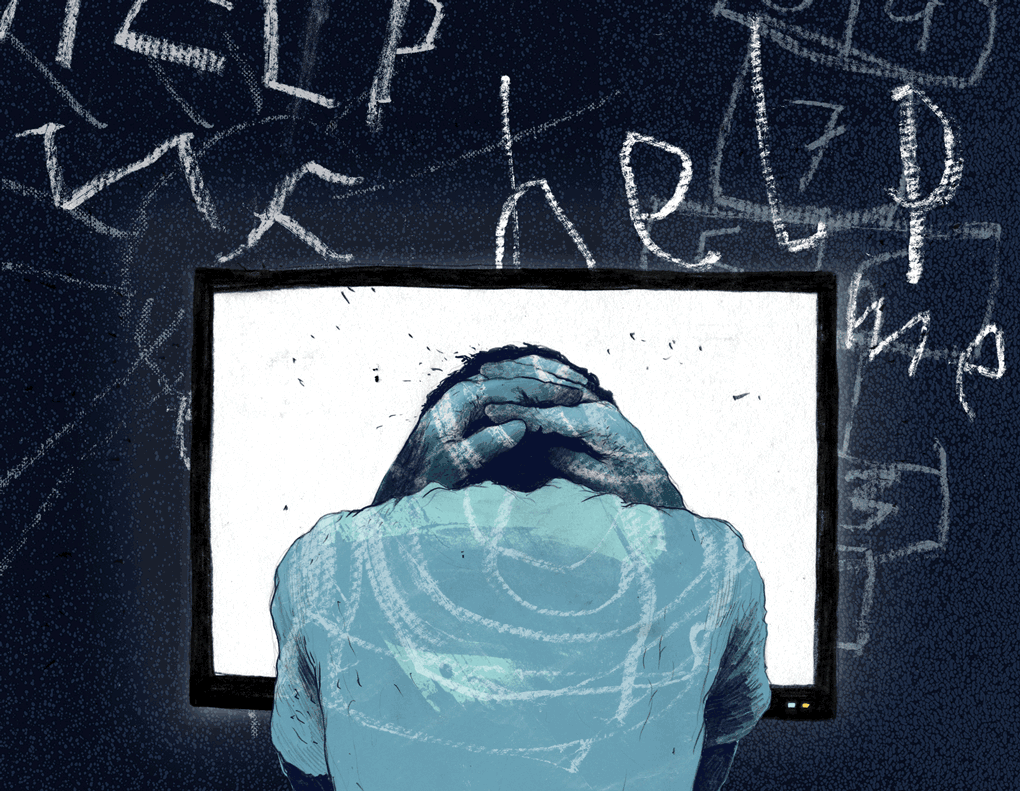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