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
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如果社会越来越广泛地接受这个说法,自由意志信念的削弱会对文明产生极大冲击。当决定论甚嚣尘上,我们可能难以应对。但是否有这样一条路,既保留自由意志信念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又保留来自决定论的富有同情心的理解?

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我们所知的文明取决于对自由意志的广泛信仰——失去这种信仰可能会是灾难性的。例如,伦理准则假定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对与错。在基督教传统中,这被称为“道德自由”——辨别能力和追求善行,而不只是被欲望驱使。伟大的启蒙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重申自由和美德的联系。他认为,若我们无法自由选择,那么我们本该选择的正义之道讲起来将毫无意义。
如今,自由意志的假设贯穿美国政治从福利到刑法的方方面面。它渗透流行文化并支撑着美国梦的信念——任何人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创造自我价值。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中写道,美国的“价值观根植于对生活的基本乐观主义和对自由意志的信念”。
如果这个信念被侵蚀了呢?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Will
But we all may be better off believing in it anyway.
科学宣称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通过发条因果定律来解释,这种观点稳步发展,愈加明显。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150年前兴起的知识革命的延续,当时恰逢查尔斯·达尔文首次出版《物种起源》。达尔文提出了他的进化论后不久,他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开始描绘自由意志的含义:如果我们进化了,那么智力等脑力必定被遗传。我们使用这些官能来做决定——有些人与他人相比拥有更高程度的官能。所以我们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并非自由的,而是取决于自身的生物遗传。
高尔顿发起的这场关于先天和后天的激烈辩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我们的行动是基因展开效应,还是环境印刻在我们身上的结果呢?可观的证据积累了两者的重要性。无论科学家支持其中一个或是另一个,抑或二者的综合,他们越来越认为行为必定由一些东西决定。
近几十年来,研究大脑的内部运作有助于解决这场争论,并进一步打击自由意志的概念。大脑扫描仪让我们得以窥视活人头骨的内部,揭示神经元的复杂网络,并使科学家们达成广泛共识:这些网络依靠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然而科学界一致认为,神经元放电不仅仅决定了一部分或大部分的(神经活动),而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希望、记忆和梦。
我们知道脑化学变化可以改变行为——否则酒精和抗精神病药物将不会有期望的效果。大脑结构也与行为有关:正常的成年人在脑瘤发育后成为杀人犯或恋童癖者的案例表明,我们如何依赖灰质的物理性质。
许多科学家表示,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证明了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众所周知,大脑的电脉冲活动先于动作增强,例如移动手部之前;利贝特表明,这种增强发生在人作出意识决定之前。决定采取行动的意识体验通常与自由意志相关,这种体验似乎是一个附加物,一种在大脑已经准备作出行动后发生的事后重建。
20世纪的这场关于先天和后天的争论,让我们开始认为自己被不受控制的影响所塑造。但它余留了一些可能的空间,至少在大众的想象中,我们可以克服现状或基因,书写自己的命运。神经科学所带来的挑战更加激进:它将大脑描述成一个物理系统,并表明我们并不用意志驱动大脑以特定的方式运作,就如同不用意志驱动心脏以特定方式跳动一样。人类行为的当代科学解释是一个神经元的放电触发其它神经元,引起我们的思维和行为,这个不间断的神经元链可以回溯到我们的出生和死亡。因此原则上,我们可被完全预测。倘若我们能充分理解任何人的脑部结构和化学反应,理论上就能以100%的准确度预测个体对任何给定刺激的反应。
这个领域的研究及其含义并不新鲜。不过新鲜的是,对自由意志的怀疑蔓延到实验室之外,逐渐成为主流。例如,利用神经科学证据的法庭案件数在过去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大多数案件涉及被告辩称他们的行为受迫于大脑。至少从那些声称从音乐到魔法来解释“你的大脑”的书籍和文章的数量来看,许多人也在其他情境中吸收这种信息。决定论或多或少地正在流行起来,怀疑论者们正在崛起。
这种发展趋势引发了令人不安且越来越非理论的问题:如果道德责任依赖于信任自己的意识存在,当对决定论的信仰蔓延时,我们会在道德上变得不负责任吗?如果我们越来越把自由意志的信念当做错觉,那么所有基于它的制度会发生什么?
–
–
2002年,两位心理学家提出一个简单而绝妙的想法:与其推测人们丢失对自我选择能力的信念会发生什么,不如进行一场实验一探究竟。犹他大学的凯思琳·福斯(Kathleen Vohs)和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要求一组被试阅读一段讨论自由意志是幻觉的章节,而另一组读一段话题中立的材料。接着他们对每个小组的成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诱导,同时观察他们的行为。抽象的哲学信仰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决定吗?
确实如此。当被试参加一个很容易作弊的数学考试时,萌生自由意志是错觉的小组被证明更有可能违规偷看答案。当给予行窃的机会——从装满1美元硬币的信封中拿高于应得数量的钱时,那些信仰自由意志的人会逐渐减少拿钱。福斯告诉我,在一系列测量后,她和斯库勒发现“被诱导对自由意志信念动摇的人更容易使坏。”
看来当人们不再相信他们是自由的个体时,便不再认为自己要为行为负责。因此,他们的行为不受责任的限制,他们屈从于本能。福斯强调这个结果并不局限于实验室实验的人为条件。“在原本就或多或少地相信自由意志的人身上,你能看到相同的效果。”她说。
例如在另一项研究中,福斯和她的同事测量了一群相信自由意志的临时工,然后通过查询管理人的评分检查他们的工作表现。那些强烈相信自己在控制行动的工人往往按时工作,且被上级评定为更有能力。事实上,比起建立诸如自我职业道德规范的措施,相信自由意志被证明能更好地预示工作表现。
另一个自由意志的心理学研究的先驱,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扩展了这些研究。例如,他和同事们发现自由意志信念薄弱的学生比起那些信念强烈的学生来说,不太可能自愿花费时间帮助同学。同样,那些读了“科学已经证明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这类报告的人萌生了确定性的观点,可能不会施舍流浪汉或借给他人手机。
鲍迈斯特及其同事的进一步研究将自由意志信念的削弱和压力、不快及较少承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当被试被诱导相信“所有人类活动都遵循以往的事件,并最终能被理解为分子的运动”,那些被试会带着对生命意义的削弱感离开。今年年初,其他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弱的自由意志信念会和学业成绩不佳挂钩。
例子不胜枚举:相信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已被证明会降低人的创造力,让人更容易墨守成规且不愿从错误中学习,还会减少人们对彼此的感激。在各个方面,似乎当我们拥抱决定论时,我们放纵自己的黑暗面。
–
–
鲜有学者有信心表明人们应该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主张谎言的永存会破坏其完整性,并违反哲学家长期尊崇的原则:柏拉图希望真理和善良携手并肩。以色列海法大学的哲学教授索尔·史密兰斯基(Saul Smilansky)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致力于解决这个困境,并得出一个痛苦结论:“我们不能让人们将关于自由意志的真相内化成思想行为的一部分。”
史密兰斯基确信传统观念里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如果大多数人意识到这点,事态将变得非常糟糕。“想象一下,”他对我说,“我在考虑是否去行使职责,比如降落到敌方领土,或者做一些更平凡的事,诸如冒着工作风险报道一些不道德行为。如果每个人都承认自由意志不存在,那么人们会说‘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怪他’。所以,我知道自己不会因为自私的选择受到谴责。”他相信这种情形危及社会,而且“人们越接受决定论,事情会变得越糟糕。”
史密兰斯基证明决定论不仅削弱了谴责,还破坏了赞美。假想我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敌方领土,执行勇敢的使命,之后人们会说我别无选择,这只是壮举。用史密兰斯基的话说,这个行为是“给定的展开”(an unfolding of the given),因此不值得称赞。正如削弱谴责将移除作恶的阻碍,破坏赞美也会消除行善的动机。他认为,我们的英雄似乎将失去鼓舞,我们的成就也不值得注意,很快我们就会陷入颓废和沮丧。
史密兰斯基提倡一个他称之为幻想说的观点——相信自由意志的确是一种错觉,但社会必须捍卫它。决定论的观点和支撑它的事实必须幽闭在象牙塔内。唯独开创者敢于在墙后 “直面黑暗的真相。”史密兰斯基说他意识到这个观点有些偏激,甚至可怕——倘若在真理和良善之间选择,为了社会利益必然选择后者。
当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是自由个体,他们不再认为自己的行为应受谴责。
考虑到史密兰斯基提出世界缺乏自由意志的看法,他的论点起初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奇怪: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决定任何事,谁在乎释放什么信息?但是新的信息,当然像其他感觉输入一样,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改变。在因果关系的表达中,相信自由意志可能不会鼓舞我们做最好的自己,但它确实激励我们这样做。
学院派哲学家中很少有人支持幻想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希望美好和真理和谐共存。但幻想说代表知识精英们的古老思想。尼采称自由意志为“神学家的诡计”,允许我们“判断和惩罚”。许多思想家认为,像史密兰斯基一样,如果我们要避免落入野蛮,判断和惩罚的制度是必要的。
史密兰斯基不提倡极权思想控制政策。他认为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它们。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与生俱来。科学家和评论家们只需要练习些许自我克制,而不是兴高采烈地纠正人们的幻想,那些幻想巩固了人们所珍视的一切。史密兰斯基告诉我,大多数科学家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想法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助长决定论是自负和危险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公开反对自由意志的学者忽视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有人只是不同意这些后果可能包括文明的崩溃。他们中最突出的是神经学家和作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他2012年的著作《自由意志》(Free Will)中,他打算解构有意识选择的幻觉。像史密兰斯基一样,他认为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但哈里斯认为我们抛弃掉自由意志的概念会更好些。
“我们需要追求真理的信念。”哈里斯告诉我。幻想,不管如何用心良苦,总是会阻碍我们前进。例如,我们目前使用监禁这种粗鲁的方式阻止人们做坏事。但他认为,换种办法,如果我们接受“人类行为源自神经生理学”,那么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做坏事,以及如何阻止他们,而不必诉诸惩罚的威胁 。“我们需要”,哈里斯说,”知道社会在鼓励人们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应该撬动哪些杠杆。”
要是按照哈里斯的说法,我们应该承认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罪犯——例如杀人不眨眼的精神病患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幸的。“他们不能选择他们的基因,不能选择他们的父母。他们并不能创造他们的大脑,然而他们的大脑是他们的意图和行动的源泉。”深层意义上说,他们的罪行不是他们的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冷静地考虑如何管理罪犯,协助他们改过自新,保护社会并减少未来的犯罪。哈里斯认为,在未来“有可能治愈精神病”,但只有我们接受大脑是变异性的来源,而非空想的自由意志,才有可能实现精神病的治愈。
接受这一点也会让我们从仇恨中解脱。人们对自身行为负责的观念可能听起来像文明生活的基石,但我们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指责令我们愤怒且心存报复,并遮蔽了我们的判断。
哈里斯提到,“比较人们对卡特里娜飓风和9/11 恐怖袭击的反应”。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劫机者是自由选择做恶的罪犯的化身。但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概念,那么他们的行为必须像任何其他自然现象那样看待——而这会使我们的反应更理性。
虽然两个灾难的规模类似,但人们的反应则完全不同。没有人努力对热带风暴复仇或向天气宣战,因此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反应只是专注于重建和防止未来的灾害。哈里斯认为对9/11的反应被愤怒和复仇的渴望遮盖了,而这导致无数生命的不必要损失。哈里斯并不说我们不应该对9/11有所反应,只是冷静的反应看起来会非常不同,并可能不那么浪费。“仇恨是有毒的”他说,“并且可以破坏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的稳定。放弃自由意志的信念会削弱永远去恨任何人的理由。”
–
–
凯思琳·福斯及其同事的证据表明,了解到我们自己的行动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可能导致社会问题——削弱我们的道德、前进的动力和生命的意义感——哈里斯认为,从相同方面看待别人的行为会对社会有益。从此优势出发,决定论的道德意蕴看起来非常不同,这看上去好多了。
更重要的是,哈里斯认为,随着普通人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大脑如何工作,福斯或其他人记录的许多问题就会消失。他在书中写道,决定论并不意味着“自觉意识和审慎思考毫无用处。”某些行为要求我们有意识地选择——衡量观点,评价证据。这是确实的,如果我们再次被置于完全相同的情况,那么哪怕在100 次里我们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就像倒带一部电影后重新播放它。”但思考的行为——与事实和我们感受到的情绪角力,这对我们的本性至关重要——再真实不过。
哈里斯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往往混淆决定论和宿命论。决定论认为我们的决定是牢不可破的因果链的一部分。宿命论则与之不同,它认为我们的决定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命中注定会发生的终将发生——就如同俄狄浦斯娶了自己的母亲,尽管他努力避免这种命运。
大多数科学家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想法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助长决定论是自负和危险的。”
当人们听到没有自由意志时,他们错误地成为宿命论者;他们认为他们的努力不会改变什么。但这是歧途。人们不会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要是用另外的刺激物 (如关于自由意志的不同想法),他们会有不同的行为和生活。哈里斯认为,如果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细微的差别,失去自由意志信念的后果将不会比福斯和鲍迈斯特的实验显示的更消极。
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呢?是否有这样一条路,既保留自由意志信念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又保留来自决定论的富有同情心的理解?
哲学家和神学家们习惯于谈论自由意志,就好象它不是打开就是关闭;好像我们的意识像个幽灵一样浮在水面,完全悬浮于因果链之上,或者好像我们的生活似一块石头滚下了山。但应该还有观察人类能动性的另一种方式。
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应该把自由选择作为我们非常真实和复杂的对某一特定情况作出多种潜在反应的能力来考虑。这些学者其中之一是布鲁斯·沃勒(Bruce Waller),他是扬斯敦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新书《有所补益的自由意志》(Restorative Free Will)中写道,我们应侧重我们的能力,在任何给定的设定中为自己生成一组范围宽阔的选项,并在没有外部约束时在它们之中决定。
对于沃勒来说,由一连串因果链般的神经元放电实现的这些进程无关紧要。在他看来,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是常被认为的那种对立关系,它们只是在不同程度描述我们的行为。
沃勒认为他的解释符合我们如何进化的科学认识:觅食动物——人类,老鼠、熊或乌鸦——需要能为自己生成选项,并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作出决定。脑容量大的人类比其他动物能更好地思考和权衡选择。我们的选择范围广泛得多,也更自由。
沃勒对自由意志的定义与大量普通百姓的看法相仿。一项2010年的研究发现,人们大多按照遵循欲望来考虑自由意志,认为自由意志免于胁迫 (如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只要我们继续相信这种切实的自由意志,这应该足以维持福斯和鲍迈斯特所审视的那类理想和道德标准。
然而沃勒对自由意志的解释仍然导致了与如今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大不相同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的观点。无人造就自己:人们无法选择基因或出生环境。因此没有人对他是谁和他做什么负有最终责任。沃勒说他支持奧巴马 2012年“你并未有所建树”的讲话,总统呼吁人们关注带来成功的外部因素。他也不惊讶这一观点吸引了那些想要相信他们是自身成就的唯一缔造者的人的强烈反应。但他认为,我们必须接受人生成果由先天和后天方面的差距决定,“因此我们可以采取实际措施补救不幸,帮助每一个人发挥他们的潜力。”
为了了解未来数十年的工作是什么样子,我们得慢慢解开大脑的本质。在许多领域,研究工作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同情:给那些发现自己处于不利位置的人提供更多 (和更精确的) 帮助。而惩罚的威胁作为一种威慑是必要的,它会在许多情况下与变强的努力平衡,而不是削弱任何人所必需的可以过上体面生活的自制能力。通向成功的意志是可以培养的——为自己看到积极的选择,做出好的决定并践行,而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最需要培养。
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毫无道理的企图,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它是在抛弃最坏的打算时保留自由意志信念系统最好部分的一种尝试。奥巴马总统——不仅捍卫“自由意志的信念”,而且辩称我们不是自身财富的唯一缔造者——不得不学会如何踩在这条细微的界限上。然而在这个科学时代,它可能是我们需要用以拯救美国梦的东西,而且实际上还有这个世界上关于文明的许多理念需要被拯救。
翻译:巧酱,赵一鸣 校对:岳川
哲学家,作家,英国外交官员,现居柏林,剑桥大学 the 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的执行主任和高级研究员。他的写作领域广泛,涉及哲学和科学问题,并为《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卫报》和其他刊物撰写文章,著有《Immortality: The Quest to Live Forever and How it Drives Civi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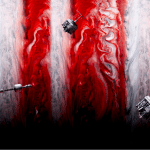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