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如何重塑大脑:切除颞叶重返大师的奇迹
脑部手术切除了马蒂诺70%的左题叶这篇文章描绘了他从手术中恢复的过程。恢复后,他重新找回了精湛的吉他演奏技巧。

“大脑的有趣之处在于,”2015年,吉他手帕特·马蒂诺(Pat Martino)告诉Nautilus杂志,“它是运输工具,但它不属于旅途的终点。大脑能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但它终究不是你自己。”马蒂诺的思考出现在我们文章的末尾。动静脉畸形的脑部手术切除了马蒂诺70%的左颞叶,我们的文章描绘了他从手术中恢复的过程。马蒂诺是爵士乐传奇人物,名声在吉他手之间口口相传。恢复后,他重新找回了精湛的吉他演奏技巧,这让神经科学家非常惊讶。
这篇文章发表后,布莱恩·加拉格尔(Brian Gallagher)和我一起,在马蒂诺于纽约蓝色音符(Blue Note)的一场演出后见到了他。你懂得这种感觉吗:当你见到某些人时,会感觉他们有些特别之处,就像一种轻柔的存在,能让你对自己感觉更好。马蒂诺就是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很欣赏那篇文章,也很高兴我们能能来听他的演出。他说话的方式和弹琴一样,带着一种宽大自由的气息。

—
Kevin Berger
5年前,当神经外科医生马塞洛·加拉尔扎(Marcelo Galarza)看到爵士吉他手帕特·马蒂诺的大脑核磁共振成像(MRI)时,他震惊地说:“我无法相信他的左颞叶被移除了那么多。”1980年,马蒂诺做了脑外科手术,移除了一团畸形的静脉和动脉。那时,他是爵士乐最富盛名的吉他手之一,然而少有人知道马蒂诺癫痫发作、头痛欲裂且患有抑郁,他被关在精神病房里,忍受着使人衰弱的电击疗法。
直到2007年,马蒂诺才进行了核磁共振成像,神经科学家们也是直到最近才发表了他们对于马蒂诺核磁共振成像的分析。跟其他医生和乐迷一样,让加拉尔扎感到惊讶的是,马蒂诺在手术后虽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大脑和记忆,但他的吉他技能却完好无损。2014年,在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医院《世界神经外科》(World Neurosurgey)的一份报告中[1],加拉尔扎和来自欧美的同仁们写道:“就我们所知,该病人从严重的遗忘症中完全恢复并重返了艺术大师的地位,这项个案研究属于临床观察上的首例。”
马蒂诺现在70岁,已经发布了超过30张专辑。他持续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根据许多爵士乐评论家和音乐家的说法,他的演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幸福且富有创造力。在马蒂诺的案例中,这的确说明了一些问题。从青少年起,作为一名吉他手的他就因灵活的手指和震撼的即兴创作而知名。格莱美奖得主、吉他手乔治·班森(George Benson)在受采访时说,他自认为是60年代纽约市的“卓越新星”,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在哈莱姆区观看了马蒂诺的演出。“你懂吗,我真的目瞪口呆!”班森说,多年来,马蒂诺“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我知道还有另一个标杆,所有吉他手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马蒂诺制定这个标杆;他让我们看到,吉他比我们听到的要多得多。”
马蒂诺也为神经科学家上演了一场演出。来自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医学中心亚克医院(Hôpital Gui de Chauliac)的教授、神经外科医生雨果·迪福(Hugues Duffau)研究了马蒂诺的案例。他写道,其案例展现了神经可塑性,即发育和学习过程中大脑非比寻常的“优化脑网络功能”的能力。这名吉他手的康复体现了大脑也能“即兴创作”,通过连接恢复运动、智力、情感功能的大脑区域,以弥补畸形或损伤的创作能力。在神经科学家看来,马蒂诺的故事是关于音乐以及音乐如何帮助塑造其大脑使他康复[2]。
马蒂诺在费城出生长大,他现在也住在这。虽然自10岁起他就有幻觉和癫痫,但是他被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误诊了20余年。他们一直跟他说他患有躁郁症、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直到1980年,在马蒂诺35岁时,他才在自己的首次计算机断层扫描中得知病因是动静脉畸形,即在他左耳后面的大脑部位形成的静脉和动脉的异常缠结。在2009年的纪录片《马蒂诺的神经错乱:一场大脑未解之谜》(Martino Unstrung: A Brain Mystery)中,拯救了马蒂诺的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西蒙尼(Frederick Simeone)说,马蒂诺静脉和动脉的缠结就像是“一团蠕虫”[3]。
动静脉畸形可能自出生起就存在,并阻碍了马蒂诺左颞叶功能的正常发育,尤其影响了他存储和表达记忆的能力。即使如此,马蒂诺也只记得1976年他在舞台上表演时癫痫发作的这一个例子。当时他在法国马赛郊外的里维埃拉爵士音乐节(Riviera Jazz Festival),在一个山顶露天演奏,现场有超过20万观众。马蒂诺在他的自传《此地此刻!》(Here and Now!)中写道[4],“就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令人激动的部分中段,我停止了演奏,在那里站了大概30秒。癫痫发作时,感觉就像坠入了黑洞之中。”
四年后,他在洛杉矶的吉他技术学院(现为洛杉矶音乐学院)教书时遭遇了一次几乎致命的癫痫并住院治疗。马蒂诺癫痫发作时,他的一位好友约翰·马尔赫恩(John Mulhern)(后来的吉他技术学院录制部门负责人)也在场,他记得他看到马蒂诺躺在床上“像玩具一样上下摆动”。在洛杉矶医院,医生诊断马蒂诺患有动静脉畸形,他们认为已经出现了大出血。马蒂诺被告知只有2小时可活了,但这位土生土长的费城人想回家做手术。
手术分为两步:首先,外科医生移除已经形成的血块;之后,他们对马蒂诺进行大脑血管造影术,将染剂注入大脑血流中,再借助X光,外科医生便能知道应该切除哪一部分。为了移除马蒂诺大脑里的“那团蠕虫”,西蒙尼切除了他左颞叶的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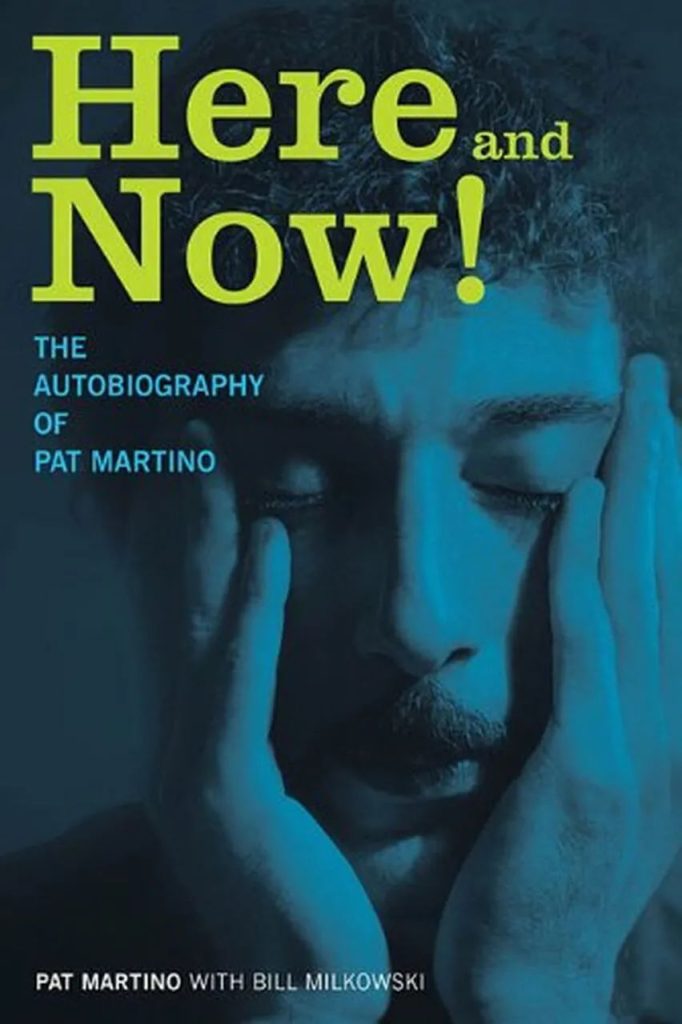
在马蒂诺的自传中,他写道,术后他感觉像是个僵尸,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认识父母,也不知道他是位音乐家。事实上,马蒂诺有严重的逆行性遗忘,他没法回忆起来那场几乎致命的癫痫之前发生的事件和学到的知识。在近期的Nautilus采访中,马蒂诺说术后经历的空白和不稳定状态让他想起了当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天钧》(The Lathe of Heaven),该片改编自1971年阿苏拉·勒奎恩(Ursula K. LeGuin)的一部同名反乌托邦科幻小说,小说中一名男子惊恐地发现,他的梦改写了过去。马蒂诺说:“那是一种可怕的境地。”
对他的音乐家父亲米奇(Mickey)来说,这也令人十分痛苦。马蒂诺说,还是孩子时,他就想成为爵士吉他手,因为他爱他的父亲,想要成为让父亲自豪的人;他的确做到了,但这也让米奇在看到儿子忘记了对音乐的热爱之后更加痛苦。术后马蒂诺回到了费城的家中,他的父亲希望能让他重拾记忆,于是在家中为儿子演奏他的爵士作品。马蒂诺写道,“我在楼上躺着,听到音乐穿过墙壁和地板,它们提醒着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马蒂诺总是毫无兴趣地走过他的吉他,父亲为此而感到沮丧,他请马尔赫恩前来为马蒂诺演奏。马尔赫恩曾上过马蒂诺的吉他课,经常把马蒂诺要求的小九度和弦弹成大七度,这让马蒂诺很恼火。而这时,马尔赫恩翻阅着马蒂诺的旧吉他谱,又弹响了大七度和弦。“挪开!”马蒂诺说。他抓起吉他,开始弹奏过去的曲子。接下来的几个月,失忆和术后抑郁带来的痛苦开始减轻。
马蒂诺写道:“随着我继续在这把吉他上演奏,记忆的闪回和肌肉记忆逐渐涌上心头:指板的形状、通往家中不同房间的楼梯。房间里一些只有你知道的密门,而你很喜欢走进去,因为它们能带给你快乐。这就是你回忆起演奏方法的过程:你想起了演奏的快乐。”术后第7年,也是前一张一语成谶的专辑《离去》(Exit)发布后的第10年,马蒂诺发布了专辑《返回》(The Return)。
在20世纪70年代,马蒂诺用他的演奏灼伤了爵士乐的乐土。如今,这位吉他手可能没有了他之前所拥有的全部的灰质,但他也将继续以无以伦比的技巧和美感进行演奏。
—
L: Michael Ochs Archives / Stringer, R: Andrew Lepley / Contributor
神经科学家说,马蒂诺精湛技艺的回归揭示了大脑中记忆的房间和秘密的大门。在2014年的《世界神经外科》(World Neurosurgery)报告中,加拉尔扎提到,在个体切除了70%的左颞叶后,海马区域会受到潜在的损伤,医生或许会预料病人“几乎完全丧失记忆”。
加拉尔扎解释道,左颞叶“直接参与”言语和听觉记忆、交流和理解对话。在2007年,大量的认知测验表明,马蒂诺难以表达一些抽象的罕见词语的含义,也难以定义常见的词语。例如,给马蒂诺看一个开瓶器的图片,他只能说出:“它被用来打开……酒瓶。”当被问及披头士何时到的美国,马蒂诺说是1961~1963年间的某一时间(他的回答几乎正确,答案是1964),但当被要求说出披头士一首歌曲的名字时,他一首也说不出来。
马蒂诺的案例强调了记忆的三个关键层次。与颞叶有关的语义记忆存储客观知识和事实,例如名字和日期。颞叶切除能够解释为什么马蒂诺记不起披头士歌曲的名字——也许是手术移除了他回忆语义记忆的能力。
情景记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把这种自传式的、体验式的记忆比作一种“直接的感觉……充满了温暖和亲密”[5]。显然,马蒂诺也受到了影响,毕竟,他想不起自己是个音乐家,记不起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和他们共同生活的经历。这一失败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情景记忆与大脑的海马与前额叶皮层有关,手术没有损伤他的前额叶。然而,《马蒂诺的神经错乱》的共同作家、《世界神经外科》报告的共同作者、英国神经心理学家保罗·布罗克斯(Paul Broks)说,马蒂诺的手术可能对于储存、激活情景记忆的区域产生了“非特异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随着术后大脑的生理调整消退了”。
而第三个层次——程序记忆,则解释了马蒂诺的故事中最令人惊奇的部分:一部分大脑被摘除的情况下,他如何重又娴熟而灵活地弹奏吉他呢?时常有职业音乐家以及运动员表示,他们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指尖是如何在纸板上飞速演奏,或是如何击中速度达到100迈的直球。这是因为,通过经年累月的练习以及重复,这些动作已经深深嵌入到他们的大脑中,以至于他们无法意识到这些动作是如何完成的。这类“感觉运动技能”通常存储于程序记忆中,与大脑基底神经节中最大的解剖学成分相关。这一部分位于脊柱上方的前脑中心,与运动控制相关。马蒂诺的这一部位并没有遭到损害,因此,在他患上动脉畸形以及手术过后,与演奏相关的记忆静静等待着被重新唤醒。
神经科学家们认为,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情景记忆还是程序记忆,都能通过一个简单的想法或动作被重新唤起。记忆的不同层次并不相互分离,而是紧密相连的。
就职于亚利桑那大学的心理学家林恩·纳达尔(Lynn Nadel)读到了这篇发表于《世界神经外科》的报告。他仔细研究了马蒂诺的认知测试结果,随后公开表示,马蒂诺并没能从手术中完全康复。“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仍旧具有此类脑损伤患者所表现出的明显或细微的缺陷。”但是,考虑到他能够重新回想起他曾经的身份,马蒂诺的案例的确“非常有趣”。纳达尔说道。这是因为,马蒂诺可能在没有回忆起过去的情况下重新成为了一位爵士音乐家。纳达尔认为,也许马蒂诺之所以能够重拾自己的身份,“是因为演奏技巧与他的身份紧密相连,深深地埋藏在他的过去中。”
手术过后,马蒂诺大脑中留下的身份碎片可能仍与吉他演奏的程序记忆连接在一起。当他重新拾起吉他,大脑中的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也一并被点亮了。加拉尔扎在那篇报告中写道,曾有人提出左颞极具有连接“情绪本能反应”与“复杂声音刺激(即音乐)”的功能,而手术并没有移除马蒂诺大脑中的这部分结构。
2000年初的一个夜晚,在马蒂诺于纽约蓝色音符爵士俱乐部的演出散场后,演员乔·佩西(Joe Pesci)到后台拜访了这位爵士音乐家。马蒂诺感到十分荣幸,他告诉佩西,自己十分喜欢他在《我的堂兄文尼》、《好家伙》和《愤怒的公牛》中的表演。“你不记得我了,是不是?”佩西问道。“我还记得1963年你在斯莫尔天堂*常点的那杯鸡尾酒。”那是一杯青草蜢鸡尾酒。
*译者注
斯莫尔天堂(Small’s Paradise),是纽约哈林区的一间夜总会,于上世纪80年代停止营业。
“在他说出鸡尾酒名的那个瞬间,我的头脑中突然涌现出一系列画面。”马蒂诺在《此地此刻!》中写道。“那一刻我重新回到了斯莫尔天堂;我想起了酒保的面容、舞台以及演奏乐器的位置。”当年,佩西也曾是斯莫尔天堂的驻唱歌手和吉他手。他与马蒂诺在那个时期成为了好友。马蒂诺写道,“我把这一切全都忘记了——直到他说出那杯酒的名字,这些回忆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
马蒂诺的恢复不仅点亮了大脑中相互连接的记忆,还照亮了音乐,尤其是乐器演奏对于大脑的影响。“演奏乐器需要我们已知全部大脑区域的参与,几乎所有的神经系统都参与其中。”丹尼尔·莱文庭(Daniel Levitin)在他所著书籍《音乐对你大脑的影响》(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中写道。神经科学家发现,马蒂诺技艺非凡的吉他独奏技巧依赖着众多神经活动的同时进行,所涉及功能包括感知、认知、动作以及执行功能。职业音乐家通常也是职业的大脑“健美运动员”。“大脑终究也是一种肌肉,”加拉尔扎说道。
颇有建树的音乐家们,大脑中的听觉、运动皮层以及连接左右半球的胼胝体通常与常人不同。在他们的大脑中,上述部位的灰质(由神经元组成)以及白质(由连接神经元的轴突组成)通常体积更大。研究显示,与其他人相比,在歌唱家以及演奏家大脑中,一簇称为弓状束的白质体积更大;而弓状束的连接着分别用于制造声音及感知声音的额叶以及颞叶。
音乐家大脑的构造印证了神经科学开创者卡哈尔(Santiago Ramon y Cajal)在1904年写下的结论:“只要有意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重塑他/她的大脑[6]。”而爵士音乐家的这种能力更强。一项2008年的神经科学研究显示,与单纯凭记忆或乐谱演奏音乐相比,爵士即兴演奏的训练对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有更强的影响,能激活大脑中感知运动以及语言区域[7]。即兴演奏反映了一种自发的创造过程,而神经学家对这类过程的神经活动非常感兴趣。他们发现,即兴演奏时的大脑活动与做梦及冥想时的活动十分相似;在这个过程中,大脑关闭了负责中央功能的区域,进而抑制了人们自我观察的倾向。
马蒂诺从没在核磁共振成像机中演奏吉他。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作为一个有超出50年即兴演奏经验的爵士乐手,他的神经可塑性一定优于常人。迪福在2014年的报告《爵士即兴、创造力和大脑可塑性》中写道,马蒂诺大脑中负责语言以及音乐加工的区域可能不再局限于左半球,而是转移至更加广泛的脑区,包括枕叶内侧负责视觉加工的区域。迪福甚至提出,马蒂诺的“爵士即兴经验(甚至在动脉畸形出血之前)促进了他的大脑重构,起到了恢复认知功能的作用”。换句话说,马蒂诺的音乐训练拯救了他的生命[8]。
这个推测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不可思议。一篇发表于《神经心理学综述》(Neuropsychology Review)上的综述总结了包括马蒂诺在内的35个音乐家,提出“音乐训练能改变音乐家的大脑,这种改变能对神经创伤后的认知功能恢复起到有利的影响。”
这篇综述的第一作者,就职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员黛安娜·欧米基(Diana Omigie)解释道,与其他人相比,音乐家们大脑中的运动、听觉区域体积更大的灰质就像是一处“大脑保护区”,这些区域反过来能够“帮助音乐家们重新学习或恢复此前的音乐功能”。她补充道,音乐训练“能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第二种策略”,在负责原始策略的脑区遭受损伤后,这些替代策略便发挥了作用。欧米基说道,“帕特·马蒂诺之所以能够重拾自己的音乐能力,或许就是因为他重新找到了这类暂时休眠的替代策略。”
这或许表明了马蒂诺的大脑在损伤发生前已经进行了自我重建,这成为了他应对损伤的保护伞。欧米基谈到,“在我们的综述中提到了,遭受早期大脑损伤、大脑畸形或脑肿瘤的音乐家,更可能恢复认知功能。与之相比,因遭受脑卒中而突然导致大部分脑组织无法发挥作用的音乐家,无法很好地恢复大脑功能。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的发展时程较长,因此,大脑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重构,音乐功能可能由损伤区域转移至其他的大脑区域。”
许多神经科学家认为,音乐家异常大脑所表现出的可塑性或许是他们音乐创作的灵感源头。“虽然我们依旧不清楚创造性的神经基础,但我们有理由怀疑,马蒂诺缓慢恶化的动静脉畸形,可能导致其枕叶所负责的一部分功能转移到其他的大脑区域,”著有《怀疑论者的大脑指南:神经科学能告诉我们些什么?》的神经学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表示。“起初,马蒂诺的替代环路或许正是他作为吉他手的音乐灵感所在,而随后也让他得以在颞叶切除手术后得到超乎常人的恢复状态。”
为了拍摄《马蒂诺的精神错乱》,神经科学家欧米基和布罗克斯与马蒂诺共处了数月之久。他们坚信,尽管大脑的修复机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马蒂诺的康复离不开他本身的努力及决心。“相信我,他的康复水平是无与伦比的。”布罗克斯说道。
与马蒂诺的访谈非常有趣。他的回答中有一种镇定自若的禅意,这像他演奏中的独奏一样,透出一种经过刻苦训练后表现出的柔和智慧。在《此地此刻!》中,他把自己手术后的长达19年的痊愈过程比做一种“更高层面的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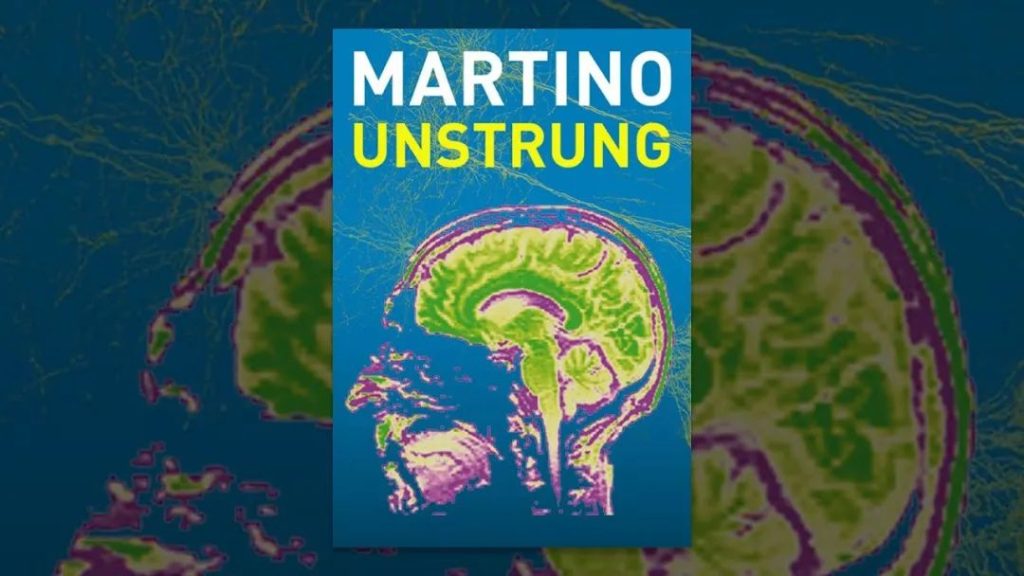
在《马蒂诺的精神错乱》的第二幕中,马蒂诺看向自己的脑成像图。他盯着自己大脑中漆黑的空洞——那一处是他被移除的左侧颞叶。“我觉得这块空洞中曾经住着我的失落、他人的评价以及指责。它们曾让我的人生如此艰难。”他说道,“这些东西也在手术中一并移除了。我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你,这不是什么坏事。”
摄制组随后问道,他的演奏生涯在手术前后有何不同。马蒂诺回答:“在这场神经手术之前,我的事业充斥着爬上更高阶梯、获得他人认可的欲望。我渴望制作出一张满分专辑,我无法面对音乐人的两星评价。而手术之后,这些欲望对我而言不再具有意义。我开始着眼现实,关注当下的感受,尝试享受每一个时刻。我开始关心与我一同工作的演奏者,关心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共同分享的情绪与感受。这些事情比我的成绩更加重要。如今,我享受我全部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评价与成就。”
马蒂诺记忆中的空洞或许将伴随他的一生。记忆专家纳达尔谈道,马蒂诺的告解在失忆失常人群中并不罕见。许多患者在遭受大脑损伤后会面临失忆的困扰,失去回忆过去或畅想未来的能力。他们因而转向重视当下的感受。而今天的马蒂诺也不再在意这类临床诊断。
“创作过程能够带来的最重要、最真实的收获是愉悦感。”马蒂诺说道,“这种愉悦感人人都能看到。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囿于创造的工匠,而是为存在本身而感到愉悦的人。”马蒂诺说,如今,他在演奏时已经无法再感受到手中的吉他。即兴演奏变得更像是一场灵修。“大脑的有趣之处在于,”他表示,“它是运输工具,但它不属于旅途的终点。大脑能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但它终究不是你自己。”
参考文献
1.Galarza, M., et al. Jazz, guitar, and neurosurgery: The Pat Martino case report. World Neurosurgery 81, 651.E1-651.E7 (2014).
2.Duffau, H. Jazz improvisation, creativity, and brain plasticity. World Neurosurgery 81, 508-510 (2014).
3.Knox, I. Martino Unstrung: A Brain Mystery Sixteen Films, London (2008).
4.Martino, P., with Milkowski, B. Here and Now! The Autobiography of Pat Martino Backbeat Books, Montclair, NJ (2011).
5.James, W.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NY (1890).
6.Cajal, S.R.y., et al. Texture of the Nervous System of Man and Vertebrates Springer, New York, NY (2002).
7.Limb, C.J. & Braun, A.R. Neural substrates of spontaneous musical performance: an FMRI study of jazz improvisation. PLoS One 3, e1679 (2008).
8.Tomaino, C.M. Creativity and improvisation as therapeutic tools within music therap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303, 84-86 (2013).
9.Omigie, D. & Samson, S. A protective effect of musical expertise on cognitive outcome following brain damage? Neuropsychology Review 24, 445-460 (2014).
作者:Brian Gallagher | 封面:Kingsley
译者:Xhaiden、山鸡;校对:阿莫東森;编辑:山鸡
原文:https://nautil.us/issue/20/creativity/brain-damage-saved-his-mu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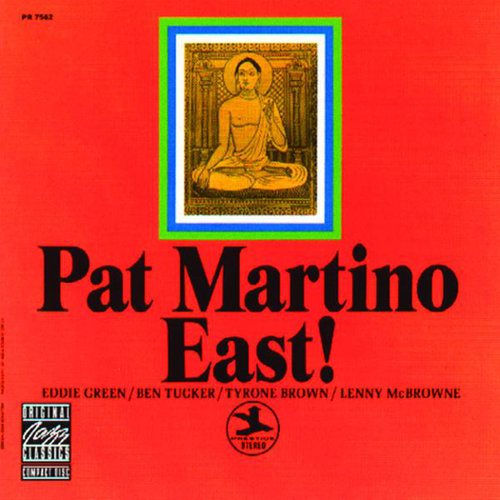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