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介绍
从神学到科学,从假想到实验,沉舟侧畔千帆已过,人们追逐心智圣杯的旅程未有停歇。随着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寻踪者或已洞察到一个简约的回答——还原论。但将心智活动与人类行为还原成神经活动,能否为数千年的探寻划上句点?为此,在这个“神经漫谈”的专栏,我们想邀你一起见证神经科学带来的心智奇迹,去寻觅那探索之途的每一步重大突破。我们希望在千万联结的星辰中,你能瞥见那些意料之外的东西,或许那便是答案。
如果你觉得,心理学是研究心智规律的科学,我们可以从中导出确定的教学项目、计划和方法,并立即运用于课堂,那么我要说,你错了,大错特错。心理学是科学,教学是艺术,科学本身永远无法直接产生艺术,这中间必须有一个创造性的心智才能实现。[1,2]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2001
乘“大脑计划”的东风,诸多神经科学词汇潜入课堂——聆听古典音乐有利神经代谢,找到“学习风格”事半功倍,错过学习“关键期”错过一切,激活“左右脑”潜能大开发。在“最强大脑”的舞动下,市场也驱使着家长们参与新一轮起跑线的竞争——“脑波反馈训练”宛如昨日,松果体神话推陈出新。纵然广为传播的近乎是充满漏洞的神经迷思(neuromyths,指对神经科学知识的误解),但“基于脑的学习”或已深入人心。人们会潜移默化地认为那些带有大脑图像或者附有神经科学研究的言论更为科学,[3]他们无不期许神经科学能为学习与教育提供科学且易操作的实践方案,但这份期待或许很快便会落空。
神经科学与教育学的交叉,被称作教育神经科学。就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这门学科主要服务于教育,但与人们的期待不相符的是,这种服务并不是对教育的精细指导,而是希望将生物学与认知科学、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学结合起来,使教育能够更牢固地立足于对学习和教学的研究中。[4]纵览相关文献,教育神经科学不仅远离教育研究的突出问题,亦未将精力集中于神经科学在教育中的应用,而是更多关注对教育神经科学自身前景与误区的反思。[5]这并不是说教育神经科学不关注教学应用,而是该学科从诞生之初便饱受争议,其立足根基摇摇欲坠,被批评得体无完肤。
首先,研究者认为能够指导教育的大部分研究,更多依仗于行为实验,而非神经科学。它们要么如“早期二语学习不影响母语学习”那样,行为数据先行,抛开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神经科学的测量依然成立;要么如“测试效应有利于学习”那样,属于纯行为实验,只是被归结于教育神经科学之下。[6]也就是说,神经科学并没有回应人们对教育神经科学的期许,它总是作为研究证据的补充,被行为数据驱动,而非直接指导教育教学实践。
其次,批评者指出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实验室研究——用孤立的系统检测某一要素对教学的影响。且不论大脑自身便是多系统共同协作,更何况教育所面对的并非简化、可控的温室,而是从个人、教室、学校、国家到文化多因素交织的丛林。诚然,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教育神经科学的分析足以头头是道,但一旦涉及个体层面,这样的分析就将四处碰壁。譬如,“机械重复固然能提高记忆”,但学生的学习动机足以左右学习效果。来自实验室的孤立研究并不总是可靠。
最后,就如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所说,不可能存在任何已为课堂预备好的神经科学知识。[7]毕竟,神经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其目标是描述神经结构及其功能,而教育是一种实践手段,注重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及其评估。这就导致教育神经科学热情洋溢地输出理论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被教师理解和接受。毕竟,即便教师知晓顶内沟在数值处理中的重要作用,也无法将学生的数学成绩提升半分。况且,教育的诸多问题也没法通过神经科学研究直接回答。所以,教师更多地将之视作陈列书架中的杂志,仅供查询参考,然后再凭借自身的理解与经验融入课堂。但不准确的理解及教师对实践的执拗,势必导致神经迷思的诞生,甚至加剧神经迷思的传播。而若涉及大范围的教学设计及其方法的改良,仅凭教师自身的力量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此这般,将学习的神经机制转化为教育实践又何从谈起?
面对这些重磅轰炸,或许有人会发问,教育神经科学真就如此不堪吗?我们究竟是在见证一门新学科的诞生,还是在观看一件“皇帝的新装”?事实上,是审查的视角让我们误解了教育神经科学的作用,也低估了其对教育的影响。如果我们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将教师所用的教育神经科学类比于建筑师所依赖的物理学或者医疗工作者所用的生物学,那我们便会发现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对特定问题的解决是大有裨益的,同时,它也为教育政策与实践提供了独特且严谨的证据。[8]
首先,神经科学在教育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预测中。相比传统的行为测量,通过神经影像技术,可以更灵敏地预测与教育相关的神经变化,反映未来的学习结果。[9]
在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研究中,富美子·霍弗特(Fumiko Hoeft)等人先对25名具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和20名无阅读障碍儿童进行阅读和语言的行为测试,以及功能磁共振成像。在两年半之后,他们再次对这些儿童进行行为测量和神经测量,并考察采取哪些大脑指标或行为变量可以预测儿童的阅读技能的变化。结果表明,行为测量和神经测量确实都能反映具有阅读障碍的儿童阅读能力的变化,但行为变量无法从统计学上预测儿童阅读能力的进步,神经测量则凭借语音处理期间全脑激活模式的多体素模式分析脱颖而出,也揭示出右侧前额叶在改善阅读障碍中的重要作用。[10]
对数学问题的解决而言,神经测量同样大展身手。一项纵向研究对在执行视觉空间工作记忆任务的6至16岁儿童分别做了行为测试(工作记忆、推理和算术能力)和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者希望借此探讨顶叶沟(与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和数字表征相关)的活动是否可以比单独的行为测试带来更多信息,并以此预测这些儿童两年后的算术表现。结果表明,与仅使用行为测量的模型相比,结合了神经影像学和行为数据的模型预测未来数学能力的准确性提高了一倍以上。[11]除此之外,结合行为测量和神经测量,可以很好地解释儿童工作记忆能力的差异,而借由对基底神经节、丘脑结构和活动的测量,还可以推断他们工作记忆能力的发展。[12]
随着机器学习的引入,神经测量也变得愈发精确,展现出远超行为测量的优势。如通过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对听力受损儿童植入人工耳蜗后的言语发展做出预测,发现在不受听觉剥夺影响的大脑区域,产生了最精确的预测结果,其特异性高达82%。[13]所以,神经测量以其特有的精准性,为临床工具的开发奠定了基础,也为医疗康复提供了依据。而借助这种术前的神经测量及术后的结果预测,也极大地丰富教育神经科学在教育干预中的可操作空间。
其次,虽然来自实验室的教育神经科学不能直接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但它所提供的依据却指导着教育干预和教育实践的开发和改进。
继续以阅读能力为例,丹尼斯·莫尔费斯(Dennis Molfese)等人通过对比新生儿和婴儿的事件相关电位(ERP)波形特征,证明了新生儿可以区分不同的语音变化。[14]其中,新生儿ERP的波形差异能预测他们之后的阅读能力发展情况,并足以揭示未来他们在言语和阅读障碍上所面临的风险。[15]此外,有研究检测了ERP波形发展的变化,为这种差异建立了系统关系。[16]这些研究为早期阅读能力的诊断提供了依据,也督促着教育工作者关注并改善早期儿童阅读能力。
另有研究发现,与正常儿童相比,患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在处理语音任务时,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未被激活。[17]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执行功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表明,针对执行功能和语音识别的干预措施,可能比仅针对语音识别的干预措施能更有效地改善具有阅读障碍的儿童的阅读成绩。随后,借由对阅读过程中神经信号的探究,研究者还发现,服用治疗注意力障碍的药物可以提高具有阅读障碍的学生的阅读能力。[18]这些研究都为儿童阅读能力的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为进一步的教育干预指明了方向。
诚然,上述研究主要针对认知障碍群体,而教育神经科学的主要目标还是普通人,但在脑科学市场的扩张下,教育神经科学对教育的指导,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譬如人脑可塑性的研究为学生的可教育性提供基础,大脑基本结构形成过程中的“敏感期”研究为儿童特定能力与行为的发展提供指导,默认网络的研究为学生日常反思提供建议,早期训练促进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的发展,[19]抑制性控制训练为儿童数学和科学的学习提供帮助[20]……

最后,借由神经科学与教育学“目标”不同、实验室证据难以转化成课堂实践展开的批判,确实直击教育神经科学的要害,但通过神经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沟通,以及教师的亲身研究与实践,这种沟壑并非不可逾越,尽管它需要经历漫长的人才培养过程。
要想让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神经科学与教育学之间进行迁移,需要神经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默契沟通与合作。[21]只有将研究成果转化成非专业人员也能听懂的语言,这种沟通才能有效。但正因为双方缺乏沟通,甚至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最终导致了神经迷思及所谓“基于脑”的教育产品洪水泛滥。同样,只有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或政策改良,这种合作才能形成闭环,但无论是高昂的试错成本,还是教育政策的限制,都让这种教育实践的尝试举步维艰。
就神经迷思而言,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拥有大脑知识量的多少与识别神经迷思的能力成正相关,[22]现实情况却是,那些具有一部分神经科学知识(参加过认知神经科学入门课程)的人,确实能在知识层面得到较高的分数,但他们同样会像外行一样被神经科学的解释所愚弄,甚至热衷于将错误的神经科学发现应用于教学之中。而只有神经科学专家(攻读或拥有认知神经科学或相关领域学位的人)才能正确识别待检验的或是被误解的神经科学发现。[23]为破解神经迷思,这对教师的“神经科学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庆幸的是,来自医学界的丰富经验或许能为教育神经科学的转化带来生机。教育与医学遵循着同样的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方法,但问题在于,每一所医学院都有其附属医院,其中的医学研究者和临床实践者共同开展研究与合作,产出了诸多有用的知识和实践方法,并培养出新一代研究者和实践者。然而,虽然部分师范学院也存在附属学校,但向附属学校输送的仍然是教学工作者,而非研究者。况且,大部分教育附属学校并不会给量化的实验方法提供太多空间。毕竟,这些花里胡哨的实验在短期内并不能给学习成绩及其学生行为带来收益,反而会直接阻碍现有的教育进度。故而,与医学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医生经常发表关于临床实践的研究相比,在教育领域,很少有从业者的研究发表在期刊上或得到传播。[24]因此,培养教育神经科学的技术人员,创建研究型学校,让教师具备“神经科学素养”,让神经科学家具备“教育素养”,于神经迷思的破解和教育神经科学的转化具有诸多意义。[25]
对教师进行的系列培训实验也证实了该举措的合理性。研究表明,当教师接受过个人、群体和系统层面的心理测量培训后,他们能够很好地转化神经科学的发现,并衡量教学变革的可能。[26]理查德·丘奇斯(Richard Churches)等人最近的研究也证明,教师可以以神经科学为基础假设设立随机对照试验和重复实验,在学校环境中展开研究,这足以为其实践提供强有力的证据。[27]所以,当教育工作者与科研工作者相辅相成,甚至合二为一,实验室证据在课堂实践的转化便有了扎实的保障。
综上,教育神经科学在成立初期确实存在诸多漏洞,但随着该学科日益成熟,对它的诸多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化解。当教育工作者开始审慎接受神经科学发现,并与神经科学家积极展开合作,教育神经科学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教育神经科学的教育也能像医学实践般山花烂漫。
注释
[1] JAMES W. 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 and to students on some of life’s ideals[M]. Mineola, NY, US: Dover Publications, 2001: 146.
[2] 周加仙. 教育神经科学的是与非/教育神经科学与国民素质提升系列丛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0.
[3] MCCABE D P, CASTEL A D. Seeing is believing: The effect of brain images on judgments of scientific reasoning[J/OL]. Cognition, 2008, 107(1): 343-352.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07.07.017.
[4] FISCHER K W, GOSWAMI U, GEAKE J, et al.. The Future of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J/OL]. Mind, Brain, and Education, 2010, 4(2): 68-80. https://doi.org/10.1111/j.1751-228X.2010.01086.x.
[5] BRUER J T. Where Is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J/OL].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 2016, 1: 2377616115618036. https://doi.org/10.1177/2377616115618036.
[6] BOWERS J S. The practical and principled problems with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J/OL].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6, 123(5): 600-612. https://doi.org/10.1037/rev0000025.
[7] JONES P H. Introducing Neuroeducational Research: Neuro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Brain from Contexts to Practice[M/OL]. London: Routledge, 2009.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867303.
[8] 周加仙. 教育神经科学的使命与未来/教育神经科学与国民素质提升系列丛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6.
[9] GABRIELI J D E, GHOSH S S, WHITFIELD-GABRIELI S. Prediction as a humanitarian and pragmatic contribution from human cognitive neuroscience[J/OL]. Neuron, 2015, 85(1): 11-26. https://doi.org/10.1016/j.neuron.2014.10.047.
[10] HOEFT F, MCCANDLISS B D, BLACK J M, et al.. Neural systems predicting long-term outcome in dyslexia[J/O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108(1): 361-366. https://doi.org/10.1073/pnas.1008950108.
[11] DUMONTHEIL I, KLINGBERG T. Brain activity during a visuospatial working memory task predicts arithmetical performance 2 years later[J/OL]. Cerebral Cortex (New York, N.Y.: 1991), 2012, 22(5): 1078-1085. https://doi.org/10.1093/cercor/bhr175.
[12] ULLMAN H, ALMEIDA R, KLINGBERG T. Structural Maturation and Brain Activity Predict Future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during Childhood Development[J/OL].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4, 34(5): 1592-1598.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0842-13.2014.
[13] Feng Gangyi., Erin M., HTTPS://ORCID.ORG/0000-0002-5498-2543,TINA, et al.. Neural preservation underlies speech improvement from auditory deprivation in young cochlear implant recipients[J/O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115(5): E1022-E1031. https://doi.org/10.1073/pnas.1717603115.
[14] MOLFESE D, MOLFESE V. Electrophysiological indices of auditory discrimination in newborn infants: The bases for predicting later language development?*[J/OL]. 1985. https://doi.org/10.1016/S0163-6383(85)80006-0.
[15] MOLFESE D L. Predicting Dyslexia at 8 Years of Age Using Neonatal Brain Responses[J/OL]. Brain and Language, 2000, 72(3): 238-245. https://doi.org/10.1006/brln.2000.2287.
[16] ESPY K A, MOLFESE D L, MOLFESE V I, et al.. Development of Auditor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in Young Children and Relations to Word-Level Reading Abilities at Age 8 Years[J]. Annals of dyslexia, 2004, 54(1): 9-38.
[17] KOVELMAN I, NORTON E S, CHRISTODOULOU J A, et al.. Brain basis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for spoken language in children and its disruption in dyslexia[J/OL]. Cerebral Cortex (New York, N.Y.: 1991), 2012, 22(4): 754-764. https://doi.org/10.1093/cercor/bhr094.
[18] SHAYWITZ S E, SHAYWITZ B A. Paying attention to reading: The neurobiology of reading and dyslexia[J/OL].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08, 20(4): 1329-1349.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8000631.
[19] HOLMBOE K, JOHNSON M H. Educating executive attention[J/O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5, 102(41): 14479-14480. https://doi.org/10.1073/pnas.0507522102.
[20] MARESCHAL D. The neuroscience of conceptual learning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J/OL].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2016, 10: 114-118. https://doi.org/10.1016/j.cobeha.2016.06.001.
[21] PICKERING S J, HOWARD-JONES P. Educators’ Views on the Role of Neuroscience in Education: Findings From a Study of UK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J/OL]. Mind, Brain, and Education, 2007, 1(3): 109-113. https://doi.org/10.1111/j.1751-228X.2007.00011.x.
[22] HOWARD-JONES P A, FRANEY L, MASHMOUSHI R, et al.. The neuroscience literacy of trainee teachers[C]//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2009: 1-39.
[23] DEKKER S, LEE N, HOWARD-JONES P, et al.. Neuromyths in Education: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Misconceptions among Teachers[J/O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2, 3[2022-02-12].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10.3389/fpsyg.2012.00429.
[24] CHURCHES R, DOMMETT E J, DEVONSHIRE I M, et al.. Translating Laboratory Evidence into Classroom Practice with Teacher-L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A Perspective and Meta-Analysis[J/OL]. Mind, Brain, and Education, 2020, 14(3): 292-302. https://doi.org/10.1111/mbe.12243.
[25] ANSARI D, COCH D, DE SMEDT B. Connecting Education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Where will the journey take us?[J/OL].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1, 43(1): 37-42. https://doi.org/10.1111/j.1469-5812.2010.00705.x.
[26] WILCOX G, MORETT L M, HAWES Z, et al.. Why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 Needs Educational and School Psychology to Effectively Translate Neuroscience to Educational Practice[J/O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1[2022-04-20].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10.3389/fpsyg.2020.618449.
[27] CHURCHES R, DOMMETT E J, DEVONSHIRE I M, et al.. Translating Laboratory Evidence into Classroom Practice with Teacher-L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A Perspective and Meta-Analysis[J/OL]. Mind, Brain, and Education, 2020, 14(3): 292-302. https://doi.org/10.1111/mbe.12243.
作者:光影 | 封面:kiki | 排版:光影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73期:https://mp.weixin.qq.com/s/bgAEtk5YKAlQRL43vsJSk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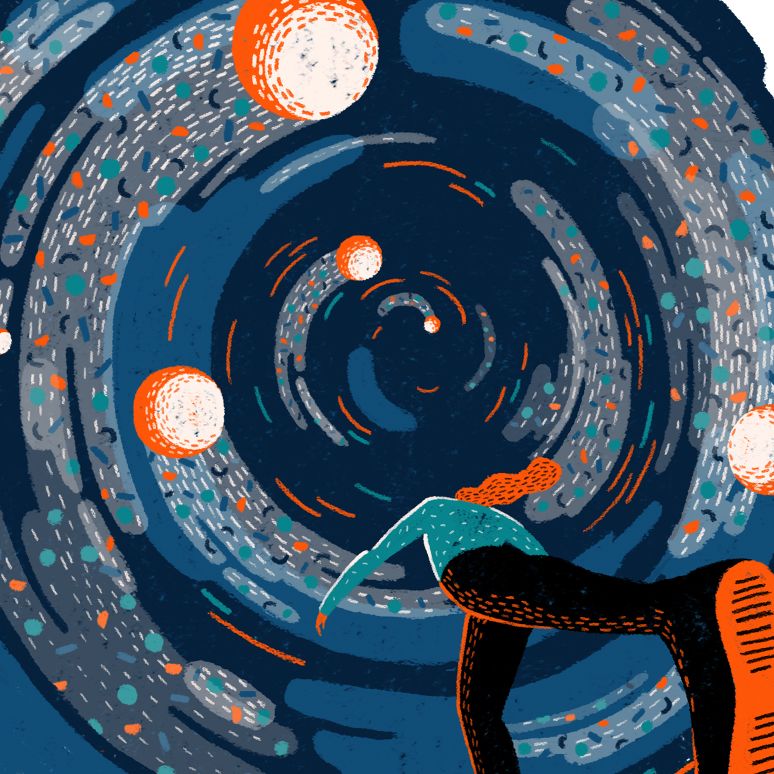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