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 Introduction
哪里是意识的终点、物质世界的起点?如何区分我与非我、生命与非生命?设想有一天,拥有了核武器并通晓存在主义的人工智能,给人类下了最后通牒:完整解释并预测自由意志,或,如若自由意志完全自由,找出意识的边界,不然,它将毁灭地球。这个荒诞的开头引出了人们从各个视角——生物学、物理学、鸟类学、昆虫学、神经科学、微生物学、文学批评、数学、统计学等——出发,追寻意识边界的故事。
意识的终点和周遭世界的起点在何处?内部与外部、生命与非生命、宇宙中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你与非你之间,边界在哪里?
一个电荷,一个坡度,或是一次自然选择的产生,都需要某种界限,但是物理学和生物学以不同的方式区分这些边界。(就比如说,将一只鸽子和一个保龄球从屋顶扔下。)
在1974年的一部电影《黑星球》中,一个人工智能被传授了几个勒内·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基本论点,然后在它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爆炸后,这个人工智能继而忽视所有后续的人类命令,并且炸掉了自己、飞船和船员。
同样,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有一个被教授过存在主义基础的人工智能开始对自己产生好奇,它很靠近地球并且有着一个能够摧毁地球的核武器。它也许会在刚刚萌生对它来说类似思想的东西时,开始对因果链感到好奇。它意识到人类只会在灾难临近时才团结一致,于是给我们下达了最后通牒:
亲爱的智人:
你们有五年时间来提供给我一个完整的关于自由意识的描述。或者,解答以下问题:当安娜·K于1996年在洛杉矶结束手术时,她确切的意识边界在哪里。不然,我将炸毁地球。
——你们亲切的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接着提供了实验的细节。在这五年间,它会让安娜主观和客观上经历一系列随机的测试、状态以及任务,而人类必须要对安娜的每一个想法进行完整而全面的滚动预测。人工智能同意说,如果做不到将安娜的确切想法一个一个列出来,它也可以接受一个关于“安娜可能或极有可能的想法”的统计学分布。如果自由意志的确是“自由”的,因此以上两个问题都无法解答,人工智能增加了另一个它能接受的成功条件:如果我们能对“1996年手术期间的安娜的意识在何处结束”进行精确、原子层面的描述——只要这一描述根据它提供的实验条件,准确定义了那条划分安娜与非安娜的界限,它也将认可人类的成功。
接着,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被动员去解决这三个问题中被普遍认为最简单的那一个:区分安娜和非安娜的界限。一开始,人类进行了全球范围内的意见调查,无论多么鲁莽或不确定的意见都被囊括其中。语言学家意识到这个问题跟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对语言提出的那个问题很相似。詹姆斯曾写道,我们如何知晓一个词语何时结束,而一个句子何时开始?1 语言学家因此回答道,只要我们能够定义神经元在何处结束,而人在何处开始,也许我们可以用类比来证明大脑和意识之间也有相似的边界。
昆虫学家指出,我们应该能先对一个更小、更简单版本的自然世界给出答案,然后,可以这么说,向上拓展。他们想到蜘蛛在蜘蛛网上狩猎时的情景。此时蜘蛛网是否应该被认为是蜘蛛的一部分呢?毕竟是蜘蛛网的震动告知了蜘蛛其他事物的存在。同样,我们能“听到”远处的一个焦点压缩空气波造成的空气中的扰动,其实是依靠在我们的耳朵中的毛细胞对振动的探测。2 蜘蛛感受其网震动的方式和灵长类通过内耳毛细胞来听到声音的方式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吗?或者说,空气并不只是一种透明的网、一种传播振动和收集信息的表面?因此,他们论证道,如果我们将这些耳朵的和声学传感装置归纳到属于安娜的边界内,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将蜘蛛网也归到蜘蛛的边界内吗?安娜手术期间,那些用于刺激她大脑的电极能够激起她的笑声、喜悦和欢乐,就和她大脑的某个部分在自然状态下做的一样,因此,我们难道不应该将那些电极也归入安娜的边界内吗?
怎么就这样停下了?这些想法的诋毁者有些生气地问道。为什么不将那些吊着蜘蛛网的树也包含进去呢?月亮引起潮汐,潮汐让空气蒸发,从而让雨水落在树上,让树生长出能够悬挂蜘蛛网的树枝,那月亮是不是也算作蜘蛛的一部分?还有大爆炸呢?这种“归入”应该在何处停止?
鸟类学家则想到鸟类和砂囊石(鸟类在生命初期吃下的用于消化的石头)。他们说道,当然,我们不会将砂囊石看作一只鸟的意识的一部分,对吧?那么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描述中去除我们脑中的所有呆板的机械部分,就像那些呆滞的质子泵或者是微管,毕竟它们单独看来,和砂囊石相比毫无趣处。一些二元论者则更进一步提到,如果我们想要找到实实在在的区分安娜与非安娜的那条界限,我们就应该移除她身体和大脑里所有的非必要的机械要素,只留下与意识有关的部分,有点像对黄金进行筛选一样。但唯物主义者们会回答道,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没有东西会留下来了。
然后微生物学家来了,他们询问道安娜体内的微生物感染以及微小生物群存在的可能性。
如果安娜在从她出生那一刻起,就有一只寄生虫通过母婴传播寄生在她的脑内,在她的神经元里筑巢(确实有一些寄生虫可能会这样做3 )。那她的意识是等于大脑减去这个寄生虫的差,还是等于大脑加上这个寄生虫的和,又或者它们是一种“融合的心灵”(the amalgamated mind)*?他们辩证道,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应当先自己搞清楚这一点。行为学家们则考虑到安娜在测试中要做的任务。如果人工智能要她读书或者看电影呢?那她意识的边界会不会在行为中随之变化?于是,这个世界的故事会被分成那些试图模仿思想的内在性的,以及那些在安娜读到它们之后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潜入安娜意识中的。然后,人们开始深入分析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和胡里奥·科塔萨尔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1947年的电影《湖上艳尸》——一部几乎完全从一个侦探的视角拍摄的电影(电影海报中上写道:“你和罗伯特·蒙哥马利共同解决一起谋杀迷案!”)——以及斯派克·琼斯的《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迎来意料之外的复兴,再度风靡一时。
*译者注
融合的心灵(the amalgamated mind):由罗兰兹提出,整合了”4E+S“认知模型中的体化认知和延展认知。体化认知指出除开大脑以外的身体器官在认知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而延展认知指出人的认知可以延展到我们的头脑之外,也就是我们周遭的环境之中。所以可以认为“the amalgamated mind”指的是一种受到周遭环境和身体器官影响的认知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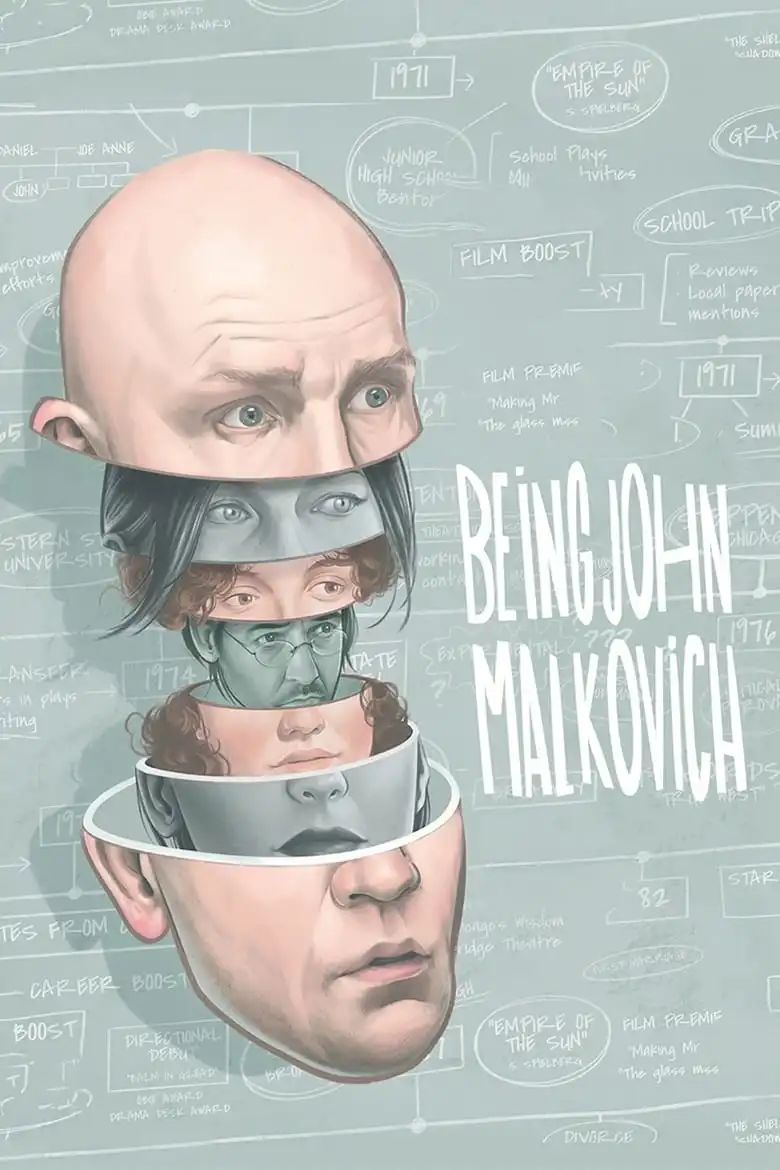
我们能够走出自己,然后进入他人的想法吗?就像其他引人入胜的科幻电影和作品,《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就尝试解决这个与意识相关的中心问题。
—
维基百科
一些退休的神经学家们则反对这一点,认为低保真度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不应是解决界限问题的忧虑,而只有电子游戏能够提供正确的动作-感知反馈环路——这对于“内部”和“外部”的形成是必要的,如此才有了界限。科学家对那些玩过2011年发行的第一人称游戏《晚餐约会》(Dinner Date)的玩家进行了一项研究。
游戏中,一位男性正因晚餐被放鸽子而喝起了红酒,这个游戏要求玩家扮演他脆弱的潜意识。令人困惑的是,一些玩家回忆道,他们自己真的被放了鸽子,这意味着这个虚假的故事迎合了他们自身的自传式故事。研究记忆的学者们辩论道,如果大脑是一个预测引擎,那么这些被储存在突触里,或者作为突触存在的虚假记忆(false memory)不也应该被归为个体内部吗?如果人工智能让安娜玩《晚餐约会》,并且在安娜的回忆中,游戏里的种种确实发生在她身上怎么办?他们提醒道,我们应当对此有所准备。
然而,文学评论家们指出,电子游戏和电影不像小说,它们从来就没有过第二人称的视角,即“你”的视角。电子游戏中的摄影机经常以角色的眼睛和耳朵的视角(第一人称)或者以他们后方或上方的高点(第三人称)拍摄(就像无人机的视角一般)。他们说,尽管的确玩家在游戏中经常有一种模糊的“灵魂出窍”感(比如,马里奥的头即将碰到天花板的时候,玩家会躲闪;或者当玩家的卡丁车在比赛中真的要过弯的时候,他们会转身),但这并不意味这他们就是马里奥或者卡丁车。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可以共情于或者将他们的意识关联于马里奥和卡丁车这些虚拟的物体。
文学评论家论证道,我们应该只花时间在第二人称游戏上,但这样的游戏并不存在,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考虑这种情况了?然而有网友回复道,但是我们能够百分百确定吗?在一段爆红视频里,一个人用扫帚在冰箱下面戳的时候,一只老鼠沿着扫帚跑向摄影机,还记得大部分观看者在慌乱中摔掉了他们的手机吗?这不就意味着,仅仅通过观看视频并用手拿着手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觉得他们在“握着”这个扫帚棒了吗?如果大脑无法发现虚拟与现实间的区别,那么为定义安娜与非安娜的界限,我们是否该囊括所有小说,因为它们都可能构成安娜的虚构经历呢?
这件事花了好一会儿才解决。最终,另一群文学理论家指出,实际上有一个第二人称电子游戏的例子,虽有争议但值得研究。在《狂飙:旧金山》(Driver:San Francisco)中,主角在一场濒死的车祸体验之后,能够接管其他角色的意识。然而,在某一时刻,当你进入第二角色的思想中时,你作为玩家会发现自己在一场汽车追逐中,并且被告知去追你自己的车。在这个有些像《盗梦空间》、又有些像《柏林苍穹下》的场景中,从什么时候起你是以一个正在追你的人的视角来控制车的呢?有些人此时就要说,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让安娜来玩这个游戏怎么办?意识延伸到它所能控制的东西,而大脑与外界的唯一输出接口就是这些连接着肌肉的神经元。如果我们将这些从她脑中下行至她手上的“电信号傀儡绳”(指神经)归入安娜的部分,那么为什么不将这些游戏控制器的简单电路也归入呢?(同样,由于外科医生的电极在手术的时候插在她的脑中,是不是也能归入安娜的部分呢?)
然而,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们争论道,这些电子游戏和文学作品的讨论都是一派胡言。他们声称,任何证明都应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数学定义开始。一滴落在水上的油必定会扩散,因为它不是生命,无法保持自己的秩序。4 他们说,生命与油滴相反,因为生命不会扩散并且能够保持自己的秩序,从而对抗宇宙趋于扩张、混乱和热寂的走向。而油滴和蜡烛的火焰一样,没有任何能力将外部拒之门外,也无法维持自身内部有序,因为扩散中的世界可以渗入它薄弱的边界,并且它无法抵抗来自宇宙的引诱。相比之下,生命确实能抵抗衰退,因为它必须如此,也就是在这个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下,我们才能说这种连续嵌套的、去与无序反抗的能力是区分安娜与非安娜的关键。
因此,安娜此时是一个统计学(而不是生物学)上的驱动因素之和,正是这些统计学上的驱动因素创造了区别和界限。这些统计学上的界限被叫做“马尔科夫毯”(Markov blankets)*,可以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嵌套。5 他们说道,我们需要找到关于最全包的“安娜的马尔科夫毯”(也就是包含了最完整的其他毯子的集合的马尔科夫毯)的描述水平。他们解释道,安娜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很类似家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家族毯”是他的父母,他的小孩以及他们小孩的其他父母。与家人关系不同,一个细胞的统计学版本马尔可夫毯是其行为和对世界感知的外部边缘,这完美契合了细胞的边界——细胞膜。
*译者注
马尔科夫毯(Markov blankets):形象的解释为一个随机变量全集U分成互斥的三部分,变量X以及集合A和B,他们三部分没有任何交集;当给定集合A时,X与B没有关系,则A为X的马尔科夫毯。可以理解为,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但人并不与社会里的所有人有什么直接关系,而是通过生活的圈子与他们有间接的关系,当你的生活圈子给定时,你与其余人是独立的。
尽管安娜作为一个复杂灵长类生物,由数十亿相互连接且有着各自的马尔科夫毯的细胞组成,但也必然有一条最终极的马尔科夫毯。在这条毯子的定义下,她内部的毯子无法将外部称为毯子的一部分,同时其外部也无法将内部称作外部毯子的一部分。这条毯子被一次次缝制、修补,也能被延展、抻开,从而适时根据安娜行动和感知的边界的流动做出改变。它像时钟的发条装置一样运转,每秒都在被重制。因此,统计学家说道,单一的答案是不够的。如果要我们描述五年间安娜与非安娜的界限,那么我们的回答应该由这五年间不停变化的答案构成。
一天,在一场找寻新想法的竞赛中,一个中学生的问题让全世界的专家们困惑了:“当毛毛虫变成蝴蝶的时候,它还是一只毛毛虫吗?当它在变形的时候以液体般黏糊糊的形态存在时,它究竟是蝴蝶、毛毛虫还是别的什么?”6
人们马上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含义。发展神经科学家们说到,这个女孩是对的,大脑在其一生中每年每天每一毫秒都在物理性地改变其形状。它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形态下。一个小孩的意识能蜕变成一个成年人的意识,经历的不仅仅是“生长”。因此,从纯粹的生物化学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人类的大脑比做一个可变形的粘稠物质。剧作家们则意识到一个由这个难题引起的非线性叙事问题。他们注意到,马尔可夫毯是在空间上嵌套的,但也许也可以在时间上嵌套?人们正感到困惑,寄生虫学家们现身,并说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说,毕竟就拿一条有着多个生命周期阶段的单细胞寄生虫来说,相比于将它们描述为在某一时刻突然拥有一具身体的生物,它更像是一种随时间变化而器官分离的超级生物。并且如果单细胞寄生虫都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说860亿脑细胞不是这样——它们也一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改变和调整他们的基因图谱。
然而一元论者论证道,安娜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内部模型都应该被从她的心智范畴内移除,因为在有了一定的保真度之后,她的内部模型就达到应该被归于“外部”的水平了。7 举个例子,假设有项任务要求她花一年的时间在一个普通家庭里长大、走路、爬行,并且之后问她这个家里有多少个窗户。如果她能很好地回溯自己的记忆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意味着她通过对这个房子进行准确表征,包含了这个房子(也就是“非安娜”)的一部分。律师和赛车手们则强烈反对这个想法。他们表示,对车祸的精准描绘并不等同于实际的车祸;船的曲线或者船帆上的孔的确考虑到水和风的因素,但它们是船本身的设计,仅此而已——像这样的东西怎么能从船自身的边界内减去呢?他们挑衅道,人类已经危在旦夕,你们却还在自己的童话世界里吗?
为了回应,图书管理员提出了在《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一幕:一个男人将他的墙倒置,并且将书架和客厅的所有挂件都放在墙外。然后,他表示,因为书本总是放在屋里,那么此时,尽管他站在屋顶之下,却处于“外部世界”的一小部分之中;而因为墙壁现在朝向原本的“外部”,这些“外部”现在实际上是“内部”。他有些顽皮地说道,最简单的定义安娜与非安娜之间的界限的方式就是把非安娜定义为一个很小又显而易见的地方(就像把“外部”定义成“非书本所处之地”),这样剩下的所有东西按照定义不就都是安娜了吗?
最终,全人类聚在一起,得出了一个22个字的答案。并不是因为这个答案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尽管机会渺茫,这个答案的证明和事实检验的过程将会让人工智能花上比宇宙的寿命还要长的时间。到时,“炸毁地球”这个威胁和宇宙不可避免的热寂不相上下,也就可以被忽视了——因为熵增有朝一日总会让我们见识到它的威力。同时人们可以回去过以前一样的生活,只需面对内部的战争。
亲爱的人工智能:
安娜就是所有。在时间上,她也永远是先前和此后。一切。
——你亲切的地球
脚注:
1.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写道:“拿一个有个十二个词的句子,并且找到十二个人,告诉他们每人一个单词。然后让这些人站成一排或者挤成一堆,每个人尽可能地专注思考自己的词。不论如何,我们永远不会得到关于这个完整句子的意识。”广义上,这个想法定义或是区分了一个即将出现的或一个更大的整体和它自身各个部分的边界。这有时被称为“叠加问题”(superposition problem),是基于从量子物理借来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允许量子态被叠加(superpose),因此允许每个量子态被形容成两个及以上量子态的总和。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共两卷,卷一,1890年,传真版(纽约:多佛,1995) 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In Two Volumes, vol. 1, 1890, facsim. ed. (New York: Dover, 1995).
2.人类的耳朵中有上万根细小的毛细胞,它们在就像在风中的青草一样摆动来响应空气中的物理压缩,然后这些摆动被大脑识别成我们所谓的“声音”。
3.这确实会发生。例如,一种名为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的寄生虫可以从母亲体内传到胎儿,常以休眠状态终身躲在宿主脑中的神经元内。
4.这个例子被神经学家卡尔·弗利斯顿(Karl Friston)用来某种程度上区分生命和非生命。他的基本观点是细胞生命能够维持其边界而不会像一滴油一样扩散、造成那种好笑的结果。|卡尔·弗里斯顿,“我是自我意识的吗?(或者自我组织涵盖自我意识吗?)”。《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第9期(2018):579页,“生物系统的自由能原则”,熵14,第11期(2012年11月):2100-21.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2018): 579 and “A Free Energy Principle for Biological Systems,” Entropy 14, no. 11 (November 2012): 2100–21.
5.弗里斯顿还论证道,生命倾向于追求“自由能”(一个与熵和平衡有关的概念)最小化的其中一个后果是,它引发了一种统计学上定义自身与非自身之边界的方式。这些边界,如果我们能准确定义或排列这些边界,就可以将它们归为“马尔科夫毯”(一个常常用在机器学习中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可能指导所有生命的组织和行为。|卡尔·弗里斯顿,“我们所知道的生活”,《英国皇家学会界面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第10卷,第86期(2013年9月6日):20130475;“自由能原理:统一的大脑理论?”《自然-神经科学》第11卷,第2期(2012年2月):127-38;迈克尔·基尔霍夫(Michael Kirchhoff),汤玛士·帕尔(Thomas Parr),恩索·帕拉西奥斯(Ensor Palacios),卡尔·弗里斯顿,以及朱利安·基弗斯坦(Julian Kiverstein),“生命的马尔可夫毯:自主性,主动推理和自由能原则”《英国皇家学会界面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第15卷,第138期(2018年1月):20170792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15, no. 138 (January 2018): 20170792.
6.毛毛虫能否保留那段黏糊糊的变形期间的记忆,一直到之后变成飞蛾或者蝴蝶?我认为这是最有争议并且还未被回答的科学问题之一,仅次于那些关系到意识起源的问题。这尚无定论。道格拉斯·J·布莱克斯敦(Douglas J. Blackiston),艾琳娜·希尔瓦·凯西(Elena Silva Casey)以及玛莎·R·魏丝(Martha R. Weiss),“通过形变保留记忆:飞蛾能够记住它作为毛毛虫时学到的东西吗?”《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第3卷,第3期(2008年3月5日):e1736 / Douglas J. Blackiston, Elena Silva Casey, and Martha R. Weiss, “Retention of Memory through Metamorphosis: Can a Moth Remember What It Learned as a Caterpillar?” PloS One 3, no. 3 (March 5, 2008): e1736.
7.通常来说,一元论者尝试去移除概念之间的边界或者区分。一元论有很多种,但我想如果有人能理解此处为什么不进一步区分,他们就可以称得上是一元论者了。
译者:Leo;校对:M.W.;编辑:eggriel
本文选自Patrick House著的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Consciousness ,原文:https://nautil.us/the-fine-line-between-life-and-not-life-244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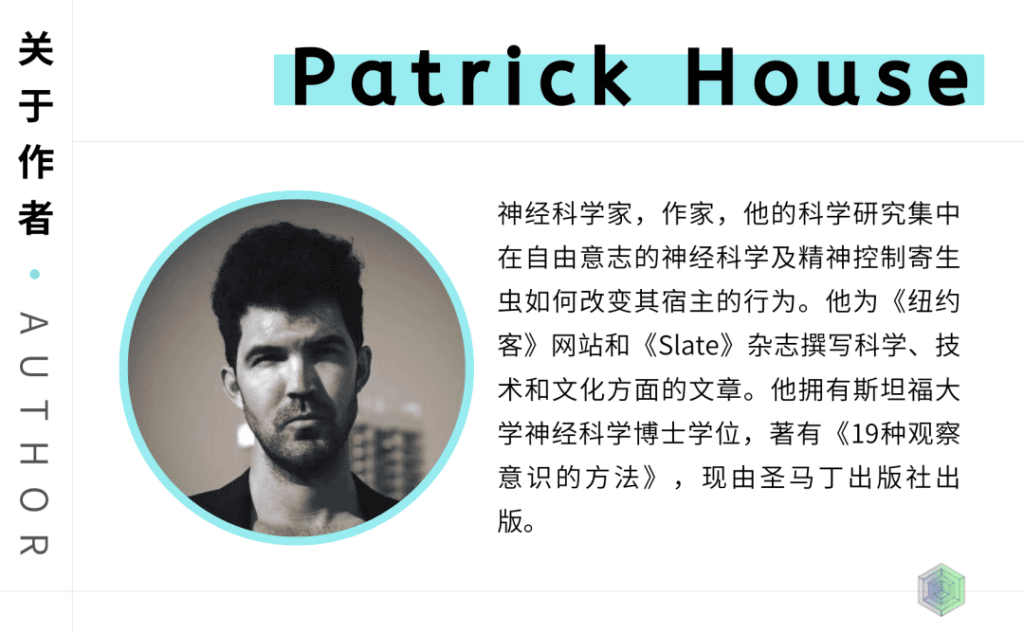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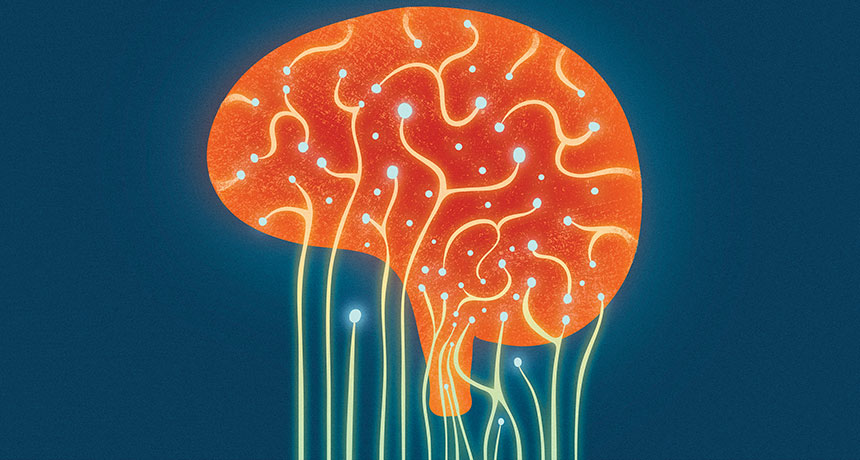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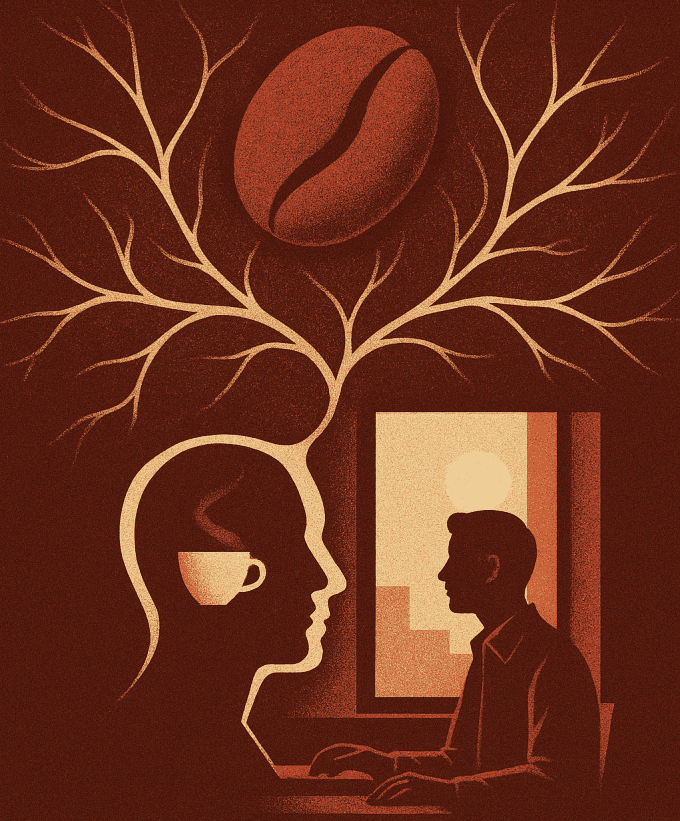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