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尽皆知,小朋友们爱问为什么。
有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可爱又深刻——“为什么月亮叫月亮?”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就很年轻,长大就很老,而不是生下来就很老,然后慢慢长得年轻?”
有的时候,他们的为什么也会变得烦人——
“宝宝,你晚餐不能只吃小饼干。”
“为什么?”
“因为光吃小饼干对你不好。”
“为什么不好?”
“它含糖太多了,没有营养,对你的身体不好。”
“为什么对我的身体不好?”
“.……别问了,赶快把菜吃了。”
哪怕是最有耐心的大人,有时也会被孩子的无尽问题“逼疯”。
但不管大人是否喜欢,会问“为什么”确实标志着小朋友不断提升的认知能力。
小朋友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会问“为什么”的。在童年期,儿童的提问行为会经历剧烈迅速的变化。在他们刚刚会提问的时候,小朋友们会主要提出与事实有关的问题,像 “那是什么”“这是谁”“她在哪里”等等(Bloom, Merkin, & Wootten, 1982)。但是,像“为什么”这样寻求解释的问题,会在小朋友两岁前后问的问题中迅速占据上风。一项经典的日记研究中,就有心理学家发现,在第二年末,小朋友们提出的每四个问题里,就有一个是寻求解释的“为什么”(Chouinard, 2007)。
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解释对于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
曾有研究发现,当小朋友在探索一项新奇的任务时,如果有大人在一旁提供解释,那他们也就更容易理解任务的精髓。相反,那些没有听到解释的小朋友们,对于任务的理解可能就会机械、更浮于表面 (Fender & Crowley, 2007)。
更有趣的是,不仅提供解释可以帮助小朋友们更好地理解,让小朋友们自己解释一件事,同样也对他们的学习效果有所帮助。在另外一项实验中,小朋友们需要理解一个新玩具的工作原理。一组小朋友需要解释一下这个新玩具如何工作,而另外一组则只需要简单的观察即可。研究结果发现,被要求提供解释的小朋友们,更容易记住玩具中的因果属性,像哪个部分会导致另一部分移动这样的工作原理。而且,相比那些没有解释的小朋友们来说,这些小朋友也更善于根据之前观察的玩具,来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玩具(Legare & Lombrozo, 2014)。也就是说,解释可以让小朋友们更好地将学习到的知识,泛化(generalize)应用到新的例子上面。
解释对于认知发展的作用,贯穿整个童年。它与孩子们的好奇心、探索行为以及科学思维的发展都息息相关(Legare, 2014)。
解释与高潮
解释的重要意义,绝不仅仅体现在小朋友们身上。
对于大人来说,我们也很难想象解释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席。我们永远都有太多的“为什么”想知道——我们想知道电梯的运行原理,想知道为什么新冠病毒这么致命,想知道为什么超市卖的猪肉价格越来越高;而当买到可乐时,轻轻吸一口,我们又会想知道:“啊,快乐水为什么会这么好喝?!”
我们想要解释,想知道为什么——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一方面来说,解释具有很高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这个世界,也能帮我们将理解更好地应用到实际操作当中去(Lombrozo, 2011)。
这就像实验中需要理解新玩具工作原理的小朋友们一样。那些需要提供“解释”的小朋友,能够更有效地抓住玩具花里胡哨的表层之下,更重要的因果结构,也能更好地将学习到的因果结构迁移到新玩具身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知道一件事或现象背后的原理也好处无穷。还拿“可乐为什么好喝”这个问题来说,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快乐水好喝背后的解释,我们也就有可能在家自制快乐水,不用破产也能天天快乐。这些解释能够带来的附加价值,都是促使我们追寻解释的原因之一。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解释是否也有内在价值呢?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抛出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时,似乎并不总是为了满足什么目的才这样做的。很多时候,对于解释的追寻都自然而然。我们不需要刻意地去计算它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这似乎在提示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抛开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好喝的可乐之后,解释本身,也具有一定驱使我们去追求它的价值。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与哲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曾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类比:从某种角度来说,解释和性高潮非常相似。两者的相似性不仅仅是达成时的那种现象学的快感,同时,从进化论的角度,两者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我的假说是,解释之于认知,就如高潮之于繁殖”。高普尼克在这篇发表于期刊《心灵与机器》(Minds and Machines)上的论文中,这样写道:“从我们的现象学视角来说,看上去好像是我们为了获得解释而构建并应用理论,为了获得高潮而发生性行为。但是,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这个关系恰好相反。我们之所以有高潮和解释的体验,正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造宝宝、造理论。”(Gopnik, 1998)。
当然,高普尼克也承认,这样的假说目前仅仅是假说。寻求解释、获得解释所伴随的情绪反应与生理反应,仍是鲜有人踏足的研究领域。她猜想,寻求解释的驱动力可能与蔡格尼克记忆效应(Zeigarnik effect)有关(Gopnik, 2000)。这种效应是指,相比较于已经完成的事情,人们往往能够更好地记住未完成的事情。另外,社会心理学常常研究的“了结需要”(Need For Closure)——对于问题答案的渴求、对于模糊性的回避——可能也与解释的驱动力紧密相连。近些年来,还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顿悟时刻(aha moment)的神经关联。他们发现,人们恍然大悟的时刻,往往伴随着下皮质多巴胺能奖赏系统(subcortical dopaminergic reward network)的激活(Tik et al., 2018)。但这样的发现也不过是一个开端。解释与高潮之间的类比究竟是否能经受得起科学证据的考验,答案仍在未来。
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因果关系错综复杂。而解释最终带来的快感,也不断地激励着我们进行费力费时的推理与思考,构建理论、探索并掌握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解释让我们更好地掌握事物背后的原理,更好地将学习到的规律迁移到新的事物上去,因此,也就能让我们更好地适应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
知其所以然
但什么样的解释才能算得上是好解释呢?
无论老少,人们都被各种各样的动机驱使着,热衷于询问“为什么”。当我们一头雾水、缓缓吐出这三个字时,那些能让我们满意的答案究竟有什么共同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科学哲学家就开始讨论对解释的规范性需求。在进入主题前,请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已知天气预报说今天有30%的降雨概率,你觉得为什么今天可能会下雨?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天气预报公布的降雨概率大于零,所以今天有可能要下雨。这个解释你满意吗?
如果你的回答是“满意”,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很有可能和你站在同一边。亨普尔是20世纪中叶科学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提倡将人类知识基于严密的数理逻辑之上。在“什么称得上科学解释”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在具备某些初始条件和至少一条“法则”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能够推导出某种结论——即“待解释项”(explanandum)——这些前提便构成对待解释项的解释。具体来说,法则既可以是普遍概括的,也可以是统计归纳的。在上述天气预报的例子中,一个统计归纳的法则(天气预报很有可能是准的)加上一个初始条件(天气预报称今天有30%的降雨概率)足以通过逻辑推导出待解释项(今天可能会下雨)。对亨普尔而言,解释就是优美而严谨的逻辑推理,具有类定则(lawlike)的性质。
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是驱使我们问“为什么”的一种规范性需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针对事实产生的“如果…”的想象。比如,如果天气预报说今天有0%(而不是30%)的机率下雨,我们大概没有理由认为天上会掉一滴水下来,毕竟我们默认天气预报是准的。亨普尔式的解释的确支持这种反事实思维,因此他的理论在50、60年代的科学哲学界里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是如果你对上面的解释不甚满意,你也绝不是一个人。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韦斯利·萨尔蒙(Wesley Salmon)就完全没有买亨普尔的帐。萨尔蒙指出,虽然天气预报和实际降雨与否之间有相关性(correlation),没有人会觉得天气预报导致了降雨。也就是说,天气预报和实际降雨与否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causation)。所以,使用类定则的解释理论只支持预测,而不见得是真正的解释。在萨尔蒙看来,科学解释的根基正在于因果关系——例如,冷暖气流交汇导致降雨,也同时大概率导致了天气预报的预测。
萨尔蒙更敏锐地察觉到,亨普尔所主张的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解释可以通过倒推的手段说明过去发生的事,但这往往不是人们想要的答案。他提出,当人们问出“为什么”,他们实际寻求的信息遵循着一种特定的、心照不宣的时间顺序:从时间上更早的信息到相对较晚的。然而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解释可以让时光“倒流”,用时间上靠后的信息去“解释”过去,而这种说明是违反我们对于“解释”的直觉的。当我们默认解释应当符合因果顺序时,亨普尔的解释理论的异样更不言而喻。
萨尔蒙的解释理论依然能够支持反事实推理。更重要的是,与相关性纯粹的类定则性质不同,萨尔蒙强调了因果关系的实在论(realism)价值。实在论强调真实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我们的感知、信念等。虽然我们的观测往往有偏差(比如天气预报不是100%准确),但是能追溯到真正的诱因(比如气流情况)。在萨尔蒙看来,正是因果关系使得我们的主观认知能够用于归纳客观真实。科学哲学界现在普遍认为,因果关系是回答“为什么”的核心。
当机器拥有好奇心
在科学哲学的辩论场之外,关于“为什么要问为什么”的理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自文明伊始,我们便探寻着对于世间万物、何为真理的解释。随着AI机器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解释的意义更是变得史无前例地丰富。一方面,我们好奇为什么机器是有用的;另一方面,机器可能有类似人类的好奇心吗?
其实你可能已经无意之间回答过机器人的“为什么”了:你在自己的今日头条主页上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无聊的文章。作为今日头条的用户,你知道,即使每天都用它来搜寻自己爱看的内容,它也的确向你推荐了不少有趣的视频,你们之间偶尔还是有一些“误解”:比如,你不过是搜索了一个关键词,它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荐包含同一关键词的其它文章,即使你只是出于一时好奇。你点了右下角的“x”。今日头条弹出了一个新的浮窗——“请选择不感兴趣的原因”——以及几个选项,包括“内容质量差”和“不喜欢”。你犹豫地选了“不喜欢”。刷新页面后,另一个类似的无聊文章出现了。
为什么机器会问“为什么”?
从计算和学习的角度,知道“为什么”能够帮助机器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来最大地优化学习效果,尤其是缺乏相关信息的情况。例如,通过捕捉用户对某一话题的兴趣和他的浏览记录之间的因果关系,机器实际上可以实现小样本学习(few-shot learning),甚至是一次学习(one-shot learning)和零次学习(zero-shot learning):只需要非常少的“不喜欢”,它就会意识到用户对某种特定的内容没有兴趣(而不是对质量感到不满意)。
但是目前的机器主要依赖于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这个区别是不是似曾相识?)。也就是说,它们主要依靠挖掘数据集中的统计规律性,从而建立用户的观看记录和兴趣之间的关系。某些意义上,这种方式更具有灵活性(各种数据集都适用),但它同时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资源,才能弥补缺乏先验知识(prior knowledge)的弊端,即对现实世界常识的无知。当数据本身不足以支持精准的学习(比如你的视频喜好),机器便不得不另求“补丁”——比如今日头条非常天真的“为什么”,通过人为介入改进结果。但这种零散的“补丁”很难被归纳、推广,所以你还是会看到其它无趣的帖文。
现代因果关系框架之父、图灵奖获得者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长久以来坚定地认为,机器必须要会辨别、树立关于世界的因果模型,AI才称得上成功,我们也才算真正理解人类智慧的本质。另一位图灵奖获得者——约书亚·本希奥(Yoshua Bengio)也对设计拥有因果意识的机器兴趣盎然。在两人最近的一次线上交流中,珀尔质疑依赖相关性的AI几乎不可能达到媲美人类的学习能力。
面对这样的问题,约书亚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疑问:科学家当然对世界的因果关系有良好的结构性理解,可是婴儿和大猩猩也是如此吗?他们难道不需要依赖信息中的统计规律性,从相关性出发,逐渐习得因果关系吗?
再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和机器看似都从单纯相关性的学习开始,我们为什么需要担心机器问不出“为什么”?
“不。”珀尔回应说,“即使接触到同样的外界刺激,婴儿对世界形成的认知也必将异于大猩猩。”他指出,对各种“为什么”的好奇给予了我们一种与生俱来的“样板”,形成了我们对世界理解的重要基础。而正是这种简洁却强大的样板使得人类在学习和拓展知识版图方面具备特殊优势,将我们与其它动物和机器区分开来。
目前看起来,珀尔的话得到了印证。机器学习研究者开始尝试教机器探索数据所包含的因果联系,提问“为什么”。为了用同样的数据量达到接近人类的学习成果,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将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规则手动写进模型,让机器认识到世界模型的一些特性,正如婴儿与生俱来的常识。要创造可与人类综合学习能力抗衡的机器、探究人类智慧的本质,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已然发现一丝光亮。
追问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问题,可以无限地问下去。
问为什么的人,自然也会问“为什么人这么爱问为什么?”“为什么人这么爱问‘为什么人这么爱问为什么’?”“为什么人这么爱问为什么人这么爱问‘为什么人这么爱问为什么’”?。
而对每一个“为什么”的解答,也都同样可以延伸出无限的为什么:“为什么人这么爱问为什么?”“因为获得解释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获得解释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因为解释可以让我们更加关注事物背后的因果机制。”“为什么解释可以……”
如果一个人愿意,她可以将一生都花在对单独一个问题的追问之中。但这样的做法并不一定能最大化所能获得的知识。当这样递归式的追问积累到一定长度时,我们所能获得答案的意义,也会愈加薄弱。这就好像曾有人这样戏谑地谈论神话故事中“地球是停在巨龟背上”的观点——如果地球是停在巨龟背上,巨龟停在哪呢?巨龟停在另一只巨龟的背上,那另一只巨龟停在哪呢?那当然是另一只巨龟上面。一层叠一层,不见尽头。而“这底下都是乌龟”(turtles all the way down)这种说法,也成为了一句经典的表达,一语道破这种拥有无限回归结构命题的缺陷所在。
但从另一角度来说,也许很多时候,蓬勃的好奇心与无意义的追问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意义,可人并不能永远都准确无误地预判出问题是否有意义。一个孩子天真的提问,若能得到悉心地解答,或许就会成为一条求知之路的起点;而我们如果能对生活中的无心之问,都报以热忱与真诚去解答,这也注定会带我们走进新的风景。这就好像风靡全球的漫画《Wait But Why》系列总能让人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又收获颇丰一样:它准确地击中了蛰伏在我们心底的好奇心、对解释的渴望。这没准就是在提示我们,也许我们时不时都需要像漫画中的那个火柴棍小人一样,停下来,喊一句:“等等,这是为什么呀?”
参考文献
- Bloom, L., Merkin, S., & Wootten, J. (1982). ” Wh”-Questions: Linguistic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Sequence of Acquisition. Child development, 1084-1092.
- Chouinard, M. M. (2007). Children’s questions: A mechanism for cognitive development.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i-129.
- Dasgupta, I., Wang, J.X., Chiappa, S., Mitrovic, J., Ortega, P.A., Raposo, D., Hughes, E., Battaglia, P.W., Botvinick, M.M., & Kurth-Nelson, Z. (2019). Causal Reasoning from Meta-reinforcement Learning. ArXiv, abs/1901.08162.
- Fender, J. G., & Crowley, K. (2007). How parent explanation changes what children learn from everyday scientific thinking.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3), 189-210.
- Gopnik, A. (1998). Explanation as orgasm. Minds and machines, 8(1), 101-118.
- Gopnik, A. (2000). Explanation as orgasm and the drive for causal knowledge: The function, evolution, 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theory formation system.
- Legare, C. H. (2014). The contributions of explanation and exploration to children’s scientific reasoning.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8(2), 101-106.
- Legare, C. H., & Lombrozo, T. (2014). Selective effects of explanation on learning during early childhoo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26, 198-212.
- Lombrozo, T. (2011).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f explanations. Philosophy Compass, 6(8), 539-551.
- Pearl, J. (2020, July 26). Radical Empiricism and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Causal Analysi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http://causality.cs.ucla.edu/blog/index.php/2020/07/26/radical-empiricism-and-machine-learning-research/
- Ronfard, S., Zambrana, I. M., Hermansen, T. K., & Kelemen, D. (2018). Question-asking in childhoo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its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Review, 49, 101-120
- Salmon, W. (1978). Why Ask, “Why?”? An Inquiry concerning Scientific Explanation.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51(6), 683-705. doi:10.2307/3129654
- Tik, M., Sladky, R., Luft, C. D. B., Willinger, D., Hoffmann, A., Banissy, M. J., … & Windischberger, C. (2018). Ultra‐high‐field fMRI insights on insight: Neural correlates of the Aha!‐moment. Human brain mapping, 39(8), 3241-3252.
作者:曹安洁,amecolli|
封面:由阿石为神经现实提供(未经授权禁止使用和传播)
编辑:E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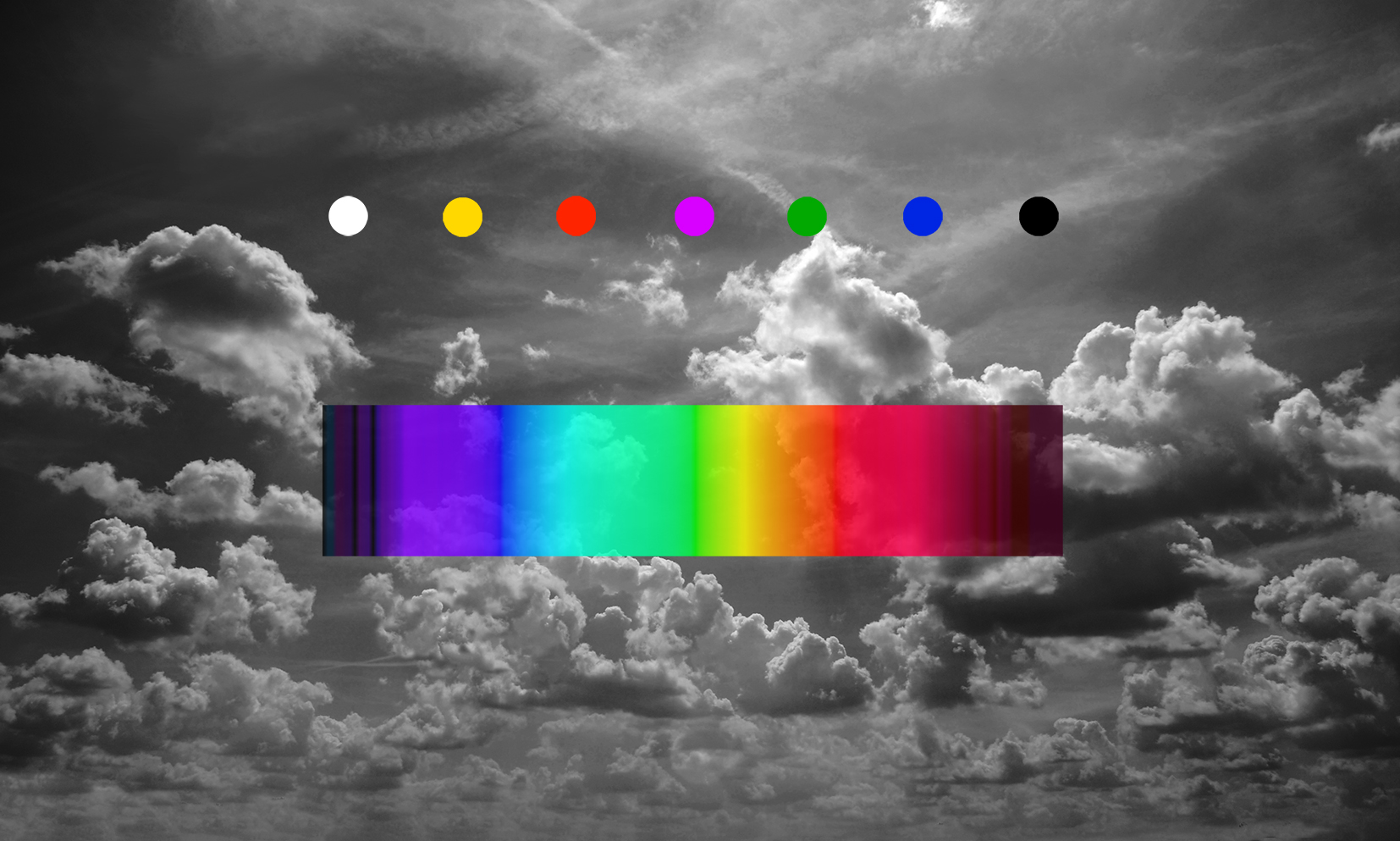






这篇文章对于“为什么”的解释让我体会到了高潮的爽感,有胜于高潮过后的满足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