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平时挺聪明的人一谈政治就开始自说自话,全然不顾别人在说什么。当人们争论人类是否拥有自由意志时,也有这种自说自话的倾向。神经科学家兼自由意志怀疑论者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三番两次扬言要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这位为自由意志辩护的哲学家决斗,还曾邀请他做客自己的播客,希望来一次伟大思想的碰撞。然而,一眨眼又变成了鸡同鸭讲。
克里斯蒂安·李斯特(Christian List)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哲学家,他的专长领域是人类决策。他的新书《自由意志为何是真实的》(Why Free Will Is Real)就试图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李斯特同宇宙学家西恩·卡罗尔(Sean Carroll)和哲学家婕南·伊斯梅尔(Jenann Ismael)一样,属于最新生代的思想家;他们消解了自由意志问题上的长久对立,并认为只要我们深入理解物理学,就会发现它与自由意志不矛盾。
怀疑论者将自由意志定义为真正的的自由选择权,李斯特接受这一定义,也承认这看似与基础物理学与神经生物学视角下的机械论宇宙观相左。但他指出基础物理学与神经生物学不是人类行为的全部。你或许是一堆被机械法则主宰的原子,但你不是一堆随意摆放的原子。你这堆原子构造精妙,而你的行为不只取决于主宰单个原子的法则,更取决于这堆原子的组合方式。在一个更高的描述层级上,你的确可以拥有如假包换的决定权。真的是你说了算。
利斯特认为怀疑论者没有领会这个关键点,因为他们轻信于关于因果的脆弱直觉。他们在基本的物理定律中寻找我们行为的原因,然而按照计算机科学家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等人发展的广义因果理论,我们在底层根本找不到因果概念。因果是一个更高层级的概念。珀尔等人的理论能完全兼容如下观点:人类及其他主体是这个世界中的因果力。李斯特的书或许不能平息这场争论——都吵了几千年了,我们早就死心了——但它至少会迫使怀疑论者在论证时成熟一些。
这些问题并不抽象。它们是司法系统以及我们日常的褒贬判断的基石所在。如果不假设我们是自己的抉择的主人,我们甚至无法合理地思考人类。然而,假设自由意志存在的实践需求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论据。
本月初,李斯特在伦敦的办公室里与我通话,刚聊了几句,我就忍不住暗叹:好想上他的哲学课啊。他循序渐进地把问题讲得明明白白,也不像很多哲学家那样满口晦涩的术语,或者掉到某个深不见底的话题里出不来了。

这本书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你很客观地呈现了你想要反驳的观点。我很遗憾很多学者做不到这一点。人们是如何论证自由意志不存在的?
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认为,首先,自由意志需要满足某种或某些属性:意向性的、目标导向的能动性(intentional, goal-directed agency);备择可能(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也就是说我必须有可能做另一件事;或我们对于行为的因果控制。然后,怀疑论者称在这个世界的基本物理特征中,我们找不到这些属性。不同的怀疑论者所关注的属性有所不同。
比如说,帕崔莎·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和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等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相较在认知和心理层面上诉诸直白的心灵状态、目标、意向等去理解人类行为,我们应该在更低的描述层级上将人类行为理解为大脑中生物物理过程的产物。人类有一种很强的倾向,将意向归属于各种现象,如天气、自然灾害或河流。这一切已成为过去。随着脑科学的进步,我们甚至可以把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种说法完全抛弃,不再将它归属于人类。
第二种论证思路是,倘若正如我们最好的一些物理理论所暗示的那样——宇宙符合决定论,那么根本不存在备择可能。决定论(Determinism)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确定了宇宙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全部状态,那么只有一条未来状态的轨迹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确定了大爆炸或紧随其后的某个时刻的世界状态,自那以后的整个事件序列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确定了。比如当你在一家小餐馆问自己,“我喝咖啡还是茶呢?”,你将作出的选择其实早已刻在了宇宙的初始状态中。
第三种论证是,当我拿起水杯以图喝水时,这一行为并不是我意向性的心灵状态(intentional mental state)导致的。事实上,它是由大脑中某种深层次的、下意识的、亚意向的(sub-intentional)物理过程导致的。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发现,有意识地决定按下按钮并不是肇始物理过程的因果序列的开端,某种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大脑活动模式在那之前就产生了;他认为这个实验挑战了自由意志。
这些论证的确很有说服力。一种应对方式是弱化自由意志的概念,使之不再必须具备之前提到的某种或某些属性。比如说,只要我赞同自己的行为就表明我有自由意志,我本可以做别的不再是必要条件。或者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备择可能。比如说,虽然我无论如何都会选择咖啡而不是茶,但是假设这个世界和现实情况稍有不同,我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但我认为这种策略毫无吸引力。我宁愿大方地承认自由意志需要意向能动性 (intentional agency),需要备择可能让我们从中选择,还需要心灵状态导致行为的因果关系。我的立场是,自由意志的经典驳议犯了个大错,它混淆了不同的描述层级。如果我们在基础物理层级寻找自由意志,那我们彻底找错地方了。
让我们逐个考察这些论证吧。有些人认为,人类拥有目标和意图并据此行动这种想法是前科学时代的遗留,你如何回应他们?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科学研究中,如果你想理解人类行为,意向性归属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大脑层级上根据天文数字般的神经放电模式解释人类行为,这根本行不通,而且毫无意义。
假设我让出租车司机送我去帕丁顿车站。二十五分钟后我就到那了。第二天我让他送我去圣潘克拉斯车站,他就把我送过去了。如果我观察底层的微观物理活动,很难辨认出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共通之处。如果我们转换到意向性的解释模式,就很容易解释司机为什么第一天把我送到帕丁顿车站,而又是什么差异导致他第二天把我送到圣潘克拉斯车站。出租车司机理解我们之间的交流,形成了把我送到某个特定车站的意图,而且有明确的诱因促使他这样做,因为他是靠这个吃饭的。
诉诸神经科学的自由意志怀疑论者说,在基础物理层级不存在意向性的、目标导向的能动性——这点没错。但他们错在认为这种能动性彻底不存在。意向能动性是一种在较高阶层涌现出来的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不真实。一旦我们对于某个现象的最佳科学解释要求我们假设某些实体或属性,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科学实践中把这些假设的实体或属性视为真正真实的。我们在社会和人类环境中观察到了模式和规律性,理解这些模式和规律性的最佳方式就是把意向能动性指派给参与其中的人。
那你如何看待第二种论证,也就是决定论的挑战呢?在我走进小餐馆之前,我会点什么早已注定了?
这个世界在根本上是否是决定的尚无定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诠释量子力学——我们姑且假设是的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世界在某些更高的描述层级上也是决定的。心理层级的非决定性为自由意志和备择可能留下了空间。这与基础物理层级的决定性完全不矛盾。
可以联想一下天气预报。气象学家感兴趣的是高层的模式和规律性。事实上,天气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高层概念。在个体气体分子的层级上,没有天气这种东西。或许在那个非常精细的描述层级上,系统的确会遵循经典物理定律,严格按照决定论运转,可是当你攀升到宏观描述,你就不再考虑那些微观细节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太无知,而是解释实践需要我们聚焦最显著的规律性。
当你考察宏观天气状态,你会发现系统不是决定的,而是随机的(stochastic)。我们可以把概率运用到很多情境中,但无论如何,现在的天气状态并不完全决定未来几天的天气状态。好多条不同的轨迹都是完全可能的。
同理,当我们描述一个作为能动主体的人的全部状态时,我们描述的不是大脑和身体中每一个基本粒子的完整微观状态,否则就搞错描述层级了。如果我们关于人类施动能力最好的理论迫使我们假设,一个人能够选择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那我们就有很好的科学理由认为备择可能是真实的。如果你分别问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或经济学家,人类是如何做出选择的,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回答你。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将人类视为面对着不同选项的能动主体,所以这些理论都假设备择可能的存在。
等等,我不确定人类层级的非决定性是不是好事。我希望我的决定是经由我深思熟虑的,而不是随机的产物。
这个问题很麻烦。非决定性有好几种形式。统计物理学的非决定性与随机性(randomness)有关。但是在社会科学中,人们所说的非决定性基于选项可得性(option availability)。在决策理论中,我们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等标准,将施动者可能(could)选择的选项和事实上将会(will)选择的选项区分开来。如果我是个理性的人,我就会尽可能系统地做出与我的信念、偏好和目标相符的选择。但其他可能性不会就此消失。它们一直向我开放着,直到我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我发现你的种种论述都隐含了一个共同主旨,那就是我们应该严肃对待科学理论的果实——而且是所有的科学理论。如果物理学说微观世界是决定的,那我们就应该接受,至少暂时接受这一点;如果将来出现更好的理论还可以再改变。如果心理学说人们有如假包换的选择,那我们也应该接受。
没错。如果你一边承认,底层物理世界是决定的(根据我们最好的基础物理学理论),一边又否认天气系统是非决定的(根据我们最好的气象学理论),那你就有点双标的嫌疑。鉴于高层科学中最好的理论已有充分的实证支持,我们有很好的科学理由去认真地对待它们,就和我们对待基础物理学理论那样。
接下来谈谈第三种论证吧,我们到底能不能因果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即使你满意我对第一个挑战的回应,认为人类的确是意向性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施动者,你依然可能怀疑我们的目标是否起到因果作用。我们需要定义一下我们所说的因果。从神经科学出发的自由意志驳议经常诉诸因果概念,然而这些驳议往往不确切言明其中因果的涵义。
在科学实践中,我们寻找那些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依然稳固的系统相关性,并认为这就是因果关系。人们在统计学、计算机科学、概率论和心灵哲学等领域建立因果模型时,往往就将这种科学方法融入他们的因果观。这种进路叫做因果的干预理论。说某个特定变量导致了另一个,其实是在说如果我们通过改变第一个变量的值加以干预,第二个变量就会发生相应变化。
假如我现在形成了移动手臂拿起这个杯子喝水的意图。我们该把什么看作移动手臂这一行为的原因?我的意向性心灵状态,更具体地说是我喝水的意图,与我的行为有着系统性的紧密关联。如果我的心灵状态改变了,它导致的行为也会改变。而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个底层物理状态中的改变或差异都会带来行为的改变。
我相当推崇知名哲学家金在权(Jaegwon Kim)的工作;他向心灵因果提出了一项严峻挑战,即著名的因果排斥论证(the causal exclusion argument)。如果你找到了某个原因,它能彻底解释某个特定的结果,那你就不应该同时假设另一个不同的原因也导致了那个结果。否则你就犯了过度归因(causal overattribution)的错误。让我们再次假设,我为了喝水而举起手臂。你只要援引我脑中的物理状态就可以彻底解释我的行为,你没有理由再假设一个原因———一个与之不同的心灵原因。
彼得·孟齐斯(Peter Menzies)和我对此的回应是,如果我们接受因果的干预理论,因果排斥论证就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在任意给定系统中,最具系统性的因果关系或不涉及最低层级的变量,却可能涉及较高层级的变量,当然,也有可能在两个层级上都存在系统性因果关系。
我借用一下出租车的比喻,看看我有没有听懂。假设你有两个开关。一个是简单的两值开关:帕丁顿车站或圣潘克拉斯车站。第二个开关是指针式的,你得仔细调节来设定目的地。你可以让它指向帕丁顿,但是稍稍用力过猛就变成圣潘克拉斯了,再调一下又变成帕丁顿了———这个开关很敏感。两值开关这种方式更便于高效地控制结果。寻找心灵原因而不是原子层级的原因,也是类似的道理?
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你对自由意志的理解,机器甚至集团公司有自由意志吗?
在和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it)合著的论文中,我论证了有组织的集体本身可以成为有意能动者,这个能动者超越了其中的个体成员。以恰当方式组织成的商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团体性能动者的认知能力和你、我这些个人不一样,但我们依然可以说它们有某种形式的自由意志。
AI系统也是类似的情况。虽然目前的AI系统是否足够先进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但并不存在什么概念上的理由,能够让我们否认成熟的AI系统可以成为自由意志的承载者。就像我们认为集团能动者应该因其行动受到责难,AI系统在其理想情况下也应该体现出某种形式的道德能动性,而不是僵化地逐利或追求其另外的客观功能。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在高风险情境中使用AI系统,我们希望这些系统能够做出符合我们伦理观的决定。
翻译:有耳;审校:Jon-Lou;编辑:EON
Yes, Determinists, There Is Free Will
You make choices even if your atoms don’t.
自由撰稿人,科学作家和编辑,《科学美国人》和《Nautilus》的特约编辑。著有《The Complete Idiot’s Guide to String Theory》和《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为《科学》、《自然》、《Aeon》、《Nautilus》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撰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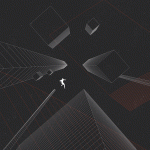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