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麻醉时仍然有意识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们往往认为麻醉状态与睡眠一样。但事实远比我们想的要匪夷所思——它更像是先拆散你的意识,再拼凑起来。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名妇女去医院接受癌症手术,手术很成功,所有的癌灶都被切除了。然而几个星期后,她感到有些不对劲。她回到外科医生那里,外科医生让她放心癌症已经消失了;她又去咨询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
然而这一切无济于事——她越来越确信自己命不久矣。她重新见了外科医生,医生再次安慰她“一切都很好”时,她忽然脱口而出:“黑色的东西!你没有得到黑色的东西!”
医生目瞪口呆,因为他还记得在手术期间,他曾无意向同事抱怨自己浴室里难以清除的黑色霉菌。癌灶在这名妇女的腹部,手术期间她处于全身麻醉状态,尽管如此,医生的话似乎已经留在她脑海里了。当她得知手术中医生的这段对话后,她的焦虑便烟消云散了。
在《麻醉:遗忘的礼物和意识之谜》(Anesthesia: The Gift of Oblivion and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一书中,美国心理学家亨利·贝内特(Henry Bennett)向澳大利亚记者凯特·科尔-亚当斯(Kate Cole-Adams)讲述了这个故事。科尔-亚当斯从麻醉医师和心理学家那里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显然,人们在麻醉状态下仍能听到声音,并且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即使他们自己并不记得。
一名妇女在子宫切除术后经历了可怕的失眠,在后来的催眠治疗中她回想起麻醉医师开玩笑说,她将“陷入死亡般的睡眠”。另一名患者在一个小手术后想自杀,随后她记起,当她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她的外科医生惊叫道:“她很胖,不是吗!”
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科学家给30名即将进行心脏手术的患者戴上耳机,并在手术过程中播放了《鲁滨逊漂流记》的删减版本。患者无一记起这件事,但不久后当被问起“星期五”这个词时,他们马上想到的都是书中的故事。
1985年,贝内特要求接受胆囊或脊柱手术的患者佩戴耳机,他们听到的是贝内特说着:“当我来和你说话时,你就轻摸你的耳朵”;对照组听到的则是手术室里的声音。当患者们见他时,那些听到说话的人触摸耳朵的频率是对照组的三倍。
在还是青少年的时候,科尔-亚当斯就被诊断为脊柱侧弯,她开始害怕未来可能要接受纠正脊柱弯曲的危险手术;到中年时,她的驼背越来越严重,她意识到手术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是为了克服恐惧,她从1999年开始研究麻醉,在近乎二十年的努力后,她写下了对麻醉这片朦胧缥缈的未知领域痴迷、神秘、恐怖、甚至是幻影般的探索。
除了麻醉,这本书还描述了科尔-亚当斯的童年、父母、几段恋爱和各种精神体验和生存危机——一种漂泊不定而又无时不在的组合,注定要唤起被麻醉的心灵。她记录下许多被遗忘的经历和未曾感受过的情绪,疑惑着: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以一种麻醉的状态生活着呢?
麻醉医师描述病人们经历麻醉的几个阶段:从迷失方向,到谵妄,最后进入手术状态。当我们进入麻醉时,他们通过监测脑电波来滴定“麻醉鸡尾酒”,以确保使用的镇静剂不会过多或过少(典型的“鸡尾酒”含有一种止痛药、一种肌松药和一种催眠药。肌松药可以防止手术刀划过时肌肉收缩,早期的肌松药来源于箭毒,是南美洲战士涂在弓箭上用以对抗欧洲人的毒药,而催眠药可以使人失去意识。)但即使麻醉医师能以精湛手法操作麻醉器械,他们对这些药物背后的机制仍然一知半解。
“显然,我们可以开具麻醉药,而且能很好地控制它,”一位医生告诉科尔-亚当斯,“但是在真正的哲学和生理学层面上,我们仍不知道麻醉的机理。”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有意识,这就好像如果你不知道太阳为何升起,就难以解释它为何又会落下。
在科尔-亚当斯试图理解麻醉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寻觅之路上,她了解到一系列异乎寻常、充满暗示,而又不可复制的实验(被澳大利亚麻醉医师凯特·莱斯利(Kate Leslie)称作是“幽灵般的小研究”)。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从1993年开始,英国麻醉医师伊恩·罗素(Ian Russell)在即将接受大型妇科手术的患者前臂上均绑上一根止血带。他配好麻醉鸡尾酒(催眠药咪达唑仑(midazolam)以及止痛药和肌松药),然后收紧止血带防止肌松药进入每个病人的手部和腕部。手术期间,通过头戴式耳机向患者播放一段录音:“如果你能听到我,我希望你张开并合上右手的手指。”如果患者移动了手指,罗素就摘下一只耳机并要求她捏自己的手指;如果她捏了,他便会要求感到疼痛的患者再捏一次。
32个受试者中,有23名捏手指表示自己可以听到,有20名再次捏手指表示自己感到疼痛。尽管罗素本应该对六十名患者进行测试,但他对这些结果感到非常不安,以至于早早结束了试验。他认为,这些女性在手术台上可能既有意识也能感到痛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身麻醉”(general anesthesia)可以被更好地描述为“全身失忆”(general amnesia)。(之后,没有人回忆起听到罗素的声音或捏过他的手指。)
是罗素没有给予充足的麻醉剂吗?(他说他使用的剂量与他在一般手术中使用的一样。)他所察觉的动作是否并非是有意识的?(科尔-亚当斯与罗素一起参加手术,他再次使用了“孤立前臂术”;这一次,当病人抓住他的手指时,他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反射运动”。)可能的是,患者有意识,但只是部分性的——能够捏罗素的手指,但不足以知道自己的名字或者回忆生活点滴。
意识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意识不是一种二元状态,而是渐进的;在麻醉下“有点”意识和“有点”自我是可能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所谓的清醒镇静(conscious sedation)状态下进行结肠镜检查:他们昏昏欲睡,可以与医生沟通,但对后来的手术记忆甚少。如果你不记得那些痛苦,它还算数吗?它发生在“你”身上了吗?也许在手术中“有点”意识也不是那么糟糕。
“无意识的心灵不是虚无的黑海”,而是一个“活跃而积极”的地方;我们可以将麻醉下的心灵想象成一个音乐厅,指挥失踪了,但管弦乐队仍在演奏。
科尔-亚当斯发现,探究麻醉状态下的意识的研究都不尽完美。像罗素那样使用真实患者的研究往往设计得不好,而使用志愿者的研究并不涉及到真正的手术。她写道,在没有手术的情况下探讨麻醉下的意识,“有点像在没有雨的时候测试你的雨刷。”“即使对于已经麻醉的患者,一个手术切口也会有刺激效果,”她解释说,“当手术刀进入时,她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有时还会抽搐。 她可能更接近于有意识。”
当然,另一种方法就是向大量经历手术后的患者询问他们还记得什么。2000年,《柳叶刀》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在瑞典两家医院接受手术的1.2万名患者,研究人员发现了18个他们确信是清醒着的患者。这些病人在术后马上以及之后的不同时间段里接受了测验,有的人术后立刻想起他们的经历,其他人一开始没有记忆,但在一两周后回想起了手术。其中还有一人在术后24天后才想起了详细的手术过程。
我们往往认为麻醉状态与睡眠一样。但科尔-亚当斯总结道,事实远比我们想的要匪夷所思——它更像是先拆散你的意识,再拼凑起来。一名叫乔治·马休尔(George Mashour)的麻醉医师告诉她,“无意识的心灵不是虚无的黑海”,而是一个“活跃而积极”的地方;我们可以将麻醉下的心灵想象成一个音乐厅,指挥失踪了,但管弦乐队仍在演奏。大脑系统仍然运作着,但并不同步。也许是因为每个人的意识退化的程度不同,因此人们在麻醉时会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经历。
墨尔本的一位麻醉医师回忆说,一名患者在搭桥手术过程中发现自己处于清醒状态;尽管这个男人经历了“锯开胸膛”,但他并没有感到疼痛,而且觉得“惊奇而不是惊恐”。(“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家伙,”麻醉医师回忆说。)
另一名医生想起一位从手术中醒来的患者看起来“非常满意”,当被问及她为什么这么高兴时,她说:“你不会相信,但我刚刚经历了半小时的高潮!”
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在“麻醉”这个主题的核心,有一则澳大利亚女性雷切尔·本马约尔( Rachel Benmayor)的故事。
25年前,她在剖腹产时,发现尽管自己的肌肉被麻痹了,却仍然留有感觉。(雷切尔的医生本打算给她全身麻醉。)
起初,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随后她感到痛苦万分,仿佛有一辆卡车在她腹部中间来回驶着。(“当你打开腹腔时,空气冲到没有保护的内脏器官上会产生巨大的压力,”科尔-亚当斯解释说。)
她觉得自己停止了呼吸。(一个呼吸机正在帮她。)只有当她听到医生和丈夫说,“看,你有一个女儿了!”时,她才意识到她在手术过程中都是清醒着的。当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开始恐慌起来,她觉得疼痛和瘫痪会让她发疯。于是她决定试着去“进入”痛苦。
她告诉科尔-亚当斯,她没有逃避这个经历,“我有意识地转过身来,开始感受到疼痛并进入疼痛中,让它把我包围起来。”她感到自己陷入极大的痛苦中 ——然后,突然间,虽然她仍然可以感受到手术的疼痛,但她发现自己在图书馆里。“这种感觉就好像我存在于人类所知道的,以及终将会知道的一切中。”她回忆道。
无论人类是否知道或理解,所有可能被知道或理解的东西都在那里,……它实在太大,太大了,我觉得我被逼到了那里,而我必须活下去。
当她在图书馆时,一个声音告诉了她几条信息:
“生命是呼吸”;
“一切都很重要,一切又都不重要”;
“只有经历痛苦,才能发现真相”;
第四条信息与她的丈夫有关(她没有告诉科尔-亚当斯是什么)。
最后,这个声音告诉她:“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生育。拥有孩子是我们作为人类的首要关注点。” 她说, 即使在手术过程中,她也反对这种想法。然后,她感到外科医生又回到身边将她的刀口缝合。
当她能够再次移动时,她叫来了医生,道出原委,当医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他哭了;她也叫来了丈夫,告诉他那些信息。一时间,她不受控制地颤抖着;过了一会儿,她抱起女儿爱兰歌娜(Allegra)。
她对科尔-亚当斯说:“宝宝的眼中有着一种漆黑的平静,而我只是把她抱在怀里,便觉得她刚从我去过的地方过来。”
读这本书时,你很可能忽视本马约尔的手术发生在1990年。科尔-亚当斯解释说,在那之后,新的医疗协议和监测技术让她这样子的罕见案例更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本书中的许多访谈、研究和轶事都是以主题联想的顺序来呈现的,你必须努力提醒自己:它们是来自上世纪的60年代(奇怪科学的鼎盛时期),还是看起来更可靠的90年代。《麻醉》这本书的内容从19世纪50年代发现乙醚开始,囊括了麻醉剂的简史。但它并不是技术进步的编年史,你也不会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去读它。它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如果麻醉剂是完美的,那我们也无从进一步了解无意识。
一无所知的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这是《麻醉》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尽管“从真正的哲学和生理学角度”,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麻醉的机理,但这并不能阻止麻醉医师每年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麻醉药的改善及其引起的涟漪效应与意识的奥秘无关,例如,改进的肌松药通过“使强大的躯干肌松弛”,可以使外科医生安全接触到重重防护下的胸部和腹部,这也使得全新的、挽救生命的手术成为可能。
然而,尽管麻醉的技术正在明亮的无影灯下改善着,其余的空间还是保持着黑暗。在科尔-亚当斯看来,这就是存在。我们体验、思考、行动和感受颇多 ,却没有完全了解我们是谁,是什么,或者在哪里。在她书中最精彩的一段内容,她描述了自己的一个梦:她正在寻找一条迷路的狗,发现它“在城镇边缘的围栏里”,这是一条美丽的红色塞特猎犬,躺在笼子里。
“当我进去的时候,这个小生物向我抬起头来,我惊讶地发现它的嘴巴被钓鱼线缝了起来,”她写道。“它跳到地面上,蹒跚着走向我,把前腿搭在我的肩膀上,又将头靠着我脖子的左侧。”她知道这只狗想要得救,但不知如何帮它;令她费解的是,她知道狗的名字是Gadget,在梦结束前她把它留在了身后。
对科尔-亚当斯来说,那只嘴巴被缝合的狗狗是“受那些麻醉后仍有意识的人们的困境所唤起”,同时,他们的拥抱意味着“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鸿沟:一个多言、领会、排他;另一个沉默、不懈、包容。”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小Gadget:无意识的、局部的、沉默的自我,而大脑无法感知它。那些自我一直都在意识深处;有时,在麻醉下,它们试图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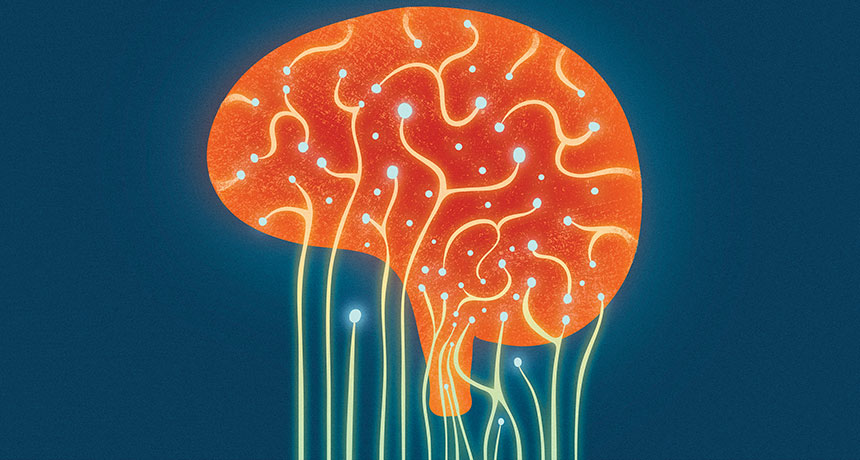

评论